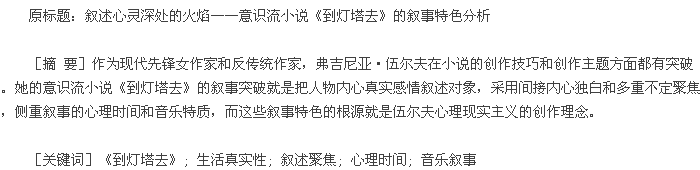
《到灯塔去》是弗吉尼亚·伍尔夫小说创作的巅峰之作。在 20 世纪中期,国内外对这部小说的研究重点是小说的意识流写作技巧[1]和文体学分析[2]。伴随着 20 世纪后期文学理论的新发展,对文本形式的研究和对文本作者的研究转向了对文本内在构成机制的研究,叙事学就是在这个转型之后崛起的新兴文学理论。在 20 世纪 90 年代叙事学已经形成了自己完整的理论并取代经典小说理论成为文学研究所主要关心的一个论题[3]。叙事学理论把小说看作叙事文本中的一个重要次类进行研究,对小说从叙事学的角度进行文本内在机制的分析,可以更加深入的分析作者的创作技巧和帮助读者进行小说阅读。这样的研究视角使小说研究摆脱了结构主义的束缚,也走出了作者与小说关系论证的困扰,而是从小说叙述者的角度出发,研究小说的构建。意识流小说和传统的小说相比,具有独特的叙事学特征。弗吉尼亚·伍尔夫作为现代先锋女作家,她心理现实主义的小说创作理念决定了小说《到灯塔去》在叙述对象,叙述视角,叙述聚焦,叙述时间,叙述方式上都突破传统、独树一帜。
一、叙述心灵的真实感受
不同于传统小说,《到灯塔去》的叙述对象不是事件,而是小说中人物的内心真实情感。从叙事学的角度看,小说叙述的对象是事件,事件依赖的是情节和人物。弗吉尼亚·伍尔夫自始自终认为小说应该把描写和探索人的欲望、情感看作小说家的基本任务。形式和情节是小说家必须重视的因素,而人物在小说艺术中占据核心地位。她认为“无论小说家如何改变小说的场景,如何变动小说各种成分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成分在所有小说中永远不变,即,关于人的成分,小说描写人,人物及其我们的情感,就像现实生活中的人一样。……为了完整的记录生活,小说家应该描写情感的产生和发展,而不是记录事件的冲突和危机。”[4]很显然,伍尔夫这里所指的真实主要是人物内心情感意识的各种矛盾。正如她自己说的小说家要描写“通过大脑传递的闪耀在心灵深处的火焰”[4]。《到灯塔去》的小说情节非常简单,整个故事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窗”,讲述傍晚时分拉姆齐夫人给儿子詹姆士讲故事然后和家人朋友共进晚餐的经过; 第二部分“岁月流逝”,讲述十年后家庭变故和别墅的变化; 第三部分“灯塔”,讲述拉姆齐先生和一双儿女去灯塔的经过。这样的情节,在一般小说中肯定会让人感觉平淡无味,但是弗吉尼亚·伍尔夫却能够把它讲述的跌宕起伏,感人肺腑,就是因为她挖掘的是人物对客观事物的真实感受和人物的内心情感。在小说的第一部“窗”中,拉姆齐夫人看似给儿子讲故事,实际上在感受儿子,感受丈夫,感受身边的每一个宾客。莉丽看似在草坪上作画,实际上在感受拉姆齐夫人,感受拉姆齐先生,感受班克斯先生。班克斯先生也在和莉丽的交谈中不断感受周围的事物和人物。拉姆齐夫人的故事频繁的被她蔓延的思绪所间断,就连对周围环境的描述也是人物感受到的环境,绝对不是对周围客观事物的照相机似的机械描写。拉姆齐夫人看着儿子的脸就开始憧憬儿子美好的未来; 听到塔斯莱谈论天气就回忆起曾经和他一起上街并亲切交流的场景; 詹姆士听到父亲的话,内心的感受是有一把斧子或其他的致命武器他就抓在手里攻击他; 莉丽看窗内的拉姆齐夫人,觉得她拥有无限魅力和需要用五十双眼睛去观察; 就连班克斯先生看到窗内的拉姆齐夫人也浮想联翩,并难以掩饰内心对夫人的仰慕和赞美。弗吉尼亚·伍尔夫正是在小说创作中把人类情感作为对象,才有了扣人心弦的独特效果。
二、间接内心独白
弗吉尼亚·伍尔夫为了把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展现给读者,大胆采用间接内心独白的写作手法。内心独白就是小说中的人物在假设没有听众的情境下,无声无息的任意流露自己的心理和意识。内心独白是意识流小说基本的写作技巧,意识流小说中贯穿了人物自身对过去的回忆,对现在的观察、思索、评价和对未来地想象和预测。翟世镜称内心独白为“内部分析”或“感性印象”,主要强调人物把自己在某一个场景中的思想情绪和主观感受用自言自语的方式直接叙述出来,而且这实际上是一种无声的叙述,一种深思冥想,是一种内心的意识流动[5]。
内心独白可以分为直接内心独白和间接内心独白两种。直接内心独白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和时态,因为没有叙述者的加入和干预,所以对人物的独白不进行加工和解释。这种的独白虽然直接、真实和客观,但是不容易理解,会给读者的阅读带来困难。间接内心独白的叙述视角是第三人称,但是作家并不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来叙述,而是由一位叙述者站在各种人物的立场上来叙述,其叙述的内容也不是作者的思想而是不同人物的观念、思索和感受。因为间接内心独白是通过叙述者间接的展示给读者的,人物的意识活动是经过加工和整理的,而且在叙述中有明显的过渡和提示,例如“拉姆齐夫人想”,“她认为”等,所以间接内心独白更易于理解。
但是,不同于直接内心独白,间接内心独白无法排除叙述者干预。作者不是彻底退出,而是在幕后充当“向导”作用,并且创造出了一个全能的叙述者,不仅给读者讲述事件的经过,又能对人物的内心独白进行不遗余力的评价。叙述者的声音夹杂在人物的心理声音之间,形成了除了人物话语之外的叙述干预[6]。《到灯塔去》中的间接内心独白随处可见: 第一部中拉姆齐夫人对塔斯莱先生的一段回忆就是采用间接内心独白的形式展现给读者的,塔斯莱先生强调明天天气不好,导致詹姆士非常失望,拉姆齐夫人对这个年轻人的厌恶感油然而生; 随后,她开始回忆孩子们对塔斯莱先生的无礼和自己在塔斯莱身上的努力。但这一段回忆不是由拉姆齐夫人用第一人称的口吻陈述给读者而是由一个全知全能的叙述者利用第三人称的口吻进行陈述,虽然从未脱离夫人、孩子们还有塔斯莱先生本人的心理思绪,但是叙述者的事件框架和对事件中人物的描写和评价形成了对拉姆齐夫人回忆的干预。例如“刚吃完饭,孩子们就向小鹿一样溜走了”,“她站在那握着詹姆士的手”,“她要去城里办点事”等是叙述者在给读者讲述事件,而“她的确对所有异性都爱护备至,她自己也说不上来是什么原因”,“孩子们对母亲的严厉态度和极端的谦恭有礼肃然起敬”等是叙述者在对人物进行评价。在小说的第二部中对十年之后拉姆齐家别墅进行的描写就是利用叙述者的视角。“黑暗从钥匙孔中溜进来,绕过百叶窗,钻进了卧室”,“光线探头探脑,挨挨擦擦的来到了楼梯口”,“屋子空了,门上锁了,地毯也卷起来了”等是叙述者对客观景物的感性印象,而“一个夜晚算得了什么,不过是短短的一段时间罢了”和“那幢房子被留下,被遗弃了”是叙述者的评论和干预。从叙事学的角度看,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到灯塔去》这部意识流小说中采用的间接内心独白是对传统叙事学的大胆突破,也是她对人物心理和意识描写的诉求。
三、多重不定聚焦
与弗吉尼亚·伍尔夫的间接内心独白相辅相成的就是这部小说的不定聚焦和多重聚焦。所谓叙述聚焦是指在叙事文本中谁在作为视觉、心理或精神感受的核心,叙述信息是从谁的眼光和心灵传达出来的,文本中所表现出的一切是受谁的眼光“过滤”[7]。由于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到灯塔去》中把挖掘各种人物内心的感受作为重点,并且采用间接内心独白的创作手法,这就决定了聚焦方式的不定性和多重性。弗里德曼认为弗吉尼亚选择的“多重选择性全知视角”决定了小说是“多个中心意识”的聚焦[8]。除了叙述者之外,《到灯塔去》的聚焦对象频繁变动在不同的人物之间。在第一部“窗”中,拉姆齐夫人是一个重要的聚焦对象。虽然贯穿整个部分的是拉姆齐夫人的心理活动: 拉姆齐夫人对着儿子,对着丈夫,对着塔斯莱先生,对自己的孩子们和对莉丽思绪连篇。然而,其中不停被叙述者的讲述和其他人物的心理活动所间断: 塔斯莱先生的心理活动,孩子们的心理活动,莉丽的心理活动,班克斯的心理活动,甚至是有卡迈尔先生的心理活动。把如此多的人物作为聚焦对象,《到灯塔去》这部意识流小说自然在叙述的视角方面高度不确定。然而,伴随这不确定性的人物视角,就出现了另外一个聚焦特征—多重聚焦。多重聚焦就是每次用不同的内在聚焦者的眼光来观察同一个人或物。《到灯塔去》的多重聚焦主要体现在对拉姆齐夫妇的人物塑造中。拉姆齐夫人的人物形象是通过不同人物的心理活动展现给读者的: 拉姆齐夫人认为自己“才五十岁,她本可以把家里一切安排的更好”,“我虚度年华,无所收获”; 年轻的学者塔斯莱认为“她是他生平见过的最美的人”; 莉丽认为“夫人需要用五十双眼睛去观察才足以了解”; 班克斯先生认为“大自然用来塑造她的粘土都是罕见的,夫人的脸庞是希腊神话中赐人以美丽和快乐的三位格雷斯女神,在绿草如茵、长满了长春花的园地里携手合作才塑造出的”。而拉姆齐先生的形象也是通过拉姆齐夫人、塔斯莱先生和莉丽的眼光“过滤”呈现给读者的。拉姆齐夫人认为丈夫“比自己重要的多,大学需要他,人们需要他,他的讲座和着作极其重要”; 而塔斯莱先生认为“拉姆齐先生有八个可爱的儿女,有能干的妻子,虽然没有在年轻时的建树上有新的突破,但算的上是在一个悲剧的世界过着幸福生活的人”; 莉丽认为拉姆齐先生“喜怒无常,脾气暴躁,而且狭隘和盲目,露骨的要求人去捧他,崇拜他”。虽然,不定聚焦和多重聚焦会在阅读中会给读者带来一定的困难,但是叙述者的从中衔接和提示使小说同样具有一气呵成的连贯性。
四、心理时间
任何事件的叙述都离不开时间,《到灯塔去》的一个重要的叙述特色就是心理时间与现实时间的自然交融。哲学家柏格森把人们常识公认的时间观念称为“空间时间”,把它看作各个时刻依次延续的、表现宽度的数量单位。他认为“心理时间”才是“纯粹的时间”、“真正的时间”,它是各个时刻互相渗透,表现强度的质量单位。他认为,我们越是进入意识的深处,“空间时间”的概念就越不适用[5]。由于伍尔夫强调小说家关注的应该是表面现象掩盖下的心理真实,所以她注意到了心理时间与现实时间的落差。伍尔夫曾经这样描述“人们感觉世界里的一小时与钟表时间相比可能被拉长五十、一百倍; 相反,钟表上的一小时在人们的内心世界里也许只有一秒钟。钟表时间与心理时间的不对等关系值得我们去注意。”[9]在《到灯塔去》这部意识流小说中,伍尔夫淡化现实时间,利用心理时间的无限长度和强度,把它任意的拉长和穿插,形成了蒙太奇式的感官效果。这是一部有关时间流逝的小说。故事的情节是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一个普通的英国家庭的一次时隔十年的灯塔之旅。小说第一部是在九月的一个傍晚时分发生在拉姆齐家海滨别墅的故事; 小说的第二部是十年以后别墅的景象; 第三部是十年后的一个早晨,拉姆齐先生和一双儿女去灯塔的经过。从现实时间上讲,小说第一部只有短短的几个小时,第二部人物经历了十年的时间。然而,伍尔夫却在小说的第一部花费了将近二分之一的篇幅,在第二部仅仅用了大约十分之一的篇幅。第二部十年的时间被象征性的压缩在一个夜晚的描绘中,开始时人物准备就寝,结束时,人物重复同样的动作,但是拉姆齐夫人已经与世长辞,普鲁死于难产,安德鲁死于一次大战。与此相反,虽然发生了如此多的事情,这一部分却没有情节,只有叙述者眼里别墅悲凉的景物描写。这种强烈的落差是现实时间与心理时间的强烈对比,也是对心理时间重视的结果。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一部的几个小时里,人物的心理时间被无限拉长。作者给予每个人物充分的展现心理活动的机会: 拉姆齐夫人在这几个小时里先是坐在窗内给儿子詹姆士讲故事,然后是和宾客们共进晚餐。
然而不论是讲故事,还是进晚餐,拉姆齐夫人的思绪都驰骋万里,心中充满了对往事的回忆,对现状的思考和对未来的憧憬。她想象几十年后儿子的庄严事业; 她回忆不久前在餐桌上批评自己的孩子不懂礼貌的情景,回忆自己曾经和塔斯莱先生一起进城办事,她思索丈夫的事业和缺点,考虑敏泰和莉丽的婚姻大事。与此同时,她还在不停的思索自己的过去,现状和困惑。所有这些心理活动涉猎了比现实时间长的多的心理时间,然而他们都被压缩在了几个小时的时间里用人物的心理活动展现出来。所以阅读《到灯塔去》,就好像打开一把时间的扇子,几分种时间被扩展到好几页,很长的时间被压缩、眼前所看到的、所回忆的、所想象的各种情景交织、穿插、汇集起来,彼此交错的呈现在读者面前,取得一种特殊的戏剧化效果。
五、音乐叙事
文学和音乐是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但它们共同的目的是激发人的情感体验。《到灯塔去》的叙事形式有不少与音乐相通的地方。故事的音乐叙事结构,小说意象与音乐主导动机意象吻合的创作特色,语言强烈的节奏感和韵律感,还有风景描写的听觉叙述方式使小说阅读的过程变成了读者的感官盛宴和情感冲击之旅。首先,伍尔夫在《到灯塔去》中借用了音乐的三部( ABA’) 曲式使读者产生与聆听音乐相同的情感体验。第一部“窗”; 第二部“岁月流逝”; 第三部“灯塔”,而这种结构安排与西方音乐中的三部曲式完全吻合。三部曲式的特点是首尾呼应,形成向内的自我封闭结构,A 段是乐曲的第一主题,B 段的第二主题通常与 A 形成鲜明的对比,且A’往往是第一主题的变奏,实际上是第一主题以不同方式的再现,从而达到深化第一主题的目的。《到灯塔去》的第一部“窗”以刻画和展现拉姆齐夫人为主题,是小说的第一主题; 第二部“岁月流逝”讲述十年时间的家庭变故。这一部分结构清晰,内容简单,时间、死亡和寂寞占了上风,它们是小说的第二主题。这一主题与第一部中明快和谐的生活主题形成鲜明的对比。小说的第三部“灯塔”比第一部略短,拉姆齐先生决定登上灯塔,完成夫人生前的愿望,而莉丽在别墅的草坪上重复着同样的事,她在试图完成十年以前未能完成的画。这样的结构安排犹如音乐的乐章自然清新,在对比和匀称的基础上给人以美的享受,这种音乐叙事结构自然是小说冲击读者内心情感的重要原因之一。小说中的象征手法比比皆是,在处理象征中的意象时伍尔夫同样采用音乐的技巧,主导意象从一开始就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后面的屡屡出现都能成功的勾起读者的联想和思考; 作为意识流小说,《到灯塔去》语言虽凌乱但并不晦涩,那是因为伍尔夫注重语言的节奏与韵律,精通长句的处理技巧,擅长频繁使用排比修辞和灵活运用押韵技巧。最后,更重要的是伍尔夫利用声音叙事给读者展示的是一幅幅优美感人的声音风景,唤起的不仅是视觉的,还有听觉体验和共鸣[10]。正是这种音乐叙事技巧与传统叙事技巧的珠联璧合才能使普通读者在阅读中不仅经历一场强烈的感官盛宴和情感冲击,而且开始审视自己的内心世界和思考人生的深刻哲理。
结语
《到灯塔去》是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叙事艺术上进行大胆创新的成功范例。与传统的叙事方式不同的是弗吉尼亚·伍尔夫使用间接内心独白这种意识流创作手法剖析人物内心的真实情感; 成功利用叙述者的干预衔接不同人物的意识流动; 对人物的塑造采用不定聚焦和多重聚焦; 把心理时间无限放大并与现实时间自然融合; 利用音乐的结构、音乐的主导意象、音乐的节奏和声音作为叙事的手段。所有这些叙事策略的使用都是弗吉尼亚·伍尔夫主观真实性的创作理念的要求,也进一步证实她心理现实主义的文学信仰。
[参考文献]
[1] 李森. 评弗吉尼亚·伍尔夫《到灯塔去》的意识流技巧[J]. 外国文学评论,2000,( 1) : 62 -68.
[2] 赵秀风. 意识的隐喻表征和合成———意识流小说《到灯塔去》的认知文体学分析[J]. 外国语文,2009,( 2) :11 - 17.
[3] 华莱士·马丁. 当代叙事学[M]. 伍晓明,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
[4] 申丹,韩加明,王亚丽. 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94.
[5] [英]弗吉尼亚·伍尔夫. 翟世镜译. 到灯塔去[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6] 刘静. 伍尔夫《到灯塔去》的叙事策略[J]. 辽宁示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般) ,2010,( 6) : 88 -90.
[7] 谭君强. 叙事学导论—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84.
[8] Friedman,Norman.“Point of view in fiction: The develop-ment of a Critical concept,”PMLA70 ( 1995 ) 1176 -1177.
[9] Virginia Woolf,Orlando: A Biography[M]. London: Tri-al / Panther Books,1977: 61.
[10] 姚娜. 现代声音风景与读者敏锐的耳朵———论伍尔夫作品中通过听觉实现的声音叙述[J]. 安徽文学,2010,( 1) : 59 - 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