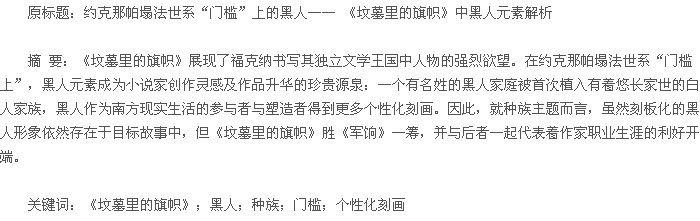
关于《坟墓里的旗帜》①,至少有两件事广为人知。其一,这是一部年轻的艺术家非常想“籍此扬名立万”却到处碰壁投之无门的长篇。他于 1927 年 9 月 29 日完成该小说的创作,并信心十足地将书稿交给他前两部小说的出版商利弗赖特(Liverright)。在给后者的信中,他写道:“这将是你今年读到的再好不过的书。”
让福克纳吃惊并震惊的是,在两个月后利弗赖特回信拒绝了该小说并劝告他不要再投其他任何地方:“实言相告,我们对此作品非常失望。它冗赘散乱,情节与人物都没有什么发展。”
②百般无奈,在朋友本·沃森(Ben Wasson)的帮助下,原版被删减至 11 万字,并被更名为《沙多里斯》于 1929 年出版。最终,福克纳的女儿吉尔·萨默斯(JillSummers)完成了小说家生前还原该小说的遗愿。她从弗吉尼亚大学阿德尔曼图书馆取出珍藏版596 页的混合书稿,交由道格拉斯·戴(Douglas Day)及兰登书屋的一名编辑处理,使得《坟墓里的旗帜》得以于 1973 年重见天日。其二,作者从此开始写他一辈子也写不完的“故乡那邮票般大小的土地”。
一、《坟墓里的旗帜》对黑人角色的塑造
确实,从《坟墓里的旗帜》开始,如该书引言所述,福克纳特别依附南方生活原型尤其是黑人民间故事来书写自己文学王国的人群,表明了他对南方传统毋庸置疑的接受。青年作家发现创作素材矿藏之喜悦无异于穷困潦倒的流浪汉误撞开了芝麻神门,太多的诱惑使得取舍非常艰难。
难怪乎,福氏第一部约克那帕塌法小说如作家本人所言“无太多目的”,且其中“六个故事并驾齐驱,千头万绪”。然而,约克纳帕塌法的发现确实使他得以浸淫于最为熟悉的氛围之中——双重种族且固步自封的南方世界,创作焦点也及时地从战后老兵及艺术家的迷惘错位转向历史悠久的沙多里斯家族。作家对人物的表现相应地更加坚实、明确。值得注意的是,在跨越约克那帕塌法世系“门槛”之际①,黑人作为南方生活实实在在的参与者成为福克纳创作灵感及作品升华弥足珍贵的源泉。
(一)黑、白家庭的并构
故事中,福克纳认真直面黑人群体。这表现在有名姓的黑人家庭被首次植入有着悠长家世的白人家族。斯特瑟一家从西蒙的祖父约比开始,到埃尔诺拉的儿子艾索姆五代伺奉沙多里斯家族。
这一内置是对《军饷》②的一种扬弃。一方面,它继承了前者黑白并构的传统。另一方面,它为近距离地观察这个双重种族家庭提供了权威视角。与《军饷》中对黑人的人为概述不同③,作为家庭成员的黑人既展示了自我生存状况,又提供了获取白人主子的信息途径。如此塑造的黑人拥有了自己哪怕是边缘化的生活。而且,尽管大部分时间扮演被动的文本角色,他们反衬并参与了患战争综合症的沙多里斯一家主导的生活。
黑白并置同样见证了作家对黑人种族美学及历史价值认识的深化。历史学家伍德沃德认为,“作为一大家族成员,福克纳与同时代美国小说家如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及其他‘迷惘一代’作家不一样,他从不抛开家庭、宗族、日渐增长的亲属及群体纽带”,所以也更擅长通过审视南方大家族来再现地区历史。如果考虑到小说家职业生涯最成功的作品都是围绕诸如康普生、麦卡斯林、斯特潘及斯诺普斯家族展开,这又的确是他的一个重要起点。福克纳本人几乎不读历史,因此,伍德沃德认为“任何企图从福氏小说(涉及南方历史)中获取通常意义上历史知识的读者都不免会失望,因为这些作品更是对过去及其对现在决定性(有时是灾难性的)影响之间关系的戏剧化表达”。《坟墓里的旗帜》乍一读来是对整个约克那帕塌法社会结构的剖析,其焦点实际在于无法对个人及家庭历史说再见的白亚德三世,以及在众多“之乎者也”式诗情感喟中想像理想生活的三角洲地区文人贺拉斯·班波。这些人物成了《喧哗与骚动》中被萨特精辟譬喻为“一个坐在敞篷车里往后看的人”的前身。对于他们,未来不可知,现在一片混沌,而“过去的轮廓是精确,清晰和不变易的。”
在双重种族的南方,黑人从生至死与白人代代相伴,是连接历史与现实之纽带的不二人选。因此,福学专家戴维斯认为福克纳将目标故事设定在南方传统大家族背景之下,原因在于福氏发现“黑人是创作可资利用的有效手段,可以将作家的主要关注与过去有机链接,可以为那个特定的‘过去’内涵增设另一个视角,也可以提升过去与现在之间的戏剧性张力。”
(二)个性化刻画
与《军饷》相比,《坟墓里的旗帜》中黑人得到更多的个性化刻画。沙家马车夫兼管家西蒙被塑造为“黑鬼”的同时又是“一个黑人”。首先,不论是源于庄园文学还是基于福克纳家族留守老仆原型(一般认为该人物与福家资深男仆耐德·巴奈特颇为相似),西蒙的素描展现了一个乐得接受南方白人家长式统治的黑人形象。他一出场便表现出与马的超常亲密与对主子沙家的无比爱戴。
西蒙高踞马车之上,左手持缰,右手很酷地倒执马鞭,口中叼着永远抽不完的雪茄屁股,一边慢声细语用恋人般的语调同马儿交心。西蒙溺爱马儿。他爱戴沙家,对他们服服帖帖庇护有加。但他宠爱马儿。在他的调教下,再蔫的劣马也会茁壮成长且如被悉心呵护的女子般端庄标致,如舞台演员般容易兴奋①。
这样的刻板喜剧黑人造型很快又会通过“展现其种族天性使然的夸张言行”得到加强。理查德·格雷认为“故事中此类笼统程式化言论同《军饷》如出一辙,将黑人简化为客体。”
具有此类黑人的共性生理特点:闻起来有“惯常的气味”且常被赋予动物形象,如他的头看上去像“所有的大猩猩好奇而又干瘪的外祖父”,在主子面前“像一个大猫一样悄然挪向桌旁”。我们最后见到其人时,他“看上去像一只青蛙”。他以沙家品质为荣,以身为声望家族一员为傲,言必称“马车行头”“绅士”,对其他“黑鬼”不屑一顾。他怀旧成性,驾车用的行话、高顶礼帽及老式掸帚都贴着过去的招牌。同老白亚德一起,他极力抵制技术诋毁机器。他甚至比上校本人还反感变革。
文中唯一展现其人内心之处,他向“主人约翰”抱怨时光不再,人心不古,礼仪不存。年轻人好端端的马车放着不用,却要去发疯似的开那鬼玩意儿。
在白人主子面前西蒙尤其显得毕恭毕敬。他与老白亚德之间是典型的“约翰与老主人”式关系。沙家女管家珍妮小姐可以像训斥他外孙艾索姆那样数落他。有趣的是,不论在沙家室内还是室外,西蒙都很少做正常人类之“行走状”,而是“拖着脚”,“蹑手蹑脚”,“轻声踱步”,“掠过”,“垫起脚”。他死心塌忠诚于主人家,直到临末了还在大声庆祝“小主人”的诞生,高呼“过去的好时光又回来了,可不是么”。因此,目标故事中西蒙虽得到足够重视,却也难逃刻版化常规。
但是批评家罗兹却指出,“文中多处福氏都试图重塑该人物,赋予他一个演员的智商与自由。”
诚然,西蒙大部分时间靠表演求生存。沃尔特·泰勒较早发现其人面具特质:“《军饷》中老列车员对南方的怀旧仅代表其人对旧秩序的一厢情愿,而同样感伤的西蒙却在忠诚中藏掖着个人目的。在‘喜剧式黑人’面具之下,福克纳见到了多重面具,旨在隐匿一个表面随和驯顺却很堕落的老者。”
赶车上路的戏剧性和处心积虑地对“沙家品质”的炫耀和维护之下,蛰伏着西蒙的清醒意识:黑人朝不保夕的所谓独立。西蒙所得报酬看起来微不足道:一处泊车之所,杰弗生镇沙家油水丰足的厨房里一份凉拌菜和冰激凌,在他们子孙五代伺候的白人家族厨房中为家人留存一糊口之所,或许还要算上偶尔替西蒙偿还的债务。然而一处工作之所,也即一种(如果并非唯一的)生存手段,对于生活境遇极其受限的南方黑人弥足珍贵,西蒙不敢贸然失去。他以沙家马车和绅士门第为傲,但更珍惜来之不易的免受饥饿和不安全的有限自由。文中老白亚德就是通过威胁驱逐一战归来叛逆求变的卡斯皮而成功制服了后者:“我一周前就给你传了话,要么立马来,要么永远别来,”随即抄起根柴火棍将卡斯皮打出门外滚落台阶。
西蒙对黑人处境的清醒认识同样表现在训子情节中。在儿子卡斯皮被老白亚德一柴火棍打落台阶之后,西蒙“扶儿子起来,略带蹒跚地拉他到马棚人听不见的地方,”一边批评他的“那些战争烧的想法,”嘟囔着“我们黑人究竟要自由干什么?”一边提醒他“当下的白人已经够咱们伺候的了。”罗兹认为西蒙“用一谄媚式谑语笑谈黑白人相互依存的状况,从而伪装了他的愤怒”,但同时“严正告诫对方不要不考虑后果就去轻易触动一个体制所能容限的些许自由”。
此外,西蒙还通过“扮演桑搏”(Sambo playing)来避免生计短路。对周围每一个人西蒙都备选一副面孔。在老白亚德面前,他感伤怀旧,不断提醒后者过去的好时光和“贵人举止必高尚”的信条。对于珍妮小姐,他“毕恭毕敬,还要大献殷勤,表现豪侠”。在娜西莎和小白亚德面前,“他就像一只悄无声息的大猫,宽厚温顺且细致周到”。有关“桑搏”和“扮演桑搏”的本质,历史学家威廉姆森曾评论道:
从黑人角度来看,扮演桑搏其实就是一种生存方式。当地方白人因肤色冲突而陷入一种歇斯底里(白人也常常如此)时,桑搏是黑人得以从暴行中生存的保护面具:低头哈腰,蹑手蹑脚,低声下气 以及一整套柔顺的行为规范。白人自创了这些表明黑人没有威胁的行为标识。这一角色有时拯救了黑人。间接地,它有时也使得白人免于诉诸狂暴危险的行径。这样的行径确实有损于白人自我标榜的光辉形象,即他们是庇护这些孩童般黑人的严父慈母。
个性多重的西蒙展现了霍华德·奥多姆所谓“一个真正的黑人所具有的特征”,“也即每一个黑人实际上是四个人的组合:黑人其人,白人心中的黑人,黑人有可能成为及想成为的黑人。”
西蒙因涉嫌贪污及与女混血儿美洛妮有染而惹祸上身。身为浸礼会出纳,西蒙利用职务之便私自挪用资金(很小的一笔)至美洛妮的美容沙龙,以图交易后者的身体。主流批评认为这一情节不过是一则花边新闻,旨在渲染一出南方“约翰与老主人”式闹剧,从而增添故事的喜剧色彩并强化主导的“黑人即稚愚孩童”的白人观念。罗兹却逆流而上,认为这代表“福氏塑造现实黑人”的企图,“将个人置于社会体制内,展现其自我奋斗历程。”
罗兹说如果读者追踪教堂资金从黑人出纳之手经由西蒙的“银行”转移至美洛妮实业的走向,会发现“交易的每一个阶段,从资金源到投资口,福氏考虑到了每个细节的社会可能性。”
因此,同一个西蒙被赋予了两种塑造模式:刻板式喜剧人物及更加复杂、独立、不断寻求机会发展自我的现实中人。然而,就在读者为新西蒙的诞生喝彩,为他巧妙利用主子的家长风范为他清偿债务感到欢欣,并急于分享其即将开发的“战利品”之际,“一周后的某个早晨,头发斑白的西蒙遭了匿名钝器的致命一击,被发现死于镇上一黑人小屋内”。笔者认为这部分解释了霍拉斯·利弗赖特“人物发展不充分”的抱怨及萨特的读后感:“从技巧角度看,小说中作者出卖了自己,通篇都可以被捉现形。”
不论故事中谁是真正的凶手,幕后操纵匿名钝器的黑手必然是伪装拙劣的小说家本人。罗兹因此不无遗憾地感叹道:“福克纳开始把西蒙描述成一个‘现实’中人,却又突然将他扔回到种族文学常见的刻板式黑人行列中去了。”
“一战”归来求变的卡斯皮是另一位稍有起色却被扼杀在萌芽状态的惨遭“黑手”者。战争改变了这位前家奴,欧洲的经历使他产生了与白人平等的要求。他对家人说,“我再也不会买白人的帐了,……战争改变了一切。如果我们能够把法国人从德国人手里解放出来,那么我们也可以拥有德国人所享有的权利。起码法国人是这样认为的。如果美国人不这样想,我们有办法教训他们。”他同样要求言论自由,理由是“战争打开了黑人的嘴巴,……给他说话的权利”。然而福克纳本就是将他当作喜剧滑稽人物来调侃的。卡斯皮的家庭和军旅履历,我们被告知,都是做“下人(手)”,干上司“推卸到他肩上的事”。当战场上实在无事可干的时候,“卡斯皮带着对劳动、忠诚以及其他东西厌恶透顶的心情和两条‘在赌博中’留下的伤痕回到了他的故乡,但与环境格格不入”。为了树立“光辉形象”,老兵卡斯皮张开大嘴巴,海吹在海外的业绩。虽然他的光辉形象只成就了艾索姆和埃尔诺拉两位崇拜者。让卡斯皮的“平等和自由”大打折扣的是,福克纳没有忘记加上他对“白人妇女”的坚决要求,而且“如果必要”,可以“不理会仁慈的上帝”。结果,他“不着边际”的想法只是让家人对他“敬而远之”,更让主人对他不满。卡斯皮可以逃避珍妮小姐的传唤,可以不理会老白亚德的警告,但当他拒绝为“上校”备马的时候,被主人用一根柴火棍打得连滚带爬,从此还为安守本分的黑奴。
毋庸讳言,黑人不论战前还是战后都很难逃脱先在命运,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卡斯皮只需要一柴火棍就乖乖归位。此公从此销声匿迹,只有零星传闻说他“除了周六晚上已大致恢复正常”。
其人最后出场时正同白亚德与那西莎一起打猎,“手提条纹状昏暗灯笼,背负母牛号角,”又恢复了下人身份。对此,萨迪厄斯·M·戴维斯精辟地论述道:“尽管只是短暂的展开便又落入俗套,卡斯皮求变的欲望和对成规的背叛不仅预示了福克纳不断增强的‘战争改变白人也改变黑人’的意识,而且从另一方面说明他不能够描述‘现代’黑人的情感。”
卡斯皮的粉丝艾索姆是伺候驴、马和菜园的一个 16 岁的黑人童仆,智力低下,似乎是作者仅为取得喜剧效果而设置的一个笑柄。在家中,他是珍妮婶婶的一个“出气筒”,被后者说成是左、右手不辨,最善于避活,还是菜园管理不善的罪魁祸首,“有这样一个傻冒,谁都甭想菜园像模像样。”他是舅舅卡斯皮坚定的崇拜者,后者的“海外传奇”让他痴迷。他还穿着后者的军装到处显摆,“脸上的神情狂喜而专注”。在其它场合,他给人留下印象的总是“龇牙咧嘴”和“不停地转动的眼白”。小说结尾处,他伴随珍妮小姐去墓地,当后者不无感伤地琢磨“西蒙(艾索姆的姥爷)也得有一个墓碑”的时候,艾索姆却在忙着上树掏鸟蛋。珍妮小姐愤然断言:“艾索姆过日子全凭生来是黑人。”我们从中明显感觉到作者不无揶揄的戏谑笔调。
(三)黑人情节的增加
此外,故事中被冠以名姓的黑人还有休斯顿、雷切尔、理查德、亨利和马夫托比。黑人名姓的增加意味着人物表现的确定与强化。连同麦克克莱姆家黑奴、蓓尔·米切尔家厨娘、乐师及教堂长老,这些黑人成了南方生活鲜活的参与者。有关黑人的情节相应增加。其中两例尤其发人深省,彰显了南方双重种族生活方式的内在悖逆本质。
两处插曲都与事故频发的白亚德相关。其中一处就发生在事故之后。约翰·亨利一家赶驴车回家途中听到河湾方向传来异响,赶到出事地点发现一辆车翻进了山脚下河湾中:“车前轱辘还在打旋,发动机在空转,排放出淡淡的废气。”看到白人司机悬挂在水中,父子俩就是否救溺水的白亚德发生了争执。阅历丰富的父亲规劝儿子不要靠近尚未熄火的汽车,也不要碰白人,因为“白人会认为这是俺们干的”,而涉世不深的儿子却一门心思要救人。父子之争反映了黑白种族隔阂之深。因此,“一个在岸上,一个在水中,父子俩较上了劲。而此时白亚德的靴子周围已经开始泛起泡泡。”最终,“虽然咕咕哝哝地埋怨着,做父亲的还是退了鞋子下了水”。救起人后,一家人还护送白亚德回家。这都反映了在种族隔离的南方黑人的人道天性。
另一处,白亚德强人所难地与一黑人农户共度了圣诞。与《军饷》中孤立、片面地对比黑白群体生活的做法不同,此处福克纳令人信服地将黑人与白人组合在一起,从而洞察真实的黑人家庭生活。这一次白亚德离家出走,一方面源于对祖父死亡的愧疚,另一方面不堪忍受孪生兄弟约翰在战争中丧命带来的创伤煎熬。他在暴风雨中迷了路,寄宿于一户黑人农家。作为不速之客,他的到来恰逢圣诞。黑人一家略显踌躇地与他分享了他们的慷慨。虽然很是敏感黑人的气味,破旧的衣装,少得可怜脏兮兮的食物和东倒西歪的住所,白亚德深深感受到一家人相依为命的温暖:“屋内闭塞且有些怪味,暖意慢慢潜入他寒夜受冻后疲惫僵直的身体。黑人一家在一间居所内来往忙碌,女人在炉灶边做饭,孩子们摆弄着廉价的圣诞礼品和脏兮兮的糖果。”在此黑人现实的经典呈现中,我们不仅注意到黑人简朴的生活状况,还了解到他们对待生存的积极态度。白亚德感受到一家人的共同奋斗与安定。黑人破旧的炉灶里用来取暖做饭的星火成了《去吧,摩西》中路喀斯家灶头永恒火种的可贵预期,不仅反映了黑人生活之简朴,也象征着亲人之间爱的纽带。
黑人再次“愉快虽则有些不自信”地邀他共饮之际,万能的叙述者发论道:“两个因种族、血缘、天性及环境因素而互相排斥的对立观念,在此一刻碰撞并在一个矛盾性错觉中融合——人类在这一天忘却了欲求、胆怯和贪婪。”这一刻也标志着年轻作家对一重大主题珍贵的尝试性挖掘,即超越社会藩篱的种族融合。该主题在《去吧,摩西》①,尤其是《押沙龙!押沙龙!》中得到充分发展②。但当下文本中,作者只能为文至此,白亚德也只是参照自身处境反思黑人家庭的人性。
二、黑人元素表现评析
《坟》中南方世界根本上是隔离的。黑人担任司机、厨师、马车夫、男管家、侍者和农夫等从属角色。不论在公共场合还是家中,黑人与白人一般不同桌吃喝③。等级制在沙家非常严格。
埃尔诺拉在厨房专司烹饪,西蒙与艾索姆负责上饭菜。难怪乎卡斯皮在家中或军队里都很难改变既成角色。隔离在死后还会继续。西蒙所属的黑人坟地“在严格意义上规划有序的公墓区之外”。
白人对黑人的种种反应也证实了这一点。在珍妮小姐看来,小到艾索姆,大到西蒙,哪一个都是“可恶的黑鬼”,“沙家用来烦她折磨她的附属品”。即便娴静的娜西莎也认为生病的白亚德身边不能没人照料,光是黑鬼肯定不行。皮保迪医生弄不清他家黑人数量就像搞不清他家有多少头猪一样。甚至镇上最好的厨娘雷切尔也未能幸免。哈利认为“雷切尔跟所有黑鬼一样是话痨”。在老白亚德和珍妮小姐(甚至西蒙)看来,黑人教会董事会成员就是一群傻蛋加蠢货。
值得注意的是,“瓦德曼先生”被白人两次提及。詹姆斯·金伯·瓦德曼及其继任者西奥多·比尔波系二十世纪初期极端种族主义者,因施行严苛的剥夺黑人选举权、处私刑和隔离种族统治而臭名昭着。一方面,这说明珍妮小姐勃然怒斥叛逆的卡斯皮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究竟是哪个傻瓜出了这么个馊主意,让黑人也像白人一样套上军装?还是瓦德曼先生有远见,他对华盛顿的那些笨蛋说这不行,可那些个政客!”另一方面,据沃尔特·泰勒考据,福克纳年轻时,他身为贵族的祖父约翰·韦斯利·汤普森·福克纳觉得有必要在政治上同“白人首领”(瓦德曼的别称)联合。
泰勒认为那些年的种族紧张局势在福克纳职业生涯中起了重要作用。这或许可以部分解释福氏作品中戏谑式黑人素描。譬如《军饷》中遭受不公正待遇的黑人士兵就重蹈了不幸。
故事中“战争综合症”患者白亚德三世的举动充分体现了“迷茫的一代”的荒唐与疯狂,黑人士兵除了昙花一现的卡斯皮和一位沦为“身穿袖口有下士条纹的卡其服”,靠墙蹲坐吹口风琴卖艺盲者外,其余都默默无闻。卖艺乞讨老兵的悲惨境遇强有力地说明黑人的命运战前和战后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但事实是福氏呈现了一幅历史场景却未对之进行任何发挥,且选择黑人老兵作为受害者,这不得不让人怀疑未圆自己军人梦的福克纳是否就像该小说中的珍妮婶婶,是瓦德曼的追随者。这一疑问将得到有力佐证,因为纵观福氏作品,其中几乎没有被正面塑造的黑人士兵。
黑人的其他元素在《坟》中得以延续。“黑人与驴”的频繁组合与疾驰的汽车形成对比,也凸显了“人与驴”的亲密性。黑人的言谈、笑声、歌唱及伴有神秘哀伤的音乐给小镇生活定下了步调,同时与迷惘的一代白人的病态形成并构。极度失落沮丧的白亚德困惑于黑人的异域特质,“行动迟缓散漫如同黑色平静的梦中人物,身上散发着动物的臭气,时而低声细语,时而放声大笑。”厨房里不断传出来埃尔诺拉的哼唱则反衬了“沙家帮”的焦虑不安。律师兼诗人贺拉斯·班波草率成婚,闲来后悔,家庭氛围极不和谐。去取妻子蓓儿喜食的臭虾途中,他遇到一群黑人在翻修街道。黑人迟缓却有条不紊的工作节奏与他们的哀婉吟唱起落有致,形成一幅近乎凝滞的静态画面。如同《军饷》中众多印象主义素描一样,此场景彰显了黑人慵懒甚至梦游般的节奏及与环境的有机融入。这让失落、失望、焦虑的新婚丈夫感受到了片刻的宁静与和谐。
因此,《军饷》中黑人更是作为“抽象的观念”出场,作用类似于诗歌中的叠句或音乐中的连复段,重在提升故事的抒情诗品质。《坟》中黑人角色无论是作为有名姓家庭成员还是南方真实生活的参与者,不仅反映且参与塑造了南方的历史与现实,所以虽然发展不足,却代表福氏对黑人群体更切近明确的表征。在此意义上,《坟》胜《军饷》一筹。
关于目标故事的黑人塑造,国内外学界皆有可商榷言论。如戴维斯认为“斯特瑟一家仍然是沿袭传统的非个性化人物,他们的存在也仅是白人家庭的附属与延伸,而非一群独具特色的群体,因而无法通过他们理解白人主导的社会。”
如上文所示,虽则未能善始善终,故事中主要黑人角色已经被赋予相当独立性与发展潜能。最为重要的是,往往在同一个人物身上,我们发现作者游离纠结于传统的程式化塑造与开明、人性化创新之间。如他企图赋予黑人个性的同时却又犹豫再三,不能坚持。可以说,正是在卡斯皮、美洛妮、西蒙、耐德等个人以及整个黑人种族这样一个“半成品”身上我们见证了作者矛盾的心路历程与和曲折的探索轨迹。
此外,杰克逊以“约克纳帕塌法”的发现为分水岭划分黑人角色,认为之前的人物塑造是对其他艺术家的盲从,“之后的一切,包括黑人都是他本人的创造”这种截然界分的做法显然值得商榷,斩断了创作的延续性。譬如国内外学者如李文俊、布罗克斯、和里查德·格雷都认为《军饷》中的查尔斯镇和密西西比州的杰弗逊镇并无区别,而且有充分证据证明该王国中的许多黑人继承了刻板形象,并非如杰克逊所言完全属于作者本人①。本文所示的众多黑人个案就是对《军饷》的继承与发展。
国内学者对福氏早期黑人塑造不乏高见,但将人物重要性与角色担当机械对应的做法笔者则认为不妥。如有论者认为《喧哗与骚动》之前小说中黑人扮演附属角色,所以不重要。上文对众多边缘化角色的分析恰恰应证了温斯坦所引德里达有关“互补”(supplement)的论述:“中心不只是‘容许’边缘的共存,而恰恰是由边缘的概念构成。”
换言之,去掉边缘便失去了中心。温氏认为“福氏黑人正是在此意义上对白人至关重要(没有黑人衬托突出其白,何谈白人?)”。
再者,早期黑人大多成了中后期作品中提高版的原型,其互文性意义不言自明。似乎可以这样结论:尚处于学艺阶段的艺术家确实未能将黑人与其核心关注有机结合,但毋庸置疑的是,黑人的存在在相当程度上成就了白人,丰满了文本。
如果考虑福氏生平家世,早期文本中其人对黑人面具后人性的偶尔窥探及优良品性的彰显尤其显得珍贵。身为大奴隶主贵族后裔,祖父同极端种族主义分子结盟①,年青时代亲历了种族歧视之嚣张,作家挣脱传统陈规之勇气可嘉。黑人批评家斯特林·布朗就很看好福氏的早期作品。
比如说,他认为“《沙多里斯》中有众多卑微却颇具个性特色的黑人人物”。在其开拓性专着《美国小说中的黑人》中,他将福克纳与同期作家如乔治·米尔本、詹姆斯·法莱尔、考德维尔等进行比较,认为“福克纳不写社会抗议小说,……却刻意反映事实真相”。如果这代表着美国黑人评者对作家初期作品极为肯定的反应,我们似乎可以安然作论:这些早期作品也代表着作家职业生涯探索种族主题的希望开始。
参考文献
[1] Blotner J. Selected Letters of William Faulkner [M]. NewYork: Vintage Books, 1978.
[2] Day D. Introduction [C] // Faulkner W. Flags in the Dust. NewYork: Random House, 1973: 8.
[3] Meriwether J B, Millgate M. Lion in the Garden: Interviews with William Faulkner (1926-1962) [M]. New York:Random House, 1968: 255.
[4] Blotner J. Faulkner:ABiography [M]. NewYork: Random House, 1974: 5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