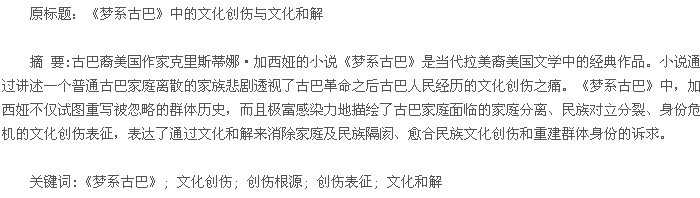
文学评论家安德里亚·赫雷拉( Andrea O'ReillyHerrera) 认为: “加勒比海后现代文艺的中心是揭开西方主导的历史文本中的虚假面具并“揭露其阴谋”( 借用海登·怀特( Hayden White) 的术语) ,同时企图重申被西方殖民势力在官方记录中所刻意否定的“‘集体记忆’和文化历史”( Herrera,1997: 69) 。
古巴裔美国女作家克里斯蒂娜·加西娅( CristinaGarcia,1958 - ) 的成名作《梦系古巴》( Dreaming inCuban,1992) 挑战了西方中心论和文化霸权主义,从古巴普通民众的角度出发重写了古巴历史。小说一经发表就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获得了 1992 年美国国家图书奖的提名奖,且很快被列入西语裔及拉美裔美国文学经典。
小说以皮诺一家三代的女性为主要的创伤叙述者,讲述了一个普通古巴家庭在古巴革命后的流散经历,并着力描写了因政治和文化信仰分歧而四分五裂的古巴家庭和民族所经历的文化创伤之痛。小说虽以古巴革命为背景,却非按时间顺序叙事记录客观事件的历史小说,它突显了宏观历史之于普通个体和家庭的效应,强调叙事者们经历文化创伤的内心感受。在《梦系古巴》中,加西娅指出文化和解和包容是愈合文化创伤、摆脱身份困境的必由之路。
一、文化创伤
文化创伤( cultural trauma) 研究起源于因战争、政治和其他灾难而面临身份危机问题的群体特征研究,耶鲁大学教授埃尔曼( Ron Eyerman) 将文化创伤总结为“某一事件或灾难对群体未来身份产生的根本且不可逆转的影响,它标志着某一群体身份和意义的骤然消失,它造成社会结构裂痕且对群体凝聚力造成不良影响”( Eyerman,2004: 161) 。文化创伤是几乎所有移民群体都必须面临的问题,出生在古巴、幼年移民美国的加西娅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作为生活在美国的古巴流亡者群体中的一员,那种既不适应哈瓦那生活又不属于迈阿密的感觉迫使我开始思考自己的身份问题”( Garcia,1992: 249) 。
在《梦系古巴》中,加西娅描绘了生活在古巴革命后文化创伤阴影下流亡美国古巴人的双重边缘化身份困境,以及古巴人民家庭分离、民族对立分裂的群体状况,并对造成古巴人民文化创伤的政治根源进行了剖析。
威廉姆·刘易斯( William Luis) 在对《梦系古巴》中的古巴历史事件研究后发现,小说的确是以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为社会历史背景,而这场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古巴的社会历史进程( Luis,1996: 223) 。1959 年古巴革命军推翻了亲美殖民政府的统治,结束了美国对古巴长期的半殖民统治,随后革命的社会主义转向使得古巴成为了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的一员,同时成为了苏联在美洲对抗美国的前沿阵地。古巴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陷入了苏美对峙的冷战模式之中,非此即彼( either/or) 的冷战思维开始瓦解原本受多元文化影响的古巴社会,因而原有身份丧失、民族对立分裂、家庭分离的文化创伤在所难免。加西娅深刻的体会古巴革命作为政治事件对于古巴社会和普通家庭的巨大影响,她注意到冷战思维衍生出的极左和极右势力正在不断地分裂着古巴民族,意识到古巴人民经历的文化创伤在代际间延续的危险。因而,加西娅在《梦系古巴》中通过皮诺家族在古巴革命前后的经历,指出极左和极右观点的对立是造成古巴人民文化创伤之痛的政治根源,并表达了对这种非此即彼政治模式的质疑和厌恶。
古巴人民间的政治对立得以长期存在实则是对立的美国主流文化通过多种媒体对人们意识形态操控的结果。在小说中加西娅借由第二代古巴移民皮拉尔之口表述了对文化专制和思想控制的反抗。
皮拉尔在逃离美国的途中意识到她从未在历史课本上读到过父亲讲述的古巴历史,在历史课上她学到的更多的是查理大帝及拿破仑的一场场战役,她对自己民族的了解无法从被美国主流资本主义思想控制的课本中获取。她意识到无形中早已有人控制了他们应当知道什么、什么才是重要的,“我痛恨那些政客和将军们,他们将一桩桩事强加给我们来构成我们的人生,规定我们的记忆”( Garcia,1992: 138) 。
正是在这样专制的思想文化控制下,无论是流亡美国的古巴人还是坚守在故土的古巴民众在封闭的文化环境下都只能看到部分的事实,他们习惯了主流媒体宣传的对抗和分裂,这也正是文化创伤延续的原因之所在。
二、《梦系古巴》中文化创伤的表征
( 一) 家庭分离
群体凝聚力的破坏是文化创伤的一个重要表征,而在《梦系古巴》中可以更明显具体地表现在家庭关系的恶化上。苏美尖锐对抗的冷战思维正在意识形态上分裂着古巴民族,也使持有不同政治理想的古巴家庭彼此隔阂甚至永远分离; 皮诺一家的经历不是独立存在特殊现象,而是整个古巴民族在这一时期创伤经历的缩影。
皮诺一家因政治信仰分歧而四分五裂的家庭状况首先表现在作为家庭基石的夫妻关系的破裂上。
西丽娅与乔治的婚姻并没能给彼此带来家庭归属感和认同感,相反政治信仰和文化信仰的分歧使彼此在精神上深受折磨。西丽娅受幼年成长经历和西班牙情人盖斯塔沃影响,极度渴望一个独立自主的古巴,她认为亲美的古巴殖民政府如同“吸血鬼”一般将人民的财富集中到了美国人和为美国服务的腐败政府手中; 然而丈夫乔治则是美国公司在古巴的雇员,他推崇美国主流文化价值观,是亲美政府的支持者。在乔治专制的男权家长统治下,西丽娅不得不压抑对古巴革命的支持和热情,这更促使她对有着共同政治理想的西班牙情人盖斯塔沃的思念。在这样的婚姻状况中,西丽娅想要逃离囚禁她自由意志的婚姻牢笼,乔治则因为付出爱得不到回报而痛苦。
受家庭政治信仰分歧的影响,父母与子女关系的恶化使得皮诺家庭分离的状况更加彻底。乔治对于大女儿鲁迪斯的爱具有明显的政治结盟倾向,他刻意造成鲁迪斯与西丽娅间的误解从而达到对鲁迪斯思想的完全控制; 他对与西丽娅关系较亲近的二女儿菲莉西娅和儿子哈维尔则刻意冷漠疏远并拒绝给予父爱。正如加西娅在采访中所说的那样,“政治真实地存在于每一个普通家庭中”( López,1995:108) ,由尖锐的政治分歧到政治和情感的结盟和对抗直接导致了皮诺一家四分五裂的家庭悲剧。乔治因为无法面对妻子西丽娅对革命的忠诚,追随大女儿鲁迪斯移居美国并在美国孤独终老; 哈维尔因父亲乔治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对,不得不远赴东欧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并与支持资本主义统治的父亲乔治至死不相往来。二女儿菲莉西娅对政治毫不关心,她试图从萨泰里阿教①中寻求精神支持,因而也难免被家庭排斥在外并在极度的孤独无依中死去。西丽娅是皮诺家族中唯一在精神和行动上支持古巴革命的人,她在为社会主义理想奉献热忱时也痛苦的意识到,由于政治信仰的分歧,“她的丈夫将被埋葬在坚硬的异国土地上”,“他们的后代沦为了流亡者”( Garcia,1992: 7) 。
皮诺家族中母亲西丽娅和大女儿鲁迪斯是政治上极左派和极右派的典型代表,她们分别忠诚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政治理想,同时这种忠诚具有极端的排他性,即完全否认其他政治理想或模式的合理性。在加西娅看来这种家庭和民族层面上政治对立的“本质是非黑即白的,是极端分化而又格格不入的,双方都自诩公平正义,彼此又毫不妥协”( 同上: 250) 。幼年时母爱之痛的阴影笼罩了鲁迪斯的一生,而政治分歧造成了她与母亲的最终分离。革命带来的文化冲突加深了西丽娅和女儿鲁迪斯的隔阂,在西丽娅眼中鲁迪斯移民美国是对祖国的背叛,而鲁迪斯每每提及古巴社会主义则愤恨不已,同时她对母亲的革命精神保持尖刻的嘲讽态度。因受各自信仰的支配,西丽娅和鲁迪斯在大海两端的古巴和美国各自守卫着代表自己政治理想的土地,时刻准备着抵御对方支持的敌对势力的入侵,她们母女也永远的被政治和大海分隔疏远。
( 二) 民族对立分裂
群体凝聚力下降是文化创伤的一种表现,由政治分歧造成的文化创伤在小的群体范围表现为普通古巴家庭的四分五裂,在民族层面上则表现成为极左派和极右派的针锋相对。每每论及政治,西丽娅则一改往日随和包容的形象,她对于亲美派的态度是极端强硬的,她曾认为依附于美国政府而暴富且凌驾于人民之上的亲家在革命胜利后首先应当被绞死。乔治离开古巴后,西丽娅每月都会志愿守卫古巴北部海岸,防止来自美国“叛国者们”的入侵企图。而在大海另一端的纽约,鲁迪斯的面包店是古巴流亡者极右派的聚集点,他们高谈阔论着如何推翻革命政府,他们甚至在面包店大肆庆祝一个主张重建美国-古巴关系记者的惨死。这让受双重文化影响的皮拉尔惊异于政治分歧是如何把母亲和外祖母变得如此不同和极端。
除极左派和极右派互不相容的政治斗争外,民族对立分裂还表现为持有不同信仰( 政治、文化、宗教信仰等) 和有着不同立场的群体对异己者的排斥和极低的容忍度。对立和彼此不满的情绪存在于古巴家庭甚至整个民族氛围之中,《梦系古巴》中对于古巴公共生活场景的描写较为直接地反映了这一点。在西丽娅居住的圣特雷莎小镇,本应私下处理的家庭情感纠纷发展成了当地 300 多人集体参与的闹剧,两个女人间的纠纷成了小镇每个观众都下了赌注的对决,参与者们都借此发泄内心对周遭一切的强烈不满。整个审判过程中,“男人和他们的妻子争得面红耳赤,已婚妇女和单身及离异女人互不相让,政治派和非政治派吵得不可开交”,这场本不宜在公共场合上演的争吵“成了每个人发泄对家人、邻居、制度和生活不满的借口,旧的伤疤重被揭开,新的伤害接踵而至”( 同上: 114) 。政治带来的文化创伤的阴霾正在人与人之间设立更多的屏障,很多古巴人不得不承受来自家庭和外界的孤立和敌对造成的创伤之痛。加西娅用极富讽刺性的口吻描述了盲目而激愤的政治极端分子的可笑和疯狂,同时暗示政治分歧激起的仇恨在民族内部不断发酵,政治极端主义只能给古巴民族带来更多的创伤之痛。
( 三) 身份危机
家庭分离意味着个体与家人精神连接纽带的断裂,而民族对立分裂则意味流亡海外的古巴移民群体与本族历史纽带的分离,因而,倍受分离之苦的古巴人民尤其是古巴的海外移民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个体和集体身份危机。身份危机是群体文化创伤的重要表征,加西娅通过《梦系古巴》中对移民美国的古巴家庭身份危机的描述,表达了受文化创伤影响的整个古巴移民群体的身份困惑。
皮诺家族中的信仰冲突使得父母与孩子的关系或紧张断裂或过分依从,家庭中的政治对抗和联盟关系极易造成下一代人身份的扭曲。由于父母关系的恶化,孩子们成了父亲或母亲的精神寄托,同时成为了受害者( 李保杰,2008: 108) 。乔治与鲁迪斯之间过于亲密的父女关系多次被隐晦得描写为恋人般的依恋( attachment) 。畸形的父爱剥夺了鲁迪斯获得完整的父母爱的权利,也迫使她形成较为单一的价值观和不完整的家庭身份认同,鲁迪斯对于自我和外界的认识和评价过早地被偏见侵蚀。她的思想深受父亲的宗教信仰和政治倾向的影响,她和父亲一样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是亲美政府的支持者,同时鲁迪斯在与母亲西丽娅的无神论和革命思想作斗争时,习惯性地把一切与自己信仰相左的东西丑恶化。
在女儿皮拉尔的眼中鲁迪斯总是“根据自己的世界观重写历史,重塑每天发生的事件,尽管她的重塑与事实大相径庭,这是有预谋的自欺欺人……她看不到事实真相,她只看到自己想看到的”( Garcia,1992: 176) 。幼时与父、母扭曲的关系和革命后与母亲关系的恶化使得鲁迪斯不可能获得完整的家庭归属感和身份认同,而这样的童年经历影响了鲁迪斯的一生。
尽管鲁迪斯移居美国后努力在异族文化中寻求身份认同,然而与古巴文化无法割舍的联系注定了她无法完全融入异国主流文化中,无法在异族文化中获得完整的归属感和身份认同。在古巴经历的梦靥让鲁迪斯对美国提供的庇佑心存感激,她选择冬天寒冷的纽约居住下来以便她能忘记一切与古巴炎热相关的创伤记忆,她排斥与古巴文化相关的任何事物,有意识地用美国主流文化的价值观重塑自己,并以同样的标准要求周围的人。成为美国“模范少数族裔”代表的鲁迪斯试图通过“阉割”自己原有的古巴文化身份来愈合心理创伤。然而,由此而来的空虚感和不满足感让她的生活经历了另一番苦痛:女儿皮拉尔为反抗她的精神控制离家出走,丈夫鲁非诺惧怕她无法满足的食欲、性欲和暴躁的脾气与她日渐疏远,父亲乔治的病逝让她丧失了精神上的唯一归属。美国文化给她提供了想象中归属和认同,然而家人和外界对她的疏离甚至怨愤让她感到极度的孤独,对家人和自我的陌生感则是鲁迪斯自我身份意识丧失的表征。
对美国生活和主流文化的难以适应使得不少古巴移民处于既无法回到过去又无力与现实认同的夹缝中,强制重复的创伤记忆不断提醒着他们所失去的一切。曾经忠厚能干的鲁非诺永远无法适应在纽约的生活,他躲在布鲁克林家中的工作间里,拒绝与外面陌生的世界过多的接触,终日郁郁寡欢,而“只有谈到在古巴的过去才能让他焕发活力”( 同上:138) 。他像是自家古巴农场上的一株深深扎根的植物,太依恋故土农场的一切,连妻子鲁迪斯也意识到,“他( 鲁非诺) 无法被移植到其它地方”( 同上:129) 。因无法适应美国城市生活鲁非诺不再是家庭经济收入的来源,在之后的生活中他逐渐沦为了妻子鲁迪斯发泄性欲的工具,他只能靠逃避现实生活来排遣经济地位和男性尊严丧失的痛楚。美国主流文化无法提供鲁非诺所需要的归属感,他又无意与古巴文化脱离关系,因而只能通过在他的工作间中养殖和发明来祭奠他无法割舍的古巴文化和在古巴的过去。
身份构建的困境是被双重边缘化的少数族裔必然面临的问题,是群体文化创伤的重要表征。作为古巴的第二代移民,皮拉尔两岁便被带离古巴,母亲鲁迪斯试图通过专制的美国主流文化的灌输把她塑造成一个美国人,然而与外祖母共同生活的记忆让皮拉尔对外祖母代表的古巴一直存在想象中的依存关系,在重回古巴之前她一直希望她是属于古巴的。
“即便我一直生活在布鲁克林,这里对我来说并不是家”。( 同上: 58) 皮拉尔与外祖母亲密的关系让鲁迪斯心存芥蒂,鲁迪斯想尽一切办法切断女儿与西丽娅的精神联系,她企图把自己的喜好强加给皮拉尔从而实现对女儿的精神占有和控制,她试图教会皮拉尔像她一样去怨恨古巴和为古巴革命奉献热忱的母亲,然而皮拉尔用出走来反抗回击了鲁迪斯的精神统治。皮拉尔对于美国主流文化的抗拒更多的源自于对母亲思想控制的抗拒,同时因为鲁迪斯拒绝回答女儿有关西丽娅的任何问题,因而皮拉尔只能通过想象填充对于外祖母和古巴认识的空白,而这无益于皮拉尔形成正常的身份认同。对美国主流文化的抗拒,以及现实古巴与想象中古巴的差异将皮拉尔推向了双重边缘化的境地: 她既不属于美国也不属于现实中的古巴。
婚姻战争和对立的家庭政治在给夫妻彼此带来伤痛的同时,消磨掉了家庭成员间应有的爱和理解,也造成了下一代独立意志的丧失和身份的不完整。
孩子在父母的婚姻战争中往往成了一方用以惩罚另一方的武器,他们被父母一方拉拢为“同盟”并形成了身份上的认同,在独立意志和认知判断尚未完全形成之前,在谎言和有意无意地教唆中本能地憎恶和异化他们共同的“敌人”。年幼的露斯在母亲菲莉西娅与父亲雨果极度不幸的婚姻中早早的意识到了这一残酷的现实: “家庭本质上是政治性的,你将不得不选择站队”( 同上: 86) 。不完整的父母爱造成的归属感缺失一直困扰着皮诺家族的后代,信仰不同、意识形态分歧的家庭氛围使得身份认同感的形成以疏离其他家庭成员为代价,皮诺家族成员间的疏离和无意的冷漠使得每一个人都成了精神上的流亡者,心理创伤的体验也在代代相传。小说中政治在无形中左右了每个人的命运,作者加西娅深刻的体会到“爱比政治艰难”( 同上: 252) 的事实正带来更多的分离和身份困惑。
三、从文化创伤到文化和解
和解( reconciliation) 是加西娅早期小说的一个共同主题。她发表于 1997 年的《阿吉罗姐妹》( TheAgüero Sisters) ,通过另外一种视角展现了被极端信仰分裂的姐妹所经历的支离破碎的人生,其中和解是小说人物重获身份认同和精神归属的唯一出路( Garcia,1997) 。古巴裔美国作家露丝·贝哈( RuthBehar) 认为,古巴的社会现实要求更多的古巴人“更加细致入微地看待古巴的复杂情形,合理地看待留在故土和流散在外的古巴人如何在战后余殃分裂的民族中给各自的生活、身份和文化赋予意义”( Behar,1995: 2) 。加西娅在《梦系古巴》中采用的多角度叙事则较好地呈现了被政治分裂的对立双方各自立场背后的历史现实,创伤叙事的手法使得每个叙述者能够有充足的空间通过讲述各自的创伤体验把历史和现实相连接,加西娅也试图通过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多种“事实”为对立和分离的家庭、民族提供理解和沟通的桥梁。因而,凯瑟琳·培安特( Kathrine B. Payant) 认为: “加西娅的作品无疑带有贝哈所肯定的细致入微和复杂的眼光,由此而来的和解正是贝哈所呼吁和渴望的”( Payant,2001:164) 。
古巴长期被殖民的历史使得古巴社会本身受多种文化元素的影响,古巴文化和殖民文化( 主要是西班牙和美国文化) 在古巴长期共存并共同铸造了古巴历史,共同影响着古巴民众个体和集体意识的形成,因而出于政治目的对任何一种文化的强行抵制都可能造成身份意识的扭曲,使更多的古巴人面临身份构建的困境。因而,加西娅借由小说中皮诺一家第三代核心人物皮拉尔的文化杂糅身份和双边视角表达了文化和解的诉求。加西娅在接受采访时承认,皮拉尔这个充满反叛精神的年轻人其实是她的另一个自我( alter - ego) ,皮拉尔在小说中的探求和她在现实生活中的探索很相似 ( López,1995:107) 。两岁时被带离古巴在美国主流文化环境中长大的皮拉尔与古巴维持着想象中的依存关系,介于双重文化和意识形态之间的身份和经历使得她拥有了不同于母亲鲁迪斯和外祖母西丽娅的双重视角。皮拉尔在反抗母亲精神控制的成长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较为独立的思考和判断能力,在试图重回古巴寻找身份和归属感的途中,年仅十三岁的皮拉尔开始有意识地抵制那些被扭曲和强加给自己的历史记忆,“谁在选择我们应该知道什么、什么才是重要的? 我明白这些事情应由我来决定”( Garcia,1992:28) 。这种独立的自我意识使她避免了极左或极右的意识形态的控制,赢得了较为自由的身份形成空间。
成年后对美国文化和古巴社会现实的批判性认识使得皮拉尔将自我身份界定为“古巴裔美国人”( the Cuban - American) 。皮拉尔逐渐从作为美国人或古巴人非此即彼的身份选择困境中解脱出来,这个过程也是她与自我身份及双重文化影响和解的过程。皮拉尔对于身份的困惑一直萦绕着她的整个青年时期,直到重回古巴,这个象征文化和解的回归之旅让她最终建立了身份获得了归属。而在此之前,皮拉尔则一直属于被双重边缘化的境地。母亲鲁迪斯的精神霸权和父亲的出轨让皮拉尔厌倦了在纽约的生活,“即便我一直生活在布鲁克林,这里对我来说并不是家。我不确定古巴是否是我的家,但我想弄明白,如果我能再见上外祖母西丽娅一面,我就知道我到底属于哪了”( 同上: 58) 。同时与古巴无法割舍的联系和想象中的认同深刻影响了皮拉尔自我身份的形成。她将印有古巴革命领袖切·格瓦拉头像的古巴革命文论集作为圣诞礼物送给母亲鲁迪斯,试图改变母亲对古巴革命者的偏见,促使母亲与古巴革命和解。她在母亲第二个面包店的墙上画了一幅布满尖钉的自由女神像,是作为边缘化族裔对美国主流文化的公然嘲讽。皮拉尔通过对古巴的美好想象来支撑与美国主流文化的对抗,然而回到古巴与外祖母西丽娅的重逢以及对古巴现实的认识让她最终意识到她想象中的古巴根本不存在,“从迈阿密坐飞机 30 分钟就可以飞过来,但这里却是永远无法到达的地方”( 同上: 219) 。皮拉尔开始剥除她想象中古巴的华丽外衣,认识最为真实的古巴---贫穷落魄、偏执不自由却人人经济平等,她看到这一切却依然无法否定她的古巴情结和她的古巴裔身份。古巴之行帮助她实现了与真实古巴的认同,也最终促使了她与美国身份的和解。“然而,我早晚都要回纽约。现在我明白,那才是属于我的地方---不是将古巴取而代之,而是与古巴并驾齐驱”。( 同上: 236)罗西欧·戴维斯( Rocío G. Davis) 认为美国少数族裔女性文学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她们的作品中都包含有爱怨交织的复杂母女关系,其中小说中的母亲往往带有鲜明的文化烙印,她们本身就是群体历史和价值的象征,女儿作为母亲的延续是一种不断完整的存在,她们与母亲以及祖辈女性人物关系的界定影响着她们对于自我族裔文化和身份的形成和认可( Davis,2000: 60) 。皮拉尔与母亲重回古巴与外祖母西丽娅相见,皮诺一家三代女性所代表的不同的历史和文化价值观由此碰撞,由于各自文化价值信仰的巨大差异,鲁迪斯与母亲西丽娅的和解只能通过她的下一代具有双重文化身份的皮拉尔来实现。在戴维斯看来,“这也正是族裔女性文学无法绕开的一种模式”。( 同上) 最终皮拉尔对外祖母记忆和叙事声音的继承则暗含了群体文化断裂后的修复和回归,移民他国的少数族裔也在精神回归的过程中重建身份和愈合文化创伤之痛。
四、结语
古巴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当政后,年幼的加西娅在古巴至美国的第一批移民潮中跟随父母移民至美国纽约,古巴少数族裔处于主流文化中的失声使得移民家庭在古巴革命动乱中的创伤体验因处于边缘文化而不被重视,西丽娅书写皮诺家族创伤历史则是有意识地从创伤记忆中寻求苦难的根源,抚慰被压抑的民族文化创伤之痛。作为古巴至美国的第二代移民,皮拉尔强烈的寻根意识不仅为皮诺家族代际间创伤的愈合带来了一线希望,同时也抚慰了民族文化创伤之痛。《梦系古巴》展示了极端的政治信仰对于家庭和民族团结的巨大破坏力,西丽娅借皮拉尔的寻根之旅重拾被遗忘的家族记忆和民族历史,试图通过皮拉尔所持有的文化包容态度书写创伤记忆。这种书写避免了文学作为意识形态传声筒的工具性作用,宣泄了被压抑的民族文化创伤之痛,也为古巴裔美国文学摆脱狭隘的民族主义、实现文化和解提供了范式。西丽娅重新书写了历史,“国家-民族的‘文本’既非单义性又非单向性的暗示”( Mitchell,1996: 55) 也为不同文化间的沟通和理解建立了桥梁。
①萨泰里阿教,Santeria,一种新兴宗教,起源于古巴和巴西,由来自西非的黑人结合西班牙殖民者的天主教而创立,它结合了对传统约鲁巴神的膜拜以及对罗马天主教圣徒的膜拜( 李保杰,2008:110) 。《梦系古巴》中二女儿菲莉西娅因极度不幸的婚姻而信奉萨泰里阿教,又因宗教信仰的不同被父亲和姐姐代表的基督徒和母亲地表的无神论者所排斥,最后在孤独中死去。这也体现了古巴在宗教和文化差异上极低的容忍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