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美国当代作家唐·德里罗的作品《白噪音》中由空间、意识形态及心理建构的多元叙述视角, 表达了男主人公试图摆脱父权危机但最终失败、认清父权衰微局面的内心及行为的复杂特点。本文以《白噪音》为研究对象, 在福勒的叙事视角综合分析框架下对作品的叙事特征和表达效果进行研究。在空间视角层面, 以人物为载体的空间视角多维度展现了男主人公父权稳固的假象及危机;在意识形态视角层面, 人物间或冲突或契合的意识形态影响着男主人公维护父权的行为准则;在心理视角层面, 男主人公认清父权衰微的局面的过程得以生动再现。
关键词: 唐·德里罗; 《白噪音》; 叙事视角; 父权;
Abstract: This study takes the contemporary American Writer Don DeLillo's novel White Nois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explores its narra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expressional effect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Fowler's narrative perspective.It is found that the spatial perspective with characters as a carrier reveals the illusion and crisis of the male protagonist's patriarchy.From the ideological perspective, the ideological agreement and disagreement between characters are reflected in the code of conduct of the male protagonist to maintain his patriarchy.From the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the process during which the male protagonist realizes the decline of his patriarchal power is vividly presented.The multi-narrative perspectives of White Noise composed of spatial, ide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reveal the complicated inward and outward features when the male protagonist tries to get rid of his patriarchal crisis but ultimately fails and realizes the decline of his patriarchal power.
Keyword: Don DeLillo; White Noise; narrative perspective; patriarchy;
唐·德里罗作为美国当代文坛的杰出代表, 其作品多能全面反映美国当代社会的现实问题, 因此, 享有“美国当代社会复印机”之称。[1]其描写美国全景的叙事方法既传统又革新, 手法多样灵活。他擅长把不同人物的故事穿插起来, 乱中有序, 并能产生一种新颖奇异的美。自1971年出版处女作《阿美里卡纳》以来, 唐·德里罗一共写了十六部长篇小说、四部剧本、若干短篇小说和散文等。其中于1985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白噪音》是他的代表作, 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 被誉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巅峰之作。
自《白噪音》问世以来, 学术界对德里罗的兴趣一直在增长。第一本较有影响的着作是汤姆·勒克莱尔的《在循环中:德里罗和系统小说》, 他将德里罗置于“体系小说家”[2]之列。随后, 不少批评家将《白噪音》归为后现代文本, 如罗纳·德灵[3]将《白噪音》中的希特勒与小说中后现代社会的描述联系起来。路易斯·卡顿[4]认为小说具有十分浓郁的后现代主义色彩。亚瑟·M·萨尔曼仔细研究了德里罗的语言, 并指出我们这个世界的毒害犹如小说中“翻滚的黑色云雾般公式化的语言”[5]。保罗·莫扎特[6]分析了德里罗的语言并发现了寻求高尚的人道主义者。弗兰克·伦特里契亚[7]则从消费、身份危机、技术和自然与人类的关系等角度阐释《白噪音》。约翰·佛柔将《白噪音》置于现实主义流派, 认为“小说中对生活琐事的描写只不过是反映现实生活罢了”[8]。随着生态意识的不断加强, 理查德·克里基[9]、格伦·爱[10]、大卫·莫里斯[11]等评论家开始探讨《白噪音》中的环境危机。路德·海勒[12]则从女性主义角度提出该作品是男性气质的代表。还有一些评论家关注小说的叙事策略, 如肯尼思·米德勒[13]指出品牌的声音“使读者怀疑男主人公对个人叙述的控制能力”。威尔考克斯[14]则认为《白噪音》揭示了宏大叙事的瓦解。此外, 批评家们还讨论《白噪音》中的死亡问题。如阿诺·海勒[15]认为德里罗在《白噪音》中探讨日益普遍的技术使我们畏惧死亡。中国学术界对德里罗及其作品的兴趣始于李淑言[16]于1996年发表的关于《白噪音》的评论。随后, 朱叶[17]、方成[18]、杨仁敬[19]、朱新福[20]、张杰和孔燕[21]、陈红和成祖堰[22]介绍了德里罗及其作品, 分析了小说中消费主义、自然主义、后现代主义、生活符号化和生态意识等主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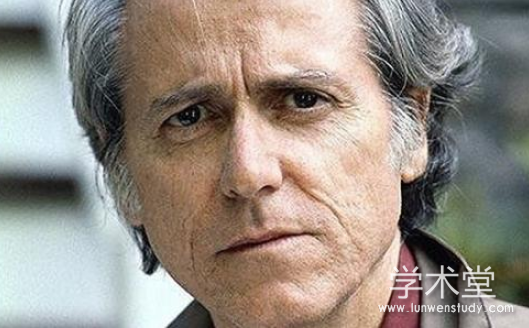
尽管国内外已有丰硕的研究成果, 但是《白噪音》的叙事视角并未引起研究者们的足够重视。在众多的批评家中, 英国文体学家福勒认为, 叙述视角包括时空、心理及意识形态三方面的含义[23]205, 并且分别从读者、人物及叙述者的角度来讨论文本的结构及叙述表达效果。本文将从这三方面来细读《白噪音》的叙事视角艺术特征, 从而挖掘作品的主题、人物性格以及心理的展现过程。
1、 空间视角
1.1、 学校空间
福勒将空间视角或空间眼光界定为“对故事中的人物、建筑、背景等成分进行建构”[23]205, 包括读者感受到自己所处的观察位置。在《白噪音》的开篇, 第一人称叙述者———男主人公杰克将不同的空间呈现给读者:“中午时分, 旅行车排成一条闪亮的长龙, 鱼贯穿过西校区, 向宿舍区前进。”[24]3读者随即被带入故事空间中, 身临其境, 感同身受。
男主人公杰克一出现就被打上了事业如日中天、享有极高社会地位的标签, 这正是其父权稳固的体现。作为山上学院希特勒研究所的主任, 杰克有着极高的学术威望。在同事默里看来, 杰克以希特勒研究为中心发展出了一整套体系, 任何从事希特勒研究的人都会提起杰克的名字。在杰克的课堂上, 学生们都带着“克制的恭敬和不明确的期待”[24]26。在办公室里, 杰克的三言两语就能帮助同事申请到本该属于别人的项目。这些看似支离破碎的叙述其实是通过不同的空间, 如“教室”“办公室”等被牢固地捆在了一起, 结构平稳, 使读者感受到整体的空间视角。在这些空间内, 读者看到的是一个游刃有余的杰克、意气风发的杰克、功成名就的杰克, 这正是杰克父权稳固的基础与表现, 是其在公共空间内地位不可撼动的标志。
随着叙事的推进, 披着权威学者华丽外衣的杰克时刻流露出不安和不自信, 其父权稳固的假象在学校空间内逐渐出现了裂痕。作为山上学院的中心人物, 杰克却不得不在校长、德语老师等多位人物之间周旋, 显得有心无力。在校长的建议下, 他将名字杰克·格拉迪尼改为J.A.K.·格拉迪尼并戴上古怪的墨镜, 以表现其作为希特勒研究者的严肃性。虽然其妻子认为新名字“暗示着尊严、荣誉和重要性”[24]17, 但改名并未为其带来公共空间内地位的稳固。德里罗曾在一次采访中表示:“改名意味着纯真和重生”[25]3-15。这有一定的道理, 但并不适用于杰克。表面上, 杰克通过改名进一步巩固了其在公共空间的威望, 获得了“重生”。但实际上, 他“好像穿了一件借来的外套”[24]17, 如同“被名字牵着鼻子走的假人”[24]17。但没有这些外力, 杰克又觉得自己无法教授希特勒课程。这种个人威望摇摇欲坠的危机嵌入了杰克的学校空间, 动摇了其在公共空间内稳固的地位, 进而打破了其父权稳固的假象。
在学校空间内, 杰克父权稳固的危机还表现在他作为希特勒研究所最着名的人物, 却完全不懂德语。在学生都至少学过一年德语的环境之下, 杰克“生活在奇耻大辱的边缘”[24]33。德语之于杰克既是“阿喀琉斯之踵”, 又是扞卫父权的工具。他被迫向霍华德讨教德语, 然而从每次课程开头的沉默尴尬气氛, 再到中途霍华德以几乎脸贴脸的方式观察杰克喉咙的古怪举动, 无不流露着整个学习过程的荒谬可笑。希特勒研讨会也以极具讽刺的方式证明了杰克德语学习的无效。当杰克在研讨会上用德语作主旨发言时, 他表现得活像一个小丑。更滑稽的是, 他的主旨发言内容涉及的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内容, 如希特勒的母亲、兄弟和狗。这一系列的空间展示无不暗示着杰克“父权稳固”假象背后的重重危机, 预示着杰克看似平静的生活将展开另一画面。
1.2、 家庭空间
在小说开篇, 对杰克住处的特别描写, 将读者随即从学校空间带入到杰克的家庭空间,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遵从着传统性别分工的婚姻家庭模式。历经四次婚姻的杰克与芭比特组成了美国典型的后核家庭, 双方都离过婚, 子女众多。身为一家之主, 杰克过着幸福的中产阶级生活。他承担着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妻子芭比特则本分地充当着贤内助的角色, 将家务料理得井井有条并照顾着众多孩子。她唯一的工作是作为志愿者教老年人如何站、坐、行走和如何正确地饮食以及给盲人读书。在家庭这一空间内, 妻子芭比特仍受传统性别角色规范的约束, 杰克的统治地位似乎不可动摇。
在家庭这一私人空间内, 杰克看似不可动摇的权威也面临着多方挑战。首先, 杰克的多任前妻就已然留下了父权衰微的隐患。其第一任妻子———做间谍工作的达娜乐使他卷入“家庭阴谋”[24]53。第二任妻子特薇迪“出生在一个显赫古老的家族”[24]235, 该家族具有“当间谍和反间谍的悠久传统”[24]235, 而且她“拿走了他所有的钱”[24]97。第三任妻子珍妮特是一位外国货币分析员, 为秘密团体做研究。在这三任妻子身上, 读者无法看到对丈夫杰克的爱和牺牲。她们在精神上和身体上都没有显露出弱势, 甚至比杰克更强势。她们代表着不受家庭束缚的女性。与她们同处家庭这一空间下, 杰克的父权遭到严重削弱。而服从传统性别角色分工的现任妻子芭比特虽然让杰克感受到了“甜滋滋”[24]6的报答, 但其传统性别角色的背后仍旧隐藏着对杰克父权的威胁。同处卧室这一空间下, 杰克与芭比特常在深夜互相倾诉。杰克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与芭比特之间能彻底地袒露胸怀。然而在讨论谁先死的问题时, 双方都向对方隐瞒了自己对死亡的恐惧。同时, 芭比特还向杰克隐瞒了她在服用祛除死亡恐惧的“戴乐儿”药物的事实, 并将药瓶藏在浴室内。随着空间的转换与叙述的演进, 读者进一步得知芭比特为了换取“戴乐儿”, 与药物的研发者格雷在旅馆发生了性关系。可以说, 婚姻欺骗了杰克。这些来自妻子对父权的威胁使得杰克的父权面临严重挑战, 也使得杰克感到强烈不安。他甚至通过“好像受创的潜水艇驶入修船码头一般”[24]189枕在芭比特两乳间以寻求慰藉。此时, 杰克作为丈夫的父权受到严重的威胁, 但令人惊讶的是, 他仍然依赖芭比特获取安全感和慰藉, 希望能够有一个母亲似的人物陪在身旁, 这种在家庭空间内的需求进一步揭露出父权稳固假象背后的危机。
其次, 作为多位孩子的父亲, 杰克稳固的父权早已蒙上阴云。杰克尤其享受与怀尔德一起的时光, 因为怀尔德在某种程度上扞卫了杰克的父权。杰克不止一次到怀尔德卧室里看他睡觉, 并感到说不出的精神振奋和情绪高涨, 这份出于父亲的保护是显而易见的, 同时也是原始的, 与生俱来的。如此看来, 杰克在家庭这一私人空间内的父权并不稳固, 因其总是需要借助一些独特的举动展现其对孩子的保护甚至是控制, 以获得内心的安定。同时, 杰克的地位也多次受到孩子们的挑战。在这个孩子众多的家庭之内, 杰克一直试图扮演“控制者”的角色, 致力于拉近孩子之间的距离;同时他又身兼“调停者”的角色, 一旦出现矛盾, 就立即站出身来化解冲突。杰克试图把控大局, 但事与愿违。在厨房内, 孩子们在吃饭前叽叽喳喳, 但一到饭桌上就全然沉浸在各自的世界中, 怪异的沉默气氛时常令人费解。每次在超市购物时, 各位孩子兴奋不已。一旦驾车回家, 都各自窝进房间, 长时间独处。于是, 杰克在家庭这一空间内不断被边缘化, 试图掌控全局又无能为力, 试图营造家庭和睦的气氛却一筹莫展, 因而父权面临严重的挑战。
父权危机正是通过“厨房”“卧室”等多个空间清晰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 使读者深切地感受到杰克虽然名义上是一家之主, 是家庭的经济来源与主要决策者, 但他已经面临来自妻子和孩子的多方挑战, 稳固父权的背后是重重危机。
2、 意识形态视角
“思想立场”是福勒阐述意识形态的内涵时所使用的术语, 作品中的人物在充当叙述者的时候所表达出来的价值观是意识形态视角的核心内容。[23]206-243随着叙事的演进, 杰克平静的家庭生活被空中毒物事件所打破。杰克与同事以及与孩子的对话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杰克与其他人物在意识形态上的冲突与契合, 意识形态的冲突与契合又融入到杰克维护父权的行动之中, 成为杰克维护父权的指导准则。
杰克始终用自己的一言一行证明其与同事默里在意识形态上是契合的, 因其始终借助默里的意识形态来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父权。在与杰克的对话中, 默里表示人类是被满世界充满敌意的事物所包围着的脆弱生物, 人类的幸福和安全时时受他们的威胁, 而“家庭的进程是向着封闭世界发展的”[24]91。尽管在杰克看来, 这个理论是极其荒诞的, 他认为无知和混淆不清不是家庭抱成一团的驱动力, 但他却用自己的一言一行证明他就是这套理论的信徒。当其家庭受到来自毒物事件的威胁时, 杰克秉持着这套原则, 立即采取近乎掩耳盗铃的方式, 将其家人与外部世界“敌意的事实”完全隔绝开来, 以期维护其作为父亲的绝对权威。在空中毒物事件的初始阶段, 杰克始终保持置身事外的姿态, 他坚信毒物并不会波及到自己的家庭。但当儿子海因利希要求杰克对此观点做出解释时, 杰克却闪烁其词, 只能搬出“就是”“它就是不会”“我就知道”“他们就是会”[24]122-125等一系列苍白无力的说辞。此时杰克希望家庭与世隔绝, 对威胁视而不见, 以此来维护他在家庭中的绝对权威。但毒物不会因为这套说辞而消失, 毒物的不可预测性使得杰克奉行的准则摇摇欲坠。随后的意识形态冲突似乎已经无关毒物是否在靠近, 而是取决于杰克如何看待形势的演变, 或者说取决于杰克如何竭力维护其早已动摇的父权。随着毒物不断靠近, 杰克认为海因利希提供的数据不重要, 重要是位置, “它在那里, 我们在这里”[24]129。接着, 化学物质开始大面积溢出, 位置的说法已然站不住脚。此时, 海因利希则显露出对生命和技术的发展有着更丰富的知识储备和透彻的理解, 他似乎正在取代杰克作为家庭智慧象征的地位, 杰克维护父权的行动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挫折。
随后默里俨然成为杰克的“精神导师”, 杰克将默里的价值观与信仰奉为圭臬, 付诸到更加疯狂的维护父权的行动当中。对于杀人, 默里颇有个人的见解, 他认为对付死亡的方式之一就是杀人, “一个人杀的人越多, 征服死亡的力量就越大, 暴力只不过是一种再生的模式”[24]322。他不断鼓动杰克成为杀人者, 让别人沦为死亡者。恰巧的是, 作为听众的杰克此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父权危机, 其妻子为了获取克服死亡恐惧的药物“戴乐儿”, 连续多月与药物的项目经理格雷发生性关系。怒不可遏的杰克一直试图寻找格雷, 为了维护男性的尊严而打算采取报复行动。此时默里颇具煽动意味的话无疑是一剂强心针, 激起了杰克内心早有苗头的想法, 只不过杰克并未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内心深处魔鬼的一面。当杰克听到默里输出这一套有关杀人的论断时, 他显得将信将疑, 认为自己一辈子都在做死亡者, 无法成为杀人者。但随后, 他立刻将这套准则付诸行动, 先是随身携带自动手枪, 使自己完成从死亡者到杀人者的转变。随后精心策划了一场杀死格雷的阴谋, 企图将谋杀变成格雷的自杀。由此, 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到, 杰克从根本上赞同默里的价值观与信仰, 究其原因就在于默里的意识形态极佳地迎合了杰克维护父权的意图。
杰克的孩子们理解世界、与世界互动的方式挑战着杰克持有的准则, 与杰克截然不同的态度折射出互为抵触的意识形态。杰克选择负隅顽抗, 企图维护遭受威胁的家庭核心位置。对于孩子们来说, 听外界的声音、关注外界的动态是理解世界的最有效方式。因此, 他们选择完全依赖外界接连不断的信息流来获取灾难的最新情况。杰克的女儿斯泰菲的“怀疑”似乎完全源于收音机的广播, 杰克从心底产生了疑问, 难道“斯泰菲从收音机中听到了幻觉”[24]138?杰克问斯泰菲为什么水一定要烧开, 斯泰菲回答“收音机里说的”[24]36。儿子海因利希在阁楼观察空中毒物时, 时刻听着收音机里的消息。而杰克对此种方式是不屑的、反对的, 他希望隔绝外界的“噪音”, 保持不受外界影响的状态。但是“敌意的事实”仍然通过孩子迥然不同的价值观入侵了杰克营造的隔离世界, 掩耳盗铃已然不具备可行性, 积极对外界做出反应成为了形势的需要, 对外界影响的妥协与接受标志着杰克维护父权行动的失败。最终, 杰克不得不放弃对家人的控制, 从而保护他们。换言之, 他需要听外界的“噪音”, 这噪音既是危险的源头也是获取保护的途径, 这一点在小说的末尾得到了最好的证明。小儿子怀尔德骑着自行车穿过高速公路, 这显然是父亲的疏忽造成的。但是过往骑摩托车的人停了下来救了怀尔德, 摩托车手将孩子举高的姿势仿佛象征着一种胜利。此时的杰克宛如一个陌生人, 一个束手无策的旁观者, 真正使怀尔德回归安全状态的反而是杰克一开始就试图剔除的来自外界的“交通噪音”, 也就是他企图隔绝在外的“敌意的事实”。结尾这一幕几乎是以讽刺的方式证明杰克一度奉为圭臬的意识形态的无用与错误, 他企图重建的父权早已千疮百孔。
3、 心理视角
福勒认为心理眼光又称感知眼光, 属于视觉范畴, 它表达了观察者由谁来担当的问题。[23]210-236小说中男主人公杰克试图保持不变的平静生活遭到扰乱。先是被迫离家出逃, 后是报复计划流产。无论杰克身处何处, 其对小说中其他人的想法贯穿小说全程。德里罗从心理视角刻画了杰克波澜起伏的内心世界, 这是直观的语言所无法描绘的, 因而生动再现了杰克逐渐意识到父权衰微现实的心理世界。
杰克作为一位父亲为读者提供了可靠的观察者形象, 他将孩子的形象通过不同的画面清晰地传递给读者, 使读者能够感受到杰克逐渐意识到自己正被边缘化, 父权正走向衰微的事实。在逃难中心, 叙述者杰克将自己与儿子海因利希进行对比。读者能够直观获取杰克的所看、所听、所想:作为父亲的杰克在“一个最挤的人堆小心翼翼地游动”, 却吃惊地发现海因利希“身处事态的中心”。海因利希正从专业的角度谈论着毒物事件, 他的“口气几乎是预言式的揭示”, 他的“化学知识新颖、现代”[24]143。他不想让儿子看见自己在那里, 随后就悄悄地走开了。当妻子芭比特问杰克为什么海因利希不和父母谈论这些, 杰克解释说海因利希可能厌烦自己。芭比特又问杰克为什么不走过去, 杰克说父子关系会“让他难堪并受约束而毁了全部好事”[24]148。在解释的过程中, 杰克对海因利希的称呼也经历了“我自己的儿子”到“这个青春期男孩”的演变, 这一指称上的变化也进一步透露出父子关系的疏远。透过杰克立体的观察, “边缘”与“中心”的鲜明对比得以呈现出来, 作为观察者的杰克显然已经意识到海因利希正在取代其在家庭中的核心地位, 自己渐渐被推到了家庭的边缘, 父权受到了严重威胁。因而杰克最终不希望被儿子看到, 选择了离开。
不单单是海因利希, 杰克的女儿比伊也使杰克意识到自己正不断被边缘化的现实。杰克将一直跟前妻生活的女儿比伊接到家。短短不到两天的相处时间, 杰克却时刻感到不自在和郁闷, 仿佛对自己“生命的意义提出质疑”, 同处一个屋檐下的比伊在杰克看来有着“温柔的居高临下的方式”[24]108。他们长期未一起生活的事实使父女十分疏远。“我听见她说”“我见她”“我不想”等一系列话语表明读者获得这些感知的途径是透过杰克的所看、所听、所想, 是由杰克这一人物充当观察者来完成的。杰克作为一位观察者传递女儿的形象, 使读者明白杰克已渐渐意识到父权正走向衰微的现实。
作为一个可靠的观察者, 杰克对父权丧失的意识清晰地体现在他对格雷的形象刻画上, 脑海中格雷的形象变化揭示出杰克的心理变化过程。起初, 格雷是强大父权的象征。他是位科学家, 是“戴乐儿”药物的项目经理, 也是将渴望获取克服死亡恐惧药物的芭比特引诱到旅馆床上的交易者。在芭比特坦白性交易这一事实后, 震惊不已的杰克不断在脑海中刻画旅馆中的格雷和芭比特的形象。他像格雷一样看到芭比特“依赖、顺从、情感上被俘虏”, 感觉到格雷“地位的支配性”[24]265。在实施谋杀计划前, 杰克曾无数次将格雷描绘为类似的形象。因此, 读者看到的格雷拥有着男性的掌控力和对女性的强烈占有欲, 与软弱无力的杰克形成了鲜明对比。
最终, 杰克见到了格雷先生。作为近距离的观察者, 杰克并未将格雷刻画为一个集中的、权威的父权形象。相反, 他是无组织的、分散的, 没有展现出能使杰克的复仇行为合理化的侵占他人妻子的丑恶男性形象。与其说格雷是一个掌控力极强的侵占者, 不如说他是一个父权衰微的体现者, 是软弱无力的象征。见到格雷的杰克告诉自己:“这位就是折磨我的那个灰不溜秋的人物, 那个偷我妻子的男人。”[24]342即使杰克想要与格雷殊死一战以扞卫父权, 但这场战争是没有实质性意义的, 因为取胜也并不意味着战胜篡夺父权的敌人。因此, 谋杀计划流产了。当杰克朝着格雷的腹部开了两枪后, 就将枪放到了格雷先生的手里, 企图制造这是一起自杀案的假象。但格雷并没有死, 他扳动扳机打中了杰克的手腕。此时, 杰克并没有奋起反击, 而是从心底感到惊讶、失望。他对格雷的敌意在此刻也彻底崩塌瓦解。此时的杰克在某种意义上经历了“顿悟”, 不过却是饱含消极色彩的“顿悟”, 蕴含着他对个人父权衰微现实的清晰认识。他开始从心理上与格雷产生共鸣, 认为格雷是他的难兄难弟, 因而第一次把格雷“当作一个人来看待”, 还感到“他们俩的命运连在一起”[24]349。在去医院接受治疗的路上, 杰克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格雷了。从本质上说, 无论是杰克还是格雷, 二者都代表着软弱无力、面对父权衰微却无法改变现实的男性。正如芭比特所说的, 格雷只是一个“多人组成的综合体”[24]211。格雷这个名字只是她为了方便起见, 给所有与她进行过性交易的多位研发人员随意起的名字。因此, 杰克脑海中的格雷也只是“四个或更多的灰色皮肤的人物”, 是没有权势、“没有自我、没有性别, 执意要指挥我们摆脱恐惧”[24]265的人。借助杰克的视角, 读者清晰地看到了杰克戏剧化的转变———从一开始将格雷视为其父权的剥夺者, 并试图谋杀他, 到最后认清事实, 意识到格雷与自己一样, 都是父权衰微事实面前的无能为力者, 这样的剧烈转变透过杰克的心理视角清晰地展现出来的。
4、 结语
叙事视角在当代文学理论及文学批评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其作为一种研究角度, 在理论与实践层面上将作品的分析带入了更加广阔的视野。本文以叙事视角的方式对美国当代作家唐·德里罗的《白噪音》进行的分析呈现出该作品的艺术特征与表达效果。从空间视角来看, 家庭空间、学校空间等不同空间的多维转换揭示了男主人公父权稳固的假象及假象背后的危机;在意识形态视角层面, 男主人公与其他人物在意识形态上的契合和冲突表现为维护父权行动的指导原则;在心理视角层面, 男主人公作为可靠的观察者, 向读者清晰展现了其认识到父权衰微的心路历程。无论是叙述的空间、意识形态亦或是心理, 《白噪音》中的人物视角都清晰地表达出男主人公企图维护父权但失败并最终认清父权衰微事实的内心及行为的复杂特点。因此, 这三个视角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并共同作用于展现男主人公焦虑、挣扎与放弃的全部过程。遵循这三个叙事视角的轨迹能够挖掘作品深刻的主题意义, 从而加深和拓展读者对作品的认识。
参考文献
[1]康立新.论唐·德里罗小说的生态之殇与叙事拯救[J].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6 (5) :138-143.
[2] LeClair Tom.In the Loop:Don DeLillo and the System Novel[M].Urbana and 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7.
[3] Dunn Robert G.Identity Crises:A Social Critique of Postmodernity[M].Lond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8.
[4] Caton Lou F.A.Romanticism and the postmodern novel:three scenes from Don DeLillo’s White Noise[J].English Language Notes, 1997, 35 (1) :38-48
[5] Saltzman Arthur M.“The Figure in the Static:White Noise”White Noise:Text and Criticism[M].Ed.Mark Osteen.New York:Penguin Books, 1998.
[6]Maltby Paul.The romantic metaphysics of Don DeLillo[J].Contemporary Literature, 1996, 37 (2) :258-277.
[7] Lentricchia Frank.New Essays on White Noise[M].Ed.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8] Frow John.“The Lasting Things Before the Last:Notes on White Noise”White Noise:Text and Criticism[M].Ed.Mark Osteen.New York:Penguin Books, 1998.
[9] Kerridge Richard.“Small Rooms and the Ecosystem:Environmentalism and DeLillo’s White Noise”Writing the Environment, Ecocriticism and Literature[M].Ed.London:Zed Books Ltd, 1998.
[10] Love Glen.Ecocriticism and science:toward consilience?[J].New Literary History, 1999, 30 (3) :561-576.
[11] Morris David.Environment:the white noise of health[J].Literature&Medicine, 1996, 15 (1) :1-15.
[12] Helyer Ruth.“DeLillo and Masculinity”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Don DeLillo[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13] Millard Kenneth.Contemporary:American Fiction[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14] Wilcox Leonard.Baudrillard, DeLillo’s white noise, and the end of heroic narrative[J].Contemporary Literature, 1992, 32 (3 :346.
[15] Heller Arno.“Simulacum vs Death:An American Dilemma in Don DeLillo’s White Noise”Simulacrum A-merica:The USA and the Popular Media[M].New York:Camden House, 2000.
[16]李淑言.《白噪声》和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J].外国文学, 1996 (6) :58-64.
[17]朱叶.美国后现代社会的“死亡之书”[J].当代外国文学, 2002 (4) :159-163.
[18]方成.后现代小说中自然主义的传承与塑型:唐·德里罗的《白色噪音》[J].当代外国文学, 2003 (4) :93-99.
[19]杨仁敬.用语言重构作为人类的一员的“自我”[J].外国文学, 2003 (4) :22-25.
[20]朱新福.《白噪音》中的生态意识[J].当代外国文学, 2005 (5) :109-114.
[21]张杰, 孔燕.后现代社会的诗性特征:生活的符号化[J].外国文学研究, 2006 (5) :40-44.
[22]陈红, 成祖堰.《白噪音》的叙事策略与文体风格[J].当代外国文学, 2009 (3) :76-84.
[23]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24][美]唐·德里罗.白噪音[M].朱叶, 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3.
[25] LeClair T.“An interview with Don DeLillo”Conversations with Don DeLillo[M].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