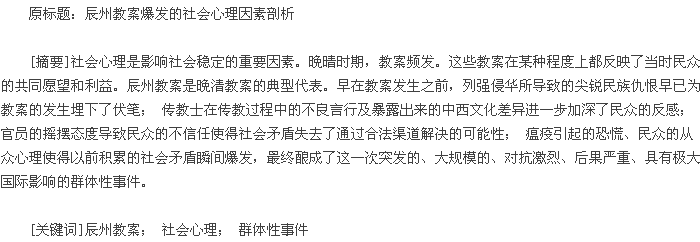
1902 年( 光绪二十八年) ,地处湖南偏远西部山区的辰州府发生严重教案。教案发生过程中,两位 内 地 会①的 英 国 传 教 士 胡 绍 祖 ( J. R.Bruce)②、罗国荃( R. H. Lewis)③被殴毙,教堂被捣毁,酿成严重的中外交涉。结果,所有涉案文武官员均受到严厉惩办。“已革辰州营都司刘良儒即行正法,统带毅字总兵颜琼林定为斩监候,参将张姚魁、桂阳营参将赵玉田革职永不叙用,辰州府知府吴积銞革职,永不叙用,并流五年。已革署沅陵县知县万兆莘充发极边,永不释回”④。普通民众中,张白狗、何家二老、李老六等十余人被杀⑤。此外,还需赔款一万英镑( 约合白银八万两) ,划天宁山前后为新建教堂所用,并于辰州府衙署门外东侧树立“永远儆戒”碑⑥。
据统计,1840 年至 1912 年间,中国发生大小教案多达 1600 余起。学者们将其统称为“晚清教案”⑦。辰州教案即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众所周知,影响历史进程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社会心理即是其中之一。自法国年鉴学派将心理因素作为影响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之一始,社会心理成为了历史研究的新视角。本文拟以辰州教案为例,从社会心理的角度出发,对辰州教案前后所反映的下层民众、士绅、传教士、地方官员、清政府的社会心理进行剖析,从一个侧面解释教案爆发的原因。
一、由西方列强侵华所引发的中国民众的民族仇恨
“人们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⑧从某种程度上说,利益冲突是人类社会一切冲突的根源。具体到辰州教案而言,西方列强入侵中国所引发的民族仇恨是辰州教案发生的根本原因。
自 1840 年英国强行用洋枪大炮打开中国的大门以来,列强蜂拥而至。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相继签订,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也引发了中国民众对于外国侵略者强烈的民族仇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既使得中国主权逐渐沦丧,也给当时的中国民众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以湖南为例: “咸丰、同治朝时,湖南省每年的财政收入约为二、三百万两白银,地方尚能维持运营。”①然而,自“甲午中日之役后,复岁摊赔款数十万两,至是本省财政,乃益形艰窘”.②《辛丑条约》签订后,“湖南省摊派的赔款金额达 70 万两,每月须缴纳白银58333 两3 钱3 分,另加俸饷、旗兵加饷、加增东北边防经费、漕折 4 项,每年需上缴白银304000 两,每月须上缴白银 25333 两 3 钱 3 分,两项加起来,每月合计需缴纳白银 8366 两 6 钱 6分”.③此外,“1900 年的衡州教案赔偿英国福音堂、天主堂 386000 两”④。赔款摊派数额的不断增加,加剧了湖南财政的窘迫。而这些款项当然是由湖南人民来偿付。俞廉三⑤在奏报中清楚地说道: “伏查湖南今年出款。以赔恤衡州教案为最巨。现在新增偿款( 指庚子赔款) ,为数更多,且须常年摊派,势不得不取之民间。”⑦为了解决摊派的钱款问题,俞廉三先是采取了“加重抽征田房赋税的办法”,因收效甚微,后又“将湖南省淮盐每市斤加价四文,全省绅民报效户口捐,亦每口加抽四文”.⑧即便如此,还无法完全解决湖南财政的窘迫。俞廉三只能增加土药税捐,甚至在田赋项下再增加“口捐”⑨一项。苛捐杂税的增加加速了农民的破产,同时,也使得中国民众对西方列强的屈辱感和仇恨感不断加深。在审理辰州案件的过程中,张白狗就曾坦率地说道: “胡教士是我用木棒打死的。我恨‘洋人'.因为他们侵略我们的国家,残害了我们的同胞。”⑩传教士尽管并非侵略者,但他们传教权利的获得是通过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而获得的,自然也成为民众仇视的对象。自 1880 年起,清政府就在列强的压力下被迫开放湖南的传教权,相继将“常德、辰州、沅州、永顺、澧州等 4 府 11 州所属 20 县及乾州、永绥、凤凰、晃州等 4 厅”开放为允许传教的区域。从表面上来看,湖南的大门已经向传教士打开,但实际上,开放的大多都属于偏远地区,而民众对传教士的反感则进一步加深,传教活动并没有因此变得容易。19 世纪 60 年代,《湖南阖省公檄》及《辟邪纪实》等宣传反洋教的小册子在湖南省内的广泛传播清楚地表明了湖南民众对于传教士的反感。一位传教士在书中无奈地写道: “尽管这个省真的向传播基督开放,但人们心中仍然存留着迷信和仇恨,这些邪恶的力量随时都会造成大的破坏和灾难。”
对于“山岳重叠,苗胞多居于其中,因绞痛阻滞,文化低落,生产落后,……加之迷信深重”的辰州地区而言,传教工作则显得更加艰辛。修承浩在《沅陵县志》中清楚地写道: “地方风气未开,洋人来,众已恶之。”①传教士的传教工作到处碰壁。在胡绍祖和罗国荃全面开展传教工作之前,内地会就曾派遣传教士管耀清②来辰州传教。“活动半年,仅有两人入教。”③由于管耀清传教不力,故而被英国驻汉口领事馆召回,由内地会传教士胡绍祖与罗国荃取代管耀清前往辰州主持传教活动。来到辰州后,两位传教士积极开展活动,取中国名字,穿中国服饰,说中国话,并高价租佃府仓巷孙姓民房为教堂,另租一间房作为医院,以行医看病为手段拉拢百姓入教。尽管两位传教士想尽办法,但入教者人数寥寥,甚至那些“少数的入教者也遭到周边百姓的谴责与唾弃”.④辰州传教工作之艰难可见一斑。更重要的是,其中所反映出的民众将传教士视为西方侵略者的代表,对他们所采取的敌视态度。
二、传教过程中传教士的言行不当导致辰州民众对传教士反感的加深
两位传教士在辰州传教过程中生活的不检点,更是加剧了民众对他们的厌恶。长期在沅陵地区进行田野调查的钟玉如先生在访谈中发现:两位传教士在辰州府传教过程中常常“与劣绅、痞棍为伍,逛街市、蹲馆子”⑤,完全不顾及其传教士的形象。更有甚者,他们还干涉教徒与非教徒之间的诉讼,“用金钱收买情报,包揽词讼”,⑥引起辰州百姓的极大反感。在教案过程中,当两位传教士受到民众追击向当地富绅修承鸿求救之时,依旧狂妄地允诺: “事平之后,富贵悉听尊便,准保汝为即补州县,走马上任; 一万两( 银子) 亦可立条照兑。”⑦可见,众人的反感并非全然空穴来风。胡绍祖还经常在大街上随意吼斥百姓,唾骂辰州人“落后”、“愚昧”、“是三等公民”,并扬言要“对辰州人严厉惩治一番”⑧。这些话落到辰州民众耳中,如何能不引起他们的反感呢?传教士传教过程中所凸显出来的中西文化差异又进一步加剧了辰州百姓对他们的嫌恶。辰州府自古以来就由宗教文化多元、传统文化盛行的特点。他们祭祖、祭天,崇尚“天地君亲师”的正统思想。自然,这些传统思想也成为人们评判事物好坏的标准。然而,基督教属于一神崇拜,禁止入教者崇拜祖先、神灵。这样一来,一神信仰与多神崇拜的冲突、宗教仪式与伦理风俗的冲突、外来宗教与本土宗教的冲突日益尖锐,从而使得民众内心产生强烈的憎恶感。中西文化的差异和矛盾不仅反映在宗教生活中,也体现在世俗生活方面。
两位传教士来到辰州之后,雇佣素有放荡之名的寡妇萧张氏主理家政,“呼之为张小姐”⑨。一个寡妇与两位男子频繁往来的情景落在辰州民众的眼中,引起了对三者关系的诸多猜测。许多居民都认为两位传教士与萧张氏通奸,对其更加厌弃。
三、瘟疫爆发导致的社会恐慌
如果说辰州教案发生之前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已经为教案的发生埋下了伏笔的话,那么,由于瘟疫的爆发而导致的社会恐慌则是教案发生的导火线。
1902 年( 光绪二十八年) 6 月间,辰州城内爆发严重瘟疫。患者的症状主要有: “( 一) 腹痛,上呕下泻、脚跟抽筋,不到对时即死; ( 二) 要呕不呕,要泻不泻,腹内绞痛,脚部抽筋,约半月即死; ( 三)四肢麻木,口不能言,身发高热,饮水不止,死后遍身青紫。”⑩关于此次瘟疫,当时身处辰州城中的事件亲历者修承浩在《沅陵县志》中载到: “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六月,城中疫起,症极危,而传染又速。旬日之间,城厢皆遍,蔓延及四乡,死人日多,人心惴惴,朝不保夕。……延至七月,疫不止,城乡死千余人。人心愈恐,……”由于瘟疫蔓延,城乡死亡人数短时间内就“超过千数”.一时间,人心惶惶,例如: “为了保护水源,百姓用木栅围护井口,并派人日夜巡守,以防有人投毒。更有甚者,不取井水,而绕远取食河水。唯恐近岸有毒,于是将船划至河心取水。挑水的木桶皆盖上盖子,派人随后防护,唯恐有人中途投毒桶中。”①百姓的恐慌之深由此可见。
强烈的社会恐慌导致民众普遍陷入危机感之中,谣言随之而来。瘟疫发生过程中,福音堂的医师罗国荃也在接待病患,但救治无效,病人先后离世。为了预防瘟疫,罗国荃常在清水中撒些粉末,或是放些颗粒状的药物,说是消毒。当时即有百姓怀疑: “只因百姓既不乐信教,复惮于就医,教士为之束手,以致出此下策,俾使百姓信其药石灵验,因势诱导,以传其教。”②谣言越传越广,导致社会恐慌越演越烈。教案发生前,早已有人在墙上粘贴揭帖,指责“传教士往城中央供应人们日常生活用水的水井中投毒”.③由于谣言肆虐,本地传教者张百顺曾劝说两位传教士去知府吴积銞家避难,但遭到两位传教士的拒绝。“七月十二日,溪子口地方有不知姓名人拾得药末一包,声称入手即肿,痞徒贾三谓系有人放毒,约同尹牛儿、李老六及在逃之孙章发等在该处搜查。因萧张氏在宋烟馆吸食洋烟。形迹可疑,即扭住该氏,于其身旁搜出藿香丸一包,指为毒药为据。”④萧张氏在拳脚之下被迫承认。一时间,群众大量聚集。教案随之发生。
而事实上,正如修承浩在书中解释的那样:“是岁之疫,发源于城内杏浒冲。冲介两山间,纳城外诸山之水,濠宽而深。居民不知卫生,平日倾渣滞濠中,岁久填满,直与地平。数十年不挑深。春夏骤雨,水泛滥无所归,溢入两旁民宅深一二尺,人尽苦之。是年春,里人雇工挖壕。取出秽污,不倾于河,皆堆于路旁,长数十丈,高与人齐。五六月,阳气蒸发,奇臭横流。路人掩鼻急趋,胸中扰作恶欲吐。居于是者,朝夕薰染,受毒自深,故疫作而死人独多焉。愚民不察,乃归咎于洋人,草菅人命,酿成国际交涉,并衍成地方一大辱史,岂不冤栽,岂不谬哉! ”⑤简而言之,是恶劣的卫生状况和炎热的天气导致了瘟疫的横行。而官方的解释是: “因惧生疑,因疑致误。”⑥在后来的审讯过程中,张永太甚至供认: “萧张氏所拿药包,系藿香丸两粒,并非毒药。”⑦由此可见,谣言虽然是在瘟疫横行的背景之下开始传播的并直接导致了教案的发生,但究其原因,除了瘟疫造成的恐慌以及民众对于医药知识的匮乏之外,其根源却是民众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痛恨以及“胡、罗以特权者的身份种下恶果”.
四、民众的从众心理以及责任扩散效应
从众是指“个人的观念与行为由于群体直接或隐含的引导或压力向与多数人相一致的方向变化的现象”.⑨群体性事件的初期往往有很强的从众色彩。在此方面,辰州教案也是表现得十分明显。俞明颐在写给湖南巡抚俞廉三的公文中描述道: “孙章发复觅得铜锣,令幼童高老二鸣锣聚众,谓已拿获放药之人。喝令每户各出一人,将萧张氏送官究办”.⑩其后,“有一人以竹竿高挑药粉纸包,向群众宣布事情始末,一致肯定瘟疫之起,系由洋人贻害所致”.立时,百余人应声而至。孙章发高呼: “打洋人去! ”众呼: “赶走洋鬼子! ”沿途观看的越来越多,游行队伍愈来愈大。而从后来被惩办的“凶手”名字来看,如: 张白狗、贾三、王大、尹牛儿、李老六、高九老儿,他们连正式的名字都没有,可见,这些教案中的积极参与者大多来自社会下层。其中许多人并非有明确的目的和意图,仅是怀着对侵略者的痛恨,在从众心理的促使下参与到其中。
在群体性事件过程中,参与者普遍有法不责众的想法,认为群体决策分散了责任,使得任何一个人都用不着对最后的选择负责任,因而,他们采取的行动往往比个体独处时更加激进、冒险。在被“正法”的“凶手”中,何家二老仅有十四岁,只是一个茶馆的学徒会审时,庄庚良问: “你系乳臭小儿,也敢打洋人?”他答道: “我平日最怕洋人,岂敢打他们! 只是在洋人被打死后,我踢他一脚是实。”①从众心理使得大量民众参与进来,而责任扩散效应使得参与则采取了偏激的行为,使得教案越演越烈,最终酿成了这样一场后果严重、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教案。
五、官府的摇摆态度导致社会公正缺失以及民众的不信任感
社会公正既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也是社会稳定和谐的前提。社会公正的缺失将会导致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而信任感的缺失又是导致社会关系对立和对抗的重要因素之一。因为在民众担心自己的合理要求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往往容易在冲动之下采取非法的手段来解决问题。这样一来,便提高了群体性事件爆发的可能性。
辰州教案发生之前,传教士与中国民众之间的矛盾、冲突已经暴露出来。然而,随着清政府日益沦为列强侵略中国的工具,政府不仅不思平息民愤、保护民族利益,反而坚决站在西方列强一边,弹压中国人民,对各地方政府三令五申“切实设法保护各处教堂、教士人等”②,规定“借端滋扰报复者,即捉拿正法,毋稍宽恕”③,甚至警告地方官员,“惟闻得该处营官坐视旁观,毫未弹压,应请先行彻查”④。1900 年,衡州教案发生后,俞廉三负责处理教案。由于事情直到案发后近五个月才结案,因此,俞廉三被追究“疲软蒙谴”⑤的罪责。此外,衡州教案结案后签订的《衡州法国天主教案议结合同》中规定: “出示保护教士、教民身家,以后不得阻挠教民奉行教规,亦不得族谱削名,并勒派迎神赛会诸冗费; 倘有教士复来湖南传教,应由地方官妥为料理,沿途护送,认真保护。”⑥清政府对传教士的肆意包庇产生了两个不良后果: 一是造成了地方官员在处理涉及传教士事情时的摇摆态度。地方官员作为中国人民的一员,就内心而言,他们并不愿任意牺牲国家利益和民众利益,甚至他们本人也对洋人极为仇视。据《中外日报》载: 统领颜琼林就对洋人颇为仇恨,“有一次其部下某武弁与教士交好,竟被开去差使”⑦。另外,他们治理地方,与民众直接联系,更不愿意因此而得罪同胞,被冠以卖国贼的恶名。
因而,对涉及传教士的纠纷时,为了避免清政府的追责和民众的反感,他们往往采取能躲就躲、能拖就拖的态度。辰州教案爆发之前,其实民众对传教士的不满和怀疑已经十分明显。“迨 7 月 26 日( 光绪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竟有在墙遍粘揭帖,传此恶言”⑧。两位传教士将揭帖抄写一份送到知府吴积銞处,希望他能平复谣言。然而,吴积銞“孤傲自大、官气尤深,平日不接见士绅,不接触百姓,不体察民情,不了解当地风俗”⑨,对此坐视不理。而时任沅陵知县的万兆莘“已卸职离任,交印一日,只待休息五日后离开沅陵,故不理政事,民情诉讼一概推诿”⑩。七月初十,“百姓扭送有”投毒“嫌疑的邓铁匠和蕲老八到官府,万兆莘既不审讯,也不收押嫌疑犯”,以致民众以为官员不管此事。当时初来辰州筹办邮政局的供事薛亨也因“相貌略似洋人习惯早期散步”而引起百姓怀疑,成为人们攻击的对象。案发前,他“闻有匪徒将往攻之说,乃以文凭往见知县,请为示禁,知县亦允之而不为”.于是,他转而求救于知府吴积銞,但又被推诿,要求他找知县。总而言之,尽管教案发生之前,早有多方面的情况表明传教士已经成为众矢之的,教案一触即发,但地方官员却视而不见,没有及时调节传教士与民众的矛盾,甚至没有采取措施将二者隔离开来。
教案发生之后,聚集的民众在前往福音堂的过程中,先后途经沅陵县署和巡防毅字营统领衙门。然而,前知县万兆莘并未出面调解。时任防营统领颜琼林尽管得到了消息,却以“未接到府、县通知,不可妄动! ”①为由,不允许士兵予以制止。而辰州府营都司刘良儒早在半月前即未经上级批准前往沅陵柳平乡一带巡视。因此,被民众追击的传教士罗国荃逃至营署时,营弁“闭门不纳”②。在整个事件发展过程中,唯有刚刚到任的沅陵知县陈禧年积极投身于教案的处理之中。但由于他势单力薄,且参与群众人数太多,情势难以控制,最终只保住了被群众扭打的薛亨,却无力制止民众追击传教士,其本人也在此过程中受伤。地方官员的漠视、拖延使得政府失去了将矛盾消灭于萌芽状态的最好时机。
教案结束后,地方官员作为清政府在地方的代表,为了贯彻政府的命令,也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纷纷倒向传教士一边,维护传教士的利益。当知府吴积銞听闻两位传教士被殴致死,深感大祸临头,竟然咬牙切齿地说: “百姓要我前程,我要百姓脑袋。③”为此,他竟然“封锁教案消息,诬称土匪谋叛,报省请兵”④。而巡抚俞廉三一反处理衡州教案之旧态,“办理极为迅速认真”⑤,立即电谕张之洞提出从严处理。他“将辰州府知府吴积銞,甫经到任一日之调署沅陵县知县陈禧年,均奏参撤任,留于地方协缉,听候查办,或以革职留缉之处”⑥并委托沅陵东关厘金局总办何俊廷署理知县。后,何俊廷处理教案之时,也丝毫没有手软,严令差役限日捉拿凶手。三天之内,官府便即逮捕嫌疑犯三百多人。另一方面,对于普通大众而言,无论是官府的肆意包庇还是拖拉态度,实际上都导致官府失去了民众的信任。在涉及传教士的冲突中,民众宁肯选择自己解决,也不愿通过官府途径解决。
综上所述,辰州教案的发生其根源在于教案发生前,中国民众心中早已根植的对西方侵略者的痛恨; 传教士的胡作非为、中西文化的差异进一步加剧了民族矛盾; 瘟疫的爆发以及谣言的传播是教案的导火线; 最后,在地方官员的不作为和民众从众心理的推波助澜之下导致了规模浩大、后果严重的辰州教案。辰州教案虽已处理完毕,但清政府对西方列强的妥协、对传教士的偏袒却进一步加深了民众对于外国侵略者及清政府的痛恨。正如《中外日报》上所发表文章《论辰州教案》中所评论地那样: 辰州教案处理过程中,英国“逞其势力,逾其分以相施,并波及无辜之人,是使内地人民益增其仇恨外人之心而已。犹冀其永远相安,是犹南辕而北其辙也。”⑦据教案亲历者张浑回忆,在运送“永远儆戒”碑的过程中,民工随口作歌: “岩头哥呵,上府坡呵---嗨嗨呵,红毛鬼子害人多呵; 岩头王啦,上府堂啦---嗨嗨啦,皇帝老子狠心肠啦; 岩头神呀,上府坪呀---嗨嗨呀,有仇不报枉为人呀。⑧”这也是辰州教案受到从严从重处理,但之后教案依然频频发生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