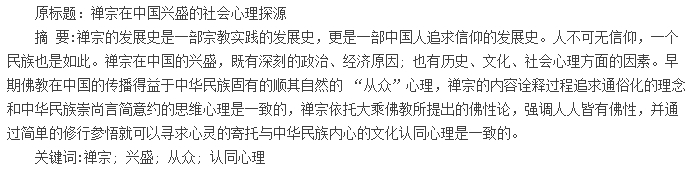
禅宗的兴盛史,是一部语言的发展史,也是一部宗教实践的发展史,更是一部中国人追求信仰的发展史。人不可无信仰,一个民族也是如此。在社会转型期,缺失信仰的部分中国人从形式上在皈依某种宗教,但没有多少人能理解自己信仰某种宗教的目地究竟是什么,我们的精神家园究竟又在哪里? 禅宗在今天中国局部的繁荣,让人们看到了人们回归、渴望精神安宁的迫切性,同时也给佛教界、宗教理论工作者等提出了许多严肃的课题! 看到遍及中华大地各地寺院的重建的恢宏态势以及众多知名网站的佛教栏目的火爆,我们依稀看到了芸芸众生那渴望信仰、追求内心安宁的眼神,同时也提醒我们宗教理论工作者应该为他们去做些什么。
在建设 “美丽中国”的伟大事业中,我们既需要富足安康的物质文明,也需要抚慰心灵的精神追求。禅宗契合了中国人的心理诉求,其简单的修行方式也便于当下的中国人追求内心的宁静。只是时代变了,禅宗的语言、修行方式也应华丽地转身以更好地适应这个时代的人们的心理需求。
一、早期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得益于中华民族固有的顺其自然的 “从众”心理
诞生于印度的佛教,其兴旺发展的地方却在中国。佛教自公元前后传入中国就一直演绎一个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佛教在中国所走的发展之路,一方面有其内在自身的逻辑发展轨迹; 另一方面,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和传统的中国儒家文化及道家文化之间难免有一个冲突、融合的过程。纵观整个佛教的思想发展史,佛教在中国的兴旺发展时期,也是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最好的时期。禅宗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国本土化的佛教派别之一,它的兴衰发展已经完全融入到了整个传统文化发展的脉络中。禅宗在中国的兴衰史,既有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也有历史、文化、社会心理方面的因素。禅宗被中国民众广泛接纳和笃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因为它的传播方式契合了中华民族顺其自然的内在心理。也正是中国这一特殊的 “文化心理气场”
为禅宗在中国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最佳的环境。
第一,早期佛教的传播方式巧妙利用了中国人崇尚自然、注重直觉的哲学思维方式。社会心理学理论提示我们: 一个人的认知模式和行为模式都会受到一个群体内在心理特质的影响。千百年来在中华传统文化架构下积淀而成的中华民族固有的心理特征时常会影响到每一个人行为举止。许苏民先生在其 《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简论》中曾指出:中华民族对外显现了一种崇尚自然 “赞天地之化育”的参与精神; 在思维模式上则强调将部分与全体的交融互摄; 在致思途径上表现为一种借助于经验基础上的直觉法去洞察对象的本质,以求把握宇宙和人生的根本原则。
可见中国人历来有崇尚自然、重直觉的思维心理。孔子曰 “默而识之”,就是倡导直觉的思维方式。老子则说“道”只能意会不能 “言传”。东晋的王弼提出“言不尽意”的观点。关学的创始人张载在其 《正蒙》一文中则说: “穷神知化,乃养盛自至,非思勉所能强”。可见上述学者都是强调直觉思维方式在认识自然与社会中的重要性的。佛教在中国要想生存发展就必须适应这一环境。实际上,佛教刚刚传入中国的时候就面临着三大难题: 一是如何面对来自传统中国儒家文化的冲击? 二是佛教本身的逻辑思维方式如何转向以适应中国人的惯常的心理思维方式? 三是怎样化解来自传统道家哲学的拷问?
这几个问题对承载佛教传播使命的人来说是不得不要去仔细思考的问题。西汉末年,“谶纬神学”的兴起而形成的神学思潮足足影响了东汉整个时代。
神秘主义的盛行,使得中国人内心深处不免产生了一种面对现实生活的困惑和焦虑,对自己的未来和归宿产生了严重的不安,于是乎再一次去重新审视董仲舒的神秘的 “天人感应”学说,将自然、人事勉强地结合在一起来论证社会中的一切事物和现象。就如中国流传的民间俗语所说的那样 “天意从来高难问”。当一个民族的内心世界逐渐偏离理性主义的轨道时,就只有顺其自然依赖神秘的直觉来把握人生的未来了。加之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主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逆来顺受的心理,这就为佛教传入中国后提供了一个利于其传播的 “心理温床”。佛教是一种主张人生要出世的宗教理论,它与中国儒家强调纲常名教,即修身、齐身、治国、平天下的伦理践行方式是格格不入的。然而深处于东汉末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人民一直饱受战争之苦,人民连安居乐业的基本要求都保证不了还谈何政治理想信念追求呢? 当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发现现实生活中的追求各种物质利益、精神快乐的各种通道均被堵塞之后,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文化,其强调人生、社会是苦海,世间 “一切皆苦”,而主张人生应寻找解脱脱离苦海之道的理论受到中国人的关注,也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
第二,佛教的早期传播方式与中国人的 “从众心理”。众所周知,无论如何准确地翻译佛典,由于中外话语系统的差异,要完全再现佛教经典的本来意义是很难的。一种文化现象要吸引人的关注,其最初的传播方式必须符合当地环境中人们的审美心理需求。佛教传入中国的早期,由于信息的闭塞及传播手段的局限性,加上语言翻译 ( 后文详加论述) 等方面的障碍,其生存空间受到了很大的约束。因此佛教在中国要有所发展,佛教经典的翻译问题是绕不过去的。佛教经典本身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有很大的差异,在文字、话语系统等方面都有不同之处。另外,中外之间在一些重要的观点诠释方面也有许多不一致的地方,因此我们不难理解早期佛教经典的传播为什么要依附中国道家的相关语义来加以宣传自己的教义,这种做法的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当时中国民众的关注。因为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佛教经典的翻译依然是一项打基础的工作,佛教本身若想在中国发展,没有创新,不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很难有大的发展空间的。
我们知道,一种文化要赢得人们的关注,首先必须要能吸引人的 “眼球”。社会心理学上有一种 “从众”现象,所谓 “从众”心理是指单个人受到了来自外部人员行为的影响,从而使自身的判断、认知等行为表现与大众的舆论及多数人的行为方式呈现出趋同性。从众行为对个体的社会适应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任何时候,在一个群体社会中,不管是从人类文化传承的角度还是单单就社会功能的执行而言。大多数人的行为和信念保持一致是很重要的。这是人与人进行交往的必备条件,也是社会正常运转的一个前提。中国的民众从了解佛学开始,再到接纳佛学,到最后主动去改造佛学并逐渐使之中国化而达到禅宗的发展阶段,这些佛经的翻译者们和传播者们实际上是仔细研究了中国人的文化审美心理的。佛教从开始不为中国人所知到后来能拥有如此之多的信众,并不仅仅是完全依赖其自身的信仰内容,同时也应关注它的理论的说服力并着眼于对人类自身的心理活动的研究。佛教早期经典的翻译和教义的传播就比较注重翻译方式与中国传统哲学和中国美学的渊源之间的关系。例如支谦提出的 “不加文饰”到道安的 “案本而传”以及唐朝玄奘提出的 “文质统一,圆满调和”等理论无不显示了这些大翻译家们精通中国人强调简约的阅读心理。西方接受美学的创立者饶思曾指出,由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翻译者既要保持原文的精华部分,同时也要注意接受者 ( 读者) 的阅读审美心理。从中国流传至今的佛教经典的翻译文本来看,多数佛教经典的翻译从两汉开始直到隋唐,都一直贯穿了这一个原则,一方面保持佛教经典本身的玄妙深奥; 另一方面又从理论上阐释,论证并告知大家 “人人皆有成佛”的可能。或许那时的许多中国人只是从形式上接受了佛学,并没有从心底完全接纳它,但佛教引起中国人的关注却是不争的事实。
直到今天,当下许多信佛者身上依然表现出了这种 “从众”心理: 我未必清楚佛是什么? 我不知道佛法丰富的内涵? 我不清楚虔诚礼佛的复杂仪式、步骤是什么? 但很多人在神面前都烧香、都跪拜神灵,愿菩萨保佑自己,他们可以这样做? 我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去做呢? 因为佛教已经用 “不可思议之妙说”深深地吸引了中国人,也为很多中国人所认同。在这种心理行为当中,我们依稀可以看到中国人 “跟着感觉走”的追求人的直觉判断、“顺其自然”的心理影子。
二、禅宗的内容诠释与中华民族追求简洁的知识表达方式的心理不谋而合
我们回顾包括佛教等各种外来文明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常常会发生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外来文化往往会被中华文化所吸收和同化并有所发展。
传统的中国文化主张求变创新, 《周易》当中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句话最能体现传统中国文化的变革精神。佛教传入中国后,其内容要为中国人所理解,就必须研究了解中国人的审美阅读心理,就应该有一个依据中国的文化氛围重新诠释和革新其内容的过程。作为佛教中国化的最完美的代表———禅宗,其教义蕴含了丰富的精神智慧,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诠释方式,或者偏离了中华民族所喜爱的追求知识的特有的心理思维模式,是很难得到芸芸众生的认可的,更不用说兴旺发达了。纵观禅宗的思想发展史,自达摩初祖到六祖惠能时期的禅宗,无不在禅宗的内容诠释方式方面做了大胆的改革才使得当时的禅宗发展表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第一,禅宗的内容诠释追求通俗化的理念和中华民族崇尚言简意约的思维心理是一致的。任何经典文献只有经过系统的诠释方能显示其固有的魅力。我们知道心理需求是人们追求宗教信仰的一个重要因素。宗教作为非理性化的世界观也是人类生存发展的一种精神上的一种需要。中国人关注佛教、信仰佛教教义是从了解佛教的经典教义中逐渐得到启示的。例如佛教用简明的语言所传递的“因果业报论”的教义,很契合中国思维心理。
“神明在上,苍天有眼”、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等语词表达方式通俗易懂。
这些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的观念给那些佛教的信徒们在心理上带来了一种极大的震撼,亦满足了人们弃恶扬善的心理需求。所以,一直以来佛教经典文本的翻译及诠释即便到了禅宗初祖达摩时期依然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佛教发展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期,逐渐进入到了一个普及的时期。只是源于印度佛教的经典教义过分追求抽象的表达方式与中国人强调简约的思维心理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许多当时的中国文人最初都有畏难的情绪,更不用说普通民众了。为了打开佛教经典的阐释与中国民众的强调的简约心理一致性的通道,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支谦、道安、僧肇等人通过不懈的努力对印度佛学进行了改造,期间还借鉴了中国儒家的心性论的观点,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人的理解的语言表达方式才深深赢得了中国人内心的心理认同。这些学者将中华民族强调直觉、悟性的思维心理融入到对印度佛教经典教义的阐释与表达中。这其中表现为两方面: 一是普通民众渐渐认识和开始接触佛教; 二是部分僧众在理论上加强了经、律、论的研究。为佛教的大规模的普及奠定了一个理论基础。佛学中国化的衔接点是玄学,玄学简洁的语义表达法在魏晋时期受到了当时社会的普遍欢迎,其中突出的内容诠释方式便是以义疏体来阐释经典。 “玄学重思辨,注重对三玄义理的理解,不纠缠于章句的义疏体自然受到欢迎。而由于文本的特点,佛经传入时,一般人在阅读理解上颇觉困难,而讲疏体由于能够理清条贯,会通文理,使经义显明,因此自道安之后,佛教学者注经,也往往采用疏体。”
因为疏体形式是那个时代流行的阅读形式。另外,我们注意到菩提达摩对 《楞伽经》的研究就提出了后来禅宗所涉及到的佛性问题: 众生皆有 “如来藏自性清净心”,这便是佛性。众生皆有佛性,即只要你潜心学佛人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菩提达摩将 《楞伽经》视为 “印心”,他对于 《楞伽经》的研究和注释,并不是专注于逻辑上论证,而是从理论层面论证开始,再到结论的提出尽量让高高在上的 “佛和佛法”回到 “平凡的人间”,这就使得当时的中国民众从心理层面开始逐渐接受了佛教。
这也为佛教的中国化打开了一个时间之窗。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达摩禅法强调众生必须理解佛教的经典理论,从而建立自己的信仰。这是修行禅法的基础,并明确提出教义是行动的向导。同时要求弟子讲法时必须关注语言表达的通俗性,他将 《楞伽经》传授给慧可也可见达摩的一番苦心。达摩用通俗、简洁的语言强调佛教经典理论与禅法修行二者之间的关系的方法深得当时民众的普遍欢迎,这也是禅宗受到日后众人关注的主要原因。
第二,禅宗的内容诠释的语言表达强化简洁的方式符合中华民族的惯常阅读心理。“与佛教其他宗派相比,禅宗的实践明显地更贴近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因而其语言也更明显地具有一种本土化的倾向。”语言学研究的出发点是为了寻找到语言表达的内在的发生规律及诠释的逻辑表达结构。
不同时代的、不同时期的人们都有不同的阅读心理。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在谈到语言的深层结构时曾指出: “语言是一个体系,也就是一种先验的结构,与人们日常的言语不同。语言的特点并非由语音和意义本身构成,而是由语音和意义之间的关系构成一个网络,成为一个语言体系,这就是语言结构。这种语言体系被看成是一个符号体系。”
禅宗自达摩初祖到六祖惠能,有关禅宗教义内容的诠释已经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语言 “符号体系”。日本学者忽滑谷快天将禅宗达摩到六祖这个时期的禅宗发展史概述为 “纯禅时代”; 而将六祖之后的中国禅宗称为 “禅机时代”。前期的 “纯禅时代”对佛法内容的诠释大多遵循简洁质朴的原则,语言表达上显示出朴实无华的特征。而后期的 “禅机时代”则由最初的简洁而演变为机锋转语。禅宗由“不立文字”转变为 “不离文字”; “不用文字”逐渐变为 “善用文字”。比如马祖道一提出的说禅过程中诸如 “竖拳”、 “斩猫”、 “声喝”、 “举佛”等方式的使用。从形式上看,似乎玷污了佛的庄严肃穆,但这种说禅的简洁方式恰恰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大道无言,大道至简”的阅读心理。“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因为佛法如“道”一样是一个难与言说的东西,假设非要诠释的话也只能如惠能所说的那样: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 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禅宗大师们深深洞悉中国传统文化中用语言表达真理时简洁风格。追求的是将深奥的禅法理论诠释行为回归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行为当中去,让众生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去领会佛法的内在含义。换句话说,“道在平常日用中”。
在中国历史上,人们内心深处推崇 “知简行易,以简则易知,易知则易能”的获取知识的心理。看 《论语》、 《老子》等经典乃至 《金刚经》等文献,在使用语言表达真知灼见时特别崇尚简洁的表达方式。这表明中华民族崇尚言简意约的心理在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语言作为思维的工具,人类的理性思维若离开语言这个工具是很难进行的。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曾说: “从自身的存在中编织出语言,在统一过程中他又将自己置于语言的陷阱之中; 每一种语言都在使用该语言的民族周围划出一道魔圈,任何人都无法逃出这道魔圈,他只能从一道魔圈跳入另一道魔圈。”
禅宗前期的教义诠释遵循简洁明了的方式,深得众生的欢迎。遗憾的是禅宗自宋以后逐渐衰微,其主要的原因是那些所谓的 “狂禅”的出现,原本强调佛法阐释重简洁的方式逐渐演化为只是变为形式上的一种丑陋的表现,变成了只是注重玩弄语言文字游戏的禅法解说方式。禅宗鼎盛时期提倡的 “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以心印心”的语言宗旨逐渐转变为 “不离文字,滥用文字”,这种状况的持续加剧了禅宗内部分分化和斗争,其发展势头渐渐走上下坡路也就不足为怪了。世间的事物往往就是这样,越复杂化越繁琐反而离真理越来越远…… 《金刚经》上佛陀告诉我们: “法无定法,无有定法可说”,禅宗的兴盛发展之路难道不正是这样吗?
三、禅宗强调自由的修行方式与中华民族内心的文化认同心理是一致的
源自印度来到中国的禅学,只是印度多种佛教修行方式的一种。参禅修行主要是通过调整身心来进行内心体验的一种修炼方式。禅学在进入中国之后,逐渐揉合吸收了了魏晋玄学及老庄哲学的观点才变成了我们所熟悉的中国化的禅宗。禅宗之所以能为中国普通百姓所广泛接纳,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禅宗追求自由的不受拘束的修行方式与中华民族内心的文化认同心理是一致的。
第一,禅宗自由的修行方式赢得了中华民族的心理认同。中华民族的心理认同是建立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氛围中的。它一方面强调民族文化心理的差异性,另一方也认识到各民族文化优越性是建立在有益于自身发展的基础上的也就是其包容的心理。任何外来文化能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就接受它。佛教在传入中国后逐渐为中国人从心理上认同是因为它首先从心理层面尊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教。包括禅宗在内等改造后的佛教派别,其内在的佛教教义以及所强调的学佛的过程就是儒教所倚重的先学做人。这样佛教徒们的责任就和儒教所崇尚的人生使命感巧妙地结合起来了。其次,禅宗之所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和禅宗发展的过程特别注重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分不开的,也就是中国人内心所推崇的人的觉悟只有依靠自身的努力。这样的禅宗,中国人很 “熟悉”,它受到人们的关注也是很自然的事。禅宗有别于中国其他宗教派别,它虽然不推崇经典,但说禅修行的过程引用经典却随处可见。但就这一点而言,无论是禅宗当中的南宗还是北宗,二者都有类似的描述。不过仅就参禅修行过程来看,以神秀为首的北宗提倡渐悟; 而以惠能为首的南宗则提倡顿悟。
我们知道,禅宗将大乘佛教的佛性论视作其修行的重要理论基石。在这之前,自晋宋时期的竺道生提出 “人人悉有佛性”的观点以来,后经由 《大般涅槃经》的介绍弘扬,实际上中国佛学理论界就进入到了一个 “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的新阶段。赖永海先生在其 《中国佛性论》中曾指出,禅宗提出见性成佛、直指人心的理论和道生的 “人人悉有佛性”是一脉相传的。这种理论的提出意味着普通百姓都有机会接近佛学并接受佛法,让普通民众看到了自己能成佛的希望。我们知道宗教尽管有其神圣庄重的一面,但它终究是要面向现实社会人生的。禅宗的修行方式能直面当时中国的现实状况,一方面固然有为适应当时环境有关; 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尽快能得到中国普通民众的心理认同有关。事实上,惠能和道生一样提倡人人皆有佛性,他曾说 “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所说依此修行,西方只在眼前。”他后来又说: “人即有南北,佛姓 ( 性) 即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惠能强调佛性应该平等,说明他对当时社会不平等的等级制度深恶痛觉。他还强调: “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没意智。”
道生和惠能的上述观点和传统中国伦理道德秩序中强调 “人人解可以为尧舜”的说法也是一致的。参禅的过程也就是悟的过程,禅宗的修行抛弃了繁琐的仪式,主张坐、卧、住、行都可以参禅,如惠能所言: “迷时师度,悟时自度。”修行的原因你不用去管,禅悟的曲折过程你也不用去计较,重要的是在禅悟的仪式中认识你自己。如马祖道一所说的那样: “马车不走了,要打马而不是打马车。”禅宗这种追求自由简单的修行方式在立足中国特有国情的基础上更容易赢得中国民众心理上的认同,也比其他宗教派别更具生命力和发展前途。
第二,禅宗直面现实的修行方式符合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心理,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人的宗教认同心理的内涵。在部分学者看来,中国历来无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因此也就谈不上有所谓的 “宗教认同心理”。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人淡于宗教。钱穆教授认为,宗教是西方文化体系中的重要项目,中国文化中不自产宗教。作家张爱玲也认为,中国人是没有宗教可言的,中国的智识阶级这许多年来一直是无神论者。
我们并不认可这种结论,一个民族有无宗教信仰应看他将这一问题置于何种坐标系中来考量。中国是一个注重伦理道德文化传统的国度。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是一部充满苦难的艰辛的历史,不论在物质层面还是在精神层面,每一步的发展都伴随者巨大痛苦,这似乎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但中华民族就是在这样的境遇中一步步走向自己的辉煌。我们不排除在历史上的一些时期,老百姓所面对的苦难远远超出了他自身所能承受的能力,因此皈依某种宗教也就成了一种他们的选择。例如从东汉以来,中国的社会秩序就一直处在一种十分混乱的时代。在这样一个痛苦的时代,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处在哀伤的状态中。没有一个人不希望能从这种苦难的状态中迅速解脱出来。对于生活在苦难中的普通民众来说,他们迫切需要一种精神信仰上的寄托,佛教从那个时代得到中国人的关注,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国不光民间宗教派别繁杂多样,而且许多外来宗教亦能在中国生存发展。
中国民间众多民众见神就信、见神就拜的现象足以说明中国有浓重的宗教信仰氛围。禅宗依托大乘佛教所提出的佛性论,强调人人皆有 佛性,并通过简单的修行参悟就可以寻求心灵的寄托。禅宗对处于苦难徘徊中的人来说,可以借虚幻的途径从心理上得到抚慰从而摆脱现实社会令人绝望的困境,爱因斯坦曾说如果世界有什么宗教能够符合现代科学的标准的话,那只有佛教。和禅宗同时代的佛教派别还有很多,如唯识宗、天台宗和华严宗等。他们或因过分侧重繁琐的理论证明来解释佛教教义 ( 如唯识宗) 或者因所宣传的教义内容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有冲突的地方而没有注重协调、融合而失去了发扬光大的机会 ( 如华严宗) ,此后皆销声匿迹。禅宗独自兴盛是因为其简单的修行方式与中国儒教和道教的观点不相违背,一方面文化知识缺乏的人容易理解它的教义和修行,另一方面也引起知识分子士大夫的心理认同,有普及的民众基础。另外禅宗在不断发展过程中继承了佛教的全部要义,有极强的生命力,这也是禅宗超越其它宗教教派而成为中国佛教主流的原因。也是禅宗深深得到中国人的心理认同的。
综上所言,禅宗能在中国繁荣发展并最终得到中国人的心理认同,很大程度上在于它能将印度佛学中部分教义精神,以中国人所熟知的简易方式表现出来并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种人人都认同的修行方式。将佛法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积极的相近的内容巧妙地结合起来方赢得了芸芸众生的认可。
参考文献:
[1] 许苏民 . 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简论[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
[2] 汤用彤 .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M]. 北京: 中华书局,1983.
[3] 周裕锴 . 禅宗语言[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4][转引]刘放桐等编著 . 新编现代西方哲学[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5][转引]卡西尔 . 语言与神话[M]. 北京: 三联书店,1988.
[6][转引]石峻 等 . 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二卷第四册[M]. 北京: 中华书局,1983.
[7][转引]沙莲香 . 社会心理学[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