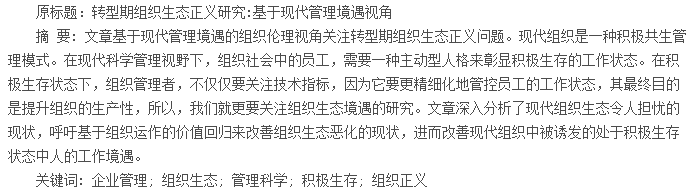
一、引言
在传统社会中,人的生存状态是求安、求稳的,而资本主义社会以来的现代社会人的欲望,被积极诱发。在无限制的商业竞争中,组织中的员工不得不去积极生存。19世纪50年代以后的现代激励理论更是从身心视角、多元化利益视角等诱发人的积极生存状态。在现代组织管理中,员工的积极生存状态的变迁可以理解为,由自发的积极生存到自觉的积极生存,进而商业运动员式的奔跑状态的变迁过程。对此现状,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同程度地感同身受。人的这种生存状态该如何理解?本文认为,这是一种借用技术支配进而激发组织中员工的积极生态境遇。而组织境遇的健康发展需要组织运作重视技术支撑和利益诱发的同时,还应关注组织正义研究或说不同类型组织中的环境正义研究。
这是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竞争性组织运作的应然要求。不过,在组织管理学界,对此的相关研究,还很少。而在美国管理转型期,有一些学者基于工业民主的大环境,在关注组织中人的身心状态问题,对转型期组织中人的生存状态的诊断,有一些理论心得。这值得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管理学界的学习与借鉴。在这其中,作为管理学开拓者的管理思想家福利特就是深处美国进步时代社会转型背景下关注组织成员生存状态的专家。她较早开启组织管理境遇价值关怀的先河。她在组织场域基于价值回归在工业民主探讨大背景下,与谢尔登、朗特利、莉莲·吉尔布雷斯等人一起来探讨组织中人如何更积极的生存问题,引领了这方面的讨论,从而被现代管理学家厄威克、赫茨伯格、麦格雷戈、本尼斯等管理学者认可。
中国当下组织发展整体状态也类似于美国转型期的组织发展境遇。因为中国转型期的组织发展仍处于重视技术支撑和利益诱发的时期。在这种状态下,已经出现“富士康事件”等令组织生态运作堪忧的事实。虽然富士康领导人一开始想基于利益为主导的假设改进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但这种导向仍是一种基于经济人的假设,仅仅从这种视角看问题,事实证明是不够的。本文认为,现代组织中的员工,需要积极生存,但诱发员工去积极工作不能仅仅靠心理技术支撑下的利益诱发机制,还需要在组织生态场域呼唤人的价值回归,所以说,重塑组织生态学的环境正义研究,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必要性。
二、从组织生态学到转型期组织生态学
组织生态学是一个借鉴生态学的理论、概念、思维与方法来诊断组织内外部关系的学科。在学科定位上,它属于衍生性交叉学科。从组织生态的学术谱系概况来看,它有三种路径:第一种是管理生态学,它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高峰期,分为1930年代梅奥从组织社会学视角以霍桑实验为切入提出的非正式组织思想路径;1970年代末兴起的组织文化或企业文化研究路径;1990年代兴起的积极心理学研究路径。管理生态学路径是一种宽领域的组织生态学研究视角。第二种是行政生态学研究路径,美国的高斯开行政生态学之先河,里格斯的行政生态学研究也为世界所瞩目,行政生态学实质是一种利用比较方法研究行政环境的广义的组织生态学;第三种是新制度经济学视野下的商业和经济的关系研究路径。
本文基于管理学视角,主要关注第一种研究类型。我们不研究一般的组织生态学理论及其历史,而是关注中国转型期管理理论创新需要重视转型期组织生态的构建与批评分析,因为它更需要积极借鉴国外相关管理理论的合宜经验,基于此,我们从处于梅奥社会人时期的组织生态大视野下,通过关注美国管理转型期对组织与人关系的论述,批判地考察并吸收与中国管理发展阶段相匹配的的合宜管理经验。
三、组织生态的现代技术支撑与人的积极生存隐喻
何为积极生存的人?对此,可以从以下几个取向得到体认。
(一)“螺丝”与“螺母”的关系
现代组织生态学认为,在现代组织中,个体人与组织的关系,不仅仅是大机器流水线与零部件的关系。个体人不是静态的孤立的原子,不能被简单的量化,然后被“加总”。支撑个人的世界观不应仅仅是以经济利益为诱发的机械的原子论人生观。个体与组织的关系,可比作机器零件,却是螺丝与螺母的“相配”关系,意指个性的彰显只有得益于深入的与社会关系互动,才能得以体现。更关键的是,这种“相配”关系暗示了,螺丝与螺母的配套关系是辩证的。螺丝与螺母有相配关系,但一个螺丝或一个螺母,并非与一个特定的螺母或螺丝相配。
社会组织中的个体人的亮点,应既要体现其个性,又能体现其深处社会组织关系之中的整体性、职能性。组织中的成员是个体我,但不是孤立的自我之我,它也应该能够拥有团体意识,其主体角色可以升华为“团体之我”(Group-I)———“我们之我”(Weself)。个体我的角色,经过自我反思或他人引导,从“自我之我”可以升华为“我们之我”,以便使个体的社会经历、工作经历得以丰富。这种升华是为了承担责任,而非逃避义务;同样,个体我的角色也可从“自我之我”升华为“他者之我”,这种升华是为了化解矛盾,以利于共赢。这就是身处组织关系中拥有关系思维的自我。这种自我是为了克服种种消极共生现象并基于乐观的建设性的态度走向积极共生。这一点被组织文化研究者和后来兴起的组织积极心理学的研究者得以更深入的认可、拓展和践行。
(二)被动与主动的社会生态
组织生态学认为,组织社会中的员工是一个有生命力的力量存在,因主动参与到组织关系中为组织目标而积极奋斗而获得如鱼得水之感,进而有可能把潜能转化成强大的为组织而奋斗的现实力量。对此,可以这样理解,作为社会存在的人,不仅仅是物理个体,而是精神力量的存在,而精神力量的相互融合,造就了个人与具体组织的积极共生关系。个体人“不是一个单位(units),而是力量(forces)中心(向心力和离心力)”,从而使“它(在能量上)辐射和汇聚、交叉和再交叉”。
组织中的个体创造性是个体生命力旺盛的体现。但这种状态不可能在自发、无为的状态中产生,它需要积极的、持续的有策略的引导,才能得以展现。
也就是说,人之个性,不可能在自发、无为的模仿中展现。因为模仿仍是人被动地适应环境的表现,更关键的是,习惯于模仿的人,最终只能被量化处理,进而失去个性,而且模仿其本质就是跟从、随大流。有个性的人不能随大流、无主见,否则,长此以往,将失去人的主体性,最终也将意味着在社会参与中逃避责任,在组织中做一个不称职的员工。
四、组织成员的积极共生态
组织生态学认为,个人不是先单独造就出来,然后才被投入到社会中。因为人只有越参与公共生活,与社会组织关系越紧密,个人、组织与社会环境才能越处于积极共生关系之中。组织与成员之间的共生关系就是组织生态研究的重要内容,这种共生关系,就是转型期组织生态学研究的焦点话题。因为它能塑造并引领社会、组织与个人间的积极的良性的生态关系。个人以社会组织关系为之立;组织成员以积极的共生关系为之生、为之荣。基于此,转型期个人与组织能否有积极共生关系,值得关注和深入研究。
现代组织中的个体我,追求平等———淡化阶级意识、身份意识、血统论等造成传统社会序列关系中“位格”意识的种种痼疾。但,个体不追求平庸,而以多样化的个性追求自尊进而得以自立、自强。个性不是守拙,而需要去彰显,需要深度地融入广泛的组织关系中。个人需要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勇于面对困境、承担责任的气魄和勇气。即个体我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是一个活在当下又希望拥抱未来的兼有理想主义和干事创业的实干家(doer-thinkers)角色定位。
因为现代组织环境中的个体我,面对的不可能都是优越的环境,他或她要处理各种复杂关系,要通过克服种种困境才能提高能力、发展个性,使之成长进而成熟。
以上表明,组织生态学能够对个体我(个性人)定位做深入其理的阐发。可以从个体与整体、个体与群体、从量到质,从应激性的线性反应模式到关系回路反应模式、从被动到主动等强烈对比模式中,突出个性人。从正面塑造个性人进而锤炼个人主体性。它是一个在关系互动中升华自我的自由感、多样化个性、彰显自我能力的组织生态。这种情境使得组织中的个体,有可能成长为一个勇于承担责任、又愿意尽义务的人,一个有着积极向上心态的人,一个有激情、有毅力,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积极共生关系之中去的人。自我追求个性,但也积极融入共生关系。这种组织生态,深入了揭示现代商业社会的时代精神。
五、现代组织生态中个体人存在状态的成因分析
(一)转型期的社会生态分析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美国现代管理学初创时期,是各项事业蒸蒸日上的时期。奴隶制在法律上被废止,自由、民主、平等观念不但在法律上得以确立,而且深入人心。这一点决定了现代组织中的个性人,能否被塑造的社会大环境。美利坚国力强盛,成为引领世界的翘楚;普通人向往哈德逊河畔的自由女神。这是一个各民族、种族、不同地域的文化大融合的“进步时代”(TheProgressiveEra)。在这种融合中,美利坚逐渐展现其自立的个性。美国人的心态也表现出“今天很美好,明天更美好”的阳光、乐观的特点。边疆开发、淘金热,使美国人看重事在人为,并在这种氛围中成就自我。这种氛围逐渐塑造了现代商业社会中积极生存个人的品格。
(二)转型期社会生态的思想氛围
当时社会哲学家杜威、库利、法社会学家庞德以及之前的威廉·詹姆斯在“社会进步”思潮中就个人与社会关系论域,有诸多相似性、相通性的论述。例如,杜威早年受过德国哲学的影响,而在其思想的成长中又都致力于批判地超越老黑格尔主义以图发展出美国特色的实用主义哲学。这也可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论述中略见,如杜威认为,人是社会性动物。人的自我意识、自我实现都建立在共同的社会参与的基础上。
杜威强调,“交流”是人追求有意义生活的关键所在,而交流意味着与他人处于更紧密的社会交往中,意味着深入到、参与进更广泛的社会关系、团体组织之中。杜威的这些论调,其中心议题就是人不能被视为孤立的个体置于实验桌上作解剖式分析。他重视民主,认为民主不仅仅是投票方式,更体现在公民的生活中,它就是现代公民的生活体现,“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进步时代”的美国思想家在19世纪末致力于继承德国文化、哲学,也继承英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并使两种思想在美利坚汇流,致力于创造出美国自己的以实用主义为代表的美国价值观。
(三)组织生态境遇中人的相反相成现状的对比分析
工业民主时代的管理思想家福利特致力于追问、探讨那些能够体现工业民主时代的更积极参与式民主的运作理念和模式。福利特不仅仅批判现实组织运作体制,她更剖析出现这种现象在组织哲学上的人学前提。她批判17世纪、18世纪直至19世纪累积下的原子式的孤立的人学观。这是资本主义私利长期发展并以其为首要原则所导致的。更关键的是,这种唯私人主义(particularism)反映出来的个人与组织关系处于极端对立之中。一方面,随着机器大工业、工业革命的普及,工业生产日益机械化以至自动化。这种工业背景造就了相对立的个人与组织关系及其社会关系。劳工———组织中的普通人,只管按照程序,接受命令,完成规定的程序化动作就可以。这种操作只要求过程规范化,不要求工人有其它想法。工人,最好把自己当成一个工业流水线上的机器人,尤其理解为一只或一双完全自动化的机械“手”。人的定位就是一个“人手”。
更戏剧化的是,在当时,这反映的不是愚昧,而是所谓的科学。而这种关系越“和谐”,个人与组织关系就越对立。这种对立揭示了个性被泯灭,个人被同一化在机械组织中极端恶化的组织生态境遇,体现的不是个人与组织的关系,而是机械“手”与整个机械组织的组织生态观。而拥有理性或说能够把知、情、意溶于一身的人,在组织中不见了。工业管理被叫做机械工程学,它延伸到公共行政中与韦伯所指认的官僚制有相通性。这是美国转型期管理实践面对的个人与组织对立组织生态境遇的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是,员工的利益与组织所有者的利益因组织生产率提高后利益分配中的分歧,从而延续了工业革命以来的新的劳资对立升级。在利益分配中,基于两大阶级的对立,基于一贯的工业文化,劳方有时不得已以工会方为阵地与资方对立。
问题在于,社会转型期的这种个人与组织对立组织生态境遇,与现代社会中民主、自由的人性的大发展、大繁荣不一致,与现代社会所崇尚的个性以及对自我价值的追求欲求不一致。在工作时间中,表现在以上个人与组织诸多对立关系中,而在业余时间里,在非雇佣工作关系中,在参与广泛的社会团体和兴趣俱乐部中,人可以积极投入到广泛的个人爱好当中,发挥人的主动性、创造性,每个人能力得以彰显。这就是美国“社会进步”时代的人参与社区工作的写照,反映出社会关系中的个人与组织的积极共生关系。这种状态下,人在业余时间表现为人,在工作时间幻化为“人手”———“非人”,其实质是人的工作时间与业余时间相对立。这种对立在马克思的着作中就已揭示了工作时间与闲暇时间的矛盾。马克思主张的是,在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境遇中,只有闲暇时间才能发展人的个性,工作时间不得已就成了一种为买断闲暇时间的成本。似乎闲暇时间越多,人越能得到全面发展。马克思当时社会状态中的人基本没有闲暇时间,人的大部分时间被工作时间所占用,即工作时间本身就必然存在个人与组织的对立。这一点到科学管理的泰勒时期,一直没有变。虽然出现了生产力提高,普及8小时工作制,但工作时间中的个人与组织关系仍处于对立组织生态境遇之中没有根本改变。即人仍处于业余时间与工作时间两个时间阙域的角色对立之中。而个人与组织积极共生论的组织生态观的深度探讨和广泛探讨以能否消解这种对立关系为出发点。
六、由旧人学到新人学:现代组织生态中的人学转向
针对这种个人与组织对立关系的人性前提,要积极批判这种唯私人主义人学观,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现代组织生态境遇中的新人学观。这种人学观在基层公共组织以及社会团体互动中得以酝酿。旧人学观造成私人生活与工作时间的对立,而新人学观主张,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之间没有一堵墙。个人的公共性生活与其私人生活是贯通的,个人的业余时间与工作时间有相通性,基于这种相通性而产生和孕育的个人与组织的积极共生生态关系。基于个人的业余生活与工作生活相通的可能,基于这种基点不是把工作中个人与组织关系推广到业余生活中,而是基于个人对业余生活中个人与组织积极共生模式的接受把其推广到工作生活中去。美国转型期时代的人对此种推广,抱有乐观态度。更主要的是,有不少社会活动家积极主动地身体力行。例如,管理思想家福利特基20年社会实践经验以及集诸多主客观条件写就《新国家》,初步提出自己的个人与组织积极共生论,并通过《创造性经验》的写作,使这种理论更加条理化和具体化,写完这部书没多久(1925年左右)就致力于把其思想推广到工业组织管理和企业咨询中。当时英国的朗特里等开明工业管理者也积极推广个人与组织积极共生模式的组织生态。这种从正面推行个人与组织积极共生论来消解工业关系中现存的消极的个人与组织对立的消极共生论,给20世纪的组织管理社会带来了希望。
泰勒认为,科学管理得以推广的关键在劳资双方的“心理革命”。他看到了个人与组织关系对立的症结,但这种“革命”的表态过于抽象并没有被劳方,也没有被资方所认可。后来的人际关系学派梅奥从科学的工业心理视角来诊断问题,认识到重视工业关系中人的问题的可能性。巴纳德开始从个人与组织更积极关系来审视工业管理。福利特是基于管理哲学探讨的理念先行然后再引导实践的方式来推行,而梅奥、巴纳德以及其他现代管理学家是基于企业管理实践本身的内在发展,构建出积极组织共生生态关系。现代管理研究者们可能并不认同福利特的业余时间与工作时间的组织逻辑合流的说法,但会积极利用把个人在业余时间生存状态的理论成果借鉴到工作时间中,发展出工作-生活平衡[11]的组织行为学理论。
七、现代组织生态中个人积极生存状态的问题关切与基本定位
(一)不仅仅为工资而活
组织生态学认为,积极生存的人是有未来的人,是一个只争朝夕的人,其生存不靠神力,而靠自己的主观努力。[5]102人的积极生存其实质也是可以通过心理技术(组织文化灌输)以及利益需要诱发的一种积极“入世”。其一,积极参与到组织、社会团体当中,做一个热心公共事业之人,这是人积极生存的第一要义;其二,把入世之心进行到底,让雇佣关系中的普通个人,也不仅仅为工资而活。这在美国管理转型期的1930年代,只能在少数人身上得以体现。随着职业经理人在企业经营中普及,以及这一阶层逐渐职业化,因这种个人的积极生存观与引导人、激发人的创新精神的企业家精神有了相通性。在组织社会时代来临以后,人把更多的时间运用到组织生活中,人的私人生活和组织中的公共生活有了合流的倾向,这在查尔斯·汉迪的组织理论已经论述到这种征兆。汉迪的相关着作,如《觉醒的年代》(1990)、《个人与组织的未来》(1989)、《组织的概念》(1983),对此多有论述。
(二)私人性与公共性兼容
人只有把自己更深入地融入广阔的组织关系、社会团体中,其个体我的多样性能力才得以展现。当然,这是不是意味着,越被一个组织运作模式所固化,就越有多样化的差异化的人之个性?个性与社会性、公共性是不是对立的?这也是其私人性与公共性兼容的一个延伸和具体例证。美国社会转型期的早期管理学家们深入关注人的个性,后来的管理学是基于个性与创新精神、创造力相联系,才激发个性,其最终是为组织服务。因为参与不同类别的组织,意味着人生经历的丰富多彩。这潜含着人将更有个性。这已经不是理论上假想的个性,而是刻有现实多元化经历印记的个性。
八、转型期组织生态的辩证分析
(一)管理领域中人的身心能二分吗?
奥古斯丁有个着名观点: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上帝的精神王国与世俗世界是二分的。即在世俗世界,在政治及其延伸的———管理领域里,人的信仰、精神不被涉及、不被管辖或说无权管辖。这种隐喻就是在组织社会领域,人不必投入的太多;组织,不管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管理者不能要求人的心灵归属,人也不能把组织拔高赋予其对个人太多的精神意义。组织是人活着的一种借据,是人为更好活着,为了挣取衣食不得已的一种对自我自由时间的出卖。这就是雇佣关系的实质。例如德鲁克就这样认为,“‘良好的人际关系’如果不是植根于良好的工作绩效,所带来的满足感与和谐合理的工作关系”,是“非常脆弱的”。
而积极共生的人性观认为,公共性与私人性兼容,业余时间的经历与工作时间可以兼容。这意味福利特打破了自圣奥古斯丁间接引申来的身心分离,归不同领域的常规。对此,福利特正面论述个人与组织积极共生可以身心和谐,同时也正面谈到个人精神对组织归属问题。这一理论的深层指向是,人在组织领域中的目的与手段的定位是合一的。这一点在现代组织管理中也有类似地把人的目的与手段定位合一的做法,如学习型组织中,但学习型组织最终以工具论为基点。在学习型组织视域中,组织中的人,一般以物质刺激为先,即使精神价值也一般换算为物质的量化比较来衡量人的精神以及其创造性的价值量。现代社会的组织人(OrganizationIndividual)是身心一体的,但,仍归结在可量化的物质刺激上,而且最终是一个无形的货币符号大小来代替这种量化的差异。最终,现代组织中人的身心仍归属于奥古斯丁的定位而福利特试图以乐观的心态缜密的个人与组织积极共生论突破这种定位,不过这种突破到后来可能仍使得身心二分更严重了。这是福利特主观上不愿看到的。
(二)现代雇佣关系下人的积极生存能否成真?
在社会进步思潮下,积极共生论基于深度融入组织关系之中,表征个人的积极生存状态。这种表征在工业民主大行其道的背景下,其试图被乐观地推广到工业组织和企业咨询中。但,在现实雇佣关系为主导的个人与组织关系中,能否落实?落实后是基于什么样的前提和基点?值得深思。当个人主动而自发地加入组织,在其中激发起自己的知(觉)情(感)意(志)的全面投入之时,在自发组建的小团体中,将会有中正平和的发挥。问题是,这种个人状态推广到雇佣组织等更广泛的组织类型中时,个人知、情、意同样会被激发,有时候(如传销组织中)是超常规的激发。现代管理中已有诸多激励理论,其目的是,激发人的积极工作热情。问题是,这种激发是知、情、意的和谐高涨?还只是对人的欲求,特别是对人的无限制的情与欲的激起?这是否是一种情大于理的状态,是否仅仅是一种偏激亢奋?更主要的是,这种亢奋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时,其后果很可怕。如传销。
在现代管理转型中,组织行为学与积极心理学比较专注的积极生存之人的状态,很好地表征了当时乐观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潮,蒸蒸日上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有所想,必会有所为”的价值观导向。这种人生观集中体现在企业家精神的诸多表征上。这种生存观与现代管理中诸多激励理论不谋而合。这种理论提升了竞争社会中急需的人的亢奋、热情与信心。在竞争社会的风险环境下,人的积极生存状态倒成了稀缺资源。这种状态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商业社会中人的生存观。人可以有一种自发的积极生存状态,到后来现代管理中通过激发成了自觉的生存。这种自觉地积极生存与自发地积极生存可能会造成不同的后果。这种后果其极端状态就是传销组织中人“被”蛊惑成一种因失去社会常识和理智的极端异化的状态。按常理看,“被”积极生存的状态,是一种人被传销理论和传销管理者耳熏目染后的一种妖魔化的状态。个人与组织的积极生存变成一种妖魔化的积极共生态。积极共生论被应用,尤其是被非常自觉地利用后,其蜕变就具有了不可控性。
(三)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合流的设想可能吗?
在个人的积极生存中,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业余时间与工作时间的合流是一种很惊人的想法。这意味,个人积极生存在“公”、“私”领域是共存、互通、共荣的。人的积极生存适用于、也得益于这一背景。若进行扩大化应用,能否经受住考验?这种应用会不会变成畸形?西方一直有保护私人生活不被侵犯、警惕私人生活公共化的传统。至少,私人生活公共化是像阿克顿、哈耶克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者所极力反对的。私人生活公共化对个人生存意味着什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个人生存?现代组织生态研究者应该深入思考。
九、基于利益诱发下人的积极生存幸福观的批判考察
这种积极生存———这种人身心的知、情、意积极投入的生存状态仅仅是一种闲庭信步“不动心”的积极生存状态吗?似乎不是,但它有可能蜕变成商业社会中运动员“奔跑”状态,[13]更有可能是一种竞争性极强的“奔跑”。这种“奔跑”状态能否是一种良好的生存感受?还是把人抛入永恒流变的不确定动态工作环境之中?有些人可能喜欢这种状态,因为会使人像弄潮儿一样,在与命运的搏斗中自立、自强。有些人可能不习惯这种奔跑状,因为它也可能导致“随波,逐流”进而生成失去自我的挫败感,失去对自我、对环境的熟识状态。这是一种脱离真正“自我”的状态,一种可能使积极生存观转向消极生存观的趋向。当积极生存观广泛应用到商业环境中时,诸多批判型理论家如弗洛姆等人也指认了这种状态可能的消极后果。企业中激荡人心的各种激励理论,在现代公司各种招聘的对外宣传中,已各显其极了。在这种状态下,尤其身负各种内外压力状态的人,真的有良好的生存感吗?还是仅仅吹起一个大大的虚假组织境遇中的意识形态“泡沫”。
十、结论与展望:中国转型期组织生态正义的价值呼吁
在转型期的现代组织生态境遇中,这种积极生存状态对人的影响,与科学管理、官僚制模式时代的组织境遇相比,是切入“身”“心”的。因为它影响的不仅仅是人的体力,更是对人的知、情、意的身心影响。更关键的是,它可能表面上仍体现以人为本,以给人创造全面发展的机会为标榜,但也有可能导向传销模式的蛊惑人心。马克思仍通过工作时间与闲暇时间的区分,认可了工作时间的工具理性思维,通过充分利用闲暇时间来发展人的全面个性。而这种工作时间与闲暇时间职能的二分被打破之后,在全身心投入工作时间以后其可能的变迁走势与原有初衷是否一致?这种身心投入的状态也完全可能,或说已经成为现实中的5+2(白+黑)的工作模式———五天加上周末二天,白天加上黑夜。问题是,这种状态有无可能导向更大异化的可能?人越表现为积极生存,其可能的后果将会使人的生存境遇越畸形。在商品拜物教高度发展的状态下,人越被号召要积极生存,其后果可能适得其反。这种状态使人的身心处于类似于火与冰双重对比强烈的考验中。在组织生态境遇中,个人可能会变得更坚强,但也可能会变得更加脆弱和颓废。人的身体与芦苇无异,因有精神,人可能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动物。处于火与冰状态中人之精神、意志能否如组织管理者所愿?显然,大部分人做不到。因为有相当一部分人可能其芦苇般的身体承受不了火与冰的考验。基于此,希望现代社会组织领导者关切组织生态可能恶化趋势,而不仅仅是关注组织中人的物质福利问题;[14]为减少“富士康问题”的发生率,减少“过劳死”和缓解高度竞争性组织中人的心理压力而呼吁组织生态正义。
组织生态正义其实质就是,呼吁一种在保持组织竞争力状态下的暖心工程的价值关怀,组织生态学属于组织文化学、组织行为学的大研究领域。为了防止利益诱发独大的局面继续强化,需要深化对竞争性组织中价值内涵的组织生态学的相关研究,积极营造内容正义的组织境遇的生态建设,以在更大范围内形成健康和谐、积极向上的社会生态环境,以扭转中国社会转型期广义的竞争性组织(包括企业、地方各级政府等)过度强调利益诱发而可能导致的社会生态环境恶化蜕变的可能。
参考文献:
[1]俞文钊.现代激励理论与应用[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4:114-117.
[2]刘敬鲁.论组织生活价值冲突的正义管理[J].学习与探索,2011(1):22-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