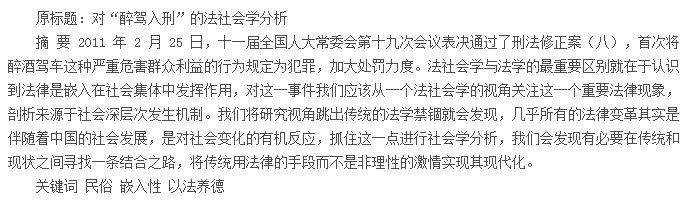
“醉驾”这样一个社会事实一直以来其实是被整个社会所不认可的,但是因为没有相应的法律程序来对其进行处罚,因此对这一问题的处理也只能停留在一个认知的层面,但在实际的程序处理上则是在一个尴尬境地。而在刑法修改的过程中,将“醉驾”认定为犯罪,明确量刑尺度,使得其能够被司法机关有法可依,这一点很值得肯定。
所以,“醉驾入刑”这一举动实现了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相统一。在之前,我们社会的主流观点是肯定“醉驾”这一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所以社会对于处罚这种行为是有一种正义的诉求来维护社会的正义。但是,因为缺少相应的手段进行制裁,使得实质正义不能通过程序体现出来,导致了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脱钩,并最终导致社会正义缺失。
我们对“醉驾”这样一个社会现象的理解不应该单纯地由法学的视角,从权利义务关系上来着手认为是法制的进步必然,而是要将其视为一个嵌入性的社会问题来考量。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会把“醉驾”这样一个社会现象纳入到要由国家刑法加以控制的视角下来呢?我觉得这才是法律社会学对这样一个问题认识的应有之意。
不得不联想起“麦克弗森诉别克”这一个案件。在这样一个案件中,我们看到由于别克公司没有对轮胎进行检测而导致后来对当事人麦克弗森的伤害,在最后的审判中,州上诉法院最终认定别克公司对麦克弗森的意外受伤负有责任。这个案例中最重要的是一种对未来的预测性,因为从逻辑上讲当时汽车还不是一个普及物造成的社会危害有限,但是法官意识到汽车将会在以后的发展中普及,就会导致这种潜在危险性的上升,因此麦克弗森的胜诉其实是一种对后来社会价值结构的定位,因而这样一来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判例影响了后来类似案件的审判。
同样的道理,随着中国自身经济的发展,汽车的普及已成为必然趋势。伴随这一过程整个社会中驾驶汽车的人将会越来越多,就像“麦克弗森诉别克公司”一案所体现的,随着社会发展,驾驶必然会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对于这样一种社会惯习的约束,尤其是对其中会造成可预测消极后果行为的约束是大势所趋。
在这样的视角下来考虑,“醉驾入刑”是用法律的手段来限制社会中强大暴力 对社会造成的伤害,这与现代国家对个体公民私权保护的理念相吻合。而“醉驾入刑”还暗含着另外一层规范的价值取向,就是对于社会优势阶层的规训。在中国经历着高速的经济转型,伴随着市场化发展起来的新优势阶层在中国这种条件下有一种对法律的漠视感。所以我们看到大量的富二代、官二代乃至是这些优势阶层人本身,都对于现行法制持有一种暧昧的态度,所以社会是需要法律的力量来对于这种对法律的冷漠进行规训。
而高晓松的例子就传递给社会一个声音,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行为的重要性在于其警示作用,如果在这个时候法律没有对这些“吃螃蟹”的违规者严惩,就势必会出现群体参照,反而会鼓励以后的人尤其是优势阶层因为这个先例而挑战法律。
“醉驾入刑”的实施很好地体现了如何将社会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而进一步实现对其的国家约束力。但是,有了好的立法不代表着就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在多数案例中,我们看到当事人都是因为出了事故才被发现,我们假想他们如果在酒后驾车没有发生事故,是否还会被发现?所以,我们应该反思的一点,“醉驾入刑”虽然已经实施,但是我们依然要看到其存在的空间。
我觉得这里就表现了一种长期存在于我们中国心中的一种侥幸心理,总是认为制度只是制度,只要没有被发现就相安无事,那种“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的观点不仅仅是在醉酒驾驶这一个案中体现,因而我们必须要意识到法治的观念并没有内化到人的心中,有些时候只是喊喊口号而已。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一个社会而言我们决不能仅仅依赖于国家通过出台立法,严格执法来对我们的社会中某些方面的问题来进行约束,而这也就是当前中国面临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不是我们没有法律而是我们中国人没有一种法律的自我约束精神,换句话讲就是在中国的市民社会中没有一种法律道德的土壤。
要培养起一种全社会的法律气息,不仅仅是国家公权力介入,更重要的是来源于民间自身的力量。在习惯和制定法之间,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习惯。就像《就制定法与民俗习惯间张力论村治》一文中提到的,显然我们要意识到制定法是在社会的实践中有着巨大的局限性。因为作为市民社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制定法本身也是来源于社会的习俗,肯定和否定某些行为。同时,制定法在很多时候是有其局限性如滞后性,不可实施性,但是,作为一个迈向法理型的社会国家,我们要意识到这种缺陷是可以通过我们自身的提高来降低我们现状带来的误差。
而回到高晓松案件本身来看,我觉得我们的报道与其说是在对于这样一个法律进程的通告,还不如说是我们在打造一个异类的“明星”,各家媒体都是在找谁是第一人这种有点类似于选秀的性质。所有的人都是在一种期待中等待着醉驾者被法律所惩罚,我觉得与其说这是中国人法律意识变强的表现更不如说是一种集体的欢腾,在等待着一场演出。一项法律出台不能依靠民众的激情来实施,而是要用一种理性的操作来规范化其运行。真正能取得好的效果的法律是要依靠在后来的实施过程中等激情褪去而变成一种每天去遵守的习惯。
“不因善小而不为,更不因恶小而为之”,在社会生活中每件事情都是有其规则的,或许不是关乎正义但是却讲求规范。我们反观之前对于“醉驾”的态度,会发现我们已经太熟悉对于“醉驾”的不满。所以,我们不能否认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很重视这个问题,只是用一种相对温和的德治方式在进行,以宣传为主。
而退而求其次地想反思这个问题,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似乎是在对待“醉驾”观念是继承着之前的理念,但是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则是有一种追求自己修炼的德育变成了一种严刑峻法的法治。就像前面讲的,法律的问题是嵌入在社会中运行的,本身其实就是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AGIL模型的一个组成部分,属于其中的维模。“醉驾”本身是一个来源于现代社会的概念,在我们传统的社会模式中没有驾车这一概念,自然也就没有“醉驾”这一概念,但是在进入或是即将进入“汽车时代”的时候,我们原来的AGIL模型已经发生了变化,有诸如驾驶汽车这样的新元素补充进来,因而相应的模型也要进行修改,有必要对这个模型进行调整,建立起新的平衡机制,将新出现的问题纳入到整个社会体系中解决,才能维护好整个社会结构的运行良好。
所以,“醉驾入刑”这一条款的意义不仅仅局限在其本身,而且还对中国的整个立法司法领域的实践有着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商务印书馆。2000.
[2]何珊君、郑杭生。和谐社会与公共性--一种社会学视野。甘肃理论学刊。2005(1)。
[3]何珊君。社会结构变迁与转型的动因探索。学海。2007(2)。
[4]何珊君。法与非政治公共领域制度间博弈对社会结构之影响。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
[5]何珊君。就制定法与民俗习惯间张力论村治。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
[6]秦晖。传统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