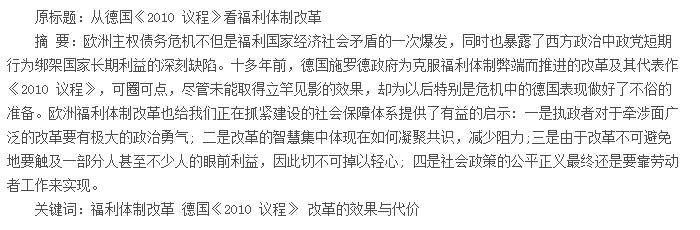
美国金融危机尚未消停,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又接踵而至,给还没有缓过劲来的全球经济很大冲击。导致欧债危机的原因相当复杂,还可能由于流动性紧缺,通过信贷危机引发新一轮金融危机,形成多重危机交织在一起的局面。危机对欧元前途乃至欧洲(盟) 治理模式也带来了不小的挑战,使福利国家改革话题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若干年来,这些国家的改革,风风雨雨,众说纷纭。谁也不会否认福利体制的社会进步意义,但问题是要建立怎样的福利体制。这对于我们既要尽力而为,建立适合国情的发展型社会保障(福利) 体系,又要量力而行、防范道德风险,具有借鉴意义。
一、福利体制的困境
伴随着冷战降温乃至后冷战时代的到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朗,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全球资本的流动性大大增强了,劳动者地位下降,而具有保险性质(事后救济) 的传统福利体制的弊端便暴露了出来。在右翼政治家看来,“福利国家机构强加于资本之上的管理和税收负担等于是抑制了资本投资的动力; 同时,福利国家所认可的要求、权利以及工人和工会所拥有的集体权力,等于是抑制了工人工作的动力,或者至少不能迫使他们像在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那样努力而有效率地工作。概括起来,这两方面的结果导致这样一种合力的产生: 它既使经济不断衰退,又使期望不断上升……”
全球化时代的新型风险纷至沓来,社会开支捉襟见肘与福利“刚性”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为了应对这些问题,各国的福利体制纷纷有所改革,并构成了欧洲社会治理改革的主要内容。全球化以及强势资本的压力是改革的“外因”。
欧洲福利政策可追溯至 17 世纪初的英国《济贫法》(1601 年) 。19 世纪后期俾斯麦治下的德国颁行的疾病、工伤和养老保险办法被认为是现代福利体制的开端。二战以后,欧美福利国家的实践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分配不公,避免了严重的社会分化。传统福利体制之所以奏效,主要是工会可以把劳动者组织起来,通过各种途径影响政府行为,政府再督促劳资双方寻求合作性的规制,以维系资本主义体系的运行。但是全球化尤其新兴国家的崛起使这个世界今非昔比了,以信息技术和产业为代表的新技术和产业革命,新兴国家门户开放有力促进了资本流动; 但是,资本可以全球化,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而福利却不可能全球化。
高福利国家因此面临着双重挤压: 低福利国家劳动力涌入和本国资本蜂拥而出。居高不下的福利成本严重削弱了国家竞争力,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财政包袱。或者说,全球化猛烈冲击了“资本—政府—劳工”相对稳定的博弈结构,改革就这样成为福利国家的被迫选择。
福利体制无法适应社会变化构成改革的“内因”。上世纪 90 年代,西欧国家进入“后福特主义”阶段,在网络化生产条件下,就业结构、社会结构均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福利体制在为困难人群提供救济的同时也诱发了不以为耻、“鼓励”懒惰甚至骗保的“道德公害”(moral hazard) 。以德国为例,2002 年社会福利支出为 4870 亿欧元(占当年 GDP 的 23%) ; 从 1991 年到 2002 年,政府债务翻了一番,2001 年财政赤字为589 亿欧元,2002 年为 743 亿欧元,2003 年为 860 亿欧元,主要原因就是福利开支不断增加。
欧债危机以前,希腊劳动者退休养老金与工资收入相差无几(95%) ,平均退休年龄是 53 岁,每年还有六周休假,这么舒坦的安排很难产生工作激励。由于福利开支居高不下,2011 年末希腊政府债务占 GDP 比重高达170% 。传统福利体制的缺陷被认为: 第一,强调社会公正往往与追求结果公平相混淆,后果是忽略了积极奋斗和责任意识,缺乏对创新性、差异性和卓越性的鼓励; 第二,不断增加公共开支以实现社会公正,而没有考虑这些开支的实际作用; 第三,政府权力扩张以及由此滋生的官僚主义,使公民的重要价值观(个人成就和个体责任、企业精神和集体精神) 成为附庸; 第四,权利超越义务,忽略个人对家庭和社会的义务; 第五,夸大了国家调控经济的能力,低估了个体和企业创造财富的重要性。
这就注定了传统福利体制不可持续。
政党政治使竞选承诺只能“透支”的方式不改不行。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经济重心转向非物质生产部门,2/3 以上的就业人员在第三产业工作,制造业工人无论绝对数还是相对数都明显下降。
英国工会的组织程度在 1979 年是 55%,到了上世纪90 年代只有 35% ,结构性失业严重削弱了工会的力量和号召力,较灵活的产业形态更加剧了工会组织的涣散。左翼政党为了在多党政治中站稳脚跟,争取选票,也不再以工人政党身份标榜自己。英国工党在1992 年败选后,布莱尔就提出工党必须以中产阶级和政治中间势力为主体。1994 年他大刀阔斧地调整工党政策,声称工党不仅是劳动者的党,也是企业主的党。“政党意识形态中间化是政党对社会结构变化的适应形式。”
执政党刻意淡化意识形态色彩,多方面迎合中产阶级的要求,包括承诺进行有利于他们的改革。为了能够上台,政治家竞相提出各种许诺,吊起选民的胃口,而在台上的执政者既不敢得罪资本家,也不敢增税,那就只能靠举债度日。“本来设计为‘安全网’的福利制度就变成了舒舒服服的‘靠垫’。一个社会,如果大家都想从国家那里多拿一点,却不愿为国家增加财富出力,还能维持下去吗?”福利体制改革成为无论“左”抑或“右”的共同选择。社会福利原来是一个具有左翼色彩的价值目标,福利国家实践也是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压力下,资本主义文明和进步的重要表征。然而,这些国家的道德优越感正在流失,批评者认为福利制度是“寄生的社会主义”(creeping socialism) ,它只能使弱者越来越依赖于国家,造成庞大的财政开支,削弱了竞争力。上世纪 80 年代,新自由主义就把福利国家当作理想主义的神话,因为当追求平等和再分配变得比经济增长更重要之时,个人的选择及其责任感就被削弱了。美国里根政府推行“为工作而福利”政策,英国撒切尔夫人政府更充当了改革的急先锋。90 年代欧洲多国社会党上台执政,也不甘落后地强调理论纲领必须与时俱进,必须调整那些不合时宜的东西,包括缩减福利供应、调整个人所得税等等。在这些方面,欧美各政党的社会政策大同小异,“超越左右”,并聚焦于福利国家的转型。
福利国家的改革在世纪之交风生水起。改革者主张用所谓“积极的福利”(positive welfare) ,即变“事后”消极地(或被动地) 应对为“事先”积极地(或主动地) 防范,这个“积极”主要是强调通过扩大社会投资,创造就业机会和岗位,使“福利国家”转变为“社会投资国家”。“福利国家如何促进(经济) 增长、(社会) 发展和个人活力及自我责任,而不是培养惰性”就成为一个高度关注的问题。福利不能简单地以国家或社会行为去代替个人责任,而是通过改善社会促进每个人自我完善的实现; 相应地,每个人也必须为社会承担责任。要言之,改革就是要建立更有效率的工作福利制,防范过分依赖福利的风险,包括放松对市场的限制、鼓励自立、重视培训以及强化责任意识。
今天看来,十多年前德国施罗德政府的改革及其代表作《2010 议程》(Agenda 2010) 可圈可点。
二、施罗德改革与《2010 议程》
全球化既带来更大的市场、更多的机会,也伴随着更激烈的国际竞争,但福利国家的表现差劲。一是人口老龄化使社会背负了沉重的养老负担,这些国家需要充足的劳动力和新的就业机会来支撑养老社会化,但又苦于劳动力与社会所提供的就业机会很不平衡。二是就业结构和人口结构的变化使社会福利越来越入不敷出。就业结构方面,大量相对稳定的劳动关系被灵活工作所替代,就业时间缩短,就业不足使失业时间增加; 人口结构方面,进入养老阶段人口比例逐年增加,造成养老金供求比例失调和资金水平下降。1999 年 6 月,德国总理施罗德与英国首相布莱尔共同提出《欧洲社会民主党人的前进道路》(施罗德/布莱尔文件) ,试图寻找一个突破口,这也被认为是欧洲左翼执政党推进福利体制改革的重要标志。
十多年过去了,不少南欧国家在长期财政赤字和靠借债度日中苦苦挣扎,终因支撑不住而导致危机爆发;只有少数国家,特别是德国得益于前十年的未雨绸缪,在危机中表现良好。
上世纪 80 年代,德国社会福利开支年均增速4. 7% ,90 年代这个增速达到 6. 6% ,但 GDP 每年仅有3. 9% 的增幅,收支缺口不断扩大,不得不一再提高缴纳率,施罗德上台(1998 年) 前的两年达到了创纪录的 42%(上世纪 70 年代为 26%) 。德国人口结构严重老化,新生儿比例持续下降,居民寿命仍在延长,领取养老金的时间也相应延长,这使得医疗和护理保险开支大幅上升,成为最大的一笔社会福利开支。
一时间德国竟被视为“欧洲病夫”(kranker MannEuropas) 。
1992 年,德国采取了将退休年龄推迟到 65 岁等措施,但缓解压力的效果不明显。而且依靠现收现付筹资方式的法定养老保险筹资难度巨大,总体金额呈下降趋势,养老金水平越来越难以保证,而法定养老保险的缴纳率也不可能一直往上涨。
1998 年,施罗德政府采纳了吕鲁普(Rürup) 委员会的改革方案:第一层次基本养老金仍以法定养老保险为主,辅之于“吕鲁普养老金”(积累制,可享受政府大数额、高比例退税和补贴等) ; 第二层次养老金是以基金积累制为主要形式的企业辅助养老金,另外还增加了“里斯特养老金”(对投保企业年金的保费给予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 ,目的是为了吸引企业进行补充保险; 第三层次养老金仍由原来的个人自愿养老保险等组成。
在任何国家,降低养老金水平都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情。养老金总开支不可减少,那就只能想办法“开源”。施罗德政府没有再增加缴纳率来开源(反而把养老保险费率下调了一个百分点) ,而是通过继续调整增值税、开征生态税(包括 4 芬尼/公升的燃油税、2 芬尼/千瓦时的电力税) 投入养老金。1998 年4 月起,德国增值税增加一个百分点,新增收入全部用于补贴养老保险; 生态税的实施更可谓一举两得,这个新税种不但弥补了养老金缺口,而且使德国成为世界上节能新技术的先行者、国际市场上运用可再生能源的优等生。依靠这些补充,德国退休年龄 2012年已逐步过渡到 67 岁。
施罗德政府还提出建立以个人负责为基础的养老保险第二根支柱。围绕第二根支柱是自愿还是强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野的联盟党指责改革是“养老欺骗”,他们不断追加苛刻的条件,使联邦议会有关谈判久拖不决,拖延战术逐渐形成了不利于社民党执政的氛围。社民党内部也一片哗然,施罗德感叹在自己阵营里花费的力气常常比在克服议会和社会上的阻力时还要多。
面对社民党的传统盟友工会被联盟党拉过去的危险,施罗德政府与工会经过艰苦谈判,促成了《法定养老保险改革法》在联邦议院的通过(1999 年) ; 政府还准备了 200 亿马克的养老补充保险,终于通过了修改后的“养老补充保险扶植计划”(2001 年) 。养老金改革的趋势是: 尽可能使养老保险费率平中有降,以降低工资附加成本; 在养老金计算或税收和家庭政策中对于生育子女给予更多优惠待遇; 同失业作斗争是解决养老金问题的关键,提高妇女就业率,以及放宽移民政策等等。改革目标是:未来 30 年,个人领取的养老保险金之 60% 来自于社会保险,40% 来自于财政基金。应该说,养老金保险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德国社会政策的走向。
改革以前,德国劳动力市场相当僵硬,一方面劳动力不足,另一方面许多人宁愿领取救济金,高不成低不就。为此,施罗德政府修改《国籍法》,简化了入籍要求,允许定期的双重国籍。德国还有计划地从东欧、印度引入一万多名计算机专家,并吸引外国留学生毕业后短暂留在德国工作,另外大量使用土耳其劳工来从事清洁工作等。德国总统约翰内斯·劳在“没有恐惧和梦魇,共同生活在德国”的演讲(2000 年) 中呼吁德国应帮助生活在德国的 700 万外国人融入社会。针对右翼极端分子制造的暴力事件,政府号召“正直的人站出来”,决不允许违法行为发生。
造成与劳动力不足并存的失业问题之原因,既有劳动力市场的过度保护,比如解雇保护规定必须根据被解雇的员工家庭情况给予补偿,结果企业不敢解雇那些困难员工; 失业者领取的救济金时间过长、数额过高,许多人丧失了寻找工作的积极性; 还有对劳动力的要求不断提高,没有接受或完成必要教育培训的劳动者,往往难以找到合适工作。德国中学生约有10% 不能毕业,移民子女的这个比例高达 40% ,由此不断产生新的失业者,甚至是长期失业者。
2002 年,德国政府委托哈茨(Hartz) 负责劳动力市场改革委员会,并提交改革方案。哈茨委员会一连推出四个方案,即哈茨Ⅰ - Ⅳ(哈茨改革法,正式名称是《劳动力市场现代服务法案》的四个执行阶段),这些改革不仅关乎劳动力市场,也牵动了社会福利体制。特别是哈茨Ⅳ方案,将失业救济与社会救济合并为基本安全津贴(Grundsicherung) ; 失业者领取失业保险金Ⅰ(普通失业保险) 的时间缩短为一年,之后只能领取失业保险金Ⅱ(哈茨Ⅳ救济金,即合并之前的失业救济金和社会救济金) ,其金额以“仅可度日”为标准,仅仅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领取失业保险金Ⅱ者须接受“合理可期”的工作,也须接受劳务部门安排的职业培训,无正当理由拒绝者第一次拒绝减少30% 金额,第二次拒绝减少 60% ,第三次拒绝则全部取消,仅剩住房补贴。
改革的重头戏是 2003 年 3 月 14 日,施罗德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宣布《2010 议程》,表示将在 2010年把国家带到福祉和就业的巅峰! 《2010 议程》的目标是: “改善基础条件,带来更多的经济成长,创造更多的就业”,以及“社会国家的转型与更新”。《2010议程》的主要措施包括:
(1) 鼓励就业的劳动政策。合并失业保险金与社会救济金,所有具有劳动能力的失业者只能领取 12个月的失业保险金Ⅰ(55 岁以上可领取 18 个月) ,此后只能领取失业保险金Ⅱ,领取者没有理由拒绝能够胜任的工作,否则就减少保险金。
(2) 简化解雇保护规定。为了改变企业对困难劳动者支付更多补偿的情况,一方面对于那些短期雇佣者、借用雇员及临时工可不适用解雇保护规定的标准; 另一方面有选择地引入补偿机制,使企业能够留住高素质的员工。
(3) 改进工资协议法。在不触及职工参与权、不取消行业工资待遇普遍适用协议的前提下,工资协议增加有更多选择性的例外条款。劳资双方力争达成一致,当双方意见不统一时,由立法者出面协调。
(4) 要求企业对每一个寻求培训岗位并具有培训能力的人提供培训机会。如果企业未能履行承诺,将追索企业的培训费。
(5) 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由于人口结构变化,医疗开支增加,必然导致工资附加费攀升和劳动力成本提高,进而影响新的就业机会。为此必须进行医疗保险方面的配套改革,增加自费部分的比例。
这些改革甫一出台,德国即遭遇了罕见的因立法而引起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工会威胁不惜与社民党决裂,也不再邀请施罗德参加传统的 5 月集会,他们提出这样的口号: “要改革,不要削减福利。”反对党要求将例外条款以法律形式写入工资法,以减轻企业的负担; 工会反对立法,提出宁愿与资方在工资合同内解决这些问题; 社民党内部也有人指责施罗德的“背叛”。施罗德不得不到处游说并以党内不支持《2010议程》就辞职相要挟。6 月,社民党召开特别党代会,高层根据《2010 议程》内容提出的党纲修正案获得80% 支持,紧接着绿党党代会也以 90% 支持。10 月,联邦议院终于多数通过《2010 议程》,决定于 2004 年1 月 1 日起生效。
然而,施罗德政府的改革并没有立竿见影。似乎存心与之作对,改革实施一年后,即 2005 年初德国失业人口突破 500 万(占总劳动力 12%) ,社民党在德国所有地方选举和欧洲议会选举中接连受挫,施罗德被迫提前宣布大选,结果黯然下台。接盘的默克尔政府没有勒住缰绳,而是继续推进没有施罗德的施罗德改革。2006 年下半年,失业人数下降到 400 万以下,2008 年 10 月,失业人口下降到 300 万,这是多年来没有的。
三、改革效果的评价及其启示
二战以后,英国工党政府在《贝弗里奇报告》(Beveridge Report) 基础上建立起福利国家的样本,社会福利成为福利国家令人羡慕的“名片”,但因时间长了,这张“名片”也要刷新了。1998 年,德国社民党在野 16 年后重新执政,施罗德在竞选纲领中提出“新中间道路”,确立了在经济效率、生态持久和社会团结之间保持平衡的施政战略,已经有意要动福利体制的奶酪。
可惜施罗德改革“出师未捷身先死”。一晃十多年过去了,特别是危机的爆发及其应对措施使越来越多的人对那些改革刮目相看。施罗德本人在 2013 年的一次访谈中感慨: “德国比其他欧洲国家开始改革要早,‘2010 议程’的改革举措让德国提高了竞争力。现在许多欧洲国家需要改革,这是十分必要的。”
2005 年 11 月,接替施罗德任联邦总理的大联盟领导人默克尔在就职演说中,称赞施罗德用《2010 议程》勇敢地撞开了改革的大门,并克服各种困难予以贯彻。
把“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用以形容改革的效果再贴切不过了: 在危机最严重的 2009 年,德国经济呈4. 7% 的负增长,但就业水平仅微挫 0. 2% ; 并于此后分别实现了 4. 2% (2010 年) 、3. 0% (2011 年) 和0. 7% (2012 年 ) 的增长,远高于同期欧元区国家2. 0% 、1. 4% 、停滞甚至负增长的平均水平。德国是欧洲最大的经济体,经济产值占欧盟总量的 1/5,出口量占欧盟的 1/4; 德国现在的失业率为 5%~6%,是欧洲平均失业率的一半左右,特别是青年失业率已降到20 年来最低点; 德国预算收支大抵平衡,德国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约低于欧元区国家 5 个百分点。作为欧元区最大的债权国,德国在决定欧元前途方面举足轻重,也是经济社会表现最好的发达国家。
2000 年 5 月,欧洲领导人签署《里斯本议程》(Lisbon Agenda) ,确定了十年战略目标: “成为世界上最具活力和竞争力的知识经济,保持持续经济增长,提供更多、更好的工作岗位,加强社会凝聚力,珍视环境。”
欧盟试图通过实现“欧洲社会模式现代化”建立起欧洲经济增长、就业与社会公正之间新的平衡关系,推动成员国的社会政策体系从“消费型”转向“投资型”。所谓“开放的协调方式”(openmethod of coordination) 机制,即尊重各成员国社会领域的差异性,自愿根据本国的情况灵活地实现欧盟的目标; 也不制裁落后者,其效力来自压力、点名和耻辱感。但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些东西都靠不住!
有的成员国不但违反了约定的财政纪律(赤字不得超过 GDP 的3% ) ,更遑论进行货真价实的社会政策改革! 欧盟和欧元区这些年的实际表现与预期目标相差甚远,特别是其福利体制改革可以使我们获得如下启示:
第一,推进涉及公众福利的改革要有极大的政治勇气和足够的牺牲准备。如果执政者(党) 只考虑维护自己的党派利益,就不可能冒这样的政治风险。现在看来,德国改革的最大受损者是社民党: 当年部分干部纷纷退党,党主席拉封丹另立门户,十万党员流失,一直到现在还没有缓过来,领导层甚至还不敢公然为《2010 议程》评功摆好。施罗德上台后一段时间,推进的是开源不节流的改革,并没有遭到强烈的反对。但当施罗德意识到改革必须治本,并准备挪动许多人的奶酪时,立刻迎来汹涌澎湃的抗议浪潮甚至人身攻击。由于改革效果的滞后性,大多数民众缺乏足够的耐心,改革的决心面临巨大的考验。如果选民尝到的是眼前的苦滋味,对日后的果实将信将疑,他们就倾向于对改革者说“不”。由此可见,多数原则对于改革来说具有强大的杀伤力,即便有勇气也未必能够扛得过去。其实,施罗德政府无论是坚定不移推行改革还是半途而废放弃改革,社民党都元气大伤了。
今天人们在享受改革红利的同时,也未必能记住改革者的好———这恐怕也是历史和现实许多改革者的“宿命”吧!
第二,改革的智慧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如何凝聚共识,尽可能减少阻力。顺利推进改革的关键,一是弥合执政党内部的分歧。针对党内总有些人思想比较陈旧、行动比较僵硬,施罗德认为,社民党不但要坚持自由、团结、公正的基本价值观,而且必须果断拿出国家迫切需要的明确改革议程,捍卫并坚决予以实施。二是争取工会的支持。福利国家的工会力量虽然今不如昔,但仍然不容小觑,工会在与资本家的长期斗争中也学会了博弈与妥协,争取到工会的支持就能增加改革的胜算,问题是工会作为利益集团有它自己的算盘。三是摆脱反对党的掣肘。施罗德任内联邦参议院反对党势力强大,他们 29 次对改革的立法文件提出异议(这个数字是 1949 年到 1994 年 12 届政府启动协调机制次数之和) 。“显然,联邦参议院多数在审议各类提案,如税收政策、削减福利措施时,关注的已不是在内容上如何寻求妥协,也没有考虑国家的政治责任,而只热衷于政党的争权夺利。”
这就是为什么后来联盟党政府并没有放弃《2010 议程》的改革路线图,为什么 2012 年 4 月联盟党政府拟对 25 岁以上有收入人群征收年龄税,这时轮到社民党作为反对党为反对而反对了。反对党的“在野策略”、政客为了拉票,都可能导致政党的短期行为绑架国家的长远利益。此一时,彼一时,这也是西方政治生态“左”“右”面目日益模糊的一个写照。
第三,改革不可避免要触及一部分甚至不少人的眼前利益,必然使改革举步维艰,切不可掉以轻心。
所有的改革都是利益调整,要动某些奶酪。其实大多数人都知道高福利难以为继,口头上谁也不反对改革,但要是动了自己的哪怕一小块奶酪就不干了。民意调查也显示,大部分国民希望这个国家进行改革,但人们似乎只想要抽象的改革。一旦改革涉及具体,拥护改革者马上就会变为反对者。
德国福利体制改革再次告诉我们: 从来就没有什么免费的午餐。社会福利首先要考虑的是支撑福利供应的生产力水平,其次是人们所享受到的福利待遇必须有劳动者工作进行储备。福利的“刚性”特点意味着调高了会皆大欢喜,下调了则怨声载道,但很少有人认真对待和理解社会福利主要来自这两点。福利体制的设计需要大智慧。德国老龄化问题严重,但改革并没有削减养老金,而是通过调整增值税、开征生态税,取得了别开生面的效果。“一个聪明的社会保障体系反而会增加经济活力。一个好的社会保障体系不能仅仅依赖于薪酬支付,否则工资水平上升将直接导致生产成本上升,相反,建立在税收基础上的保险体系就不会增加劳动力成本。”
今天看来,改革迫使失业者必须积极寻找工作,灵活就业也使资本更愿意雇佣新人; 但是,危机中的有效社会保障措施究竟是为了扩大内需而撒胡椒面,还是继续进行结构性调整和人力资本投资,德国政府又将面对新的抉择。
第四,社会政策的公平正义必须依靠劳动者工作而不是别的什么来实现。当年社民党党内批评者指责《2010 议程》“破坏了既有的社会公平正义”,他们认为国家应该让“所有全职工作都有缩短”,并质疑哈茨 IV 方案对劳动力市场的改革。根据德国《社会法》Ⅲ第 16 条,失业被定义为“有工作能力,且有工作意愿,但现在无业者”,亦即失业仅仅是工作能力的暂时丧失,任何保险或救济都不应使失业者安于现状而放弃工作机会。随着我国批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97 年签署,2001 年批准) ,自当履行该公约所要求的各项义务; 2004 年社会保障条款写入宪法和 2011 年《社会保险法》生效,社会保障权(socialprotection rights) 作为社会与经济权利获得了国家法约的地位; 我国明显加快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谋划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发展型福利”,这也是维护发展、改革和稳定的大局所决定的。尽管我国政治制度不允许政党轮替和政客拉票,但也不能排除有人迎合民粹、煽动民意,鼓吹不切实际的赶超型福利,利益集团不肯放弃特殊地位和优厚待遇而千方百计阻扰重新切分福利奶酪等情况。发展型福利不但要求实现普惠的社会保障,而且必须量力而行,要体现激励和引导原则,坚持权利与义务相适应。由于以往长期福利短缺,公众的预期比较强烈,我们的社会保障体制建设,一定要“治未病”(福利糖尿病) ,防患于未然; 一定要避免不可持续的过度承诺,避免社保缴费率持续提高(我国社保缴费率已超过 40%,在世界上名列前茅) ; 同时,还要谨慎探索推迟退休年龄和实行新人口政策,等等。劳动者为自己做了力所能及的保险储备,就应当获得相应的回报; 而对于弱势群体,则理应由社会统筹给予救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