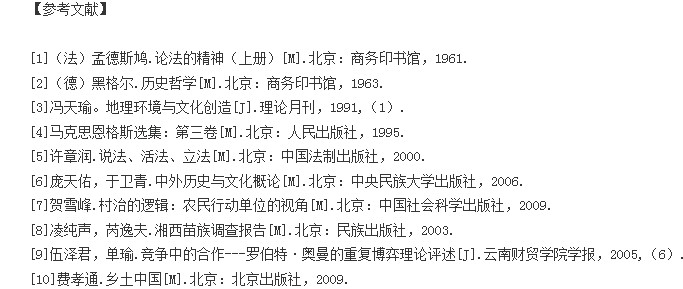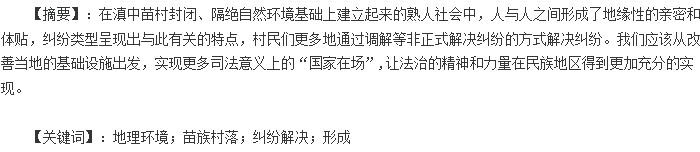
在中国横断山脉的皱褶深处,分布着大大小小几百个苗族村落,它们所处的行政区域,包括了楚雄、昆明、玉溪等州(市).龙村所属的W县位于楚雄彝族自治州东北部,地处滇中高原北部,云贵高原西部,县境内地表崎岖,群山连绵,山区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97%,乌蒙山余脉从东贯穿全境,组成一系列南北走向的高山重叠的地形。龙村村委会是一个普通的苗族村落,距县城69公里,其方圆近4000亩的土地上,分布着10个自然村(10个村民小组),共有169户581人。其中苗族580人、傈僳族1人。龙村村委会这10个自然村处于南北纵向分布的两列山梁上,地理位置较为分散,每个自然村少则8户,多则20多户人家,村与村之间多为土路。村委会距镇政府驻地有29公里山路。
几年前,这29公里路已经修成了通乡公路,只是这条公路并非全为柏油路面,还有一半多的路面是弹石路面。这条公路沿着山梁的斜坡蜿蜒而下,两旁崇山峻岭,显得分外雄奇,和众多苗族村落一样,龙村是一个集山区、贫困、民族、宗教为一体的闭塞村落,自然条件恶劣,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从社会秩序角度看,龙村是一个典型的无讼村落,村民们为人淳朴,待人友善,重和谐、讲情面,不轻易为一点小事起纠纷、打官司,遇有争端往往惯于用调解的方式解决。形成龙村无讼村落社会秩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苗族法文化“以和为贵”的深层次缘由,也有当地较为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
此外,不可忽视的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地理环境。
一、地理环境与文化的关系
地理环境,通常指环绕在人们周围的自然界,包括地形、地貌、气候、土壤、生物、水文、自然资源等等,它是人类生活和生产的物质基础,也是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基础。
孟德斯鸠从文化等诸多综合因素入手来考察社会政治制度,尤其强调地理环境的重要意义。在他看来,地理环境决定人们的气质性格,人们的气质性格又决定他们采用何种法律和政治制度,也即是说一个民族的性格、风俗、道德和精神风貌及其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主要取决于社会赖以存在的地理环境。
黑格尔是继孟德斯鸠之后另一位重要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者,黑格尔视地理环境为“历史的地理基础”,他把世界上的地理环境划分为三种类型:干燥的高地、广阔的草原和平原;巨川、大江所经过的平原流域;和海相连的海岸区域。他认为各种不同地理环境中的人们形成了不同类型的生活和性格。他认为:“我们所注重的,并不是要把各民族所占据的土地当作是一种外界的土地,而是要知道这地方的自然类型和生长在这土地上的人民的类型和性格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个性格正是各民族在世界历史上出现和发生的方式和形式以及采取的地位。”
我国古代思想家对地理环境对人类文化的作用也有过很多论述。《周礼·考工记》作者看到了自然地理对人类物质文化发展的影响:“橘逾淮北而为枳。”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礼记·王制》的作者认识到了地理环境造成地域文化的差异:“凡民居者,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当代学者冯天瑜也认为:“如果把各民族、各国度有声有色的文化表现比喻为一幕接一幕悲喜剧,那么,这些民族、国度所处的地理环境便是这些戏剧得以演出的舞台和背景。”
这些都充分说明地理环境与文化的深刻联系。马克思、恩格斯并不否认地理环境在人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而是辩证地、历史地看待地理环境的作用。一方面他们将地理环境视为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参与者,是劳动过程的要素之一。他们认为,地理环境中的土地、森林、河流、矿藏等是劳动材料、劳动对象,而劳动材料、劳动对象是劳动的要素之一。
因此,作为物质生产活动要素的劳动材料或劳动对象的这些地理环境因素,当然会影响到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并对社会经济关系以至人类文明的其他方面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恩格斯也批判了孟德斯鸠、黑格尔等“地理决定论”的片面性,指出它只看到“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
纠纷属于人们权利表达方式之一,是一种上层建筑范畴内的斗争和博弈。人们对待纠纷的观念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纠纷解决机制内在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内在机理,体现出了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存在。纠纷都是发生在一定环境和场域中的事件,其发生、发展和演进受到其所处的各类环境的影响。地理环境对文化具有深刻的影响,体现不同民族的价值追求和准则的纠纷文化,同样不可避免地由于迥异的地理环境而形成殊异的面相。人们对待纠纷的态度如何,以及纠纷解决方式怎样,都与一定的地理环境有关,只是这种关联度有大有小,并随着时间的不同而不同而已。
二、地理环境与纠纷观念的形成
许章润指出:“一民族生活首先在于它是特定时代之地域生存经验与知识,一种组织人事而安排人世之有限的能力与智慧,而迄今为止,任何生活均可谓一种地域性生活,任何生活经验及其知识、能力与智慧,均可谓是一种地域性生存力量。”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的文化生成具有重要作用。人类的古代文明发祥于富饶的黄河流域、恒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史实说明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有重大的影响。从地理上看,中国东临大海,西北是戈壁和沙漠,西南有世界上面积最大的青藏高原以及云贵高原,这种近乎封闭状态的地理环境,非常有利于形成一种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农耕文明的形成。封闭的生存空间,无法借助外部力量,使得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联系和影响很少,处于一种与世隔绝的状态。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形成了中国人一系列独特的文化观念,如知足、中庸、稳定、和平的社会环境及“家国一体”的宗法制度等,形成了中国文化传统和特色。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中国人喜欢采取中庸的态度,对人谦让,对上尊敬,不喜欢与人发生分歧和争吵。这与地理环境有一定关系:“中国地处温带大陆,温带气候适中,就使中国民族形成温和的性格,在天人之际和人伦的关系上采取持中的中庸态度。”
贺雪峰也认为:“中国季风性气候和精耕细作农业,使中国传统社会有能力养活大量人口,同时也产生了强烈的生产和生活合作的内在需要。”
对于云南苗族的地理环境,凌纯声早年曾经写道:“苗族的迁徙,在西南各民族中,时代最晚。滇越虽说地旷人稀,而山上可耕之地早为倮罗等山居民族占有。苗族后至不易找到广大山地,不能聚族而居,势必四散,各找出路……所谓的垂直分布,是说滇、越境内,地形复杂,多高山峡岭与深箐峡谷,各方迁来的民族,多限于其过去的地理环境,择居其适宜之地而居。……苗族老家的贵州海拔在一千公尺以上,西南诸省中,山坡较好之地,早为先至诸山居民族占有,苗族后至,只得居在山巅,故其垂直最高,有高山苗之称。”
龙村等地的滇中花苗自清朝中后期才从黔西等地迁入,并且来时的身份是家奴,随后才出现了佃户等。由于社会地位较低,饱受汉族、彝族地主的欺凌,基本上只能靠仰仗地主才能生存下去。实际上,到他们来到滇东北、滇中地区时,好田好地早已被汉族、彝族所占据。他们只能到人迹罕见、自然条件恶劣的高寒山区开荒生存。在龙村附近,这一特点就体现得很鲜明。
在当地,汉族一般居住在土地肥沃、开阔的坝区,彝族以居住在半山区为多,一部分也居住在山区,而苗族则都是居住在高山上,很多是在深山密林之中。
高山之上气候冷凉,交通不便,环境闭塞,土地贫瘠,无论对于农牧业生产,还是对于对外交往来说,都殊为不易。山箐之中路途难走,周围都是高山峻岭,更加显得辛苦难忍。笔者在当地体验过,从镇政府到龙村29公里路,是一个不断爬坡的过程。镇政府驻地处于坝区,地势平坦,河流水量充足,往龙村方向前行,就慢慢开始蜿蜒着上坡。
再走几公里后,就到了半山腰,海拔还不高,气候与坝区相差不大。再往上走,几乎都是在绕着山腰在不断地攀爬,随着远处坝区的景致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此时已经身处2000米以上的高海拔地带,两旁山岭陡峭,远处山崖如削,莽莽苍苍的黛绿色山峦一眼望不到头,龙村就置身于这些群山中的一个山梁上。这样艰险的路途,在县乡公路没有修建之前,班车无法通行,村民出行全靠拖拉机和摩托车。遇到雨季,泥滑路烂,车辆难以通行,村民只能步行下山,或者把待办事项暂时搁置起来,待天晴时骑摩托车或坐班车到镇上和县上去办理。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的人们,每日面对的都是默默无言的崇山峻岭,接触到的生人少而又少。大部分人靠耕种不多的田地,放养一些不多的牛、羊以及圈养一些鸡、猪为生,自然环境塑造出人们的乐天知命、与世无争的处事原则。由于日常生活中缺乏外界的刺激,人们自然形成一种安静自适的精神状态,人们变得更加沉稳、平静、中庸,对人对事不再斤斤计较。
自成一统的自然环境,无形中使得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种地缘性的亲密和体贴。
从行为选择理论上讲,地理环境影响着人们对待他人的行动原则。由于地理环境限制,龙村是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交往间的利益博弈是一种长久的“重复博弈”.顾名思义,重复博弈(repeated game)是指同样结构的博弈重复许多次。按照罗伯特·奥曼(Robert J. Aumann)提出的重复博弈理论,当博弈只进行一次时,每个参与人都只关心一次性的支付;如果博弈是重复多次的,参与人可能会为了长远利益而牺牲眼前的利益,从而选择不同的均衡策略。因此,重复博弈的次数会影响到博弈均衡的结果。“虽然人们每天都要面对一些所谓的对手和竞争者,战略情形也大量重复出现,个体间也常常发生直接的利益冲突,但是达成合作的几率还是会上升。”
如果是在一个每天面对陌生人的社区,互不相识的人之间很可能为了一点点小事争吵、打架,因为彼此都知道,这是一次性博弈,吵过、打过以后谁也不会再见到谁,因此谁都不想吃亏。但是,在龙村这样的村落中,很少有陌生人,发生矛盾的都是以后将要经常见面的人,大家都会互相谦让,免得以后抬头不见低头见时尴尬。因此,在传统的村落中犯罪率都会很低,人们之间处理纠纷的方式也显得比起城里人更注重关系的维护,不会轻易让一两次纠纷打破以后长久的和谐关系。
隔绝、单调的环境,迫使人们共同生活在一起,虽然相互的交往增多必然会发生更多的分歧和日常生活的摩擦,但这种日积月累的密切接触,也能使彼此间更熟悉,加深相互间的感情与理解。所以,俗语说“远亲不如近邻”,表明长期的相邻而居能够形成一种亲热和默契,这种感觉能够使得人们之间在进行交往时显得更能宽容和亲近对方,进而构筑起和谐的关系网络。从更深的意义上说,长期的共同生活,为形成一种共同的村落文化提供了条件。尽管“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血缘与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但“没有共同的地域,也就没有中国的村落家族。”所以,“共同地域是十分重要的,它对透视村落家族的意义,不低于血缘关系。因为一定规模的血缘关系网络,都是在能提供一定的物质资料或生活资料的地域上发展起来的,没有这一项条件,定居型的村落家族文化难以形成。”身处同一村落文化范围下的村民们,能够保持一种较为一致的行动逻辑,形成一种较为相似的待人接物方式,彼此间也更容易沟通和理解,从而形成村落人际秩序的和谐局面。
三、地理环境与纠纷类型的表现
龙村的纠纷类型中有几类是与地理环境紧密相关的。其一,山区交通肇事纠纷。山区路途遥远,很多村民为了出行方便或到集市赶街,都骑摩托车或坐拖拉机出行,但由于路况差,安全系数低,导致近年来摩托车、拖拉机翻车等事故频频发生。其二,喝酒引发的纠纷。龙村男性村民喜好喝酒的人不少,因为喝酒导致的吵架、打架等纠纷出现较多。
龙村村民喜欢喝酒的原因,除了个人习惯外,还有气候、地理方面的原因。因为龙村地处高寒山区,平均气温总要比坝区低几度,人们为了驱寒,总是喜欢喝酒以达到暖身的作用。而封闭的自然环境,让人生活在一个熟人社会中,村民们总喜欢围坐在一起喝酒、聊天,往往会因为喝酒斗嘴引发纠纷。并且,嗜酒也会引起家里人的不满,导致家庭内部的争吵。其三,家庭内部纠纷。在闭塞的地理环境中,家庭内部的纠纷一直是数量最多的纠纷类型,这也许是由于封闭的环境更容易让人们眼光向内,专注于家庭生活,对家庭矛盾无处排遣,由此矛盾纠纷增加。其四,资源争夺纠纷,突出的是争水纠纷。由于龙村地处滇中干旱区,缺水问题历来严峻,致使争水导致的纠纷这些年来在龙村一直占有较大比例。这些纠纷,既有本村人之间发生的,也有本村人与外村人之间发生的。
但是,地理环境也会使得某些纠纷出现的可能性降低。比如,由于封闭的地理环境,龙村商品经济不发达,村民的经济交往活动不多,经济纠纷自然就少,至于名誉权、知识产权等方面的纠纷更是闻所未闻。并且,地理环境也会使得纠纷发生的范围较为局限。比如,封闭的地理环境导致对外交往匮乏,与陌生人之间的纠纷发生频次少,纠纷主要发生在在本村人之间,或者是与邻近相交往的人员之间。正因为这样,才使得龙村纠纷显示出了熟人社会的诸多特征。
四、地理环境与解纷方式的选择
埃文斯·普理查德在《努尔人》中论述了空间结构与政治机构之间的关系,认为一定的空间结构影响着政治结构及其政治价值观念,即“努尔人把构成其政治结构的某些价值观念赋予到了这些分布中去”.在普理查德笔下,空间结构包含了物理距离与生态距离。物理距离是“棚屋与棚屋、村落与村落、部落区与部落区等等之间的距离以及它们各自所占的空间。”而生态距离则是“社区间的一种关系,这些社区是以人口密度及其分布状况来界定的,同时也与水源、植被、野兽以及虫害等情况有关。”比较而言,物理空间的“意义非常有限”,因为“尽管生态空间受着物理距离的影响,但它并不仅仅是物理距离,因为它还要通过介于地方性群体之间的土地的特性以及它与这些群体成员的生物需要之间的关系进行推算。”因此,以“价值观表达”的“人们群体之间的距离”更为重要。
在这里,普理查德的研究旨趣在于探寻空间结构对于社会中政治行为的影响,以及空间结构距离与关系距离的可变关系。普理查德所讲的空间结构,其含义虽与地理环境有一定出入,但地理环境应该是空间结构的一种表现。从具体的一个村落或一个社区的人们的行为方式来看,探讨地理环境的影响是较为贴切的。其实,空间结构距离不仅仅能对政治结构产生影响,也能对人们的纠纷解决发生作用。从笔者观察到的龙村实际纠纷解决来看,这种作用在多个方面都有体现,但其中最应该引起注意的是地理环境对村民们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具体而言,这一影响主要体现在人们对纠纷解决主体和纠纷程序的选择上。在龙村,当人们有了纠纷,最能寻求的解纷者首先是村内有威望的人,这些人包括宗族中的长者、退休回家曾经在外面工作过的人等等。这些人就生活在村民们中间,与纠纷当事人的“空间距离”基本处于无缝隙状态,请他们解决纠纷,较为方便快捷。如果他们解决不了的时候,村民们往往会把纠纷提交到村委会解决。相比村内权威的解决而言,村委会解决带有“公”的色彩。而从地理距离上看,到村委会解决纠纷需要花一定的成本,如果是属于村委会驻地的村民,到村委会很方便,不需要化过多时间。但龙村另外的一些自然村,分布在方圆几公里远的范围内,崎岖的山路决定了这几公里路具有比坝区平路上同样里程远得多的物理距离。如果是青壮年,可以骑摩托车和驾驶拖拉机,这点路程倒不算什么,但对于妇女和年老者来说,只能步行,这就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所以,当遇到纠纷的时候,住得离村委会较远的村民就会掂量一下有没有必要跑这么远的山路来村委会寻求解决。在实践中,大家普遍的做法是等到每周一次到龙村集市赶街的时候,顺便到村委会反映问题,寻求解决。有的时候,纠纷双方能够一起到场,这样村委会干部就能很方便地进行调查、调解;但很多情况下,只会有一方先来反映、控诉,这样,村委会干部就只能用电话通知另外一方到村委会来参加调解,或者约定一个时间让双方同时到场举行调解。
在龙村,村民们很少把纠纷提交到镇里、县里解决。笔者在镇司法所看到的一些案例,往往都是司法所主动送法下乡,为村民解决纠纷的结果;而在派出所看到的案例,一般也都是派出所主动出击进行治安调解的成果。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除了观念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地理环境。几十公里远的路程让村民们在选择解决纠纷机构时,往往都会把镇里、县里的正式解决纠纷机构排在最后。
只有那些在村委会确实难以调解成功的事情,当事人才会“不计成本”地到镇里寻求解决,一般情况下,大家都觉得到镇里、县里请求解决纠纷是一件“划不着”的事情。并且,地理条件还会影响人们对纠纷解决结果的认同。在当事人不认可村委会调解意见的时候,如果镇司法所就在不远的地方,当事人肯定会到镇司法所请求再调解。但如果镇司法所距离很远的话,当事人也许就会认为“算了,不想花时间和精力了,亏一点就亏一点吧”,从而对村委会的调解意见予以认同和接受。唐纳德·布莱克的研究从“关系距离”的角度阐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关系距离的存在容易引起法律的使用而亲密性排斥法律的使用。”
而关系亲疏的形成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地理位置的远近。龙村这种封闭的地理环境形成了人们之间密切程度很高,关系距离很近,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当有了矛盾的时候,都顾及相互之间的情面。在龙村,选择到镇里去反映、去打官司等等举动,都会被视为是不讲情面的贸然行为,遭到的将会是对方的心理排斥,今后两家关系面临着断绝的危险,至于纠纷处理结果如何,反而倒不是很重要了。因此,人们一般通过调解等方式解决纠纷,不到万不得已,大家不会选择提起诉讼,“当一个纠纷当事人完全有可能诉诸法律时,为了和对方当事人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他极可能会选择忍受对方对自己的伤害或者选择非正式的程序解决自己所遇到的纠纷。”
多年来,虽然村民之间会有纠纷发生,但大多属于鸡毛蒜皮的小事,村民们在处理这些纠纷时都显得较为克制,一般通过相互协商或村内权威人士调解得以化解,很少提交到国家正式解决纠纷机构处理。因此,龙村村民在解纠纷纷方式上的选择,与当地的地理环境有着内在的联系。
五、结语
纠纷内部并不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封闭结构,相反,纠纷是一种社会中的事件,反映着社会结构中的诸多要素。在西方人类学的发展史上,纠纷研究一直是众多学者关注的核心问题。如马林诺夫斯基、霍贝尔、格拉克曼、吉尔茨等人都对纠纷和纠纷解决倾注了大量的研究心血,并从对纠纷的研究中获得了关于人类社会的诸多一般性理论。总结他们的研究,可以看出他们持有一种把纠纷放诸于社会环境中进行考察,以及对纠纷进行文化分析的进路,这与此前不少法学家习惯于从规则和制度角度进行的规范研究相比有了较大的视野扩大和理论提升。而正如龙宗智教授所言:“文化研究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特征,它注重制度与现象发生、存在的环境(参照系)并利用社会学方法作环境考察。”
在我们对当前少数民族地区村落纠纷解决的研究中,也需要采用这种进路,即不单纯分析当地纠纷解决的规则,而是从社会和文化的视角来分析纠纷。通过本文的论述,我们看到了地理环境对当地苗族村民解决纠纷机制的形成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我们知道,在广大西部民族地区,地理环境闭塞、交通落后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对此,我们应该从改善当地的交通、水利、通信等基础设施出发,让广大村民更多地实现与外部世界的接触,让国家司法机关更多地为村民们熟悉,实现更多的司法意义上的“国家在场”,使得国家正式解决纠纷机制成为村民们解决纠纷时的实然选择,让法治的精神和力量在民族地区得到更加充分的实现。当然,我们从地理环境角度强调其对法治的重要意义时,也不应走入另一个极端。因为,相比地理环境而言,在实现社会变革方面,人的作用毕竟是更为积极和关键的,因此我们应该辩证地、历史地看待地理环境的作用。
本文之所以提出要通过改善交通等基础设施来提升当地村落纠纷解决的法制化程度,就是意欲阐明人在自然面前并不是无能为力的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