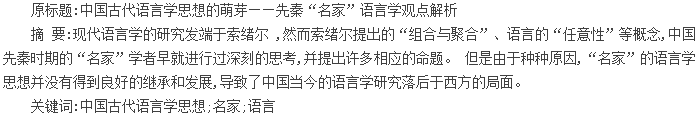
由于种种原因,当今国内的语言学研究并不是传承于中国古代文明体系,而主要是通过借鉴西方的语言学研究理论而展开的。西方现代语言学研究发端于索绪尔,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让人们认识到了语言的巨大力量, 从而引发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场“大风暴”。 其影响不仅仅局限于语言学,而且还延伸到了文学、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诸多人文学科领域。从这一点来讲,我们甚至可以把 20 世纪称之为语言的世纪。 经过长期的发展,今天的西方语言学研究产生了诸多的学派,但是无论如何,谁也无法绕过索绪尔这位现代语言学之父提出的言语与语言、能指与所指、历时与共时、组合和聚合等基本概念。
事实上,索绪尔提出的某些语言学概念,早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就有人进行过思考。 在先秦时代,以惠施和公孙龙为代表的“名家”提出过很多看似匪夷所思的观点,被当时的学者文人斥为“狡辩之徒”,一直到近代才有人认识到名家思想的价值并为其平反,但是近现代的名家思想研究主要是集中在了哲学和逻辑学领域,而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名家之学的学者却为数不多。其实“名家”提出的许多观点用哲学理论来解释稍显牵强, 而如果从语言学的角度去理解,就会变得豁然开朗起来。
一、 “白狗黑”等命题和“语言的任意性”
“白狗黑”,这是“名家”提出的一个著名论断。 这个论断乍看起来似乎是自相矛盾、难以成立的。 对于这句话历代以来有多种解释,其中较为流行的解释为《经典释文》中引用司马彪的话:“白狗黑目,亦可为黑狗。”这种解释认为白狗的身上也不可能到处都是白的,比如眼睛就是黑的。 以毛色论,可以称之为“白狗”,而以眼睛的颜色来论,却可以称之为“黑狗”。 这种哲学角度的解释颇为勉强,缺乏说服力。 如果“名家”的本意确实如此的话,真要沦为不折不扣的狡辩之徒了。
那么“名家”此言的本意究竟如何呢?让我们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看, 为什么白狗也可以叫做黑狗呢?事实上,“白狗”只是人们给白色的狗人为加上的概念而已,如果在命名之初,把白色称为“黑”,那么白狗不就应该被称为“黑狗”了吗? 其实这个论断的提出,就是为了说明语言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语言的任意性。
语言也是一种符号,并且是人类使用最广泛的符号, 索绪尔认为:“我们把概念和音响的结合叫做符号,用所指和能指分别代替概念和音响形象……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指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更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例如‘姐妹’的观念在法语里同用来做它的能指的 s-觟-r(soeur)这串声音没有任何内在的关系; 它也可以用任何别的声音表示。
语言间的差别和不同语言的存在就是证明:‘牛’这个所指的能指在国界的一边是 b-觟-f(boeuf),另一边却是 o-k-s(Ochs)。 ”
索绪尔在这里明确地告诉了我们:事物本身和人们用来指称事物的语言符号并不是一回事,在语言确立之前,二者并无必然的联系,这就是语言的任意性原则。索绪尔使用了“姐妹”和“牛”这两个词来论证语言的任意性, 而先秦的名家则使用了“白狗黑”这一更加形象更具智慧的说法,反映了名家对于“名实关系”的深入思考。因此,“名家”提出“白狗黑”的论点,并不是要颠覆人们的常识,更不是故意违反语言的“约定俗成”的特性,而是名家的学者们通过对语言的深刻思考,提出了语言的任意性这一超越当时人们认知水平的命题。 可惜的是,当时的先秦诸子并没有认识到语言问题的重大意义而缺乏对语言的了解和思考,使得他们对语言的认知能力远远落后于“名家”的学者,这就造成了“名家”在当时得不到理解的尴尬局面,而沦为诸子口中的“诡辩之徒”。
除“白狗黑”外,“名家”的一些其他命题如:“狗非犬”、“犬可以为羊”、“龟长于蛇”等,都可以进行类似的分析。 这些命题虽然听上去大悖于常识,但却都是为了说明语言的任意性这一原则,其中包含了“名家”对语言问题的深刻思考。
二、 “白马非马”的语言学诠释
白马非马”见于《公孙龙子》中的《白马篇》,由“名家”代表人物公孙龙提出,是先秦最著名的辩题之一,这个辩题含义颇广,长期以来有很多人对它提出过各种不同的见解。 与“白狗黑”一样,这个辩题也可以用语言学的理论来进行分析。索绪尔提出,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是语言系统中的两种根本关系。 在公孙龙看来,“白马”就是由两个构词语素组合而成的一个偏正结构复合词,而“马”只有一个语素, 或者说它只是一个单音词, 由此看来,“白马”和“马”自然不能等同。
对于“白马”一词,有一种新颖的观点认为:在公孙龙看来,“白马” 一词不是偏正结构而是并列结构。其理论基础是公孙龙在《坚白论》中提出的“离坚白”理论,认为公孙龙把“坚”、“白”、“石”看做是三个独立存在、相互之间没有必然联系的概念,这三者之间的地位是等同的,所以把这个理论用到“白马”上,“白”和“马”一个指的是色、一个指的是物,二者之间也是平等的关系。 让我们看看《坚白论》的原文,这种观点真的正确吗? 请看《坚白论》中这样一段话:
“坚白石三,可乎? ”
曰:“不可。 ”
曰:“二,可乎? ”
曰:“可。 ”
曰:“何哉? ”
曰:“无坚得白,其举也二;无白得坚,其举也二。”
曰:“得其所白,不可谓无白;得其所坚,不可谓无坚。 而之石也之于然也,非三也? ”
曰:“视不得其所坚而得其所白, 得其百也无坚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坚,得其坚也无白也。 ”
在第一个问答中, 公孙龙就明确说明:“坚白石三,不可。 ”因此,公孙龙并没有把“坚”、“白”、“石”看做是三个并列关系的概念。 接着他又说:“二,可。 ”这说明他认为“坚”和“白”都是用来修饰“石”的形容词,或者是“坚石”,或者是“白石”,所以他认为是“二”。其后他又论证了“坚”和“白”这两个形容词的关系,“坚”和“白”二者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他们并不能融为一体,因此才要“离”。“离坚白”理论总的“离”字,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其一,要把“坚”和“白”这两个形容词相离,这二者一个是触觉形容词,一个是视觉形容词, 是不能合二为一的。 “他主张,‘既认为此石是坚的,则不能同时认为是白的’,‘既认为此石是白的,则不能同时认为是坚的’,这叫‘坚白石二’。 ”
其二,要把“坚”、“白”这两个形容词和“石”这个名词相离,这两个形容词都可以用来修饰名词“石”,但他们又都并不固定附着于“石”:“坚”可以用来形容“石”,也可以用来形容其他坚硬的东西;“白”可以用来形容“石”,也可以用来形容其他白色的东西,这其实是一种聚合的关系,形容词或者名词在语言中是可以被替换的。
在公孙龙看来,形容词在语言中虽然占据重要地位,但仍然是用来修饰限定名词的,所以“白马”一词还是应该理解为偏正结构而不是并列结构。“白”是用来修饰“马”的,但是“白”也并不附着于“马”,是可以进行替换的,因此不仅“白马”非“马”,“黑马”、“黄马”乃至“瘦马”、“小马”皆非“马”。 通过“白马非马”这个论题主要想说明的问题就是:复合词的含义不等同于单音词,在偏正结构中形容词处于一种可替换的聚合关系中。
三、 “名家”语言学思想传承缺失的原因
(一)“名家”在先秦诸派中地位不显,和其他显学相比处于劣势
虽然名家之学和儒、道、墨、法在当时被并称为“显学 ”,但 “名家 ”的地位远不能和其他四家相提并论。其原因主要在于,儒、道、墨、法四家不论观点如何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提出的主张都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都是所谓“经世致用”之学。 即便道家的主张是“无为”,但其根本目标还是“无不为”,“无为”只是方法和手段,“无不为”才是其目的。而名家的提出的各种命题更像是纯粹的学术研究,在当时人的眼中看来,这是“无用之学”。 庄子虽然与“名家”的惠施是好友,然而他对惠施的学问却也并不认同:“惠施日以其知与人之辩,特与天下之辩者为怪,此其柢也。
然惠施之口谈,自以为最贤,曰天地其壮乎!施存雄而无术。”如果说庄子对惠施的评价还算是给好友面子的话,他对公孙龙等人的评价则更加不堪:“桓团公孙龙辩者之徒,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辩者之囿也。”可见,“名家”在当时虽然名声不小,但大多数人对它产生兴趣只是因为它的新奇论点,说到底只是好奇心作祟,其真正的心理是不相信名家学说的。 因此,当时的“名家”学者只是学术研究路上孤独奋斗的一群。“名家=诡辩之徒”,这就仿佛是一条不可置疑的真理一般误导着后来者对于名家的认知,使得名家思想在两千年的中华文化传承当中一直处于尴尬的地位。
(二)“名家”的语言学研究远超其余几家,当时的人难以理解
先秦诸子们对语言多少都有涉及,主要体现在对“名”的认识上:孔子讲“正名”,老子讲“无名 ”,墨家讲“以名举实”。 但他们讲“名”还是为他们的政治主张而服务的,在对语言本质的认识上,远远比不上“名家”。因此,“名家” 的学说对他们而言就显得难以认知,甚至是无法认同。 四川大学的刘利民先生认为,名家不被诸子认同的原因有很大一部分是源于古汉语本身存在的问题,他说:“他们为何又被那么多传统哲学家所误解呢? 这恰恰又是由于语言的原因:古汉语不重形式,甚至连标点符号都没有,如果我们给名家的这些‘诡辩’加上合适的标点符号,主要是引号,则他们的思路线索可能就昭然若揭;不仅不是诡辩,而且包含着重要的哲学思想价值……如果一个词在语句中只是被提及,那么通常应该给它加上引号,以示区别,名家那些被视为诡辩的语句也极有可能是名家对其中语词的‘提及’使用,反映了他们关于语言本身的哲学自觉。 ”
这种看法当然有其道理,古汉语缺少标点符号的问题也确实会对理解“名家”的主张造成极大的困难,但是究其根本,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名家”语言思想的超前性,正因为“名家”的语言学研究远远超过当时的认知水平,所以才会被误认为是在进行诡辩。 “名家”思想难以被人理解,自然也就后继乏人。
(三)重实例,轻理论
“名家”学者虽然对语言进行了很多思考,但他们更倾向于举例和比喻, 而很少去进行理论性的概括;他们只是提出一些命题,却并没有从理论上对这些命题进行语言学的解释。因此只能说“名家”的语言学思想还处于萌芽状态。 “重实例”是好的,这能使说理更加形象;但是在“重实例”的同时,也不能“轻理论”,因为举例就是为了更好地说理。 因为缺乏概括性的理论,不利于“名家”语言学思想的传播,这就使得中国古代处于萌芽状态中的语言学思想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展,形成了今天中国在语言学方面落后于西方的局面。
四、小结
中国早在先秦时期就出现了对语言的理性思考,产生了语言学思想的萌芽。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名家”的语言学观点既没有得到接受和普及,也没有得到传承和发展。这使得刚刚处于萌芽状态的中国古代语言学思想被扼杀于摇篮之中。如果当时“名家”的语言学思想得到了很好的接受和传承的话,那么在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发展史中,对于语言的认知和研究必然会达到一个相当的高度,而中国当今的语言学研究状况可能将会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番局面。
参考文献:
[1] (唐)陆德明.经典释文汇校[M].黄焯,汇校.北京:中华书局,2006:830.
[2]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02-103.
[3] 公孙龙.公孙龙子[A]//谭业谦.公孙龙子译注[C].北京:中华书局,1997:37-38.
[4] 庞朴.公孙龙子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79:84.
[5] 庄子·天下[A]//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3:896.
[6] 刘 利民.论先秦名家 “诡辩 ”的语言哲学意义———从 “ 使用”与“提及”的观点看[J].四川大学学报,2005(6):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