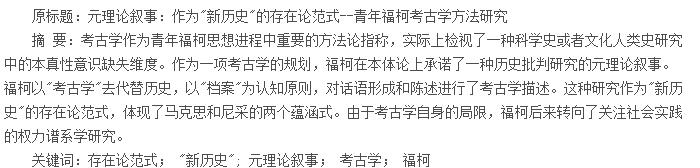
考古学是青年福柯哲学沉思的重要方法论范式即"用一种隐性理论和文化结构有序性读出可见事实和文字背后的某种'未说出之物'"的侦探路径,其核心构件是"认识型""档案""非连续性"及"话语实践"等认识论命题。考古学在福柯早期文本那里大致勾描了《古典时代的疯狂史》(1961)中的"沉默的考古学"、《临床医学的诞生---医学视角考古学》(1963)中的"视的考古学"、《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1966)中的"观念考古学"、《认知考古学》(1969)中的"话语考古学"、《话语的秩序》(1971)、《尼采、谱系学、历史》(1971)中的"谱系学的考古学"以及《性经验史》(4卷)中的"性的考古学"等几种类型。虽然福柯认为其考古学可以设想许多不同的类型,但是他最终只阐述了认知考古学一种类型,我们这里讨论的就是这种有别于观念史、科学史、思想史、哲学史和文学史等专门史的所谓"新历史"一种的认知考古学。在本文中,笔者将重点讨论青年福柯的《认知考古学》中出现的这种批判语境中的考古学范式、发生机制、存在论新意及方法论局限等观点,以期作进一步的深入思考。
一、方法论的隐喻:考古学的范式生成
考古学作为青年福柯思想进程中重要的方法论指称,实际上检视了一种科学史或者文化人类史研究中的本真性的意识缺失维度。从《疯癫史》到《性经验史》,福柯认为他的研究有别于正统的观念史或者思想史叙事,他称自己的作品为"描述思想的考古学","这种研究反对理性主义的目的论和总体性的连续历史描述,而转向断裂性地关注边缘和黑暗处的异类生存。"[1]
福柯以"考古学"去代替历史,是对其研究姿态的一种隐喻式描述,话语的比喻理论源自维科,福柯作为后继者把这种修辞技巧诗学化了,并形成了一套描述差异和他者的独具"风格"的话语体系。他说:"与历史十分相似,考古学只有重建某一历史话语才具有意义。历史现在不断地趋向于考古学---即对历史重大遗迹作本质性的描述。"[2]PP6-7所谓考古,就是对传统思想主题的全然漠视。认知考古学只对历史中的裂缝、非连续性和实证性的崭新形式乃至突然的再分配感兴趣,对意识历史中的多种时代之间的差异而不是类同感兴趣。传统历史学家对连续性的研究只不过是一种时间广场恐怖症。[3]P113因此,福柯说:"考古学针对处于知识与认识论形态和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知识"[2]P218.
那么,考古学、科学和知识之间如何架起联系的桥梁呢?何以形成有效的知识为科学和考古学区分出不同的范围和领域呢?这是认知考古学范式得以生成的重要认识论前提。青年福柯说,他关注的考古学测探"观念和科学知识得以确立的现实历史基础,正是由于这个作为隐秘基础的'有序空间'的存在,知识才得以建构,它正是现代合理性得以塑形的真正基石。"[4]
诚然,"考古学并不贯穿意识-知识-科学这条轴线,它贯穿话语实践-知识-科学这条轴线。"[2]P204换句话说,认知考古学得以确定的根基不是"通过越界或者隐退行为开辟一个由语言去"言说"的空间,而是把以下事实作为出发点:在一个既定领域内的任何既定时期,都存在对人们思维方式的实质性限制。"[5]P34
这种限制的规则就是青年福柯指认的那个看不见的"未说出之物",即考古学揭示的知识的实证的无意识,这就是福柯在《词与物》中表述的:认识型,"它是在话语实践的实证性中使认识论形态和科学成为可能的东西。它与所有其它的知识哲学的分界线是它不把这个事实归结于对某个可能在先验的主体中建立事实和权力的原初的馈赠的审定,而是把它归结于历史实践的过程。"[2]P215这里,福柯把话语实践的形成分析作为再嵌入的历史分割把超越实证性、认识论化、科学性和形式化界限的努力,实现为不同界限之间相互支配、彼此包蕴和轮番建立的条件在时间上的分配或某种连续、间距和可能的巧合,作为考古学开发的重要领域之一。笔者以为,福柯的这种考古学界定倒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存在某种内在的同构性,因此,我们回过头来审视福柯的考古学范式生成不能仅凭其构思的"我思"(纯粹话语分析的规划)和"无思"(解释的力量)性,而惯性判定其作为某种新话语的非连续性和盲目性。考古学的隐喻只是为了更好地说明福柯研究方法的明确性和本真性。
二、考古学的发生机制:话语形成分析中的陈述和档案
福柯认为,考古学是确定"话语实践独特的特殊性"的工具。考古学只有通过对"话语事件的领域"进行分析和描述(显而易见,这个描述有别于语言分析)才能显示其意义,描述话语事件就是描述一个话语是怎么形成的即话语形成分析。我们试图通过福柯对"话语事件领域"的分析来揭示其考古学的发生机制。"话语事件领域是由一整套陈述(口头的或书面的陈述)建构而成的,这些陈述通过它们作为事件的偏离和它们每个都专有的直接性而全部起着作用。"[6]P55德勒兹认为福柯"只看重那些陈述"[7]P7,考古学的基本概念是陈述,福柯的"话语"概念是建筑在"陈述"概念的基础上的。在福柯看来,陈述是属于符号域的范畴。从符号群中,语法学识别出句子,逻辑学识别出命题,考古学识别出陈述。陈述标识一种符号的功能,特定数量的陈述被归结为一个集合(话语),对这个集合形成规则的描述,涉及了某个具体话语形成的考古学分析。
实际上,依福柯自己的理解,每一个话语事件整体都以某种话语配置确定自身的领域,这个领域与"诸陈述被约定俗成地划归其中的那些传统、可见的统一体没有丝毫重叠",它作为一种差异和离散的控制系统即"话语的实效范畴",支配着话语的形成。简言之,"话语描述所关注的是把握处身于话语事件狭隘性和唯一性之中的那个陈述;测定它的存在条件,尽可能确定它的边界,确立它与其他陈述之间的关联---它在其中与其他陈述联系起来的那种关联,并说明它所排除的其他联结方式是什么。它并非是在显白话语之下去竭力谛听其他话语的喃喃私语。"[6]P56就观念考古学家而言,一个知识历史的特定时代便是一个发掘的遗址。为进一步勘探这种考古学的发生机制,福柯把对个别话语事件的描述升级为对文化中话语事件的存在模式的考察,这就涉及对福柯关于"档案"的理解,即"在话语实践的深度中看到一些把陈述当作事件(因为它们具有出现的条件和范围)和看作事物(因为它们包含使用的可能性和范围)的系统。"[2]P143在考古学看来,这是它的意义的诞生地,档案作为话语形成可能性的一般条件,建立起了考古学可说(话语实践)与不可说(非话语实践)的界限。
然而,福柯紧接着又强调,档案作为可能性的一般条件,其所体现的规则并不是形式的先验知识,也就是说,它不是一种"其权限并非偶然的扩展",而且"本身辩证法的形式的必然性展开"的永恒不变的规则;恰恰相反,档案所体现的规则是一种"历史的先验知识",简言之,"它要阐述话语不仅具有某种意义,或者某种真实性,而且还具有某部历史,即一部特殊的,不把话语归结于某种与它无关的变化规律的历史。"[2]P142我们说,一个既定时期的档案是由话语形成的总体或全体陈述组成的,这种话语形成的总体或全体陈述通过实效范畴建构起一套元素(对象、表述类型、概念和理论选择)形成了一种既定领域的知识。在这里,福柯对知识进行了区分:知识和认知,这两个词分别被福柯用来指知识可能性的条件与历史决定的知识形式。
依福柯自己的说明,"在档案的一般要素中分析话语事实,就不能把这些话语事实看成是记录,而要把它们视为遗迹",档案的工作就是去做"词源学规则允许我们称之为考古学的事情"[6]P58福柯在话语的形成分析中,引入档案这一构件,规范了陈述的活动,夯实了话语实践的认识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