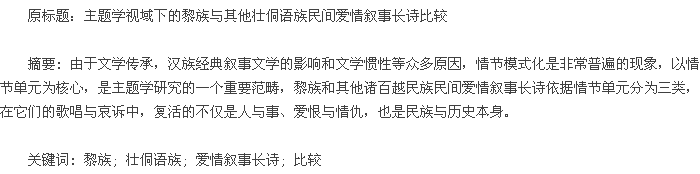
民间叙事长诗是与创世史诗、英雄史诗相并列的一种叙事长诗类别。它不像创世史诗和古代英雄史诗那样反映部落历史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而主要表现个人生活中的爱情纠葛,个人合理欲望与社会制度、社会习俗的矛盾关系,是当时社会婚姻制度和习俗的反映和当时人民的爱情理想和愿望的表现。其中爱情类型是一般民族中叙事长诗较为丰富的。黎族与居住在云南、贵州、广西等的傣、壮、布依、侗、水、毛南等族属于汉藏语系的壮侗语族,他们的渊源可追溯到古代百越族群的滇越、骆越、西瓯。黎族中属于爱情长诗的如《甘工鸟》、《猎哥与仙妹》《巴定》《四季歌》等; 傣族的如《召树屯》《娥并与桑洛》《宛纳帕丽》《玉南妙》《南波冠》《葫芦信》等等,极其丰富; 壮族的如《唱文龙》《唱离乱》《幽骚》,布依族《光铁芳》《布卡和兰莎》,傈僳族的《重逢调》《逃婚歌》,侗族的《珠郎娘美》,《秀银与吉妹》等等。在民间叙事长诗特别是爱情叙事长诗中,由于文学传承,汉族经典叙事文学的影响和文学惯性等众多原因情节模式化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以情节单元为核心,是主题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范畴,下面就把黎族和其他壮侗语族民间爱情叙事长诗依据情节单元进行分类、阐释,挖掘他们同属壮侗语族的共性和在发展中形成的各自的民族特色。
一、爱情—阻挠—幻化成某种东西的情节模式
《甘工鸟》在黎族中有民间故事、叙述短诗与杜桐由搜集的短诗创作的叙事长诗三种形态①。作为文人创作,《甘工鸟》由二十几行的短诗增加的两百余行,也由完成了原来的民间爱情故事到国家意识形态的转变,爱情在故事中升华,斗争也在长诗里形成。从长诗中的爱情形态来看,《甘工鸟》讲述的是民间爱情故事中最为常见的爱情与阻挠主题,像所有这类爱情故事一样,长诗中的人物或者说角色除相爱的男女外,有一个第三者,也即角色中的三号。这样故事的主角即是阿甘、劳海这对爱人和帕三顺这个反面角色,围绕这正反两面,形成了两种观念与意志的抗衡,最终是恶与丑的代表赢得了某种胜利,但善与美却在失败中或失败后赢得了另一种胜利,而且这种胜利往往是最终意义的。因此《甘工鸟》所形成的故事是这样的: 美丽善良的姑娘阿甘和勤劳英俊的猎人劳海相爱,但地主奥雅之子帕三顺看上了阿甘,于是逼婚,逼婚不成便抢亲。劳海受伤逃入山中,阿甘被关押起来。恶与丑先取得一场胜利。在关押中阿甘得到仙人的帮助,插上银翅变成了一只美丽的飞鸟,这时劳海恰好来骑马来解救她,双双逃走。于是爱情出现了转机,命运开始倾向于善与美的代表。从这里开始故事的讲述开始出现分歧: 一种结局是他们在与随后追赶来的帕三顺的混战引起的大火中双双化为飞鸟,鸣叫声如“甘工”,于是人们就叫它们为甘工鸟; 另一种结局是他们打败了随后追赶来的帕三顺,而且阿甘重新恢复人形,和劳海一起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而且还要为其他的穷人谋取幸福。从中可以看出,前一种故事结局是悲剧性的,在这种结局中,恶与丑在胜利的同时又失败了,而善于美在失败的同时又胜利了,前者的胜利属于世俗意义上的,从精神这一维度来说是失败的,后者与此恰好相反。后一种结局显然是喜剧性的,是大团圆的典型。在这种故事结局中,命运最终和善与美同在,当它们同时胜利到达终点时,它们已经完成了一种道德训诫。因此,这种胜利的主角其实是道德,而不是爱情本身。不言而喻,这两种结局都有它的现实基础,但依然能够作出某种区分,如前一种现实的基础是历史,后一种的则是心理。在前一种结局中,善恶美丑都分别得己之所得、失己之所失,从而形成历史的辩证、达到了历史的平衡; 后一种结局的心理基础使善恶美丑本身被强大的国家意志取代,由此也使民间爱情胜利转变为国家意志胜利,于是民间故事的主角及主题都悄然滑向国家意志,并失去历史的辩证与平衡,最终,国家意志被自身的强大逻辑推向历史,成为历史本身。这种角色与主题转变的实质,就是民间伦理被纳入了国家意识的轨道。当然,杜桐的《甘工鸟》选取的是后一种结局。
从历史演变角度看,这种在民间爱情长诗中广泛存在的三角模式,应该是人类远古婚姻从群婚向一夫一妻对偶婚,“从夫居”取代“从妻居”过渡阶段在后代的某种遗留,而这种男人或者说雄性间的角力又是所有生物的本能。不过在“甘工鸟”这个故事中,还有另一种原型,即“羽衣仙女”故事。
“羽衣仙女”故事是广泛存在于民间的一种故事模式。一般而言,故事讲的多是作为凡人的男主人公和仙子相爱,而由于某种阻挠或者过失,仙子或者丧失了羽衣化仙的可能,或者男子失去仙子。当然,“甘工鸟”的这种“羽衣仙女”故事色彩已经很淡了,只保留了“变形”。不仅开始阿甘也是凡身俗体,而且从故事来看,可以说它本来说的是“甘工鸟”这种鸟的来源,是属于风俗、风物诗范畴的。但在傣族《召树屯》《孔雀姑娘》中,“羽衣仙女”故事原型色彩的很充分。
《孔雀姑娘》讲的是一个由现实变成的神话故事: 从前南浪湖畔有一个叫勐庄的寨子,有一个姓刀的老人有七个莲花一样美丽的女儿,最大的女儿依腊和邻村的岩永相爱。岩永是孤儿,但勤劳善良。同样住在岸边的凶恶残暴的魔王看上了依腊,提亲不成就抢亲。依腊被关了起来,岩永在救依腊时被魔王发现并被打死,依腊自杀。魔王仍不甘心,在丧礼中要来娶二姑娘。被赶走后,魔王为了报复,当天夜里把老人住的竹楼烧毁,在浓烟烈焰中飞起七只孔雀,它们沿着寨子和湖面盘旋三圈后飞走了。原来这七个美丽的姑娘是孔雀的化身,因羡慕人间而下凡,但最终失望而去。此后每年的正月初七的晚上,就会有七只孔雀在湖中洗澡。飞来时她们哀伤的唱道:
飞啊,飞啊
我们又回到我们思念的地方
啊,我们不知道是欢乐,还是悲伤
一想起我们住过的竹楼
就听见亲人那含泪的呼唤
只是一看南浪湖
又高兴地看到可爱的故乡
在天亮前她们必须飞回天堂。她们在湖面飞来飞去,凄楚而歌:
故乡啊,我们又要分离
过去的伙伴啊,我们还来不及问候
只一瞬间,我们又要飞走
恨只恨那恶毒的魔王
再见了,故乡让我们再看看你的面貌
从此在元江傣族中形成一种风俗,在每年的正月初七,男女来到湖边歌舞,自由选择爱人; 这一天是青年农男女的洗澡节。
可以看出,《孔雀姑娘》和《甘工鸟》很相似。它们都既是爱情长诗,又是解释风俗风物起源的风俗诗。
在内容上,爱情的角色、过程都如出一辙,不同的只是结局: 《甘工鸟》有不同的结局,而《孔雀姑娘》的结局是唯一的。
《召树屯》中喃婼娜也是孔雀仙子,但召树屯不是猎人和孤儿,而是王子。后来召树屯因为战争出征,留下喃婼娜在王宫,灾难于是降临。国王做了个奇怪的梦,解梦的摩古拉说只有杀了喃婼娜才能解除即将降临在国王和人民的灾难。在利益面前,国王和百姓对喃婼娜的哀求与解释不敢回应。喃婼娜提出在死前要调最后一次舞,“我是来自欢乐的孔雀国。请把我的羽衣还给我,让我最后跳一次舞,再享受一次人生的欢乐。”[2]于是她得到自己的孔雀衣,最后飞走了。出征回来的召树屯得知喃婼娜飞走后历尽艰辛去魔国寻找心上人,下面就出现了在民间爱情故事中经常见到的“难题”求婚故事。当然,相爱的人最终相拥一起。
《召树屯》和《孔雀姑娘》里的孔雀本来是傣族的图腾,其故事是鸟图腾神话和羽衣仙女故事相融合而成的。傣族生活在亚热带的森林中,那里一直是孔雀之乡。但这里故事的背景也有佛教的影子。如在《召树屯》中,解梦的占卜师摩古拉无疑是代表原始巫术的,而他对喃婼娜的忌恨以至于要借机除掉,可能就另有意味了。
二、爱情—阻挠—生离死别或双双殉情的情节模式
黎族的爱情叙事长歌《巴定》具体地叙述了黎族古代社会的婚姻悲剧,巴定在“布隆闺”里有了情人,龙闺是黎族青年男女分别建造在村边的草房,供青年们娱乐,谈情说爱和睡觉用,也就是说黎族社会风俗是允许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但婚姻不能自主,要听从父母之命父亲看重的是钱财是富有,正如诗中所唱:
“龙闺”里头别情郎
铜锣米酒换侬去,巴定终回还
牵来了大牛,送来了蛙锣,抬来了银元,挑来了米酒
父亲眼中女儿心中那炽热的、坚贞的爱情根本不值一提,他根本看不到爱情对女儿年轻的生命有多重要,他以自己的阅历,多年生活的艰辛,一厢情愿的认为经济条件好,女儿出嫁后不愁吃、不愁穿,自己也能得到大量的聘礼,岂不两全其美,所以他先是骗女儿说嫁的是同村寨的伙伴,布隆闺的好友。巴定嫁到番阑,因为公婆刁如猴,整天骂不休。因为新郎又老又难看,巴定心紧楸。重新回到娘家,可是家里人除了他母亲同情外,其他人都历数番阑人家的富有,看重的还是经济条件,爱情只是附庸或者根本不存在,巴定只有重踏公婆家的门,在阵阵大风狂中,忍受对情人的相思之苦; 忍受公婆的辱骂; 忍受丈夫的无情。
巴定最终和情人分离了,独自踏上了悲剧人生的征途,分离他们的与其说是她的父亲不如说是那个物资匮乏、穷苦的社会,古代黎族大都生活在海南岛中部的群山之中,交通不便,自然资源匮乏,一年忙碌到头能吃饱饭就不错了,所以父亲,这个爱情当中阻挠着的角色就非常普遍、典型了,可以说是黎族社会爱情婚姻悲剧的一个缩影。这种因为经济原因有情人劳燕分飞或双双殉情的爱情叙事长诗在其他壮侗语族中也大量存在。如侗族的《秀银与吉妹》,周秀银是崔吉妹家的长工,他们“一年长工,他俩同山做工来相伴;两年长工变成一对难离的情人”[4]290。可见他们是在日常生活中,互相欣赏、互相爱慕,最终成为难分难离的情人的,他们的爱情有坚固的基础,也为日后的殉情做了铺垫,可他们的爱情不被吉妹的母亲理解,她女儿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这么多情? 一天三餐白饭吃得这么香甜,她母亲不知道长工为什么这么高兴? 秀银白天上山不怕苦和累。她母亲不理解女儿为爱痴狂的情谊,不解爱情为何物,也许她只是认为那是小儿女过家家,于是她就自作主张把吉妹许配给薛家财主,她象巴定的父亲一样,首要看的是家庭经济条件,爱情在她眼里是根本不存在的。显然,势单力薄的一对情侣是无力与财高的薛家抗衡的。他们只能用自行支配的言行来控诉无情的现实。例如:
吉妹说: 假如相爱不成妹心碎,黄泉童子带路我愿同哥去阴城。
秀银说: 活着我们应该是一家,死了也要共葬一丘坟。[4]291言语的反抗终究改变不了残酷的现实。秀银终于积气成疾,悲愤难平,最后咬牙翻眼不再醒。吉妹实践了“生要共一家,死要共坟堆”的誓言,吞食了鸦片,双双殉情而死。
傣族的《娥并与桑洛》也是这一类的爱情悲剧。景多昂英俊的小伙子桑洛外出做生意,在孟根找到了意中的姑娘娥并,两人一见倾心,可是他们的爱情遭到母亲的反对,她想把同样是富有商人( 沙铁) 的外甥女阿扁作为自己的儿媳,,在此我们可以看出桑洛的母亲和巴定的父亲、吉妹的母亲是一样的,他们看不到爱情对年轻生命的重要性,看不到爱就是年轻生命的灵、生命的根,桑洛的母亲把儿子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不尊重儿子独立的人格,以自己的好恶、以财富的多寡为儿子选择儿媳妇,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留下桑洛一个人,活着也不再有生命。”[1]617爱人死了,心中炽热的爱恋也没了对象,生命也就从此枯竭,于是他一刀自杀了,倒在了娥并的身旁。壮族的《幽骚》,傣族的《南波冠》同样是这一类爱情故事。《南波冠》
的爱情悲剧是这样的: 管水头人的女儿南波冠在父亲死后给寨子放牧,一天她在山上遇到一只猛虎,危险中猎人首领的儿子宰坝杀死猛虎,救了她,从此两人相爱了。但在结婚前夕,南波冠被国王看中,国王想霸占她,便欺骗宰坝,让他 去森林里捕大象,趁机抢走南波冠。宰坝发现受骗,从宫殿了偷偷带着南波冠,和她一起逃入森林成婚。严冬来临,他们没有食物,也没有火,这时南波冠已怀孕。宰坝外出寻找火种,结果被大雨所阻,当他终于回到家时,南波冠已经在狂风暴雨里因分娩虚弱死去,婴儿也已经被蚁群咬烂。于是他顿脚捶胸,愤愤然质问苍天: “人间为何有这样的灾难?”[1]647宰坝悲愤的埋葬了妻儿,走进大雾之中。
以上长诗中的男女主人公都为争取恋爱婚姻的幸福与自由,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甚至不惜以生命殉情,造成这一悲剧的直接原因是人民的贫富、门第等观念; 是父母对儿女爱情的不理解,不懂爱。不知道他们一味的阻止会造成什么后果; 是爱情与婚姻冲突的结果,南方百越民族有很多习俗是给青年男女的自由恋爱创造机会的,比如黎族的“三月三”壮族的歌玙侗族的“坐夜”“走寨”等等,爱情与婚姻相关联,但爱情不等于婚姻; 在爱情中,主体是人,是相爱双方忠贞不渝的情感; 而婚姻的主体是物,是“聘礼”———是牛和羊,是米酒、肥猪、稻田新房、奴儿,总之是财富与地位。很明显,在二者的对抗中,爱情处在不利的地位。
爱情会导致婚姻,但爱情不一定能成就婚姻。在这里,婚姻并不仅仅只是维持爱情,它还要维护家庭、维持社会。爱得强烈而持久,如不能结合,悲剧便发生了。
三、爱情—阻挠—团圆的情节模式
黎族的《抗婚歌》偏重于抒情,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可能把其归为抒情诗更合适。但从它确实具有事件过程以及和其它黎歌相比篇幅稍长上来看,这里仍把它放在叙事诗的范畴中。
《抗婚歌》叙述的是一对相爱的男女为了爱而远走他乡的故事。整个歌是以女主人公的口吻叙述“我俩”的爱情经历:
双双坐在山坡上
拔弄着茅草尖
扫弄着茅草尾
我俩的爱情很不幸
心里象针扎一样苦
因为阿拜给我另定婚
我俩转来转去
哭上了溪流和深潭
你站在溪那边哭着
我站在潭这边哭着
眼泪把纱线染上色
他们相爱了,但他们的爱情遭到女方父亲的反对,给女儿另定了婚事,他们被迫到遥远的天边,到汉人居住的地方。在那他们与异乡人友好相处,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男女主人公的爱有了归宿,但他们陷入对家乡和亲人的无尽思念中,最终踏上了回家的路。当他们———远远望去,见到了故乡的椰梢,我们轻轻的,轻轻的叹气———[3]2长诗的开头和结尾时诗中最为动人心魄的部分。一个是离乡前的彷徨哭泣,一个是多年之后回乡是的遥望叹息。对于这对相爱的人来说,回乡可能是另一种离乡。这种开始就是结束、结束即开始的故事结构,使时间与空间静止,从而和“抗婚”“逃婚”主题的紧张相呼应,叙述效果令人震感。黎族的另一篇叙事长诗《猎哥与仙妹》也是以大团圆模式结尾,猎哥从小父母双亡,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慢慢长大,猎哥勤劳、勇敢、技艺高强,虽然有很多姑娘爱猎哥,但因为他是“孤寒仔”,父母都不愿将女儿嫁给他。七指岭上的仙女听到猎哥的爱的哀歌,下凡和猎哥成亲,有情人成眷属,同村的财主打西看到仙妹长得漂亮,就派人把仙妹劫走,猎哥在神仙的帮助下,最终战胜打西“忽然山洪滚滚下,冲得打西命都无”[3]479。猎哥与仙妹的胜利得益于仙人的帮助,这是幻想的胜利,是一种精神胜利法的表现。在古代社会,爱情在金钱与权势面前,抗争也是无用的,往往会落得悲剧性的结局。所以他们便借幻想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慰藉。如果第二种爱情模式是现实残酷的反映,那么这一类爱情叙事长诗则是人们美好愿望的体现。
这种通过神仙救助或有威望的人帮忙取得爱情胜利的情节模式,在壮侗语族爱情叙事诗中占相当一部分。如布依族的《金竹青》,她叙述布依族姑娘郎秀和后生凡龙在丢花包中相爱,两个削金竹为誓,要让爱情像榕树一样长青。他们的爱情得到父母和寨邻的祝贺。可是他们的爱情遭到第三者的阻挠,卜苏家的绍宋早就垂涎郎秀的美丽,看见郎秀和凡龙成亲,他心“象辣椒烧一样又汤又辣”[5],和他爹想出毒计,要害死凡龙,夺取郎秀,威逼成亲。幸亏好心的鲤鱼千里迢迢给凡龙送信,凡龙骑上天马赶回来,与绍宋展开了搏斗,绍宋凶狠地杀害了郎秀。在满寨男女老少的帮助下,凡龙杀死了绍宋,用绍宋的头祭郎秀,郎秀复活。他们乘着金竹的光华升天而去,这里出现了神物: 鲤鱼、天马、金竹,正是借助他们的力量,爱情胜利了。还有布依族的《布卡和兰莎》是在布依族老人的帮助下杀死爱情的阻挠着,爱情才得以胜利。
布卡和兰莎的父母,都是由于受有钱有势的土司冷麻的残酷迫害才离开人世的。随着岁月的流逝,年龄的增长,布卡和兰莎这两个无依无靠的孤儿,心中萌发了纯真的爱情,并立下了永远相爱,白头偕老的誓言,但是坚贞而纯洁的爱情,都遭到了土司冷麻的无理阻拦。冷麻软硬兼施,企图占有兰莎。忠于爱情不畏权势的兰莎与冷麻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兰莎身陷虎口后,布卡怀着对情人的爱,对仇人的恨,黑夜进入土司衙门,在布依族老人的帮助下,杀死了土司冷麻,救出了心爱的兰莎。有情人终成眷属。
黎族和其他壮侗语族的爱情叙事长诗有共同的情节模式,诗歌中的男青年与女青年相爱,他们的爱情由于第三者的阻挠而发生爱情悲剧,结局由于人们美好的愿望,也可能戴上神话的色彩,使男女主人公仙化而去或在人间结合。民间叙事长诗是民族活的文化记忆,在它们的歌唱与哀诉中,复活的不仅是人与事、爱恨与情仇,也是民族与历史本身。
参考文献:
[1]岩峰. 傣族文学史[M].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 658 -659.
[2]岩叠,陈贵培,刘绮,等. 召树屯[M]/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中国民间长诗选: 第一集.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482.
[3]符桂花. 黎族传统民歌三千首[M]. 海口: 海南出版社,2009.
[4]杨通山,蒙光朝,过伟,等,侗族民歌选[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5]布依族文学史编写组. 布依族文学史[M]. 贵州: 贵州民族出版社,1992: 3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