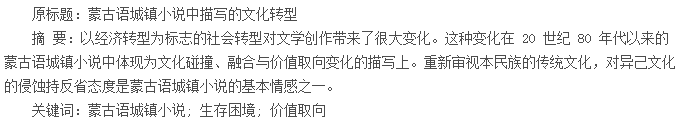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经济改革而发生的社会文化转型对文学创作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蒙古语城镇小说中体现为文化碰撞、融合与价值取向变化的描写上。人类的生存是通过劳动创造文化的过程。人类通过劳动不断认识和改变着自然与社会,从而驱使人的本质特征达到更高级的发展状态。所以我们可以说,人类是通过劳动和文化行为体现着自己当前的生存状态和生存特性的。其实,因人类的文化生存与社会生存具有同一性,文化的本质属性既是社会本质属性的全面而深刻的认证。文化的本质属性不仅是人类劳动本质力量的体现,也是客观体现物质和精神产物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交往实际上是不同文化交融的反映,其中的文化产物则展示着社会的本质力量或社会的精神。因此可以说,虽然是人类创造了文化,但他们同时也只能在文化的熏陶中才能够体现自己的社会生存的本质。换句话说,文化是人类社会化的文化,社会是人类文化的社会,人类社会劳动的过程既是创造和丰富文化的过程,社会转型的过程也是文化转型的过程。社会文化的转型过程被反映到“文学创作”这一特殊的文化活动中时,又可以再次演绎其本真面目。
一、文化转型中的生存困境
新时期以来的蒙古语城镇小说中描写了数量较多的蒙古民众走向城镇化道路的现状。其中,年青一代进城是由通过做买卖挣钱、通过打工改善生存现状、通过考学成为城镇生活者、家乡生态环境的破坏迫使等等原因而至,而认为城里的生活比农村生活安逸、舒服是他们共同的认识基础。此外,还有一部分老一代人的进城原因主要是为投靠或帮助已进程的子女为目的。这些以不同原因进城的蒙古族人身上带着浓厚的乡土文化气息,他们很难融入城镇里的现代文明环境,内心常常处于悲凉状态,体现出被现代文明所排斥和挤压的痛苦感。在农村时邻里间和睦相处,人际关系简单而直白,而城镇环境是弱肉强食的、人际关系是复杂多变的,这种新的文化空间使刚刚走进城镇生活的蒙古族人感到非常陌生和无法接受。丰富多彩、绚丽先进、开放多样的现代文明对贫穷落后、封闭保守的乡土文明既有无限的诱惑力而也不时地流露着蔑视和排斥的态度。
在现代文明的挤压与排斥面前部分人物选择了逃回农村,还有一部分人物选择了死守城镇,而又有一部分人物则表现出犹豫不决很难做出抉择的状态。大学毕业后留在城里安家立业的“我”(《农村来的是我的母亲》) 的母亲被接到城里后只待了五天就回到了农村老家。她在儿子的家里时刻严格把关着自己的一举一动,生怕让城里出生的儿媳妇不舒服,她认真观察着满口是“他奶奶来了”的儿媳妇的表情,最后选择了离开。母亲离开后,“我”与爱人一边讨论着子蜘蛛只有吃掉母蜘蛛才能够长大的罪孽现象,一边准备午餐,打破了五天以来没有过的沉静状态。坐到办公室后的“我”聆听着楼房窗外飘来的嘈杂的声响感叹道,“这些也在展现着城市这个怪物! ”对于“我”来说,“城市是人声和车马声相混杂的,彼此没有关系似的忙碌的,子女都嫌弃自己母亲的,冷漠的而没心没肺的地方。”同样,《街道闲聊》中进城与儿媳妇同住的婆婆的内心痛苦、《金黄色的土地》中恩和的爷爷的恐惧、《阴凉处》中的敖日浩台和胡日格台两位老汉对家乡人文的思念、《雾城的早晨》中的普日布老汉的遭遇等等都体现着无法接受城镇文化环境的现代、开放、冷漠而向往农村的人物的内心世界。
在城乡文化相撞面前,采取逃离措施的大都是老一代的人,其中《雾城的早晨》是一篇描写文化碰撞过程中传统文化被颠覆和消解的典型作品。作品中的普日布老汉和他的猎狗是传统农牧文化的象征,他们遭到了以“众人之父”为首的现代文明的排挤后最终走向了绝路。普日布老汉因在楼房内捣茶,在阳台上抽烟而遭到“众人之父”的严厉批评,正在他惊慌交错的时候发现自己的猎狗也不见了。楼房、“众人之父”、“猫眼”、放在水表上的磁铁等是城镇文化的产物或象征。普日布老汉的猎狗被“众人之父”卖掉和被杀害宣示着传统文化的被摧毁。猎狗被吊死的过程与猎狗死后普日布老汉的苦痛起到了悲剧的审美效应。
与厌恶和逃离城镇文化环境的老一代人物相比,大部分的进城年青一代人则表现出了虽然深知现代文明的冷酷无情也不愿离开此地的选择特点。斯琴花儿(《午夜的深圳》)认为,“对于一个人来说,没有比放弃自己向往的东西更可耻的! ”她向往的东西是“我不回去,我为什么要回去? 深圳不仅是深圳人的深圳,我要在这里立足,过上比任何人都富裕的生活。”这与阿丽玛(《玫瑰岁月》) 说的“我是有继母的人,我必须过上好日子让她看看”是相似的愿望,过上好日子是她们留在城里的目的。这个目的让她俩选择了城市的环境,选择了成为有钱男人的玩偶。同样的愿望致使斯琴(《大海中的泪水》) 、托丽玛(《湿滑的高坡》) 、天花儿(《雅宝路》) 、陶格斯(《红灯区记》) 、乌英嘎和苏龙嘎(《人为什么会变成狼?》) 、陶笛其木格(《爱· 笛子·花瓶》) 们留恋城镇环境,过上了小姐、妓女和舞女的生活。和她们相比,格日勒玛(《音扎干布日都与云顿毛都》) 、乌兰花儿(《乌兰花酒店》) 、兰(《蝉鸣声》) 选择城镇是被迫的选择。失去双亲的格日勒玛被城里的亲戚利用遭到强暴后回到了农村老家。而迎接她的是兄嫂离异、家园被占的惨景,无家可归的格日勒玛第二次踏上了进城的路。她的命运不比因家庭贫困而进城打工后遭遇老板的强奸至疯的乌兰花儿和为逃避酒鬼父亲的折磨跑到城里后丧生的兰的命运好多少。
二、文化转型中的价值取向
新时期以来的蒙古语城镇小说家共同的一个特点是表现时代精神,描写社会重大主题,反映民族劣根性,对本民族采取高度的责任心。对此,作家阿云嘎总结为: “我们的小说家们更是个个都成了思想家、哲学家似的,审视本民族的命运、寻求阻碍民族发展的病因、从体现社会不合理现象延伸到了揭示本民族的文化心理层面。”
审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对异己文化的侵蚀持反省态度是蒙古语城镇小说的基本情感之一。在民族的生存和发展遇到危机、蒙古语言文化被排斥和丢弃、民族精神匮乏、越是发达地区的民族消亡越严重的现实面前,描写那些城镇蒙古人的精神状态成为小说界的主要选材之一。在传统习俗、传统观念、传统价值观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的新的文化大环境中,是闭住眼睛等待末日呢还是打起精神寻找出路是摆在每个蒙古人面前的现实课题。
赛音巴雅尔的《都市蒙古人的故事》系列小说“折回到了民族意识,从民族文化学或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表现了蒙古人千百年来的文化积淀给本民族每个成员身上刻上的烙印以及这种传统力量在新时代新环境中遇到的无情的考验之规律,至此来呼吁了蒙古民族的更快更彻底的觉醒。”
《新年宴》《朝台吉》两部小说给我们展示了传统习俗在新的环境中的境遇。过年接神灵的时候,在农村“院子里堆上土堆上面放上盛在生里的炒米,点上烛火叩拜苍天之后放炮。进城以后无奈只留了放炮这一环节”的额日赫木图先生(《新年宴》) ,在大年初一那天,早晨因为子女们没有履行拜年的习俗而白白准备了很多祝词,白天因为邻里们没有过来拜年又白等了一整天。朝台吉朝格图都楞(《朝台吉》) 给巴老汉的女儿操办了蒙古民族特色的婚礼,在现代化的住宅楼门口组织和演绎了一场科尔沁地方特色的婚礼仪式。朝台吉“依照尊老爱幼的传统习俗,把婚礼的主桌安排给了老人们”,因此那些领导干部们却都没坐宴席就匆匆离开了婚礼现场。
“对于朝台吉来说婚礼是主要的,而那些领导干部的离开是次要的”但又“不知为什么朝台吉的双眼中噙满了泪水”。
我们从以上例子中可以看到,传统文化习俗的被冷落和遗弃对于像额日赫木图和朝台吉这样的城镇蒙古人带来的苦痛。作者恩和吉日嘎拉在小说《蒙古世界》里借助作品中人物的话描述了民族语言文化在城市里的处境: “内蒙古的首府城市可谓是蒙古文化的源原地。可是除了机关单位和商铺门牌上的蒙古文字之外没看见能够体现蒙古文化的东西。更不用说讲蒙语的人了,不管男女都在讲汉语。找见个讲蒙语的人真像是在大海捞针,不过仔细想想……真是到了投胎换骨的时候了。”如果说让子女们用英语或汉语考学的宝音图(《长叹》) 和嘎日麻(《债》) 等人的遭遇使读者有所启发的话,让孩子学了蒙语却又落榜了的脑日布(《长叹》) 的叹息更让人深思———连自己的母语都学不好的城镇蒙古族孩子们通过其他语言考学能够到达什么层次呢? 即使是用其他语言考学也能够达到理想的状态,但这样做又促使了母语丧失的危机,这又该怎么办? 是母语就读还是其他语言就读的问题,作品中嘎日麻的梦给出了明确的答复,也表明了作者的态度。关于民族文化与世界发展问题仁钦道尔吉提出: “在新时期的经济与文化的大杠杆下,随着我国现代化的进展,各民族的,尤其是少数民族的文化生态和传统文化遭受着严重的竞争与冲击。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如何面对全球化趋势,如何面对现代化的竞争都是他们值得深思的迫切和重要的问题。”
他所提倡的我们必须要培养民族文化的“危机意识”“保护意识”和“发展意识”的观点既是蒙古语城镇小说中描写和提倡的价值取向问题。
参考文献:
[1]青格勒图. 跨世纪蒙古文学现象批评[M].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
[2]扎·仁钦道尔吉. 蒙古小说: 21 世纪的门槛上[J]. 花的原野,2001(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