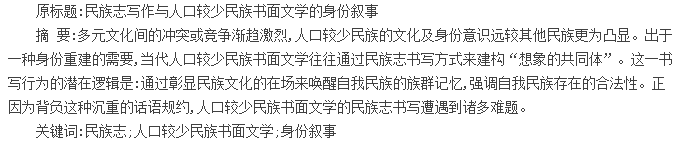
尽管出于一定的文学理念和价值立场加以创作的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志书写不能等同于民族学、人类学理论指导下的民族志文本“[民族志是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家对于被研究的民族、部落、区域的人之生活(文化)的描述与解释。民族志是英文“Ethnography”的意译,词源出自希腊文“ethnos”(民族)和“graphein”(记述)。在古代,民族志曾经是各种身份和职业的人,根据自己的见闻,对其他地区、其他民族的一些记录。当民族学(文化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建立以后,民族志就逐渐成为民族学家所作调查和研究报告的专称。”
但是,当代人口较少民族书面文学以“扎根于民族文化与信仰……用心、用富有民族色彩的叙事来寻求根本性的个性文学表达”的方式,对民间生活场景的生动描绘、民俗风情的真实再现、特定时空背景中特定情境中少数民族主体的情感体验及人情世故,以及民间民俗语言和民间文化与艺术的尽情铺排等,还是作为能够彰显地方性知识和异质性民族特征的民族志书写成为其不断受到关注的基本面向,人口较少民族书面文学价值也往往与其中所蕴涵的历史追忆和文化场景再现构成了一体两面的问题,成为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研究者的基本阐释向度和研究视域,并成为读者或民族文学研究者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期待视野”。正如有学者所说,“除了在田野工作中被研究者的口头叙述之外, 来自于第三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大量当代小说和文学作品, 也正在成为民族志与文学批评综合分析的对象(例如 Fischer,1984)。这些文学作品不仅提供了任何其他形式所无法替代的土著经验表达, 而且也像我们自己社会中类似的文学作品那样, 构成了本土评论的自传体民族志(autoethnography),对于本土的经验表述十分重要。”
一、族群记忆中的民族志写作
长期以来,人口较少民族群体因不掌握文化资本而使其民族文化往往被他者所书写,“声音”被他者所“替代”,沦为他者的话语想象或飘浮的能指。新时期之后,随着文化全球化步伐的日益加速,以文化单一性取代文化的多样性、以文化的同质化取代文化的多元化进程对文化承载人口较少、文化存续能力脆弱、文化更新能力和自我造血功能相对不足的人口较少民族来说,更是感受到自我民族文化日益被强势文化所冲击,甚至被取代的风险。因为,文化的他者化也就意味着民族身份的他者化,“何去何从”的问题成为现代性语境中人口较少民族的集体性焦虑。按照德勒兹、瓜塔里等人的“少数族裔话语”理论,在多民族国家中,少数民族“在与主流文化的关系中,融合运动一直是不对称的,主流文化中的成员很少有人感到不得不去理解各种各样的种族文化,可是,少数族裔们为了生存却总是不得不去掌握霸权文化。”
正是基于强弱势文化间不平等的焦虑,如何维系自我文化、如何在多元化语境中重塑自我身份、又如何在强势文化面前维系自我文化的历史记忆并在与强势文化对话中重构自我民族文化,就成了当代人口较少民族书面文学表述的基本主题。人口较少民族作家开始从“被看他”“转向了‘看己’,所谓的‘己’,意思是开始正视自己本民族的存在,正视民族心理的历史变化,包括开掘自己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剖析本民族文化心理、追寻民族文化之根等,还包括赞美性的描绘、审视式的反思和质疑,乃至探询本民族在当下的心理走向等所有方面在内。”
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在保留着文学审美起源论特征的同时使其呈现出强烈的文化表述功能,并以自觉的民族志写作来强化自身的族群记忆和历史想象,呈现出鲜明的“地方性知识”特征。
达隆东智的《遥远的巴斯墩》(《西部散文家》2011年 1 期)以“我”对巴斯墩的有关回忆和历史、传说、故事的大量穿插,再现了“尧乎尔”的迁徙历史、风土人情。作家为了追求自我民族历史的在场性,甚至让华洛老人等长者以当事人第一人称的口吻讲述“尧乎尔”的过往兴衰、荣辱变迁,并引领叙述者不觉走向保存与弘扬自我民族文化之路,从而追溯属于他们自己的历史,建构族群。作为不断迁徙的民族,裕固族漫长而惨痛的迁徙历程、辉煌而英雄辈出的祖先故里给现实生活中存在诸多风险的裕固族群体以诗意的想象空间,现实的文化和生存焦虑自然转化为历史的重叙动力,以强化自我身份的归属意识,并蕴含抵制他者文化侵扰的可能。裕固族作家铁穆尔的《苍狼大地》由五个小节构成,每个小节开端都回响着一首尧熬尔古歌,古歌的重复性回响,表述着叙述者“寻找草原”这一心理冲动,以及对建构民族历史和族群记忆的焦灼渴盼。在《哪里还有静静的草原》(《飞天》2009 年 21 期) 中,叙述者先以“在酒泉和张掖的旧地方志和档案文件中简单地记载着我的族人———尧熬尔人的情况……”之后,详细呈现出裕固族关于族名和人名来源的文献展示,然后再以给中日两国的孩子讲故事的方式,“给孩子们讲讲尧熬尔民族的事。那天天气晴朗,我盘腿坐在花草丛中给围坐成一圈的孩子们诵读了尧熬尔创世长诗《沙特》中的片断……”接着把尧熬尔族称来源和自己的姓名讲了起来。整个文本就是以民族志写作方式把裕固族的起源、迁徙、现实状况等展示出来,以达到文化认同目的。《一个牧人写作者记忆》(《大家》2010 年 13 期)的叙述者甚至以诸多文体混杂方式,对裕固民族在“文革”期间的遭遇进行了“探源性考察”。
文本以成年后的“我”作为叙述者,对本民族群体在“文革”期间遭受重大创伤的原因展开调查。同时,为了还原本民族的迁徙历程,叙述者甚至以“调查访谈”的方式加以佐证,接着又以人物视角对本部落群体在“文革”期间的遭遇进行报道……正是通过对日常生活生产方式的描述、对民间歌舞习俗的再现、对民族仪式节庆的吟唱、对古老生活场景的描摹等,建构出人口较少民族多元文化语境下的文化认同,共同承担起民族生命的诗意想象。正如英国后殖民理论家艾勒克·埃博默所说,“叙述本身变成了一种召唤一记忆的途径。对于一个历史被毁灭了的民族来说,一则关于过去的故事,即使它的全部或部分是虚构的,也能起到一种补偿过去的作用。这是因为另一部具有编年记忆性的小说或一首这样的叙事诗歌,都带有一种通过激发想象而把被压缩的现在和传统中的过去联系起来的能力。”
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民族志写作不但因具有与日常生活的密切关系而建构一种身份的基础地位与文化总体性,而且为读者如何看待人口较少民族文化提供了意义边界与提问方式,并且为研究者对人口较少民族文学民族志写作阐释提供了有效的阐释符码与价值准则。
就此意义而言,民族意识觉醒和深化后的人口较少民族创作主体,在以民族志写作方式呈现本民族文化的真实样态时,并不是一味执着于自我民族文化的简单展演和文本展示,而是以“赋魅”的方式对本民族文化加入了身份叙事的意义规约,使人口较少民族书面文学的民族志写作背负着强烈的价值关怀。也就是说,人口较少民族书面文学民族志写作并非一种叙述技巧的选择,而是基于自我民族文化心理和现实处境双重视阈融合后的必然选择,并使之成为彰显人口较少民族书面文学独特价值和文化身份认同的必要方式。
二、民族志书写的空间建构与诗学形态
人口较少民族因其生产生活方式的单一而与其生存环境存在直接依存关系,人口较少民族文化也就具有极为重要的地域性特征。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出于一种重构身份认同的现实焦虑而以民族志写作来呈现其民族文化时,自然会主动而自觉地选择那些能最大限度呈现其民族性的独特地域景观作为其认同对象,地域性空间建构就成为这一文学的基本特征。在这样的文本中,“我们必须同时看到一个特定的场所如何获得文化意义,以及文化又是如何利用这些场所实现其意义的。”
裕固族作家铁穆尔的《苍狼大地》、《童年》、《遥远的黑帐篷》、《奔向草原腹地》、《北望阿尔泰》、《焦斯楞的呼唤》、《苍狼大地》、《北方女王》、《草原挽歌》、《星光下的乌拉金》等作品,一再表征着作者对“祁连山北麓”草原生活的执着书写;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的《老人与鹿》、《森林里的歌声》、《琥珀色的篝火》、《敖鲁古雅祭》、《玛鲁啊,玛鲁》、《萨满,我们的萨满》、《丛林幽幽》等,始终建构着“敖鲁古雅”这一狭小的空间地域;达斡尔族作家萨娜的《流失的家园》、《天光》、《白雪的故乡》、《金色牧场》、《有关萨满的传说与纪实》等,重复叙说着渗透浓厚萨满气息的“达斡尔小镇”的故事;独龙族作家罗荣芬的《在路上》、《泛滥河水》、《我的故乡河》等,也是把笔触投向民族文化的根脉“独龙山乡”;仫佬族作家鬼子尽管不承认自己的少数民族作家身份及其创作的民族性特征,但他的《年夜饭》、《一根水做的绳子》等,也蕴藏着对罗城“仫佬山乡”的回望……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对地域空间的民族志书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本民族地域文化的认同和再现,在另一个维度上意味着对民族性内涵的建构,以及试图在这一具有浓厚民族属性的地域空间内能够自由呼吸的内在渴求。如普鲁斯特所说的那样“:我试图在自己从未想到会有美的地方寻求它,在最常见的生活中和自然静物的深处发现它。”
人口较少民族书面文学选择民族志写作作为地域文化空间的诗意建构无疑是源于强势文化压力下族群认同的现实需求。
毛南族作家孟学祥的《迎春》(《民族文学》2010 年2 期)、《猴鼓舞》(《民族文学》2008 年 9 期)等对“迎春节”、“猴鼓舞”等独具民族风情的歌舞介绍就是民族志写作的典型文本,具有鲜明的地域空间的建构价值。在《猴鼓舞》中,叙述者以民族志写作呈现毛南山乡独具民族特色的民间艺术———猴鼓舞的演出现场,“歌唱到情浓处,老人们把身上穿着的长衫往裤腰带上一扎,然后拿起鼓棒,走进场院中,围着摆放在场院中间的木鼓, 模仿着猴子的激情动作, 跳起了奔放的猴鼓舞。在歌声的伴奏下,在有节奏的鼓声中,只见场地中间的老人们闪、转、腾、挪,时而鱼跃,时而腾跳,时而抓耳挠腮,在模仿猴子们滑稽动作的同时,时不时地来一两个空翻,一招一式,宛若群猴嬉戏打闹,洋溢着生命的活力,渲染着大山的灵性。”布朗族作家陶玉明在《歇山窝铺》(《民族文学》2012 年 2 期)中也以这一方式对布朗族的民间建筑及传统仪式进行了审美呈现“……歇山窝铺通常用质地坚硬的黄栗树丫杈作柱子,用山茅草作窝铺盖顶,用长约两米的红木树板作围壁。窝铺一般盖在地头最宽阔平整的地方,前面没有高大的树木遮蔽,视野比较开阔。歇山窝铺可以作为隙望台观察整个地块,庄稼的长势和地里每一个地方的风吹草动尽在眼中。”再如,其在《谁家的公鸡在打鸣》(《边疆文学》2010 年 2 期)中对“洗寨子”的介绍,“‘洗寨子’就是犯事的人要杀猪杀牛祭寨心桩,又用祭祀过的猪牛肉来犒劳村人。这不算,当事人还要被罚来从村头至村尾打扫寨子。这样做的目的都是为赎罪,求得神灵的宽恕和村人的原谅。”在人类学看来,每一族群都有决定或表达成员身份的方式, 用来指示或指明群体成员身份的这些显性因素, 就称为族群象征或称为族界标识。如语言的选择、宗教形态的聚焦、对神圣地方或事件的记忆、特殊歌舞、社区和/或自愿组织的维持等,在族群维持上都起着作用。当前人口较少民族文学民族志写作对民族文化空间的建构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试图建构出多元文化语境下的族群象征体系,以维系自我民族的身份认同。达斡尔族女作家昳岚在《霍日里山啊,霍日里河》(《骏马》2006 年 5 期)里对定居前达斡尔族的房子建造过程的民族志叙述,就是上述问题的典型表征,“达幹尔族的房子先在房址上堆上 30%-60%的黏土,夯实硬固,再挖 8 个 60 多厘米厚的土坑,土坑里夯进平整的方型石头。入土的房柱上要抹上厚厚的松子油,再用桦树皮包实柱子的根部,便可以防腐……这些横梁、檩木、托上竟然没有一个钉子,都是凹凸型的槽咬合的。搭完架子,幵始刨墙,再铺柳色,这种柳条编成的房色是达斡尔人传统的造房工艺,干净、好看、结实,年代久远也不会漏掉泥土。”叙述者之所以如此详细的以此方式再现达斡尔人造房的经过和要点,在文本最后叙述者一语道破,“我这样罗哩罗嗦地讲述一个房子的建盖过程,你一定烦了。可是,我憋不住不讲。因为我再也不会讲了,再也不会盖这样的房子了,就连子孙后代,也住不上这样的房子了。”在这无奈的语气中,是老一辈人对传统的居住方式的深深眷恋之情,对“根”的追问与寻求,对身份重构的执着与眷恋,成为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民族志写作的根本要意所在。
莫里森在《根》中说,“根的地理意义远不如历史意义重要,这种历史感与某个确切的地理位置的关系远不如内在空间重要。比如,成为自己的自由,比如作为一个部落的成员。因此,他认同他作为小说家的艺术是和一直生活在黑人音乐和宗教中的黑人传统相伴随的。”
全球化在不断加剧的过程中,不能不以时间来消除各个空间的独特性,“地球村”恰是这一过程的典型概括。在这一显在的冲击面前,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化之根(身份认同)不能不受到干预和破坏,人口较少民族书面文学也就祭起民族志写作的大旗,以一种直观的方式呈现出人口较少民族文化的地域性特征,并使之转化为民族认同的象征或标志,规定着对人口较少民族文化阐释的限度与向度。各种风俗禁忌的频繁描述、诸多生活场景的真实再现、不同服饰神器的往复穿插,都是力图建构能够实现民族认同且独属自我民族的文化空间。单以服饰而论,“服饰从诞生起,就有标志作用。首先是各氏族部落成员着相同的服饰,以作为这一氏族部族成员的共同身份标志,这是社会成员群体之间的区别,具有向心排异的族徽符号功能。”
所以,克朗指出:“我们采用空间速记的方法来总结其他群体的特征,即根据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对‘他们’进行定义,又根据‘他们’,对所居住的地方进行定义……空间对于定义‘其他’群体起着关键性作用,在被称为‘他者化’的过程中,‘自我’和‘他者’以一种不平等的方式建立了起来。”
三、文化景观的民族志再现及其现代性反思
在文学社会学看来,文学中的一切生活景观都是意识形态过滤后的结果,是创作主体依据特定的价值立场、道德准则、社会规范等而对原生态生活场景“筛选”后的审美再现。也就是说,民族志写作并非是对民族文化或民族生活场景的真实再现,而是充斥着主观性、选择性、修辞策略、情感体验乃至虚构的“部分真实”文本。
就此意义而言,人口较少民族书面文学的民族志写作对民俗事项的立体性呈现、对地理景观的全方位营造、对庆典仪式的多层面临摹,甚至对惯例禁忌的一再再现,都起着对现实生活的道德干预作用。或者说,人口较少民族书面文学的民族志写作自身就是一种道德、禁忌的文本化写作行为,为人口较少民族多元文化语境下的生活价值和意义阐释“立法”。如美国学者伊罗生所说,“生于斯长于斯的那个大环境,根本就是一群人身体存在的延伸;在形塑这一群人的性格、历史、道德与生活方式上,它是一个无可取代的因素。”
乌热尔图在《萨满,我们的萨满》中对部族“最后一个萨满”达老非老人跳神仪式的再现,在《丛林幽幽》(《收获》1993 年 6 期)中对鄂温克人风葬习俗的讲述、对鄂温克族的生育禁忌的描述、对鄂温克人风葬习俗陨落的叹息,始终渗透着浓厚的感伤、哀婉气氛,弥漫着一种浓得化不开的忧思,如在谈到鄂温克人的生育习俗时,叙述者说,“有关鄂温克人的古老习俗,坦率地讲,在时间之流的冲刷下,早就变换旧有的模样,这也许就是学者们谈到的文化断裂。”叙述者援引史禄国的著作中找到的有关鄂温克人生育的记载情况并认为“其真实性是可以相信的”。紧接着叙述者详细展示了鄂温克妇女的生育禁忌。在这里,叙述者并不是在刻意呈现鄂温克人生育习俗的方方面面,而是对这一习俗消失所引起的“文化断裂”深感忧虑;在对鄂温克人的风葬习俗书写时依然说,“丛林里的游猎部族,究竟在什么年代放弃延续千百年的风葬习惯,改用土葬,现在无人讲得清楚说得明白了。”作为鄂温克文化“活化石”的“老人”的渐趋消失,鄂温克文化也逐渐被外来文化所冲击而烟消云散。传统是什么、传统对现实意味着什么、什么是鄂温克的精神支柱和生存依靠?……这一系列问题都迫使叙述者不得不思考本民族何去何从的问题。因为,在叙述者看来,鄂温克的传统文化已不存在于鄂温克人的民族记忆和文化传统之中,而是成了与鄂温克人生活相脱离的书本知识。叙述者在文本中不断引用俄国学者史禄国的《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写的《使用驯鹿鄂温克人的调查报告》等民族学、人类学著作,并不是出于对上述著作的尊重或敬仰,而是以此反衬出鄂温克人丢失文化传统后的无所适从和茫然迷惘心理,以及对民族文化传统保护的必要性、紧迫感。乌热尔图先生在《丛林幽幽》后弃“小说”而从事文化散文、文化随笔等文体创作,因为这些文体更能使他充分且随心所欲地“写鄂温克文化”。《沉默的播种者》、《述说鄂温克》、《呼伦贝尔笔记》等文化随笔正是“乌热尔图吸收后殖民理论的反抗性和质疑性的思想”“,捍卫本民族的自我阐释权”,并将民族文化和民族生存忧患的心理体验呈现出来,他从人类学、生态学、考古学、历史地理学和哲学的多层面、多角度中,揭示了鄂温克人的生命历程,并“以虔诚的态度敬重这片土地及古老的本土文化”, 以及他“历史的眼泪”和“现实的忧伤”,完成了由个体身份向群体代言人角色的转化,乌热尔图与他的文学文本存在着互文关系,共同表述着一个柔弱民族在经受来自强力文化挤压的痛苦。在这种意义上说,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民族志写作就是一种现代寓言。一如学者在评论苏华作品时所说,苏华的写作总是有着“那种试图通过自己的写作,把自己民族的文化风貌展现出来,把达斡尔古老的人文精神与现代文明的冲撞和融合展现出来,通过自己的写作,去探求达斡尔文化底蕴的愿望。”
黑格尔曾指出,“所谓‘象征的’或‘寓意的’就是指每一件艺术作品和每一个神话后面都有一个普遍性的思想作为基础, 因此在进行解释时就要把这种抽象的思想指点出来。”
基于现代性冲击所引发的文化消失风险尤强于人口较少民族这一在己性体验,人口较少民族文学总是在营构独特空间景观的同时为其烙上强烈的现代性反思色彩。在裕固族文学中,民族志写作背后总是与牧场萎缩、植被退化、动物消失、人欲无限等问题相关。裕固族作家铁穆尔在《失我祁连山》(《延安文学》2004 年 5 期)中一再揭示这一危及到本民族生存的问题:“无止境的开垦草原、庞大而密集的灌溉农业、林木的滥砍滥伐和采矿引起的是祁连山水源的干涸,雪山雪线的不断上移或消失。而近几年各种文件和汇报材料中,都说是因为牧民的超载放牧(即过度放牧)引起了植被毁灭、导致祁连山地区水源干涸。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几个老实巴交的山里牧民和山羊耗牛身上。世界的荒谬以至于斯。我不知道,人们是装作不懂还是有意而为之,到处都是令人做呕的沉默”;鄂温克族作家敖蓉在《古娜杰》(《青年文学》2009 年 8 期)中,以人物古娜杰之口对鄂温克地区因现代性过度开发所造成的生态恶化问题进行了沉重的反思:“‘……她没有想到的是,姥爷他们用生命换来的天路,却给今天的森林和驯鹿带来了灭顶之灾。这是驯鹿和森林的悲哀,更是鄂温克人的悲哀啊!……狩猎已不再,驯鹿又前途未卜,驯鹿可是我们民族的象征啊!驯鹿没有了,我们这个民族还能存在么?这是在保护多元文化还是取缔传统文化?难道我们的传统文化远离现代文明么?……一个连文字都没有的民族,母语的渐渐消失和远去的鹿铃声真是令人堪忧啊!’”……这一书写立场是当前人口较少民族群体的集体性言说和道德焦虑,人口较少民族书面文学的民族志写作的根本初衷也就在于通过对现代性的批判性反思,重建人口较少民族生存的诗意空间,并在这一空间内拥有完整而明确的身份记忆。就此而言,人口较少民族书面文学的民族志写作与其说是为人口较少民族设立了生活的价值坐标或道德取向,不如说是人口较少民族出于强烈的身份诉求与自觉认同而为自己的民族文化走向设置的象征符号。
问题的吊诡是,当人口较少民族作家出于族群身份的执着建构而试图抵制外来空间的缠绕和干预时,却不期然走向对自我民族文化采取既在空间上也在时间上将其同质化的策略。在空间上刻意忽视本民族内部群体对现代文明强烈向往的诉求,并把民族内部有着这种现代文明诉求的群体看作是“欲壑难填”的沉沦化象征;在时间维度上则将本民族文化想当然地永久保存于传统之中。在此话语逻辑中,人口较少民族社会就可能丧失了进入当代性的可能,因为它们的现在只能是对其过去生活的简单重复或再生产,结果如汉娜·阿伦特所说,这种退缩、这种放弃,实质上就是从公共性里面退出来,就是从人类最丰富、最有尊严和最有能力的区域内退出,它本质上是一种自我及自我发展的剥夺。在这种意义上说,萨娜在《有关萨满的传说与纪实》中的“萨满用语言的冰川隔断了阅读者进入他神秘莫测的古老城池的路径”,就成了一种极富象征意味的谶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