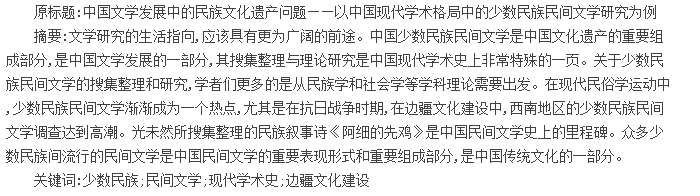
撇开“民族国家”的概念不谈,关于中国文化传统与中国文学发展中的民族文化遗产问题,在当前的学术讨论中成为一个新的课题。
1950年代的文化遗产阶级属性问题,1950年代末亚洲作家会议以及1960年代亚非作家会议、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等关于殖民性背景的民族文化遗产问题讨论,都成为我们今天应该深思的内容。自2000年以来,关于文化遗产与文学发展的关系讨论并没有与其重要性相等的理性思索,学者们更多的是在强调民族存在与文化遗产存在的社会文化伦理意义。从文化遗产被置之于文化工作的体制性意义讲,《民族文学研究》《中国民族报》《中国文化报》等报刊展开相应的讨论,许多民族院校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课程讲义,以及一些少数民族专题文学史,不同程度上涉及汉民族文学主体背景下的文学发展问题。具体说来,学者们的研究更多的是从文化联系、文学形态关系问题展开。从1950年代到今天,毛星、吴重阳、朗樱、杨恩鸿、仁钦道尔基、白庚胜、刘亚虎、朝戈金、陈岗龙等学者,也都论述过相关问题。西方学者强调人权背景下的少数民族文化形态的研究,特别是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重大题材,诸如《格萨尔》等民族史诗的研究,出现不少有价值的成果。总体而言,中外学者多从文化遗产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的意义上以中国少数民族文化权益保护为视角,强调中国多民族国家文化格局中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包括文学繁荣的重要性,很少有学者具体论及民族文化遗产问题在学科建设中与文学发展的密切联系。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历史文化遗产的现代价值,在1949年建设新的国家政权之后,仍然坚持历史主义的文化立场。这在事实上形成了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机制与体制。
1950年代,《光明日报》开辟“文化遗产”栏目,以更多地进行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性研究。
1938年,毛泽东就直接表明道:“我们是马克 思 主 义 的 历 史 主 义 者,我 们 不 应 当 割 断 历史。”那么,割不断,就需要继承和发展,而任何形式的继承与发展都是有选择的,需要具体的认同与表达。或者可以说,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主义文化观直接影响到了新中国不同时期的文化政策,构成中国多民族文化遗产抢救、保护、研究的理论体系。对于少数民族的文化遗产,包括古典文献、口头文学等遗产形态的保护与发掘,始终是处在优先地位的,这应该是因为将其纳入了民族政策。中国可以向世界展示的是,中国各个少数民族现在都出版了自己的文学史,这是人类文明的奇迹。据统计,目前,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366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1028项中少数民族项目有367项,1488位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中少数民族者有393位。新疆木卡姆、内蒙古长调等少数民族艺术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今天,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形成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态势,甚至出现了文化遗产的学科建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命题与之相呼应,形成强烈的文化自觉,因而,现在讨论这样一个问题,也就更有价值。
讨论这个问题,笔者将分别从现代、当代不同阶段陆续展开,具体论述。在这里,一个重要前提是应该认真梳理中国现代学术体系中的少数民族文学作为文化遗产的学理建构与发展过程。抛开这样一个学术背景,许多问题就很难说清。
一、西方学者与西方学术的介入
关于我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在晚清时期就有西方学者参与,如,1896年英国传教士克拉克在贵阳、在黔东南黄平苗人潘秀山的协助下记录的苗族民间故事《洪水滔天》《兄妹结婚》《开天辟地》等;英国学者斯坦因等人发现敦煌的西域研究;俄罗斯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等人对中国传统年画等民间艺术的研究,都具有这种学理意义。中外学者受到西方人类学的重要影响,力图了解中国底层社会,在事实上将中国文化遗产地图直接融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地图;中国学者的边疆文化建设运动应该是受到他们的启发。西方学者的学理探索重视细节与技术,改变了中国文化传统中游记等的印象感悟式的思维习惯。如,1902年,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在《苗族调查报告》中记述道,“关于苗蛮之神话,以往文献史上最著名者,为《后汉书》中所记《盘瓠之传说》及《夜郎大竹之传说》二种。此等神话,凡欲言苗蛮事者必引用之,此处则无叙述之必要,兹所宜研究者为关于现时苗族有如何之神话传说耳”,其记录整理了“青苗间有一种甚有趣味之创世记(纪)的传说”,称此“为人类学上最有裨益之材料”,其援引“安顺附近青苗之耆老”曰:
“太古之世,岩石破裂生一男一女,时有天神告之曰:汝等二人宜为夫妇。二人遂配为夫妇各居于相对之一山中,常相往来,某时二人误落岩中,即有神鸟自天飞来,救之出险。后此夫妇产生多数子孙,卒形成今日之苗族。”又记曰:“太古之世,有兄妹二人,结为夫妇,生一树,是树复生桃、杨等树,各依其种类而附之以姓,桃树姓‘桃’名Chèlá,杨树姓‘杨’名Gai Yang,桃杨等后分为九种,此九种互为夫妇,遂产生如今日之多数苗族。此九种之祖先即Munga chantai,Munbān(花苗),Mun jan(青苗),Mun lō(黑苗),Mun lai(红苗),Mun la’i(白苗),Mun ahália,M’man,Munanju是也。”他由此总结道:“多数人产生后,分居于二山中,二山之间有深谷,比次等落入谷中时,有鹰(LanPalè)一羽自天上飞来救之出,由是苗族再流传于四方。因此吾人视鹰为神鸟,常感其恩而祭之。吾等苗族,贵州最多,明时,吾等中有移住于西部及Sio tsuo者。据以上神话考之,白、黑、红、青、花苗等皆出自同一祖先,且皆以Mun为名,故此传说实可证明苗族为同一种族也。”当年,钟敬文曾发表《种族起源神话》(《民众教育季刊》第1卷第3期,1931年4月30日)、《南蛮种族起源神话之异式》(《艺风》第3卷第4期,即《民俗园地》第3期,1935年4月1日),已经表现出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学科独立意识。中央研究院成立民族学和民间文学的研究机构,制定有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在内的调查研究计划,成为搜集整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学术活动的重要开端。
学者们尤其强调对少数民族的尊重。当年,严复翻译英国甄克斯的《社会通诠》,其注释中说:“古书称闽为蛇种,盘瓠犬种,诸此类说,皆以宗法之意,推言图腾,而蛮夷之俗,实亦有笃信图腾为其先者,十口相传不自知其怪诞也。”此不无鄙视之意。薛汕在《反对称“特族”》说:“以汉族为本位,将其他民族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时代应该是过去了。
或者是如《周礼》所云,把‘四夷、八蛮、九闽、九貉、五戎、六狄’等说得有声有色的高傲态度也应该收起来了。不久以前,有不少人已经知道将其他民族的名称,加上从‘犬’、从‘虫’、从‘草’、从‘豸’等贱视的符号为不当了。我们算是解除《说文》所注视的谎语,什么‘南方蛮闽,从虫’。同样,对存在于各县的所谓“通志”的大片骗词,什么猺,什么獞,什么‘兽身犬祖宗’……虽然‘狗头瑶’传说中是以犬为祖先,甚至连他们本族的习俗亦显示出这一点,但单凭这粗浅的看法是危险的。我们由于有所谓历史‘武功’,对他们加以迫害,更由于历史的记载极其模糊,对这一点是值得考虑的。到现在,亦始获揭发了。是的,我们很赞成教育当局将有侮辱性的字眼改为从‘人’。”
在现代民俗学运动中,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渐渐成为一个热点,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在边疆文化建设中,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调查达到高潮。
1928年5月,中山大学生物系辛树帜教授等深入广西瑶族和壮族中去做调查,钟敬文翻译古代典籍《粤风》中的少数民族歌谣,张清水也曾经记述瑶族民俗与相关的民间传说,等等;尤其是钟敬文等人“要解决西南各种人是否一个种族的问题”,并通过编辑《西南民族研究专号》集中探讨这个问题,余永梁的《西南民族起源神话:盘瓠》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1928年第3集第35、36期合刊发表,形成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的热点。而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真正形成规模,则是在1930年代之后。如,芮逸夫的《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集刊》,1938年第1期)。对此,岑家梧的《黔南仲家的祭礼———作桥的道场与经典》做了补充,并提出异议,他说:“这个文化区的文化特质,除铜鼓,芦笙及所谓兄妹配偶型的洪水故事外,尚有口琴(Harmonica),蜡染,纹(文)身,几何花纹及盘瓠传说。但他(指芮逸夫———作者注)推测兄妹配偶型的洪水故事起源于苗人,我们却愿意保留未决权,因为这种传说,除他所述者外,如广西都安县的板瑶,融县罗城的瑶人,川南的苗人,贵州威宁的花苗,下江的生苗,黔南的侗家,云南鲁魁山的黑夷,以及荔波,二都的仲家水家,都极盛行,所以此刻要解决它的起源问题,颇觉为时过早。”对于芮逸夫《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常任侠也表示了不同意见,他将汉文典籍记载中的伏羲女娲传说、苗瑶民众流传的洪水传说进行比较研究,认定沙坪坝石棺上所刻之人首蛇身像,就是中国上古传说中的伏羲女娲:“稽考中国古史,苗瑶之民,亦中夏原始民族之一。古先传说,谓伏羲女娲而后,黄帝常与蚩尤战而败之。至舜更窜三苗于三危。说虽不必为信史,而古者苗民亦常混居中原,殆属可信。故于伏羲女娲二灵,称为人类之祖。崇敬既深,传说亦富,固不仅为汉族之神话也。苗瑶相传为盘瓠之裔,干宝《搜神记》,述之颇详。而盘瓠亦即盘古。《赤雅》载《刘禹锡诗》曰,‘时节起盘瓠,’谓苗人祀其祖也。《岭表纪蛮》引《昭平县志》曰,‘瑶人祀盘古,三年一醮会。
招族类,设醮场,行七献之礼,男女歌舞,称盛一时,数日而后散,三年所畜鸡犬,尽于此会。’《洞溪纤志记》苗俗曰:‘苗人祀伏羲女娲。’伏羲一名,古无定书,或作伏戏,庖牺,宓羲,虑羲,同声俱可相假(此承胡小石师说)。伏羲与盘瓠为双声。伏羲庖牺盘古盘瓠,声训可通,殆属一词,无间汉苗,俱自承为盘古之后。两者神话,盖亦同出于一源也。”其“声训可通,殆属一词”,是神话语言学研究的可喜尝试。诚然,语言学的研究是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的重要拓展,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中的语言固然是语言学研究的重要资源,而田野作业中也面临言语不通的巨大困难。如《西南采风录》的作者刘兆吉在记述自己的感受时称:“我国领土广大,交通不便,各省言语差异很大,尤其北方人初到南方来,时时会感到言语不通的困难。当我采集民歌的工作开始时,第一步便受到这种痛苦,因为民歌童谣不像载诸书册的诗词,它是村夫野老以当地土语吟咏出来的,听他们歌唱也很悦耳,但有时不懂歌的意思,要把歌词记下来,而没有相当的字能恰巧符合它的音意。求他们解释,但问答有时不能互相了解。再者一般的农夫牧童,虽然能唱歌谣,而多不识字,请他们把歌词写出来更不可能。往往为了仅仅四五句的短歌,费了不少的话和时间。还有一点也是因为语言不通而引起的困难。一般老守乡里又没受过教育的乡民,逢着异言异服的外乡人,生疏得很,即便好心好意和和气气的(地)请他们告诉几首歌谣,也曾引起他们的怀疑。虽再三地解释他始终不肯尽量的(地)告及,这也是由于自己的经验不够,不能洞悉民众的心理,以致在湘西碰了不少这样的钉子。”刘兆吉所谈现象,在这个时期的学者中是普遍存在的。
二、文化遗产的中国“田野”
与上述研究同时期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与理论研究还有马学良的《云南土民的神话》(《西南边疆》,1941年第12期)、《云南罗族(白夷)之神话》(《西南边疆》,1942年第15-17期),楚图南的《中国西南民族神话之研究》与马长寿的《苗瑶之起源神话》(《民族学研究集刊》,1940年第2期)等。正如楚图南所说:“要想对于西南民族及其文化得到一个明确的认识,最先得探检(险),调查,搜集,和根据于过去的成文的与未成文的史实,各作分科或专题的研究。譬如言语,文字,民族,社会组织,风俗习惯,宗教思想等,由初步的分析,比较,以进于统整的认识和理解。又由统整的认识和理解,以进于与四邻文化和民族的交互的影响的研究。在所能得到的资料中,有属于神话,或是近于神话的,也只能把它作为神话或传说来加以研究和处理,不能即直截了当地作为史实或信史来应用。过去已被误认,或误用了的史实,现在也得先将它们还原为神话,然后以对于神话的态度,以神话学的一般的方法,来将它们清疏,整理,研究,判断,得出正确的结论。又从这些结论中,来推论,来研究出西南民族的比较可靠的信史来。”管思九、丁仲皋受吴泽霖影响,编纂出《江口情歌集》,吴泽霖在该书的序言中写道:“近年来我国青年的注意和努力又转入革命的思想和活动,对于这一类‘无聊’的研究工作,又遭唾弃,这或许又是一种时代精神,我们很难与之逆流对抗。但是我们如能放大眼光,我们立刻就可以看到这一类民谣、情歌、风俗的研究,也正足以明了中国社会的结构、变迁和动向。这类的调查研究倒是一种脚踏实地的工作。这本情歌集的编者能在国家扰乱之际,苦心地搜集了百首之多,再加上注音解释,实足令人钦佩。如果他们的工作能够引起江口以外人的兴趣,而去同样的搜集研究,那他们的功绩,真是大呢!”吴泽霖主持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关于少数民族社会风俗生活包括民间文学的调查研究,其深入少数民族中,调查记录了贵州花苗中流传的大量兄妹婚神话、大花苗民间古歌《洪水滔天歌》、八寨黑苗洪水遗民神话、短裙黑苗洪水神话。他在《苗族祖先来历的传说》中讲,“他们所述的”那些洪水神话与祖先神话,“都不是开天辟地后第一个老祖宗的故事”,“乃是人类遇灾后民族复兴的神话”,其中的兄妹婚“很可以证明在这些神话形成的时候,兄妹间的婚姻已不流行或已在严厉禁止之列”,包括神话传说中的铁器等物质的出现,“这又可以证明这样神话的形成,当在春秋以后又产生了许多的变化”;他举例“美国的人类学家在美洲的印第安人中得到不少材料,证明摩擦的方法,较撞击法为早”,解释说“这在花苗的神话中,火是用铁块投掷于石上而产生的”,“这明明是撞击的方法,当然撞击不一定需要铁块,在事实上人工造火的开端,远在使用铁器以前,凡燧石之类互相撞击,都可以生火星,铁块显系由苗人后来改编的”,“无论如何这是撞击较摩擦为早的证据,并且证明造火方法的次序至少带有地方性,而不一定循古典派所主张的一定的程序和阶段”,最后,他强调说,“所以,这一点在人类学上也是值得注意的”云云。陈国钧曾经搜集整理黑苗、花苗、红苗、白苗、生苗、花衣苗、水西苗、仲家、水家、侗族等少数民族的965首民间歌谣,编成《贵州苗夷歌谣》和《广西特种部族歌谣集》等;陈国钧是一位极为勤奋的学者,他还曾发表《生苗的人主神话》(《社会研究》,1939年第21期)、《广西蛮傜的传说》(《社会研究》,1942年第46期)、《广西特种部族歌谣之研究》(《说文月刊》,1940年第6、7期)、《广西东陇瑶的礼俗与传说》(《说文月刊》,1945年第3、4期)、《恭域大士瑶的礼俗与传说》(《风土什志》,1948年第2期)等著述。他研究神话传说中的兄妹婚等历史遗留物现象,称:“古时候曾经有一次洪水泛滥,世上人类全被淹死,只有两个兄妹躲免过,后来洪水退却,这对兄妹不得已结成夫妻,他们生了一个瓜形儿子,气得把这瓜儿用刀切成碎块,撒在四处,这些碎块即变成各种人了。”亦如其在《贵州苗夷歌谣》“自序”中所说,“我专事调查贵州苗夷族生活,已历多年,早就打定主意,在我所编的书中,一定要先编这本书。因为当我每次作苗夷族调查,附带搜集歌谣材料,是件轻而易举并有意味的事,而且材料积到相当多时,也不必花多大的整理工夫,就可以编成书。现在,经过了几年的采集,略有一些所得”,“本书在国内尚属第一本集录特种民族的歌谣,所以,我不敢随便在中间加以修改和诠释,只原原本本把它转译编汇在一起,以便保存它本来朴质的真面目,并就它的内容种属分了先后,我想,这样仍不会减却它的价值,也可以供研究苗夷族者,一大堆材料”。 因而,有学者给予其很高评价,称“陈先生对于调查与汇集的工作,不辞劳苦!这一部歌谣集就是陈先生费了许多心血汇集而来的。此集出版以后,贵州苗夷族的歌谣始有定本。我们翻开来一看,其中无一首不是天籁。我们很庆幸,中国的民间文艺从此又增加了一种宝贵的资料”云云。
这些记录文本,一方面成为当时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流传状况的证明,另一方面也成为他们进行科学研究的珍贵历史文化资料。正如张小微为《贵州苗夷歌谣》写的序中所论:“人类社会文化有了种族性和地方性的区别,学术上的研究便不能够一概而论,除非个别的加以分析之外,结果一定难望深刻彻底。个别研究的途径固然很多,但是利用歌谣来作分析的资料,实不失为犀利的工具之一,倘若所研究的社会文化是属于缺乏文献的落后民族,则这种工具尤擅重要。因歌谣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副产品,可以反映出来各种族和各区域的特有形态。不过歌谣的研究系客观研究的性质,必须首先从事于多量歌谣的汇集,否则便无法着手研究。
是以汇集歌谣乃是以分析歌谣为研究人类社会文化的途径的初步工作。”其他如王兴瑞曾发表《海南岛苗人的歌谣与传说》(《文史杂志》,1944年第3、4期)、《苗人起源传说之研究》(《新政治》,1938年第2期)、《海南岛苗人的来源》(《西南边疆》,1939年第6期)、《海南岛的苗人生活》(《边疆研究季刊》,1940年创刊号)、《黎人的文身、结婚、丧葬———从史籍上所见》(《风物志集刊》,1944年第1期)等。学者们的论述形成一个通则,即从文献记录状况(包括有无文字)出发,按图索骥,寻求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口头记录,并以此展开田野作业,进行不同形式的研究;他们都强调通过一定的社会风俗生活,具体研究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或通过民间文学研究风俗,以及通过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在风俗与民间文学中发现历史文化。
卫聚贤主编的《说文月刊》是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的重要理论阵地。在这里,郭沫若曾提出“禹化黄龙”;孔令谷提出“神话还原论”,论说“古代原始民族往往以歌谣神话表叙自己民族的著名史事”,“神话传说决无无因而至”,“神话并不是梦话,而是实际的事”。其他如常任侠的《重庆沙坪坝出土之石棺画像研究》(《说文月刊》,1945年第10、11期合刊)等文章,在不同程度上论及少数民族民间文学。陈志良曾经发表《广西特种部族歌谣之研究》(《说文月刊》,1940年第6、7期)、《广西东陇瑶的礼俗与传说》(《说文月刊》,1940年第3、4期)等著述,他还翻译发表了藏族史诗《格萨王传》(即《格萨尔》)“序幕”之一、“序幕”之二,发表在《康导月刊》1947年1月第9、10两期。其他还有朱祖明的《塔弓寺与其神话》,发表于《康导月刊》1943年第2、3期合刊,岭光电辑《圣母的故事》(倮民故事),发表于《康导月刊》1943年第7、8合刊,任乃强的《关于〈蛮三国〉》发表于《康导月刊》1947年第9、10期。《风土什志》也是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刊物,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文章,如,吕朝相关于羌民端公神话的文章《羌民生活一瞥》(《风土什志》,1944年第3期)、李元福的《倮倮的文学》(《风土什志》,1944年第4期)、陈志良的《板瑶情曲》(《风土什志》,1946年第6期)、陈志良的《恭城大土瑶的礼俗与传说》和林荣标的《介绍几条高山族民歌》(《风土什志》,1948年第2期)等。《风土什志》还发表了许多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如,第1卷第6期的《瑶民情歌四首》《苗民恋歌》、第2卷第2期的《独龙族创世故事》、第2卷第4期的《闷域(门巴族)的传说》、第3卷第1期的《西藏民歌》等。另外,李霖灿(李灿霖)所编《金沙江情歌》,也是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优秀之作。这些现象背后,充满无数艰辛,表现出年轻的学者们对学术事业的执着追求,也为后来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特别是他们不畏艰苦、孜孜以求、坚韧不拔、勇敢开拓、精益求精的科学精神,是后来者应该倍加珍惜的学术传统。
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为文化遗产的发现常常在于学者们艰苦的田野作业。在现代学术体系的构建中,将《格萨尔》纳入中国文学研究格局,是一个奇迹。在世界各民族文化遗产地图中,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古巴比伦的《吉尔伽美什》、古印度的《摩诃婆罗多》、古英国的《贝奥武甫》、古日耳曼的《尼贝龙人之歌》、古法兰西的《罗兰之歌》、古马里的《松迪亚塔》等浩若繁星。现在,中外学者都认同我国藏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的《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一部史诗。目前,可以看到《格萨尔》有120多卷、100多万诗行、2000多万字,流传于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内蒙古、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
2009年9月,我国《格萨尔》史诗传统作为文化遗产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1716年,我国出版蒙古文刻本《格萨尔》;1776年,俄罗斯学者帕拉莱斯在蒙古发现《格萨尔》刻本,将其介绍到西方;1836年,施密特院士本在俄罗斯出版。
1929年夏天至1930年春天,四川南充中学的任乃强考察康定、雅江等少数民族分布较密的县,偶然间发现这些地区流传的《格萨尔》,他做了详细的记录,并自1930年5月开始在《四川日报》副刊上连续刊载。这是我国现代学术史研究《格萨尔》的重要开端。这一学术发现的意义并不亚于敦煌文献、居延文献、甲骨文献和大内文献的发掘。这是中国现代学术体系构建中田野作业科学考察方式的硕果,开辟了中国文学研究的新纪元。
总之,我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学者们更多的是从民族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理论需要出发。相对于中国文学发展中民族文化遗产意义的研究,其无所谓补充、纠正或缺失,学术的多元并举,更有益于文化的繁荣。走出文学,走向生活,或许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文学的生命力与规律所在。
三、彝族叙事长诗《阿细的先鸡》
最后要特别提到的是《阿细的先鸡》,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部具有特殊意义的优秀作品。光未然在《我怎样整理〈阿细的先鸡〉》(代跋)中声称自己是在原来民间演唱的基础上做了适当修补,所做的是忠实于彝族人民民间文学原貌的搜集整理。“阿细”,指彝族支系阿细人,“先鸡”指他们的歌曲,这首叙事长诗的搜集整理过程与意义,颇类似于芬兰人的《卡列瓦拉》,都属于民族危亡特殊背景下的民族传统被强化记忆与认同的结果。
其内容如光未然所述,“据我们现在所记录下来的,全部约计两千行,内容包括丰富的神话传说,男女的恋情,和民族生活与民族风习的忠实而准确的记录;阿细人民的幻想与希望,欢乐与痛苦,大概都可以从他们自己这部长诗中窥见一斑了”;其“第一部的神话传说的部分,来源一定是极其悠久的,而且我猜想,说不定其中还保存了若干已经湮灭了的汉民族神话传说的转化或变形。至于《创世纪》和《洪水记》的部分,是不是搀杂了后来传播到该地的基督教传说的若干影响,我这时还不敢断言”,其“第二部描写民族风习的地方,形成的年代自然较后些,其中汉民族文化风习的影响,显然占有重要的支配地位”,包括“在阿细部落中所流传的原诗,全部是五言体,这里是由阿细族青年毕荣亮君逐句口译,由我在不失原诗情趣的原则下略加润色发展而写定的。原诗天然地分上下二部,现在由我分为若干章并加上标题”云云。他说,“《阿细的先鸡》是一部活的口碑文学”,“随着他们的历史与生活的发展,随着一代代的流传,这部长诗也不断地在增加它丰富的创造性”,同时,他也指出其濒临失传的危险,称“然而我们也可以说,这种发展到今天为止已经告一段落。
因为即(使)在阿细部落中的男女青年,能够从头至尾唱完这先鸡的全部的,已经不多了”,“这部先鸡的生动的形象和语言,哪些是由来已久的,哪些是由于毕荣亮君的发展和创造,此刻也很难辨别了。我所以说这位毕荣亮君,这位保存了先鸡而且发展了先鸡的阿细人民的诗人,不愧为‘阿细的荷马’,其理由也就在此”,而“把这部长诗逐句传述给我的阿细青年毕荣亮君,是在邻近的数十个村落中能够唱完‘先鸡’全部的唯一的一人,所以被当地同族的青年戏呼为‘王子’,大家都不敢和他对唱”,“毕君是路南县中学毕业的学生,他的家住在弥勒路南两县交接处的深山中。在这个山岳地带里,散布着许多大大小小的阿细族的村落,其中有些已经汉化了。毕荣亮君的家乡磨香井,因为位置在崇山峻岭的最深处,所以还大部分保留着自己的文化面貌”,其称“这也许就是这部《阿细的先鸡》所以在磨香井部落得以保全下来的重要原因吧”。这是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史上关于民歌手即民间文学发生主体研究的表现;其感慨“当地的男女青年们日常所歌唱着或者说所使用着的,大概都是这部‘先鸡’中的某些片段。如果不很快的记录下来,再经过若干岁月,我想这部长诗会有逐渐泯灭的危险”,所以,光未然记录、整理了这部长篇叙事诗。田野作业是这部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经典形成的重要基础;或曰,没有光未然从民间歌手那里的详细调查,就没有这些脍炙人口的民间歌唱。
光未然是一个特立独行的诗人,富有表现时代的政治热情和文化热情。他在为《阿细的先鸡》做“题解”时,详细论述了自己的记录过程,包括自己对民歌的理解。其记曰,“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
我们在昆明附近常见的夷人(Lolo),是云南少数民族中间的一系;而阿细族又是夷族(Lolo)中的一个支系;他们的地区散布在路南、弥勒、陆良一带的高山峻岭中”,“夷族各支系(如阿细、撒尼、阿哲、黑夷等)彼此之间,在文化上虽大同小异,语言上却相当隔阂,甚至到彼此不能通话的地步。这种种族上语言上的隔阂,或许就是今天云南的少数民族不能团结起来走上进步的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他进一步论述说:“据我们所知道的,分布在云南各地支派繁多的少数民族中间,经过年长月久的积累,都有他们丰富而瑰丽的史诗一般的民歌流传着。
《阿细的先鸡》就是千百年来流传在阿细族中的一部长诗。”他解释称歌名“阿细语asy的音译”,意即“歌曲”,所谓“阿细的先鸡”,即“当地汉人恒译为先鸡”而得名,其接着记述道,这部长篇民间叙事诗“是一部活的情歌”,“有着现实的使用价值”,即“在阿细族的村落中,青年男女们在耕作之暇互相对唱,作为求偶的手段”云云。
这里,他提出问题说:“受过近代文明洗礼的我们,或许觉得惊异;在男女恋爱的场合,为什么要反复无穷地歌唱一些与当前的现实无关的神话故事以及风俗习惯这一类的题材呢?”然后,他自己做答曰:“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解释:在原始文化的部落中,歌唱是发挥青年智慧的重要手段,甚至可说是唯一的手段。谁唱得最多,谁记得最多,谁创造得最多,谁的歌声最响亮,最美丽,也就代表谁的智慧最丰富,谁才有资格博得异性对手的欢心。这和我们的社会中某些人以资格学历学位等等头衔来换取异性的赞佩,或者说,如在鸟类与昆虫社会中以羽毛、以歌喉来换取异性的爱悦,是初无二致的。”显然,这种解释未必就是文化人类学的理论,而是文化演进的推论与假设。
光未然的成功与李季《王贵与李香香》的实验有许多相似之处。那么,中国当代文学重视少数民族文学的传统及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否应该从这里更深入地思索呢?
民间文学是千百年来无数民众共同的创造,蕴含着中华民族丰富的聪明才智。尤其是我国众多的少数民族,他们能歌善舞,其民间文学更富有特色。
《阿细的先鸡》是一个典型,三大民族史诗《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也是典型。其他如壮族的民族史诗《布洛陀》,讲述一位“山中无事不晓的老人”如何开辟世界,造就敢壮山、五子山,劈开右江河等充满豪情的故事等。所有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意义,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众多民族和睦相处,相互尊重,使中国民间文学事业充满生机。
随着国际间交往的频繁,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越来越多地受到国外学者的关注,其内容也形成了更大的影响。诸如国际纳西族学会、国际瑶族学会等,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取得可喜成就。尤其是国外学者对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他们一方面表现出自己的研究方法与思想理念,另一方面在交流中也向我们提出挑战,当然,在挑战中也形成学术发展的诸多机遇。我们不再仅仅把意识形态问题提到很高的高度,而是更重视相互学习,共同发展。这是社会发展巨大的进步,改革开放让我们越来越清晰我们与世界各民族间的联系,看到我们的位置,包括我们应具有的立场和态度。想当年,西方人揭开敦煌的面纱,曾经给我们带来多少尴尬;今天,一切都在改变,因为一切都在发展,更重要的是我们逐渐战胜了自我,逐渐摆脱了唯我独尊的文化本位主义,越来越自信,越来越从容。但是,完全纯粹的学术研究是否在每一个地方都存在,或者是否能够完全消除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别,真正做到平等的交流,这还需要用事实验证。而无论如何,我们研究民间文学,将之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任务相结合,这绝对没有过错;一味用西方学者的理论衡量中国民间文学,也未必就是走向了世界。
四、生活的指向
众多少数民族间流行的民间文学是中国民间文学的重要表现形式和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有为数不少的学者并不懂得或不完全懂得民间文学这些内容,动辄说什么民间文学充满封建糟粕,在1940年代对于民族形式的讨论中,如,胡风、葛一虹等人,极力谴责民间文学所显示的封建糟粕,十分武断地把民间文学当作与时代发展相悖的封建迷信,放大了那些所谓低级趣味的内容。这种现象在1949年之后表现得更强烈。民间文学未必完美无缺,但是,把民间文学完全等同于落后,视作小农经济的产物,这未必不是新的蒙昧,未必不是一种极其狭隘而肤浅的理解。中国现代社会政治动荡不断,军阀混战,外敌入侵,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胸怀救国救民壮志的年轻一代知识分子,不畏艰险,始终走一条与人民大众相结合的道路,在田野中发现问题、思索问题,立足脚下,放眼世界,运用各种新说、旧说,重说中国民间文学,发掘出一大批珍贵的民间文学。他们的民间文学思想理论是属于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财富;他们献身民族独立自由解放事业的豪情与品格,更是整个民间文学思想理论的光荣传统。
除了这些,在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队伍中,还有许多民间的宗教团体与个人。另外,许多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得以保存,源自民间宗教中民族文化教育的需要,它们或作为教材,或刻写在教堂宣传墙壁,或作为民族文化的文献典籍而进行整理。
如,伊斯兰教自唐代传入中国以来,在明末之前其传播还比较单一,主要使用阿拉伯语、波斯语作为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语言。明末清初以来,汉语逐渐成为回族社会生活中的共同语言,中国伊斯兰教文化的传承与传播,除在经堂中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之外,还有许多穆斯林学者开始用汉文译述伊斯兰教文化经典。他们称之为“不但使吾教人容易知晓,即儒教诸君子咸知吾教非扬墨之道也”。这也构成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的重要内容;其典籍整理在后来形成《回族经堂歌》。有学者称,这是中国穆斯林学者发起的一次护教辩教的宣传活动,也是中国穆斯林内部振兴宗教信仰的自救活动,它和经堂教育一起,对中国伊斯兰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其中有许多经歌采用三字经、四字经、五更月、哭五更、十叹、十夸、十二叹等传统民间文学形式。其民间歌谣篇,收集有《信主歌》《伊玛尼颂歌》《十二等复生》《可叹歌》《劝世人》《劝青年歌》《劝老人歌》《戒酒歌》《穆民要知道》等。如,其《回教女子三字经》中唱道:“嫂子前,有礼行。多礼请,少任性。
人亏人,主不亏。亏人者,主必罪。”这是宣传民族道德传统的瑰宝。从搜集整理的范围看,有江苏南京、河南商丘、宁夏银川、甘肃兰州等地;从搜集整理的时间来看,有近现代,也有当代。这是中国民间文学的重要内容,却被许多民间文学史著作所忽略。
总之,文学研究的生活指向,应该具有更为广阔的前途。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的特殊财富,具有历史记忆的重要基础性意义。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遗产,东西南北中,上下五千年,它们伴随着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历史,经历风雨,体现了中华民族古老的文明历史、非凡的聪明智慧及独特的审美情操。这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共同创造的文化宝典。众所周知的阿凡提、巴拉根昌成为电影文学的典型,许多少数民族民歌震撼文坛。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文化问题,在中国文学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一方面,它融入中国文化传统之中,成为中国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它以独特的文化风格,不断激活中国文学,使得中国文化充满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