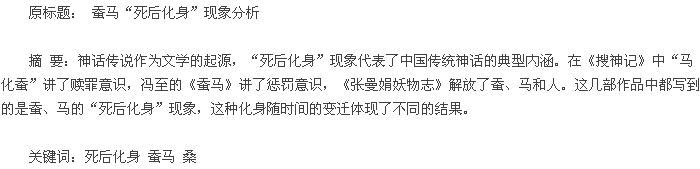
从盘古开天辟地神话开始,与中国传统文化息息相关的“死后化身”现象影响了数代中国人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涵之一。中国历来有许多死后化身的神话与传说, 蚕在传统文化中代表奉献和劳作,马代表速度和力量。 爱上人类少女的马历经艰难险阻,仍然难以求得心上人。 在爱情失败之后带走心目中的爱人,之后化身为“蚕马”,《搜神记》《蚕马》《张曼娟妖物志》作于不同时期,“蚕马”所承载的内涵不断变化,命运也大为不同,分别体现了中国古代、现代和当代蚕马的“死后化身”现象的不同内涵。
儒家为禁原蚕(原蚕指一年中的第二代蚕)而提出的“蚕马同气”(“蚕”与“马”同居辰星,是同类,而同类相克,此涨彼消,此盈彼虚,不可能同时得利,故欲养好马,必先禁蚕)[4]说在民间并未得到呼应,反而,民间的“蚕马”说与之有着很大不同。 《搜神记》中的“马男”最能代表民间的“蚕马”形象。
一
旧说:太古之时,有大人远征,家无余人,唯有一女。牡马一匹,女亲养之。穷居幽处,思念其父,乃戏马曰:“尔能为我迎得父还,吾将嫁汝。 ”马既承此言,乃绝缰而去。 径至父所。 父见马,惊喜,因取而乘之。 马望所自来,悲鸣不已。父曰:“此马无事如此,我家得无有故乎!”亟乘以归。为畜生有非常之情,故厚加刍养。马不肯食。 每见女出入,辄喜怒奋击。 如此非一。 父怪之,密以问女,女具以告父:“必为是故。”父曰:“勿言。恐辱家门。 且莫出入。 ”于是伏弩射杀之。 暴皮于庭。父行,女与邻女于皮所戏,以足蹙之曰:“汝是畜生,而欲取人为妇耶!招此屠剥,如何自苦!”言未及竟,马皮蹶然而起,卷女以行。邻女忙怕,不敢救之。走告其父。父还求索,已出失之。 后经数日,得于大树枝间,女及马皮,尽化为蚕,而绩于树上。 其茧纶理厚大,异于常蚕。 邻妇取而养之。 其收数倍。 因名其树曰桑。 桑者,丧也。 由斯百姓竞种之,今世所养是也。 言桑蚕者,是古蚕之余类也。[1]
故事的过程经历了桑女许诺 (缔约)---反悔杀马(违约)---马皮裹女(践约)---化身为蚕(马头女身),这个故事之后,民间有了“蚕神”. 在后世许多有关咏蚕的诗词歌赋中,化生后的蚕的一生还要经历变蛹---化蛾---成茧---吐丝,周而复始,无休无止,似乎成为一种“赎罪”的象征,蚕最终成了奉献与劳作的象征,这种“化蚕”的结果明显缺乏“化蝶”的浪漫色彩。 那么,我们是否能认为“蚕马”这个形象在民间的广为流传,是否蕴涵着中国人的“原罪”意识?
二
《搜神记 》之后 ,蚕马形象经历了许多变化 ,在民间和官方有着不同的解读。到了现代,冯至以“故事新编”的手法写的新诗《蚕马》给蚕马形象注入了新的内涵。《蚕马》这首诗,冯至分了三段来书写,每段开头都用了相似的咏叹调,使诗歌的最外层面目是一个青年弹着琴、对心上人歌唱爱情的歌曲,他所唱的乃是个忧伤的、热烈的远古传说:蚕马-女化蚕。这就构成了类似复调小说的框架,叙述者本身是一个故事,他所叙述的故事又与他本身有非常密切的联系。诗的结尾如下:
一瞬间是个青年的幻影,一瞬间是那骏马的狂奔:在大地将要崩溃的一瞬,马皮紧紧裹住了她的全身!
姑娘啊,我的歌儿还没有唱完,可是我的琴弦已断;我惴惴地坐在你的窗前,要唱完最后的一段:一霎时风雨都停住,皓月收束了雷和电;马皮裹住了她的身体,月光中变成了雪白的蚕茧![2]《搜神记》里,无言的马由于不能作为第一主角来书写,马是缺乏感情的,只是作为承载象征的一种物;是冯至将马-白色骏马-青年打通,使“它”成为了“他”,抹去了因果报应、负誓受罚等陈旧的话题,却描写和肯定了他执拗的爱情、深切的哀伤和生气勃勃的勇力,写了客观外在对他最灼热的要求的强硬压迫和他虽已死亡、但仍要抵抗、并最终完成了和所爱之人变成一体的过程。 错落有致的笔调里,洋溢着新时代学研究的特色,蚕马脱去了赎罪的内涵,成为勇于追求的斗士。
但是人与兽的隔膜与生俱来, 所以马带走了姑娘,和姑娘变成了同类,结合在一起,变成了“蚕马”,马和人再也无法分开。 冯至的这首诗中,我们能否认为“蚕马”是对不守信诺、忘恩负义的惩罚?
三
到了当代张曼娟的笔下,这个故事焕发了新的光彩。这个故事有些不像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反倒有点像一个世外桃源, 或者是更古老的故事。 不管是环境(罗浮山下广阔的牧场),还是人物职业(教头、马师)、称呼(姨娘、爹爹),都和其他的故事不太一样。
这个故事更纯粹地将情感的部分停留在两个点上:陪伴与奔跑。白马追风的陪伴,让萱儿在寂寞的少女时光中懂得了什么是爱,什么是温暖。 每当萱儿跨坐在白马上,这是一个何等亲密且贴近的动作。 躲在马肚下取暖的细节, 更彰显了白马对萱儿的重要性。
而这,就是两人情感稳定下来的基础。
而突破口,则是追风的奔跑。第一次的奔跑,他在她面前停下,从而成了她的马。第二次奔跑,他从火里救出了她,带她到山林,并化为人形,与她交合。 第三次奔跑,则是他带着她奔进永夜,奔向属于他们自己的人生。
这三次奔跑,一次比一次强烈,犹如战鼓,节奏越来越高昂。在模糊了年代的故事里,追风的奔跑,是一种对爱的勇敢向往。 而这个故事,似乎也是一个因为勇敢而成了最完美的故事。
故事中,少女被亲友合力骗走,人们要杀掉追风,萱儿明白之后:“带我走.”萱儿在追风的耳边轻轻地说,“带我回你的家去……”追风带着萱儿奋力奔驰,萱儿的泪被风吹进鬓发里,她俯下身,感觉着自己与追风合二为一,永远都不再分开了.那天很特别,太阳一直没有高升,天沉沉地黑着,仿佛,永不黎明.[3]张曼娟写人间诸般情事细腻而不缠杂,这篇《永夜的奔驰》中,少女和马之间两情相悦,情深义重,完全没有传统的“蚕马”形象的沉重感。马有了自己的名字---追风, 也有了人的形体---英俊健壮的少年。
虽然人和马之间仍然有着很大的隔膜,这集中表现在少女萱儿之外的人类对人马恋的排斥,但是在少女萱儿和白马追风之间体现的则完全是少年男女之间真挚浓烈的人间爱恋。排斥人马恋情的人类阻止不了青年男女间纯洁炙热的爱情,最后白马追风和少女萱儿回到他们的世外桃源,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四
中国传统文化中化身的神话和传说有很多,盘古化为万物,滋养人类;梁祝化蝶,歌颂爱情;独独马和少女化身为蚕,承载着赎罪的重任。 马匹裹着少女化为蚕蛹,作茧为庐,生死不离。 这是古代的蚕马,也是冯至笔下的蚕马。张曼娟笔下的马却只有世外桃源的家,只有永夜的奔驰,它无需做茧,只要带着心爱的少女回家,就是永恒。
马在文化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它通有灵性,它的拟人化的形象出现在许多角落。 蚕更是由于吐丝成茧,繁衍衣物,和人类生活息息相关,“春蚕到死丝方尽”是它的写照。同样,外国文学中也有许多“马人”的传说,这些传说中马具有人的意识和身体,同时保留有马的四肢,有意思的是,这些马人尽管十分高大敏捷,但是其地位却远远低于人类。 英国有部着名的舞台剧“恋马狂”,男主角 Alan 极度爱马,甚至将马当成神只崇拜,他夜半裸体骑马在郊外狂奔,既是他独创的敬神仪式,也是一种欲望的发泄,他之所以刺瞎马眼,是因为他不愿让他的“神”/“爱人”眼看他与女友在马厩里亲密(众马环视之下),无法完成男性“庄严”之任务。 马是 Alan 的救赎,马主宰他,他同时又主宰马的命运。纵观中外文化,马、人之间的关系复杂又深邃。
蚕在中国文化中成为极具象征性的事物,这与蚕吃桑叶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因为蚕与桑树之间关系紧密,而扶桑木是太阳树,代表了太阳,是阳性的,我们的先人用桑树来作为社木,就是表示太阳,作为人类的生命之树、生命之木。先人们也多选择生命之树、太阳之树---桑树作社丛,也就成了桑林。 这桑林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功能, 就是专供男女相会交合之用。
《墨子·明鬼》中有:“燕之有祖泽,当齐之社稷,宋之桑林,楚之云泽也。 此男女之所乐而观也。 ”《淮南子》中有:“桑林者,桑山之林,能兴云作雨也。 ”这种男女的自由交合,并不是现在人们以为的淫乱,而是古人祭社的一种仪式,这种仪式和古人推崇天地阴阳交合平衡与企求生命的延续和旺盛密切相关。从这个角度去分析,桑叶是蚕生命的来源,桑林是蚕的理想天堂,那么蚕马结合在一起成为茧状生死相依,就是可以理解的了。所以,后人有说孔子生于“空桑”,也就是说生于桑林了。 可见,桑林中的野合,在其时是正常的,不仅不为人所诟病,还可以理解为何蚕、马会和人类之间的关系被不断推衍。
“蚕马”之说在中国文化中延续了数千年,“蚕马”承载的赎罪或者惩罚的内涵,从古至今,这种死后化身的内涵被不断变化和演绎。 有意思的是,生长于台湾的张曼娟在她的妖物志中使蚕马得到解放,马没有“作茧自缚”, 他最终和深爱的少女住在世外桃源,爱情至上,遑论其他。
参考文献
[1] 干宝。搜神记(卷十四)[M].上海:中华书局,1979.
[2] 冯至。冯至选集[M].四川: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
[3] 张 曼娟 . 张 曼娟妖物志 [M]. 北 京 : 中国画报出版社 ,2008.
[4] 徐湘霖。“蚕马”杂谭[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