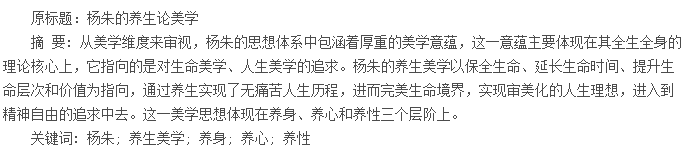
杨朱又称作杨子、阳子居、阳韩生,生卒年代未详,大约生活在墨子与孟子之间。杨学本身并无鸿篇巨制传世,其思想散见于《孟子》、《庄子》、《淮南子》、《吕氏春秋》等,《列子·杨朱》虽疑为魏晋人撰辑,且杂糅有魏晋的恣情放纵思想,但它所记述的杨朱思想是可以通过先秦其他典籍得到佐证的,至少是在其思想原貌基础上的进一步发挥。目前学术界对于杨朱思想的理解,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隐逸遁世思想的早期理论,二是个人本位主义和朴素的自由主义政治理论,三是享乐主义,四是纵欲主义。这些观点都在不同侧面看到了杨朱思想的某些特质,自有其理论价值和启发意义,但享乐主义和纵欲主义的观点却是值得商榷的,其仅仅通过《列子·杨朱》中的一些论述,并忽视对这些言论的社会历史背景的考察而作出结论,是不尽符合杨朱的真实思想的。
实际上,如果从美学维度来审视,其思想体系中蕴含着厚重的美学意蕴,这一意蕴主要体现在全生全身的理论核心上,它指向的是对生命美学、人生美学的追求,而这正是养生论美学的精神实质。杨朱的思想,整体上看都是在阐述养生的问题,其旨在逐鹿争霸、纷纭动荡的年代里让人们认识到身体的唯一性和生命的不可重复性,倡扬合理的利己主义与适度的自然欲望,远害保宜,情趣生活,放达人生。因而,杨朱的美学思想可以称之为“养生美学”。杨朱的养生美学以保全生命,延长生命时间,提升生命层次和价值为指向,通过养生实现无痛苦人生历程,进而完美生命境界,实现审美化的人生理想,进入到精神自由的追求中去。它主要包含了重己贵生的生命美学,全真保性、不以物累形的放达超逸的人生美学,而这一美学思想具体体现在养身、养心和养性三个层阶上。
一、养身:贵生重己,轻物重生
“身体”是一个有机实体,是情感欲望的载体和思想意识的发出者,同时也是活动的实践者。[1]身体是世界中的变动的物质存在,处于各种关系之中,所有的事情都要通过“身体力行”,才能达到与外界的沟通联系,“凡事之本,必先之身。”(《吕氏春秋·先己篇》)[2]77《庄子·养生主》认为养生的目的就是保身、全生、养亲、尽年,把保身放在首位。人不是身体之外的其他什么东西,而是身体自身,心灵、精神和语言也只能附属于身体。所以,养身是养生的第一要义。杨朱的养身美学思想,以贵生重己、轻物重生为理论核心,主要体现在珍惜形体、去除壅阏,适度张扬欲望以及解放身体,不为物累,乐生逸身等几个方面。
第一,贵生重己,珍惜形体。杨朱首先认识到作为身体的重要性。《吕氏春秋》说:“今吾生之为我有,而利我亦大矣。论其贵贱,爵为天子不足以比焉。论其轻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论其安危,一曙失之,终身不复得。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孟春纪·重己》)[2]16身体的重要性在这里被着重凸显出来了:即使失了天下,也许有朝一日能够再得,但是一旦死了,就永远不能再活过来。它揭示了感性的物质肉体是人生命的本根。因而杨朱认为,“身故生之主”,它是我们生命的主体和载体,“存我为贵”,“全身”为贵[3]201。所以,身体之重重于天下,我们没有理由不去好好保养保全它。
身体是宝贵的,杨朱同时也清楚地认识到它的局限性和脆弱性。“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卫,肌肤不足以自扞御,趋走不足以从利逃害,无羽毛以御寒暑。”人的身体如此局限和脆弱,所以自然要加以保护,即使一毫一毛,也要珍惜。
“禽子问杨朱曰:去子体之一毛,以济一世,汝为之乎?杨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济。禽子曰:假济,为之乎?杨子弗应。”
杨朱不予回答的原因是他的确看重身体的一毛一毫,因为在他看来:“微于肌肤,肌肤微于一节,省矣。然则积一毛以成肌肤,积肌肤以成一节。一毛固一体万分中之一物,奈何轻之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是一个人立身处世的本基,是不能随意损毁的。而且他认为,让肉体去“践锋刃、入汤火”也是不可以的,不能故意戕害自己的生命。这里,杨朱之言足见他对身体的珍视,尽管有夸张之辞,但如果我们结合他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也许就能理解他过分强调珍惜一毫一毛的原因了。在逐鹿争霸无义战的年代,统治者们为了争夺权利,扩大疆域,对人民采取诱战政策,诱以利禄或强迫人们为之流血作战。杨朱力倡重生,呼吁人们珍惜自身的生命价值。在杨朱看来,墨家儒家过分强调社会国家整体而忽视个人利益,而他的这些言论,从规定人的义务转向了对人自身生存权利的肯定与追求。在这个意义上,杨朱的养身理论不仅具有养生论美学意义,也具有社会伦理学美学意义了。除了《列子》中有这样珍惜身体的论述,在《韩非子·显学》中也有类似的记载:“今有人于此,义不入危城,不处军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
冯友兰认为《韩非子》里说的杨朱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与《孟子》里说的杨朱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有些不同。《韩非子》所表达的是杨朱“轻物重生”的思想。
杨朱还为养身找到了本体论意义上的理论支撑。他进一步指出:“然身非我所有,既生,不得不全之……身固生之主,物亦养之主。虽全生,不可有其身,虽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横私天下之身,横私天下物……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身体不是我所有的,但是既然生了,就不得不保全这个身体。因为身体是生命的主体。他所主张的贵己重生,他所竭力保全并令之愉悦的身体,并不是自己的,而是一种类似于归天属地之类的“公天下”之物,它们属于天下公有,而我只是代为保管,任何人无权损伤,每个人所具的身体和欲望,是至高无上的、至圣至公的。这就升华了杨朱的生命哲学,使他的养身美学思想不仅建立在合理的“为我”主义上,更建立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高度,把个人与社会统一起来,更符合群体社会的审美理想。
第二,去除壅阏,适度张扬欲望。“身体自身的特性,即它是个体的、差异的、并且是充满无限欲望的。”[6]64但人的欲望首先是身体的欲望。人之所以有欲望,是因为人有身体。因此只要人是具有身体性的,那么人就有欲望。这样,人们根本不可能绝对地禁止欲望,而只能是在何种程度上限制欲望。欲望就是人的身体的基本存在,是它天然的需要和满足。“人的身体的肉体性表现为它的欲望。其生死爱欲就是吃喝性的欲望。”[6]66“人的身体就是其肉体性,而不是这个肉体性之外的其他什么。作为肉体性的存在,人的身体是其基本本能的冲动和实现。因此人的身体实际上是一个欲望机器,是由欲望而来的不断的生产和消费。”[7]143
身体是欲望的身体,对于人的自然欲望,杨朱提倡要适度“肆之从之”,勿壅勿阏,满足应有的欲望,身体就不会出问题,这样才能做到养身。杨朱认为:“夫耳之所欲闻者音声,而不得听,谓之阏聪;目之所欲见者美色,而不得视,谓之阏明;鼻之所欲向者椒兰,而不得嗅,谓之阏颤;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谓之阏智;体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从,谓之阏适;意之所为者放逸,而不得行,谓之阏性。凡此诸阏,废虐之主。去废虐之主,熙熙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谓养。”只有“意之所为者放逸”,而得以行,才符合人性自然欲望的要求,也只有符合人性欲望的生命,才是养生的。只有“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这样熙熙然以至于死,才是享受生命。反之,“拘此废虐之主,录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万年,非吾所谓养”。
杨朱说:“人之生也奚为哉?奚乐哉?为美厚尔,为声色尔。”也就是丰屋美服、厚味姣色。房屋豪富,衣服鲜美,佳肴陈列,妻妾娇美,这确实是大多数人欲望的愿望所在,但丰屋、美服、厚味、娇色并不是杨朱所讲的人应有的欲望,而是理想中的欲望。因而获得身体的审美快感仅仅是不人为刻薄地限制自然欲望,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让身体的欲望得到满足,而不是以禁欲主义的方式壅阏堵塞。人性的实现、人生的快乐和美就在于感性欲望的满足,是歆享当下感官享受带来的生命之乐。杨朱追求的身体的感性快乐欲望,构成了他养身美学的第一大要素。
养身不能禁欲,但也不是纵欲。杨朱的“意之所为者放逸”,并不是毫无限度的纵欲,而是明确地指出,欲望也是有限度的,是应当加以自制的:“丰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于外?有此而求外者,无厌之性。无厌之性,阴阳之蠹也。忠不足以安君,适足以危身。”在满足基本欲望之后,不能贪得无厌,无厌的追逐,会破坏身体内部的阴阳平衡,从而危害身体,不仅于个人有害,对于社会和国家也是不好的。
不唯身体的欲望需要节制,就是日常生活也不应当过于铺张,甚至埋葬死者也“不含珠玉,不服文锦,不陈牺牲,不设明器”,这种生活态度是对适度生存的理智思量。因而,杨朱的身体欲望理论,是带有明显节制主义倾向的“适欲”论,其侧重点在于重生养身,是“适欲”的养身美学理论。
第三,解放身体,不为物累,乐生逸身,情趣生活,任智而不恃力。杨朱说:“原宪窭于鲁,子贡殖于卫。原宪之窭损生,子贡之殖累生。然则窭亦不可,殖亦不可。”
原宪贫穷有损于身体,子贡经商有累于身体。所以贫穷也不行,经商也不行。这里似乎有点矛盾,其实,杨朱在这里举例想要说明的是做事要有一个度,这个度就是不以伤害身体为基准。既不以穷损生,也不以富累生。原宪要做一个隐士而隐耕于乡野之中,但过度的贫穷有损于身,子贡经商过度追求财富也有累于身体,由于贫穷和过度追逐财货都会损坏身体,所以应当解放身体,不为物累,也不为物所累。杨朱说:“其可焉在?曰:可在乐生,可在逸生。故善乐生者不窭,善逸生者不殖。”要怎样才行呢?要生活快乐才行,要身体安逸才好。所以,不因为求得虚妄的名声而在偏僻之地受穷而损生,不因追求过多的财富去劳碌而累生。杨朱这里所说的“乐”,是指“安贫乐道”的“乐”,而不是“贪图享乐”的“乐”,所说的“逸”,是指“身劳心逸”的“逸”,而不是“贪图安逸”的“逸”。乐生逸身,过一种平静闲适的情趣生活,不失“当年之乐”和“当身之娱”。
由于人维持身体的存在必将资物以为养,这就需要身体的劳作,而过度的劳作又会损毁身体,所以,杨朱认为,养身就要学会惜力,学会以智求乐。因而“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贵,存我为贵;力之所贱,侵物为贱。”杨朱认为应该“任智而不恃力”,用智得到所需来养生,是上策;用力侵物得到所需,为下策。这点他与古希腊居勒尼派早期的快乐主义有某种相似的地方。他们都认为有智的人是更懂得驾驭快乐而不为其所奴役,并且相信尽可能地利用每件事物,要么限制欲望,要么用聪明和自制来确保和满足快乐的条件。“从无原则批判出发的身体美学无非主张身体的自由和解放,同时主张感觉的自由和解放。”[6]侯外庐在《中国思想通史》中则肯定杨朱的“为我”乃是把人首先理解为生物性的存在,坚持从人本身去说明人,而不是人为地附加更多虚假与神圣的东西,并直言:“在今天阐述杨朱学派的理论时,也许会使人产生一种现实的不快感”,但“这一理论的个人主义的思想背后,隐然潜伏着承认感觉体的光辉。”[8]348
二、养心:不逆万物,不以物累形
养身是一种具体行动,而行为决定于意识,一切外在的行为皆“从心而动”,因而养身必先养心,它是生命活动的直接决定因素。养心就是个体对待外物的思想观点,所持的态度等方面应有的涵养,它要求排除外在诱惑,不以物喜悲,追求心灵的宁静平和,顺应万物规律,随遇而安进而达到神行同一。杨朱的“养心”美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顺从自然,不逆万物,不违自然。事物在变化,但事物变化的规律不变。一个人如果懂得了这些规律,并且遵循这些规律以调整自己的行动,他就能够使事物转向对他有利,从性而游,不逆万物所好。杨朱认为:“生民之不得休息,为四事故:一为寿,二为名,三为位,四为货。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谓之遁民也。”追求这四样东西,就会怕鬼、怕人、怕权势、怕刑罚,这就是违背自然本性的人。相反,不逆万物,就可以成为“顺民”,即顺从自然本性的人,这些人可以顺应自己的心性,控制自己的命运。
(二)顺从天命,且趣当生。对于个体的人来说,这里更多的是顺从天命,且趣当生。杨朱认为人要“不逆命”。
什么是命呢?他说:“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今昏昏昧昧,纷纷若若,随所为,随所不为,日去日来,孰能知其故?皆命也夫。信命者,亡寿夭;信理者,亡是非;信心者,亡逆顺;信性者,亡安危。”(《列子·力命》)[3]167现有的一切都纷杂混乱,日子一天天过去,一天天到来,其中的缘故都是命运。相信命运的,无所谓长寿与夭亡;相信天理的,无所谓是与非;相信本心的,无所谓困难与顺利;相信天性的,无所谓安全与危险。这就是杨朱的天命观。
杨朱“顺从天命、且趣当生”的思想主要表现在他的生命时间观和生死观上。杨朱认为:“百年,寿之大齐。得百年者千无一焉。设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几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昼觉之所遗,又几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忧惧,又几居其半矣。量十数年之中,逌然而自得亡介焉之虑者。”在他看来,由于人的寿命最长不过百岁,其中“孩抱”时代和“昏老”时代占了一半,睡觉时间又占了一半,“痛疾哀苦”又占了一半,真正可以使身体享受感性之乐的时间少之又少,因而更应抓住。生命存在的时间有限,幸福与美好在于解脱心灵,在于适度地放逸,就要“从心而动”,“从性而游”,“自肆于一时”而不违天命。这是一种洒脱达观的生命时间观。一个人要清楚地了解生存时间的数量,就会有意识地提高生存的质量,就会从容对待生死,就会珍惜生命而不是畏惧生命,就不会有畏、惧、烦、扰,也就常常持有从容不迫、恬静安适的心情,这样也就达到了养心的目的。不仅仅时间不常在,事业也不常在,杨朱说:“太古之事灭矣,孰志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觉若梦,三王之事或隐或显,亿不识一。”无论多么宏伟的事业也是过眼云烟,会被湮灭在历史的风尘之中,因此,要心存恬淡,不要心性太高,不要心鹜高远而劳神劳心。
杨朱对于生死也有清醒的认识,他深知对于个体来说,“理无不死,理无久生,生之难遇,而死之易及。”所以对于生死,就要洒脱对待,“无不废,无不任,何遽迟速于其间乎?”心中明了这个道理,就没有什么舍弃不了的,没有什么理由不去放任身心的,何苦为生死之间的迟缓或者迅疾而整天惶恐忧虑呢?而且,“太古之人知生之暂来,知死之暂往;故从心而动,不违自然所好;当身之娱非所去也……年命多少,非所量也,然而万物齐生齐死,齐贤齐愚,齐贵齐贱。十年亦死,百年亦死……孰知其异?”有了这样的生死观,就会保持一颗平常淡静之心,从心而动,“且趣当生”,享受有这种平和心态带来的生命乐趣。
(三)顺从自心,不求虚名,不求清贞。不违天命是杨朱养心理论的外在方面,是对于心灵的外在要求,顺从自心则是人对于自我心灵的内在要求,它要求个体不违背自己的心性,不求虚妄的荣誉,不求过分的清高贞洁,不以礼义自苦,而是顺从自心的呼唤,从性而游。
杨朱说:“名乃苦其身,燋其心。”“实无名,名无实。名者,伪而已矣。”养生就要顺从自心,自自然然做个真实的人。
而有名声的人就不会真实,真实的人是不需要名声的,名声不过是虚假作伪罢了。因此,名声让人身体劳累,心情焦躁,是养生的大患。但这并不是说,杨朱完全否认和抛弃名声,他所反对的是对于人的形体心神有害的虚名,反对为博取名声而戕害身心的做法。他说:“名胡可去?名胡可宾?但恶夫守名而累实。”名声怎么可以抛弃,名声又怎么可以当做附庸?只是厌弃那些死守名声而损害身心的做法啊。
杨朱基本上分出了两种虚假名声,一种是所谓的政绩政德,一种是所谓的人格操守。这两种名声都有害于身心,无益于养生。他举例子说:“但伏羲已来三十余万岁,贤愚、好丑,成败、是非,无不消灭;但迟速之间耳。矜一时之毁誉,以焦苦其神形,要死后数百年中余名,岂足润枯骨?何生之乐哉?”又说:“伯夷非亡欲,矜清之邮,以放饿死。展季非亡情,矜贞之邮,以放寡宗。清贞之误善之若此!”伯夷过分清高了,以至于饿死山中,展季并非缺乏感情,而是坚贞过分了,以至于缺少后代。博取清高贤贞的名声就会造成这样大的失误啊!
所以,人要“不为名所劝,从性而游,不逆万物所好。”不为名誉所引诱,放纵本性而游历,不背逆万物的好恶,不去着意追求死后的名声,不去考虑名誉的大小,寿命的长短,做一个不慕虚荣的人,那么“去名者无忧”,无忧则心神愉悦,这就是养心,就是养生。
杨朱的养生美学思想,虽然落实在贵己重生上,但这一切都要靠人的主观意识来支配实现,养身必须通过养心来完成,所贵的是身体性命不受伤害,但更进一步,所重的是真性情不违自然,不违天命,这一观念共同构成了杨朱的“生命”的概念,构成他生命美学的主要内涵,是他的养生美学思想的核心所在。
三、养性———全性保真,追求自由的人格和自由的精神
养性,指的是精神情志的调养与道德修养,通过自我反省体察,使身心达到完美的境界。《淮南子·俶真训》:“静漠恬澹,所以养性也;和愉虚无,所以养德也。”[9]48
道家主张淡泊无为,涵养人的自然本性。实际上,在杨朱的养生美学思想中,尽管在实际生活中养身、养心、养性这三者是彼此间相互联系,甚至重复交叠,无法清楚分开的,但从理论上讲,养身是肉体层面,养心是在心理(心灵)层面的追求,养性则是在精神层面的追求,这是一个不断提升迁跃的过程。杨朱的养性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自由人格和自由精神的追求
反对礼仪,反对虚名,不为名所劝,从性而游,放意所好。这是杨朱人生美学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其养生思想的内核。
杨朱见梁惠王时说:“君见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棰而随之,欲东而东,欲西而西。”这既是在谈论治国者要顺从民意民心,也是在说作为个体的人应有的自由精神。杨朱说:“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人人治内贵己,互不侵损,人人自重自爱,则天下治矣,这正是一种超逸的自由精神。他借用好酒的公孙朝、好色的公孙穆的故事,不赞成“欲尊礼义以夸人,矫情性以招名”的做法,指出:“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内者,物未必乱,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暂行于一国,未合于人心;以我之治内,可推之于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反对礼法和君君臣臣的等级秩序,鄙视功名利禄,个人通过“治内”来自我完善,塑造独立自由的人格精神,达到怡然自适的人生目的。
(二)“行贤去贤”,建树博爱的德行
“行贤去贤”是一种道德追求,是马斯洛自我价值实现的需求,也犹如克尔恺郭尔的道德存在或宗教性存在,是一种祈祷和爱的生活,是对“神”的自觉和崇敬,从而使精神有所寄托的存在。《韩非子·说林上》曰:“杨子过于宋东之逆旅,有妾二人,其恶者贵,美者贱。杨子问其故,逆旅之父答曰:‘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恶者自恶,吾不知其恶也’。杨子谓弟子曰:‘行贤而去自贤之心,焉往而不美’。”
杨朱这里所赞扬的这种人格,是一种超越现实功利、臻达天地道义的精神追求,也是一种天人合一的审美人生境界。
博爱也是养性应有的途径和应该达到的境界,它体现在均贫富、“生相怜”等思想上。杨朱说:“相怜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饥能使饱,寒能使温,穷能使达也。”所谓怜惜,并非只是动之以情;而且能使劳苦的得到安逸,饥饿的得到饱饭,寒冷的得到温暖,穷困的得到显达。他举了一个乐善好施的例子:有一个叫端木叔的人家累万金,却不经营家业。他在放意所好之余,奉养门客之余,先把钱财施散给宗族,再施散给乡里,又施散给整个都城的人民。杨朱借段干木的话来评论说:端木叔的德行超过了他的祖先,他所行的尽管众人都感到惊骇,但确实是符合自然之理的啊。这个自然之理就是人间大义,天地道义,是博爱,是冯友兰所说的道德境界。
此外,杨朱认为养性就是要做到性情超迈飘逸,表现在治事上,就是散淡粗放,不拘于细末,不斤斤计较。他比喻说:“吞舟之鱼,不游枝流;鸿鹄高飞,不集污池。何则?其极远也。黄钟大吕不可从烦奏之舞。何则?其音疏也。将治大者不治细,成大功者不成小。”将要治理大事的人不去做小事,成就大功的人不纠缠小功。不在一些细枝末节上纠缠考究,而保持一种恢宏放逸的气度,这既是对待事情的态度和策略,也是在治事中全性保真,顺应事情自身情理而涵养人的性情的一种途径。
总之,养性就是要通过内修道德的修养方式,来达到“内圣”,提升生命的层阶,获得精神的自由,实现审美化的人生理想,完美个体的生命境界。必须指出,就《列子·杨朱》而言,杨朱养生言论中有不少偏激夸张之语,这一是当时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所致,二是魏晋时期放浪之风的遗留,三是杨朱个人思想本身有不够通融的自我矛盾之处。但就其养生美学意义上看,养生作为一种人生审美理想,始终是杨朱所注重阐述和倡扬的,因而是相对系统和圆融的。
参考文献:
[1]拉·梅特里.人是机器[M].顾寿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2]吕不韦.吕氏春秋[M].陆玖,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
[3]列子.列子(杨朱)[M].叶蓓卿,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
[4]王先慎.韩非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3.
[5]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
[6]彭富春.身体与身体美学[J].哲学研究,2004(4).
[7]彭富春.美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8]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卷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9]刘安.淮南子[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