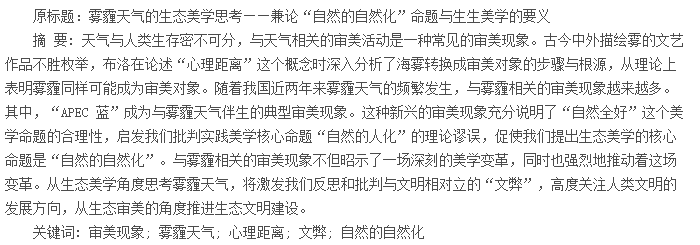
一、引言
中国当代着名美学家李泽厚的《美学四讲》开门见山地提出了一个问题:“美的现象极多,却各不相同。松涛海语,月色花颜,从衣着到住房,从人体到艺术,从欣赏到创作……在如此包罗万象而变化多端的领域里,有没有、能不能存在一种共同的东西作为思考对象或研究对象呢?”对于这个问题,李泽厚在《美学四讲》中所作的回答无疑是肯定的。
以他为代表的中国当代美学所致力研究的,就是隐藏在各种“美的现象”背后的那种“共同的东西”,也就是学术界普遍接受的“美的本质”或“美的规律”。如果遵循这种美学研究思路及其所隐含的美学观,将雾霾天气与美学联系起来至少会遭到如下两个强烈质疑:第一,雾霾天气是“美的现象”吗?第二,如果雾霾天气不是“美的”,它就不可能让我们产生“美感”,那么,雾霾天气在什么意义上能够成为美学的研究对象呢?将这两个质疑结合起来也就是追问:是否有一种新型的美学理论,能够从理论上回应与人们的健康生活密切相关的雾霾天气?
笔者一直坚信,任何理论的功能和价值都在于解释现象,美学理论的价值也在于它对现实生活中各种审美现象的解释效力。一种美学理论无论逻辑多么严密,无论它的哲学基础多么高深,只要它无力解释人类现实生活中的审美活动,它的存在价值就会大打折扣。我国最近两年雾霾天气频繁发生,围绕雾霾天气而产生的幽默段子、摄影作品不计其数,某种程度上正在挑战国内的主导性美学理论即实践美学,正在激发美学研究者对雾霾天气引发的审美现象做出理论回应。
本文尝试从生态美学角度对雾霾天气做出理论回应。我们将首先考察与雾、雾霾相关的审美现象,着重分析雾霾在什么意义上能够成为美学意义上的审美对象,然后分析与雾霾天气伴生的典型审美现象“APEC蓝”所展示的“自然的人化”这个命题的理论谬误,最后从生态美学的角度论述“自然的自然化”这个新的理论命题,简单勾勒生生美学的要义,从而尝试勾勒出“雾霾天气美学”的大致轮廓。
二、雾霾天气成为审美现象的美学理论根据
天气是一种自然现象,而审美活动则是人类生活中常见的一种社会现象。尽管二者有着质的不同,但它们经常联系在一起,古今中外的文艺作品中都有与天气相关的审美现象。最为我们熟知的例子应该是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其中描写到天气与人的情感体验的关系。从“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到“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那段文字,描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天气———“霪雨阴风”与“春和景明”,以及与之对应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情感体验———“感极而悲”与“其喜洋洋”。这就有力地表明,无论是阴雨天气还是晴好天气,都可以引发人们的情感体验而成为人们的审美对象。
需要辨析的是“审美对象”(aestheticobject)这个术语,它不同于汉语美学中比较随意而含混的概念“美的对象”(beautifulobject)。“美的对象”也就是各种美丽的事物,它们一定是“美的”;美学理论中的“审美对象”则有丑、美之分,也就是说,有“丑的审美对象”。从日常语义上来看,“丑的审美对象”这种表述似乎是个自相矛盾的悖论,但汉语美学中的“审美”二字,决不能望文生义地理解为如同“审稿”“审案”这样的动宾词组“审—美”———对于美的观审。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西游记》中的典型形象猪八戒形貌丑陋,但它一直是人们喜闻乐见的“审美对象”;罗丹的着名雕塑《老妓》所塑造的人物形态年老色衰、干瘪丑陋,但她依然是世界艺术宝库中的代表性审美对象。
雾是一种常见的自然现象,在古今中外的文艺作品中同样常见。比如,南朝梁萧绎的《咏雾诗》、清代袁枚的《良乡雾》。西方着名文学家写到浓雾的作品也很多,比如狄更斯的《双城记》曾经用“恶灵”“波涛”两个比喻来描绘浓雾,把雾刻画成了生动的艺术形象。那么,作为普通天气现象的雾,为什么可以成为审美现象?也就是说,从自然的天气现象到人类的审美现象,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转化?笔者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美学的“阿基米德点”,也可以称为美学的“内核”。对于这个问题,最经典的解释是布洛做出的。
英国美学家爱德华·布洛1912年发表了一篇影响深远的长文———《作为艺术要素与审美原理的“心理距离”》,文章的主旨是论证那种能够产生“审美特性”(aesthetic qualities)的距离。布洛特别强调了“审美的”这个修饰语,表明事物有着各种各样的“特性”,他着重研究的则是在“心理距离”中产生的“审美的特性”。这就是说,审美距离是审美特性得以呈现的前提条件。为了解释“心理距离”的性质与作用,布洛以海上浓雾为例来展开论述。
对于在大海上航行的人来说,海雾往往是焦虑和烦恼的根源,因为浓雾会延误航程、导致危险。但是,布洛指出,“海雾也可能成为强烈风味和乐趣的来源”,关键在于人们用什么样的心情、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看待浓雾。根据布洛的描述,这种奇妙的转换过程包括如下三个步骤:第一,暂时从海雾体验(比如它的危险和让人讨厌)中超脱出来;第二,将注意力指向“客观地”构成海雾这种现象的各种特征———海雾如同面纱那样环绕四周,像牛奶那样既透明又不透明,模糊了各种事物的轮廓并将它们扭曲得奇形怪状;第三,观察、注意浓雾笼罩的天空与海水,从中体验各种奇妙的感觉。布洛特别指出,这种转换通常是突然发生的,“就像一束亮光闪过,照亮了那些或许最普通、最常见事物的景象———这种印象是我们有时在某些极端瞬间所体验到的;当此之时,我们的实际关切(practical interest)像电线突然由于电压过高而断开,我们就如同一个极其冷淡的旁观者那样,观察某种即将临头的大灾难的极点”。
布洛所概括的三个步骤其实就是对于审美体验发生过程(也就是审美活动)的描述,我们可以从中概括出审美体验的构成要素及其基本模式:人(审美关切→审美注意→审美感知能力)+事物(感性特征)→审美体验根据上述模式可知,世界上任何具有感性形态的事物都有可能成为人们的审美对象,促使这种“可能性”转换为“现实性”的则是人们的“心理转换”:从实际关切转向审美关切,从计划中的事务转向当下事物,从而使得当下事物的“感性特征”在人的审美关切中呈现出来而成为“审美特性”,人们也同时从事物的审美特性中获得审美体验,此时的寻常事物也就成了美学意义上的“审美对象”。
雾霾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雾,但从一般视觉感知上来说,雾霾与普通的雾并没有显着差异,以至于雾霾最初出现时,人们误以为那就是通常的烟雾。根据我们上面所分析的审美心理学原理可知,雾霾与任何具有感性形态的事物一样,也可以在人们的审美关切中呈现出来,从而形成一种非同寻常的审美现象。
文艺作品通常是表达审美关切的典型媒介,雾霾肆虐期间我国出现了不少与之相关的文艺作品,其中,最为着名的例子是《沁园春·霾》:北京风光,千里朦胧,万里尘飘。望四环内外,浓雾莽莽,鸟巢上下,阴霾滔滔!车舞长蛇,烟锁跑道,欲上六环把车飙。须晴日,将车身内外,尽心洗扫。空气如此糟糕,引无数美女戴口罩。惜一罩掩面,白了化妆!唯露双眼,难判风骚。一代天骄,央视裤衩,只见后座不见腰。尘入肺,有不要命者,还做早操。
这首戏仿毛泽东《沁园春·雪》的“打油词”传遍了大江南北,并被不断“戏仿”,比如出现了郑州版、武汉版的《沁园春·霾》等。这些作品之所以被称为“戏仿”,是因为很难说它们的艺术水平有多么高,很难说它们就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但是,我们必须客观地承认如下事实:用词的形式描绘日常生活中的雾霾天气,这无疑表达了人们对于雾霾的某种程度的“审美关切”。词中的雾霾不再是一种日常天气现象,而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一种“审美对象”。简言之,采用诗词的形式来记录、描绘雾霾天气,无疑是我国新兴的一种审美现象。
如果说上面所引用的“打油词”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艺作品的话,那么,下面的一篇回忆性作品无疑是一篇比较优秀的报告文学。2014年10月12日,凤凰网的“凤凰博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它杀死了我的父亲”———那场夺走12000条生命的雾霾》。该文由英国露丝玛丽等人口述,由邓璟整理撰稿,比较详尽地描述了1952年12月5日的伦敦雾霾及其恶果。露丝玛丽是一个学生,其父是伦敦公共汽车场的一名管理员,1952年12月6日那天,包括露丝玛丽的父亲在内,大约有500个伦敦人死于雾霾,还有无数人正步行赶往市内各大医院。
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写得非常生动,可以视为出色的“雾霾报告文学”,我们不妨摘录如下:死于这场雾霾的人,有一个共同特征:他们的唇部是蓝色的———严重雾霾让他们的心肺加速衰竭,悬浮颗粒和二氧化硫等酸性污染物导致大量炎症,这带来致命一击。实际上,他们死于窒息。
起初,没人知道这场雾霾会夺走如此多的生命,因为很多人死在家中和医院,而不是街头。不过,有大量人员死亡的迹象开始出现:伦敦的棺材和鲜花被抢购一空。
直至五天后的12月9日,一场毫无征兆、突如其来的冷风,吹走了雾霾,这场灾难才算按下暂停键。克里布做了60年殡葬生意,他说自己一生只有两次中止生意。
一次是1952年这场雾霾,12月5日到9日,短短几天,超过4000个伦敦人直接死于这场雾霾,而根据60年后的最新研究和统计,这场雾霾的死难者,不是4000人,而是至少12000人;另一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40年9月到1941年5月,纳粹德国对英国发动闪电战,空袭伦敦共造成超过30000人死亡。
成千上万伦敦人的生命,换来了四年后,1956年英国议会出台《清洁空气法》,最为重要的举措是:告别工业化时代的粗放与无序,开始严控严管煤炭等能源的使用,从根源上减少雾霾的产生。
人们常说,要以史为鉴。而现实表明,人类会不止一次跨入灾难的同一条河流。
如果我们同意上面这段文字是“雾霾报告文学”的话,那么,就无法不承认如下事实:雾霾可以成为审美现象。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这篇文章最后附了一组1952年伦敦“杀人之雾”的灾难照片。这些六十多年前拍摄的老照片,由于时代的久远而与现实生活拉开了一定的距离,也就是布洛所说的“心理距离”;照片中的景象,包括雾霾、雾霾笼罩下的建筑、行人,等等,都因为“心理距离”的“转换”功能而成为今天的“审美对象”。人们在欣赏这些老照片时,所获得的情感体验是悲痛、怜悯、哀伤等“否定性”情感,否定性情感所否定的是审美对象的原型,也就是当时残害上万人生命的雾霾。
三、作为审美现象的“APEC蓝”
上述论证表明,我们当前经常遭遇的雾霾天气也可以成为审美对象;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人们基本上都已经认识到雾霾的严重危害,避之唯恐不及,很难带着审美态度来对雾霾进行审美欣赏,所以,难以从心理上将雾霾与审美现象联系起来。
然而,颇具辩证意味的是,正因为人们普遍厌恶、憎恨雾霾天气,对于蓝天的渴望与欣赏才空前增强;饱受“霾伏”之苦的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渴望蓝天。所以,每当霾过天晴的时候,拍摄蓝天的照片就会大量涌现:蓝天已经成为我国人民最珍惜的审美对象。这集中体现为一个新的词语“APEC蓝”,该词的网络释义如下:在2014年北京APEC会议期间,京津冀实施道路限行和污染企业停工等措施,来保证空气质量达到良好水平。2014年11月3日上午8点,北京市城六区PM2.5浓度为每立方米37微克,接近一级优水平。网友形容此时天空的蓝色为“APEC蓝”。
APEC蓝,也是2014年新的网络词汇,形容2014年APEC会议期间北京蓝蓝的天空,引申义为形容事物短暂易逝,不真实的美好。当然APEC蓝也是中国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APEC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英文的第一个字母的缩写,2014年11月10日至11日APEC峰会在北京召开。
2014年11月10日,国家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在北京为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各经济体领导人及配偶举行欢迎晚宴。***主席在晚宴前致辞中明确讲道:“我希望并相信通过不懈的努力,APEC蓝能够保持下去。
谢谢,我们正在全力进行污染治理,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我希望北京乃至全中国都能够蓝天常在,青山常在,绿水常在,让孩子们都生活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之中,这也是中国梦中很重要的内容。”可见,“APEC蓝”不仅仅是一般网络词语,也成为我国最高领导人的用语。
我们这里关心的是“APEC蓝”出现的原因:它到底在自然现象,还是人工现象?因为这个问题涉及“APEC蓝”这种审美现象的哲学根据。新华网2014年11月13日发表的一篇题为《“APEC蓝”能留下吗?》的文章中,首先引用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主任张大伟对于“APEC蓝”成因的解释:“老百姓说,过去要赶走雾霾,就得靠大风吹。但这次风没来,依靠北京、河北等五省一市大范围的提前、紧急减排,同样留住了蓝天。”
这表明:“APEC蓝”不是一般的“自然现象”,某种程度上已经是一种“人工现象”,用哲学的术语来表达就是“自然的人化”。
国内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实践美学”在解释“美的基础”(或“美与审美的秘密”)时,依据的主要理论根据是一个着名的命题:“自然的人化”。“自然人化”甚至成为李泽厚参与主编的《美学百科全书》的一个词条,足见其影响范围之广泛。这个条目指出,“自然人化”的“要义”是:人类通过漫长历史的社会生产实践,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为人所控制、征服、改造、利用,人的目的在自然中得到实现。
这个词条还总结提出,“自然人化”思想“确乎从最深层次上揭示了美和审美的秘密”,足见这个概念对于美学(特别是实践美学)来说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
其实,从美学史上来看,较早论述“自然人化”思想的是17世纪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Locke)。洛克在1690年出版的《二论政府》中指出,没有被文化影响的、没有被人化的自然,不如“被文化影响的、被人化的自然更有价值”,“完全遗弃给自然的土地,没有被放牧、耕作或种植改良过的土地,被称为荒地(它的确就是这样);我们从中发现的益处几乎等于零”。
但是,这种观念随后就发生了改变,19世纪以来主要在美国兴起的荒野保护运动与荒野审美思想,就在很大程度上走向了洛克思想的反面。特别是伴随着全球范围内环境运动而兴起的环境美学,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然全美”(或“自然全好”)的理论命题。这一命题首先由加拿大美学家艾伦·卡尔森在1984年发表的论文《自然与肯定美学》中提出,后来收入其代表作《美学与环境》,成为该书的第六章。卡尔森开门见山地写道:本章将考察如下一种观念:所有自然世界都是美的。根据这种观念,自然环境只要未经人类改变,它就主要具有肯定性审美特性(pos-itiveaestheticproperties),比如,它是优雅的、精美的、强烈的、统一的和有序的,而不是乏味的、呆滞的、无趣的、凌乱的和无序的。简言之,所有处于原始状态的自然根本上、审美上是好的。
对于自然世界的恰当或正确的审美欣赏基本上是肯定的(positive),各种否定的审美判断(negativeaestheticjudgments)很少或没有位置。要准确理解这段话,关键是要准确把握positive这个英文词语。positive的意思是“肯定的”“正面的”“积极的”,其反义词negative的意思则是“否定的”“负面的”“消极的”。全文的核心意思是:凡是没有被人类触及过、改造过、污染过的自然环境,即卡尔森所言的“所有处于原始状态的自然”,“根本上、审美上是好的”。因此,这句话也可以简单地概括为“自然全好”,也就是说,只能对它进行“肯定性审美判断”。
卡尔森的美学理论可以用“自然全好”来概括。这种美学观念的本义不易领会,初看起来有些让人难以理解和接受,国内不少学者对此疑虑重重,我们不妨进行更多的解释。卡尔森在论述环境美学的时候,经常对比艺术欣赏与自然欣赏的异同,所以,我们不妨来对比一下与自然审美判断不同的艺术审美判断。人类创造的艺术品数不胜数,优秀的艺术杰作固然不胜枚举,但客观地说,质量低下的作品数量则更多,比如,我们可以说唐诗宋词达到了中国古典诗词的高峰,但是,翻阅《全唐诗》《全宋词》会发现,缺乏艺术价值的作品比比皆是;对于那些优秀的艺术作品,我们的审美判断当然是“肯定的审美判断”,比如说“《红楼梦》实在太伟大了”;但是,对于那些粗制滥造的艺术作品,我们的评价和判断则是“否定的”,比如我们可以做出如下审美判断:“我国每年产生的长篇小说多达千部,但大部分作品艺术水平很低。”这表明,我们在评价艺术品时可以做出“否定的审美判断”。但是,卡尔森坚持,对于自然世界,我们只有在做出“肯定的审美判断”时,我们的审美欣赏才是“恰当的或正确的”;做出“否定的审美判断”则是不当的或错误的,这就是“自然全好”这个美学命题的真正含义。
简言之,如果说实践美学所认定的“美和审美的秘密”在于“自然的人化”的话,那么,当代环境美学特别是生态美学所认定的“美和审美的秘密”就是“自然的人化”的对立面———“自然的自然化”。
笔者在此郑重提出:“自然的自然化”是生态美学的核心命题。
四、“文弊”与“自然的自然化”命题
“APEC蓝”的出现表明了至少有两种意义上的“自然的人化”:第一,本来洁净、碧蓝的天空被人类排放的各种污染物污染,导致严重的雾霾天气,这是一种“从自然到人为”的人化过程;第二,通过各种人工措施,艰难地将雾霾天气这种高度人化的天气状况尽可能地恢复到正常天气的自然状态,这是一种“复得返自然”的人化。所以,从逻辑思维的角度来看,“APEC蓝”这种审美现象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悖论面前:天气本来就是自然现象,但是由于过度人化而威胁着人类的健康生存,所以,必须通过人为的方式将之重新自然化,即“自然的自然化”。这一简单的事实告诉我们,在今天这个雾霾天气频发的环境危机时代,“自然的人化”不是“美的基础”,而是“丑的根源”,真正的“美的根源”在于“自然的自然化”:“复得返自然”。
客观地说,“APEC蓝”出现时,空气的质量也只不过是“良好水平”。这无疑是个比较级,对比的是雾霾笼罩时的空气质量。如果我们放宽一下时间尺度,把对比的参照改换成工业革命发生以前的前现代时期,比如上面所提到的洛克的时代,那么,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那时候的空气质量绝不仅仅是“良好水平”,那时的天空比“APEC蓝”要蓝很多。
前现代时期尽管也有数不胜数的文艺作品描绘到蓝天,如王勃《滕王阁序》中的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但是,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蓝天作为审美对象所激发的情感体验则有着本质差别:当今的蓝天体验是以雾霾为参照的,是以环境危机意识作为思想背景的,简言之,是一种带着对生态危机进行反思与批判的“生态审美”;而前现代的蓝天体验则是一种一般意义上的自然审美,而不是笔者一直倡导的“生态审美”。换言之,“生态审美”之所以必要,“自然全好”这个命题之所以成立,关键在于当下严峻的环境污染和环境危机。
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来思考环境污染问题,我们应该将这种负面的“人化”现象称为“文弊”。当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我们有必要从哲学高度对文化进行反思和批判———反思文化的创造原理,批判已有文化成果的利弊得失。在笔者看来,“文化”是一个与“自然”相对的概念:凡是由人类创造的、超越自然的东西都是文化产品,它包括器物、制度和精神三个层面。人类的所有文化创造都是以自然为基础的,都必须从自然之中获取能量和资源。所谓的“自然的人化”,无非就是将自然改造为符合人类需要的形态。因此,人类的文化创造过程,的确就是“自然的人化”的过程。彻底否定“自然的人化”,就无异于完全否定了人类文化创造。因此,“自然的人化”这个命题无疑有着极大的合理性。
但是,纵观人类文化史特别是20世纪的文化历程,我们就会发现,文化生产往往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导致一种奇异的“文化悖论”。这里特别值得辨析的是经常与文化混淆的另外一个概念“文明”。
笔者一直认为,人类超越动物而成为人,关键在于人类有着超越动物本能的价值观———动物只按照本能活动,而人类的所有活动都是在特定价值观的制约、指导或引导下进行的。也就是说,动物只就其本能的“本然”讲“实然”,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能就“应该”讲“应然”。因此,笔者一般将符合特定价值观的文化产品称为“文明”,而将不符合特定价值观的文化产品称为“文弊”。所谓的“文化悖论”就是指“文明”与“文弊”在文化整体之中既并存又相悖的奇异现象。这种文化哲学思路可以简化为如下一个理论模型:自然—文化→价值观文明(正面价值)文弊(负面价值)根据这个理论模型,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环境污染是当今之世最大的“文弊”。我们之所以强调“当今之世”,是为了突出人们判断“文明”与“文弊”的标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变化的。
比如说,当新中国成立初期刚刚开始进行现代化建设时,车间里轰鸣的机器声往往被赞颂为美妙的音乐与歌曲,高烟囱上翻滚的浓烟甚至被赞颂为美丽的黑牡丹,简言之,这些都是现代化与“文明”的象征。但是,随着环境危机的日益严峻,我们又会将轰鸣的机器声视为噪音污染,将烟囱冒出的浓烟称为空气污染,简言之,不再将其视为“文明”,而是视为“文弊”。因为今天的价值观不再是现代工业文明的价值观,而是生态文明时代的生态价值观。
正是因为人类的价值观已经演化为生态价值观,我们才发现“自然的人化”这个命题并不总是正确的,因为它只强调对自然进行“人化”,而忽视了如下三个重要问题:其一,为何人化?其二,如何人化?其三,人化的限度是什么?我们可以从生态价值观的角度来回答这三个问题,答案如下:其一,为了创造生态文明;其二,人化自然的原理从哲学层面上讲就是“赞天地之化育”,从科学与技术的层面讲就是遵照恢复生态学原理,这主要适用于那些已经被人类损毁的自然界;其三,人化的限度是自然的可承受能力。因此,在生态文明时代,我们必须从生态价值观的角度反思和批判传统的“自然的人化”命题,从生态伦理学与恢复生态学的角度倡导“自然的自然化”,也就是倡导党的十八大报告所提出的“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作为文明的创造主体,从伦理态度上应该尊重自然,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应该顺应自然,从行为方式上应该保护自然。
“审美”(而不是“美”)是美学理论的内核,因此,“生态审美”就是生态美学的内核与研究对象。
从思想主题的角度来说,生态美学就是对于人类“文弊”的美学反思,就是对于“自然的自然化”这个理论命题的弘扬。正是因为“文弊”的大量存在并日益严峻,我们才从生态价值观的高度倡导“自然全好”(亦即“自然全美”)这样的美学命题。没有受到人类改造、污染处于原初状态的自然,比如纯粹的“蓝天”“绿地”“清水”,从审美上来看都具有肯定性审美价值,都是“美的”“好的”,因为这些自然事物最纯粹、最彻底地摆脱了“文弊”。
中国当代自然美学基于“自然的人化”观念,认为自然事物“美不自美,因人而彰”。笔者的生态美学与此完全不同。笔者认为,自然事物自身就是美的、好的,正所谓“美者自美”。人作为自然事物的欣赏者而不是改造者(更不是占有者、掠夺者),其作用主要在于展示自然本来就具有的魅力,让自然事物自身如其本然地显现出来,正所谓“因人而显”。生态文明时代的审美必然也必须是“生态审美”,研究生态审美的美学,应该是一种以“生生”之宇宙力量作为本体论、以“生生之德”作为价值观的美学,也就是“生生美学”。只有这样,人类文明才可能避免灭绝而得以生生不息。我国所倡导的“美丽中国”建设有着明确的审美目标———“天蓝、地绿、水净”,这也正是生态美学所应该努力的方向。简而言之,生态美学(也就是笔者倡导的生生美学)的核心命题是“自然的自然化”,其理论要义可以概括如下:美者自美,因人而显,生态审美,生生不息。
五、结语
在漫长的自然史和悠久的人类文明史上,天气本来只是一种自然现象。但是,随着人类对于自然无限度地“控制、征服、改造、利用”,原本是自然现象的天气变成了雾霾这种高度“人化”的天气。而要想重新回到自然天气状态,又需要人类付出更多、更艰难的努力来“人化”。坚持“自然人化”观的实践美学提出,通过“自然人化”,“人的目的在自然中得到实现”。面对日益严重的雾霾天气———这种高度的“自然人化”现象,我们不禁要问:什么样的“人”的目的得到了实现?人的什么样的“目的”得到了实现?答案很可能就是:通过掠夺自然资源而暴富的少数人的目的得到了实现,被实现的目的是攫取丰裕的物质财富。
但是,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冷酷现实却是:无论是什么人,无论拥有多少财富,只要身处天地之间,就无法从根本上逃避雾霾天气的伤害。呼吸一口洁净的空气,欣赏一下洁净的蓝天,饮用一口无毒无害的清水,竟然成了当前现实生活中的极大奢望,这不是对于人类“文弊”的最大嘲讽和严厉批判吗?!我们从美学理论特别是生态美学的角度思考雾霾天气,正是出于对人类“文明悖论”的高度关切。这种美学思考将激发我们高度关注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生态文明,从生态审美的角度推进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