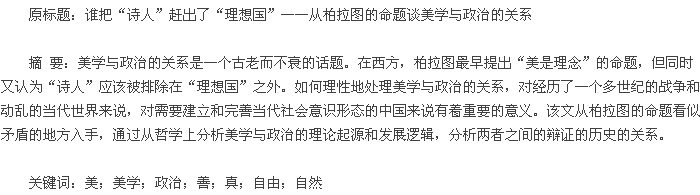
最高的理式是真善美的统一。
——柏拉图[1]
诗比历史更真实、更普遍。
——亚里士多德《诗学》
一、“诗人”与“理想国”——并不矛盾的命题
柏拉图认为“美是理念”,而“理想国”又是按照“理念”建立的理想的王国,而诗人和艺术家应该被排除在“理想国”之外。有人以此来判断柏拉图高扬美,却反对艺术,其实不然。
在这个看似矛盾的命题背后,我们不妨分析柏拉图生活的那个年代的背景。就像生活在春秋“礼崩乐坏”时期的孔子一样,柏拉图生活在奴隶制的希腊城邦,当时的自由民主精神和民主势力萌芽,作为一个雅典贵族阶级,自然看不惯民主政权统制下的迎合大众的文艺活动,认为其“低级趣味” 、“伤风败俗”。
事实上柏拉图的“灵感说”已证实他并不是排斥艺术,只是轻视技艺训练而强调天才和灵感。他认为“艺术是说谎” ,强调艺术创作要间接叙述而反对直接叙述,提出严苛的艺术的审查制度,这一切都是为了让艺术起到陶冶人美好的心灵、培养人高尚的道德情操,让艺术符合城邦的利益。
可见柏拉图把美和艺术,与政治伦理教化结合得非常紧密。而这对几千年后今天的中国建立和完善社会意识形态来说,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不能否定政治对美学的影响,同时也不能取消美学的独立性,应该怎样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下面将步步展开论述。
二、乱世与治世的辩证法——美学与政治的关系的历史发展模型
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美学作为一门以艺术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哲学,与政治有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大致有着这样奇妙的现象:
每逢战争祸乱的时代,旧的政治意识形态便抑制美学思想的创新发展,人们为了推翻旧的政治体制建立新的社会而建立新的美学思想,此时的美学在旧的和新的政治之间被拉扯,但总是离不开政治,与政治结合密切,显示出为政治服务的功利性。比如在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尽管战争使中国的古老的文化牢笼被打破,五光十色的文化随着八国联军排山倒海地进来,使文化界形成截然不同的各门各派,但知识分子的话题或者说占主要地位、最有影响力的话题,始终围绕着“救国”的主题。
而当政治局面稳定,社会正处于建设中甚至社会政治文化已渐趋成熟时,政治往往鼓励美学往多元化的方向开放式地发展,这时政治环境宽松开放,美学与政治之间就没有束缚和被束缚的关系。
比如在封建社会历史上版图不是最大、经济也不是最繁荣的盛唐,由于其政治稳定,社会文化呈开放式吸纳,形成封建史上空前绝后的儒道佛三家并重的文化多元化现象,此时的美学、尤其是诗歌美学更是发展迅速。又比如改革开放后的中国。
美学与政治的关系的历史发展模型体现着某种乱世与治世的辩证法,让人不得不深思其中千丝万缕的逻辑。
三、美学与政治关系的共通性
因此,有必要透过种种历史的现象,在哲学起源的角度上分析美学和政治的逻辑起点,在理论上模拟其发展相似的二律背反性;并且通过分析其异他的本质特征来分析两者的互斥性,大胆假设一个两者关系的理想模型。
(一)哲学起源与逻辑起点
人类在最初产生意识的时候,由于生存条件恶劣,生存的本能功利让人分辩出自我和对象(生存和生存的条件),这就产生了对象意识和自我意识。后来随着生存实践的发展,对象性的表象上升为“概念” ,对象性的功利欲望上升为合目的的自觉意志,对象性的生物情绪上升为情感,这就形成了后来人所说的“知”、“意”、“情” 。由此,人通过劳动实践,通过智慧和理性经验的积累,对对象的认识形成一种超经验的直观的概念性和规律性的智慧,也就是随着实践主体性的发展,产生了精神主体性,如果说实践主体性是“善”、是有目的、有意志等特性,那么精神主体性是它向对象方面发展的成果,比实践主体性更高一层。这是人通过实践,主体性向对象方面的发展,而向人自身发展,就产生了审美主体性。从历史我们可以得知,人对自我的认识、人的“自觉”的诞生明显比实践主体性、精神主体性要慢。
后两者几乎与人的意识同时期诞生。而人类到了文明社会,如古希腊时期,才提出“人,认识你自己”的命题。人类自我认识和自我独立的愿望,如果最初只是一种生物性的情绪,那么要到了它转变成一种情感时才成为一种自觉。美国着名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人的需要层次理论”虽然有对人性过度乐观估计之嫌,但仍为大部分学者所接受。他认为,人只有其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先被满足了,他才会考虑其他需要。而其他需要按应该先后满足的顺序排列分别为:社交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4]也就是人希望和他人(同类生命体)交流、希望自我得到认同、自我的价值得以实现的需要。人的自我意识比对象意识要“觉醒”得晚,这是人的认识和实践的一个正常顺序,人类必须要通过欲望的实践来积累经验,形成智慧,最后才满足自己的感情需要。而人最高层次的主体性——审美主体性,也只能在人的自我意识觉醒了之后才有条件诞生。简单来说,这就是“ 善”、“真”、“美”三个范畴的哲学起源。政治和美学原则意义上都是一种知识,它们最早并不“分家”,应该都属于人类求“真”知所得的结果,只是可以看作一门是关于社会实践的知识,另一门是关于审美的知识。
(二)理想与现实的二律背反
事物是按照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规律来发展自身的,政治和美学也不例外。分析美学与政治其自我否定的内部结构,会发现两者有着惊人的相似。
1. 秩序事实上,政治和美学的诞生都起源于人类对“秩序”的追求。
在远古时代,人类生产力还很落后的时候,人类实践和认识最初始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认识大自然。姑且不论“可知论”和“不可知论”孰胜孰负,在人类对大自然有了初始的认识时,这种认识是零碎的、混乱的、混沌的,只有把认识的结果明确化、条理化、清晰化,知识才得以建立,这种“明确”就是一种“秩序”。在中国古代的神话中,“盘古开天”之前,在《圣经》里,上帝“创世纪”之前,世界都是混沌一片的,人类原初时头脑中认识到的大自然也就是这样的。而这给予了世界“秩序”的盘古神和上帝,其实就是人类的先知。他们不是真的给予了世界“秩序”,而是给予了自身对世界的认识、对世界的“表象”一种秩序。这是知识产生的原初含义所决定的。
而人们凭借着对自然的“秩序”的认识,模仿这种“秩序” 建立自身的社会生活,这就有了文明,也就是所谓的“第二自然” 。正如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政治实际上就是人们把“秩序”用于建立群体社会生活的制度,使之人人遵守,以利于群体里各个个体的生存。而美学实际上就是把“秩序”用于建立人们心灵情感的规范,使之合乎人的伦常道德。可以说,政治的目的是“善”,而美学,不管它有意无意,它最终的旨归都是“善” ,而对秩序的追求,目的就是建立一种“善”的规范。
2. 自由及其对秩序的反抗。
然而,对秩序的追求只是对政治和美学的基本要求,是政治和美学在现实中能够达到的目标。事物的发展往往带着“自否定”的方向。那些最伟大的政治家绝不是只希望建立一种可行的国家社会制度而已,而是往往梦想着推翻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而不管政治家们的“乌托邦”被描绘得多么的不同,其中绝对少不了“自由”这道最明亮的色彩。
这就产生了一个悖论:政治就是为了实现每个人获得真正的“自由”这一理想,而行建立稳固的“秩序”这一现实措施,但“秩序”就其本义来讲,必然是限制“自由”的。两者构成“压制-反抗”的张力,政治就总是和“斗争”、“革命”、“战争”等联系在一起。
对美学来说,建立一种心灵的秩序,让美陶冶人的心灵达到“至善”固然重要,但人毕竟不是圣贤,人性中必然有着自私而不是利他的“恶”的部分,人和人之间必定存在着“恶”的因素,建立在群体利益的意义上的“善”就只能是一种美学的理想。
而现实的美学则往往更加重视对人个体生命的关照,如个体感情的表达和宣泄,甚至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这些就是上述马斯洛的“人的需要层次理论”的最后几个需要,也就是一种心灵的自由,与政治理想的肉体的自由区别而言。而现实中,不是每个个体生命对群体利益的“善”来说都有价值,而且往往实现了甲的心灵的自由就会让乙陷入心灵的痛苦中,最简单的例子是“爱不得”。人和人之间无论是现实利益冲突,还是情感自由冲突,都是必然存在的。这也产生了一个类似政治的悖论:美学就是为了实现人的心灵的自由和幸福,而建立一种最美好的心灵感情的规范,从而人心灵的“恶之花”
就无法自由地盛开,甚至正常的感情自由表达也受到束缚,自由在何处?在中西的美学史上,都不鲜见“秩序”和“自由”的互相斗争,如儒道之争,“格调说”和“性灵说”之争,如西方的古典和浪漫之争。美学史也就在这样的论争中发展前进,就像政治在一次又一次的战争后走向文明。因此,二者都存在着相似的二律背反的结构。
四、结语
美学不等同于政治,美作为一个哲学范畴,有其异于政治的本质特征。美植根于规律又超越规律的无概念性、无法脱离“善”的道德伦理的束缚又独立于功利之外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在康德那里已经阐述得很详细,既证明了上述的二律背反,又表现出与政治的本质的不同。这是本文论述的前提。
美学不可能脱离政治,但也必然独立于政治之外,美学的发展得益于政治才不至于失去应有的“善”的秩序的控制,这是美学与政治的必然如此同时也是应该如此的关系。
参考文献
[1]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64,61, 42-43.
[2]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55.
[3] 孙绍振,毛丹武.审美与政治[J].江苏社会科学·文艺理论研究,1999:56.
[4] (美)马斯洛(Maslow A.H).自我实现的人[M].北京:三联书店,19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