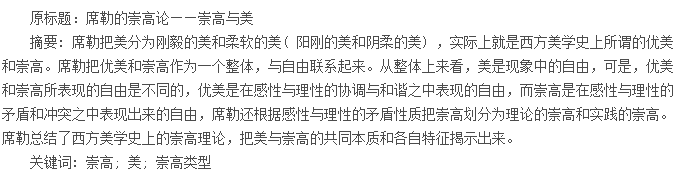
席勒论述崇高的专文有两篇,第一篇是他于1793年写的《论崇高———对康德某些思想的进一步发挥》(“VomErhabe-nen”),大约于1793—1795年间又写了另一篇《论崇高》(“berdasErhabene”)的专论。二者译成中文都是《论崇高》,但是在德文中以不同的介词标明细微的区别,所以我们把前者简称为《论崇高(Ⅰ)》,后者就简称为《论崇高(Ⅱ)》。席勒还有几篇文章比较多地论述到崇高,这就是《关于各种审美对象的断想》(1793年)、《秀美与尊严》(1793年)、《论激情》(1793年),此外,在《审美教育书简》(1795年)和《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1794—1796年)中也论述过崇高问题。席勒的崇高论是他的人性美学思想体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崇高和美的关系,实际上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崇高作为“广义的美”的一种,与另一种“狭义的美”(优美)具有共同的本质;另一方面,崇高作为与优美(狭义的美)相对立的“美”,具有自己的特征。席勒把优美与崇高的共同本质规定为“现象中的自由”,而把优美(狭义的美)规定为“柔软的美”或者“平静的美”,把崇高规定为“刚毅的美”或者“激荡的美”。在《秀美与尊严》一文中,他把这二者又称为“秀美与尊严”。实际上,二者就是西方美学史上的优美和崇高,也相当于中国美学思想史上的“阴柔之美”和“阳刚之美”。席勒主要在《论崇高———对康德某些思想的进一步发挥》中对崇高进行了概念和理论上的分析和论述。
一、崇高的本质
席勒把美分为刚毅的美和柔软的美(阳刚的美和阴柔的美),实际上就是西方美学史上所谓的优美和崇高。他像康德一样,分析和论述了优美和崇高的共同本质,同时也辨析和阐释了优美和崇高的区别,指明了崇高的特征和类型。
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第16封信中把美分为柔软的美和刚毅的美两种。他指出:“理想美,虽然是不可分割的,单纯的,但是在不同的关系中显示出柔软的特性和刚毅的特性,而在经验中就有柔软的美和刚毅的美。”
席勒把优美和崇高作为一个整体,与自由联系起来。从整体上来看,美是现象中的自由,可是,优美和崇高所表现的自由是不同的,优美是在感性与理性的协调与和谐之中表现的自由,而崇高是在感性与理性的矛盾和冲突之中表现出来的自由,席勒认为,崇高的对象与优美的对象一样要显现人的自由;面对崇高的对象时,我们的感性本性与理性本性是不协调的,显示出矛盾和斗争的;对象的崇高性质是在客体与主体两种本性的不同关系中显示出来的。他在《论崇高(Ⅰ)》中写道,“在有客体的表象时,我们的感性本性感觉到自己的限制,而理性本性却感觉到自己的优越,感觉到自己摆脱任何限制的自由,这时我们把客体叫做崇高的;因此,在这个客体面前,我们在身体方面处在不利的情况下,但是在道德方面,即通过理念,我们高过它”。为了更好地理解崇高的本质,席勒把崇高与美(狭义的美,即优美)作了比较:美是自由的表现,不过不是使我们高过强大自然和从一切物质的影响中解放出来的那种自由的表现,而是我们作为人在自然本身中充分享受到的自由的表现。我们在美的领域中感到自己是自由的,因为感性冲动适应于理性法则;我们面对崇高感到自己是自由的,因为感性冲动对理性的立法不起作用,在这里精神这样起作用,好像它不服从除开自己本身的法则以外的其它法则(《论崇高(Ⅱ)》)。
席勒这样把自由作为美和崇高的共同本质,在西方美学史上是在康德的基础上的前进。众所周知,在康德以前,从古罗马的郎加纳斯到英国启蒙主义美学家博克都把优美和崇高看作是完全对立的。特别是博克,他认为美(优美)与人的社交本能相联系,是爱的表现,而崇高与人的自我保存本能相联系,是恐惧的表现,二者判然有别,而且在外在显现形态上是对立的,比如,美(优美)是细小的、光滑的、变化而不露棱角的、明亮的,而崇高则是巨大的、粗犷的、直棱固定的、晦暗的。康德虽然认为美(优美)和崇高都包含在审美判断力的范围之内,似乎具有共同的本质,也就是说,崇高的审美判断同样是无功利性的令人愉快的、无概念的必然令人愉快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无概念的普遍令人愉快的,可是他主要仍然是强调二者的根本区别,也就是说,美是有形式的而崇高则是无形式的、美是知性和想象力的和谐而崇高则是知性和想象力的矛盾冲突、美产生积极的愉快而崇高则产生消极的愉快或者崇高的快感是由痛感或压抑感转化而来的;因此,崇高的理论只应成为对自然界的合目的性的审美判断的一个附录。然而在席勒这里,优美和崇高达到了一种本质上的统一,它们都是“现象中的自由”,都是人性自由本质的现象表现或者感性显现。这种美和崇高的本质上的统一,应该是西方美学史上的一个新的进展,而且也是把美学范畴真正从本质上联成一个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的范畴体系的重要一步,对谢林和黑格尔的美学范畴体系的形成具有直接的启发意义。而且,席勒所谓的自由,是一种理性的“自我规定性”,不过是人的理性法则,也就是精神的最高法则,亦即精神的自规定和自律,因此,席勒的崇高论和美学范畴论的客观唯心主义性质也就制约了谢林和黑格尔的崇高论和美学范畴论发展的客观唯心义性质。同时,席勒这种把“现象中的自由”(自由的感性显现)当作美和崇高的共同本质的理论观点,实质上就是他继承启蒙主义时代“自由、平等、博爱”精神,要求通过美和崇高(即他在《审美教育书简》中所分析的“柔软的美”和“刚毅的美”)来超越封建专制主义现实的限制,而追求完整人性的自由境界和自由本质的启蒙主义理想。
实际上,席勒的这种把美和崇高的共同本质统一规定为“现象中的自由”或者“自由的感性显现”的理论观点,从根本上来看也是有其合理性的。从根本上来看,美和崇高都具体表现了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它们都是在以物质生产为中心的社会实践中人对现实对象的关系由“自在的关系”转化为“为人的关系”的直接后果。实质上,如果没有这种人对现实对象的关系的转化,对象的自然性质是不可能转化为审美性质的,现实的对象也不可能成为人的审美对象。因此,崇高与美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人类以物质生产为中心的社会实践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使得自然“人化”的结果所形成的对象的感性现象显现的一种价值,即显现人类社会实践的自由的形象的肯定价值,它们都显现出了人对自然的必然性的认识和运用,即实践的“自由”。不过,美所显现的“自由”是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实现了的,人们已经充分享受到的,因而,“美是显现实践自由的形象的肯定价值”,它更多地在经过人类直接加工改造过的自然界中显现出来,比如,春风细雨,杨柳依依;而崇高所显现的“自由”带有严重的人与自然的矛盾、冲突、斗争的痕迹,是现实中尚未实现却在未来必达的,因而,“崇高是显现实践准自由的形象的肯定价值”,它也就更多地在暂时未经人类直接加工改造的自然界中显现出来,比如,大漠落日,崇山峻岭。
因此,席勒认为,我们面对崇高所感到的自由,是由感性(身体方面)的限制(对自然的依赖性)向理性(道德方面)的自由(对自然的独立性)的矛盾斗争的转化过程,是由人的感性本性遭受压抑而激发出来的人的理性本性的优越性。席勒以这种德国古典美学所特有的思辨分析,结合着刚刚兴起的英国经验派的心理分析,也就是大陆理性主义与英国经验主义相结合的方式概括了崇高对象的形式特征。他的两篇《论崇高》的专题论文和《关于各种审美对象的断想》等相关论文,曾经反复指出了这一崇高本质的形式特征:在崇高中理性和感性是不协调的,矛盾的,冲突的,动态的,激荡的。例如,突然横扫天空的暴风,乌云密布和电闪雷鸣,平地矗立的山峰,满头蛇发、瘦骨嶙峋的复仇女神,古希腊悲剧中亲手杀死自己孩子的美狄亚和杀死自己的母亲的俄瑞斯特,激怒的马和疯狂的狗,等等。
面对这些巨大或可怕的对象,它们的力量使我们感到自己的肉体力量是微不足道的,然而我们仍然被迫与这种力量较量,因而我们的精神处于运动和紧张状态,在感觉器官中表现出害怕的明显痕迹,沉思的精神沉陷在自身之中,好像依靠着自己独立自主力量和尊严的崇高意识,保持着人性的自由本质。换句话说,只有当这种由感性本性的压抑而引发出来的理性本质的意识状态占据绝对压倒优势时,我们才可能喜爱这些巨大或可怕的东西,它们才能对我们具有审美价值。由此可见,席勒把主体与客体、主体身上感性与理性之间的矛盾斗争,精神的紧张和感官中明显的害怕痕迹,最终的精神振奋,作为崇高的特性。因此,席勒主要是从人性自由本质中,从人的理性意识中来寻找崇高的根源,这与康德美学是基本一致的;不过,他还认为,“虽然崇高首先是在我们主体心中创造出来的现象,然而必须仍然在客体本身中包含着使我们恰好只这样运用这些客体而不是另一些客体的原因”;“理性和想象力之间的某种确定关系属于前者,被直观的对象对我们审美的大小尺度的关系属于后者”(《关于各种审美对象的断想》)。这样,席勒在崇高论中与在美论中一样,把康德的主观唯心主义美学观点向客观方面挪移了一大步,因而也可以更好地揭示崇高对象的客观基础和审美效果。
二、崇高的特征
席勒大致分析了崇高范畴的基本特征。第一,崇高对象一般都是数量比较巨大、威力比较强大、形式比较粗犷的令人害怕的事物或者丑怪的东西。席勒在《关于各种审美对象的断想》中举例说明了崇高对象的这种感性行驶时的特征。他指出:“突然发生的风暴,使天空和整个景色变得阴沉昏暗,压倒或窒息了其它声音,也突然夺走了我们的一切快感。乌云遮蔽着地平线,震耳欲聋的霹雳在低处炸响,电光闪闪,我们的视觉和听觉都感到痛苦不堪。闪电闪烁只是为了使骇人的黑夜变得更加鲜明;我们看到它怎样闪击,甚至开始害怕它会击中我们。但是我们将会完全确信,在这种交替中与其说我们失败了,不如说我们胜利了,除开那些被恐怖夺走了一切自由判断的人们。我们被我们感觉所反感的风暴的可怕景象所吸引,迷恋于它的某些方面,并且让感觉直观这种景象,虽然这种感觉不能叫做原来意义上的喜悦;但是人们常常更加偏爱这种喜悦。然而,这时自然的这种景象与其说是有害的,不如说是有益的(至少为了从这种自然现象中得到愉快,完全不必想到风暴的实用);与其说是美的,不如说是丑的,因为黑暗作为剥夺光明设法得到的一切表象的东西,无论如何不能使人欢喜;而且由雷声引起的空气突然震动,正如由闪电引起的天空突然闪亮一样,与一切美的必要条件相冲突,一切美都不容忍任何突然的东西和任何强制的东西。再者,这种自然现象与其说使感觉愉快,不如说使感觉痛苦,因为视觉和听觉神经被这种从黑暗到光明,从劈雷的炸响到沉寂的突然交替痛苦地绷紧,然后又被迫突然松弛。但是,尽管风暴是这一切不愉快的原因,它对于不害怕的那些人说来还是一种令人神往的现象。”这是说崇高的对象往往是具有巨大的威力,足以使人感到害怕和痛苦。“还有,如果在一片微笑的绿色草原中间耸起一座荒芜光秃的土丘,遮住了眼前的部分风景,每个人都希望这种破坏整个风景的土堆让开。现在就让土丘在想象中变得越来越高,在它的其余形式方面并不作任何微小的改变,使它在高度和广度之间的关系保持不变。起初,它所引起的不愉快感觉将会增加,因为它体积的增大只会使它变得更加触目和令人不快。但是,如果继续使它高到超过钟楼的两倍,那么对它的不愉快感觉就会不知不觉地消失,让位给完全不同的感觉。当土丘最终达到一眼望不到的高度时,对于我们它就变得比周围整个平原的美更加有价值,而且我们不会愿意用另外一种无论多么美的印象来调换它在我们心中形成的这种印象。现在假如在想象中使这座高山有一面眼看就要倒塌的峭壁,以前的感觉就会与另一种感觉融合起来;恐惧就会与它结合起来,而对象本身只会变得更加令人神往。但是,假定这座倾斜的高山能够被另一座高山支撑住,恐惧就会消逝,而我们的大部分喜悦赞叹也会随之一起消逝。……因此宏伟的东西和可怕的事物在某些情况下本身就是愉快的源泉。”这是说,崇高的对象往往是一些数量巨大的宏伟的对象。“在希腊罗马神话中没有比从地狱里出来追捕罪犯时的复仇女神福利亚或爱伦尼更可怕和更丑的形象了。令人厌恶地扭歪的脸,瘦骨嶙峋的躯体,一群蛇代替头发披在头上,既激怒我们的感觉,又伤害我们的审美趣味。但是当我们在舞台上看到这些怪物如何追捕弑母者俄瑞斯特,怎样挥动着火炬不知疲倦地从一个地方到另—个地方追赶他的时候,看到她们最后使满腔义愤平静下来,消逝在地狱的深渊的时候,我们就会以一种愉快的恐怖注视着这个表象。除了由福利亚体现出来的罪人良心的苦恼,甚至违反义务的行为,他真正的犯罪行为也能在表现中使我们欢喜。古希腊悲剧的美狄亚,杀死丈夫的克丽特姆涅斯特娜,杀死母亲的俄瑞斯特,使我们体验到一种令人战栗的快感。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会发现,对我们冷漠无情的,甚至使我们苦恼和可怕的事物,只要它一接近成为某种庞然大物或令人恐怖的东西,就开始使我们感兴趣。一个极其普通的小人物,只要强烈的激情在最微小的程度上也不提高他的价值,就会使他成为可怕和恐怖的对象;那么,一个平庸的无足轻重的对象,只要我们使它增大到接近超越我们的把握能力,它就成为快感的源泉。一个丑人由于愤怒会变得更丑,但是就在这种激情的爆发中,只要这种激情不是可笑的,而是可怕的,他就可能对我们具有最强烈的吸引力。这种观点甚至也适用于动物。拉犁的牛,套车的马、狗,都是常见的对象;如果我们激起公牛参加战斗,使一匹安静的马激怒,或者我们看见一条疯狗———所有这些动物就会成为审美的对象,我们也开始带着愉快和尊敬的感情观看它们。一切人所共有的对充满激情的事物的爱好,在自然中迫使我们观照痛苦,可怕和恐怖的同情感,在艺术中对我们有那么大的魅力,在剧院中那么吸引我们,使我们那么喜爱对巨大不幸的描写,这一些都证明,除开愉快、善和美之外还存在着快感的第四个源泉。”
这里说的是艺术中的丑怪的东西也有可能成为令人愉快的崇高对象。席勒在其他的相关文章中也举过一些例子,在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第二,崇高是一种从人的感性本性与理性本性的矛盾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动态的美、激荡的美。席勒在《关于各种审美对象的断想》中举例说明了崇高对象的感性外观形式上的巨大数量、强大威力、粗犷形象、丑怪模样以后,就进一步阐明了崇高是如何从感性与理性的矛盾冲突中生成出来而具有动态性、激荡性。他说:到此为止所举的一切例子都与它们引起我们感觉的某种客观的东西互相有共通之处。在这一切中我们得到某种“超越或接近超越我们感觉能力或感性反抗能力”的东西,然而并不使这种超越完全强制这两种能力,也不镇压我们认识或反抗的企图。这里给了我们多样性,我们的直观能力力图使多样性引向统一也就同时被迫达到了自己的极限。在这里有一种力量出现在我们面前,对于这种力量来说我们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然而我们仍然被迫与这种力量较量。二者必居其一:或者这个对象出现在我们的直观能力面前并同时回避我们的直观能力,而且它激起表象的企图并不让希望得到满足;或者这个对象好像敌对地反对我们的存在本身,简直就是在向我们挑战,挑战的结果是使我们担忧。上述一切都使精神处在一种不平静的运动中并使精神紧张。可能上升为庄严的某种严肃,占据着我们的心灵,我们的感觉器官中就表现出害怕的明显痕迹,深思的精神沉陷在自身之中,好像依靠着自己独立自主的力量和尊严的崇高意识。如果要使巨大的和可怕的东西对我们具有审美价值,这种意识就绝对必须占压倒优势。因为在这样的表象面前,精神才感到振奋并且感到高过了自己平常的水平,那么人们就用崇高这个名称来表明它们的特性,尽管对象本身客观上没有任何崇高的东西,因此更恰当地应把它们叫做“有崇高意义的”(erhabened)。也就是说,崇高对象必须在感性形式上令人害怕和痛苦的动荡过程中提升人的精神,使人感到自己的理性的优越感(独立自主的力量和尊严),所以崇高是一种“刚毅的美”,动态的美,激荡的美。
第三,崇高所引起的崇高感是一种混合的情感,是在痛苦的激情中激发起一种自由的快感和道德的愉悦。席勒在《关于各种审美对象的断想》中指出:“没有一定强度的想象,巨大的对象就完全不会成为审美的对象,相反没有一定强度的理性,审美的对象也不会成为崇高的对象。绝对事物的观念(1dee)要求比最高理性能力的一般发展更多的发展,要求观念(理念)的一定丰富,要求人透彻地认识他最高尚的自我。谁的理性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他就永远不会从感性的大小中形成超感性的运用。”
也就是说,崇高是想象力和理性能力得到充分发展的结果,实质上就是崇高对象压制着人的感性本性却激发起人的想象力和理性能力的超感性的运用,因此,崇高感就是感性能力、想象力、理性能力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的混合情感。恰恰是人的理性的“道德主动性”使得对象成为崇高的对象,而同时使人产生崇高感的自由感和愉悦感。“在道德精神中(想象力的)可怕的东西迅速而轻易地变成崇高的东西。根据想象力丧失自己的自由的程度理性表现出自己的自由;而精神在向外部受到限制时,就更加向内部扩展。从能给感性本质找到肉体掩护的防御工事中冲出来,我们将迅速奔向我们道德自由的牢不可破的堡垒,正是由于我们在现象界失去了单纯相对的和不稳定的保护,我们才获得一种绝对的和无限的安全。但是,正是因为在我们从自己的道德本性那儿寻找援救之前,事情必须达到这种肉体的痛苦,所以我们除了用痛苦的代价来获得这种高度的自由感以外,没有其它办法。庸俗的心灵仅仅停留在这种痛苦之中,而且在激情的崇高之中除了可怕的东西,再也感觉不到任何东西;相反,主动的精神恰好从这种痛苦中取得感觉自己最壮美力量作用的中介,并会由任何可怕的东西创造出崇高的东西。”
因此,威力的崇高对象所引起的崇高感同样是感性能力、想象力、理性能力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的结果,也是混合着痛感、自由感、愉悦感的混合情感。后来,在《论崇高(Ⅱ)》中就更加直截了当地说明了崇高感的情感混合性和情感转化性。他说:“崇高感是一种混合的感情。它是表现最高程度恐惧的痛苦,与能够提高到兴奋的愉快的一种组合,尽管它本来不是快感,然而一切快感却更广泛地为敏感的心灵所偏爱。两种对立的感情在一种感情中的这种结合,无可争辩地证明着我们道德的主动性。因为同一个对象绝对不可能与我们有相反的关系,那么由此得出结论,我们自身与对象有两种不同的关系,所以在我们心中对该对象的表象表现出完全相反兴趣的两种对立的本性就必定结合起来。
因此,通过崇高感我们得知,我们精神的状态不一定由我们感觉的状态来决定,自然法则也不一定就是我们的法则,而在我们心中有一种完全不依赖于感性活动的独立自主的原则。”
席勒关于崇高的审美特征的分析和阐述在几篇相关的论文中是反反复复地进行着,应该是阐述得非常充分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席勒的论述实际上是把英国经验主义美学家博克的观点、德国古典美学奠基人康德的观点综合起来了,实质上就是总结了西方美学史上关于崇高论的分析和论述。而且,席勒关于崇高的审美特征的分析和论述是非常详尽、细致和全面的,结合着崇高的主观方面与客观方面、肉体方面与精神方面、感性本性与理性本性,强调了崇高感的混合情感性和情感转化性,也可以说是西方美学史关于崇高的审美特征的集大成,对19世纪以后的崇高论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主导作用三、崇高的类型。
席勒对崇高的类型划分同样是在康德美学的基础上,多方面考虑了崇高的构成要素得出来的,因而也是值得高度注意的。而且,在不同的文章中,席勒的崇高分类的名称也有一些不同的称谓,比如,理论的崇高与实践的崇高,认识的崇高与力量的崇高,直观的崇高与激情的崇高,静穆的崇高与行动的崇高等等。
席勒的崇高类型的划分是根据崇高的感性与理性的矛盾冲突的特性来确定的。他在《关于各种审美对象的断想》中说:“如果一个客体要叫做‘崇高的’,那么它必须与我们的感性能力对立。这又可能主要想到两种不同的关系,事物处在这两种对我们感性的关系之中,与此相应也必须有两种不同的反抗。
它们不是作为我们力图认识的客体来看待,就是作为使我们的力量与之相较量的力量来看待。按照这种区分也就有两种崇高:认识的崇高和力量的崇高。”席勒还进一步说明他所谓的“认识的崇高”也就是康德所谓的“数学的崇高”。“但是现在感性能力所认识的,除了它理解已有的材料和使这些地处在空间和时间中的各种各样的材料彼此靠近以外就什么也没有了。
区分和整理这些各种各样的材料是理智的事情,而不是想象力的事情。对于理智来说只有一种杂多性,对于想象(作为感性)来说仅有一种单一性,因而从感性上理解现象时,能够进行区分的仅仅是许多单一的事物(量,不是质)。因此要使感性的表象能力屈服于一个对象,这个对象就必须在自己的量上超过想象力。所以,认识的崇高是以数量和体积规模为基础的,因而也可以叫做数学的崇高。”
那么,相应的,席勒所谓的“力量的崇高”也就应该是康德所谓的“物理的崇高”。这种划分方法似乎还是根据康德的思路来进行的。
在《秀美与尊严》中,席勒认为“尊严是崇高思想的表现”,因此,似乎可以把尊严与崇高在席勒的崇高论中视为同义术语来对待,于是,席勒把尊严分为高尚(Edel)、威严(Hoheit)、庄严(Majestat)等层次,形成了“尊严→高尚→庄严→崇高”的序列,似乎也可以看作是对崇高的一种分类。
在《论激情》中,席勒从激情的角度提出了静穆的崇高与行动的崇高的概念。他说:“在一切有激情的情况下,感觉必须是由痛苦引起兴趣的,而精神必须是由自由引起兴趣的。如果激情的表现缺乏受苦的自然的描写,那么它就没有美学的力量,而我们的心就始终是冷漠的。如果它缺乏道德禀赋,那么哪怕在具备感性力量的情况下它也不可能是激情的。而我们的感觉不可避免地被激怒。受苦的人永远应该由一切精神的自由显露出来,主动的或者能够达到主动性的精神永远应该由一切人类的痛苦显露出来。”在这里,席勒是从崇高中的感性(肉体)痛苦与理性(精神)自由的矛盾冲突状态来进行分析。这样,“主动的精神在痛苦的状态中按两种方式显示出来。或者,当道德的人不服从肉体的人,而不允许状态有对思想的因果性时,就是消极的;或者,当道德的人给肉体的人提供法则,而思想保持着对状态的因果性时,就是积极的。静穆(Fassung)的崇高来源于前者,行动(Handlung)的崇高来源于后者。”席勒认为,“静穆的崇高可以直观,因为它以共存性为基础;相反,行动的崇高只可以沉思,因为它以连续性为基础,而且为了从自由的决定中推导出痛苦,理智是必需的。因此,只有第一种崇高才适用于造型艺术家,因为这种艺术家只能成功地表现同时存在的东西,而诗人能够详述两者。甚至当造型艺术家表现行动的崇高时,他也必须把它化为静穆的崇高。”
换句话说,静穆的崇高就是一种空间的崇高,行动的崇高则是一种时间的崇高;或者说,静穆的崇高是一种直观的崇高或认识的崇高,而行动的崇高是一种威力的崇高或力量的崇高。
席勒对崇高的分类,最有理论创建性的应该是在《论崇高(Ⅰ)》中所划分的理论的崇高与实践的崇高。席勒在《论崇高(Ⅰ)》中从理性与感性在人类心理中的二元对立出发认为,一切作为感性本质对我们起作用的本能,基本上有两种:第一,我们具有一种改变我们的状态,表现出我们是有积极作用的存在的,或者同样是获得我们的表象的本能,这种本能因此可以叫做表象本能或认识本能。第二,我们具有一种保持我们的状态不变,继续我们的存在的本能,这种本能可以叫做自我保存本能。表象本能趋向于认识,自我保存本能趋向于感情,即趋向于对存在的内在感知。正是通过这两种本能,我们人类处在对自然的双重依赖性之中。当自然缺乏使我们达到认识的条件时,我们感到第一种依赖性;当自然为了使我们成为可能,继续我们的存在而与条件相矛盾时,我们感到第二种依赖性。然而人还有理性,借助于理性,我们就确定我们对自然的双重依赖性,因而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中超越自然条件的界限,这时自然对象就成为理论的崇高和实践的崇高。在理论的崇高中,自然作为认识的客体,处在与表象本能的矛盾之中,在实践的崇高中,自然作为感情的客体,处在与自我保存本能的矛盾之中。席勒把崇高的感性本性归结为表象本能和自我保存本能两种心理要素,从这两种人类感性本性与理性本性的矛盾冲突中归纳出认识的崇高与实践的崇高。这样,席勒的崇高分类就把崇高的类型与不同的两种人类本能联系起来,与英国经验主义美学家博克一样,找出了崇高的心理学根据,对崇高进行了心理学分析。与此同时,席勒的这种分类也沿袭了德国古典美学的奠基人康德的哲学思辨方法,大致对应于康德的数学的崇高和力学的崇高分类。不过,席勒站在更高的平台上,从人类的理论和实践的两大生存领域来划分,因而更加具有概括性和全面性。此外,这样的分类可以更加合乎逻辑地把美和崇高当作从自然王国和认识(理论)领域过渡到自由王国和道德(实践)领域的中介因素,从而也就自然而然地把美学范畴体系与人类的自我生成的历史过程相对应起来,开启了黑格尔把逻辑的和历史的两方面结合起来的思维方法。
对于认识的崇高与实践的崇高,席勒作了进一步分析。他认为,一个对象,如果它随身带着无限性概念,想象力感到自己是不能胜任表现无限性的,因而与表象本能相矛盾,就是理论的崇高。一个对象,如果它随身带着危险性概念,我们肉体的力量感到自己是不可能克服危险性的,因而与自我保存本能相矛盾,就是实践的崇高。风平浪静的海洋是理论的崇高,风暴中的海洋是实践的崇高。因而认识的崇高的对象是一个无限的对象,而实践的崇高的对象是一个危险的对象,可怕的对象。
这样,虽然二者引起人的心理反应都是不愉快的,但认识的崇高不引起人的痛苦,实践的崇高由于关系到人的存在与否,就必然引起人的痛苦。因此,后者比前者所引起的人的自由感和超越感更强烈,因而愉快感也更强烈。席勒的这些分析是符合人类审美经验事实的。
他一再强调崇高引起的自由感是精神的,道德的,非肉体的和技巧性的因而他把伟大与崇高划分开来,同时,又把实践的崇高分为(威力的)观照的崇高和激情的崇高。这种划分的根据是三种相互跟随的表象的作用:(1)一个客体的物理威力,(2)我们主体的肉体的软弱无力,(3)我们主体的道德的优势。
据此,席勒这样来分析观照的崇高:如果一个作为威力的对象,仅仅表现为痛苦的客观原因,却不表现为在直观时的痛苦本身,而且判断的主体在自身中创造出一个痛苦的表象,同时已有的对象,借助于与自我保存本能的关系变成一个可怕的客体,以及借助于与他的道德人格的关系变成一个崇高的客体,这个客体就是观照的崇高的。这时,对象不那么粗暴地抓住精神,因而精神能保持一种静观状态,想象力的活动仅仅是从自然提供的对象创造出一个可怕的东西来。例如,一个显现在我们脚边的深渊,一场暴雨,一座喷火的火山,一块悬垂在我们头上仿佛马上就要坍塌的磐石,一场海上风暴,南北极的严冬,热带的酷暑,凶猛或有毒的野兽、洪水等等,就是观照的崇高对象。他认为,一切异乎寻常的东西,神秘的和难以捉摸的东西,黑暗等都适合于观照的崇高。那么,激情的崇高就应该是这样的:如果除开作为威力的对象以外,它对人的可怕性客观地表现为痛苦本身,而且使判断的主体一点也不留地运用到他的道德状态之中,同时由可怕的东西中创造出崇高来,这种客体就是激情的崇高客体。这时,对象使主体同情地感到痛苦,想象力使他产生痛苦的错觉和虚构,从而使我们情绪激动,又意识到我们内在的道德自由。比如,我们面对别人的悲惨遭遇和痛苦经历时,就是面对着一个激情的崇高对象。
这种崇高分类是席勒美学的独到之处,也是席勒崇高论的特殊贡献。
参考文献:
[1](德)席勒.席勒美学文集[M].张玉能,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