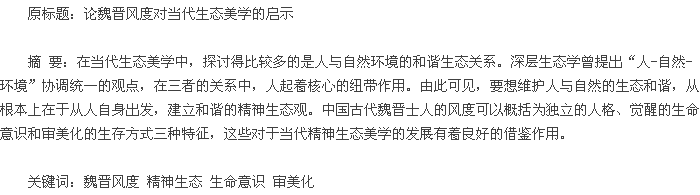
一、精神的独立、人格的自觉
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写到魏晋风度之时,开篇便以“人的主题”为标题,魏晋风度最为耀眼的地方正是在于人的自觉,具体表现在士人们精神上的独立与人格的自觉。 在魏晋之前,受政治-社会-伦理紧密结合的思想风气的影响,人们普遍追求的都是官方所推崇和赞扬的思想与人格,看似光芒万丈的大写的“人”,实则在一定程度上缺少了多和广的灵动与自由。
成复旺先生曾总结:“先秦两汉时期,我们知道很多人的姓名、职业、学说、业绩乃至履历,却不太清楚他们的性格、爱好和日常生活。他们是个体的人,却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个体的人,没有想到在自己的职业、学说、业绩之外,还应该有独立的兴趣、性格,没有想到在公共生活之外,还应有仅仅属于自己的日常生活。 一般人是如此,连诗人也是如此。 例如屈原,他似乎除了忠君爱国关心政治之外什么都没有想过。魏晋以后就不同了, 我们看到许多人都各有自己的秉性、爱好,都在过着自己的与众不同的日常生活,以至于, 我们可能不大知道他们的社会角色和社会活动,却清楚他们的仪容风度、个性特征。就是说,在这个时期我们才看到了许多活生生的、血肉丰满的人。”魏晋之际,儒学的核心地位不断被冲击,封建礼教不断被人所弃置, 对于传统的反叛带来的是个性解放的大潮。 在《体别》篇中,刘劭将人物依其个性特点分为强毅、柔顺、雄悍、惧慎、凌楷、辨博、弘普、猬介、休动、沉静、朴露、韬谲十二类,多种多样的人格品评标准一改以往立人唯求中平正和的单一。 摆脱了精神的束缚,从本心出发,士人们完全有了独立自主的人格发展空间,精神自由的光辉也由此显现出来。魏晋士人,无论是嵇康式的“手挥五弦”的潇洒风流,刘伶“死便埋我”的不拘礼法,阮籍“穷途而哭”的任诞狂放,还是陶潜“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逸缥缈等等都是精神人格多样化的显现。
值得注意的是,魏晋士人人格的多样性并不等同于放纵和轻浮。 在精神自由与人格独立之上,同样有着对于理想人格的追寻,但其追求的已不再是之前的朝廷美学体系所追求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人格,而是在自然的基础上追求内在神韵与气质的超越人格。 关于自然,阮籍承接了庄子关于至人、圣人、神人的定义,在《大人先生传》中描绘了“大人先生”之一摒弃了一切身外之物,高吟着天地虽大,心安自在即是归处的理想人物。
在本性自然之外,内在气质也是理想人格所必不可少的部分。人外有筋骨皮,内有精气神,为人处世中时时刻刻散发出来的是由内而外的精神修养,也即是魏晋士人所追求的“清朗”“神韵”. 只有内外兼修,形神兼备的人格才值得后人所敬仰与崇敬:王戎云:“太尉神姿高砌,如瑶林琼树,自然史风尘外物. ”(《世说新语·赏誉》)王公目太尉:“岩岩清峙,壁立千仞. ”(《世说新语·赏誉》)世目李元礼:“谡谡如松下风. ”(《世说新语·赏誉》)卞令目叔向:“朗朗如百间屋. ”(《世说新语·赏誉》)二、生命意识的觉醒==余秋雨先生在《遥远的绝响》一文中以“这是一个真正的乱世”来形容魏晋。魏晋是中华历史上大动乱、大分裂的时期。 政治黑暗、乱党专政、哀鸿遍野、人命如草芥, 整个社会充斥着阴谋和残忍,“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的现象随处可见。百姓们得过且过,能活一天是一天,灾难随时可能降临到头上;士人们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 权力富贵都如烟云般虚无缥缈,朝为庙堂之高臣,夕已为荒野之新骨。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士子文人们承受着人生无常的痛苦,在心底里用最沉郁的声音吟咏出大量关于生命短促的诗句:
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
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
(《回车驾言迈》)
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
(《青青陵上柏》)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
何不策高足,1.艺理论(《今日良宴会》)
浩浩阴阳移,年岁如朝露.
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
(《驱车上东门》)
在这些诗句中, 溢满了对生命的感慨与悲叹,“在表面看来似乎是如此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叹中,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一个人的生命中是否能闪现美的光彩,决定于是否能执着于生,只有意识到生命的美好,才会珍惜每一天的生活, 努力赋予有限的生命以无限的意义。它实质上标志着一种人的觉醒,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
魏晋士人们生命意识的觉醒首先表现在对于生的价值追求,如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中有:“眼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及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在他的眼中,生的价值因人而异,无论是嵇康在生活中“目送归鸿,手挥五弦。 俯仰自得,游心太玄”的潇洒俊逸之姿,还是曹操对待人生“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的豪迈态度,抑或是百姓们“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的及时行乐的人生观,只要自己的一生过得充实圆满, 在老之将至之时就能回首而无悔。生命的真谛,正在于活出一个“气韵生动”的自我。
其次还表现在对死的淡然态度。 死是生的终点,是任何一个人都无法摆脱的最终结局,《庄子·至乐》中写道:“人之生也,与忧俱生。”而人生中最大的忧愁莫过于生命的消逝。死的凄凉与生的美好相比总是更能引发人情感上的共鸣,由此也产生了独特的诗歌形式---挽歌。 在别的年代中,文人们对于死的态度总大多是消极的、悲痛的:“处处蓬蒿遍,归人掩泪看。 ”(刘长卿《穆陵关北逢人归渔阳》)“路柳夹灵轜。 韄蒠随风征。 车轮结不转。 百驷齐悲鸣。 ”(傅玄《挽歌》)魏晋动乱的社会中,死亡的阴影在人们的心头上笼罩得更深,但魏晋的挽歌大多已经不再仅仅沉寂于悲叹死亡的痛苦之上,在玄学风气的影响下,“缘起性空”“生死有道”等等思想使人们能以一种比较通达的态度对待死亡,在诗歌中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大彻大悟之后的超越态度: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陶渊明《神释》)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陶渊明《挽歌》)魏晋文人的一生之经历, 大多都溢满了坎坷变数, 人世间的得失荣辱在他们眼中是瞬间万变的事情。 大悲之后是淡然,也许可以说,这些文人都是在生死中挣扎过来的智者,人生实难,死又何所惧。“如果我们只热爱生命而不热爱死亡, 那是因为我们并不真正热爱生命。 ”路易-樊尚·托马的话并不是怂恿人们疯狂地去迷恋和追求死亡, 而是教导人们生命本有生死两极, 生如夏花之绚烂, 死如落叶之静美,看淡了死亡,才能在生的过程中活出自我的本色与精彩。
三、审美化的生存方式
嵇康在《释私论》中说:“夫称君子者,心无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 何以言之? 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这里“心无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所提倡的是一种超越于礼教而又谨守内心最基本的道德本分的生存方式,也即是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社会属性始终是人最根本的属性,在人与人的交往中,道德并不是束缚,而是一种最起码的行为准绳,罗梭说“人生而自由,却无所不在枷锁之中”,人若追求脱离规则的自由只能沦为无尽纵望的奴隶。
“不违乎道” 使人有了追求审美化生活的基础,“心不存乎矜尚”“情不系于所欲”则以无功利的态度赋予了生活以美学的色彩。
除此之外,魏晋之士还以多情善感的真实生活为后人打开了一扇通往洋溢着情感音符的伊甸园大门:王长史登茅山,大恸哭曰:“郎邪王伯兴,终当为情死! ”(《世说新语·任诞》)恒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 ”
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 ”(《世说新语·任诞》)“一往有深情”,魏晋士子文人的多情 ,实际上不仅仅止于具体情感的抒发,而是以一颗饱满的情感之心去面对生活,去体会人世间的百味。 也正是因为生命被描绘上情感的色彩,被玄学思想所浸染的生活才能与美学接轨,才有了登高舒啸,才有了采菊东篱,才有了临清流赋诗,才有了闲钓碧溪之上,才有了各种各样顺心恬淡的艺术人生。
魏晋风度虽与我们遥隔着历史的鸿沟,但其自觉的精神人格,其觉醒的生命意识,其溢满了情感的审美化生存方式都给当代出现严重精神生态危机的人们以启示。柏拉图将美定义为一种永恒的存在,这说明美并不仅仅局限于外在的具体事物, 天地万物唯精神之光长存,精神内蕴是支撑起一切形式的美的脊梁柱。朱光潜曾说:“我坚信情感比理智重要,要洗刷人心,并非几句道德佳言所可了事,一定要从‘怡情养性’做起,一定要于饱食暖衣、高官厚禄之外,别有较高尚、较纯洁的追求。要求人心净化,先要求人生美化。”这种对于审美化的人生追求实质上正是对于精神人性之淳美的一种向往,若能还精神生态的空间以一片澄净的天空,则必然亦能推动自然生态向着和谐与美好的方向发展,生态审美的路也将走得更好更远。
参考文献
[1] 王 茜。生态文化的审美之维[M].上 海:上 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
[2] 张 海明 . 玄 妙之境 [M]. 长 春 :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3] 张法。中国美学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
[4] 李泽厚。美的历程[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