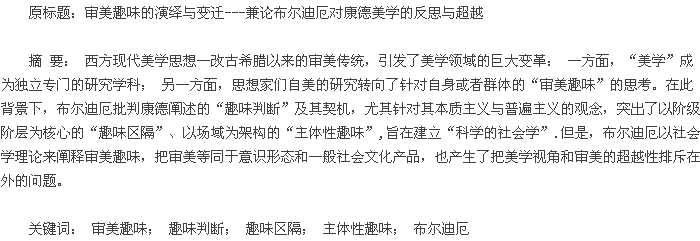
哲学家如何看待“美”? “美”究竟是客观事物本身还是事物的属性,是主体自身还是主体的感知,抑或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 哲学史上围绕美的讨论可谓众说纷纭。古希腊哲学家一般认为美是绝对和永恒的存在,犹如柏拉图所宣扬的永恒的“理式”,这是站在了本体论的立场上;[1]中世纪基督教亦认为美是绝对永恒的存在,不过却是站在生命的先验属性或者“神”的属性的立场上。[2]
但是,在文艺复兴向古典主义过渡的时期,以物理学的新发现为契机,哲学家们认识到“世界”实际上是一个被“主观化”了的存在,“美”是通过内在感官才得以显现,因而就由过去的形而上、客观性走向主观化,自超验性的存在走向感知经验的存在,这一过程具有心理的、意识的特征。
这样一来感受者就会对事物进行美的鉴赏、判断,“审美趣味”就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和美学史上的重要概念。
换言之,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的传统美学思想出现了巨大的转变,引发了审美领域的变革: 一方面,“美学”成为独立专门的研究学科; 另一方面,思想家们自美的研究转向了针对自身或者群体的“审美趣味”的思考。本文即以“审美趣味”这一概念为基础,通过阐述被誉为“德国古典美学开山祖”[3]
康德视野下的“审美趣味”,进而聚焦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针对康德美学的批判和反思,揭示出在这一概念背后所隐藏的美学的时代变迁与布尔迪厄文化社会学的问题意识。
一、何谓“审美趣味”
何谓“趣味”? 根据范玉吉的研究,这一概念古希腊文写为“γευ ~ σιζ”,是指“味觉、味感”; 拉丁文写为“taxare”,则指“敏锐的触觉”.[4]
简言之,自古希腊到文艺复兴,趣味的意义主要是指“味觉、口味、滋味”.现代英语“taste”和法语“go?t”至今仍然保留着“味觉、味道、滋味”的基本语义,而趣味、审美力、鉴赏力等含义则为其引申义。亚里士多德说,“( 感觉所得的) 这些印象,未必一一都是正确的,唯有审辨机能为之榷断了的,才属可信。”[5]
由此可见,较之感觉性的“趣味”,亚里士多德更重视“审辨机能”,且参照其后期提出的“宇宙理性”概念,“审辨机能”大概也带有先验形而上学的性质。或许正是基于此,“趣味”一词最初只是感觉的印象,与主观性的审美鉴赏、审美判断基本无关。
然而,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这一概念却出现了一大转变。文艺复兴之前,神学禁欲主义思想长期禁锢欧洲人,文艺复兴则令欧洲人重新发现自我,肯定人性,开始热衷于展现个性。由此,过去被贬斥的人体感官和感觉得到重新审视,“味觉”虽然还不能与真正意义上的审美鉴赏划上等号,却开始拥有新的含义,包含价值判断的引申义。根据美国学者达布尼·汤森德( Dabney Townsend) 的研究,味觉和审美判断产生关联最早源于 15-16 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皮科·米兰多拉( Pico della Mirartdola,1463-1494) 于1486 年在为诗歌做注之际,运用“优雅”一词对人体之美进行了最初的鉴赏判断。[6]
16 世纪中后期,意大利的风格主义作家费德瑞拷·祖卡洛( Fedrico Zuccaro,1541-1609) 曾指出: “优雅是……一种温柔与甜美的陪伴物,它吸引着目光,包含着品味……; 它完全依赖着好的判断和好的趣味[gusto].”[7]
在此,趣味判断引导品味,好的趣味判断形成优雅的品味,优雅是类似于“温柔与甜美”的东西。至此,趣味不仅与人的触觉、味觉等感官感觉直接联系起来,还成为评判人体之美的关键词。
对趣味一词的引申义的使用和传播,不少学者将之归功于 17 世纪西班牙宗教作家巴尔塔瑟·格拉西安( Balthaser Gracian,1601-1658) 创作的《谨慎艺术的演说教材》( 1'Oraculo manual y artede prudencia) 一书,断言正是格拉西安凭借此书首次将趣味一词引入美学。不过该书只是一部类似于道德说教的书籍,旨在于教导贵族们如何谨慎行事才能举止优雅,提示要做到优雅就必须具备“gusto relevante”,即敏锐的趣味。在此,趣味是指一种精神上的审辨能力,是指在所有事物中分辨好的成分的能力。由此可见,趣味不仅是美学意义上的评判标准,更是衡量其他事物行为好坏的准则,规范着人们的道德风尚。与格拉西安同时代的沙夫兹伯里( 3rd Earl of Shaftesbury,1671-1713) 亦在着作中使用了趣味的引申义,将之等同于天赋、礼貌、礼仪,认为它可以引导人们互相尊重、行为谦让、正派、文雅。由此可以推断,沙夫兹伯里笔下的趣味含义亦在于摈弃野蛮,具有规范道德修养的社会意义。换言之,在 17 世纪到 18 世纪初,趣味在一定的程度上是规范人的言行举止的社会准则,也涉及美的形式判断,但还未真正独立成为美学领域中的价值判断术语。
正因为“趣味”一语本身与主体的感官经验密不可分,因此以哈奇生、霍布斯、洛克、休谟为代表的一批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认为,应该站在经验主义认识论、人性论的基础上来认识审美趣味及其标准。[8]
与之相反,笛卡尔、布瓦洛、莱布尼茨、莱辛等一批法、德理性主义哲学家则极为推崇理性认识的强大作用,指出只有通过理性才能直接可靠地把握事物本质,感觉经验完全靠不住。就这样,针对趣味的审美判断问题,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两大阵营展开长期论争,趣味逐渐成为西方文艺理论与美学的核心议题之一。而且,不少哲学家认识到,美和趣味的问题不是单纯依靠感性经验或理性分析就可以完整解释的,因而试图调和二者的矛盾。但是,只有康德才真正实现了两者的矛盾统一。通过《判断力批判》和《实用人类学》( Anthropologie in pragmatischer Hinsicht) 的着述,康德首先将美从善、真、愉悦之中独立出来,站在统一感性与理性的立场,系统全面地就美和趣味的问题进行了阐述。可以说,正是 18 世纪哲学家们对于美的思考与研究,最终形成了独立学科---美学。
与此同时,在这一学科观念下,“趣味”作为辨识美的内在感官( 第六感官) 的能力,亦成为美学研究的专门术语。
二、康德的“趣味判断”及其契机
作为美学的集大成者之一,康德究竟如何看待“趣味”? 针对趣味,康德曾在《实用人类学》中提到: “美仅仅属于趣味的领域。”[9]
审美的问题就是如何判断趣味的问题,并解释指出: “鉴赏,……是一个器官( 舌、腭和咽喉) 的属性,即在吃喝时受到某些溶解了的物质的特殊刺激。它在自己的应用中要么仅仅被理解为辨别的鉴赏( 口味) ,要么也同时被理解为精鉴赏( 例如,某种东西是甜的还是苦的) ,或者,所品尝的东西( 甜的或者苦的东西) 是否适意。”[10]
该处译者采用的“鉴赏”,实际上就是趣味、口味。不过,不管是辨别的鉴赏还是精鉴赏,鉴赏的德文 geschmacksurteil 内含趣味 geschmack 和判断 urteil,即是作为审美的“趣味判断”.①正如康德所强调的,趣味就是“评判美者的能力。但是,要把一个对象称为美的,这需要什么,必须由对鉴赏判断的分析来揭示”.[12]
不仅如此,康德指出,鉴赏判断,即是趣味的评价能力依据了一种先验的共通感( gemeinsinn) :
一种被想象成适用于所有人的既定规则来判断。康德将这两种趣味( 鉴赏) 定义为“反射性的趣味”( 亦译作“经验性的鉴赏”,gustus reflectens) 和“反思性的趣味”( 亦译作“玄想性的鉴赏”,gustusreflexus) .反思性趣味依据先天性建立的、必然性的规则。先天性建立的规则,不仅会通过一个对象的观念与快感相关联来进行评判,而且理性也隐性地参与评判活动,呈现为一种理性的趣味( vernunftelnden geschmack) .因此,反思性趣味综合了感性与知性,成为康德论述审美的趣味判断的先验普遍有效性理论的基础。而后,“在《实用人类学》的后半部分、包括《判断力批判》中,康德便直接用趣味代替了反思性趣味',趣味原初的味觉感性意义也因此被完全剔除了。”[12]
就这样,经过一番由味觉感官,到辨识客观味道的辨别的鉴赏,到主观发挥作用的鉴赏,再到反射性趣味( 经验性的鉴赏) 与反思性趣味( 玄想性鉴赏) 的精确划分,康德将论述的重点放在了基于感性与知性综合体的反思性趣味( 玄想性鉴赏) ,其简称---“趣味”则成为审美的代名词,审美判断就是“趣味判断”.换言之,趣味( 鉴赏) 作为一种感性的评价能力,既具有主观性、个体性,又被赋予客观性、普遍性和必然性,这就是康德试图融合感性与理性,实现二者对立统一的独特之处。
那么,康德如何来实现审美鉴赏判断的先验原理的建构? 就此而言,康德尤为突出了“趣味判断”的四个契机,以此作为建构的基础。所谓“契机,在德文里有关键的意思”.[13]
康德指出: “为了区分某种东西是不是美的,我们不是通过知性把表象与客体相联系以达成知识,而是通过想象力( 也许与知性相结合) 把表象与主体及其愉快或者不快的情感相联系。”[14]
美的判断不应诉求于客体、不应抽象为逻辑知识; 美的鉴赏是在人的想象力与感知力作用下,人自身的主体感受与客体对象相照映、相作用,而后生发的主体快乐的情感。
具体而言,首先,从质的关键角度来讲,审美趣味具有无功利性。康德认为,只有既是感性又是理性的人才享有审美愉快。人的“鉴赏是通过不带任何兴趣的愉悦或者不悦而对一个对象或者一个表象方式作评判的能力”.[15]因此,康德认为,审美趣味的判断不同于逻辑判断,它在于主体自身的理性,在于自身与对象的关系。不过,关涉欲念、利益兴趣的“快适”和“善”的愉快情绪都是功利的,皆不属于审美的趣味判断范畴。“快适”受制于感性刺激; “善”受制于理性规则,其愉悦之情皆是不自由的。也就是说,惟有主体认识到自身与对象实质上是处于一种无功利性的自由状态,才会构成审美的特殊领域,才能感受到与理性相关的审美愉快。
第二,从量的关键角度来看,审美趣味具有普遍性。康德认为,愉快引起判断,不过是满足官能、欲望的感觉上的快感而已; 判断引起愉快,才使审美具有普遍性。审美的普遍性,只能来自判断。判断一般是通过逻辑、范畴或者通过概念来确定的。但是,康德所谓的“审美判断”却是“无须概念而普遍地让人喜欢的东西”.[16]“是对诸心理功能活动的协调的情感”.[17]康德试图强调这样的审美判断要求的不是概念本身,而是一种“共通感”.借助李泽厚的诠释,也就是“想象力与知性( 概念) 处在一种协调的自由的运动中,超越感性而又离不开感性,趋向概念而又无确定的概念”[18]的主观普遍性。
第三,从目的的关系的关键角度来看,审美趣味具有必然性。具体而言,康德认为,审美判断唤醒的不是以客观对象为目的的行动,而是一种从情感上觉得愉快的主观的合目的性,是对象符合主体“诸心理功能活动的协调的情感”的自由运动,即一种审美的合目的性。康德认为,这样的合目的性正是没有特定的、具体的客观目的的“主观合目的性”.换言之,作为审美判断的主观,并不指向特定的、具体的客观对象。但是在康德看来,“至少可以依据形式”---“就我们意识到这种形式而言,才构成我们评判为无须概念而普遍可传达的那种愉悦,因而构成鉴赏判断的规定根据”[19]---来“察觉到一种合目的性”.对于这一范畴,康德提示了“无目的的目的性”这一概念,并突出了“非功利而生愉快”“无概念而趋于认识”.[20]
最后一个契机,即“模态”,即审美趣味具有先验性。康德认为,“无须概念而被认识为一种必然的愉悦之对象的东西,就是美的。”[21]
所谓“无须概念”,也就是不能依据主观与客观之间的概念性的认识或者判断; 同时也不能是以客观对象为目的的主观的经验论。康德认为,“只有在假定共通感的前提下”,我们才能实现审美判断。[22]
这样的共通感,就是人共同感觉的“理念”,它不单具有人的自然生理性质,同时还具有社会性的内涵。正如李泽厚所指出的,这样的社会性或者这样的“模态”,既是个体所有的( 人的自然性) ,同时又是一种先验的理念( 人的社会性) .[23]这就是康德提出的一个人类先验的主观性原理。
综而述之,正是通过这四个契机,康德系统阐述了审美活动中的“趣味判断”的特质和原理。
就康德而言,趣味判断就是鉴赏者无功利地对客观对象的形式产生的情感,无须借助逻辑知识形成的概念,而是通过预设的人类“共通感”,这样的审美判断也就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 趣味判断能力不是先天的禀赋,而是后天的习得; 人经过后天性的学校教育陶冶,可以获得趣味判断能力; 趣味判断应该注重形式、且无关功利。[24]
康德的这一论断成为后来的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唯美主义、先锋艺术的理论基础,亦对布尔迪厄的文艺场域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
三、布尔迪厄围绕康德美学的批判与反思
承前所述,康德的审美理论对于后世美学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度成为形式美学遵循的理论典范。尤其是新古典主义者,他们追求“超验与唯一的美的范本的共同信念”,并将之作为“每一个特定艺术家的价值的衡量”标准。但是,在一个犹如约翰·斯图尔特·穆勒( John Stuart Mill) 所主张的“没有真正的美,凡是有用的都是丑陋的”[25]的审美现代性的关照下,康德的先验的、形而上的,即以趣味判断为核心的美学理论遭到不少理论家的批判。
站在社会学的视角,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齐美尔( Georg Simmel,1858-1918) 从消费社会时尚的角度对康德趣味理论进行反思,指出货币成了上帝,银行构成现代城市的中心。人的一切感官知觉皆离不开货币,但是人应该保有自己的自由权,在货币之外拓展视野。这样一来,艺术家不仅仅为钱,更应为自己的精神而创作。站在艺术社会学的角度,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文化批评家伊格尔顿( Terry Eagleton,1943-) 对康德的审美无功利的立场展开了意识形态的反思,尤其在《美学意识形态》( Ideology: An Introduction,1991) 一书中,伊格尔顿采取意识形态理论剖析现代“美学”,指出整个西方现代美学史就是一部意识形态话语史和政治反应史,现代美学的兴起和发展是资产阶级反对专制主义、建构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的结果。站在反思康德美学的立场,意大利文艺批评家克罗齐( Benedetto Croce,1866-1952) 突出了“艺术即直觉”“直觉即表现”,强调要将审美的再创造和审美主体皆纳入审美历程之中,使之成为一个具有生命的动态过程,并由此而承认趣味标准的绝对性。[26]
站在阶级分析的社会学角度,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哈拉普( Louis Harap,1904-1989)反对从普遍人性的立场进行纯粹的美学思辨,指出了趣味的社会性、阶级性,提出“趣味是阶级斗争的晴雨表”“时尚的本质是上层阶级的趣味竞赛”“大众艺术趣味受制于资本家控制的大众媒介”等一系列命题。[27]
正是基于这样一批后现代的文艺理论家对于康德美学趣味理论的反思与批判,西方美学趣味理论进入到了一个“后康德”时期。
作为一个思想兼收并蓄、研究包罗万象的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美学家。但是,布尔迪厄却意识到康德的理论局限于思维、上层建筑的完善构建,忽略了趣味与物质基础、社会历史的互动,因而对“趣味判断”这一概念尤为关注。在《区隔: 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 la Distinc-tion: critique sociale du jugement) 之中,布尔迪厄系统探讨了文化消费社会领域的趣味问题: 一方面,布尔迪厄批判与反思康德美学所谓的无功利、普遍性、必然性、先验性的理论基础; 另一方面,将趣味还原为日常生活的实践,并将之与社会阶级区隔、社会空间的场域、惯习、资本、实践等概念结合在一起,赋予趣味以超越于纯形式审美的社会性功能。就这样,布尔迪厄在回顾传统美学领域下的趣味探究的基础上,针对康德的趣味判断的一系列问题,尤其是趣味判断的本质主义与普遍主义进行了理论反思与重新诠释。
首先,布尔迪厄质疑康德美学的无功利性、先验形而上的本质主义。康德认为,趣味判断乃是一种无功利性的快感,无需确定的智性概念,并将这一判断归因于先验性的综合判断的思维范式。
对此,布尔迪厄批判指出: 在日常生活中,普通大众的审美判断难道只是通过先天禀赋而得来的综合判断? 趣味判断是否需要采取社会化、历史化的维度来加以考量? 康德所谓的“纯粹凝视”是否绝对“纯粹”,是否掩盖了审美主体自身的物质因素和文化因素? 站在社会学的立场,布尔迪厄进而指出: “假设艺术品存在( 亦即作为一个具有意义和价值的象征对象) ,确切地说,只有当它被具有所要求的意向和审美能力的欣赏者所把握时,才可以说正是一个审美者的眼光使得某个艺术品得以成为艺术品。”[28]
在此,布尔迪厄尝试告诉人们,审美趣味不单是先天禀赋的能力或者普遍存在的共通感就可以完整地加以解释的,而应该将其放置在历史建构的社会场域、文艺场域之中来加以考察。这样一个自美学向社会学的转向,可以说是布尔迪厄不同于康德且尝试超越康德之处。
其次,康德认为,趣味判断的基础来自人类的共通感,且这样的共通感是一种人类先天普遍具有的综合判断能力的理念、共同感觉的能力。针对这样的审美判断的普遍主义,布尔迪厄指出,人并不是生来就拥有审美趣味。主体的趣味何以产生? 不仅要考察美感的潜能,还应着重考察主体所处的社会场域,尤其是主体在其所处场域中的位置、社会轨迹、资源的配置、所拥有的资本状况等一切内容。康德试图跨越时空的范畴,抽象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审美判断。但是,布尔迪厄则质疑一切的普遍主义,指出: “怎么可能会有这样一种历史活动,比如科学活动,它本身处于历史中,却又能生成既贯穿整个历史又独立于历史的真理,它超脱于一切,却又具备具体的时间地点,并且还永远地、普遍地有效?”[29]
因而他主张审美趣味需要依凭潜在的美感能力,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境中激活,求得进一步的形塑。挖掘隐藏在纯粹目光之后的社会物质、文化继承等条件,就此成为理解“趣味”是什么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而且,布尔迪厄指出,“审美者本身就是长期接触艺术品的产物。”[30]
事实上,正是通过长期接触艺术品,使自身沉浸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情境中,审美者才成为真正的审美者。就此而言,注重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境,强调实践对于主体自我形塑的重要意义,正是布尔迪厄对于康德的反思与超越的关键之所在。
布尔迪厄曾经宣传自己探究的就是“科学的科学”,且一直在寻找社会学研究的科学化契机。
这一追求令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研究充满了反思与批评: 批判康德美学的本质主义与普遍主义,反对把鉴赏行为抽象化、普遍化。在布尔迪厄的眼中,康德美学的上述特征或许不过是一种充满了知识精英气息的理想化形态而已。布尔迪厄自身所倡导的,就是一种以批判与反思为基调、以文艺场域为实践对象的“结构的建构主义”( constructivisme structuraliste) ,最终指向“科学”的社会学。[31]
四、布尔迪厄的“审美趣味”
既然布尔迪厄不赞同康德本体论美学之中的纯粹趣味的普遍主义和先验性,质疑审美的无目的、无功利性,那么布氏自身力图建构的“趣味”概念究竟如何? 围绕这一概念,布尔迪厄通过《区隔: 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 1979 年) 、《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 1992 年) 、《文化生产场》( 1993 年) 三部论着展开了详细论述。《区隔》是国际社会学联合会评定的 20 世纪最为重要的十部社会学着作之一,《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文化生产场》则是当代社会学和美学的必读经典。在这一批论着中,布尔迪厄力图反思康德的纯粹抽象趣味,超越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决定论,批判超越政治经济利益的文艺非功利论断,树立自身的审美趣味理论。
究其要点,首先,布尔迪厄“审美趣味”理论的基本立场,就是必须回归日常生活实践,通过日常文化实践来重新审视趣味的意义。布尔迪厄指出,“除非日常使用中狭义的、规范的意义上的文化回归到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并且人们对于最精美物体的高雅趣味与人们对于食物口味的基本趣味重新联系起来,否则人们便不能充分理解文化实践的意义。”[32]在此,布氏所指的“狭义的、规范意义上的文化”,即类似于精英知识分子所定义的文化概念; 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则是指广义上与普通大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人类的实践。只有将审美趣味转移到对日常生活物品的趣味,与大众文化相联系,才能完全理解文化实践的真正内涵。因此,布尔迪厄一方面强调要回归到法国社会民众的饮食、服饰、装潢、运动、阅读、音乐、电影、绘画等日常生活之中来审视普通大众的生活趣味; 一方面亦强调文艺鉴赏者必须将文艺品放置于具体的生产、流通、消费、分配的社会历史语境中,掌握文艺创作者如何获得文化资本、社会资本、象征资本,占据自身在文艺场域或者其他场域的位置,树立自身文化权力与塑造审美趣味的问题。
其次,布尔迪厄认为,审美趣味不仅是美学意义上的鉴赏判断,而且还具有社会学意义上的阶级分层区隔的作用。在《区隔》之中,布尔迪厄指出: “趣味能分类,也能分类分类者。”[33]分类即指规划社会阶级阶层,审美趣味不仅可以对社会群体进行区分,而且亦可以针对以此为对象而进行研究的分类者进行阶层分类。正是因为权力社会之中存在着阶级等级的差异,社会主体的生活方式、文化消费也就必然不同,因此他们的审美趣味亦必然不同。一言以蔽之,审美趣味的不同,恰恰与阶级等级的不同归属相互照映、异质同构。具体而言,一个社会行动者的阶级阶层与身份地位,决定了他具有该身份所特有的生活格调和审美趣味。为此,布尔迪厄重点探讨了统治阶级阶层、中产阶级阶层和被统治阶级阶层的趣味,指出各阶级阶层文化消费的操作实践不仅标示出社会区分,同时也在持续地维持着、不断地再生产着阶级差异。
第三,布尔迪厄利用“审美趣味”来区隔阶级阶层身份,指出统治阶级追求一种衣、食、住、行等各方面的、作为自由趣味的“雅趣”,且较之功能更为注重形式; 中产阶级的文化能力、文化消费、趣味追求皆是有限度的,既不同于被统治阶级,亦与上层社会的自由趣味区隔开来,是一种可称为“文化意愿”、具有双重否定性的美学品位,并且是“假设的一种趣味,一种文化客体,一种没有确定性的判断标准”;[34]被统治阶级的趣味则是一种“粗俗的趣味”,[35]一个带有必然性的趣味。布尔迪厄指出,正是资本、教育、惯习、幻觉信念( illusio) 等一系列核心要素造就了这样的阶级阶层身份,并且在一定社会关系、阶级群体中的所有行动者皆传承着共同的、相似的文化资本。也就是说,布尔迪厄“审美趣味”最终指向的正是“文化资本”这一核心概念。
事实上,布尔迪厄并没有停留在“审美趣味”这一立场,而是进一步深入到“文化资本”这一范畴。作为布尔迪厄社会学理论的核心概念,文化资本涵盖审美趣味; 审美趣味乃是反映文化资本的价值形态。不过,布尔迪厄亦曾提到: “文学场是一个力量场,也是一个斗争场,这些斗争是为了改变或保持已确立的力量关系: 每一个行动者都把他从前的斗争中获取的力量( 资本) ,交托给那些策略,而这些策略的运作方向取决于行动者在权力斗争中所占的地位,取决于他们所拥有的特殊的资本。”[36]在此,所谓的“特殊的资本”就是布尔迪厄界定的“文化资本”.在此,审美趣味成为行动者“惯习”的主要体现之一,它引导着行动者的审美实践,同时也可以提高行动者的文化趣味。就在这样的过程之中,文艺场域得以不断地产生、不断地经历着再生产。
围绕“审美趣味”的演绎与变迁,再度审视布尔迪厄针对康德美学的反思与超越,我们可以认识到: 布尔迪厄诠释的“趣味”,不同于古希腊、文艺复兴、康德美学以来的欧洲传统,即并没有将审美的目光停留在纯粹的美学领域,而是转向了普通大众日常生活实践领域,转向了文化商品消费活动的趣味。布尔迪厄并非是站在纯粹的美学理论的立场来批判康德,而是站在一个自康德美学向社会学转向的立场,进一步超越“审美趣味”的范畴,树立了以“文化资本”为核心的阶级阶层学说。
不过在此,反过来我们亦不得不指出,布尔迪厄立足于社会学理论的视野阐释审美趣味,将审美趣味与一般社会文化产品,尤其是意识形态、阶级区隔等同起来,不仅将美学的视角或者立场排斥在理论批评的视野之外,同时也就以社会性的阶级阶层划分为直接目标来把握审美趣味,忽略了审美给予人的超越性范畴。
布尔迪厄阐释的“审美趣味”,是以“趣味”为基准来透视消费者的阶级身份,展开阶级阶层区隔。这样一来,与马克思将阶级理解为物质上的有产与无产、政治上的剥削压迫与被剥削被压迫的关系不同,布尔迪厄突出了社会行动者的主体性审美。而且,布尔迪厄还通过审美趣味而提示出“文化资本”这一概念,其目的在于揭示现代社会中被遮蔽、掩饰了的象征性统治、资源不均等、地位不平等、阶级差异及其对立的内幕。这样的社会学式的拓展,应该说亦具有了现实性与合理性。
不过,布氏所突出的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主体性审美,亦可以为我们诠释个体性主体的审美行为提供一条通道: 作为社会行动者,一方面不可避免地会接受、形塑社会惯习---按照布尔迪厄的解释,这样的社会惯习与个人惯习“同源同构”,会受制于生产关系的影响与禁锢,投入到场域的社会性、历史性的建构活动中; 一方面,亦可以抱着一种“为艺术而艺术”的神圣信念,在“幻觉信念”的感召下以个体性主体的方式进入到社会场域,把场域“建构成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一个被赋予了感觉和价值,值得你去投入、去尽力的世界。”[37]概而言之,布尔迪厄尝试利用自身重新诠释的文化资本、惯习、幻觉信念等一系列概念,重新标示作为独立个体的社会行动者,确立其在场域中的地位,由此而构建起以主体性为前提的、场域内的主体间性对话。布尔迪厄的审美趣味这一概念的社会学意义,大抵可以归结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