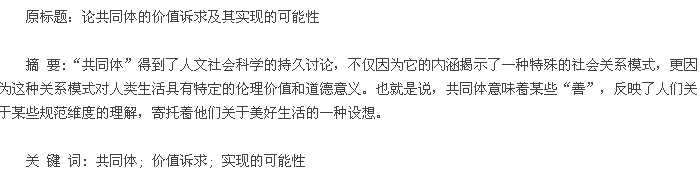
在共同体主义者看来,共同体语义环境承载着特定的伦理价值与道德意蕴,其对“善”的觅寻有着独特的情怀。在倡导者眼中,共同体的伦理意义不仅表现在存在论维度上,而且直接地体现在道德规范与品质上。即作为“共同体”样式存在的生活社会将是“好”公民的有效孵化温室———让他们明晰个体的身份与价值定位,拥有积极正向的社会生活方式和人生追求,并对他者与社会整体表现出由衷关切。但是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现代社会结构正面临着巨大转型,现代性世界不仅“在群体构造与生活专属领域存在着迥异,且在宗教、组织、国家间亦有多变的关系和复杂的互动模式存在”[1]。因此如何在现实意义上论证共同体实现的可能性,使得其回归现实生活,重拾关于“善”的信仰,呵护“那片‘心灵的港湾’和‘诗意的栖息地’”成为重要命题。
一
当古希腊人设计或建设他们的共同体( 城邦)时,看重的正是共同体这种群体生活形式的伦理含义。据普鲁塔克记载,以严密的纪律和几乎苛刻的集体原则组织起来的斯巴达城邦,其在城邦之内充分实现共同的利益。在斯巴达人看来,通过完整而一致的集体行为把全体成员构造成一个大家庭,这才是纯粹的共同体。因为“‘家’这种样态的存在是集合与团结的象征,她使人们更好地融入他者与集体,并尽可能地为集体目标实现而缩减个人物欲———在这里,‘私人’可能不复存在,成员个体犹如勤劳的蜜蜂,为共同的巢穴和生活努力地工作着,他们各司其职,怀着整体的信念让这个大家庭发展得更好”。[2]这些所述成为斯巴达人最为推崇和珍视的生活样态。
相比于斯巴达人的严格与恪守,雅典民众的生活宽松了许多,但是亚里士多德同样认为,“政治共同体( 城邦) 的发展应成为每一位邦员个体心所维系的,而非仅追逐自己的幸福生活”,“所以‘城邦’的概念是时刻关乎于美德的遵守: 个体美德的践行正是使得城邦成为真正的‘共同体’,以此区别于松散的群居联合体”[3]。可见,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社会民主观,一个政治共同体的“中心目的不只是要最大限度地发展个人自由,而且更重要的是要为公民准备和提供一个健康成长的人类生活。以亚里士多德的视角来看,具有高尚道德和知识美德的公民,才可以组建安排社会与政治机构,并以此推动和实现整体‘类’的繁荣和幸福”[4]。也就是说,一个共同体不仅自身是以自我完善为宗旨,而且它还兼具培养其成员的能力及以下责任: 不但为其成员提供生活的背景和学习的渠道,而且更担负着对他们进行教化、熏陶、提升的责任。
这种教化或提升不仅是道德上的,更多的是在熏陶和提升他们对于一个完整的美好生活的理解,以及培养他们对于建设这种美好生活的政治途径的实践能力。而 19 世纪的社会学家之所以大量地讨论共同体,也主要是出于某种道德忧虑和道德怀乡症。他们把共同体视为富有伦理倾向和道德内涵的社会结构,认为这种结构能够有效地遏制和治疗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的道德滑坡。对此点,卡尔霍恩曾提到:
“共同体概念不仅仅具含人口、群体、地域要素,其对于道德的诉求更为强烈。可以说早期社会道德的缺位更加唤醒了共同体倡导者迫切注意‘城市化’或‘现代性’生活……大众生活人际关系的日益交互化和复杂化才使得共同体关于道德与伦理自觉的话语迅速增长。”[5]正如滕尼斯影响早期的共同体辩护者深远的二分法所表明的,“社会”体现了相互算计的选择意志和相互逐利的货币逻辑,而“共同体”则体现的是基于亲缘的自然意志和相互帮扶的道德逻辑。因此,共同体之所以值得倡导甚至留恋,原因之一在于,它更具有道德的温情感,使人能够相对自然全面地生长,而不会被剥离、抽象或异化。
二
20 世纪的共同体主义者对共同体的倡导,同样也出于某种道德考虑。他们认为,占据西方主流地位的自由主义思想并不能够真实地反映人的生存状况,不能反映人类群体生活的重要价值,因而不能提出人类自我完善、自我塑造的完整性方案。在共同体主义的政治哲学观念中,共同体的最大意义和最不可忽视性在于,它具有构成性———无论是在存在论意义上还是在伦理学意义上,皆是共同体建构了个体而非个体构成共同体,即在顺序位阶上共同体比之于个体具有优先性。正如迈克尔·桑德尔( Michael Sandel) 提及的,在共同体主义者眼中,“共同体”的概念内涵更甚于“联合体”之处在于前者清晰地勾勒出社群对其成员的塑造性和构成性,而这一重要内涵在自由主义者那里往往被掩盖。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共同体的构成性特质及其与个体间的关系: 成员个体归属于共同体,共同体稳定而自然的规范、传统、记忆、历史、习俗决定了成员身份及其自我认同的内容涵盖; 个体是无法退出构成性共同体的,否则他们将会丧失自身的完整性和理解世界的框架[6]。仅从个体生存图景的完整性和真实性来讲,真正的“人”须具有“类”的属性,其终生不可脱离共同体而存在。以异化的视角来看,没有被共同体纽带所维系的个体,往往会迷失在单向的经济生活中,使其失去主体意识并沦为亚人类存在物。因此,个体趋于真实和完整的唯一路径是处在道德关系网络之中,践行其多面化的角色认知。在这方面,阿米泰·伊兹欧尼( Amitai Etzioni) 甚至不无夸张地指出,共同体与个人正常生活状态之间也存在显见的生理联系: “共同体所给予和带来的温存感和安全感是孤独的个体所体味不到的,当个体没有可依靠的共同体之时,其往往会在身体和心理上面临痛苦( 身体更易于患病且不易恢复,精神上缺乏自信、情绪低落) 。处于现代社会之下的人们时常感到没落、孤独、离间之感的原因之一即缺乏足够的共同精神纽带。维系精神的纽带断裂或不复存在之时,甚至会使个体做出反社会的异常举动,比如加入帮派、邪教、犯罪组织( 寻觅共同体以求慰藉) 或吸毒、酗酒……共同体可能不是人生存所必需的,但她一定是人生活所必需的,若脱离了她,很难想象个体如何‘完善’和‘真实’地建构。”[7]与之相比,自由主义语境中的那种注重“权利”和“自我”的个体,难以把“责任”和“仁爱”等价值置于优先地位,因为前者并不必然地蕴含后者。所以,共同体主义者倡导共同体的目的在于,重新唤起人们的群体意识和归属感,让人意识到自己其实是属于某种共同生活的“有依赖性的动物”,人本身就生存于一定的背景或语境中。这样,一方面使之认识到共同生活对自己的重要性及自己对这种生活的责任; 另一方面,也能使之有效地形成善恶观、清楚地设定人生规划,从而走上一条自我完善的道路。具体而言:
首先,个体生存境遇与价值实现必须具备一定的公共语境,而共同体恰恰可以提供这样的语境,“个体依据族谱、亲戚朋友、社会地位、公共空间等所生存和遭遇的环境人物要素来定义自己,并结合以上认知规定自我发展的航向与行动目标”[8]。显然,以上种种要素尤其是公共的话语环境更能为个体透彻了解自我、分析自我提供价值参考,这种经由共同体提供的公共话语环境较之其他的共同生活和联合体更有助于个体实现自我确认和完善发展,对于其社会伦理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激发及卓越人生的追求实现大有裨益。
其次,共同体还为个体卓越的人生追求与幸福生活的实现提供了更为清晰的价值导向与标准界定,那即是在此过程中必须得到萃取的要素———美德。虽然但凡共同生活的样态皆有各自对于“卓越”与“幸福”的定义与理解,但是普通的联合体或者共同生活在对个体的规范力上较之于共同体显然软弱许多,而且其在详尽的规定内容上可能也充满分歧。前两种群体中,若向置身于其中的个体询问“何为幸福”以及“如何追寻幸福”的问题时,因为共同伦理价值指引的缺失,他们的回答很可能与群体内的其他成员甚至整个群体的道德诉求相左。鉴于此,如若期望个体与其他成员及整个群体的道德期待相同,对于实现“幸福”的追求和方式产生共鸣,我们就必须恰当地期待与假设,人们的共同生活可以提供一种关乎整体成员的道德伦理传统和善恶观念,且这些理念与传统对个体的价值取向及其实现路径进行有效的构造和指引。
所以,共同体其本真属性所诉求的“卓越”“幸福”等价值观念为公民个体的美德践行提供了概念指引和意义背景。因为以上价值诉求往往在公共领域被理解为个体“应为”或“所是”的正确优秀言行———美德。伯纳德·威廉姆斯( Bernard Williams) 曾提到以下论点,人类个体往往习惯于“从已然获得自我所期望的或者构成性的‘所是’此种价值伦理作为始基来理解或看待伦理的善及他者的善”。但是共同体恰恰“作为个体进行价值、意义性行为和思考的准据与背景性存在,个人并不能像脱离自愿结社的联合体一样脱离自我所生活存在的社群[9]。个体存在于共同体这样的意义构造中,能够比之于其他共同生活类型时刻地为其实践行为提供价值导引与评价框架。
在这个框架结构之上,共同体成员往往可以就社群所面临的问题达成一致并付诸有效的行动。而这种效应和群体意识往往有利于表现出美德行为和道德诉求的成员及时得到其他成员的反馈并形成共鸣( 而非冷嘲热讽) ,进而激励共同体成员协同一致地按照某种“善”的导引去实践和行动。就像卡尔霍恩所言:
“成员个人对于整体行动有所影响; 而社群整体之于个人的行动轨迹亦有很大的反馈和制约力。这种系统性互动的效果之一,便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行动提供相对确定的认同感。这个认同感对社会活动与集体行动中的个体行为范围的可能性有着有效的规范维度。”即处于共同体之中的个人更易感知他者成员存在的重要性及对自我行动的巨大影响力和构造性,他人对善的追求与善的行为表现往往揉入到自我行动和思考的部分之中。所以,他者的幸福构造自我的幸福,当处于共同体之内的个体打算成就自我时,他对他者成员之于己身的意义更加注重,也因此更可能积极地将他者美德展现在集体的公共活动领域之中。
三
如果把共同体理解为一种特定的社会存在模式和社会关系模式,那么,它就会在现代社会遭遇“是否可能”的质疑。正像哈贝马斯所言及的那样,现代社会的公共领域结构日益变得复杂化、结构化和层次化。信息时代的真实世界图景具含以下表征: 利益多元性、成员众多性、结构复杂性。伴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通信和交通技术的提升,地方社区的地理空间范围被无限地放大,“地球村”的演进使得传统的社区朝着独立化、分散化的特点不断推进。若借用滕尼斯社会、共同体二分之法,那么可以这样断定: 现代社会已然是典型的“社会”而非“共同体”了。可以明确的是,现代社会成员所追求的“共同利益”是以个体权益为核心的,即个人利益置于集体利益之前; 且这些利益结构之间并非有序和一致的,他们面临多元化、分割化,他们之间存在着冲突与矛盾。
鲍曼曾对韦伯的“利益共同体”概念做出较为详尽的分析,他提及,在现代社会个人利益的觅寻性和追逐性被不断强化,使得群体“进行一致性决策和持久性行动的能力丧失了”。此外,伴随群体内部利益分割的日趋零散化,内部个体之间的联系被大大削弱,直接导致人们之间的认同感降低,个体依己欲和所求作为思考和行动的出发点。在这种情形下,当在群体内部缺乏利益相关的一致性而不能进行凝聚且在其外部又缺乏“足够强大的压力或动力,使其边界定位在合适的地方,并将它变成一条战线”[10]时,共同体便难以存在于现实生活之中。此种情形下人们在公共领域中政治谋划一致性的原因往往是迫于生活的压力而妥协或者绥靖,并非源于个体心底本真的诉求和价值寻觅,更谈不上为他者考虑或成全他人了。
分化的利益基础必然导致个体所诉求的伦理立场的冲突。因此,在现代社会处于其中的每个领域和部分均有其所属的利益追求和美德清单。在如此的社会环境中,普世性的、为每位个体所敬仰的价值美德是缺失的,甚至对于连续、持久意义上的美德定义和概念表述也不存在。现代世界所缺位的价值统一性和道德一贯性恰恰是共同体主义者和美德论者提倡和追寻的理想化共同体存在的先决条件。市场经济下道德体系的多元化和伦理价值的破碎亦对我们时常所感、所想的现实社会境遇与道德混乱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同样从反面论证了当下人们对于大谈美德及相关话题抱以冷漠甚至嗤之以鼻态度的原因。因为,现代社会在公共领域层面已经很难为个体提供清晰、持久、有感召力、有说服力及构造性的道德尺度与伦理背景。
呼吁共同体存在和回归的人们可能会认同,现代社会并非在以共同体的样态和形式运作是人们不能在公共领域展现美德的最重要原因。可是他们绝对不会认可这样一个事实,即当下社会共同体已然破碎或者没落而不复存在。于是,他们仍然竭力维护共同体并呼吁共同体应当在公共领域中进行重构,将公共生活复归成为“共同体”。
但是,现代社会现实图景及其他理论好像对上述理想并不认可。赫尔穆特·普莱斯纳( Helmuth Pless-ner) 指出,从共同体语义的根基来看,共同体是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阐述的,其作为基本的政治理念或想象在最本源的层面上应当归于血缘上的共同体。前文已经论及,古希腊( 特别是古典时代之前的) 城邦实际上具备上述特质,即其组织和构造以相同的宗教崇拜和血缘种族为始基。在城邦中,“国家被视为一个家族意义上的集团而存在,社会的成员因血缘上的相近性而连接在一起……一个个活生生的血族群体构成了群族认可的国家。而国家完全可以被划分为众多小规模意义上的家族集团,这些家族集团是血缘上的宗族和兄弟会,而非遵循行政毗邻或地域相近的原则”[11]。上述的集体共同生活样态显然距离建设一个更为理性文明的社会还较远。亦正是因为此种生活形式的多种弊病,才使得后续的雅典执政官克里斯塞尼( Cleisthenes) 针对血缘胞族的公民权改革。改革的推动才使得希腊城邦得以更加繁荣发展,希腊文化更加璀璨炫目。从这个层面上讲,一个并非真正、典型化的“共同体”恰恰推动了人类政治发展与文化的进步。
即使近些年来在政治哲学中为共同体主义倡导者所频繁提及和使用的共同体概念,但其在更多的层面上仅仅是提醒人们需要注意,个体是无法摆脱社群环境及其所在的共同生活对自我构造的影响。而且这种理解和使用界定,仍然以“类血缘”或者血缘关系的存在作为理解的基础。比如,一个常见的现象是,我们在论及共同体成员间及其与他者的关系时,时常借助“同胞”( 同一胞胎) 这个词汇,而该词具含典型的生物学上的血缘族亲意义。虽然我们不可武断共同体倡导者皆希望依血缘族群构建形形色色的共同体,但是当他们一再使用类似词汇或者呼吁建构类似的生活情境时,不可避免地需要倡导与营建一种家庭般或亲族般的形式氛围,这样才可确立共同体的特殊性与合法性。更甚,若仅仅像共同体主义者所辩驳的那样,倡导共同体的缘由仅仅是着重强调共同体所在的群体社会对个体具有显着的构成性而不一定非强调共同性,那这样的话,共同体也便不能明确清晰地划定其与他类共同生活的相异点,而共同体主义理论也会变得与其他着重强调社会生活重要性的理论没什么本质上的不同。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不再可能在现代社会获得共同体? 是否连同共同体所具有的积极价值和伦理意义都将一道丧失?
四
事实上,现代社会公共领域中无法寻觅共同体的身影,但是并不代表其在现代社会的其他领域就难以存在。实然,共同体所具含的概念属性里包括紧密的“共同性”和强力的“构成性”的显着要素,这些在当代社会的公共领域内较难发现。但是———“家庭”( 规范意义上的) ———这类基于血缘、个体情感、共同利益诉求的小规模群体社会的私人领域中依然有着共同体的魅影存在。
第一,在一个家庭中,家庭成员仍然共同拥有生产和生活资料的支配权和使用权。而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婚前的财产公证总会让人感觉别扭。因为该法律程序所带来的明晰划分,实际上是在瓦解家庭“共同的”经济基础。即使人们现在接受这种公证过程及其协议结果,也只是由于现代法律为之提供了一定的合法性( legality) 。但是,这种合法性更多地在于,它能够更有效率、更加方便、更加清晰地处理家庭纠纷和家庭分裂。也就是说,当一个家庭不再像个“家”,不再是个“家”,不再构成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共同体时,上述法律程序和法律文本才有意义并发挥作用。此外,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婚内的“私房钱现象”常常会给家庭带来不愉快,因为它使共同体中的部分成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丧失了对财富共同支配和使用的资格,这样就会导致共同体生活发生信任危机。固然,家庭内部也有相对固定的财富使用权划分,比如,谁用哪个饭碗、哪双筷子; 谁用哪条毛巾、哪个卧室。但必须注意到,这只是功能性的划分( 出于使家庭生活更加健康、和谐的考虑而做的划分) ,而不是财富所有权的划分,它绝不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都只有你才能支配那个“属于”你的碗筷,只有你才能出入那个“属于”你的房间。财富所有权在一个家庭内部被泾渭分明地确立起来,这是难以想象的。
第二,家庭成员在今天的社会分工体系中可能具有相当确定的主体性,如可能是科学家或音乐家等,但他们在“家里”则常常是浑然不分的,彼此之间没有明确的分工。虽然现实也存在相对稳定的家庭职责分配( 如妻子做饭,丈夫洗碗) ,但这绝不是固定的劳动工种,更不是职业性的任务。妻子某天因为某些原因没有做饭,或者丈夫某天因某些原因没有洗碗,绝不应当成为被谴责乃至被惩罚的理由,否则,打理家务就会因为明确而固定的分工变成个人在八小时之外的另一份职业。于是,一个人为家的操劳和付出,就不再是心甘情愿地精心经营,而是任务乃至义务; 在家务劳动中,体味不到幸福和快乐,有的只是“职责”,甚至是迫不得已的烦苦。“异化劳动”似乎从职场上渗透到了家庭中,当一个家庭到了这种局面时,它已经不能称其为“家”了。
第三,由于没有明确的劳动分工,家庭成员也就无所谓劳动产品的交换或利益的博弈。他们不是为了更多的个人利益而走到一起来,而是首先因为情缘、血缘才联结在一起,然后在一致的利益基础上共同打理家庭财富。每个人在满足自己的利益和乐趣的同时都会考虑是否对家庭其他成员和家庭整体有利———即使某件事并不直接于“我”有利,但如果它能够满足家庭中其他成员的利益和乐趣,那么“我”也希望或促使这件事情发生。因为当家庭其他成员拥有这份利益和乐趣后,“我”并没有失去什么,反而随之也得到利益和乐趣。可见,“家庭”是符合“共同体”中“个人与整体利益成正比”这个标准的。
第四,家庭成员的利益关系决定了其成员必然要相互关心、相互爱护和相互尊重。他们不仅互为目的,也把家庭本身当作目的。也就是说,让家庭生活成为一种“休戚与共”的状态,让家庭生活更美好,这是家庭的内在目的,也是家庭成员最终追求的东西,而不是借家庭生活来实现某些独立于家庭之外的目的———比如,结成一个家庭是为了贪图可能从对方那里获得的社会资源。否则,家庭只不过具有法律的有效性,只不过是虚伪的共同体! 纵然它在表面上能保证家庭成员共同支配财产、没有明确分工,但是他们并没有共同利益,他们走到一起来也是有人心怀鬼胎,视对方为实现自我利益的工具罢了。
五当然,即便上述论证是可以接受的,也至多能说明严格意义上的共同体依然有可能在现代社会的私人领域里存在。然而,一方面,由于现代社会的公共化程度越来越高,公共生活越来越成为人们的主要生存场景,因此,共同体只能在私人领域中存在,这本身就不会放大共同体的积极伦理意义。另一方面,私人领域的共同体关系即使再强烈,也不能解决它在公共领域所造成的主要问题,即以种族、民族和国家为主体的认同与团结问题。以威尔·金里卡( Will Kym-licka) 为代表的一批北美学者的研究成果,为这方面的讨论提供了有价值的框架。通过他们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为了应对多民族国家的认同和团结,至少存在五种策略[12]。
第一类策略是,采取舆论影响与媒体宣传等方式着力倡导主流民族的认同情感,在此基础上同化其他民族,使其上升为国家认同。这类策略的目标是转化或“收编”他类民族成员为同一民族群体成员,即主流的民族成员个体。此种境况下,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边界范围才可达到契合的程度。以学理的视角来看,同化主义的民族认同策略虽可在相当程度上解决民族多样化的分歧,从而倡导较为一致的民族国家观,但是其在现实应用中却日渐缺乏人心。因为此种策略成功的后果之一,必须是少数民族族群愿意被同化,放弃自我的民族认同( 或少数民族还没有确立起固定的民族认同感) 。但此种情形在当代文明社会里基本上已经不复存在了。与此恰恰相异正是各民族自我认同的强大感召力才造成当今世界多民族国家的冲突与困境。由此,若再想推行强制性的民族同化主义策略,这往往是不明智的选择,因为这类策略与当今政治与民族伦理的基本原则相悖,其必然引起少数民族的激烈反应,最终使得中央政府在道义上陷入不利的境遇。
第二类策略是,对待各类民族( 主流的和少数的民族) 应当以平等公正的视角切入。这一策略为国际社会多数国家所采取( 如我国的少数民族政策即是如此) 。这一民族政策被称为“多元文化主义”。此种策略视角下的少数民族拥有自己的独立居住空间和地理活动范围,并采取特别的政策与法律对其发展进行扶持。依这种策略而建立的少数民族自治区域,在相当程度上他们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在自治权范围内,他们可以依法使用自身的语言,拥有自己的学校和媒体,践行自己的民族习俗,并传播自己的信仰和文化历史观念。鉴于此种策略赋予少数民族充分的自治权和宽松的认同空间,实践证明,其确实可以大大减少少数民族走向分裂尤其是暴力分裂的可能性。
但是,即使相当程度的本民族( 少数民族) 认同感已在民族内部建立起来,而更大程度和范围内的国家认同并没有在此基础上形成,便不能期望看到一种更具积极性、主动性的集体意识与行动局面,最多在主流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达成“各自为政”“互不侵犯和干扰”的消极局面。即多元主义文化政策在多民族国家里的推行,实然可以营造表象的和平氛围,但是更为深层面的主动合作和积极互动却是缺失的。这可能对多民族国家稳定的基本要求会有所满足,但是距离民族繁荣、共同发展、国家团结正义的实现仍有一定差距。
第三类策略是,如第二类策略所述,如若在多民族国家内部形成真正的团结认同,需要在平等公正看待各民族认同的基础上建立一种“超民族认同”。即被许多学者视作第三类策略的“超民族认同”策略———视“国家认同”为专项任务,而非将其寄希望于从各民族认同中自觉产生出来。比如,在英国政府放权允许威尔士、苏格兰自治,同时对全英国公民积极倡导“大不列颠”认同; 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人拥有专门的自治行政领域及法律、民族政策支持,但其仍需面对及在何等程度上接受关于“西班牙”国家认同的问题。
建构国家认同是通往政治共同体的重要而基础的路径,但是如何铺设这条路径需要仔细斟酌和思考,否则可能根本无法取得成效甚至逆道而行。金里卡就指出,推动超民族的国家认同,必将使人们担心这种策略是否意味着推进主流民族的民族认同,这会使少数民族怀疑这种策略而有可能退化为同化主义( 第一类策略) 。可知,若通由国家认同的路径安排不畅而有所纰漏,这类策略往往会被少数民族所误解,会认为主流民族以牺牲他们的利益为前提来定位国家认同,进而引发敌视或反动的行为。
第四类策略是,之于超民族认同的怀疑,一方面是少数民族在民族认同方面敏感性的写照,同时在另一方面反映了主流民族在倡导和完成国家认同上的尴尬境遇。鉴于这种情形,国外一些学者持有另外一种观点,即第四类策略———不再视“民族认同”为国家团结和政治共同体形成的必备要素———真正地抛开“认同”,民族属性的划归分类并不是政治生活的绝对部分,代之而起的是作为“公民”的个人要素。
政治哲学家罗尔斯便持有以上论点。其眼中的民族国家和政治团结的决定要素是作为“公民”的个体而非作为“民族成员”的个体。因此,他认为国家认同培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当是如何培养具有正义感、有利于国家团结和繁荣的公民个体,这样一种关于正义的观念影响社会的团结———“公众对于政治团结与社会正义问题上的共识应当成为维系公民友谊的纽带,成为保护协作关系的节点”。保证此点的实现,必须排除个体种族、血缘、出身、信仰的差异性,而需要一种平等的视角来对待每一个个体,即赋予所有公民“共同的公民资格”。此种公民资格不关乎群体的成员资格,而仅仅是所有个体共同享有的身份标识。
此类策略从表面看来似乎较为合理和平等,但是依然存在些许问题: 第一,种族、民族概念及认同感伴随着人类社会产生就已出现,这种观点根深蒂固,强制主观地取消这些范畴并不合理; 第二,虽然在就国家走向、民主体制等大类事项上忽略各民族知识水平和价值观念的差异,但是在最终的投票或表决态度上仍会不自觉地凸显自己所在群体的基本取向; 第三,公民平等与自觉意识的显现,虽然实现了个体权利的实质平等( 在投票表决时) ,但是由于主流民族与少数民族在人口数量上的差异和悬殊,使得主流民族的意见仍为多数———这就导致少数民族的意见不被重视或者遭到否决的危险。鉴于此,金里卡一针见血地指出,所有公民享有共同的公民身份,则意味着在进行经济和政治政策表决时少数民族无力避免主流民族对其造成的伤害。这里的问题从“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问题发生了质的转变,即“多数人针对少数人”。
美国政治学者赫斯特·汉纳姆( Hurst Hannum)和泰德·格尔( Ted Gurr) 都曾指出,从历史的视角来看,以共同的公民资格为由取消“民族”的自治架构是不合理的,甚至导致暴力性抗争运动。反之则再次说明了,依据少数民族习惯风俗从行政上划分其专门自治区域的重要性,必须尊重和承认少数民族自身的民族认同和信仰,这对于缓和民族矛盾,减少其脱离国家的危险极为重要。这就论证了,现当代多民族国家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优先采取上述第二类策略。
但不可否认,第二类策略有其固有的弊端,为了弥补完善,我们还需要在主权国家内部建构某种“跨民族认同感”。而且这种跨民族认同感的生成不能依上述第三类策略展开,必须进行完善和修正,通过创造第五类策略———“共同分享的民族认同”来建构和推行国家认同。此种策略下,我们必须在多民族国家内部发掘各民族间所具有的共同道德诉求和伦理价值目标( 如共同发展、和谐幸福) 和共同的历史境遇与记忆( 如对农奴制的废除,共同抗击他国侵略者)等,在此基础上对各民族所认同的内容进行充实完善,使得这些民族认同产生共鸣和交集,进而有利于国家认同的最终构成。
若要可行地塑造和实现上述情境,彼此生活在一起的人们需要暂时把自己的共同体和认同的优先性悬置起来。因为这种优先性是在我们的生活未与外部世界展开深入交往时确定的,实际生活的变迁及全球交往时代的到来,其实给每个曾经只生活在自己共同体中的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反思和调整的机会。
既然营造团结需要某种意愿,那么,在这种意愿足够成熟和强大之前,最好的方式就是给予彼此足够的时间以倾听和协商。在多元化世界成为必然的现实之后,虽然我们难以在短时期内( 甚至可能永远都无法) 让自己和某些共同体成员完全彼此认同,但是我们可以从现在开始就认真对待“妥协”的重要性———“妥协促使持不同观点的人共同协作,创造一个和平繁荣的国家……经验表明,这些紧张状态是能够得到控制的,而且,只要人们重视实际效用多于意识形态的纯粹性,那么就能够避免潜在的冲突”[13]。当然,妥协并不是目的,它甚至都不是一个能够处理大多数问题的药方。但是,适当的妥协却使那些来自不同的共同体而拥有不同认同的人们有机会冷静地思考,有机会尝试着把生活交织在一起,有机会达成利益上和伦理道德上的共同诉求,有机会避免剑拔弩张的悲剧发生。对于身处多样性和风险性并存的世界中的人们来说,有这样的机会存在,便也弥足珍贵了。
参考文献:
[1]Onora O’Neill. Towards Justice and Virtue: A ConstructiveAccount of Practical Reasoning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20.
[2][古希腊]普鲁塔克. 希腊罗马名人传: 上[M].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0: 117.
[3]Richard McKeon. The Basic Works of Aristotle[M]. NewYork: Random House Inc. ,2001.
[4]徐向东. 自由主义、社会契约与政治辩护[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