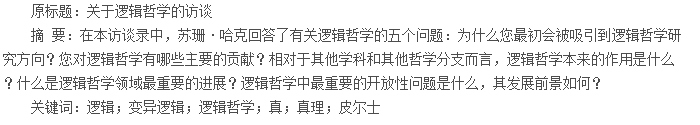
1.为什么您最初会被吸引到逻辑哲学研究方向?
在我的学生时代---虽然那时人们也承认(不过仍有些勉强),女性或许也·能·够从事哲学研究---但是,人们通常会认为我们更适合去从事哲学学科中那些看起来较"软"的方向,尤其是伦理学。但是我发现伦理学难得惊人;实际上,我依然牢牢记得:当我读牛津大学 B.Phi(l一种处于硕士和博士之间的学位---译者注)时,我在道德哲学方面得到费丽帕·福德的指导,我写了一篇道义逻辑论文---她和善地鼓励道:"是的,我看·这更适合你。"所以,那时我被吸引到逻辑哲学领域,或许部分原因是出于对那些关于女性智力倾向的未经思虑的假设的情绪化反抗;部分原因是,这个领域的问题似乎足够困难从而构成真正的挑战,但它却并非狡猾易逝以至于完全超出了我的理解能力;当然,还有一部分原因,当我开始阅读弗雷格、罗素、塔斯基、蒯因有关这一学科的着述,以及稍后阅读皮尔士的着述时,我发现有如此多的问题值得去思考。
2.您对逻辑哲学有哪些主要的贡献?
我将从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后来成为我的第一本书《变异逻辑》(Deviant Logic)开始谈起。常言道,这是年轻人的书。但是其中涵盖了很多的内容:有关变异逻辑(与经典逻辑具有相同的初始符号,但有不同的定理和/或有效的推理规则的系统)和扩充逻辑(增添新的初始符号,以及涉及这些新的初始符号的定理和/或有效的推理规则的系统)二者区别的考察;对蒯因过去和现在都令人困惑的论证---变异逻辑学家(又名"前逻辑人")是"由于糟糕的翻译而产生的神话"中何处出错的诊断;对各种变异系统中真的理解(和误解)的探索;该书中有关未来偶然事件、直觉主义、模糊性、指称失败,甚至量子力学的各章节。
第一本书仍在印行,目前印行的是它的一个有较长标题的扩展版---《变异逻辑,模糊逻辑:超越形式主义》.这个长标题背后有一个故事:原版的一位审稿人曾指出,虽然这本书涵盖了广泛的内容,但其中却没有包括模糊逻辑。事实上,我此前从未听说过模糊逻辑;于是我直奔图书馆一探究竟。那是在计算机检索的初期;我还记得,当我读到图书管理员为我列出的文献目录中的第一篇文章开篇时,我是如何笑出声的:"在本文中,我们将讨论模态逻辑和概率论,但我们不会涉及模糊逻辑。"但目录中的其他内容则给出了更多的信息;在适当的时候,我会撰写有关模糊逻辑及有关真是程度问题这一观念的批评性文章。
模糊逻辑的提出者、电气工程师卢特菲·查德将模糊逻辑描述为:模糊逻辑的真值是模糊的、局部的、主观的,在通常的命题运算中真值集并不封闭,为保证其封闭,不可避免地要引入"语言的近似值";其中推论是近似的而非精确的,是语义的而非语法的;完全性、一致性、公理化方法和推理规则都是"次要的".但是,这牺牲了弗雷格希望由形式逻辑获得的所有那些长处。此外,当你仔细阅读时,你会得知,真正的工作是由非形式的语言分析完成的,而精心建构的形式化系统在很大程度上是多余的;尽管查德坚持认为模糊逻辑本身是模糊的,但他最后仍强加了一个完全人为的精确度:真被定义为"0.3/0.6+0.5/0.7+0.9/0.9+1/1"---也即被定义为这样的模糊集,其中真值度从 0.6 到 0.3,真值度从 0.7 到 0.5,……;而"真本身"被定义为"方方正正的真"(true squared)(!).总之,查德的基础性信念即"真"是模糊的,是他的下述错误相叠加的结果:他先曲解正统术语,如"真本身"("very true")、"非常真"("quite true")之后,然后再引进俚语"很真"("rather true")、"相当真"("fairly true").
模糊逻辑的一些扞卫者反对说,我确定无疑是弄错了;他们论辩道,无论如何,在电气工程的应用领域中,模糊逻辑管用。所以在新版的《变异逻辑》中,我增加了诸如应用于空调系统的"模糊控制器"的工作说明,以表明:事实上,它们并不依赖于模糊逻辑.第二版出版不久,我收到一个来自巴特·柯思科的神秘包裹,我把它放到耳边,以确保它不是滴答作响---没有,它不是炸弹,而是有关模糊逻辑的一本热情洋溢的书稿,题词为"致苏珊·哈克,带有温暖模糊的感觉".(据我所知,查德教授从来没有回应我对模糊逻辑的批评,也没有回应我对模糊控制器的意见;但是,迄今他会偶尔寄给我有关模糊工程学的小文章。)当我在牛津读研究生时,我讲授基础逻辑课程;我在剑桥大学当讲师时,我与雷福特·班步拉达成协议:如果他在新学堂给女生讲授伦理学,我就在圣约翰学院给男生讲授逻辑;自此以后多年中,我都在华威大学讲授为期一学年的逻辑哲学课程。然而,不久我就开始为缺乏合适的教材而苦恼;这就是我开始撰写我的第二本书《逻辑哲学》的缘由.
这本书也被证明很畅销;并且以各种版本的形式,如西班牙版、意大利版、葡萄牙版、韩文版和中文版,在世界各地被使用.似乎,无论我在何处讲演,听众中都有人在"菲利斯"(这本书在英语圈内的昵称)的教育下长大。尤其令人难忘的是:2008 年我访问智利的瓦尔帕莱索大学时得知,自本书出版以来,该校哲学系就将此书作为教材(教师使用英文版,学生使用西班牙文版),我在那里做了一场题为"《逻辑哲学》,三十年后"的报告,解释我现在会如何撰写此书;而最近来自英国的一位法医科学家的电子邮件---回应我对指纹匹配软件工作原理的相关信息领域的研究人员名单的请求---问道:"你就是那位撰写了《逻辑哲学》的苏珊·哈克吗?"嗯,是的。
正如第二版《变异逻辑》的题目一样,《逻辑哲学》书名中复数的"逻辑"("logics")也有一段故事。在最后一章,我仔细厘清了有关逻辑的至关重要的形而上学和认识论问题,并给出了我的解决方法。在形而上学方面,我仔细阐述了对于全面多元论的一种尝试性辩护。在认识论方面,在同时期发表的论文《演绎的证成》中,我论证了如下一点:在试图证成归纳时会出现的那些臭名昭着的难题,也会以类似的方式出现在证成演绎的尝试中。
在《逻辑哲学》中还有很多其他内容:包括对逻辑、逻辑哲学和元逻辑进行区分的章节;有关有效性、命题联结词、量词、单称词项、真值承担者、真理论、悖论、模态逻辑和多值逻辑的章节。也许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对蒯因反对模态逻辑的论断,以及对塔斯基真理论的阐释.细致地清理塔斯基的理论及其哲学影响中纠缠不清的问题是一项艰辛的工作;然而,坦率地说,当时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了不起。但是现在,塔斯基通常被描述为符合论者、紧缩论者、去引号论者,或者被视为提出了一个有关命题的真理论,如此等等,我的阐释对于澄清问题而言似乎比当初所设想的做出了更为重要的贡献。
在意识到需要对我早期关于变异系统和扩充系统之间的对比区分做修正,以承认一些相干逻辑既是变异的又是扩充的之后,我对相干这一概念进行了认真思考;我开始认识到,它不是一个形式概念,而是一个实质概念。我现在料想,这会使相干逻辑形式化的希望破灭。这也会有助于解释为何库恩会得出一个被误解的想法---关于证据的质量标准是相对于范式而言的;此外,它阐明了相干的概念对证据法的重要性.
随着我的哲学兴趣的扩展,我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领域,撰写了有关认识论和科学哲学的书稿和大量论文,并在语言哲学、形而上学、社会哲学等领域发表论文;是的,甚至还发表了涉及伦理学领域---涉及道德研究(1996 年)、平权法案(1998 年)和学术伦理(2010 年)的论文。而且,如今我已经投入其他领域---其中最为显着的是法律领域。一些年以前,我开始致力于现在仍在开展的工作,涉及证据、证明、科学证言等问题,以及更为一般性的法哲学问题。但我并没有放弃对逻辑哲学的兴趣,例如,我写了有关真理的一系列论文;有关皮尔士与逻辑主义的论文;有关哲学的形式化方法的论文;以及被大量下载的关于逻辑(包括道义逻辑!)在法律中的地位的研究.
"真理"系列论文的开头两篇为真概念的合法性做了辩护,紧跟着的两篇阐明在真(truth)即那个现象与真理(truths)即特定的真实的断言、信念、命题等等之间的分别。虽然有很多真理,但是我认为,却只有一个真(概念);虽然有些真理是模糊的,但真并不是一个程度问题;虽然有些真理是因人们的行为而成为真的,但真理是客观的;虽然有些真理仅仅相对于地点、时间或裁决才有意义,但真理不是相对的;虽然一些命题只是部分地真实的,但真理不能分解成部分.1974 年,我已经表明,波斯特的非标准多值逻辑可用来在"P 的一部分为真"这一意义上表征部分真理;2008 年,我还探讨了"p 是部分为真","p 是真理的一部分"的其他意义.此外,1974 年,我撰写长篇论文讨论有关(我现在称为)有关精确度的逻辑概念;2008 年,我还探讨了有关精确度的诗学概念;同一年,我发表论文对科学中的真和法律中的真做比较,到 2010 年我已经准备好提出有关法律真理的正式阐释.
我对逻辑的范围及其限度的长盛不衰的兴趣近来开始取得新的成果。在《扞卫科学---在理性的范围内:在旧尊崇主义和新犬儒学派之间》一书中,我表明,无论是归纳论者、演绎论者或是概率论者所主张的科学推理的形式化逻辑模型都必然会失败,并论述了其原因;因为"绿蓝"悖论告诉我们,推理并不仅仅依赖于形式,而且依赖于科学词汇与现实世界的各种事物和材质之间的关系.在《论法律中的逻辑:"重点,而非全部"》中,我阐明形式化的逻辑模型也不足以把握法律推理,并论述了其原因;因为这些推理必然涉及到应用和采纳法律的概念,后者随社会、科技和生产等等而发展。并且,在《意义的生长与形式主义的限制》一文中,借助于皮尔士和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我发展了结合这两条论证线索的意义理论。
3.相对于其他学科和其他哲学分支而言,逻辑哲学本来的作用是什么?
正如我的回答将揭示的,我对"本来的作用"(the proper role)中隐含的独特性感到不安。
首先,我要对"逻辑"一词的两种用法或意义做出区分:广义上,它指称关于一切好的推理方式的理论("LOGIC");狭义上,它仅仅局限于好的推理在语法上可表征的方面("logic").按如此构想,广义逻辑包括狭义逻辑和逻辑哲学---正如人们在皮尔士的文章中所看到的那样。这种广义的概念也可以在(比如)杜威的《逻辑:探究的理论》中被发现.但在弗雷格的迄今仍有巨大影响的在狭义逻辑方面工作的影响下,这种狭义的概念占据主导地位。
正如杜威那本书的标题所暗示的那样,广义逻辑包括的范围很广,至少我们今天视作认识论、科学哲学等领域的很多东西都可以涵盖其中。但是,狭义逻辑与其他领域的关系问题则会迥然不同,且并非一目了然。
正如我在回答上一个问题的最后一段中所解释的那样,狭义逻辑远没有穷尽在科学中、在法律论证中,我现在还要补充说,在哲学中的推理能够说的一切。的确,哲学家偶尔也会犯形式逻辑错误。例如,我在《变异逻辑》中论证说,亚里士多德对未来的偶然事件要么真要么假的论断建立在模态谬误的基础之上;而且,如我在《证据和探究》中所论证的,戴维森表明我们的信念绝大多数为真的全知解释者的论证亦是如此.但更多的时候,以我的经验来看,哲学争论的问题很可能是如下因素的后果:未被注意到的模糊性,松散冗余的概念,站不住脚的二元论,虚假的预设,以及诸如此类。
如果逻辑主义是对于数学的可行说明,那么数学哲学将会是逻辑(狭义的)哲学的一个分支。但我并不认为逻辑主义是可行的。同样,如果自然种类词是严格指示词,那么至少科学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将会是逻辑(狭义的)哲学的一个分支。但我并不认为自然种类词是严格指示词;相反,我认为它们有意义,其意义还会随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的增长而生长.
我从未被说服去相信下面一点:形式逻辑工具对我们的自然语言理解提供了很多的帮助,而不是非常有限的帮助。"戴维森纲领"的崩溃表明,塔斯基的一贯坚持是正确的,他所提出的严格的形式化方法仅仅适用于雅致的形式化语言,并不适用于诸如英语或波兰语这样的自然语言.戴维森最终作出结论说,在他以及很多语言哲学家所假定的那种意义上,根本没有像语言这样的东西.我的看法是:我们一般所说的自然语言,可以看作是那些足够相似的个人习语的结合,至于何种相似才是"足够相似",则取决于我们手头上正在进行的工作.
4.什么是逻辑哲学领域最重要的进展?
我对这个问题有些疑惑:是要求我谈论逻辑哲学中曾经取得的最重大的进展,还是只谈新近的进展?显然,即使是勾勒亚里士多德、弗雷格或皮尔士所做重要成就的一部分,也远远超出我有时间去谈论的范围。而且,很可能在世界某个地方,有一个新皮尔士或新弗雷格,他们正在默默无闻地工作,他们的想法像皮尔士和弗雷格的一样具有开创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遗憾的是,我并不熟悉他或她的工作。
我所熟知的情况是,也是我担心的,逻辑哲学并没有与哲学的最新趋势背道而驰。就像在其他领域一样,它似乎越来越脱离它自身的历史,越来越支离破碎,越来越小集团化,越来越自我沉溺,并且越来越倾向于搁置一些悬而未决的老问题,而将注意力转移到新的时髦论题上。虽然我肯定其中也做了某些有价值的工作,但如今发表或出版的压力是如此严峻,大量的出版物堆积如山,人们几乎不可能从诸多糟粕中找到精华。尽管这样说,我在对下一个问题的回答的脚注中将提到一些我认为新近有前景的工作。
5.逻辑哲学中最重要的开放性问题是什么,其发展前景如何?
我对"最重要的"一词感到不适,就像我对"本来的作用"感到不适一样。首先,我会谈到在诸如真理、意义、模态和逻辑的基础之类的关键性问题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之后,我会列出一些论题,对这些论题我相信我们应该有比我们目前所有的更好的理解---毋庸置疑,在这个列表中,皮尔士占据突出地位。
(1)在《逻辑哲学》中(与同时期的其他人一样),我称拉姆塞的真理论为"冗余论".然而,由于目前能够读到拉姆塞有关真理的所有论文,很显然,拉姆塞并不认为"真"是冗余的,我更愿意称之为"简缩论"(laconicism).更重要的是,对拉姆塞的解释中悬而未决的一些问题的探究是很有价值的,其中涉及:是否对命题量词(如"对于一些 p 而言,柏拉图说了 p,并且 p")有合适的理解,该理解本身并不依赖于真概念;以及对语义悖论的一种详细的简缩论说明会是什么样子.
(2)如上一点所表明的,真理论的那些显着困难的一个推论是,我们还没有完全理解语义悖论的根源或者对其最恰当的回应。在这种情况下,我会提到皮尔士对我们现在称之为强化的说谎者悖论的值得关注的表征和诊断。皮尔士从两个并列的论题入手:一个是从前提"本命题不是真的"是真的,得到该命题非真的结论;另一个是从前提"本命题不是真的"不是真的,得到该命题为真的结论。皮尔士主张,其中每一步都是有效的;因此,问题的来源必定是它们所唯一共享的前提,"本命题所说的就是它不是真的".他认为,这一点是假的;相反,像其他每个命题一样,这个悖论性的前提也同样断定其自身为真.
(3)对强化的说谎者悖论的分析仅仅占据了皮尔士的早期论文《逻辑法则有效性的根据》中的几页。然而当时(1868),皮尔士使用的逻辑仍然是三段论逻辑,他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方法比后来出现的如约定论要复杂得多。特殊地说,对皮尔士提出的论证做更深入的思考;更一般地说,对悬而未决的逻辑的基础问题做进一步探究,都是值得欢迎的工作。
(4)当我想到皮尔士的时候,我还会提到,尽管现代模态逻辑起源于 C. I. 刘易斯的工作,但皮尔士在很久之前在其"伽马图"中表述了模态论证。或许因为他的图示记法在命题层次上非常直观,在量词层次上却相当复杂,在模态层次上则令人望而生畏,因此似乎很少有人探究皮尔士的模态逻辑研究;但对此的严肃研究可能证明是有价值的工作,就像对他在 1909 年的三值逻辑试验所做的考察所表明的那样.
(5)在《意义的生长》一文中对语言做动态探究的一个后果是:什么语句是分析的(或表达分析命题,如果你喜欢的话)是随时间而变化的。令人震惊吗?并非真的如此。在莎士比亚时代,"愚蠢的"("silly")意味着"单纯的"("simple")且"真实的"("sooth")---正如"说真话者"("soothsayer")中一样---意味着"真理"("truth"),"傻傻的真实就是单纯的真理",这句话如今几乎无意义,在当时却是分析语句。但我至今对这种时间相关性的后果仅有很不完整的理解;如果我们严肃地对待意义生长理论,我对关于命名的新描述论究竟会是什么样子也仅有很不完整的理解.这个列表不同寻常;但我说得已经够多了,超出了给我的篇幅,就此打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