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当代中国教育逻辑学研究走向实践的契机
时间:2018-11-26 来源:当代教育与文化 作者:张建鲲. 本文字数:8488字摘要:探寻教育活动的客观价值, 既是教育逻辑学研究的价值理性传统, 又反映了当代逻辑学走出传统形式逻辑的必然趋势。从促进“教育质量”的合理化出发, 为面向“服务满意度”与“公众满意度”的教与学的活动探求从纯粹价值理性走向实践技术理性的生成路径, 乃是推动当代中国教育逻辑学研究走向深入的实践论契机。要使得对“教育的当为”的把握走向价值理性与技术理性的统一, 人们需要在认识论的层面克服近代“教育活动”所舶来的极端国家主义倾向, 将“教”与“学”的价值生活领域作为今后教育逻辑学研究的核心范畴。
关键词:教育逻辑学; 价值理性; 技术理性; 教育质量; 核心范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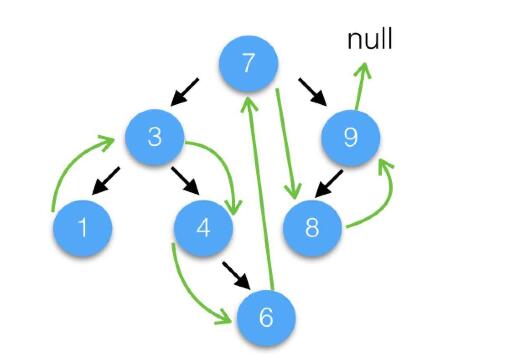
The Rationalization of Education Quality:Rationalized Mission of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Logic
ZHANG Jian-kun
College of Teacher Education,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Exploring objectively the value of education, on the one hand, is the academic convention of axiological rationale in educational logic;on the other hand, is an inevitable trend for contemporary logic shifting from traditional formal logic.Rationalizing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pursuing practical rationale from pure axiological rationale through both service-oriented and public-oriented teaching and learning provide a practical opportunity to deepen contemporary Chinese educational logic study.To achieve balance between axiological and practical rationale, excessive nationalism in epistemology borrowed from outside world in modern times should be abandoned, and the value of both “teaching”and “learning”be the core of hereafter educational logic study.
Keyword:
educational logic; axiological rationale; practical rationale; quality of education; core category;
就如同马克思对1846年英国《工厂法案》中“教育条款”的理性把握, 既表现为他从共产主义的社会哲学理想出发, 在“教育作为价值性活动”的层面坚决否认这种工艺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工人阶级“守你们的本分罢”。同时又表现为, 通过“工人阶级不可避免地夺得政权之后, 将会使工艺教育在工人学校内占有适当的位置”的前提性判断, 他对强制性工厂教育合理性成分给予了“教育作为技术性活动”层面的相对认同。[1]而1870年, 英国政府颁行的《初等教育法案》开始将包括童工在内的全国儿童纳入到国家教育体系中来, 则在“教育公平”的维度上充分印证了马克思这种辩证性的判断具有充分的逻辑合理性。
仅就当代中国教育逻辑学研究的发展而言, 伴随着“教育质量”的问题日显突出, 我们不仅应从明确教育事业质量标准与评价尺度的需要出发, 在对当前教育活动正在展现出哪些客观价值进行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理性追问中, 重建教育逻辑学研究的价值理性传统。为了帮助人们更趋理智地看待“教育质量”问题的理论实质、不断提高“教育质量”理论与实践的合理化水平, 我们还需要从破解知性思维在“事实命题”与“价值命题”之间的天然分野入手, 将对现有教育质量给予纯粹价值理性的去伪存真, 发展成为就今后教育质量的理想价值取向、核心评价尺度以及潜在生成路径, 形成实践技术理性的真知灼见。
一、教育逻辑学研究的价值理性传统与技术理性重建
国内普通逻辑学研究者指出, 由于事实与价值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异质性, “传统形式逻辑以超主体的、客观事实为处理对象”, 注定“走向无主体、必然性、静态化以及程式化”。[2]为此, 人们今后应当转向从“价值生活实践”入手, 着力推动逻辑学研究朝着实践性、主体性、具体性以及生成性的“价值逻辑”方向发展。其实早在1923年, 我国近代教育哲学家范寿康不仅曾经同是论者相向而行, 主张只有对教育的客观价值进行“超主观”的把握, 人们才能对“教育的当为”形成理性预期。他甚至还从“教育的形式价值不是反主观、而是超主观的———客观”出发, 认为对教育进行论理学 (“逻辑”最初引入中国之旧称) 的把握, 固然同人类试图在教育活动中进行真、善、美的追求有所关联, 但其直接关注的“教育的当为”不仅拥有相对独立的学科地位, 这种独立性更有可能构成了“教育学成立的根据”。[3]
不过, 就如同20世纪90年代, 我国当代教育学家瞿葆奎曾用“权且聊胜于无”来鼓励郭元祥承担起《教育逻辑学》一书的撰写。[4]虽然, 相比林熹等学者在20世纪80年出版的《教育逻辑》还只是从既有逻辑规则在教育中的运用出发, 试图探寻智育、美育、德育、教学以及教师语言等“教育活动的逻辑”。在2002年出版的《教育逻辑学》中, 郭元祥力图与英国分析教育哲学家赫斯特 (Hirst) 和皮特斯 (Peters) 在20世纪70年代开创的“教育思维的逻辑”相契合, 对国内外教育热点议题中的范畴、命题以及语言等给予追究。但由于刚刚从拨乱返正中恢复的国内教育事业还不足以在实践取向的多样性与价值生成的系统性上为教育逻辑学进行面向辩证逻辑和复杂性思维的方法论变革提供实践基础。历经长期沉寂的国内教育逻辑学研究, 仍未完全回归到面向教育实践、诠释“教育当为”的价值理性。
并且, 尽管不同于范寿康将“非从各种内容分别入手”才能有效应对“教育内容的种类繁多”作为其“无暇论及教育的内容价值”的直接理由。在2003年出版的《教育逻辑学引论》之中, 刘邦凡与何向东力图对数学、汉语、英语、物理等学科的“教学逻辑”进行广义模态逻辑的阐发, 这不失为在“教育作为技术性活动”的层面帮助人们对“教育的内容价值”给予理性把握的有益尝试。但是, 就如同斯宾塞发现, 随着“所有领域中的知识都曾被人们偶然性地评价为重要”, 人们即使尝试追问“花这些时间获得相应重要程度的知识是否值得、是否可以把这些时间转投到某些更重要的事情”, 其答案也总是“依据个体偏见”做出。[5]由于两位学者的“应用教育逻辑学”其实是以“有所价值” (即斯宾塞所指的“半内在价值”) 的各学科知识为逻辑起点, 对“智育当为”进行技术理性把握。这种并未完全超越近代哲学“知识论”中心的“教学逻辑”研究, [6]固然有必要成为人们推动教师教学行为合理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就教育“为人”与“人为”之间的伦理秩序而言, 基于知性思维的“教育实践技术”显然不应在“教育的当为”意义上, 对人们进行“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的价值理性追问构成某种僭越。
于是, 范寿康以“所有人类都想将他们的文化生活来永久化及伟大化”为起点, 力图在“教育与文化生活”的命题方式中阐发“教育的形式价值”具有自在性, 这固然对我们超越当代教育理论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教育目的价值取向二元对立, 走向在个体、社会与“文化”的复杂性维度中辩证看待教育的客观价值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是, 从其仅凭“教育的形式价值”具有自在性, 声称“将教育看作社会生活的预备手段, 实在是谬误的意见”, 我们却可发现:由于不理解“教育的当为”乃是价值理性命题与实践技术理性命题的辩证统一, 范寿康其实只是将教育价值取向二元对立的基本范畴设定成了“社会”与“文化”。
而事实上, 正是从更具个体关照的“学习与全部生活”命题出发, 斯宾塞才在“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的问题上拥有了“有限学习时间”的个体性起点与“我们怎样生活”的社会性终点。继而将在《社会静力学》一书中对“国家教育”和公共学校依靠家庭强制税负供养有违社会公正的价值理性质疑, [7]发展成为在实践技术理性的层面上, 将“为完整生活做准备的程度”作为评判“教育的内容价值”与生成“自觉教育”的价值理性尺度。这样看来, 走出知性思维在“事实命题”与“价值命题”之间的天然分野, 乃是包括教育逻辑学在内, 逻辑学研究将辩证思维方法转化成对人类实践给予理性把握的必由之路。
另外, 针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辩证逻辑”, 列宁评价道:“他不是证明了, 而是天才地猜测到了逻辑形式和逻辑规律不是空洞的外壳, 而是客观世界的反映。”[8]而对照列宁藉此提出的认识论、辩证法与逻辑三者统一的基本原理不难发现:随着在“教育与文化生活”的命题方式下声称“人类生来就具有尊重教育的倾向”, 范寿康也就在将康德唯心主义的“绝对理念”作为认识论前提的同时, 忽视了越是试图对“教育的当为”给予理性把握, 越是要从绝对理念化的教育范畴走向对“教育实践”的价值主体性、现实生成性、文化差异性进行辩证考察。而为了切实推动教育逻辑学研究走向价值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统一, 我们则应对当代教育逻辑学的核心研究范畴进行面向辩证思维的认识论改造。
二、当代教育逻辑学研究的实践论契机
鉴于“仅以旁观之态度”归纳和演绎世事的“形式论理学”存在着“以吾人理智仅有记录之用, 不能兴于创造之事业”的严重弊害, 我国近代教育家刘经庶还曾从改造“以古人所诏为天经地义”的保守国民性格出发, 倡导国人应当学习杜威的“试验论理学”。[9]相应的, 虽然从教与学的活动在学校教育中的基础性地位看, 我们既有理由针对近年来高等学校招生规模的急速增长, 将“本科教学质量评估”作为监控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核心手段;又有必要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面临的课堂教学瓶颈出发, 将强调对于既定课程标准达成程度的“有效教学”作为追究中小学教育质量的直接取向。
但是, 正如杜威从断言“科学注重使知识的逻辑内涵成为现实”出发, 将逻辑学与心理学视为人们推动课程科学发展的基本方法。[10]如果我们从教育“为人”与“人为”的基本属性出发, 将探问教育存在与发展的广义教育科学, 分别视作在纯粹价值理性的路径中超越现实以便追求教育应然性价值的“教育哲学”、以及在实践技术理性的路径中切近现实进而追究教育实然质量的狭义“教育科学”。那么, 既然将研究论域深耕于“学”与“教”的心理与行为机制的“教育心理学”研究既直接促进了实验取向的狭义教育科学在人类社会工业化进程中的蓬勃发展, 又在全面认识学习行为的社会性、教学过程的生成性以及教育价值的主体性等方面, 对采取哲学人类学范式的教育研究者们积极关注学与教的感性成分助力良多。在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的当代, 我们同样有必要将当前教育科学层面的“如何达成教育质量”与教育哲学层面的“什么是教育质量”, 视为推动教育逻辑学研究从价值理性走向技术理性的实践论契机。也就是说, 我们不仅需要通过对“教育质量是什么”的逻辑学问题给予纯粹价值理性的追问, 继续克服实证主义教育科学“不问价值”的工具理性态度。我们还需要针对教育哲学研究“不对任何行为和举动发挥任何影响”的知性思维悖论, 将促进“教育质量命题的合理化”作为当代教育逻辑学研究逐步走向实践技术理性的理论生长点。
相应的, 或许是由于对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片面解读, 使我们轻视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在获得教育真知与谋求教育道理上的基础性地位。面对着社会各界对“教育质量”的关切, 当前的国内教育理论显然更热衷于对“如何达成教育质量”的科学问题与“什么是教育质量”的哲学问题表达见解。至于“教育质量是什么”的逻辑学问题, 即便是出于确保教育理论周延性的考虑对其偶有触及, “教育质量”的逻辑根源往往也只是被抽象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教育事业正在发生从数量与规模化发展到质量与内涵建设的形式逻辑转换。
问题在于, 尽管就形式逻辑而言, 当前国内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所追求的“教育质量”, 似乎的确是与此前以义务教育普及化和高等教育大众化为主要动力的“教育数量”发展, 分别从属于“数量”与“性质”这两个相对独立的范畴。但其实, 将教育数量与教育质量置于形式逻辑上的二元对立, 这恰恰是对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某种背离。因为, 只需稍加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历程便不难发现:国人对“教育质量” (quality of education) 的追求不仅可以在“性质”的范畴上追溯于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 人们对承载着个体人格质量的“素质教育” (quality-based education) 给予了热切的希冀。即便仅从“数量”的范畴看, 我们其实也曾学校数量、教师总量、高校学科专业数量、各级学校适龄入学率、在校生规模等“教育数量”的显著成就, 隐喻成当代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总体质量。
然而, 就如同胡适先生指出:“哲学的发展决定于逻辑方法的发展”。[11]不同于受到国内舆论迫切关注的升学率、就业率、大学生薪酬等“成本—收益”取向的教育质量既存在着确定性与客观性的优势, 却也面临着有学者以“谁的教育质量”的价值理性设问, 质疑我们对教育价值的主体性问题有失关照。[12]从美国高质量教育委员会宣称“并不相信致力于教育高质量和进行教育改革, 就必须牺牲公众的强烈要求”, 我们可以发现:由于是将更具世俗性色彩的“生活质量”作为逻辑起点, 国外学者们眼中的“教育质量”不仅更具价值主体关怀, 还表现为学生、家庭、社会公众、学科专家以及产业精英们的“教育满意度”。随着将知性的教育理论与主体的感性成分紧密结合, 进而在差异化和动态化的统计权重下全面分析教育的“服务满意度”和“公众满意度”矛盾, 这种在感性、知性与理性的结合中最终落实“生活幸福指数”的教育质量, 无疑也就更为充分体现了纯粹价值理性与实践技术理性的统一。
这样看来, 既然就教育“为人”的核心价值属性而言, “教育质量”问题受到中国社会集中关注的根源在于, 本土教育实践价值取向的多样化、评价尺度的复杂化、现实生成的系统化。那么, 由于在已被唯物辩证法确证为完全可以诉诸于人类价值实践活动的“辩证逻辑”中, 所谓的“教育质量”乃是人们通过以质量互变规律把握文化传承与个体生成的某些价值之量和关键尺度, 解释教与学的对话实践的发展规律。随着“办让人民满意的教育”日益成为当代中国对于自身教育事业的核心价值诉求, 不论偏重学校教育机构及其专业技术视野的课程标准、有效教学以及教学质量评估, 还是更具社会公共产品收益取向的各级教育入学率、第三级教育就业率、毕业生专业与岗位对口率, 这些“教育质量”无疑只是衡量当前教育活动客观价值的现实尺度。而当代中国教育逻辑学研究走向深入的实践论契机, 也就在于从促进“教育质量”在客观价值尺度上的合理化出发, 为本土教育事业既在提升专业服务水平的意义上走向学习者及其家庭的“服务满意度”、又在创造社会人力资源财富的属性上切近利益相关者的“公众满意度”, 探索融教育主体感性、教育理论知性与教育价值理性于一身的、教与学的活动的实践技术理性生成路径。
三、本土教育逻辑学研究的认识论变革
尽管, 每每谈及“教育”的内涵, 国内的相关专著、教材和学者们都时常会提及《孟子·尽心上》中的“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然而, 正如有学者在教学理论的形式逻辑问题与教育活动的本土文化属性之间建立联系, 认为建立独有的话语体系、避免带有异国口音, 是人们“以一种理性的精神从事教学理论研究”的必然要求。[13]要在价值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统一中对“教育的当为”给予更趋理智的把握, 对于既符合近现代人类学习活动的普遍发展趋势、又反映本土历史与文化特殊性的“教育”范畴, 我们还需更为切近地追溯于张之洞在《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学折》中指出的“考日本教育总义, 以德育、智育、体育为三大端, 洵为体用兼赅, 先后有序, 礼失求野, 诚足为我前事之师。”
毋庸置疑, 就增强此前“壬寅学制”的严密性与可操作性而言, 张百熙和荣庆两位管学大臣, 的确邀请到了当时“第一通晓学务之人”的张之洞来完善“学制”。而随着以往仅在“抡才取仕”环节才对个体学习质量进行检视的封建“科举学制”, 最终让位于“癸卯学制”系统化和政府导向性日盛的“教育体制”, 清末通过模仿军国主义日本确立的、更具公共产品特征的“学堂教育”也的确是在教育价值生成的实体性机构问题上, 解决了以往书院和家塾中过于自由的“个体学术”活动对于所谓“强国兴学”构成的客观阻碍。
但是, 明显区别于张之洞还曾在《劝学篇》中用“学术造人才, 人才维国势”来诠释“兴学”的学术性价值取向。由于明治维新时期的近代日本其实是将“于危机之际, 勇敢为国献身”, 作为其“军国民教育”对于人的培养与发展的基本价值诉求。在引入了“教育”这个舶来的社会活动范畴之后, 国人的“学习”时空固然是更多地转向了官办学堂的活动情境。但“兴学”的最初价值寄望也在某种程度上从更具知识创造取向和文化本体意蕴的“学术”与“学科”, 弱化成了在“富国强兵”的国家主义教育寄望中“办教育”所更加热衷于的“说教”和“训育”。
当然, 回顾近代中国“教育”的舶来品属性和军国民情结, 这绝非是要对“公共学校教育”的形式或者“教育中的国家主义”理念给予全盘否定。[14]只不过, 如果我们将清末“兴学术”与当代“办教育”的价值诉求视为从“中学与西学”、到“旧学与新学”、再到“求功名与务实学”的教育目的价值取向进化。那么, 这里的公共学堂与学校“教育”其实只是在学习内容上对“新学”与“实科”给予了价值认同。[15]至于将“新学”中求真务实与知识创新的学术理想视作“教育的文化功能”、将“实学”对人的生计、生活以至生命所担负的客观价值务实为“教育的个体功能”, 同样急于“维护皇室基业之繁荣地久天长”的清末学制改革, 显然还无暇在“民富国强”的中国传统政治理想中对这些予以考虑。
并且, 随着极端国家主义的“教育活动”遮蔽了人们的价值理性, 公共学校教育对于文化与个体所承担的价值“公能”, 也就时常被我们在技术论的层面打入“教育当为”的另册。作为对中华民族传统学术理想的某种回归, 国务院在2010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中提出, 我们应当将注重“学思结合、知行统一、因材施教”作为教育教学方法改革和人才培养体制创新的指导思想。然而, 尽管早在1928年的《大学院公报〈发刊词〉》中蔡元培就曾指出:“民国纪元以前, 管理学术及教育之机关曰学部。民国元年改为教育部。依教育一词之广义, 亦可包学术也”。但从我们前期调研的情况来看, 相比与西方国家的“差异化学习”存在着明显的实践技术性契合, 造成了我们对“因材施教”更为普遍的价值认同。由于主要是在价值论的层面上契合于当代教育文化创新功能的日趋强化, “学思结合”的本土文化传统不仅尚未转化成为中小学教师对于“研究性学习”与“启发式教学”的专业技术认同。即便是在日益重视学术研究工作的国内高校, 将科技与文化知识创新视作自身本体性职能的“从容学术”, 也依然要靠我们的科研管理部门给予专项支持、靠新闻媒体给予大力宣传。[16]至于从“增强学生科学实验、生产实习和技能实训的成效”出发, 将最初基于道德教育的“知行统一”, 发展成为开发面向生产劳动与社会实践的现代活动课程。我们与其像20世纪90年代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那样, 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亚洲国家总是忽视技术和职业教育, 看似深远、实则抽象而无能为力地归咎于“轻视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和商业”的社会价值观和本土文化传统。[17]不如从更为具体的“教育价值观”入手, 将陶行知的平民教育、黄炎培的职业教育、世纪初的高等职业教育、近年来的研究生专业教育总是被我们在“另一种类型的某某教育”的技术路径下艰难推进, 归结为本土“教”与“学”的社会实践活动在近代舶来的、极端国家主义的价值倾向, 遮蔽了我们从教育的个体价值维度出发, 将这些“另类教育”视作各级学校教育为人的生存、生计以及生活服务的职业准备功能。
继而, 正如自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世纪60年代提倡将“学习化社会”作为今后教育世界发展的核心取向以来, [18]便不断有西方学者通过“职业学校的谬误 (Vocational School Fallacy) ”“过度教育 (over-educated) ”“非学校教育 (nonschool education) ”以及“去学校社会 (de-school society) ”的证伪性命题, 提醒人们理性看待学校教育的实际价值、探求更为合理的教与学的价值实践。虽然陶行知将教育与生活的关系描述为彼此分离的第一时期、“教育即生活”和“学校即社会”的社会化时期、“生活即教育”和“社会即学校”的创造教育时期。[19]但既然, 教育心理学研究曾在“学校社会化”的20世纪初叶经历了从既有心理学理论在教育中的简单应用, 转向对“学”与“教”的心理与行为机制进行全面阐释的重大变革。而出于对这种认识论转换的认同与遵从, 国内外的很多学者都将教育心理学也同时称之为“学与教的心理学”。那么, 鉴于“创造教育”的当代教育世界正日益呈现出某种“既建构学习化社会、又走出学校化学习”的价值辩证性, 为了明确和规范今后教育逻辑学研究的核心认识范畴, 我们有必要面向“教”与“学”的生活领域在教育价值实践中的基础性地位, 将致力于对教育事业的存在与发展给予从纯粹价值理性到实践技术理性把握的教育逻辑学研究, 同时也称之为“学与教的实践逻辑”。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 (第一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5:526-527.
[2]孙伟平.逻辑学的革命:从形式逻辑到价值逻辑[J].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1, (5) :111-116.
[3]范寿康.教育哲学大纲[M].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3:20.
[4]郭元祥.教育逻辑学[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2:314.
[5]斯宾塞.斯宾塞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5:14.
[6]高伟.知识论批判:一种教育哲学的反思[J].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2, (4) :95-99.
[8]斯宾塞.社会静力学[M].张雄武,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176.
[9]列宁.列宁全集 (第55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0:151.
[10]刘经庶.杜威之论理学[J].新教育, 1919, (3) :15-18.
[11]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237.
[12]胡适.先秦名学史[M].北京:学林出版社, 1983:4.
[13]周作宇.论教育质量观[J].教育科学研究, 2010 (12) :27-32.
[14]王兆璟.教学理论研究的“知识传统”[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 2004:75.
[15]石中英.20世纪教育中的国家主义:回顾与讨论[J].教育学报, 2011, (6) :3:13.
[16]于洪波.日本近代国家主义教育体制的发展理念[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3 (4) :102-105.
[17]刘建军.后期资助项目让我的研究更为从容和踏实[N].光明日报, 2011-02-16 (11) .
[18]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财富蕴藏其中[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6:237.
[19]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与明天[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6:206.
[20]陶行知.生活即教育[M]//陶行知教育名篇精选.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6:177.
- 相关内容推荐
- 探究当代教育逻辑学的价值和趋势2018-07-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