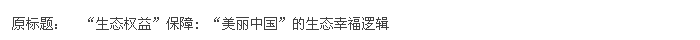
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西方先发现代化国家的有识之士就开始对以片面追求物质财富增长( GDP) 为主要标志的以发展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进行全面的反思,其反思的最主要结果,就是孕育、催生了生态理性、生态价值观以及总体性意义上的生态文明观的出场。
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以及愈加严峻的生态问题,国人逐渐意识到,社会经济发展的真正目的与最终意义在于使人类获得更加健康、幸福的生活,其中,生态与环境质量关系亿万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国民获得、拥有并持续性地享有幸福生活和幸福感的前提条件。
十八大报告首提美丽中国,美丽中国被赋予了新的内涵,蕴藏着多层寓意,发人深省、令人惊喜。以现代生态文明的立场做理论和实践观照,我们认为,美丽中国的背后,或者其底色,不是别的,是全体中国民众生态权益意识觉醒的体现,是生态中国和谐发展的生态幸福追求的美好价值理想。
一美丽中国呼唤社会共同体之生态权益的保障实践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刚刚开始实施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与国民幸福体验之间的关联性问题已经引起了国外学者的普遍关注。1990年荷兰伊拉斯漠大学对中国国民的幸福感进行了第一次调查,以1一10为标度,当时的国民幸福指数为6. 64,这一数据在五年后发生了变化,1995年调查数据上升到7. 08,可见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国民的普遍幸福感处于上升期;2000年以后又转入下降期;在2001年的调查中,数据为6. 60,而美国密歇根大学公布的幸福调查数据显示,到2009年12月,中国人的幸福感持续下降,现在的中国人远没有10年前。
究其原因,归结于现代化的城市问题的涌现。城市是人类社会文明的符号和集中体现,城市的生活曾经是富裕、和谐、文明、优雅的象征,令人向往。但是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随着现代化的全球推进,随着世界范围内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逐渐成了一个问题的场所,各种城市病不断出现,城市居民的幸福感不断下降。
就中国社会而言,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实践的三十年历程,社会转型的加速,同样的问题开始出现。从2003年开始,中国官方每年都要进行全国范围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的评选活动。评选的结果,杭州(被称之为品质生活之城)、珠海(被称之为花园城市,中国十大最有幸福感城市等)、长春(一直被誉为北国春城)等城市屡次名列前茅。这些并非经济最发达城市的入选,引发我们的思考,虽然城市居民的幸福感与城市经济发展有正相关意义,但绝不是惟一决定因素,而带给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实质是一种更优美、更安全的自然环境和更便利、更和谐的生活氛围。可见,人类社会的发展目标是求生存求幸福,而经济的发展只是达成这一目标的手段。社会发展的目标驱动更应该关注社会总体主观幸福感的增长状况2007年1月15日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发布《中国公众环保民生指数(2006) 》,调查数据显示,86%的公众认同环境污染对现代人的健康构成了很大威胁,影响了自己的幸福生活,另外有39%的认为环境污染给本人和家人健康造成了很大影响或较大影响因所有这些事实都表明,社会经济主体的生态权益的保障和实现问题与其幸福感的有无、大小呈正相关。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随着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和实践的崛起与不断深入,人类对拥有一个美好的生存与生活环境的吁求愈来愈强烈。这就涉及与当代人的生态幸福追求密切相关、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构成其前提的生态权益问题。生态权益在法学界被界定为环境权利,简称环境权,是一项以环境为客体的权利,对环境权的侵害也往往是通过改变环境而影响人的身心健康。一般认为,公民环境权是指公民享有现有的环境受到保护,使之不被破坏,以及在某些情况下使环境得到改善的并在不被污染和破坏的环境中生存及利用环境资源的权利。
法律体现的是人性的尊严,是普遍的国民的福社的保障。在现代法律思想史的意义上,环境权主要是本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性环境危机和环境保护运动的产物。从国际范围和历史角度看,环境权的观念和运动主要发端于美、日、欧等工业发达国家和地区,并在20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形成了两次理论研究和立法的高潮,20世纪70年代,随着工业污染危害的日益凸显,各国在环境立法的问题上出现转机,美国一些州的法律环境保护纳入到公共信托理论的保护范围。1970年,密执安州的《环境保护法》的第2节第1条规定,把空气、水体和其他自然资源列入公共信托原则所保护的物质客体的范围;宾夕法尼亚州宪法中则明确声明:人民享有对于清洁空气、纯净水和保存环境的自然的、景观的、历史的和美学的价值的权利。
宾夕法尼亚州的公共自然资源是全体人民包括其后代的共同财产。作为这些财产的受托管理人,州政府必须为全体人民的利益而保护和保持它们,在亚洲旧本的环境立法也经历了一个自下而上的推动过程。早在1902年,日本着名学者宫崎民藏就在其发表的《人类的大权》一文中提出,地球为人类所共有、为天下生成的全人类所共有的主张。由于学者的集体性努力与呼吁,环境权逐渐在各主要发达国家的学术界得到认可,也促进了环境权益在立法部门的法律确认和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贯彻。
其中,1969年颁布的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和日本《东京都防止公害条例》,在这些法律条文中都出现了关于环境权益保护的内容。1972年6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会议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提出:人类环境的两个方面,即天然和人为的两个方面,对于人类的幸福和对于享受基本人权,甚至生存权利本身,都是必不可缺少的,同时基于人类对子孙后代的基本生态责任,宣言同时指出,人类有在过尊严和幸福生活的环境中享受自由、平等和适当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护和改善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
二、生态权益保障基础上的生态安全是美丽中国的充分必要前提
现代人的生存,本质上是一种非安全性生存。人们的生存与生活不断遭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威胁,而首当其冲的,是生态环境的安全回身处多重艰难困境中的现代人,需要在文明的新起点卜开始新的精袖成长与人性亨归的压程牛杰圭福理念和实践正是这场伟大的复归运动的惟一合理根基和可靠支点。生态幸福作为幸福观的当代形态,致力于恢复属人之真实幸福的生态位,澄明此种幸福的总体性意义上的生态本体性前提。在具体的实践中,该观念推崇以包括人在内的生物多样性生态幸福状态的是否达成作为评判人类一切活动之合理性和确当性的惟一刚性新尺度。换言之,生态幸福尺度旨在超越以往评价人类进步的历史性尺度( 实质上是生产尺度) 和价值性尺度( 实质上是人的自由和发展尺度) 的诸多弊端,着力彰显生态系时代人类历史的新伦理文化意蕴,是当代以及未来人类生存之道德秩序赖以形成和确立的价值新向标,已经引起并将在更大范围、更大意义上引起人类生存和生活方式的深刻、根本而持久性的革命性变革。
毫无疑问,人的安全性生存的基础是其周围的生存环境,但是,自工业革命以来,环境的被破坏已经到了威胁人的生存条件的底线的地步。环境污染指由于人为的因素,污染物质进入环境,使自然环境的组成、状态发生了变化,结构、功能遭到破坏,引起环境质量恶化,生态系统破坏和对人类生产、生活产生危害的现象。
人类生存质量和身体健康状况的下降是环境污染所带来的最直接、最容易被人所感受的后果,例如空气污染或水污染( 特别是饮用水的污染) 所带来的发病率上升、胎儿早产或畸形,等等。已有专家研究证明,目前我国75% 的慢性病与生产和生活中的废弃物污染有关,癌症患者的 70% ~80%与环境污染有关。特别是随着人们的生态意识和环境保护意识的不断加强,面对生活环境遭受严重污染或潜在威胁时,一些群体性事件的爆发开始在各地显现,越来越受到各方的关注。环境污染已经不仅仅是危害人民的身体健康,更带来了严峻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形成了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国民的和谐、幸福的生活更是无从谈起。
身处后发展时代,全球社会范围内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政府开始认识到,创造条件,加大投入,以技术和政策保障的方式为民众提供优美、健康的生存与生活环境,其实就是最大的民生。现代社会的基本生态文化共识是: 环境状况直接决定着人的生存质量,直接影响着普通民众的幸福感体验的程度。湛蓝的天空,清新的空气,新鲜而干净的蔬菜、瓜果,宜人的气候,安静的环境,富饶而适宜耕种的土地,生机勃勃的树木花草,鸟语花香的世界……这是每个人都期望拥有和享有的。
三、生态幸福是真实的生态权益和生态安全的实现状态
围绕幸福概念,从古到今—直争论,大致可以归结为两派: 快乐论与德性完善论。快乐论的主要代表在中国有杨朱及道家的某些支派,在西方有穆勒、休谟、霍布斯等; 德性完善论的代表在中国主要是儒家,在西方有亚里士多德、柏拉图、阿奎那等。快乐论认为幸福即快乐; 德性完善论认为幸福即自我完善、自我实现、自我成就,是自我潜能的完满实现。两派观点分歧的根源主要在于幸福的结构和类型的不同理解。
与本文的主题相结合,我们需要反思的是这样一个问题: 在追问幸福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总是以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为立场的? 反思的结果表明,幸福的涵义被做了基于牺牲和忽略生态意义上以财富占有和人类为主体的享乐意义上的非常狭隘的理解和使用。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导致我们忽视了其中一个最为简单的道理: 没有良好的生态为基础,一切幸福都只能是暂时的、难以长久的。具体而言,以往关于幸福的理解,实际上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 真实的、具体的、实在可触的幸福生活的最重要的基础———生态。宇宙间的万事万物之存在,本质上是一种基于系统性要素整体的生态性存在。同样道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幸福作为一个总体性概念,本质上是关涉生态的。生态性存在同样是人类幸福的根本,真正的、真实的幸福应该是一种生态性状态的确立与达成。
现代社会酷烈的生存环境与生活情景,使愈来愈多的人们逐渐深刻地认识到: 属人的幸福以及人属的幸福本质上理应是一个有机整体。既然幸福是社会与个体生活的美满圆融状态,那么,生态性生存境界就是通达这种幸福理想的最为合理的通道。生态幸福的观念是要申明,符合生态的生活,才是可欲的幸福的生活。属人的幸福,一定是基于、并同时为了一种优良的生态整体的,换言之,优良的生态整体意义上的幸福的获得,才是可理解、可追求的幸福生活和幸福体验本身。属于人类的幸福,仅以人类文化与制度系统为参照是难以得到自洽和自足性证明的,此处所谓生态是关涉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关联的。
在幸福问题的理解和诠释上,生态维度的切入,意味着人类必须承认和重视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的永久性关联,意味着人类必须承认并保护、完善和实现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现代生态学的研究成果表明,生态系统关涉人类的全部福祉。在这个意义上说,属人的幸福一定是生态的,是生态幸福,一点也不过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提供给人类的价值是巨大的。事实上,远在在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这一科学术语明确提出来以前,人们就已经在长期的生产活动中逐渐认识到自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然而,启蒙运动以来,人类高举科学理性和自由的旗帜,改造自然的获得越来越密集、工业和土地开发越来越快速,新能源、新化学药品的使用导致了高污染型的产业发展,造成了农田、森林、草原和湿地的生态遭到严重破坏。
自上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的一个非常严峻的社会问题是: 自然生态非安全现实已成了一个客观的显在的事实( 实际上,除了自然生态以外,社会生态和精神文化生态的失衡和危机也变得越来越突出,这是另外两个相关的问题) 。生态环境的被持续不断地破坏,已经使一代中国民众忧心忡忡。不仅其健康,而且其精神和心理都难逃厄运。
生态非安全现实主要表现在包括不可再生资源的迅速枯竭( 不可再生资源主要指经过漫长的地质年代形成的矿物能源和其他矿物资源) ; 由于物质生产的持续高速发展和破坏性的开发利用使可重复利用资源迅速贬值;伴随着森林尤其是天然林的破坏和生物多样性的逐渐消失,可再生资源锐减; 包括酸雨沉降、有毒化学品污染、海洋污染、臭氧层破坏等环境污染现象日益严重等。而所有这些问题,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中普遍存在,甚至日益严重。
发展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但需要选择一个可持续的发展模式。经济增长创造了财富,但不一定使人们更幸福。
怎样才能使经济增长与人们的幸福感具有一致性? 如何核算经济增长引起的财富损失? 当前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绿色经济、低碳经济、生态经济与可持续发展和人类幸福是什么关系? 怎样评价我们的幸福? 财富与幸福是什么关系? 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社会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富裕起来的一代中国人的生存和生活观念开始出现了非常重要的变化。有人做出了这样的概括: 从养生到养心,从纵情到怡情。我们的这个时代就处在这一拐点上。无论你是否意识到,人类对自然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从掠夺转为感恩,从征服变为敬畏,彼此如同一对恋人在交往与对话中,寻找一种微妙甚或美妙的平衡感。有关生态幸福的感受,其实很直接、很切身、很真切,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体验和感悟。的确,当人以赤子般的心情对待养育自己的大自然的时候,一种敬意和敬畏必然油然而生。富裕起来的一代人开始用心打量和思考自己与自然的关系,上水怡情———为什么大漠的壮美会让我们胸中涌动豪情,为什么大地上的田园艺术会让我们感动天地的神奇,为什么那一座座耸立的山峰,会让我们折服上天的造化? 或许那仅仅因为我们在与自然对话时,听到了内心里自己呢喃的声音: 幸福其实很简单,就是心里的那一点点欢喜,世界其实很丰盛,就是那在早晨的阳光中,响起的花开的声音。
事实上,进入生态幸福话语本身视野中的生态本身一直是建立在发展主义或进步主义这一线性思维下的一个反思性实践。所以,20 世纪以来,生态学为什么突然兴起? 这与西方左派对于现代性及全球化的反思是息息相关的。在人类学、伦理学意义上,强调生态的目的是为了回到本土化、在地化、自然化的生存空间。因此,实际上生态本身还有着保守的一面。生态在中国,一方面有我们自身的历史渊源,有我们自身对于自我生存空间的自觉与反思; 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回避西方意识形态在中国所面临的困境,包括社区、社群,在西方,它有一个前提和底色,就是自由主义( 价值取向上的个人主义、生活方式上的消费主义信念均源于此) 。我们认为,站在人类文明的新起点上,作为一种理念,生态幸福无疑是传统幸福文化的现代表达,它汲取了以往幸福观念的合理因素,辩证地扬弃了其不足,力图实现幸福观念的现代超越。
在生态幸福的理论范式里,幸福是人格信念的高超境界,代表了人在宇宙、生命和社会秩序中的不同位置应有的修养成就,这就为契合西方的真理或称契合东方文化的道提供了可能,但与后者的不同点在于使人的出发点和终极目标产生不同的道路和表达。幸福满足指我们存在的完备和生命的完美运动,其深层含义在于,幸福也就是人格及其生态的上升与满足。这一识见要求我们对幸福的理解必须完全深入到人和环境协调的发展当中去。
人在人格及其生态的上升与满足过程当中,有一个基本的观念甚至是能力,那就是要让人的环境在维护生态平衡的状态下保持自然的上升。人格及其生态的上升与满足的识见将人的肉身、精神、灵魂及其依托进行整体净化,并与社会的真理结合起来,是人类对幸福理解上的价值新向标。
生态幸福的语义所指以及语用学意义,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就生态学与生物学意义上的生态指涉生物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而言,所谓生态幸福一定是作为认识和实践主体的人对自身与生态环境之间复杂的关系样态进行评价的结果,因为生态本身无所谓幸福或者非幸福。
其二,生态幸福是环境对人的生存和活动正向影响的最大公约数。作为一种评价性结果———价值认识,即所谓生态是指生物体之间的一种和谐美好的存在和有机整体关系状态而言,生态幸福一定是属人的,是指文明发展的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社会文化共同体中,人依据自身的生存和生活经验,从对人类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前景展望和理性预期的立场,通过对自身生存环境进行综合认知的结果。这种认知的结果启示我们,人的真正的、真实的幸福系于环境本身,人的幸福感和幸福体验离不开特定的生存环境。因此,人不仅要改造环境,更要适应环境、维护和不断改善环境。
其三,生态幸福话语实践的合理性表明,生态是幸福的本体。生态性存在是社会演化和人自身发展的高级状态,是人属的以及属人的对象世界存在的本真状态。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属人的幸福事实上是一种趋生态性存在、拟生态性存在,并最终实现准生态性存在的理论真趣和生活目标。
其四,生态幸福追求整个地球和人的生存本身的全安全性、合宜性,并认为一切制度安排都应该遵从生态幸福的实现规律,并以此为内在规约,反思、调整甚或重新设计人的存在的方式。
科技和人文的进步、经济的增长、社会的发展,都要以保护人与自然长久的和谐为目的。和谐的价值取向能引导人们以亲近、同情、爱护的态度对待大自然。正忙于现代化建设的中国,应当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与自然相和谐、相融合的思想资源,以免我们陷入物质的陷阱。我们在肯定自然的价值的同时,要妥当地处理经济发展与利用资源、保护环境的关系,使其得到和谐的发展。这就是幸福的自然生态观,能制造幸福、创造最完善幸福的自然生态观。由此,我们对于生态幸福的内涵,有了新的理解和界定。
1. 追求幸福是人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这种权利的实现是有前提的,必须得到社会的保障。西方文化认为,幸福感的获得是社会进步和个人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英美和欧洲的国民健康生活指标、日本的国民福祉指标等涉及对民众生存与生活环境的改善。联合国所制定人类发展指数中,其中有两项指标都与人们生存与生活环境的质量有关。
2. 良好的生态是属人的以及人属的幸福 ( 生存与生活) 的根本。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被剥夺了与自然之间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的现代人,是一个生活在失乐园中的流浪者,谈不上所谓生态幸福。从此处所谓生态,首先是自然生态,其次还包括优良的社会和文化生态。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人,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正如生命权、发展权和自由权等是神圣的、不刻剥夺的一样,生态权利以及生态权益同样是个人和社会幸福生活的基础和重要内容。很难想像,一个生态极其恶劣、根本不适合人居的社会共同体,有所谓真正的、真实的幸福可言。
3.生态幸福是最基本的、最重要的民生,对生态幸福的追求,包涵、寄寓着民生的深蕴、精义,是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民生问题理论和实践转向的普遍的国民福祉的目标、方向和最终的落脚点。实现生态的幸福,是当代中国社会民生新政的应有之义。生态幸福的提出和实践,表明正在享受着现代化的成果和惨痛代价的中国社会,正在告别传统的对 GDP 的迷恋,而果断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向对国民生活品质、生存的体面和尊严感、责任意识以及健康的生活方式的向往。在这个意义上,生态幸福应该成为衡量民生改善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指标。
4. 生态非幸福是绿色生态劳动严重缺失的结果。传统的劳动实践观,本质上是一种主体单方面征服、改造和支配客体的活动形式,它所造就的是一个占有性的主体,导致了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紧张以及生存的非安全状态。
生态幸福观吁求一种新的生态劳动观念的提出,它致力于实现人和自然以及全部对象性世界之间的合乎自然和社会本性意义上的合理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
生态幸福观念指导下的人类实践有其明确的理论和现实表征。长期以来,由于我们对属人的劳动、实践活动本身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自然、社会、文化等与人本身存在的生态性内在关联本质缺少明确的、清楚的认识和自觉,因此,传统所理解和被规定的幸福本身必然是非生态性。非生态性表明这种幸福其实一直是以异化状态得以存在的,是与人相对立的。
在生态幸福的理论视野下,现代人对于自己日益升级、日益多样化的需求的合理满足,其必要而充分的前提,在于肯定自然、社会( 历史) 本身的全生态、拟生态性质,即必须认识到,属人的幸福的真正实现,取决于人与对象世界( 自然界、人类社会) 之间全生态的深切、持续关照。马克思对此有深刻论述: 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 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如此,生态幸福才是实际可触摸的真实的、真切的幸福,是整体意义上的幸福,而不是传统所谓的原子化个体的一种不可通约式的纯粹主观感觉和体验等。个体化的幸福之所以不可通约,根源在于基于个体的私利化欲望的非正当性吁求,是反生态的碎片化的幸福,而幸福的碎片化意味着真实的幸福对人性的疏离。
参考文献:
[1]郄建荣: 《环保部鼓励公众参与建设美丽中国》,载《法制日报》2012 年 11 月 29 日。
[2]唐珍: 《谁偷走了我们的幸福》,载《工友》2011 年第 7 期。
[3]《中国 20 城市获选2012 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新华社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12 年 12 月 30 日。
[4]吕忠梅: 《再论公民环境权》,载《法学研究》2000 年第 6 期。
[5]杜群: 《论环境权益及其基本权能》,载《环境保护》2002 年第5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