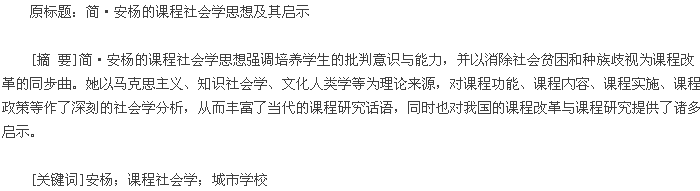
20世纪70年代以后,课程社会学成为课程研究领域的新视野,其主要代表有杨(M. F. Young)、伯恩斯坦(Basil Bernstein)、阿普尔(Michael. W. Apple)、布迪厄(PierreBourdieu)等。目前,国内研究者对杨、伯恩斯坦、阿普尔等学者的课程社会学思想已有较多论述,但对简·安杨(Jean Anyon)的课程社会学思想并未引起足够重视。为此,本文力图对安杨课程社会学思想的理论基础、基本观点等方面进行系统介绍,并分析其对我国课程研究与课程改革的启示。
一、简·安杨简介
安杨(1941-2013)是美国着名的批判教育学家、教育社会学家。在她的童年时代,其父母积极参加当时激进的社会运动,同时也是一些劳工运动的组织者。因此,安杨自称为“红尿布婴儿”(red-disper baby)。受父母的深刻影响,安杨坚信自己应该为反对社会中的种族与阶级压迫做出努力。在其高中和大学时代,美国如火如荼的民权运动深深地吸引着她,在此期间,她参加了种族平等代表大会(Congress of RacialEquality)北方支部的活动。安杨的这些生活经历使她在以后的学习、工作中对研究马克思主义、教育社会学充满了热情。1963年,她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并相继取得教育学学士和教育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在华盛顿地区的小学教书。1976年,她在纽约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随后进入新泽西州的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工作。
2002年,转入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Graduate Center of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York)工作,讲授有关社会学、教育政策和社会批判理论方面的课程。2013年,安杨因癌症离世。
安杨多年对种族、社会阶层、教育政策和经济等方面的交叉研究,使她在教育社会学、人类学、课程理论和文化批判等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尤以课程与教学、教育社会学、教育政策等方面的成就突出。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她与阿普尔等学者共同为批判教育学研究领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安杨批判当今学校的课程内容及其实施实质上反映的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学校教育是社会再生产的工具。比如,她通过对美国历史教科书的分析,在《意识形态与美国历史教科书》(Ideology and U.S.History Textbook,1979)一文中,抨击了美国学校的课程知识主要是以社会上层阶级文化为主,忽视了工薪阶层的文化。《社会阶级和隐性课程的运作》(Social Class and theHidden Curriculum of Work,1980)和《社会阶级与学校知识》(Social Class and SchoolKnowledge,1981)这两篇论文通过鲜明的案例阐释了教学过程中的隐性课程传播了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及行为方式,再生产了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和结构。此外,她早期对社会阶层与学校改革、学校课程运作关系等方面的研究,使人们开始意识到城市学校改革与社区经济、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在《种族教育:城区教育改革的政治经济学》(Ghetto Schooling:A Political Economy of Urban Education Reform,1997)这一着作中,安杨指出,城区教育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是改革主体忽视了城市居民所处的政治、经济环境,没有意识到弱势群体的贫困是教育改革的一大阻力。基于此,安杨认为,“美国城区内部经济的优先发展及自身的经济复兴是美国城区教育改革的必要条件。”
[1]安杨也在其晚期着作《激进的可能性:公共政策、城区教育和新社会运动》(Radial Possibility:Public Policy,Urban Education,and a New Social Movement,2005)中,有力地论证了城区学校的改革需要与社会经济政策、新社会运动结合起来,从而为社会理论和教育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安杨通过对种族、社会阶层与学校教育的分析,使她在教育政策方面也有与众不同的思考。如在《教育政策的“关键”是什么?》
(What “Counts” as Educational Policy,2005)一文中指出,城市学校教育改革政策的实施需要经济和政治力量的支持,教育政策的关键是创造条件,使教育改进措施在学生的生活中生根、发芽、结果,真正对学生的发展发挥作用。在《进步的社会运动和教育公平》(Progressive Movements and Educational Equity,2009)一文中,安杨通过历史分析法论证了进步的社会运动可以促使联邦和州政府出台有利于弱势群体生存和发展的政治经济政策,从而促进城区学校的课程改革与发展,促进美国教育公平。安杨的一生除了致力于改善城市薄弱学校、促进教育公平方面的教育社会学研究,还为这一目标付诸实践,她曾筹集70万美元来帮助改善纽瓦克(Newark NJ)地区教师、校长及行政人员的在职教育,并为一些高中配备计算机等教学设备。安杨对教育研究与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受到教育理论界的高度赞扬,于2010年获得美国教育研究协会教育社会学领域中的“终身成就奖”,并于同年被任命为“美国教育研究协会研究员”(AERA Research Fellow)。
二、简·安杨课程社会学思想的理论基础
安杨的课程社会学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并结合西方的知识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成果而形成的。
(一)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化与阶级理论、意识形态理论等是安杨课程社会学思想的理论基石。“马克思的社会分化与阶级理论是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占有方式即社会分工作为社会阶层划分的主要指标,并将公民共同的生活方式、阶级利益和教育程度以及明确的自我的意识作为划分阶级的必要条件。”[2]
基于此理论,安杨选取了5所代表不同阶级的学校并将其划分成工薪阶层、中产阶层、富裕阶层、精英阶层学校。另外,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中关于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人类精神生产资料的观点,促使安杨进行教科书分析并得出这一结论:学校的课程内容实质上反映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和价值观,是统治阶级进行社会控制的工具。
(二)知识社会学知识社会学由德国社会学家舍勒(Max Scheler)于1924年首次提出,其原理被规定为知识的集体的和社会的性质,知识通过一定的社会组织(如学校)的分配以及社会利益形成不同类型的现实。[3]
知识社会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曼海姆(Karl Manheim)、韦伯(Max Weber)、涂尔干(Emile Duikeim)。知识社会学的基本观点是:主体所处的社会存在对其认识有决定作用,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生活环境的主体拥有不同的思想方式和知识体系。这一基本观点促使安杨思考不同阶级背景学校中的课程知识建构与课程实施中是否隐藏了不同社会阶层利益。为研究这一问题,她决定深入学校去了解不同阶级背景学校中教师在课堂上是如何进行授课的,学生是怎样建构属于自己的知识体系的,处于不同背景中的学生是如何获得社会身份认同的。此外,知识社会学常采用的文献研究法、历史比较法使安杨采用历史分析法研究美国历史上的社会运动,并发现社会运动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并倡导弱势群体进行新社会运动。
(三)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是从文化角度研究人类社会文化起源及其各方面发展的问题、规律。“该学科所持有的基本方法是实地研究方法(或称现场研究),即注重通过直接的观察来收集第一手资料”.[4]另外,文化人类学者还以符号互动理论作为解释日常生活中人们在互动情境中是如何创造意义的这一问题的理论基础。其代表人物主要是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弗雷泽(James Frazer)等学者。文化人类学所持有的现场研究、符号互动理论都为安杨的课程社会学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基础。现场研究主张研究者深入所要研究对象的实际生活中,以此获得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来了解被研究者的生活和文化等。安杨的研究一般是深入到不同阶级背景的学校中进行课堂观察、正式与非正式访谈来了解教育现状、课程知识与课程实施。符号互动理论主张通过分析日常生活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符号互动来研究人类群体生活,探究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发生的方式、机制、规律。符号互动理论使安杨通过观察课堂教学中师生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来了解教师所讲授的知识及师生建构知识的方式。
三、简·安杨课程社会学思想的基本观点
安杨的课程社会学思想主要涵盖了对课程功能、课程内容、课程实施、课程政策的社会学分析这几方面,为当代课程话语注入了新的活力。
(一)课程的社会功能分析
安扬认为,学校的课程不仅应促进学生知识、技能、情感态度的发展,还应帮助学生获得积极的社会身份认同。她指出,当今社会结构的显着差异会对青少年积极身份认同的形成构成威胁,而在社会规范、主导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影响下的学校,对青少年的身份认同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使那些因种族、民族、社会阶层或性别等原因被边缘化的青少年获得积极的身份认同,学校的课程内容应让学生学习和使用社会交往中的主流语言,使学生有机会接触主导群体的文化和社会资本,帮助学生在成年后能尽快适应社会,使他们有机会获得成功。她建议:“学校在讲授数学、科学、历史时应使用一种跨越民族、种族、性别、阶级障碍的教学方式,培养青少年的社会正义感,促进学生的身份认同,使学生在成年后很快适应这个充满活力的、全球化的后工业社会。”[5]
这样可以充分发挥学校课程积极的社会功能。此外,安杨还主张课程应注意培养学生的批判意识与创造能力。教师在教学中应鼓励学生通过语言、图表等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情感、思想。教师不应机械地讲授书本知识,而应引导学生分析、思考事件发生的原因及过程,同时还应让学生了解当今社会制度、文化、权力运作中存在的不平等现象,鼓励学生批判性思考,培养学生改变社会环境的能力。
(二)课程内容的社会学分析
安杨对美国学校课程内容作了深刻的剖析和批判,她通过对美国历史教科书的分析发现美国教科书的内容大多体现的是社会上层阶级的观点,很少涉及工薪阶层的历史、文化,即使出现也将弱势群体的形象歪曲化、刻板化。她认为,美国“意识形态结构和权力分配的不均,导致了其课程内容社会阶层的明显性”.[6]
她认为,美国学校的课程内容实质上成为了统治阶级进行社会控制的工具,同时也使现有的社会关系和占统治地位的阶层的身份合法化,再生了社会不平等的阶级结构和社会关系。
正如她所说的,“学校课程内容传递了关于社会优势群体的合法信息,并且这种信息逐渐转化为社会成员在日常决策中支持特权阶级,而弱势群体没有能力向上层阶级提出挑战的力量。”[7]
安杨还指出学校教科书的内容很少真正向学生提供有助于学生进行批判性思考的话语和概念性框架,她通过对不同社会背景学校知识的比较分析发现,不同阶级背景的学校拥有不同的课程知识与目标,如工薪阶层子女学校(working class school)里1school)课程知识的重点是一般性概念、传统知识,富裕阶层学校(affluent professionalschool)的课程知识注重的是知识的创造、发现与学生的个体发展。精英阶层学校(executive elite school)则重视高难度概念方面的知识,教师注意发展学生的推理与思考能力。安杨进一步分析了工薪阶层学校的课程知识很少提到社会上具有争论性的话题,课程内容也很少涉及关于少数民族、妇女权利与文化方面的内容或主题。关于工人阶级的信息也很少出现,课程知识并未让学生意识到不同种类的工人同属于工人阶级并且拥有共同的利益,更没有引导学生去认识工人阶级在经济和社会服务等方面面临的困境。这样的课程内容使得学生只是机械地接受知识和技能,而不去批判性地分析与思考问题,更不鼓励学生去进行改变现状、维护其权利与利益的行动。
基于上述分析,安杨认为,应将少数民族、弱势群体学生拥有的群体文化注入学校课程内容中,让学生了解自己民族、阶层的历史和现状,认识到自己阶层、民族所面临的挑战。课程内容应有助于学生批判性地思考,有助于发展学生的社会政治意识,使学生通过学习有改变现实的勇气和行动。另外,课程内容还应让学生有机会接触主流文化,接触优势群体的文化,使学生进入成年期后能很快地适应社会,增加弱势群体在进入社会后成功的机会。
(三)课程实施的社会学分析
为了试图为“不同社会阶级背景的学校是社会阶级再生产的工具”这一观点提供经验性支持与事实证据,安杨决定深入不同背景的学校进行现场研究,她在新泽西选取了5所小学并依据学生父母的工作、家庭经济社会背景将前两所划为工薪阶层学校,将其他三所依次划分为中产阶级学校、富裕阶层学校、精英学校,对它们进行人种志研究。通过观察课堂中师生互动的方式,安杨发现不同社会背景的学校在课程实施过程中产生了不同的隐性课程。虽然这5所小学的课程在主题和材料上是相似的,但是不同学校的教师在实施课程时传授的是不同的知识、能力、价值观。如在工薪阶层学校,教师对学生的期望比较低,在课堂上传授的是基本事实与一般的手工操作技能,教师要求学生严格按照自己的要求机械地去做题、学习。这种课程实施方式使学生在进入社会后只能成为被他人利用、为他人获取利润的工具。在中产阶级学校,学生的学习就是“获得正确的答案”,教师的教学就是试图让学生去理解书本知识,但是关于创造性、批判性的教学活动很少展开。这种课程实施方式适于学生成年后进入白领阶层。而在富裕阶层学校,教师会在教学过程中“鼓励学生表达他们的情感、观点和应用其所学的知识,教学中包含学生个人的思考和表达,学生可以对老师、书本的观点进行补充说明,学生也可以自主选择合适的教学材料和学习方法。”[8]
这种教学过程有利于学生发展他们的言语表达和科学创造能力,为他们将来成为艺术家、科学家提供条件。在精英阶层学校,教师在课程实施过程中注重发展学生的推理和系统分析能力,所学的知识具有一定的逻辑性和学术性,这些为学生以后成为高级管理人员和行政人员作了很好的铺垫。
基于以上分析,安杨认为:“在不同社会背景条件下的学校,采用不同的课程实施方式,强调的是不同的认知和行为技能,使不同社会背景的学生形成不同的价值观,获得不同的知识和工作技能。”[9]
课程实施中教师传授给学生的知识和能力具有质的差异性,影响着学生在未来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职业选择和社会地位。基于对课程实施的社会学分析,安杨进一步指出学校课程实施中隐藏着与社会再生产过程相联系的隐性课程,“这些隐性课程传递了不同的知识,加强了社会的分化,并使社会阶层的分化更加合理,从而再生了社会不平等,达到了社会控制的目的。”[10]
(四)课程政策的社会学分析
安杨基于对美国城市学校大量的现场研究发现,现今美国出台的许多课程政策对促进城区学校发展、实现教育公平几乎是不起作用的,甚至许多学校的教师、学生强烈抵制这些课程政策。如当前纽约州政府为促进教育公平采取的“基于年级标准的政策”(on grade-level policy)中的课程内容反映的主要是上层阶级的内容,“课本上虽然有关于少数民族、弱势群体的文化,但其本质依然是中产阶级利益和现状的缩影”.[11]
课程内容与社会经济地位不利的学生的生活无关,使学生对课程学习非常厌恶,这阻碍了课程改革的进行和学生学业成功。另外,安杨深刻剖析了当前课程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指出:“课程政策制定者--政治家、教育家及相关的行政人员虽然在进行积极的教育改革,但是他们忽视了应将课程改革、课程政策的出台置于学校所处的社会背景中”.[12]
因此,安杨认为,课程政策制定者在制定课程政策时,要考虑学生所处社区的经济、社会环境,不能将学校和社会二者隔离,课程政策的实施应有相关的经济、社会政策给予支持。如安杨曾说:“提高贫穷家庭学生学业成就的有效的改革方式之一,是将贫穷家庭的住所并入中产阶级社区和学校的附近。”[13]
对于课程政策制定的主体,安杨认为,现今一些课程政策制定者或行政人员由于与城区学校学生、教师的社会阶层和文化背景不同,又缺乏对这些弱势群体文化等方面的认识,可能会阻碍改革者与学校人员之间的交流、相互信任、联合行动,从而阻碍课程政策的顺利实施。通过研究发现,“那些少数民族、黑人统治的地区对改革具有催化作用,有利于促进城区学校对黑人等弱势群体的学生更加负责,行政机关可为自己的机构成员赋予选择变革形式的权力。”[14]因此,必须注意课程政策制定者的价值观、文化背景,还需将课程决策主体多元化。
四、简·安杨课程社会学思想的评价
安杨经过大量的现场研究并结合相关理论,对当代美国特别是美国城区学校的教育与课程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与批判,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对当今学校发展与课程改革指明了方向,其学术思想、批判精神和勇气是令人敬佩的。
(一)批判的深刻性与思想的独特性安杨从美国资本主义性质的课程出发,抨击了美国学校教育中课程的不合理之处,揭示了当今学校课程知识的本质、价值特性及不同层级学校中潜藏着“隐性课程”,使学校成为社会再生产的工具,加剧了教育的不公平。为改变这一局面,安杨通过历史分析法、现场研究总结出影响美国城区学校教育质量的根本原因是学生所处的社区、家庭经济困难、父母失业、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它们阻碍了城区学校的改革和学生的学业成就。她指出应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特别是学校、社区团结起来,为改变国家的法律、社会政策等进行草根的新社会运动。安杨对美国教育深刻的批判和独特的见解为当今课程研究带来了新鲜空气,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二)课程研究方法的独特性与创新性安杨将学校课程研究置于广阔的社会大背景下进行分析,“将宏观场面(社会结构、权力关系等)与微观过程(课程知识的选择、组织与传递等)联系起来”,[15]揭示了美国不同社会背景下的学校潜藏着不同的“隐性课程”这一本质。另外,安杨在研究中将社会学、政治经济学与批判理论综合起来作为一种理论分析方法,并采用了观察法、访谈法等一系列的质性研究方法来分析学校的课程内容、课程实施与课程政策等,这种研究方法打破了传统的“实证主义”课程研究范式。她还采用教科书分析方法去研究课程内容的价值特性,采用课堂观察法、访谈法研究课程实施,采用大量的历史分析方法去研究课程变革、学校发展的出路,这些研究方法为我们以后的课程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三)其思想具有一定的极端性与理想化色彩安杨的课程社会学思想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科学性,但是她的思想也具有一定的极端性与理想化。如安杨在分析教科书知识时,认为课程知识完全受制于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反映了统治阶级的利益这一观点就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因为任何认识活动都是在特定的意识形态框架内进行的,无时无刻不渗透着主观因素。同时意识形态有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之分,在正确意识形态下产生的知识完全有可能成为真理性知识。”[16]
此外,课程知识的选择、组织、评价还受学科自身、学生身心发展、经济、科技等因素的影响。另外,安杨主张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如黑人、工薪阶层等进行草根社会运动,但由于这些群体自身经济、文化的限制,是否有时间、精力、金钱加入社会运动中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安杨认为:“学校能够在质疑、发起运动和挑战经济不平等及其功能运作方式和种族政治方面扮演关键性角色。”[17]
但对于学校应怎样有效组织、领导弱势群体进行社会运动,她并没有提出具体的措施和策略。
五、安杨课程社会学思想的启示
安杨的课程社会学思想虽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其中某些观点可能与我国教育实际情况有所不同,但是安杨丰富的课程社会学思想可以为我国现今的课程改革与课程研究提供有益启示。
(一)培养学生的批判意识与创造能力
鉴于以往应试教育对学生创新精神与批判思维的压制和束缚,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明确提出“新课程的培养目标应体现时代要求,要使学生具有初步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18]实际上,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的培养又离不开学生批判意识与能力的养成。这与安杨提倡的教师要重视对学生批判性思维与创造性精神的培养相吻合。她提倡教师在教学中要善于鼓励学生表达自己的情感、态度,批判地认识社会制度、权力,敢于揭示现今教育背后蕴含的权力控制现象,提高学生的批判能力和创新能力。因此,中小学教师在教学中不应只是让学生理解、掌握知识,而应让学生积极地将知识与社会现实结合起来,鼓励学生表达出自己的观点,勇于对教材、教师进行质疑、批判,逐步培养学生的批判意识和社会政治意识,促进学生思想的解放。
(二)课程内容的多元文化取向
安杨反对当今美国的课程内容以优势团体的文化为主,课本中使用的也是社会上层阶级所使用的标准英语,而忽视了少数民族、弱势群体的自身文化和语言习惯,认为这加剧了教育中的不平等。当今,我国为统筹城乡教育、实现教育公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农村学校标准化建设、城乡教师交流制度,这无疑为实现城乡教育公平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是我们却忽视了当前基础教育学校课程内容的一个事实--以主流文化、城市文化为主,而忽视了其他文化在课程中的价值。例如,教科书存在农村素材的遗忘、农村文化的遗忘等问题。课程内容中农村文化缺失的现象对于促进农村学生的身份认同、增强农村学生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竞争力都是不利的。“教育实践中的大量事实已表明,对于社会背景与文化特征处境不利的学生来说,与教材内容之间的文化失谐乃至文化冲突往往是导致他们学业失败的首要原因。”[19]虽然国家为改变这一现状提倡学校开设地方课程、校本课程,但由于农村学校师资、经济力量等方面的限制,成效不显,并有可能进一步增大城乡教育差距。因此,我国的课程改革仍需将多元文化视为合法化的课程知识,对课程内容中有关乡村、民族、社会阶层、性别上的缺失与偏见,不断予以批判更新,培养学生的多元文化意识,促进教育公平。
(三)关注课程实施中的“课程分化”
安杨分析了不同社会背景学校课堂中教师通过不同的课程组织、传递方式向学生传授了不同的认知、行为技能、情感态度等,认为这加剧了阶级分化。这种课程分化的现象同样在我国不同区域、不同学校也有所体现。虽然在我国拥有全国统一的课程标准,但是各地区、各学校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选择在相同的基础上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特别是新课程改革以来重点高中选修课的不断发展,更是使其开设的课程与普通高中有巨大差异。另外,由于各地学校师资力量的差异,城乡教师在课堂上的教学手段与方式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使城乡学生的知识建构也不同。在我国的教育评价体系开始逐步转向能力、综合素质为主时,对于农村学生、弱势群体的学生来说无疑又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此,我们的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在增强农村学校的师资力量时,更应关注教师在实施课程时注重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发展学生的实践操作、语言表达等能力,注意与学生保持和谐民主的师生关系,增加师生之间的交流与讨论,缩小城乡学校之间课程实施中课程分化的差距。
(四)课程决策的民主化、多元化
基于安杨对美国课程功能、课程内容、课程实施、课程政策等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课程决策包含着社会权力的运作和意识形态之争,课程决策是一个充满冲突的过程,体现着社会权力的平衡与妥协。当前许多国家也已经认识到“学校课程的决策不可以由封闭的某一组织或个人加以控制,政府、课程专家、学校领导、教师、学生、社区人士都有权对课程进行诠释、质疑、争论和批判”.[20]因此,当今我们应坚持课程决策的民主化、多元化,善于听取薄弱学校教师、学生、家长的声音,在课程决策中平衡与协调好各阶层、各团体之间的利益。
(五)课程改革与社会改革同步进行
安杨通过对教育与经济、政治及相关政策关系的研究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课程改革和社会改革是相互影响的,课程改革需要学校周围社会环境结构性变化的支持。这启示我们在深入推进学校课程改革时,要同时推进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改革。如在一些城市农民工子弟学校,我们应为学生家庭提供医疗、住房等社会保障,为失业的家庭提供资助等,满足这些弱势群体的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从而使这些学校的师生能全身心地投入到新课程改革的进程中。在农村学校标准化建设的同时,要注意着力提高农民的收入,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工作岗位,改善农村的卫生、社会服务设施等,这样有助于教师走向农村开发课程资源,促进农村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校本课程等的顺利开发与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