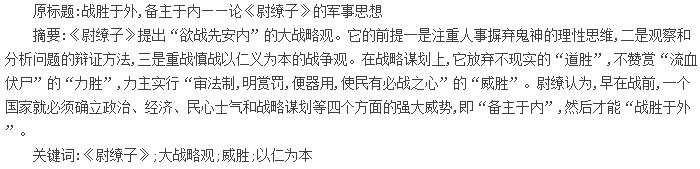
由于著作本身在形成和流传过程中的变故,现在《尉缭子》一书的许多议论显得驳杂和不连贯,给人以拼凑之感。但瑕不掩瑜,认真研读,仍能从中感受到一种明哲之辉光和人性之美丽,而不仅仅是血腥的杀伐之气。
一、注重人事摒弃鬼神的理性思维
中国古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与戎的连接点就是兵祭和神占,此类内容充斥于最早的甲骨文、金文中。因为兵战不仅事关军国大局,凶险无比,而且还有许多难以预料的偶然因素,胜败往往系于一念之间,于是人们往往求神问卜,以求安心。
《韩非子》有《饰邪》篇,说赵、燕、齐、魏等国盛行战前“凿龟数策”,或以龟兆,或以星象。后来专门形成一派“兵阴阳家”,即《汉书·艺文志》所谓“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正是由于军事实践中卜筮迷信的盛行,使得古代许多兵书也不能免俗。《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兵家类》就称“其间孤虚王相之说杂以阴阳五行,风云气色之说又杂以占候。故兵家恒与术数相出入,术数亦恒与兵家相出入”。这种情况,即使古代一些杰出的兵书也难有例外。
银雀山一号汉墓在出土简本《孙子兵法》的同时,还有简本《阴阳书及风角、灾异、杂占》,多是阴阳术数荒诞迷信之词,但仍不脱兵家本色。其内容虽不见于今本十三篇《孙子兵法》,却与《隋书·经籍志》所著录又被《太平御览》三三八卷所引《孙子兵法杂占》的六条文辞类似,有学者认为此即当初曹操删削《孙子兵法》之余。也就是说,汉魏时代的原本《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就有此类内容。看今本《孙子兵法·火攻篇》有“起火有日”,“日者,月在箕、壁、翼、轸也,凡此四宿者,风起之日也”这样的话,可谓痕迹犹存。
《吴子兵法》是一部带有儒家色彩的兵书,也有相当数量的军占之说。《图国》说有道之君在战前,“必告于祖庙,启于元龟,参以天时,吉乃后举”。《料敌》说“有不卜而与之战者八”“有不占而避之者六”;反过来说,除了这八种或者六种情况,作战仍然是需要先占卜的。
反观《尉缭子》,却是完全彻底地摆脱了鬼神迷信,非常强调“人事”在兵战中的能动作用。全书以《天官》开篇,首先以梁惠王的名义设问:“黄帝刑德,可以百胜,有之乎?”尉缭回答说:“(刑德)非所谓天官、时日、阴阳、向背也,黄帝者,人事而已矣。”
接着又以攻城为例,假如四个方向都攻不下来,证明不是顺不顺天时和方位的问题,而在于城池、兵器、财谷等物质条件的优与劣。他再以武王伐纣和齐楚之战的胜负为例,说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所谓的“天官之阵”,而在于人的主观能动性。所以最后结论是:“天官时日不若人事也”,“先神先鬼,先稽我智,谓之天官,人事而已”。尉缭的这种认识是贯穿全书的。如《战威》讲:举贤任能,不时日而事利。明法审令,不卜筮而事吉。贵功养劳,不祷祠而得福。又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圣人所贵,人事而已。
又如《武议》讲:武王不罢士民,兵不血刃而克商伐纣,无祥异也,人事修不修而然也。今世将考孤虚,占咸池,合龟兆,视吉凶,观星辰风云之变,欲以成胜立功,臣以为难。这种理性经验,是从长期的实践中得来的。战场,是敌我双方生死较量的场所,要求指挥员始终清醒冷静从实际出发,来决定自己的行动,否则只能碰得头破血流。尉缭认识到任何迷信不仅无助而且有害于战场指挥,提出为将必须“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摆脱干扰,专心谋划战争:“凡兴师,必审内外之权,以计其去。兵有备阙,粮食有余不足,校所出入之路,然后兴师伐乱。”(《兵教下》)当然,尉缭的理性思想还是一种感性经验的总结,还没有能像同时代的荀子那样上升到哲理的层次将之概括为一种自然规律,也不可能真正科学地说明“天道”与“人事”的关系。他曾经无限感慨地说:“苍苍之天,莫知其极;帝王之君,谁为法则?往世不可及,来世不可待,求己者也。”(《治本》)在当时,这种“求己”思想和荀子“唯圣人不求知天”的思想是相通的,也是难能可贵的。
二、观察和分析问题的辩证方法
战争是主客观多种因素交互作用下的产物,十分复杂和富于变化。能否及时认识战场形势的种种变化,能否深刻认识促使变化发生的种种条件,能否充分利用这种变化以加强我方的优势,将决定战争的结局。尉缭通过对战争现象的缜密观察,总结出一些带规律性的原则,从而体现出他所具有的辩证思维方法。
首先他不相信有所谓的“常胜将军”。《战权》云:“凡我往则彼来,彼来则我往,相为胜负,此战之理然也。”这也就是后人所说的“胜败乃兵家常事”。但这种胜负又不是宿命论的,而是一定的主客观条件作用下的结果,“兵弱能强之,主卑能尊之,令弊能起之,民流能亲之”(《兵教下》)。也就是说,强弱不会永远不变,假如制度或政策不好,就会“虽战胜而国益弱,得地而国益贫,由国中之制弊矣”(《制谈》)。而表面弱小的力量,也可能成为最终的胜利者:“胜兵似水。夫水,至柔弱者也,然所触丘必为之崩。”(《武议》)故“知彼弱者,强之体也”(《原官》),最要紧的是知道弱点并及时弥补。
其次,所谓条件的“利”和“害”也是相对的,关键是如何待之。如“分险者无战心,挑战者无全气”(《攻权》),占据险要地形者会无求战之心,恃强挑战者往往轻视敌人而不能全力以赴,都可能招致失败。所以作战的大敌是盲目和冒进,“有者无之,无者有之,安所信之”?敌人究竟有没有实力怎能轻易相信呢?“故知道者,必先图不知止之败,恶在乎必往有功?”(《战权》)
又次,尉缭主张在战场上要紧随形势及时调整部署和行动,灵活机动,不拘一格:“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制敌者也。”(《勒卒令》)“诸将之兵,在四奇之内者,胜也。”(《踵军令》)“善用兵者,能夺人而不夺于人。”(《战威》)只要主动权在我,就要果断根据敌方暴露的弱点一举制之:“凡将轻、垒卑、众动,可攻也”,“伐国必因其变,示之财以观其劣,示之弊以观其病。上乖下离,若此之类是伐之因也”。(《兵教下》)最后,尉缭在《十二陵》中还对治军中常见的经验教训进行归纳总结,提出了十二组具有辩证联系的范畴,以供将帅们自我警诫:威在于不变,惠在于因时;机在于应事,战在于治气;攻在于意表,守在于外饰;无过在于度数,无困在于豫备;慎在于畏小,智在于治大;除害在于敢断,得众在于下人。悔在于任疑,孽在于屠戮;偏在于多私,不祥在于恶闻己过;不度在于竭民财,不明在于受间;不实在于轻发,固陋在于离贤;祸在于好利,害在于亲小人;亡在于无所守,危在于无号令。
这些范畴的特点,一是每组的两个(“威”与“惠”,“机”与“战”,“攻”与“守”,“无过”与“无困”,“慎”与“智”,“除害”与“得众”,“悔”与“孽”,“偏”与“不祥(详)”,“不度”与“不明”,“不实”与“固陋”,“祸”与“害”,“亡”与“危”)总具有一定程度的内在联系,如攻和守,进攻的关键是出敌不意,防守的要害在于坚固工事,都抓住事物的本质属性,在作战中可以根据条件的变化灵活转换。二是这些总结不管经验也好、教训也好,都和人的主观指导有关,都不是外在意志决定而不可扭转的。如祸和害是词义近似的一对范畴,《说文》“祸,害也”,本意是天降神祸。但作者将之进行了改造,认为不贪财好利就不会有灾祸,不亲近小人就不会被伤害,问题都出在人的行为选择上,另如屠戮、竭民财的行为更被严厉谴责。所以尉缭秉持的是一种能动而灵活的辩证思维。
三、重战慎战以仁义为本的战争观
尉缭所生活的战国晚期,统一大势已成,各个学派的战争观也由对立趋向接近和融汇,形成了一种新的以仁义为本的战争观。战国中期时,思想家在如何统一的问题上出现了尖锐对立。法家是“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如《商君书·画策》主张“以战去战,虽战可也;以杀去杀,虽杀可也”,全力以战争手段兼并统一。而《孟子·离娄上》则强调“仁者无敌”,认为“不嗜杀人者能一之”,甚至主张“善战者服上刑”。
这时几乎没有人对儒、法两种对立的观点进行调和。历史进入战国晚期,一方面,孟子的空洞说教在现实中根本行不通,所谓“行文王之政者”不但不能“为政于天下”,甚至也不能“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另一方面,残酷战争对社会经济的破坏和使人民受到的痛苦程度越来越严重,“杀人盈野”“杀人盈城”,如著名的长平之战,白起坑杀赵卒四十余万,造成极大的社会震动,秦被指责为“虎狼之国”。当时的思想家既看到通过战争途径实现统一的不可避免,也看到单纯使用残酷的武力手段会使“天下民不乐为秦民”,难以巩固统一局面,于是原来对立的儒法两种战争观就被加以有机综合,逐渐产生了以仁义为本的战争观,其代表就是《荀子》和《吕氏春秋》。如《荀子·议兵》云:“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吕氏春秋·荡兵》云:“有义兵而无有偃兵……兵诚义,以诛暴君而振苦民。”认真对照《尉缭子》的相关内容,可以发现它们之间不仅在精神上相通,甚至在词句上也颇类同。
其一,尉缭重视战争,认识到作为政治的工具,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战威》云:“务耕者民不饥,务守者地不危,务战者城不围。三者先王之本务也。本务者,兵最急。”《兵令上》云:“战国则以立威、抗敌、相图而不能废兵也。”即使战争结束后也“必当备之”(《攻权》)。
其二,尉缭又主张对战争持谨慎的态度。《武议》云:“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将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兵谈》云:“兵起,非可以忿也。见胜则兴,不见胜而止。”《攻权》云:“战不必胜,不可以言战;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因为在古代脆弱的自然经济之下,战争损耗了大量人力物力,容易激化社会矛盾。
其三,尉缭已经能够区分“挟义而战”与“争私结怨”两类不同的性质的战争,区别在于战争目的。对于后者,他主张慎重:“争私结怨应不得已,怨结虽起,待之贵后。”(《攻权》)对于前者,他说:“故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武议》),“王者伐暴乱本仁义焉”(《兵令上》),“凡挟义而战者,贵从我起”(《攻权》)。这种正义战争的外在表现,就是不能滥杀无辜,毁坏公私财物:“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兵之所加者,农不离其田业,贾不离其肆宅,士大夫不离其官府”(《武议》);军队入人国,“无丧其利,无夺其时,宽其政,夷其业,救其弊”(《兵教下》),总之“孽在于屠戮”(《十二陵》)。这样做,并非出于良心发现,而是直接关乎主导者的政治利益。非如此不能争取人心,瓦解对手,“使敌之气失而师散,虽形全而不为之用”(《战威》);非如此不能得到敌国贤良对自己的拥戴,巩固胜利成果:“不能内有其贤而欲有天下,必覆军杀将。如此虽战胜而国益弱,得地而国益贫。”(《制谈》)其四,尉缭在治军问题上也能礼法调和,德刑并用。儒家强调以礼治军,《礼记》云“军旅有礼则武功成”,孔子也说过“勇而无礼则乱”(《论语·泰伯》)。法家却是专任赏罚,强调以法治军。《商君书·开塞》说“任其力不任其德”,《韩非子·显学》也说:“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故不务德而务法。”尉缭则因应时代需要,对二者加以调停。
首先他认为军队不能不严明法制:“凡兵,制必先定”,“民非乐死而恶生也,号令明,法制审,故能使之前”。为使法制能贯彻推行,就要以赏罚为手段,“明赏于前,决罚于后”(《制谈》);“凡诛者,所以明武也。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喜者,赏之”;“当杀而虽贵重,必杀之,是刑上究也;赏及牛童马圉者,是赏下流也。夫能刑上究、赏下流,此将之武也”(《武议》)。这样才可以达到“吏畏其将”“民畏其吏”“敌畏其民”(《攻权》)的效果。
其次他认为仅有法制还不够,志不励则士不死节,还要有“励士之道”。《战威》云:“将之所以战者,民也;民之所以战者,气也。”人是有思想的,“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者也,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战者也”。那么又如何能使民致其死战呢?就要像“古者率民”那样,“先礼信而后爵禄,先廉耻而后刑罚,先亲爱而后律其身”。励士的手段要物质和精神结合,“民之生,不可不厚也;爵列之等,死丧之亲,民之所营,不可不显也”。使之有“田禄之实,饮食之亲,乡里相劝,死丧相救,兵役相从”;一旦走上战场,“使什伍如亲戚,卒伯如朋友”,上下齐心,动静一身,没有不打胜仗的。
最后,治军的关键一环是将领能够做到身先士卒、严于律己。《战威》云:“勤劳之师,将必先已。
暑不张盖,寒不重衣,险必下步,军井成而后饮,军食熟而后饭,军垒成而后舍,劳佚必以身同之。”何以如此?“不自高人故也”。而且,“将受命之日忘其家,张军宿野忘其亲,援枹而鼓忘其身”(《武议》),要以这种态度感染所有官兵。总之,“善将者,爱与威而已”(《攻权》)。
四、“欲战先安内”的大战略观
同其他兵书比较起来,《尉缭子》有自己的特色,即它涉及具体作战方法的内容并不多,大部分内容都是围绕着战前各个方面如何准备而展开的。《战威》云:凡兵,有以道胜,有以威胜,有以力胜。讲武料敌,使敌之气失而师散,虽形全而不为之用,此道胜也。审法制,明赏罚,便器用,使民有必战之心,此威胜也。破军杀将,乘闉发机,溃众夺地,成功乃返,此力胜也。
“道胜”是用兵的最高境界,相当于齐桓公的“九合诸侯不以兵车”和孙子的“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非圣人莫能为。所谓“力胜”也好理解,就是流血伏尸的硬攻之战,武夫皆可,尉缭并不赞赏。他真正关注的是“威胜”,即如何“审法制,明赏罚,便器用,使民有必战之心”。要威胜,必须把功夫做到战争之前和战场之外,所谓“权先加于人者,敌不力交;武先加于人者,敌无威接,故兵贵先”(《战权》)。兵贵先,就是在战前造成一种强大的威势,先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尉缭认为可从政治、经济、民心士气和战略谋划四个方面来做。
首先是如何确立政治上的必胜形势。尉缭认为路径有三:一是好的制度建设,二是政治清明,三是统治者爱民富民。《制谈》云:吾用天下之用为用,吾制天下之制为制。修吾号令,明吾刑赏,使天下非农无所得食,非战无所得爵,使民扬臂争出农战,而天下无敌矣。故曰:发号出令,信行国内。既然可以利用天下的资财来充实我们的国力,为什么不能参考天下的善政来修订我们的制度呢?
制度是根本,它可以充分稳定地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从根本上培育人民对政权的向心力,也是举贤任能、政治清明的根本保证。相反,“虽战胜而国益弱,得地而国益贫,由国中之制弊矣”,制度可以决定一切。除此还要政治清明,不能任由国中权贵贪赃枉法,败坏人心,因为它会影响军队的战斗力。《制谈》云:“衣吾衣,食吾食,战不胜守不固者,非吾民之罪,内自致也。”为什么?《战威》云:“王国富民,霸国富士,仅余之国富大夫,亡国富仓府。所谓上满下漏,患无所救。”只满足上层(上满)而忽略下层(下漏)的国家肯定会被人民抛弃。另外,若“良民十万而联于囹圄,上不能省,臣以为危也”(《将理》),冤狱的普遍存在也很危险。
最重要的是统治者爱民富民,“地所以养民也”,“民之生不可不厚也”(《战威》);应注意招抚流亡,开垦荒地,使“民流者亲之,地不任者任之”(《兵谈》)。同时还要“均井地,节赋敛,取与之度也”(《原官》),解决土地问题,减轻人民负担。国家能够“无夺民时,无损民财”(《治本》),就是放水养鱼,储蓄民心。
尉缭对政治和军事关系的认识十分深刻:“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能审此二者,知胜败矣。”(《兵令上》)军事是手段,政治是目的;军事是表象,政治是实质。有了良好的制度,才能战场取胜,此即“兵胜于朝廷”,“不求胜而胜也”(《攻权》)。
其次是如何确立经济上必胜的形势。尉缭认为也有三条:一是军队数量规制合理,二是战略物资多生产少浪费,三是促进和发挥市场流通的作用。
古代的军事经济,不外乎“兵器备具,财谷多积”,大多取自天然资源。尉缭首先主张要做到“三相称”:“量土地肥硗而立邑建城。以城称地,以地称人,以人称粟。三相称,则内可以固守,外可以战胜。”(《兵谈》)根据自己的资源情况设置城邑,建立军队,使土地、城邑、人口、粮食的多寡与军队规模相适应,这样对内可以固守,对外可以战胜。如果军力盲目追多求大,使资源和人力不继,只能让自己陷于被动。这就是军力规制合理。
一旦战争发动,对经济资源的消耗很大,“十万之师出,日费千金”(《将理》)。如果“国内空虚,自竭民岁,曷以免奔北之祸乎?”(《兵令下》)故“备用不便则力不壮,委积不多则士不行”(《战威》)。《武议》认为这种储备的途径有两条。一是鼓励生产,“万乘农战,千乘救守,百乘事养”,不论大国小国都要在经济上自立,而不能把别国援助作为自己的经济立足点。二是发展贸易,“夫出不足战、入不足守者,治之以市。市者,所以给战守也。万乘无千乘之助,必有百乘之市”(《武议》)。不仅利用市场来交换物资,还可以抽取商税以筹措军费。尉缭很敏锐地为经济上的“自保安内”找到了一条有效便捷的途径:“夫市也者,百货之官也”,“人有饥色,马有瘠形,何也?市所出而官无主也。夫提天下之节制,而无百货之官,无谓其能战也”(《武议》)。他还建议由国家设立军市,以流通百货,为军队后勤提供民间通道。
除为战争经济开源外,节流也很重要。《治本》说:“百里之海,不能饮一夫;三尺之泉,足止三军渴。臣谓欲生于无度,邪生于无禁。”奢侈浪费的风气当然是统治者造成的,一方面是“金木之性不寒而衣绣饰,马牛之性食草饮水而给菽粟”,造成朱门内的普遍浪费;另一方面是“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腹”的小民之困。尉缭要权贵们像圣人一样“饮于土,食于土,故埏埴以为器”,只用陶器而不用奢侈品,这样就会“天下无费”。
有了经济根基上的稳定,国家“内安”,对外战争才能有保障。《兵谈》云:“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治则国治。富治者,车不发轫,甲不出橐而威制天下。故曰兵胜于朝廷。”这种“不暴甲而胜”包括“胜于朝廷”“胜于原野”“胜于市井”,不待于“阵而胜者”,不正是“威胜”吗?
再次是如何确立民心士气上的必胜形势。尉缭同样提出三条:一是提高全社会的普遍道德水准,二是从物质和精神上加以激励,三是严明法纪。
战场乃凶险之地,人的本性又总是趋安避难,所以战场上民心士气如何,常常对结局起着决定作用。要调动民心士气,尉缭认为根本路径还是提高社会整体的道德水准:“故国必有礼信亲爱之义,则可以饥易饱。国必有孝慈廉耻之俗,则可以死易生。”(《战威》)但这并不能一蹴而就,重要的是长时期的教化熏陶以移风易俗:“夫谓治者,使民无私也。民无私,则天下为一家,而无私耕私织,共寒其寒,共饥其饥……焉有喧呼耽酒以败善类乎?”像许多思想家一样,他也憧憬着一个美妙的理想社会:“善政执其制,使民无私;为下不敢私,则无为非者也。反本缘理,出乎一道,则欲心去,争夺止,囹圄空,野充粟多,安民怀远。外无天下之难,内无暴乱之事,治之至也。”(《治本》)既然善出于人性,就可以经过不懈的陶冶而使民“无私”,但前提还是“善政执其制”,有好的政治制度。
提高社会道德,既然不能毕其功于朝夕,就要重视对人们从物质和精神上加以激励。“必先礼信而后爵禄”,礼信是精神鼓励,爵禄就是一种物质优待,“田禄之实,饮食之亲,乡里相劝,死生相救,兵役相从。此民之所励也”。国家对民众有一揽子的保障措施,如殷实的生活、死丧的抚恤、功绩的奖励、邻里的督促、危急的拯救等,都是为了营造一种激励士气的氛围,“使什伍如亲戚,卒伯如朋友,止如堵墙,动如风雨,车不结辙,士不旋踵,此本战之道也”(《战威》),无形中就提高了战斗力。
要增强士气,不能只靠“励”,还要有严明的法纪。《制谈》云,“民非乐死而恶生也。号令明,法制审,故能使之前。明赏于前,决罚于后”,才能“动则有功”。从人性出发,人不能骄纵还要威逼,关键是军中各种制度的先设:“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则士不乱。士不乱,则刑乃明。金鼓所指……则万人齐刃,天下莫能当其战矣。”有了制度,才能使部队的行动整齐如一,所以《尉缭子》在后十二篇中就为军队设立了许多具体条令,强调必须得到切实执行:“刑罚不中,则众不畏。”(《战威》)到了战场上,“民无两畏者,畏我侮敌,畏敌侮我”。善于带兵的人要对士兵爱威结合,“不爱说其心者,不我用也;不严畏其心者,不我举也。爱在下顺,威在上立;爱故不二,威故不犯。故善将者,爱与威而已”(《攻权》)。一旦调动起民心士气,“兵之所及……人人无不腾陵张胆,绝于疑虑,堂堂决而去”(《兵谈》)。
这就是统治者所期待的战场效果。最后是如何确立战略上的先机和必胜形势。尉缭子同样认为有三条:一是将庙算做得高明;二是把握好关键时机;三是要“知止”,绝不图功冒进。战前的谋划决策,就是古人的所谓“庙算”。《战威》云:“刑未加,兵未接,而所以夺敌者五:一曰庙胜之论,二曰受命之论,三曰逾垠之论,四曰深沟高垒之论,五曰举阵加刑之论。此五者,先料敌而后动,是以击虚夺之也。”这里的五论,分别指朝廷决策、将帅遴选、战机选择、自保不失和临战指挥。
只有这几方面准备充分,才能进入军事实施阶段。
《战权》强调:“高之以廊庙之论,重之以受命之论,锐之以逾垠之论,则敌国可不战而服。”决策高明、将帅慎选、军锋精锐,这三项条件具备就可不战而胜。这些步骤应完成于战阵交兵前,其中最重要的是发现人才:“良马有策,远道可致;贤士有合,大道可明。”(《武议》)战争是双方的事情,尉缭非常重视扬长避短,把握战机。尉缭所说“先料敌而后动”,主要是为了能够“击虚”,即寻求敌人的弱点。要“击虚”,就要“知敌”,于是“凡兴师必审内外之权,以计其去:兵有备阙,粮食有余不足,校所出入之路……地大而城小者,必称收其地;城大而地窄者,必先攻其城”。
但这种谋划还只是建立在敌方常态基础上的,伐国还“必因其变”,从而寻找战机和突破口。如敌国内发生政治或财政危机,特别是“上乖下离,若此之类是伐之因也”(《兵教下》)。“机在于应事”,行动要果断迅速,“深入其地,错绝其道,栖其大城大邑”,遮断交通,抢占要地,使“敌救未至,而一城已降;津梁未发,要塞未修……远堡未入,戍客未归……六畜未聚,五谷未收,财用未敛……我因其虚而攻之”,这样我方就可达到“敌不接刃而致之”的目的(《兵权》)。
但是,由于战场形势的千变万化,一个将帅不仅要“贵先”,更要“知止”。《兵谈》云:“兵起,非可以忿也。见胜则兴,不见胜则止。”作为一个将帅,必须“宽不可激而怒”。《战权》云:“故知道者,必先图不知止之败,恶在乎必往有功?轻进而求战,敌复图止,我往而敌制胜矣。”要精准把握战场形势,当进时不失时机,当止时任凭敌人如何引诱,决不图功冒进。
总之,《尉缭子》在战略上崇尚“早”和“先”,主张“蚤决先定。若计不先定,虑不蚤决,则进退不定,疑生必败。”(《勒卒令》)这种“蚤决”和“贵先”,就是早在交战之前,就已谋划周详,就已从战略上稳操胜券,也就是《战威》所说“善用兵者,能夺人而不夺于人”。只有紧握战略主动权,才可立于不败之地。
《尉缭子》内容宏富,其核心观点即是《兵谈》所说“战胜于外,备主于内,胜备相应,犹合符节”。“外”就是战场决战,“内”就是国内状况,它的结论是“欲战先安内也”(《踵军令》)。只有当国家内部各方面都被安顿好,才可以在“内固守”的前提下“外战胜”,才可能“天下莫能当其战”。相反,如果内部不稳,上下阶层离心离德,战场上就可能出现《制谈》所说的“征役分军而逃归,或临战自北,则逃伤甚焉……将已鼓而士卒相嚣,拗矢折矛抛戟,利后发……士失什伍,车失偏列,奇兵损将而走,大众亦走”那样“内自败”的情形。历史上固然也有一些统治者为了转移国内不满而贸然发动对外战争,但那无异于玩火自焚。从某种意义上说,越是了解战争真谛的军事家就越是“胆怯”,所以如孙子、尉缭等人都是“慎战”论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