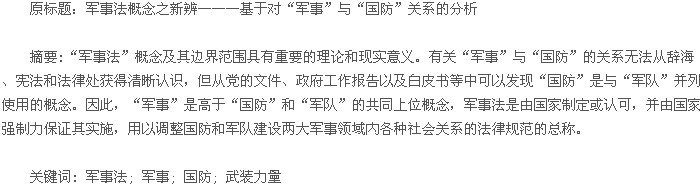
能否准确界定“军事法”的概念,不仅关系到军事法理论体系的成熟与否,也关系到军事法制建设实践的结果。而要厘清“军事法”的概念,又不得不明晰“军事”与“国防”二者间的关系。正如有的学者所言,目前军事法理论研究中突出的一个问题,正是“军事”和“国防”两个关系学科建设发展的基础概念在理解和使用上的混乱。
一、有关“军事”与“国防”的现有说法不能准确界定二者间关系
( 一) 《辞海》对“军事”与“国防”二词关系的界定不足为凭军地法学界虽然对“军事”和“国防”二词的关系存在不同认识,但在讨论“军事”与“国防”这两个词时,通常都会引用到 1999 年版的《辞海》。①该版《辞海》将“军事”解释为: “一切与战争或军队直接相关的事项的统称。主要包括国防建设与军队建设、战争准备与战争实施。”而将“国防”定义为: “国家为扞卫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防备、抵御外来武装侵略和颠覆而进行的军事及与军事有关的政治、外交、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建设和斗争。”
如果是主张“国防”大于“军事”观点的学人,就会列出《辞海》对“国防”的解释,并在解释“军事”一词时省去《辞海》对其界定的某些内容,如在《国防行政法与军事行政法》一书中,仅列出“军事”是“一 切 与 战 争 或 军 队 直 接 相 关 的 事 项 的 统称”,而省去了《辞海》关于军事“主要包括国防建设与军队建设、战争准备与战争实施”这样的解释性话语,因此得出“国防”=“军事 + 与军事有关的活动”这一结论。如果是主张“军事”大于“国防”观点的学人,则会引用《辞海》对“军事”的解释,即“一切与战争或军队直接相关的事项的统称。主要包括国防建设与军队建设、战争准备与战争实施”,而略去对“国防”的解释性话语。这样,在与“国防”定义没有可供对比的背景下,也能得出“军事”=“国防建设 + 军队建设 + ……”的结论。
然而,从 1999 年版的《辞海》对“军事”和“国防”二词的完整解释看,学界很难据此得出二者间确切关系的肯定性结论。如果将《辞海》中二者的解释摆在一起进行比较,则无法准确厘清二者的逻辑关系。
时隔十年后的 2010 年版的《辞海》也没有对二词进行大的改变,仍基本保留了 1999 年版《辞海》的观点。2010 年版《辞海》将“国防”定义为: “国家为防备和抵抗侵略,保卫国家的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所进行的军事及与军事有关的政治、经济、外交、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活动。主要包括: 武装力量建设,边防、海防、空防建设,国防科研生产,全民国防教育,完善动员机制,实现国防现代化。”
将“军事”定义为: “一切与战争和国防直接相关的事项。主要包括战争准备与实施、国防建设与军队建设、国际军事安全与合作等。军事涉及国家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传统和地理环境等各个方面,具有社会性、政治性、经济性、技术性、暴力性、对抗性和地域性等特征。”
综上所述,关于“军事”与“国防”,无论是 1999年版的《辞海》还是 2010 年版的《辞海》的解释都无法帮助人们获得二者间关系的清晰认识。
( 二) 国家法律对“国防”和“军事”二词关系界定不明
既然通过《辞海》较难准确厘清“军事”与“国防”二者的关系,那么我们可以从其他权威性的文本,如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来试图划定“军事”与“国防”的关系。
1. 宪法对“军事”和“国防”二词的规定
宪法确实多次提到了“军事”字样,但多以“中央军事委员会”“军事法院”和“军事检察院”等专有名词出现,只有一次以“军事制度”出现,即第 120条规定: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依照国家的军事制度和当地的实际需要,经国务院批准,可以组织本地方维护社会治安的公安部队。”在军事学界,“军事制度”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术语,其内容主要包括国防领导体制、武装力量体制、国防经济管理体制、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管理体制、兵役制度、国防教育制度、民防制度、战争动员制度等。
因此,在对“军事制度”进行阐释的语境中,“军事”大于“国防”的结论是成立的( 但放在国防法的整体背景下,又无法坚持这一结论) 。与之相对照的是,“国防”一词出现在了宪法的“序言”部分、第 29 条和第 89 条,分别以“增强了国防”“国防现代化”“国防力量”和“国防建设事业”的字样出现。
由于“军事”和“国防”在宪法中是以不同的语境出现的,二者并未在同一语境中出现,因此无法从宪法中获知二者间的确切关系。
2. 法律对“军事”和“国防”二词的规定
在国家基本法国防法中,“军事”一词除了以“中央军事委员会”“军事法院”和“军事检察院”等专有名词出现外,还体现在以下条文中,如该法第 2条“军事活动”,第13 条“军事战略”“军事法规”,第16 条“驻地军事机关”,第 21 条“军事训练”,第 27条“军事机关”,第五章“军事订货”,第十一章“对外军事关系”,第 65 条“军事交流与合作”,第 65 条“与军事有关的活动”。
如果单从第 2 条“国家为防备和抵抗侵略,制止武装颠覆,保卫国家的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所进行的军事活动,以及与军事有关的政治、经济、外交、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活动,适用本法”规定的内容看,国防法的适用对象包括军事活动,以及与军事有关的政治、经济、外交、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活动,似乎“国防”包括“军事”这一观点有理,但由于国防法通篇都没有对“国防”进行界定,因此无法直接依据国防法推导出“国防”与“军事”的关系。
此外,查看国防法第 55 条,也很难对“军事”和“国防”关系轻易下结论。作为国防法中唯一将“国防”和“军事”相提并论的条文,其规定“公民和组织因国防建设和军事活动在经济上受到直接损失的,可以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赔偿。”这句话至少说明“国防建设”和“军事活动”不是一回事。
二、“国防”是与“军队”并列使用的概念
( 一) 执政党的权威文件将“国防”和“军队”并列使用
“军事”和“国防”的关系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中没有直接的表述,但“国防”与“军队”的关系确有涉及。最先出现“国防和军队建设”连用的情况始于 1997 年 9 月 12 日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该报告在第二部分“过去五年的工作”中提到了国防和军队建设问题。江泽民在讲了经济、政治和文化任务之后,专门讲了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出“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是国家安全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保证。”此后的 2002 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2007 年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以及 2012 年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都使用了此种表述。
①可见,自 1997 年 9 月 12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至今,“国防和军队建设”这一固定搭配在党的文件中已经使用了 15 年,相信今后这一固定搭配也会被继续使用。而现实生活中,人们也已逐步接受了“国防和军队建设”这一搭配,并开始广泛运用。需要着重强调的是: 第一,如果说 1997年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报告中出现“国防和军队建设”连用仅是一种偶然情况的话,那在此后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议报告都出现,就说明将“国防和军队建设”连用是稳定而明确的; 第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报告将“国防和军队建设”并列,实际上隐含了二者共同的上位概念,即“军事”; 这从党的十七大报告就可以看出,在讲了“经济”“政治”和“文化”之后,专门提到“国防和军队建设”问题。“国防和军队建设”连用已经约定俗成,形成固定搭配,反映了人们对二者间关系认识的明晰。
( 二) 国家最高行政机关的文件将“国防”和“军队”并列使用
1998 年 3 月 5 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使用了“国防和军队建设”,如在“关于过去五年的政府工作”部分提到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迈出新的步伐”,而在“关于 1998 年政府工作的建议”部分就指出“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是国家安全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证。”此后,历届政府工作报告中“国防和军队”都以连用的形式出现,这一固定搭配定型并沿用至今,如 2013 年 3 月5 日温家宝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曾三次提到国防问题———“国防和军队建设开创新局面”“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巩固的国防和强大的军队”———其中“国防”与“军队”被并列使用。
2011 年 10 月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白皮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集结了中国现有法学理论和法制建设成果的白皮书。该白皮书指出: “我国制定了国防动员法、军事设施保护法、人民防空法、兵役法、国防教育法和征兵工作条例、民兵工作条例等法律法规,建立健全了国防和军队建设制度”。从这一段话可以看出,国防动员法、军事设施保护法、人民防空法、兵役法、国防教育法和征兵工作条例、民兵工作条例等法律法规是隶属于国防和军队建设制度范围内的。就整个国家法律体系而言,国防和军队建设制度属于国家法律制度的一个方面。
三、军事法概念的界定
综上所述,当我们无法从辞海、宪法和法律处获得有关“军事”和“国防”关系的清晰认识时,寻求党的文件、政府工作报告以及白皮书等的帮助无疑是明智且有效的选择。笔者认为将“军事”作为高于“国防”和“军队”的共同上位概念将有助于现有问题的解决。
所谓“军事”,是与国防和军队( 此处的军队实际上与武装力量等同) 建设直接相关的事项的统称,包括国防建设领域和军队建设领域两个方面。
军事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用以调整国防和军队建设两大军事领域内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所谓“国防”,是指国家为防备和抵抗侵略,制止武装颠覆,保卫国家的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所进行的防务活动。所谓“军队”,是指国家或政治集团为准备和实施战争而建立的正规武装组织。在我国具体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部队和预备役部队、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和民兵。将“军事”作为高于“国防”和“军队”的上位概念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首先,将有助于解决军事法学基础理论问题。军事法学作为法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其研究的对象是军事法,具体而言是军事法律现象及其规律。可见“军事法”无疑是军事法学的一个元概念,①不解决“军事法”概念问题,就无法建构起科学合理的军事法学理论体系,也无法深化军事法学理论研究,提升军事法学研究的质量。现有的研究对“军事”和“国防”关系认识模糊,“军事”大还是“国防”大的争论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至今仍未达成共识。如前所述,建立在对“军事”或“国防”片面理解上的孰大孰小结论不具有说服力。而将“军事”作为统摄“国防”和“军队”的上位概念,把军事分为“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两个领域,把“军事法”界定为调整包括国防和军队在内的军事领域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以这样的逻辑起点来建构军事法学基础理论体系具有可行性和生命力。
其次,将“军事”作为高于“国防”和“军队”的上位概念有助于解决军事法制建设现实问题,有助于明确军事法在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纯粹由中央军事委员会制定的军事法规以及由各总部、军兵种、军区制定的军事规章的地位尚需明确; 并且在七大部门法的划分中,这些军事法规和军事规章也不知该归属于何部门法下。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现象,部分原因在于将军事法仅仅看作是军事法规和军事规章的集合体。在这种观点支配下,军事法就不可能涵盖国防建设领域,国防和军队建设领域的法律法规自然被划分到宪法或行政法部门下;作为只能调整武装力量建设领域的军事法就被自然地排除在国家法律体系之外。而将军事法规和军事规章排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之外,显然既不符合法治国家的要求,也不利于国防和军队建设。将“军事”作为高于“国防”和“军队”的上位概念,军事法自然涵盖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全领域、全流程,因而军事法作为这样一个法律集合体,其必然就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赢得其应有的地位。
参考文献:
[1]田思源,王凌. 国防行政法与军事行政法[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2]辞海[Z].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
[3]薛刚凌,周健. 军事法学[M]. 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6.
[4]夏征农,陈至立. 辞海( 第六版缩印本) [Z].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
[5]陈振阳. 军制学教程[M].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
[6]张艳. 再议军事法在国家法律体系中的地位[J]. 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12( 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