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婚姻制度是家庭社会学中的关键视域, 家庭的本质即为婚姻关系, 历史上各类型的社会对于婚姻关系的内化与期待便形成了某种相对系统且稳定的婚姻制度。以颇具特色的中国古代婚姻制度为切入点, 从内容、弊端、合理性三方面作简要的功能分析, 力求对当今社会的婚姻关系有所启示。
关键词: 家庭社会学; 古代; 婚姻制度; 功能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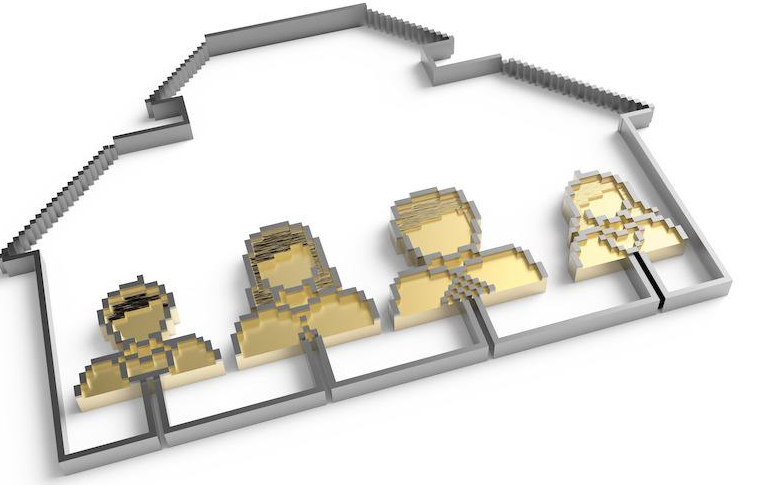
社会学从奥古斯特·孔德创立至今, 不仅理论内核日臻完善, 其分支旁系亦在不断扩充, 家庭社会学即是社会学繁花中的一枝奇葩。这门学科从产生伊始便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其原因之一在于“家庭是作为社会的细胞而存在的。家庭的和睦团结, 是稳定社会的基本因素。……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政治安定以及人才的培养教育和良好的道德风尚等”[1]1。家庭社会学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 借鉴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等多种学科的理论成果, 研究婚姻家庭变化规律。
在纷繁复杂的家庭命题之中, 笔者对于婚姻制度颇感兴趣。家庭的本质即为婚姻关系, 主要理由有以下两点:其一, 婚姻关系是家庭所固有的本质关系, 是家庭所涵盖的人际关系的基础。没有婚姻关系, 便没有构成家庭纽带的夫妻关系, 其它各种关系更无从谈起;其二, 婚姻关系是家庭独有的特质, 是“区别于动物本能的性结合的最根本特征”[1]20。历史上各类型的社会对于婚姻关系的内化与期待便形成了某种相对系统且稳定的婚姻制度。笔者以中国古代婚姻制度为主题, 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其内涵与功能。
一、“一夫一妻”与“一夫多妻”
现代人时常津津乐道于我国古代的婚姻制度, 尤其是广大男性, 一谈及古代婚姻, 无不对“三妻四妾”、“六宫粉黛”心驰神往, 俨然以为在那个时代“一夫多妻制”是受法律保护的。不过笔者在这里要先界定一个概念, 即中国古代从未实行过“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假如我们穿越回到古代并宣扬这个名词, 恐怕要被古人视为不守礼法之徒了。我国历朝历代一直恪守一夫一妻制, 即使皇帝也只有一个妻子。不过, 在社会的实际运行中却出现了“变异”, 男子被允许拥有小老婆, 即“妾”, 但不能算作合法配偶。妾下面还有通房丫头, 只有办了手续的丫头才能称妾, 比如《红楼梦》中的赵姨娘即属此类。从人类学的角度而言, 婚姻制度源远流长, 历经多次演变, 可分为“血婚制、普那路亚制 (伙婚制) 、偶婚制、父权制、专偶制”[2]18。由此可见, 我国古代实行的是一种介于父权制和专偶制之间的独特的婚姻制度。或许是人类学过多地观照了原始异文化领域而忽视了我国古代的特殊现象, 这种婚姻制度若严格界定应为“一夫一妻多妾制”, 堪称世界奇观。
通过上文的简述, 我们可以看出, 妻与妾有着严格的区别。古代的婚姻制度尊崇妻之地位, 称“娶妻”, 必须经“六礼”的程序娶进家门才行;纳妾的形式等同于买卖交易, 一般不举行特别的仪式, 有羞辱、贬低的意味, 与娶妻之礼可谓天壤之别。古人缔结婚姻的“六礼”程序自西周沿袭而来, 礼数严密、层层递进, 随社会整合的进程逐渐深入人心。首先是“纳采” (即媒妁之言, 男方托媒人到合适的女方家里去求婚) , 此后再经过“问名”、“纳吉” (占卜吉凶) 、“纳征” (下聘礼) 、“请期” (商定婚期) 、“亲迎” (结婚仪式) 等几个步骤, 婚姻才算是正式成立。值得一提的是, 上述聘娶六礼之中, 雁是最重要的礼品。这是因为, 雁是一种候鸟, 象征男女婚前互守誓约而婚后坚贞不渝;雁也是随阳之鸟, 比喻女子出嫁从夫[3]。
古代社会的价值标准与公众期待是“千年修得共枕眠”, 即男女结为夫妻后就要白头偕老、从一而终, 离婚被视为一种社会越轨行为。一旦涉及离婚, 便要严格遵循颇为繁琐的“七出”之制。“出妻”即男子强制休妻, 为古代社会最主要的离婚方式。
论及古代的婚姻制度, 其内涵极广、角度颇多, 笔者认为其中的姬妾制度是一个既独特、又具针对性的视角。
二、妾的悲剧:古代婚姻制度的负功能
罗伯特·默顿对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作了进一步完善, 他认为在分析社会结构的运行效果时, 除了着眼于正功能、显功能, 还要区分负功能与潜功能, 这使得功能主义的体系日臻成熟。潘光旦先生对功能学派颇为推崇, 他曾评价道:“我对于这比较新颖的学派是相当欣赏的, ……乃是因为它于推陈出新中能比较的综合, 比其它社会学派或文化学派为更有题目中所用的‘汇’字的意趣。”[4]386
中国古代社会实际运行的这套“一夫一妻多妾”制度, 其负功能是显而易见的, 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的整合与良性循环, 而“妾”的话题更是众矢之的。姬妾制度可谓源远流长, 大致可追溯到氏族社会时期。那时, 各氏族部落盛行的“媵制”, 为一种氏族首领才有资格享有的婚姻方式———岳家在女儿出嫁之时还必须以同辈女性陪嫁, 这些跟随而来的姐妹或者女奴, 便“顺理成章”地被男方据为己有。当封建社会来临, “妾”这种身份便正式出现了。妾在家庭格局中, 虽然也承担着生儿育女的义务, 却无法享受“妻”的待遇。此中缘由颇为复杂, 免不了一番历史背景的探究, 而最初原因与家庭出身不无关系。因为为妻之女子, 其家庭出身与男方通常遵循“门当户对”的原则, 自然要胜过“妾”许多, 而后者一般来自破落卑贱的家庭, 甚至是战败方的贡纳之礼。因此, “妻”谓“娶”, “妾”谓“纳”。娶妻时“恭送”至岳家的财物称为“聘礼”, 而纳妾时施与对方家庭的财物, 则多称“买妾之资”。身份等级的桎梏也是古人无法实行自由婚姻的重要原因, 比如西周时严格禁止贵族与平民通婚;魏晋南北朝时期推行的“九品中正制”使得门第等级蔚为森严, 士族与庶族之间的婚恋更是咫尺天涯。南朝曾有士族王源将女嫁与庶族富阳满氏, 便被当朝弹劾为惟利是求, 拟禁锢终身。
《谷梁传》有云:“毋为妾为妻”, 意即“妾”没有资格扶正为妻。嫡妻一旦去世, 丈夫即使姬妾满室, 亦仍为无妻的鳏夫, 须要另寻良家以聘娶嫡妻。妾的悲剧性身份于唐宋时已然被制律立法, 譬如《唐律疏议》明文规定:“妾通买卖”、“妾乃贱流”、“以妾及客女为妻, 徒一年半”;而《汇苑》中的阐释更是触目惊心, 定会让女权主义者暴跳如雷:“妾, 接也, 言得接见君子而不得伉俪也”, 这里, “妾”被定性为供男女交接之用, 她们只具备与夫君亲热的功能, 却无法获得“妻子”的资格。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绝对家长制的阶级社会, 婚姻大事必须由父母做主, 对自由恋爱的禁止也上升到了制度层面, 或许是为了从根本上杜绝青年男女、尤其是不同阶层间的自由恋爱, 法律条文就更要严格规定妻妾之分。《礼记》中对此有明确记载, 如“奔者为妾, 父母国人皆贱之”、“良贱不婚”, 指的是青年男女若相约私奔以追求自由恋爱的话, 则女方没有为妻的资格, 双方家族都只承认她不过是小妾而已。白居易曾有感于这种“奔者为妾”的社会现状而创作了新乐府《井底引银瓶》。诗中记载了一个“有殊资”的良家女子, 只因与爱人私奔, 便从此丧失了身为人妻的资格。她侍奉了丈夫与公婆五六年之久, 都无法换来男家的认可。不仅如此, 她甚至没资格涉足家族祭祀, 所生之子亦不算夫家首选继承人。白居易在诗的结尾慨叹:“为君一日恩, 误妾百年身。寄言痴小人家女, 慎勿将身轻许人。”[5]65
此外, 由于“姬妾”只是一种商品, 可谓“命比纸薄”, 古代男子平日里不免对“妾”实行非人道的待遇, 家庭暴力、性虐待可称家常便饭, 而且有着“合理化”的倾向, 毕竟“妾”只是“交接之用”。
“姬妾”之制所蹂躏的, 不仅仅是这些被误终身的女子, 爱她而无自主权的丈夫、子女, 都在这种制度下有苦难言。男子只能与父母们选定的嫡妻同床异梦, 无计可施地看着心爱的女人沦为嫡妻的生育工具。这种不合理的婚姻制度, 千百年来上演了多少人间悲剧?它是强加在我国古代妇女身上的沉重枷锁。若以现代社会的文化规范来衡量, 这种“姬妾制度”不免有些剥夺人权、惨无人道。因为它将“阶级”元素嵌入了家庭与亲情的结构之中, 强行把血脉相连的一家人异化成压迫与被压迫的两类, 严重制约了家庭内部的积极互动与人际关系建构。儒家常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理想, 家庭的协调发展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石。如此看来, “姬妾制度”对家庭所造成的负功能, 无疑将导致整个社会结构的失调。
三、古代婚姻制度的合理性
一种社会制度纵然千疮百孔, 我们还是要注意到它的正功能。一旦正功能符合了特定时代与社会的实际情况, 适应了生产力的要求, 甚至满足了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利益, 这种制度也就具备了合理性, 进而存在于历史长河之中。诚如马克思所言, 权利永远无法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这种结构所制约的社会、文化发展。“早婚”及“媒妁之言”是中国古代婚制的基本原则, 现代人几乎都会批判“这些原则是对古代纯真爱情的一种束缚, 因为它剥夺了适龄青年自由寻找幸福的权利”[6]49。然而, 若采用功能分析的方法, 站在历史的高度, 从问题产生背景的角度出发, 还是可以发现其合理性的。
比照现代社会的结婚年龄, 古人婚龄不免颇早。史料曾有记载, “越王勾践欲报吴仇, 凡男二十, 女十七不嫁者, 罪其父母”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唐太宗于贞观元年下诏:“男二十, 女十五以上无嫁者, 州县以礼聘娶。”唐玄宗时又将婚龄继续提前, 男子十五、女子十三岁以上时必须嫁娶。这种婚姻状况是由其所处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社会, 医疗卫生水平不尽如人意, 人均寿命只能维持在40岁上下。倘若结婚年龄仿照当今法律规定, 依当时的历史条件是无法保证种族繁衍的。对古代的婚龄进行分析, 若“16岁结婚, 到40岁去世时, 其长子女20有余, 已结婚成家, 故完全可自主谋生”[6]49。而且, 其他子女一般也可投身社会劳动, 即便幼子尚小, 长子女也可肩负起监护、教育的责任, 这正是古时“长兄如父, 兄嫂如母”的真实反映。因此, 受古代社会生产力的掣肘, 早婚被认为是种族社会存在与延续的必然选择。此外, 中国古代生产技术以手工劳动为主, 一家一户为生产基础单位的家庭社会结构模式, 其再生产能力比较脆弱, 而扩大再生产的有效途径就是劳动力的大量投入, 早婚正可加速这种投入, 此为客观推动力。
“媒妁之言”固然制约了男女自由恋爱的发展, 但也不应忽视其本身的优点。若追根溯源, 这种方式仍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密不可分。男耕女织的生产方式里, 除了与存在血缘、地缘关系的人发生颇为有限的往来之外, 没有必要与其他人发生更多的联系, 此即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 再受限于交通闭塞、地广人稀之客观阻力, 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频度。由此, 一旦有从属不同交往集团的家庭欲建立姻缘关系时, 势必要依仗中介, 而当时“媒人”是一个所谓积德积善的“朝阳产业”, 真可谓一拍即合。更何况, 现代男女固然实现了自由恋爱的理想, 但“门当户对”的标准仍旧是选择伴侣时的一个评判尺度。因为“门当户对”意味着相似的成长经历与生活习惯, 即双方拥有“共同语言”, 可以最大程度地保持日后夫妻生活的和谐及持久。媒妁多为老熟人、老邻居, 在一个信息相对匮乏的社会里, 能够优化、整合婚配资源, 最终达成“门当户对”的目标, 实在要比当今的婚恋节目高明不少。除此之外, 媒人还承担了监督近亲婚配的责任, 她们更近似地发挥了民间舆论的正功能。
费老曾阐述过对婚姻的看法:“结婚不是件私事, 婚姻是由社会力量造成的。”[4]449我国古代婚姻制度是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相辅相成的, 可视为长期社会生活实践的产物。以历史的角度而言, 它兼有长期存在的合理性及适时性, 亦源于其尽可能平衡了各方利益, 故引致历代统治者的推崇与世人之认可。
人类学纪录片《酋长的第五任新娘》阐述了关于婚姻制度的道理:任何婚姻制度的文化都不是横空出世的, 它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与时代背景中产生的, 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现代人也许很难理解古代婚姻制度的意义, 亦无法评判其优劣性, 然而我们却不能否认它的存在。譬如, 有些社会学者曾在非洲做过实地调查, 研究结果不免令很多现代人费解———“时至今日, 许多受教育程度不高的非洲女性仍然认为一夫多妻制对她们是有利的, 因为这是让她们能够接触到那些具有较高地位并且拥有较好经济资源的男性的一种途径”[7]99,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婚姻制度无法超越时代而独立存在。正如恩格斯所言, “群婚制是与蒙昧时代相适应的, 对偶婚制是与野蛮时代相适应的, 以通奸和卖淫为补充的一夫一妻制是与文明时代相适应的”[8]51。当今西方已逐步迈入后现代主义社会, 时代的演进对婚姻制度也产生了冲击, 换妻、同性恋、性爱俱乐部等现象愈演愈烈, 我们不禁心生疑云:现行的婚姻制度会顺应社会发展出现哪些变化?中国的婚姻制度将何去何从……这些问题将是今后家庭社会学领域所重点关注的。
参考文献
[1]郭俊丽, 胡健.理想家庭探寻———家庭社会学漫议[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7.
[2]朱炳祥.社会人类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4.
[3]韩冰.中国古代婚姻制度[J].半月选读, 2009 (16) .
[4]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5]白居易集[M].严杰, 注.南京:凤凰出版社, 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