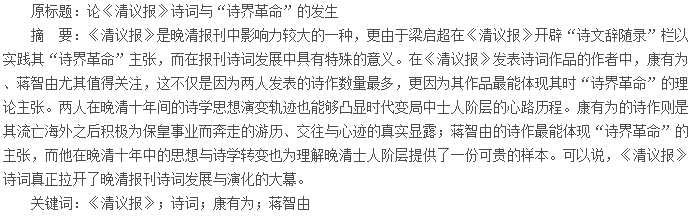
梁启超参与办报活动,始自1895年创办《中外纪闻》时期,其后陆续主编十余种报刊至1920年才“正式脱离报馆生活”。纵观其办报生涯,在国内时期,主持《时务报》,令梁启超声名鹊起,而流亡日本后主持《清议报》、《新民丛报》无疑是其辉煌的顶点。李泽厚认为,1898年至1903年是梁启超作为资产阶级启蒙宣传家的黄金时期,是他一生中最有群众影响,起了最好客观作用的时期。李泽厚甚至还着重指出过,“《时务报》时期,梁氏的政论已风闻一时,在变法运动中起了重要的宣传作用。
但梁氏所以更加出名,对中国知识分子影响更大,却主要还是戊戌政变后到1903年前梁氏在日本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撰写了一系列介绍鼓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文化道德思想的文章的原故。”
可以说,《清议报》、《新民丛报》时期,既是梁启超影响力最大的时期,也是其超越康有为思想藩篱、形成自我文化认知的重要时期。文学方面,《清议报》、《新民丛报》阶段的梁启超,其以“诗界革命”观为代表的“文学新民”观念尤其值得关注。在《清议报》发表诗文的作者中,康有为、蒋智由更与之有桴鼓之应。
一、《清议报》“诗文辞随录”:诗界革命的号角
于所主持报刊中,辟专栏刊发诗歌,在梁启超是自然之事,毕竟梁本人及其师友圈中多为熟稔诗词创作之文人,凭借诗词为媒介以沟通联络是他们所习惯的方式,而其“诗界革命”观念的形成,及借由报刊来推动“诗界革命”,则与晚清以黄遵宪为代表的新学诗-新派诗的发展密不可分。
不可否认,梁启超的“诗界革命”说是在黄遵宪、夏曾佑等人触动下而提出的。梁启超对以黄遵宪为代表的新派诗给予了理论上的概括,并于1899年在《汗漫录》一文中提出了“诗界革命”的口号。同时,在该文中,梁启超对“诗界革命”提出了三重要求,即新意境、新语句、以古人之风格入之。这一要求无疑是极高的,它既要求诗的新开拓,又要求承续中国诗的传统。因此,即便是梁启超推举的黄遵宪、夏曾佑、谭嗣同三人,梁氏也指出了他们的不足。然而,梁氏的“诗界革命”,又并非是以“诗界”之革命为归依的,而是以“诗界”之革命,“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这当中至少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梁启超论诗极力推重黄夏谭三人,这与其早年与三人的密切交往有关,二是梁启超的论诗,实则是论学,而其所论之学,正是黄、夏等人所求之新学,且最终乃是“欧洲之精神思想”的西学。梁启超曾回顾其与谭嗣同、夏曾佑论学情形,三人曾“衡宇望尺咫”,逐日问学辩难。梁启超回忆说,“穗卿自己的宇宙观人生观,常喜欢用诗写出来”。这实际说明了当时三人诗文过从之密切,而他们皆是“治乾嘉派考证学有相当素养的人”,此时相与论学却认为“中国自汉以后的学问全要不得的;外来的学问都是好的”。虽然梁启超批评夏谭二人之新学诗,在新语句的追求中,失去了旧风格,以至“已不备诗家之资格”,但结合三人论学之情形,与追求“欧洲意境”、“欧洲精神”的“诗界革命”理论对读,则不难发现,正是在北京三人的交往中,新学诗的基础支撑起了梁启超“诗界革命”的大旄。
1895年与夏穗卿、谭复生论学作诗的梁启超,可能还没有达到以诗“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的理论自觉,然而,这一时期之后,以黄遵宪为代表的“新派诗”蓬勃发展,梁启超的诗歌革新观念逐渐清晰起来。而利用报刊发表诗歌、鼓吹“诗界革命”理论,在《清议报》、《新民丛报》时期,便成为自然而然之事了。
梁启超于1898年10月20日抵达日本东京,不久之后的12月23日,即于横滨创办《清议报》。该报为旬刊,月出三期,每期40页,三万余字,连史纸印刷,装订为书本式,至1901年12月21日该报停刊,3年共出刊100期。其时,梁启超仍为清廷通缉要犯,《清议报》的署名印刷人为日人铃木鹤太郎,编辑兼发行人则署英国人冯镜如,而梁氏则为实际主编。
3年中,梁启超曾于1899年往檀香山、1900年往澳洲,这期间由麦孟华主持报务。梁、麦二人皆是康有为万木草堂中高弟,由此奠基了该报的基调,“专以主持清议、开发民智为主义”,实际上则成为维新派在海外的舆论中心。这一时期,梁启超的“文学革命”思想逐渐成熟,《清议报》自创刊号起便辟有“诗文辞随录”栏(在《清议报全编》出版时,亦更名为“诗界潮音集”),共刊发诗作526题。其后,《清议报》停办,梁启超继而主办《新民丛报》,其影响力更胜过《清议报》,黄遵宪称“《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今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新民丛报》继续办“诗界潮音集”专栏,自1902年2月8日第1期始,至1904年10月9日第54期止,其中27期有该栏,自55期后则专发梁启超《饮冰室诗话》,成为引领“诗界革命”之潮音的最主要阵地。
《清议报》既是维新派在海外创设的机关报,又以万木草堂诸子为核心,其诗词作者群便以万木草堂师弟及其友好为主。而至《新民丛报》,梁启超的思想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思想发展上,逐渐脱离了康有为的方向,所以《新民丛报》“诗界潮音集”中诗作,内容上如潮音般,更趋激烈;作者群体则脱离了康门弟子为主的状态,如蒋智由、高旭等人的作品占据了主要地位。考察从“诗文辞随录”到“诗界潮音集”的变化,其内容、作者队伍、思想倾向的变迁,不仅昭示了梁启超“诗界革命”思想和“诗界革命”实践的发展脉络,且能见出此一时期梁启超思想的“流质易变”般的激烈变化。
“诗文辞随录”栏目自《清议报》创刊伊始便开辟,一方面是维新派在国内运动的失败以及清政府的反扑带来的维新派牺牲之惨烈,在维新派思想中造成了激烈的情绪,而流亡生活中的康、梁等与其他维新派人士的情感联络客观需要,使得诗歌成为最佳的载体,而《清议报》的媒介影响力也能保证这一栏目稿源不断。在“诗文辞随录”栏中发表诗作的诗人共有150余位,诗作发表数量超过10首的诗人有梁鼎芬(毋暇)共38题81首、康有为(更生)共45题78首、谭嗣同33题48首、蒋智由(观云、因明子)45题56首、梁启超(任公)21题54首、邱菽园(星洲寓公)19题、麦仲华(?庵)7题等人。这当中,谭嗣同诗作为遗作,因此除康、梁、麦师弟外,“诗文辞随录”中的诗人尤值得关注的便是梁鼎芬、蒋智由等人。康梁师弟间以罹祸罪身流往海外,尤其是康有为,在《清议报》刊发诗作颇为可观,一方面在于为戊戌间一段史实留存诗史,另一方面自其诗作亦可察知此间师弟思想之迁演;梁鼎芬氏以张之洞幕中最得力维新幕僚而在戊戌间与康梁由故交而仇雠,其对康有为、黄遵宪等人在维新变法前后态度变化之巨,向为人诟病,而“诗文辞随录”披露之梁鼎芬诗作或可揭示此一时期真实梁鼎芬与表现梁鼎芬之差距,此中或可见出当时中国士人文化心态的复杂性;蒋智由的思想变化,则可以说构成了此一时期的一份典型,他先是积极鼓吹维新变法,特别是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他的态度反而转趋激烈,甚至发表了大量带有排满色彩的诗作,梁启超对蒋智由诗作的推崇中便有对其这一态度的肯定;其后却政治上保皇立宪,至民国而为遗民,较梁启超的态度转化又令人愈发惊讶,其诗作上也一改报刊诗词的色彩而为同光体诗人所激赏。研究此一时期的诗学转向,可以说,蒋智由是极具研究价值的。
二、《清议报》中康有为的海外诗作
戊戌政变后,康、梁师弟东渡日本。梁启超先行抵达,筹办《清议报》。康有为则自香港辗转赴日,开始了长达15年的海外流亡和旅居生活。在这15年中,康有为创作了大量诗歌。自抵达日本到1899年游历加拿大、英国,创立保商会(保皇会),再返日本,1900年应邱菽园请赴新加坡,7月赴马来西亚丹将敦岛,旋即居英督署大庇阁居又年余,《清议报》“诗文辞随录”栏所刊康有为诗作,署名“更生”,大率作于这一段时间,收在其《明夷阁诗集》当中。
《清议报》创刊后,先前在日本东亚同文会机关报《东亚时论》上刊载的梁启超名著《戊戌政变记》即同时在《清议报》刊发,内容皆是回顾戊戌政变、抨击后党。而此时《清议报》刊康有为诗歌也主要是这样的内容。在日本的康有为片刻不忘国家,沐浴温泉时,看“热海涌烟冲地上”,所思却是“太平洋远天还近,夜夜惊波却不平”,时刻系念光绪帝与国内形势,应该说是康有为此一时期诗作的主要思想倾向。若以题材来分,康有为在《清议报》上发表的诗作,大约可以分为纪事类、游览类、赠酬类三种类型,在日本期间,康有为与从亡诸子及日本各界人士偕游富士山等日本名胜,诗作多记录其交游情况。《清议报》上的这些诗作便反映了此一时段内康有为的生活状况。
1.纪事之作
戊戌变生,康有为作为首犯,遭到清廷的追捕与暗杀。人生经此一大变,康有为将此中曲折诉诸诗文。这些诗文经《清议报》的传播,于其个人,固然是情性激越,不得不发,于社会舆论,则是博得舆论支持,争取保皇力量的绝好动员令,对于后党则无异于一纸纸檄文。
《清议报》创刊号“诗文辞随录”栏刊载康有为与谭嗣同诗,其中康有为诗为《戊戌八月国变纪事四首》。据《康有为全集》,有为戊戌变法期间诗仅《怀翁常熟去国》一首,政变起至日本前,则有数首,分别为《戊戌八月纪变八首》、《戊戌八月国变纪事》,其中《清议报》创刊号所载即为《戊戌八月国变纪事》。诗中“小臣东海泪,望帝杜鹃红”、“更无敬业卒,空讨武+文。痛哭秦庭去,谁为救圣君”等句,皆是哀哀惨惨、痛哭救君之语。诗笔所录,不惟一段史实纪事,亦是当时流亡心境的表露,其意盖为唤起“勤王”之军、“敬业”之卒。《戊戌八月纪变八首》,据《康有为全集》则仅存其五。《全集》所录五首原无题,以自注为题,并言“今佚其三,乃怀徐东海及哀诸新参也”。这一组诗曾于《清议报》第五册刊载,对照发现,全集认为的三首佚诗,实则于《康有为全集》中已见编排,其一题为《八月九日在上海英舰,为英人救出,得伪旨称吾进丸弑上,上已大行。闻之一痛欲绝,决投海,写诗系衣带。后英人劝阻,谓消息未确,请待之,派兵船保护至香港》、其七、八两首则题为《住香港半月,日本总理大臣伯爵大隈重信招游,令前驻中国公使矢野文雄电告九月二日乘“河内丸”。遂东》,《康有为全集》视为另诗进行编排,以至于误以为《戊戌八月纪变八首》组诗有三首佚失。这一组诗,据全集五首,诗后皆有自注,《清议报》所载则无自注,《清议报》与《康有为全集》两相对照,则可知,《康有为全集》中另行编排的三诗诗题,正为原诗中诗注。《戊戌八月纪变》与《戊戌八月国变纪事》两组诗,可看作是康有为对戊戌变法失败的沉痛表达:一方面抒写维新壮志未酬、后党大肆张捕下对光绪帝的愧意与忠心;另一方面是对维新死难志士的哀悼,其中既有前路未卜、谁为救君的迷惘,但更有“不信神州竟陆沉”的坚定信念。虽时有感伤、悲痛,但康有为人格执毅,此刻心中仍抱定坚定信念,在《赠日本驻港领事上野季三郎》中,康有为写道:“横飞金翅决青岑,不信神州竟陆沉。龙战玄黄翻海水,鲲图南溟动潮音。岱宗灵气连员峤,帝座星辉豁太阴。击揖感君相济意,共看腰剑作龙吟。”这首诗编次失确,在《康有为全集》中被编入《万木草堂诗集》的最末一首。考其诗意,乃是1898年居港半月后即将东渡日本时赠诗,须编入《明夷阁诗集》方为妥当。诗中“不信神州竟陆沉”的语句数番出现于此一时期康有为诗作中,而“共看腰剑作龙吟”,则直接表露了其维新壮志不曾少歇。
除去纪录戊戌一段史实的诗作之外,康有为的纪事之作,还有重要一类,即对国内时局的关注与纪录,诗作中多是对列强环伺下的国家危局之忧虑与焦灼心态。如《清议报》第10册刊有《闻浙事有感》:“凄凉白马市中箫,梦入西湖数六桥。绝好江山谁看取,涛声怒断浙江潮。”
《康有为全集》以《闻意索三门湾,以兵轮三艘迫浙江。有感》为题,说明了此诗写作之缘由,即1899年意大利强索三门湾事件。由于中国政府态度的强硬以及列强的压力,实力较弱的意大利侵占三门湾的图谋最终被挫败,康有为诗中表达的正是在事态还不明朗时的焦虑。此一事件中,清政府最终取得外交胜利,这也助长了后党顽固势力的气焰。
1899年的中国正在危难时局中愈陷愈深,固然清廷能够挫败二流列强意大利的侵略图谋,却无力阻止中国陷入被瓜分的泥沼。此前,1898年11月14日,德国庆祝占领胶州湾一周年,其时并立石志念。康有为阅报之后悲愤异常,写下了《阅报见德人贺得胶周岁时,又得杨漪川狱中诗,题其后》:“胶海输人又一年,维新旧梦已成烟。山河残破成何事,大鸟飞来但黯然。”从这些诗作中皆可见出康有为当时忧心国事之心境。
流亡在外的康有为忧心国事的表现,其一是关注国内外的政治局势,其二便是对光绪皇帝的感恩与祷祝。
1899年六月十三为光绪圣寿,时康有为在加拿大,有诗《六月圣寿节美洲各埠创行恭祝礼吾居文岛望阙行礼又还埠与乡人叩祝湾高华及二埠尤闹西人来庆颂饮酒者数百人也》祝寿,载于《清议报》第28册。该诗在《康有为全集》中,诗题为《己亥六月十三日,与义士李福基、冯秀石及子俊卿、徐为经、骆月湖、刘康恒等创立保皇会。于二十八日至域多利中华会馆。率邦人恭祝圣寿,龙旗摇?,观者如云。湾高华与二埠同日举行。海外祝嘏自此始也》,说明了此诗创作之背景,从当时来看,则恭祝万寿乃是创行,自历史来看,则“海外祝嘏自此始也”。康有为这种万寿祝寿行为,在《清议报》中所录不惟此一例,次年六月十三日,即1900年的六月十三日,康有为已徙居新加坡,亦有祝寿诗《六月万寿望阙即叩祝恭纪》。时八国联军已在攻打天津,京城中清军也在攻打法国领事馆和东交民巷,时局大乱之下,康有为在庆幸圣躬无恙的同时,亦在积极谋划勤王之事,其后方有唐才常自强军之事。这一首《六月万寿望阙即叩祝恭纪》作于康有为居新加坡邱菽园处时,《康有为全集》诗题为《皇上三十万寿时大乱,京津消息多绝,幸圣躬无恙,小臣在星坡,与梁尔煦、汤睿设香案龙牌,望阙叩祝。时邱炜裷鼓舞星坡人,全市祝寿极闹,前此未有也。恭记》,可知康有为所记是新加坡全城为水深火热中的光绪帝祝寿之事。
是时,战争形势已趋激烈,其后月余,康有为时见外国军舰经南洋而北上,有诗《七月朔入丹将敦岛,居半月而行,爱其风景,与铁君临行,回望不忍去。然联军铁舰日绕岛入中国,见之忧惊,示铁老》。眼见铁舰北上,康有为心情想必极其复杂。当唐才常勤王军起,康有为不禁写下《自星坡移居槟榔屿。京师大乱,乘舆出狩,起师勤王,北望感怀十三首》,一气赋诗13首,“行在无消息,看云但黯伤”,满是对皇帝的忠诚。孰料唐才常事不周密,旋即殉难,《北难日急,江南军来归,联合五省义士兴师勤王。将用日本挟藩之策,先行之武昌,事败。七月十八口,门人唐才常殉难汉口,烈士林圭等死者三十人。祭之哀怆心肺》。对康有为的这些勤王失败、悲怆痛苦之作,《清议报》未曾刊发。但唐才常的这次失败,对于康有为的打击是不言而喻的。《清议报》第六十三册刊发康有为《闻菽园欲为政变小说诗以速之》,诗为邱菽园欲作戊戌政变小说而作,内中有句:“旧党献谀狂一国,大周受命颂??。是非颠倒人心变,哀哉神州其陆沉!”向来是不信神州竟陆沉的康有为,竟发出如此哀叹,可见内心悲愤。
康有为的这些纪事诗作,具有强烈的“我”之色彩,这与康有为的个性不无关系。虽以我观世界,则世界莫不着我之色彩,以之与相关史料比对,则不仅可为诗史,更可见出一代维新巨人在此间之心路。可以说,诗史亦即康氏心史。
2.游历、酬赠之作
从1898年出亡日本,至《清议报》停刊的1901年末,康有为从日本至加拿大,短暂游历欧洲,居加拿大亦不久,又返日本,于1900年正月即赴新加坡,此后,在新加坡邱菽园、林文庆处、马来西亚丹将敦岛、槟榔屿大庇阁等留居一年有余,于1901年十月启程赴印度,在大吉岭留居半年。三年多时间里,康有为辗转东西半球,往来南北数国,与东西人士多有交往,写作了众多诗作,其中他的许多海外游历写景之作,颇有雄奇之处。《清议报》曾刊登了多首康有为的这一类作品。
康有为抵达日本后的生活情况,据康同璧(文?)言:“(1899年)正月,先君居日本东京明夷阁。
时与王照、梁启超、梁铁君、罗普等重话旧事,赋诗唱和。日相大隈伯、文部大臣犬养毅、外务大臣副岛种臣、内务大臣品川子爵、名士松崎藏之助、柏文郎、陆实、桂五十郎、滨村藏六、陆羯南三宅等,亦常来游。”
在日本的交游中,康有为写下了一些游览、酬赠之作。其第一首游览之作,是名篇《浴伊豆热海登鱼见矶》:“鱼见矶头孤屿青,冥冥云水见渔艶。茫茫身世双筇杖,莽莽乾坤一草亭。热海涌烟冲地上,怒涛卷石带梵听。太平洋远天还近,夜夜惊波却不平。”诗作以《热海鱼见矶》为题刊于《清议报》第2册。热海温泉地处伊豆半岛,是日本第一大温泉疗养地,依山傍海,美不胜收。而此时康有为所见,却是怒涛惊波,以热海温泉之景写心中之波澜。距离热海不远,即是箱根温泉,对此,康有为也有诗纪之,刊载《清议报》第4册、第5册,分别是《游箱根宿塔之泽环翠楼温泉浴》、《日暮登箱根顶浴芦之汤》及《自宫之下温泉冒雨下至塔之泽仍宿环翠楼》。据《康有为全集》,诗题为《同(原注:“同”下,稿本有“柏原文太郎”)梁任甫、罗孝高游箱根,宿塔之泽环翠楼,浴温泉》、《登箱根顶芦之汤》、《自宫之下温泉冒雨下山,仍宿塔之泽环翠楼》,可知,这一次是与柏原文太郎、梁启超、罗普同游。沐浴温泉,康有为却心绪不宁,前诗中说“温泉疗百疾,我心不可浴”、“秋心不能收,随之听飞瀑”。在诗中,康有为一方面深感此地非吾土,数度表示“怅怅非吾土”(《登箱根顶芦之汤》),“终已非吾土”(《自宫之下温泉冒雨下山,仍宿塔之泽环翠楼》),一方面又踯躅迷径路,想要留,却是“惜非吾土难淹留”(《芦湖楼望富士山》)、“岂得长盘桓”,身居异国,康有为却是“夜听呜咽声,梦魂绕长安”(《自宫之下温泉冒雨下山,仍宿塔之泽环翠楼》)。对照日本与中国现状,每有登临,辄思故土,“蓬莱回首望神州,大海波涛荡不收。忧甚陆沉天莫问,深深春色独登楼”(《登楼》;《清议报》第10册)。这种因面对日本繁华胜景,回顾故土难归带来的惆怅与愤恨,除了在康有为的这一系列日本游览诗中集中表露外,在他与日人的酬赠之作中,情感更是强烈。
如前所述,康有为抵达日本之后,与日本名流多有交游,刊载于《清议报》的赠日人之作,有《湖村先生以宝刀及张非文集见赠赋谢》(第6册,《全集》题作《桂湖村以日本刀及〈张非文集〉见赠,赋谢》)、《答山本宪君》(第7册,《全集》题作《答山本宪》)、《佐佐友房君以所撰战袍日记见赠》(第8册,《全集》题作《日本国民党领袖(原注:“领袖”,稿本作“首领”)佐佐友房以所撰《战袍日记》见赠,赋谢》)等数首。这些诗作,除去应酬语句外,多有两国比照,感慨惭愧之语,以《佐佐友房君以所撰战袍日记见赠》为例,该诗题注“佐佐君为维新勋臣(“勋臣”,稿本作“元老”),尝从西卿隆盛举兵(“举兵”,稿本作“起兵”),日记即记此事”,以佐佐氏之功绩,比照自身:“读君幽囚作,壮气起顽鄙。回首顾神州,尧台囚圣主。金轮成牝朝,谁为勤王起?奄奄待国亡,愧此健男子。”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思想原本就受日本明治维新和俄国彼得大帝改革等君主立宪实践的影响,此时,亲身感受,自然感慨良多。在这些酬赠诗作中,康有为或对佐助天皇成就维新事业的日人,表示出敬意;或对着意于孔学、礼乐文化的日人,表示出赞赏,而这些情感无不是在与自身、国人的对照中表示的。康有为对慈禧之痛恨,从诗中也可见一斑,斥其为“牝朝”,不愿“偷生甘为牝朝奴”(《湖村先生以宝刀及张非文集见赠赋谢》)。
除了将维新等新词语纳入自己的诗作当中,康有为在海外,目睹着“太平洋远天还近”的海上风光、感受着欧风美雨的现代文明沐浴与日本等国的崛起,西方文明对其诗风亦有影响。
1899年春,康有为二月十二日去横滨,赴加拿大及英国。比照当年去日本,面对太平洋时,发出“海水排山通日本,天风引月照琉球。独运南溟指白日,鼋鼍吹浪到沧洲”的感慨,这一番船行更广阔的大洋,康有为从容了许多,“老龙嘘气破沧溟,两戒长风万里程。巨浪掀天不知远,但看海月夜中生。”(《己亥二月由日本乘“和泉丸”渡太平洋【题下,稿本有注文:“以十二日出横滨,二十七日到加拿大”】》,《康有为全集》12册,第196页。)二月二十七日,康有为抵达加拿大。数天后的上巳后四日,康有为曾游加拿大温哥华公园,有诗纪游《上巳后四日与东洲兄游温哥华园泊,樱花思东国旧游并送东洲兄还国遍示东国故人正樱花大放时也》及《东洲兄还国再赋一章并呈犬养木堂柏原东亩桂湖村陆羯南藻洲子宫崎君及诸故人亦足知游者之情也》(《清议报》第16册,《全集》题作《上已后四日游加拿大湾高华公园,送译者还日本,呈东国诸公》)。诗中写道:“未敢回头思汉月,却看江户是乡亲”,可见出康有为对在日友人的感情。这之后,康有为过洛基山、渡大西洋,数月间往来于英国与加拿大。眼中所见,自然不乏新事物与新名词,沿途风光,也是人所罕见的奇景。比如“三月乘汽车过落机山顶,大雪封山,雪月交辉,光明照映,如在天上。其顶甚平,译者请名之,吾名为太平顶”。诗中不仅有新事物“汽车”、“铁路”,更有新知识“峰峦直走美洲南”,对洛基山脉地理知识的了解,以梁启超“新意境”、“新语句”、“古风格”三长的诗界革命诗歌标准,康有为的诗作,惟缺“新意境”,即《汗漫路》中所说之“欧洲之精神思想”。实际上,康有为的诗作中处处可见其以国外之新比附中国传统之处,如《清议报》第25册刊载康有为《游加拿大记》,其中有诗句:“飘泊余生北美洲,左贤特为写形留。风鬓十八红衣女,却是中原顾虎头。”
诗作所写是加拿大18岁的女画家于都琅杜为其画像之事,欲扬誉画家画技,却以东晋名画家顾恺之比拟,从中大约可见康有为对东西文化之态度。
但是,大西洋、北冰洋中的绝域,毕竟是人间奇境,中国诗人向少诗笔书写,康有为旅行途中写下的诗作颇有鬼斧神工之笔,前人所评“雄奇”,这些诗作堪称名副其实,如《四月乘船渡大西洋近北极,晓见二冰山高百丈,自北冰海流来者,船人倾视,诚瑰玮大观也》便写得极为壮观,与早年想象中的“东渡扶桑观日出,蓬岛新开列仙宫。望洋渐作太平想,合众国土期大同”,已是全然不同。康有为此次自加拿大赴英,乃是求助于英国以图光绪复辟,途中得见百丈冰山、北极冰海的绝域风光,诗作酣畅淋漓,有一扫愁云之感。然而,求助英国之事未谐,康有为旋即返回加拿大,诗中便又是“茫茫大地又何依”的愁绪了。
也许正是康有为加拿大、英伦之行成果不多的缘故,《清议报》中刊发康有为此一时期诗作较少,却刊发了其数首旧作,这些诗歌,或是赞扬甲午主战(《顺德二直歌》,《清议报》第24册),或是送行勉励门生(《送任甫入都》,《清议报》第18册,《全集》题作《送门人梁启超任甫入京》)、或是酬赠台湾抗日人物(《游桂林宴某公席间作》,《清议报》第19册,《全集》题作《丁酉元夕,前台湾总统唐薇卿中丞夜宴观剧,出除夕诗见示。即席次韵奉和》),或是上书不成出都之作(《出都作》,《清议报》第17册,《全集》题作《出都留别诸公》,有诗序“吾以诸生上书请变法,开国未有,群疑交集,乃行”)。康有为在加拿大,一方面为保皇事忙碌,另一方面恐与《清议报》方面信息交流亦不顺畅,虽时有制作,却也未能及时寄达《清议报》处。
《清议报》上康有为诗作再次出现是他旅居南洋之后。康有为赴南洋是受新加坡巨贾、有南海诗宗之誉的邱菽园的邀请,邱菽园对维新运动抱支持态度,在1898年四月初七日,创办《天南新报》,于新加坡呼应康梁的变法运动。次年末,邱菽园寄赠康有为千金,并邀请康有为赴新加坡。康有为写作《邱菽园孝廉未相识,哀我流离,自星坡以千金远赠。赋谢》、《菽园投书邀往星坡,答谢》等数首诗歌以示感谢,并于1899年十二月廿七日携梁铁君、汤觉顿、康同富启程赴新加坡。是年,康有为在新加坡渡除夕,有诗句“忽忆前年燕市夜,酒酣击筑梦中原”(《星坡元夕,乡人张灯燃爆,繁闹过于故国。触续伤怀,与铁君、觉顿、同富侄追思乡国》,《全集》12册,第201页)。康有为此番赴新加坡,不久即发生庚子八国联军入侵事件,康有为于是在南洋谋划自立军勤王事。这一段时间,《清议报》刊发的康有为诗作共10题,其中有多首为赠邱菽园之作,每一首中都可见出康有为对邱菽园的赞赏,而这种赞赏,是源于同邱菽园在维新救国事业上的同志关系。比如《题邱菽园〈看云图〉》,诗中写道:
“邱生奇气世无有,登高横脱八荒久。看云愤慨难袖手,被发问天天听否?誓呼大风扫群丑,溟海苍苍顽雾厚。抚剑间天天宇剖,绝顶独立无人从。”诗中写邱菽园之“奇气”,写邱菽园之“愤慨”,又何尝不是康有为自写心胸,正是这种志同道合,使两人走到一起。邱菽园在《六月万寿随南海先生望阙叩祝先生有诗并属和作》中写道:“翘首神京白日阴,讴歌犹系旅民心。即今万寿称同庆,见说群雄战更深。孝治官家信浚井,风流巨庶自挥琴。诸贽托命中原主,愿祝中天复旦临。”(《清议报》1900年第61期)从诗中可以见出邱菽园对光绪皇帝抱有的感情,这种感情是建立在一个“旅民”对故国神京的感情之上的,这一点与康有为对光绪皇帝感恩的感情并不完全一致,这也是邱菽园后来政治主张发生变化而康有为坚持保皇立场的原因。但此一时期邱菽园对康有为是深怀着敬慕之情的,在康有为甫一抵达新加坡,邱菽园便写有《庚子开春之三日喜晤南海先生承示除夕舟中诗叠韵赋呈》,诗作:“出亡久噬明夷毁,系易翻疑未济终。正则行吟天欲问,东山避地雨其蒙。觚眣梦断江湖囗,岛国春归草木风。回首尧台违万里,义旗会盼出艨艟。”(《清议报》1900年第62期)然而,康有为抵达新加坡后,在南洋积极谋划勤王行动,邱菽园的大力资助引来了清王朝尤其是张之洞的迫害,邱菽园与康有为的关系便发生了变化。《京津大乱乘舆出狩北望感怀十三首》组诗,《康有为全集》题作《自星坡移居槟榔屿。京津大乱,乘舆出狩,起师勤王,北望感怀十三首》,其中,省却的关键词,为“起师勤王”四字,即庚子年康有为等谋划的自立军勤王之事。在整个事件谋划、发展期间,张之洞不仅直接杀害了唐才常等人,将自立军勤王扼杀于未然,更对邱菽园进行了策反工作,使邱菽园不得不登报声明与康有为决裂。这便是邱菽园在《天南新报》上发表的《论康有为》一文:大抵康之为人,“结党营私”四字,乃其死后不磨之谥,而其结党之法,则以其学问为招徕之术,以大帽子为牢笼之方,善事之徒,一与之游,无不入其彀中,此则戊戌以前在粤聚徒及在京结党之手术也……噫!君子绝交,不出恶声,不佞以不设城府待之,被其若推入党,诚难与众辩论。
应该说,在自立军勤王事件之后,邱菽园的这种态度,同1898年梁鼎芬与康有为等人的决裂有相似之处。邱菽园与康有为的决裂是迫于压力,梁鼎芬与康有为等人的决裂也是迫于压力,只不过邱菽园身在海外,与梁鼎芬“小之洞”的身份差距悬殊,也正因此,邱菽园在刊发声明,对“压力来源”交差之后,却依旧与康有为等人保持较为密切的关系,并仍旧在《清议报》等刊发诗作;而梁鼎芬却只能以不为人知的笔名“毋暇”在《清议报》上发表诗作,与康、梁维新派人士保持着私下的秘密联系。
庚子勤王失败后,康有为庇居英督署大庇阁年余,于1901年十月离开南洋,赴印度。《清议报》亦停刊于是年。纵观康有为在《清议报》上的诗作,无论是纪事、游览或酬赠的哪一类,其情感与思想无时无刻不停留在维新与保皇的事业上。其诗作或是对维新变法的失败表示痛心、对后党逆行进行挞伐,或是对光绪皇帝表达感恩、对未能积极成功谋划勤王行动表示愧疚,或是描写海外风光的瑰奇雄丽,感怀故国与故国之亲友,不论写作内容如何,其中充沛的情感涌溢,确可称得上是雄奇。
三、《清议报》上的蒋智由诗作
梁启超提倡诗界革命,推崇诗家三杰即黄遵宪、夏曾佑、蒋智由。《饮冰室诗话》“昔尝推黄公度、夏穗卿、蒋观云为近世诗界三杰。吾读穗卿诗最早,公度诗次之,观云诗最晚。然两年以来,得见观云诗最多,月有数章。”
梁启超到日本初期,黄遵宪去职里居,夏曾佑并未实际参与维新运动,因而,《清议报》中几乎没有两人的身影。惟蒋智由诗歌在《清议报》中达46题58首,从数量上看,仅次于梁鼎芬与康有为而居第三位。
蒋智由生于1866年,长于梁启超七岁,而少于康有为八岁。蒋氏于1897年顺天秋闱中举。
1899年,自天津育才馆汉文教习任上避乱南归。
1901年与同乡赵祖德创办《选报》并为主笔。次年与蔡元培、黄宗仰(乌目山僧)等发起中国教育会,并任爱国女学校校长。自1898—1902年,蒋智由汲汲于维新事业。
1903年,蒋智由赴日本后,代出访美国的梁启超主编《新民丛报》,在该报发表了22首诗歌和大量文史、政论等论说文章,由是声名大振。同期,蒋智由诗文还见于《浙江潮》。其后,1907年,与梁启超主持政文社,并主笔《政论》。这期间,蒋智由与梁启超交游密切,思想趋近,受到革命风潮的影响而倾向革命,后又转回到立宪保皇的道路。直至立宪迷梦破灭,转而拥护民主共和。可以说,蒋智由从维新而逐渐激进的思想历程,在《清议报》至《新民丛报》的诗作中有着较为清晰的呈现。
1906—1909年间,蒋智由有诗集《居东集》,收此间诗作130首,晚年则亦与梁启超等人同步,与同光体派诗人交往密切,尽毁其早年报刊诗作,手定晚年诗作近80首,身后由其女弟子吕美荪编定为《蒋观云先生遗诗》,受到陈三立等人的称誉。
蒋智由在《清议报》“诗文辞随录”上刊发的第一首诗作为《观世》(1899年第33期)。察诗意,当作于维新变法失败、六君子蒙难之后,“铁血洒国门,党籍罹荆棘”正是指六君子罹祸遇难,而列名维新党者皆遭“荆棘”。此诗言语之激烈,较之同一时期康、梁,有过之而无不及。“莽莽万川谷,异族人经营”,竟似已萌有排满之思想。此际的康、梁,身在日本,《清议报》虽风行国内,毕竟发行于海外,清政府对康、梁的威胁不那么直接。蒋智由作为身在国内的士人,在政变之后的恐怖气氛中发出这种愤怒的呼声,便可见出在政变后万马齐喑的局面,不过是黎明前的黑暗而已。《观世》之后,蒋智由诗作开始大量在《清议报》发表,绳之以梁启超“新意境、新语句、古风格”的诗界革命理论,这些诗作可说是无不相合。具体分析,蒋智由的新意境与新语句首先体现在他对包括独立、平等、自由、文明理念的认同与赞颂上。
因严复翻译《天演论》而将“物竞天择”理论与中国所面临的弱肉强食被瓜分的境地相联系,在戊戌变法前后经由梁启超等人的鼓吹,已形成变法维新社会动员的潮流,蒋智由无疑受到了这一潮流的影响。这种影响集中体现在《观世》、《梦起》、《呜呜呜呜歌》等诗作当中。“……物竞事益烈,智力贵兼取。交通互争雄,独立养自主……吾闻生有群,群失吾何伍。所以肝肠间,坐此百虑苦。亚尘雨气腥,欧海风潮怒。来者事如何,苍茫览天宇。”(《梦起》),蒋智由对亡国亡种的担忧与强烈的自立求存理念,溢于言表。其中“物竞事益烈”的危机感与“群失吾何伍”的保存族群意识,都是一个时代的声音。而诗人肝肠之间百虑苦楚的忧国忧民之心与放眼亚尘欧海的世界眼光,都让人感佩。蒋智由虽身在国内,但他对西方文明的热情,较梁启超等人毫不少逊,他不但对先进的器物文明抱有强烈的兴趣,而且对自由、平等、文明等现代观念也有着较强的认同。在《呜呜呜呜歌》中,蒋智由写道:“呜呜呜呜轮舶路,万夫惊异走相顾……想当墨人初制时,时人亦颇相疑惧。迩来五洲食其福,亚雨欧云忙奔赴。文明度高竞亦烈,强者生存弱者仆……”
诗作虽以写“呜呜呜呜”之轮舶入题,而且诗眼却在“文明度高竞亦烈,强者生存弱者仆”。对文明之竞争,有着深刻的自觉,对亚雨欧云竞争之际的祖国河山,有着强烈的责任意识,这些可以说构成了蒋智由《清议报》时期诗作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一类诗作还包括如《北方骡(思铁路之行也)》等。
对于蒋智由诗歌的艺术境界,梁启超的评价无疑最具慧眼,在《广诗中八贤歌》开篇,梁启超即写蒋智由:“诗界革命谁欤豪?因明钜子天所骄,驱役教典庖丁刀,何况欧学皮与毛。”
无论蒋智由是否在自觉实践梁启超诗界革命的理论主张,但他的诗作无疑是“诗界革命”派诗歌中,最具“诗界革命”特色的。这么说,是因为蒋智由的诗歌已经远远超越了梁启超、谭嗣同、夏穗卿三人早年故作新名词的新学诗,甚至也远远超越了黄遵宪等人面对着海外奇景而造就新诗风的新派诗,而达到了梁启超所追求的“旧格调运新思想”、“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的境界,将诗歌之更新文明、铸造民魂的社会功用发挥得淋漓尽致,而这正是梁启超在《清议报》百期祝词中所说的“诗界革命之神魂”,是“为斯道别辟新土”之新土。从中可以看出,蒋智由与梁启超的交流颇多且相互启发,至少蒋智由是熟知梁启超在此时的政治与文化态度。对此,可以从蒋智由诗作的两方面内容来说明。
首先是,蒋智由此时诗作当中有多首批判国民奴性,而此时梁启超正在酝酿其新民思想。蒋智由诗歌中批判国民奴性的诗作,首先即可见于前引《观世》一首中。“积成奴仆性,谄谀竞为生”,这可以说是点中了中国人处世之道的命门。近三百年满清专制统治下,奴性在中国人身上仿佛扎下了根一般。蒋智由专门写作一首《奴才好》刊发于《清议报》第86册上:奴才好,奴才好,勿管内政与外交,大家鼓里且睡觉。古人有句常言道:臣当忠、子当孝,大家切勿胡乱闹。满洲入关二百年,我的奴才做惯了;他的江山他的财,他要分人听他好。转瞬洋人来,依旧做奴才……奴才好!奴才乐!奴才到处皆为家,何必保种与保国!
在这首诗后,有编者所加跋语:“此作者反言以讽世也。呜呼!世有甘为奴才之种人乎?可以兴矣!”
这首诗中,不甘为奴才及其对满洲统治者的不满均溢于言表,盖因满洲人下对上则自称奴才,而称上为主子,去“奴才”,意在反“主子”。而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创刊伊始便刊发《新民说》,《新民说》煌煌巨著,其思想虽不止于批判国民奴性,但两者之间的共同性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是蒋智由对西方自由、平等等思想观念的推重,时见笔端,这也和这一时期梁启超与革命派发生关系而逐渐激进的思想相同步。在前引《梦起》诗中,蒋智由“物竞事益烈,智力贵兼取。交通互争雄,独立养自主”的“独立”、“自主”思想与其批判奴性的思想,均是这一体现。当然,与梁启超一样,蒋智由的这些思想是与当时政治斗争的现实联系在一起的,如他在《人物》一诗中所写的:“眼中人物关心事,党派差能辨是谁。大抵粤吴楚分鼎,不妨儒佛耶差池。先出奴性斯为贵,但解方言未足奇。廿纪风涛来太恶,那堪群力发生迟。”(《清议报》1900年第68号)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蒋智由的这些思想并未加以隐晦。蒋智由于1901年11月11日在上海创办《选报》,其以“因明子”为笔名在《清议报》上刊发的诗作,也有一部分刊发在《选报》上。这些诗作依照在《选报》刊发顺序,包括:《性入世吟六首》、《北方骡(思铁路之行也)》、《世间愁》、《听丁户部话澳门山势雄壮有感》、《避津门之乱一岁余矣追忆赋此》、《时事》、《呜呜呜呜歌》、《饮酒》、《答问题》、《反前答》(1901);《归来》、《古今愁》、《闻蟋蟀有感(思俗之尚武也)》、《朝吟》、《壬寅正月二日自题小影》、《题孟广集》、《为陈四仲謇题其先世玉堂补竹图》(1902)等。诗题与诗句内容与《清议报》比照或略有差异,然两相对读,不仅对正确认识这些诗作的意蕴有着积极作用。尤其重要的是,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海外谋划勤王、还被通缉之际,蒋智由将诗作在《选报》上同期发表,虽然并非是同一署名,但他这么做,与梁鼎芬以“毋暇”为名在《清议报》刊发诗作的隐秘行为是不同的,毫无疑问是鲜明地表示了自己的立场:坚定维新信念,支持维新事业。甚至他的诗作中,言辞之激烈,反满倾向之明显,实又在诸人之上。这恐怕也是《清议报》在国内被禁之后,蒋智由出走日本的一个重要原因。
通观《清议报》的“诗界革命”诗歌,以梁启超本人和蒋智由的创作为标志,不仅摆脱了梁启超、谭嗣同、夏曾佑等人早期新学诗存在的堆砌与艰涩的问题,而且超越了《清议报》时期康有为等人海外诗中新事物与新名词的阶段,真正实践了梁启超以旧风格熔铸新思想的诗界革命理论与思想。但是这些诗作,是梁启超、蒋智由等人以特定的“新民”、“革命”等概念故意为之的鼓吹之作,其诗作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也因此,蒋智由后期对自己发表的报刊诗词并不收入诗集当中。蒋智由个人诗学观念的这种转变,实则也代表了晚清的一种诗学发展路径。披读蒋智由诗作,一方面感动于蒋氏爱国之热忱,另一方面则又感慨于晚清历史运行轨迹之诡异。早在19世纪上半叶,已被坚船利炮打破国门的中国人,何以在20世纪之初,仍对汽轮讴之歌之而自立无路?汽轮在此际之中国,也不算是新鲜事物了,何以中国在变局当中依旧是充当“弱者仆”的角色?蒋智由等维新派人士将之归因于制度文明的落后而寻求变法,但何以蒋氏最终又在失望当中充当了亡清的遗老?当中牵涉的恐怕就不仅仅是诗学理念,而是其整体文化认知的变化了。中西文明之冲突,想必在蒋智由内心发生了拉锯式的撕扯。在传统当中寻求新变、在亡国亡种的危机之下寻求自强的蒋智由或者“蒋智由们”,用一个什么样的词汇能够概括他们的“文化出处”呢?在易代鼎革之际,是做遗民还是出仕新朝,是历朝士人需要面对的拷问。此际的“出处”问题,尤为拷问士人灵魂。学界多有以“遗民”对象的文化考察,甚至对晚清遗民也不乏专门研究。“文化出处”的概念,与“文化遗民”之类概念一样,渊源自陈寅恪先生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序》,说的是王国维“文化托命”之精神,而这一概念用之于梁鼎芬、陈三立乃至蒋智由这一类人在多大程度上可为确切与妥当,则尤其值得深思。在《清议报》时期汲汲于维新事业,此后则倾向于革命,在维新与革命之间摇摆动摇过之后,选择了君主和立宪共存的道路,这是蒋智由与梁启超在清末政治中的同进退;先为诗界革命之急先锋,而晚年与同光体宋诗派诗人过往密切,以至于晚年手定诗集,于报刊诗词一作不取,蒋智由在文化上的选择甚至较梁启超更为典型。
这种在新与旧之间的摇摆,固然有文化冲突的原因,其普遍性甚至可以名之为晚清士人的“文化人格分裂症”。然而,却又不仅仅关乎变局中的中西文化冲突,背后更深层次的恐怕还有晚清士人对民族文化命运的深度思考,尤其是当政治上之目的已经达成,而现实与追求之理想间的鸿沟仍旧无法弥补之际,原先的文化反叛者或者说激进者姿态,就不得不让步于文化沉思者的身份,而希冀于毫无出路中寻觅出路。
余 论
梁启超1899年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之后,借助《清议报》强大的舆论力,“诗界革命”一时如潮,加之《清议报》辟有《诗文辞随录》栏、刊发了大量诗作,其后的《新民丛报》也刊发大量诗作及梁启超《饮冰室诗话》这样的理论作品。可以说,这两份报刊上的诗歌活动,极大地推动了晚清诗界革命运动的发展,也集中地展示了诗界革命运动中的创作实绩与理论面貌。但是梁启超其人“流质易变”,“尝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他的诗歌观念和诗学理论也并非一以贯之。实际上,波诡云谲的晚清,在世纪之交的几年中变化之剧,让很多中国人无所适从。不仅是国家的命运,文化的命脉也变得岌岌可危。《清议报》“诗文辞随录”栏以高亢的“诗界革命”之号角,奏响了文化转向的先声。就报刊诗词来说,“诗文辞随录”无疑也促使一直处于副刊地位、缺乏独立影响力的报刊诗词发生了重要的改变。除了维新派人士,不同政治、文化取向的士人,开始利用报刊发表诗词、表达意见。而对于主持《清议报》、为一时舆论骄子的梁启超,《清议报》之后的晚清最后十年中,其思想也不断发展与变化。在他主持下的数种报刊刊发的诗词,经历了由“诗界革命”而渐趋分化的过程。
报刊诗词的这种分化,从《新民丛报》便明显起来。《新民丛报》是梁启超在思想渐趋激进后所办的报刊,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诗作的诗人群体,是以“革命”、“民主”等政治理念聚合在一起的。在风云变幻的时局当中,他们的政治选择便多为时局所左右,而其原本的诗学理念本就不尽相同,或者说“诗界革命”之说,从一开始也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诗学概念。所以后期《新民丛报》上诗人群体便不断发生着分化,一部分归附于同光体为代表的传统诗坛、一部分则更趋激进的聚拢成南社等诗词团体,并各自寻求和建立了新的诗词发表阵地,以各自的报刊为传播渠道,宣扬其诗学主张。这种分化,可以被视作是报刊诗词进一步发展的标志。
对于梁启超来说,复归传统不仅是他在《新民丛报》之后的诗学选择,更是为了接近京中士人群体而采取的政治策略。《国风报》时期的梁启超已经以极大热情投身到立宪运动中。《国风报》之取“国风”二字,用意恐怕正在于以风刺上,推动清廷的变革。而从诗词来看,梁启超本人从赵熙学诗,《国风报》则大量刊发京中士人甚至是同光体诗人之作,这些都表明,梁启超已经改变了《新民丛报》早期赤裸裸的革命鼓吹与宣传,而以“称物惟芳,择言近雅”自我期许。整体来看,报刊诗词在分化中的演进可以说代表了晚清诗坛的最主要发展趋向:一方面,由新学诗—新派诗—诗界革命开辟出的晚清新诗风日渐平息了其革命的冲动而向传统复归;另一方面,延续着革命的精神,高旭、柳亚子等南社诗人以革命诗人的姿态,对旧诗坛发起了进攻。或许,唯有理解那一段历史的狂飙突进,才能理解那一代士人的无所适从和卓绝探索,才能避免用或“守旧”或“革命”的标签随意定义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