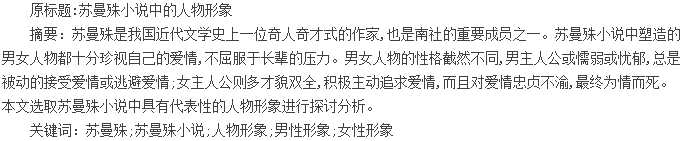
苏曼殊是我国近代文学史上一位奇人奇才式的作家,也是南社的重要成员之一。他的作品文字清丽,又工诗善画,才华卓绝。他的小说产生于辛亥革命之后,五四运动之前,以爱情题材为主,用文言文写成,描写青年男女在恋爱、婚姻上的曲折和不幸。小说中的男女人物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十分珍视自己的爱情,不屈服于长辈的压力,都无法逃脱悲剧的命运。但小说中男女人物却具有截然不同的性格特点,男主人公正直善良、懦弱忧郁、多愁善感,面对爱情时,他们总是被动的去接受或百般逃避;女主人公则多是绝色美女,见多识广,有思想、有追求,热情洋溢,她们总是积极主动地去追求爱情,而且对爱情忠贞不渝,最终为情而死。本文选取苏曼殊小说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形象来进行探讨分析。
一、懦弱忧郁、多愁善感的男性形象
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都是一个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男尊女卑”的封建传统思想牢固地统治着人们的思想意识。在中国传统文学作品中对男性形象的描写多是高大英俊的英雄或侠客,他们在追求爱情时,一般都是热情大胆、主动的“男追女”模式,他们在作品中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而苏曼殊小说中描写的男性形象则一反传统,他们具有懦弱忧郁、多愁善感的性格特点。小说中塑造的男性形象性格特征与现实中苏曼殊自身的性格极为相似,是苏曼殊性格中软弱、阴柔、缠绵一面的反映。
苏曼殊小说中塑造的男性形象主要有:《断鸿零雁记》中的三郎和《绛纱记》中的梦珠都是“看破红尘”的出家者,《焚剑记》中行侠仗义的独孤粲,《碎簪记》中的庄湜与《非梦记》中的燕海琴都是背违“翁命”、“婶命”的软弱者。他们的生活经历虽然各有不同,恋爱过程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但是他们却有似乎一样的家庭,性格中也表现出一样的懦弱、忧郁和多愁善感,而且在面对爱情时都表现出“从一而终”的固执观念。
苏曼殊小说中塑造的男性形象大都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有的自幼失怙,有的父母不全,虽然小说中没有直接描写他们由于父母不在而经历世间冷暖,但从他们不经意的表白中,我们可以想象他们怎样“周历人间至苦”。孤苦无依的身世使人物总是带有若隐若现的感伤情绪,无根的飘零感和孤独感让他们在尘世间随心来去,父母的缺失,使他认为人世间已经没有欢乐可言,无形之中在他们的性格中注入了忧郁、懦弱等特点,这就无疑对他们今后的个人经历和爱情悲剧起到很大的影响。例如:《断鸿零雁记》里三郎叹曰:“人皆谓我无母,我岂真无母耶?否,否。余自养父见背,虽茕茕一身,然常于风动树梢,零雨连绵,百静之中,隐约微闻慈母唤我之声。顾声从何来,余心且不自明,恒结凝想耳。”继又叹曰:“吾母生我,胡弗使我一见?亦知儿身世飘零,至于斯极耶?”
(下文若未作说明,皆出于是书)《天涯红泪记》中的燕影生只提到他有母亲,《绛纱记》中的昙鸾的家长就是其舅父,《焚剑记》中的独孤粲是一位奇士、义士,没有提及家人,《碎簪记》中的庄湜只有叔父和婶母,《非梦记》中的燕海琴的父母在为他准备举行定婚大典时不巧相继去世,他叔父、婶母就出面粗暴地干涉和包办他的婚姻。
男主人公多愁善感,甚至经常以泪洗面。例如:《断鸿零雁记》中描写流泪的字句很多,主要是对三郎在不同的情境之下流泪的描写。小说一开始“余斯时泪如绠縻,莫能仰视;同戒者亦哽咽不能止。”
“余聆小子言,不禁有所感触,泫然泪下。”见到自己的乳母后“斯时余方寸悲惨已极,故亦不知所以慰吾乳媪,惟泪涌如泉,相对无语”。当三郎到日本见到自己的母亲时“余即趋前俯伏吾母膝下,口不能言,惟泪如潮涌,遽湿棉墩。”回国后当得知雪梅为了爱情绝食而死的消息时“余此时确得噩信,乃失声而哭。”小说的结尾处说“余此时泪尽矣!”
《天涯红泪记》虽然没有写完,只有两章内容,但从小说的题目来看,小说肯定是悲剧,而且小说中免不了要描写眼泪。从今天能看到的两章内容中,老人的女儿问男主人公燕影生:“吾闻人生哀乐,察其眉可知。然则先生亦有忧患乎?”燕影生却莺吭一发,生已泪盈其睫。可见,苏曼殊在小说中对眼泪的描写之多,可以用沾满水的一块海绵来形容,只要不小心轻轻一碰,它就会流出许多水来。
男主人公的性格懦弱、忧郁,在面对爱情时,他们总是被动的接受甚至百般逃避。例如:《绛纱记》中的梦珠,他在接过秋云赠给他的用绛纱包裹的琼琚佩物后,没过多长时间他竟然“奔入市贷之”,也许是那块绛纱不太值钱不容易卖,否则可能也难以幸免,之后他就出家当和尚了。然而当他看到“绛纱犹在”时“颇涉冥想,遍访秋云不得”,等到秋云找到梦珠时,而他又以学佛为由横加拒绝,最终梦珠在寺中坐化。《焚剑记》中的独孤粲在阿兰向他表明爱慕之意“妾同行,得永奉欢好,庶不负公子之义,使妾殒殁,亦无恨也。”独孤粲没有一言答复阿兰就离去了,痴情的阿兰说:“妾知公子非负心者,今所以匆匆欲行,殆心有不平事耳。”“士固有志,妾与妹氏居此,盼眄公子归来。”可见阿兰的一片痴心哪!为此阿兰一再为逃婚而漂泊,最终在途中得病而死。
可悲又可恨的是独孤粲尽然在阿兰死后才出现,并向阿兰的难友眉娘解释他当年为何离开阿兰,他是去给朋友报仇,他相信阿兰会在幽冥中原谅他。当年独孤粲离开阿兰,或许是不想让阿兰知道在为朋友复仇时的危险,但他总不至于那样吝惜自己的言语没有给阿兰任何答复和承诺,就那样离开了,可怜的阿兰却用她的一生为这样一个人守候,难怪眉娘愤怒的骂独孤粲是负心之人。
《碎簪记》中的庄湜在面对两个同样优秀的女子———灵芳、莲佩时,他却表现出了反反复复地犹豫不决。从庄湜的朋友“余”———“曼殊”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庄湜一开始是心属灵芳的,但在灵芳将其玉簪赠与庄湜做为爱情信物时,他却只是沉默或者流泪,没有丝毫表露出他内心的爱意。
当他在与莲佩相处时,他又逐渐被其风采和才华所倾倒,并多次向他的好友“曼殊”表明自己对莲佩的仰慕。随后,庄湜在专横的叔父和婶母的精心导演下更加不知所措、难以抉择,最终出现了灵芳、莲佩一连串的误会,从而导致在一天之内两个优秀的女子相继自杀,而庄湜也因伤心过度而死。
苏曼殊笔下的男主人公不是风流少年,他们表现出对爱情“从一而终”的观念。他们自始至终都遵守着一种对感情经历中第一个女子的忠诚,即便是完全听从长辈之命或者因朋友之意而定下的未曾谋面的女子,这些男主人公只要认定自己的心属对象,他们就会念念不忘,即使是这种似乎是初恋般的缘分已尽,后来遇到多么才貌双全的女子,他们也会压抑住自己内心的欲望,要么痛苦死去,要么遁入空门。这种“从一而终”的观念就像紧箍咒一样一直困住男主人公的心灵和行动,例如:三郎、庄湜,他们在订婚或定情之前对雪梅、灵芳的才貌一无所知,即使后来遇上多么优秀的女子,他们仍然死心塌地忠于对方。三郎在雪梅的父母退婚后,失望地出家当了和尚,后来去日本寻母时遇到才貌出众的姨表姐———静子,他们都很爱慕对方,但三郎最终还是选择了逃避。回国后,当他知道雪梅为他绝食而死的消息后,三郎失声大哭,去寻找雪梅的坟墓。在小说中对雪梅的描写只言片语,除了赠百金帮助三郎东渡日本寻母和为情绝食而死外,似乎找不到其他情节和描写来了解和认识她,也无从别处去体味她与三郎之间的恋情,可见他的形象远不如后来出现的静子那样丰满,与其说三郎是钟情于雪梅,还不如说三郎是忠于他“从一而终”的观念。
二、中西合璧、独立大胆的女性形象
中国古代小说中塑造的女性形象往往是贞静贤淑的,而且大多是面目模糊的,有个性的形象并不多见。那些主动追求爱情的女性形象,多是狐狸精、鬼怪等的异类,或者是以“离魂”的超现实主义形式,含蓄地表达女性对爱情、自由的渴望和追求。而苏曼殊小说中塑造的女性形象则多是光彩照人的,她们大多都是绝色美女,容貌出众,除了懂得传统的诗书礼仪之外,她们还精通英文、日文、梵文等,有的还曾经出国留学,她们的生活方式西化、学问渊博、见多识广,她们有思想、有追求,而且热情洋溢,对自己的爱情更是表现出积极主动的态度,“女追男”现象在苏曼殊的小说中比较常见,她们才貌双全为男主人公所倾心。例如:静子、灵芳、莲佩、五姑、阿兰、薇香大多才貌双全,颇有见识。像《断鸿零雁记》中的静子,她美若天仙,谈吐不凡,“慧秀孤标”,不仅对古典诗歌和绘画艺术有独到的见解,还精通佛理、关心国事,就连已是僧人的三郎也掩饰不住对她的欣赏与倾慕,“兀思余今日始见玉人天真呈露,且殖学滋深,匪但容仪佳也;即监守天阍之乌舍仙子,亦不能逾是人矣!”
“静子慧骨天生,一时无两,宁不令人畏敬?惜乎,吾固勿能长侍秋波也!”《绛纱记》中对五姑的描写:“余细瞻之,容仪绰约,出于世表。余放书石上,女始出其冰清玉洁之手,接书礼余,徐徐款步而去。女束发拖于肩际,殆昔人堕马垂鬟也。文裾摇曳于碧草之上,同为晨曦所照,互相辉映。俄而香尘已杳。”
女主人公都是非常的体贴细腻,女性的柔情在她们身上得到最大限度的体现。小说中的男主人公每当患病时,都是女性温柔体贴的照顾使他们痊愈。她们能够理解男子的内心,堪称红颜知己。例如:《焚剑记》中对阿兰的描写:“女凝思久之,顾生曰:‘妾知公子非负心者,今所以匆匆欲行,殆心有不平事耳。’生闻言,耸然掣阿兰之手,嘘唏不能自胜矣。”面对这样的女子,怎么能不让人动心呢?
在中国传统文学作品中对女性的描写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贤妻良母;一类是红颜祸水。但是不论哪一类女性,她们都是男性的附属品而已,她们没有丝毫自我独立的意识。对女性形象如此刻画,其实是作者的封建思想观念在小说创作中的一种反映。苏曼殊笔下的女性形象则不同于以前,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不同质的人,只不过她们在各篇小说中仅仅是改名换姓罢了。
第一类是在几千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具有“古德幽光”,深明尊卑大义的传统女性。
例如:《断鸿零雁记》中的雪梅,《绛纱记》中的秋云,《焚剑记》中的阿兰,《碎簪记》中的灵芳。她们是中国传统文学作品中频繁出现的女性形象。她们深居闺阁,尊奉庭训,多情和善,坚守女性贞洁观,她们学习古典文学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她们“德才兼备”,表面看起来娴淑沉静,内里却柔中蓄刚,对自己所爱的人忠贞不渝,不顾一切,面对阻力,敢于以死抗争。到了清末民初,由于西风东渐,她们中的一些人由于家庭关系和所居住的地理位置,受到西方进步思想的感染。但是,这种感染在强大的传统习俗下,是微乎其微的。他们对婚姻自由的渴望,仅仅局限于内心的波动和静夜的苦思,缺少付诸实践的勇气,对封建社会这个令人窒息的囚笼还难以产生一丝一毫的破坏力。这类女性是以娴静、高雅、温柔、含蓄为特征的。
第二类是思想观念较新的现代女性。虽然她们大多都受过西式教育,但是由于她们是脱胎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现实之中,所以在她们的意识深层中,甚至在她们的举手投足中都时时带有传统的胎记,苏曼殊对这类女性形象的塑造,为中国近代社会提供了一种精神面貌全新的女性形象。例如:《断鸿零雁记》中的静子,《绛纱记》中的五姑,《碎簪记》中的莲佩,《非梦记》中的凤娴。这类新女性,她们的思想是比较开化的,尤其是对待爱情的态度更是主动、热情、大胆。例如静子,当“余”要出走,在雪地被静子发现并追上时,静子尽然“出其腻洁之手,按余额角,复执余掌”,“静子频频出素手,谨炙余掌,或扪余额,以觇热度有无增减”。此外,静子还“愁愫略释,盈盈起立,捧余手重复亲之”。亲手这个动作,本来多是男性向女性求婚时所用,可在苏曼殊的小说中,却反过来了,而且亲一下不够,还要重复亲之。再如五姑,不但主动对昙鸾指天为誓,“今有一言,愿君倾听:吾实誓此心,永永属君为伴侣!即阿翁慈母,亦至爱君”。“言次,举皓腕直揽余颈,亲余以吻者数四。”
大胆的五姑尽然频频向昙鸾施吻。可见,在苏曼殊心中,接受新思想的现代女性对于爱情的主动程度要远远超出男性,她们主动追求自己钟爱的男性,这些女性大多在尚未享受到爱情的甜蜜就过早地为爱情而失去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此外,苏曼殊小说中塑造的女性形象,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她们都不再是传统性质上男人的附属品。女性们已经初步具有个性解放的意识,她们不仅是具有一定自我意识的个体,很多时候甚至还反过来成为男性的精神支柱。例如:《碎簪记》中的灵芳,当她所爱的人庄湜因陷入她与莲佩之间的情感纠葛而左右为难、痛苦不堪时,她虽然深爱着庄湜,但同时她更理解庄湜的为难处境,为了能让庄湜“享家庭团圆之乐”,灵芳最终牺牲了自己的感情,忍痛与庄湜诀别,并央求其叔父把他们爱情的信物———一支发簪折断以表明决绝之心。而《断鸿零雁记》中的雪梅,她不仅反抗其父母把她当作货物嫁给有钱人家,而且还私自将自己的积蓄赠给三郎资助他东渡日本寻母。女性在苏曼殊笔下已经不再是柔弱的代名词,她们开始有自己的思想,她们勇于追求自己的幸福,而且还敢于为自由去拼搏。
综上所述,苏曼殊小说中所塑造的男性形象都具有正直善良,懦弱忧郁,多愁善感的性格特点,但他们却缺乏面对现实的勇气和大胆叛逆的反抗精神。女性形象则多是绝色美女,见多识广,热情洋溢,积极主动追求爱情。苏曼殊小说中的人物都在心灵深处被孤独、痛苦所折磨,他们的爱情最终以悲剧结尾,其小说正是通过对人物悲剧性格的刻画,使人物具有内在的悲剧性,增强了小说的悲剧色彩。在苏曼殊所生活的时代,那些青年男女在爱情和婚姻的问题上,其实只可能有两种结局:要么向封建势力屈服,要么以悲剧告终。
苏曼殊的小说不写前者,而写以悲剧告终,这也正是苏曼殊小说反封建主题思想的表现,也正是苏曼殊小说具有积极意义的标志。苏曼殊小说中人物的悲剧性,也是他这位时冷时热、亦僧亦俗的革命和尚、爱情和尚对时代的迷惘、彷徨在自己小说人物中的折射。
参考文献:
[1]苏曼殊.苏曼殊小说诗歌集[C].裴效维校点.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