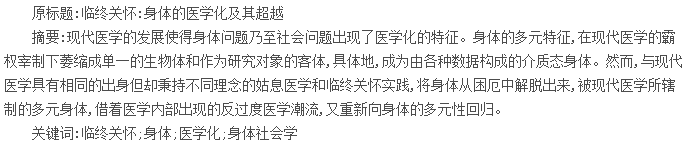
关于医学化的研究起于20世纪70年代,其集大成者康拉德提出了 “社会的医学化”,他认为,医学对个体身体实践及社会生活过度干预,出现了社会问题向医学问题的转变。几乎同时,20世纪60年代以来,医学内部对待身体的态度出现一股由一元向多元回归的潮流,即临终关怀机构及姑息医学的建立。为此,我们将分别阐述医学对身体和社会的过度干预以及医学内部的自我反思潮流,进而呈现当今社会中身体的复杂境遇。
迄今,身体社会学研究形成了四个明晰可辨的理论传统:身体不是一个自然现象,而是社会建构;身体可被理解为社会组织和权力关系的文化表征;由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在 《知觉现象学》一书中发展的 “活体”概念;人类本身如何被具象化以及人类获得诸如走路、跳舞、握手等日常活动的身体实践的方式。 将这四个理论传统并置,我们看到,前两个理论传统 “身体是社会建构的”和 “身体是社会组织和权力关系的表征”,这两个命题从相反的两个方面表达了相同的意思,即身体与社会具有映射关系。相比之下,后两个理论传统却在强调身体的活性或实践特征。这样,关于身体的理论视角可以简化为“作为表征的身体”和 “作为实践和经历之具象化的身体”。
然而,无论是“作为表征的身体”,还是“作为实践和经历之具象化的身体”,关于身体的研究都暗含了身体本身所具有的多元性。因为“作为表征的身体”因社会文化的差异而呈现多元性,“作为实践和经历之具象化的身体”也会因历史情境的不同而不同。总之,从不同视角和纬度展开的身体研究向我们展示了身体的多个向度以及多个向度之间的复杂关系。身体并非仅仅是生物的,或社会的,或文化的,或历史的,身体是它们的集合与浓缩。
一、被医学科学日渐收敛的身体
在日常生活中,尽管身体具有无可质疑的多元特征,但身体在个体经验与人类身体两个层面上皆受到现代医学的辖制。我们将从以下两个方面分别加以阐释。
其一,在面对现代医学时,个体的身体经验无法为自身的处境提供说明,而只有在被纳入现代医学的解释框架时才具有意义。阿姆斯特丹大学范丹柯 (Jose Van Dijck)教授的一次就医经历生动展示了身体经验和医学技术的冲突。
一天,她感到胃部上部刺痛,并伴以恶心。家庭医生建议她去医院做胃镜和B超检查。她觉得是胆囊出了问题,可她的家庭医生并不这么认为。因为她在23年前切除了胆囊,再次患上胆结石的可能性极低。在医院里,无论是胃镜还是B超检查皆未显示异常。在听完她的病情陈述后,消化科医生让她做个血检,以保万无一失。回到家之后,她觉得自己的担心毫无根据,而家庭医生的判断也是对的:影像没有显示病变,她该重回工作。第二天,消化科医生打来电话说,血检结果显示她的肝脏和胰腺出现了问题,让她立即到医院复查。她极可能患了胰腺炎,她必须做一个胰胆管造影。借此,手术医生从她体内取出了两粒绿色的石头。在整个过程中,范丹柯本人自身的身体经验被一再否定。在胃镜和B超检查后,她的刺痛被她自己及其家庭医生视为没有意义。然而,血液检查却重新将她拉回医院,并最终取出结石。
她的就医过程显示,在身体经验与医学技术的角力中,医学技术是当之无愧的王者,病患的身体经验在医学诊断实践中所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小,医学知识与诊断实践中蕴含的逻辑成为了医学共同体中最基本也最具说服力的知识话语。这样,作为患者的人,其感性知性能力已被否定,他/她不再是一个能动的主体,而仅仅是一具作为医学对象的生物身体。身体远离了人,而被医学所围困。
如果范丹柯的个人经历说明了现代医学忽略个体的身体经验,那么乳腺癌患者的治疗经历,则向我们展示了现代医学更为彻底地宰制人类的身体。
迄今,乳腺癌的整体治疗包括手术切除、化学治疗、放射治疗、药物治疗等。由于在长时间的治疗过程中,病人经由肿瘤切除手术而丧失了女性的重要性征———乳房,在化疗放疗的过程中经受恶心、呕吐、脱发、脱睫毛,在后续服用三苯氧胺来遏制雌激素的分泌以帮助活体康复时导致提早绝经。同样是在这个过程中,病患经历了失去乳房、毛发等身体 “残缺”,进而因为绝经而舍弃性生活。
纵观乳腺癌的治疗及病患反应的整个过程,我们看到,现代医学所面对的仅仅是 “生物活体”。现代医学仅仅为了保证 “生物活体”继续存活而采取相应的治疗手段,至于个体身体的残缺和个体的性生活皆需让位于维持机体继续存活的努力。可见,若说范丹柯的就医经历反映了医学对个体身体经验的忽视,那么乳腺癌的治疗过程则更是呈现了现代医学将身体所具有的多元特征一一阉割,身体彻底成为了单一的作为生物活体的客观对象。
其二,作为现代科学的现代医学,其将人类身体仅仅视为研究和治疗的客体。人类身体在现代医学中的客体化过程也是将身体的多元性逐步消除的过程。要理解身体的客体化过程,我们至少可以追溯到笛卡尔。对此,国内外许多学者都做了陈述,,我们就不再多费笔墨。被奉为近代科学之开山鼻祖的笛卡尔,其心身的二分更似一种隐喻,他意欲确立的是理性至高无上的作为世界主宰的地位。尽管在笛卡尔之后,有许多学者提出了关于身体和世界的不同看法,然而,时至今日,医学科学的哲学基础依然来自笛卡尔。
身体在医学领域的客体化至少体现在身体器官的对象化、身体的生化指标化和身体的影像化这三个方面。
在身体器官的对象化方面,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对身体内各器官的认识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在16到17世纪的欧洲,展示身体解剖的解剖室 (anatomy theatres) 和公开的解剖课程吸引了大量民众。 在当时条件下,作为传媒手段的解剖室将身体的内部景观展现给普通民众,而 “作为专业人员的医生和科学家要想增进对身体的认识必须亲自去进行解剖和对尸体进行近距离地观察”。 “尸体解剖提供了外科手术学习的触觉感受,但是并不能提供对生物系统紧密相关的生理学的深刻理解。” 更进一步地,近年来,德国解剖学家哈根斯 (Gunther von Hagens)创办的 “身体世界” (Body Worlds)展览,即以经过化学处理的尸体作为展品。这些塑化尸体模型既有局部身体的模型,也有人体生理系统的模型,它们在用作医学教学器具的同时,也可以供普通民众参观。身体的内部结构以这样的方式毫无保留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在身体的生化指标化方面,意大利帕多瓦大学的教授桑克托瑞斯首次将量度观念应用到医学中,他设计出体温计和测量脉搏快慢的脉动计,望诊、触诊、叩诊和听诊成为四种基本物理诊疗方法。临床医生也开始利用化学分析的检验手段协助临床诊断,如建立了血、尿、便三大常规检验方法。 相比于希波克拉底提出的体液病理说,对身体体征的量度说明对身体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身体的概念扩展成一组关于身体体征的数据构成,成为通过对身体体征的度量所获得的数据信息———身高、体重、体温、血压、脉搏、肺活量、血/尿/便检测结果等一系列指标。
身体本身是一个多维度的存在,这个数据集合可以模拟身体的机能,通过对所得数据和正常标准的比较,对身体的健康状况作出评估。
在身体的影像化和数据化方面,自病理解剖学家摩干尼提出 “病灶”概念之后,医学诊断实践需要完成的任务,就是寻找到病灶,而病灶又确切地指向病变的脏器, 所有的医学影像技术都服务于这一目的。我们看到,医学影像技术所完成的工作仍然是对身体数据的收集,只是不再采用物理测量和化学检查这样相对比较直接的数据收集方式,而是借助于计算机技术将身体转化为数据的集合,所收集到的数据信息组成了医学诊断实践中的介质态身体———数据态身体,也可以通过计算机技术转化为医学影像。 “在 ‘看见等价于相信’的文化背景中,医学影像技术生成的图像成为了内部身体的一种直接描述,医学影像技术是一种关于真实的技术,它并非反映了内部身体而是实在地创造了它。” 由此,我们认为,医学诊断实践从一种高度具身性的实践活动,转变为 “医生———介质态身体———患者”的实践。此处的介质态身体,就是借助于医学技术对身体采集到的数据所构建的数据态身体,此种身体数据可以借由计算机进行图像的再现。不断精细的医学影像技术收集到的身体的数据异常的丰富,其所再现的身体影像也更加清晰和真实。
这样,医学在身体之外重建了新的数据化的身体,这将人类的个体经验排除在外。
人们的感性能力被应用于医学领域的不断更新的诊断技术和仪器所取代。作为传媒技术研究者,范丹柯在大角度透视了身体所经历的透明化趋势过程中,她着力探究媒体在该过程中的角色,这成为了她在分析医学影像造就透明身体的视角。关于身体内部构造的医学图像,逐渐主宰了我们对于健康和疾病的认知和体验,并以同样的方式将自身发展成一套专门的话语。
然而,影像和病理之间并不是简单的一对一的关系,医学专家对医学图像中反常现象的解释也不必然是单一的,而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医学专家们多年形成的共识。 布瑞 (Burri)认为,对图像信息的解释需要专业知识的积累和训练实践,而且行动者所处社会地位对于图像解释都会产生影响。在日常医学实践中,图像可以被用作交流信息和佐证手写报告,因此在医生与病人和同事的交流中,医学影像可以用来强调观点和使对方确信诊断结果。因为,作为科学图像的医学影像被看作是具有权威效力的 “客观事实”。
也正是因为如此,医学影像所蕴含的图像逻辑遮蔽了普通个体的感受和经验,作为介质态身体的医学影像,也越来越远离身体的多元本性。医学知识和技术以各种方式走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但这却并不意味着人们对自己的身体与健康拥有了话语权。恰恰相反, “医学影像的广泛应用使得我们借助技术看到的内部身体越来越复杂,我们看到的越多,图像信息就变得越复杂”。
由此,以医学影像为代表的医学技术手段作用于医学实践之中,身体经历了一种技术的抽象,由活生生的身体转变为介质态的身体,而要完成这样的转变,就需要对身体的特征从医学的角度进行取舍,选取可以标明身体情况的数据特征进行测量,从而借助于技术手段进行身体的再造。医学检查得出的数据和影像把个体的身体经验挤压得不剩一点空间,个体对身体经验的信任在被图像逻辑所剥夺,而个体在面对医学检查数据时又处于绝对劣势地位。人们走到了无路可退的境地,而只能相信医学技术,并受其宰制。
二、临终关怀:向多元身体的回归
正因为任何科学都有限度,医学科学在努力单纯延长个体寿命的同时,也在不断尝试着将身体的多元涵义带回到医学视野中的可能性。在逐步认识身体的过程中,人们更加关注自己在接受医疗服务时作为一个人应该享有的尊重,并以此在庞大医疗体系的压制下发出自身的声音。临终关怀 (Hospice)所做的正是这样的尝试。
临终关怀以照顾 (care)为中心理念,为那些处于病患末期、治愈希望渺茫的病人提供疼痛控制和精神支持,提高其生命品质,实现对生命尊严、垂危病人权利的双重尊重。 以照顾(care)为中心理念,临终关怀强调以下几方面的内容:首先,最大限度地减轻疼痛。临终关怀直接触及了医学难以处理的两个问题,即疼痛和死亡。医学针对重症病人的治疗往往不得不以使病患剧烈疼痛的疗法来挽回或许已经无可挽回的生命个体。与此相对,临终关怀对病人病痛的处理原则是主动防止,使病痛消失,而不是被动的压抑或者控制。其次,增强病人本身的自主能力,也就是强调病人对自己死亡方式具有决定权,同时,临终关怀反对依靠延长生命的医疗器械来维持病人的生命。这与其他的医疗机构的医疗救治行为相冲突,比如ICU(重症监护室)里大量使用高科技的医疗设备来维持病人的生命。再次,让死亡的过程中充满善,即善终(good death),这是临终关怀追求的价值理想。
临终关怀强调在疼痛处理和自主决定死亡的基础上,更为重要的是提高剩余生命的质量。这需要在临终关怀过程中保持病人已有的社会关系往来,鼓励病人参与重建个人余生的意义,并将意义重建与个人经历、认同和与他人的关系连接起来,也就是临终关怀所强调的 “建立完整的生命”(making whole), 而不是仅仅听命于把人看作生物体的现代医学。
我们将通过回顾临终关怀的历史形态、现代临终关怀运动的兴起以及临终关怀医学确立的过程,呈现医学霸权对身体的宰制在临终关怀这一理念和实践中开始出现了向多元身体的回归。
(一)医院和临终关怀机构的早期形态
追溯临终关怀机构的历史,古希腊和古罗马就已经有了一些照顾陌生人、病人、过路人的场所。之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也将照顾病人当作是一项宗教任务,其结果之一就是在中世纪欧洲产生了大量的被称作庇护所 (Hospice)的场所,这种场所为路途中需要休息的朝圣者、穷人、游客提供食宿,补充给养,并且收容病人,替死去的人安葬和祈祷。同时期,与hospice并存的还有现代医院的早期形态———慈善救济院 (hos-pital)。关于基督教与医学发展的关系,西方学界一般认为,西方社会的医院和保健植根于基督教,耶稣基督被认为是身体与灵魂的医治者,而基督教的慈爱精神直接促使了现代医院 (Hospi-tal)的产生和发展。公元325年,在尼西亚召开的基督教会第一次主教特别会议上规定,主教要在每个有 教堂的城 市建造一家慈善救济院(Hospital)。早期基督教的慈善救济院并不是今人所理解的医院,其主要功能并不是医疗,而是为过往的穷人提供临时的住所和食物,虽然也收容病人。到了公元6世纪,慈善救济院已经成了修道院的一个常规部分。 基督教的慈善救济院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志愿性质的慈善机构,在中世纪也得以在地中海、欧洲地区和阿拉伯国家迅速传播。 及至十四五世纪,欧洲的医院已经星罗棋布。
仅从功能上来讲,庇护所 (Hospice)和早期的慈善救济院 (Hospital)并没有差异,两者都是基于基督教教义而设立的慈善机构。庇护所(Hospice)在最初并非为专门为照顾垂危之人而设立,而只是为病人、朝圣者、游客等人提供方便的地方。随着医学专业化的发展和护理体系的创建,为具有现代特征的医院的出现奠定了条件。慈善救济院 (Hospital)逐渐脱离了教会,实现了向专业化、独立的医院的转化。由此也导致了公立的救济院 (Almshouse)和贫民习艺所(Workhouse)的出现,这些机构担负起了照顾慢性病病人、穷人和垂危之人和那些不被医院接受的人的任务。但是,公立救济院并不足以担负沉重的收容负担,因此那些中世纪以来就存在于欧洲土地上的庇护所 (Hospice)因社会的需要而重新得以发展,但是其功能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成为专门为照顾无法治愈病人和临终者的机构。
1879年,在爱尔兰都伯林由基督教教会支持创建的圣母临终关怀所 (Our Lady’s Hos-pice)是第一个专门护理晚期病人的机构。它的成立受玛丽 · 艾肯希德修女 (Sister MaryAikenhend)的启发,她认为,死亡是生命最后的朝圣,与中世纪的朝圣相联系,她想用“Hospice”这个古老的词语命名、建立专门照顾垂危者的机构。在基督教教会的支持下,玛丽·艾肯希德修女理念的传播使得19世纪末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和美国均出现了大量专门照顾垂危病人的临终关怀所 (Hospice)。尤其是在英国,此类机构相继成立。当时成立的很多临终关怀所 (Hospice)直到今天仍然存在,它们成为20世纪60年代英国现代临终关怀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回顾 “Hospice”在欧洲大陆的产生、发展和历史变迁,不难看出,植根于基督教传统的“Hospice”在欧洲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这为现代临终关怀运动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基督教为现代临终关怀积累下了三个坚实的基础:慈爱、医院和护理。 这也是现代临终关怀运动再次启用 “Hospice”这个古老词汇的缘故。当然,作为一项医疗服务项目的现代临终关怀,赋予了 “Hospice”新的涵义。
(二)现代临终关怀运动的兴起与临终关怀医学的确立
20世纪6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人口急剧增加。加之进入20世纪后,人类的疾病谱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导致人类死亡的主要原因不再是鼠疫、天花、结核病、肺炎等传染性疾病,而是肿瘤、心脑血管病、高血压等非传染性疾病。慢性疾病患者人群在增加,癌症患者和其他疾病的晚期病人队伍日益庞大。 同时,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现代医学逐步以各种致命疾病的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由于高科技医疗手段的介入,重症晚期患者的死亡时间得以后延。现代医学本身对死亡的界定也在不断更新。死亡不再是自然的,而是被 “医学化”了。
身为人类学和心理学学者的贝克 (ErnestBecker)在1973年指出现代西方社会对待死亡的基本态度是“否认死亡” (the denial ofdeath)。其观点因发表的同名著作而在西方社会广泛流行。否认死亡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生命历程中缺少对死亡的关注,二是医疗机构中拒绝承认死亡,承认死亡无异于承认医生的失败。毛克施 (Mauksch)的社会学研究也证明,医院被认为是治疗、且能够治愈疾病的地方,而临终者威胁着医生的角色定位,垂死者给医疗人员造成了无能的感觉。库布勒-罗斯认为,一系列复杂的社会因素导致西方文化对死亡的恐惧,死亡是社会的禁忌,这加强了否认死亡、回避死亡机制的产生。这使得现代社会里死亡的过程通过各种方式变得更可怕、更孤单、更机械、更无人性。由于医生对专业知识的掌控,其具有权威地位,而病人及其家属除了可以在某些场景下拒绝接受医疗服务外,在整个治疗决定过程中,他们往往处于被动地位。最后,在亲临医学化的死亡时,现代社会中被赋予诸多权利的个人及其家属,却被抛入了多元价值的冲突中、无所适从。尽管医疗技术在日益发展,然而,如何面对和处理临终者以及临终者如何自我面对的问题,却构成了一个严肃的问题。
临终关怀所要面对的正是病患身体的多元性,现代临终关怀运动的兴起,与二战以后现代人所面临的死亡问题以及所感受到的死亡问题所具有的特点有着直接的关联。这导致了现代临终关怀在与基督教下的早期的临终关怀理念保持密切联系的同时,始终带有一种普世的道德情怀,始终把临终者本身作为首要的关切,强调对人本身的尊严与价值的发现。在这样的背景下,临终关怀便超越了宗教与文化的拘囿,形成了自身的理念。现代临终关怀实践的发起者桑德斯 (Cic-ely Saunders)将临终关怀理念在实践中逐渐明确,英国的临终关怀机构有了新的发展。同时,临终关怀的理念得以在欧美其他国家推广,并获得了广泛的接受,最终形成了现代临终关怀运动(Modern Hospice Movement)。
一般认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兴起的现代临终关怀发源于英国伦敦。经过近19年的筹备,第一所临终关怀机构由英国护士桑德斯在1967年创办,名为圣 · 克里斯托弗临终关怀机构(St.Christophers’Hospice)。与普通的医疗机构不同,圣·克里斯托弗临终关怀机构只对临终病人提供服务。临终关怀既不借助医疗手段延缓死亡,也不用它加速死亡,其目的在于通过提供舒适服务,以维护病人尊严、提升病人的生命品质。以上美好的愿望,完全诉诸医疗的手段并不能实现,因此提供临终关怀服务的不仅仅是医生、护士等从事医疗服务的人员,还有被认为能够为病人提供精神支持的心理医生、宗教人士、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
随着临终关怀逐渐被纳入西方社会医疗政策之中,并为全球五六十个国家所接受,其所蕴含的价值观念具有了广泛的意义。临终关怀运动被认为是草根改革的社会运动,是对医疗体制高消费和医疗资源分配不公的回应;它同时是一场宗教运动,尝试着将死亡过程充满灵性并使人承认和接受死亡;它也是一次专业运动,是非医生专业的健康照护工作者对权威医疗体系的挑战和反死亡医学化的行为。
与之相应的医学专科也获得了良好的发展。
1987年,作为临终关怀临床基础的姑息医学在英国被确认为临床医学的一个分支。世界卫生组织将姑息医学定义为:通过早期识别,积极评估,控制疼痛及处理躯体的、社会心理的、灵性的困扰,来预防和缓解身心痛苦,从而改善面临死亡威胁的患者及其亲人的生命质量。 由此,以姑息治疗为基础的整体照护 (Total care)或以姑息治疗为基础的多学科综合照护成为了临终关怀的医学基础。世界卫生组织对临终关怀医学的定义,也标志着临终关怀所倡导的理念和实践得到了医学科学的认可。尽管现代临终关怀发端于对医学科学缺陷的反叛,但最终临终关怀获得了医学科学内部的认可,使得多元的身体在其临终时获得了原本的多元面貌。
三、小结
身体社会学研究的四个理论传统,展示了身体所具有的多样形态和丰富内容。无论从历时的角度还是共时的角度来看,身体绝不单单是生物性的或医学态的。中世纪的慈善救济院可谓是现代医院的前身,而慈善救济院提供的不仅仅是医疗服务,还有食宿和属灵服务。当时,慈善救济院对其收纳的人提供较为全面的照护。与此同时,与慈善救济院 (Hospital)并存的还有庇护所 (Hospice),它的功能与慈善救济院没有实质的分别。然而,脱胎于慈善救济院的现代医学,借着笛卡尔的哲学根基确立了自身的科学地位。
这样,现代医学便脱离了原来的全面照护,而仅仅关心以主客二分的框架里处于客体位置的单一的生物身体。伴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和技术进步,身体越来越受到现代医学的辖制,乃至使人类社会显现出医学化的特征。
在中世纪的庇护所 (Hospice)发展成现代意义上的临终关怀机构 (Hospice)时,临终关怀机构并未像现代医学那样放弃它的前身所秉持的理念。现代临终关怀机构依然推行着针对病患的全方位照护。同时,由于现代临终关怀实践逐步在现代医学内部获得了合法地位,临终关怀的医学根基———姑息医学也成为了现代医学的一个分支。姑息医学及相应的临终关怀实践,将人类身体恢复到多元的状态,践行着针对身体的多元照护。
一个人尽管只是在其个体临终的时候,他才有机会获得多元的身体照护,但是,临终关怀的理念为现代医学所接受本身,即显示着医学的单一身体观对多元身体观的妥协。被现代医学所围困的多元身体,可以在临终时恢复多样的面孔,这一进步虽然迟缓又令人感到凄凉,但身体在现代医学内部向多元性的回归本身,即向我们昭示了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