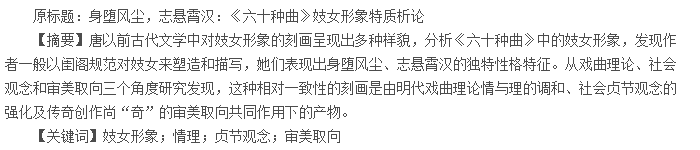
汉乐府及六朝诗歌中,出现了最初的妓女形象描写,她们大多为宴会中侍酒侑觞的角色。至唐传奇小说及长篇叙事诗,其妓女形象或侧重于男女情欲的刻画,如《游仙窟》,或参杂了志怪小说的色彩,如《任氏传》。以文士与妓女的爱情故事为主题的作品亦始于唐传奇,妓女形象呈现出执情不悔、坚贞守身的特征,如《李娃传》与《霍小玉传》。元杂剧中的妓女形象,大部分是以热情、正直和富有同情心为特征,如《救风尘》与《曲江池》等。古代文学作品中妓女形象的描写因时代背景、文学创作理论等因素的影响,自汉代以来呈现出不同的样貌,没有形成一致的特质形象。
对于《六十种曲》中的妓女形象,创作者是以一般的闺阁规范来塑造和描写的。剧作者在塑造妓女人物时,有意识地以某种特质来描写。高彦颐在《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一书中写道:“她们有的像闺秀一样,有着可圈可点的诗歌和艺术造诣,可惜她们有的是不同的结局。”
一、《六十种曲》中妓女形象
1. 才色俱佳的外在形象。《六十种曲》中的妓女大多才色兼具。她们精通诗文、书画、音乐或者演剧等才艺,能与书生们相互酬唱。这种集美貌、多才于一身的完美形象,成为她们吸引并打动书生的重要手段。许多书生对妓女一见钟情的首要原因也在于此。《投梭记》中的元缥风:“看他面如明月,辉如朝霞,色如桃葩,肌如凝雪,乍见如红莲透水,近觇如彩云出山。”[2]
《霞笺记》中的张丽容也是“名重当今,色倾上国,声闻寰宇,争睹芳容”的绝色女子。与其说是旦角外在的美貌促成了她与男主角的相恋,倒不如说是她们内在的灵气成为二人结合的重要因素。《霞笺记》中李玉郎夸赞张丽容题于霞笺上的和诗:“作此词者,休夸谢道韫,不数李易安,岂与风尘女论哉。”《青衫记》中的裴兴奴也是因为“姿容独步,才技无双”的琵琶技艺,才赢得了白居易的“十分留意”.
才色兼具虽是妓女们出名的必然条件,但当二者同时放在一起衡量的时候,才高过于色。外貌可以平常,文学与艺术的修养却必须在一个标准之上,才能得到文人的青睐。《红梨记》中的赵伯畴认为:“如小生之风流才调,必得天下第一个佳人,方称合璧。”而“妓女的成名离不开传统艺术的熏陶,艺术滋养了名妓高雅的气质,其‘色’藉‘才',而有韵味,艺术才能更是名妓参加各种交往活动的资本,为其成名提供机会和条件”[3].具备多项才能,拥有才女的美名,以此得到更多的生意,强化妓女们谋生的能力,或因此在文人群体中找到心灵的知音或终身的伴侣。
2. 坚贞自守的内在气质。贞节观念,自古即有。唐代宋若华所著《女论语》中有云:“古来贤妇,九烈三贞,名标青史,传到而今。后生宜学,亦匪难行。第一守节,第二清贞。”[4]
指出贞烈的情操与行为,能使妇女的贤明流传青史,这成为以后中国古代妇女生活中重要的礼法规范。沦落娼家的妓女也用家庭体制内良家妇女“三从四德”“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思想来规束自己,她们本应终日迎来送往即可,但若遇到条件较好的客人,也想要依附于他,便可终身衣食无虞。《六十种曲》中的妓女除表现出对风尘生活的反感与良家生活的强烈追求外,还表现出与书生定情后身体和精神上的坚贞不屈。
剧本中的妓女一出场就表现出渴望早日赎身,得到一个“名分”,过普通女人正常生活的诉求。如《绣襦记》中的李亚仙一登场,便表达了自己最渴望完成的夙愿:“自惭陋质,而获宠名公。身虽堕于风尘,而心每悬于霄汉,未知何日得遂从良之愿。”李亚仙认为“从了良,了我一生之事”,进入家庭制度之内“大小自有名分,我尽做小的道理,就是了当”.
妓女想要从良,尤其是想要嫁给自己理想的伴侣书生,无疑要经受金钱的诱惑、权贵的威逼以及来自书生家庭内部的压力等严峻考验。《六十种曲》中的妓女形象在通向从良这条路上都表现出刚烈不屈、坚贞自守的特点。这不仅源于男女之间和谐的情意,更出于对伦理、名分的考虑,为了能够使自己重新获得社会的承认,回到“君臣、父子、夫妇”的伦理序列中去,她们必须做出极大的努力,以绝对的贞节来信守对恋爱对象的承诺。
3. 敢爱敢恨的个性特点。妓女的身份固然为社会所鄙弃,但相较于整日囿于闺阁中的闺秀而言,她们拥有与男性自由交往的权利。“曲中女郎,多亲生之,故母怜惜倍至。遇有佳客,任其留连,不计钱钞。其伧父大贾,拒绝弗与通,亦不怒也”[5].她们以相对自由的身份与彼此相悦的客人交往。在《六十种曲》中,女主角一旦遇到满腹才华、风俗倜傥的理想伴侣,就会显现出超越一般闺秀女子的豪情。她们敢爱敢恨,并勇于将内心的爱情追求付诸行动,为了所爱之人拒不接客,暗夜私访,甚至以死守志。这些举动,皆是一般受到礼教束缚的深闺名媛所不能,也不敢为的。
《青衫记》中的裴兴奴与白居易一见倾心,只想与他厮守终身,不但自己跑去找白居易的小妾樊素和小蛮,要求跟着她们一起去找白居易,还威胁鸨母若不成全,就永不接客。《红梨记》中的谢素秋在太傅王黼逼迫时说到:“他若再来相逼,我拼得一死便了。”而《西楼记》中的穆素徽初见于鹃,便直言道:“情之所投,愿同衾穴,不知意下若何,自荐之耻,扶乞谅之。”
《六十种曲中》的妓女形象除《玉玦记》中的李娟奴与其鸨母一样,认钱不认人,抛弃已被她搜刮一空的书生王商外,其余全部是以正面形象出现的。她们不但具有外在的才、色、艺,还以其内在的坚贞、善良、多情的品质,最终赢得了书生的爱情。就剧本而言,剧作者对妓女或闺秀形象的描写并无太多差异,只是在情节发展上,当闺秀与男主角分离后,只要坚贞守志渡过难关,即可走向团圆封诰的结局;而妓女则必须在这分离的过程中,通过与外界的努力抗争,才能实现由妓女到良家女子的身份转变,变成名副其实的闺秀。
二、《六十种曲》妓女形象特质成因
1. 明代贞洁观念的强化。自宋代以降,妇女守节的观念被愈加重视,从历代正史统计的节妇数目来看,元代之前有记载的加起来,仅有 407 人,时至明代即有 265 人,人数开始大幅提升[6].由此可推知,至明代,贞洁观念得以高度强化,主要表现为:其一,国家政策层面的旌表制度;其二,女教书籍的普遍流传;其三,士人大量书写节烈题材的文学作品。
就明代的旌表制度而言,明初,明太祖基于匡正人心、提倡礼教风化的考虑,针对旌表节烈妇女颁诏:“凡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志行卓异者,有司正官举名,监察御史按察司体覆,转达上司,旌表门闾。又令: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制,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7]
对于那些守制的节妇除享受国家的旌表之外还能免去家人子孙的劳役差务。这在制度层面引导了社会风气。女教书籍的普遍流传,也是影响妇女崇尚贞节的因素。明代的女教书籍,除继承前代所流传的班昭《女戒》、刘向《列女传》、唐长孙皇后《女则》等书籍外,皇宫中也有后妃编纂的女教书籍流传,例如明成祖时有仁孝徐皇后著《内训》、世宗生母章圣太后的《女训》等。而神宗万历时的吕坤,写《闺范》一书,在民间广为流传,甚至流入宫中,由明神宗御赐郑贵妃得以重刻,并为之作序。
明代士人书写节烈妇女传记已蔚然成风,他们不仅描写家族中的妇女,还把视角投向娼家女子。如宋濂《记李歌》中描写娼妓李歌“自是缟衣素裳,唯拂掠翠鬟,然姿容如玉雪,望之宛若仙人”[8],后聘为妇,在逃难之际遭遇贼兵迫害,“我宁死绝不从汝做贼也”[9].作为娼家之女,李歌一直以来就以良家女子作为闺训,装扮上素洁,待客时“俨容默坐”,矜持自重,遇害时以死抵抗,坚守节操。冯梦龙在其所编纂的《情史》“情贞类”中,也涉及了数名妓女守贞的故事。
南徐妓女韩香“与大将叶氏子交,闭门谢客”,后因叶父投诉官府,官府集结未婚官兵以射箭决定其终身,一名老兵射中箭靶,韩香在婚礼前“入更衣,久不出,自刎矣”.韩香之死表面上是因不能与爱人厮守终身而自杀,实则是“死其志也”.
“志,匹夫不可夺,匹妇亦然”[10].
明代的贞节观念在国家政策层面的推动、社会风气的熏染以及妇女自我精神的完善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逐渐趋于严格化、规范化,形成一种全社会范围内的道德力量,这股力量影响到各个阶层不同身份的妇女。而戏曲作为艺术作品是“时代生活的综合反映,虽然不是每一部艺术作品都直接描摹生活的原型,但社会生活的风貌却一定会在作品中体现”[11].《六十种曲》中的妓女形象正透露出了浓郁的时代气息,她们不仅拥有闺中女子的才貌,而且如闺中女子一样严守闺训。
2. 明代戏曲理论“情”与“理”调和之产物。明传奇发展的初期,在文人着手进入传奇剧本的编写之际,他们目睹民间野台搬演古代名人时所使用的贬抑手法,萌生了改编旧有剧目为主的创作方式。元末明初的文人高明将南曲戏文《赵贞女》改编为《琵琶记》,从此开启了文人翻案的风气。高明在《琵琶记》首出便述及编剧的目的为“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高明认为,戏剧的中心题旨在于淳厚人伦,变化风俗,如果没有涉及风化,纵然剧情再好,也都称不上是好作品。他所提的“风化体”,正是此时文士编写剧本的主要目的,希望藉由戏曲人物的演出,收到教化人心的社会功效。明初大臣邱濬也认为戏曲创作“若与伦理无关系,纵是新奇不足传”[12],这种将道德填入曲文中的理念,导致了《五伦全备忠孝记》的重点不是为了说故事,而是为了演绎道德和伦理观念。邵璨也认为“传奇莫作寻常看,识义由来可立身”也同样忽略了戏曲首先要能感人,其次才能实现教化的作用。
高明倡导“风化体”虽然将戏曲创作理念导向了风教之说,但《琵琶记》中的内容情节并不让人觉得突兀艰涩,因此在明中晚期依然作为文人戏曲理论中评述戏曲发展的标准之一,而邱濬和邵璨则将这种理论推向极端。王阳明也认为:“今要民俗返朴还淳,取今之戏子,将妖淫词调俱去了,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晓,无意中感激他良知起来,却于风化有益。”[13]
在戏曲创作中,搬演忠臣孝子的故事,让人民在无意中受到影响,进而移风易俗。王骥德则从戏曲创作本质的角度认为,只有先“令观者籍为劝惩兴起,甚或扼腕裂眦,涕泗交下而不能已,此方为有关世教之文字”[14].他认为编写剧本首先要激起观众的感动,才能够达到教化的功用。
继明初教化说之后,文人将戏曲创作的本质内涵转移至“情”的内涵,强调“情”是文学艺术的出发点和原动力。汤显祖正是这一主张的代表人物,他认为“人生而有情”,不管是戏曲的创作者还是表演者,只有充分展现人间的种种世情样貌,才能打动人心,发挥戏曲对人的感染力。《牡丹亭》中的杜丽娘便是汤显祖笔下“情至”的代表。如果说汤显祖的“情”乃是就其内在的深度而着眼,那么冯梦龙所谓的“情”,乃是就其广度而言,折射出人情多元化的面貌。他编纂《情史》的目的就是择取古今令人感动的情事,“使人知情之可久,于是乎无情化有,私情化公,庶乡国天下,蔼然以情相与,于浇俗冀有更焉”[15],虽然书中多记载男女之情,但“曲终之奏,要归于正”[16].对于戏剧中“情”与“理”的冲突,冯梦龙认为,自古以来那些忠孝节烈之事,依从道理去做,那是一种勉强自己的举动,出于真情实感去做,才是真切的。无情的男子或者女子,一定不是义夫节妇。当世的人们认为需要用“理”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殊不知人们的行为出于“情”才显得真切。所以“妾而抱妇之志,妇之可也。娼而行妾之事,妾之可也”[17],这都是真情所致,并不因理法规范才去做。冯梦龙的观点在“情”与“理”之间找到了调和之处,并没有贬抑“理”的说法。孟称舜则认为男女之间互相有意,都是因情而起,这种情看似非正,但只要是至情之女子“不以妍夺,从一而终,之死不二”[18].这种情由真而生,能坚贞自守,那么最终能归为正。
《六十种曲》中的剧作者,大多会安排妓女身份的女主角首次出场就表明其心志不同于他人之处,如《金雀记》第十出“守贞”、《西楼记》第三出“砥志”、《霞笺记》第三出“丽容矢志”等。她们在“理”的引导下自述心志,一心从良,在“情”的触发下坚贞守志。这种缱绻缠绵的男女爱情,在历经苦难后终成眷属,既实现了戏剧“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19]的教化功能,又带动了文人对于人生真实处境的关怀。让时人评价妓女守贞的行为,不仅是以礼教规范作为标准,更是出于其内心真情的诉求。
同时,“晚明名妓文化的繁荣,促进了家内和家外才华之美这一种理想,城市经济的动力也使其成为可能,不少男人实际渴望拥有有文化的妻子”[20].但在现实生活中,文人的渴望却未必能实现,他们通过创作来弥补这一现实中的缺憾。
晚明出现的名妓正是男子心中理想的女性的代表。《六十种曲》中妓女形象的塑造,在“情”与“理”戏曲创作理论指导下,完成了自身的调和。她们不仅“才、艺、色”三者兼备,并且具有妓女这一身份难得的坚贞守志,形成了“德、才、艺、色”兼具的理想品格,再通过皇帝诰封旌表实现其身份的转变。
3. 明代传奇创作尚“奇”的审美取向。
“传奇”一词首见于唐人裴鉶小说集之名称,宋以后人们就以“传奇”指代唐代文言文小说,明人则借用“传奇”作为戏曲的通称。胡应麟从戏曲创作来源的角度称:“……若今所谓戏曲者,何得以传奇为唐名?或以中事迹相类,后人取为戏剧张本,因辗转为此称不可知。”[21]若从戏曲评论的部分考查,元代的钟嗣成早在其《录鬼簿》中讨论当时的杂剧作品具有新奇的特点。明人以“传奇”命名这一新兴的长篇戏曲剧作,正凸显了明代文人创作这类剧本时所追求的审美观点便是“奇”,传奇作品能否呈现“无奇不传,无传不奇”[22]的情节内容,也是时人作为评价作品优劣的标准之一。
明传奇创作之初虽以“奇”为尚,剧作家编写剧本时,也希望在既定的传奇格局规范下,就人物的选择与情节的发展上做到既真实又新奇,传达出真情实感,来打动观众的心。然而从传奇的发展脉络来看,明后期的一些剧作家将“奇”之观点过度延伸,导致情节上的荒谬牵强,忽略了人物应当情真,剧情发展也须合理的基本原则。“今世愈造愈幻,假托寓言,明明看破无论,即真实一事,翻弄作乌有子虚。总之,人情所不近,人理所必无……演者手忙脚乱,观者眼暗头昏,大可笑也”[23].这样的剧作失去了戏曲的功效,因而使得一些士人也对此风气提出了批评,认为:“新奇是源于真实的新奇,真实是新奇表现的真实。新奇凭情理而立,悖情理而毁,情理是传奇艺术生命的守护神。”[24]
就《六十种曲》中的妓女形象而言,时人追逐尚奇的审美标准以及明人在编写剧本时,往往偏好将生旦设定为“生必为狂且,旦必为娼女”[25]的模式。究其原因,一是根据笔记史料记载,中晚明时文人与名妓之间的交往频繁,名妓常作为文士交际圈的重要成员。二是相对于一般传奇剧作以闺秀千金为女主角,以妓女为女主角更能凸显尚奇的创作主旨,当妓女成为剧作的女主角后,其守贞自持的特质已经先让观者有一股新奇之感,而妓女与书生最终能够旌表婚配这又推翻了以往剧作之套路。此外,《六十种曲》中的妓女对待感情的态度更具超出一般闺秀女子的执著与大胆,她们以美丽的容颜、不凡的才艺、大方的处世态度带给时人惊喜,产生一种不可抗拒的魅力。这既满足了传奇“尚奇”的审美旨趣,又合乎常理使之“奇”不出于人们的日常生活。
三、结语
《六十种曲》中妓女形象所表现出的独特样貌,除融合了时代背景、戏曲创作理论以及传奇创作本身的特点外,也融合了剧作者自身的思想与意识。自元以来,读书人的地位空前下降,当时就有“九儒十丐”的说法,再加上废除科举考试七十余年,不仅读书做官的路行不通,连生存都成了问题。剧作家大多为不得志的文人学士,“兼名位不著,在士人与倡优之间”[26].这使得他们能够与沦落风尘的妓女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对她们的命运有深刻的了解和同情。所以,“在典型生活情境出现时,作家以类同的叙述结构来传达集体欲望”[27].创作者通过创作达到心理上的补偿。于是众多来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的妓女形象得以呈现于世人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