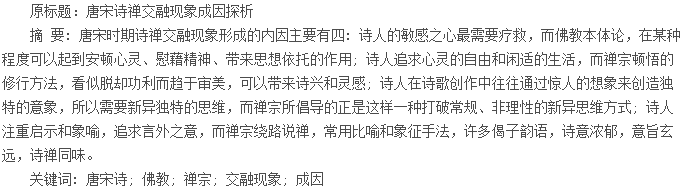
面对最为繁荣的唐宋诗歌,面对唐宋时期趋于鼎盛的佛教禅宗,面对它们在历史文化发展历程中那些相交合的部分,总会让人想到元好问“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的诗句。其实,这精粹诗句包含着极其复杂的内容,牵扯了许多问题,其中最根本的问题莫过于———唐宋二代诗禅交融的动因是什么?佛教和禅宗中的什么吸引了诗人们并令他们趋之若鹜的?据此,本文不揣冒昧,拟从四个方面探讨这一问题。
一、佛教本体论与诗人的超脱之途
禅宗能深入诗人内心与其精神契合的原因,在于它是心的学问。它承袭了佛教的本体论,又改造了它的方法论。佛教认为世界的本性为“空”,世间万物皆是因缘和合生成,也因因缘和合而灭,都空无自性。佛教这种对现世世界的本体论解说,是颇能引起共鸣的,即使是在唐朝盛世,又有几人能如愿以偿快乐一生呢?李白漂泊终生,杜甫困顿一世,王维躲进了山里。“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相对于正置身其中的今日烦忧,昨日不可留的忧愁是淡薄的,但“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每个人仿佛都置身于一个无边的大泽难以解脱,而这大泽的名字即是愁苦。李白的诗句有切肤之感。宋代官场之争甚剧,诗人们更是热心参禅问道,与佛教过从甚密。苏轼、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等大都具有官场受挫、党争失败的经历,“一生做官今日被谪,觉见从前但一梦耳”(《丛林盛事》卷上,安相国语),佛教所宣扬的这种人生如梦、朝夕异世的故事真切地发生着,他们的失意和痛苦“不向佛门何处销”?
诗人是一群痛苦的精灵,痛苦的原因是他们不能停止对生命意义的追寻、追问和追求,是操修心灵者。佛教以另一种方式解答了诗人追问的问题,不论赞同与否,都可以让心灵稍事休憩。于是李白说“天以震雷鼓群动,佛以鸿钟惊大梦”(《化城寺大钟铭并序》),“宴坐寂不动,大千如毫发”(《庐山东林寺夜怀》);杜甫也说“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余亦师粲可,心犹缚禅寂”(《夜听许十一咏诗爱而有作》);王维被称为诗佛,他“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终南别业》),徜徉于山水田园与修禅行道相融的生活之中,自然任远,心无所缚,摆脱了很多俗世的烦忧。中晚唐以来,社会的动荡也带来了人们内心的动荡不安,加剧了内心的苦痛感,去佛教中找寄托的诗人更多了,韦应物、白居易、柳宗元、常建、司空图是为代表。赵宋一代,诗人无不浸淫于佛教,籍此来满足其追求高雅空灵精神乐趣的需要,他们“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东坡诗),将参禅与作诗融合,寄托对世事变幻、人生苦痛的感受,表现出一种禅学化的审美意趣,所谓“诗风慕禅”。苏轼的诗赋正是由于注入了禅的意境和意趣,而在自然、朴实之中又多了一份幽远、超拔、深邃。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则善用佛典禅语入诗,“夺胎换骨”别具一格。
可见,佛教本体论,在某种程度可以起到安顿心灵、慰藉精神,带来思想依托的作用,诗人的敏感之心最需要疗救。于是诗人多向佛。
二、禅宗方法论与诗人的闲适追求
佛教的本体论思想已经建立了完备的体系,禅宗无从发挥,也不必发挥,便在修行方法上作了突破。禅宗尤其南宗不再否定惹人烦恼的尘世,主张“即心即佛”,修行不必外求,外求和他求都是“骑牛觅牛”,南辕北辙。《五灯会元》中记有很多公案,来宣解这一思想。卷第五《石头希迁禅师》记曰:上堂:“吾之法门,先佛传受,不论禅定精进,唯达佛之知见。即心即佛,心佛众生,菩提烦恼,名异体一。汝等当知,自己心灵,体离断常,性非垢净,湛然圆满,凡圣齐同,应用无方,离心意识。三界六道,唯自心现,水月镜像,岂有生灭?汝能知之,无所不备。”[1](P255-256)卷第三《百丈怀海禅师》记有这样一段问答:问:“如何是大乘顿悟法要?”师曰:“汝等先歇诸缘,休息万事,善与不善,世出世间,一切诸法,莫记忆,莫缘念,放舍身心,令其自在。心如木石,无所辨别。心无所行,心地若空,慧日自观,如云开日出相似。但歇一切攀缘,贪嗔爱取,垢净情尽,对五欲八风不动,不被见闻觉知所缚,不被诸境所惑,自然具足神通妙用,是解脱人。对一切境,心无静乱,不摄不散,透过一切声色,无有滞碍,名为道人。
善恶是非俱不运用,亦不爱一法,亦不舍一法,名为大乘人。不被一切善恶、空有、垢净、有为无为、世出世间、福德智慧之所拘系,名为佛慧。是非好丑,是理非理,诸知见情尽,不能系缚,处处自在,名为初发心菩萨,便登佛地。”[1](P133-134)禅宗这种“歇诸缘,休息万事”“道不用修,只莫污染”的修行方式对很难走出情感家门的诗人有极大的吸引力,“即心即佛”“自性清静”的理论激发了他们修心的决心和信心,带来了摆脱现实滞累和烦恼的希望。禅宗改变了佛教严苦的修行,以活泼洒落的风格呈现出来,一新当时文人学者的耳目,吸引了大批文人士大夫。王安石在其诗《寓言三首》中就质疑了以往面壁坐禅的修行方式,肯定了自性清净的禅法,其曰:“本来无物使人疑,却为参禅买得痴。闻道无情能说法,面墙终日妄寻思。”黄庭坚《寄黄龙清老》则肯定了南宗禅自身即佛、无需外求的观念和方法,曰:“骑驴觅驴但可笑,非马喻马亦成痴。一天月色为谁好,二老风流只自知。”可见这种修行方式很得诗人们的认可和喜爱。
葛兆光先生曾对禅宗南宗的特点作过深刻的分析,他说:“我心是佛———我心清净———依心行动———适意自然,这种宇宙观、时空观、人生哲学、生活情趣极为精致的结合,是一个脉络十分清晰、顺序十分自然的发展过程,所以在慧能、神会之后,几乎每一个禅宗大师都要大讲这种适意的生活情趣与现世自我精神解脱的人生哲学。”[2](P106)这种闲适的生活情趣和淡泊超然的人生哲学,对整日受苦痛煎熬的诗人来说具有莫大的吸引力。
于是居士多起来,尤其是在宋代,如六一居士(欧阳修)、东坡居士(苏轼)、浮休居士(张舜民)、姑溪居士(李之仪)、邢沟居士(秦观)、清真居士(周邦彦)、易安居士(李清照)、幽栖居士(朱淑真)、石湖居士(范成大)、稼轩居士(辛弃疾),等等。
诗人们以居士自居,不仅是追时髦,更是一种不与社会生活的利害琐屑相关涉的生活姿态的表示。禅宗由北宗的净心、澄心到南宗的无心,其非功利的思想一脉相承并更加突出。《五灯会元》卷第十四还记有:真州长芦妙觉慧悟禅师,上堂:“尽大地是个解脱门,把手拽不肯入。雪峰老汉抑逼人作么?既到这里,为甚么鼻孔在别人手里?”良久曰:“贪观天上月,失却手中桡。”僧问:“雁过长空,影沉寒水。雁无遗踪之意,水无沉影之心。还端的也无?”师曰:“芦花两岸雪,江水一天秋。”曰:“便恁么去时如何?”师曰:“雁过长空聻!”僧拟议,师曰:“灵利衲子。”
[1](P911)“雁无遗踪之意,水无沉影之心”,这是一种无心状态,是完全脱却功利的,因此能看到“芦花两岸雪,江水一天秋”的澄明之境,而这种非功利之心正与审美心理相一致。因此,禅宗不仅是诗人们安顿心灵、澡雪精神的所在,而且可以带来诗兴和灵感。据《宗门武库》载,王安石受蒋山元禅师指点,学习坐禅,其后“一日谓山曰:坐禅实不亏人。余数年要作《胡茄十八拍》不成,夜坐间已就”。王安石晚居钟山,读经参禅,因此摆脱了早、中期诗歌的那种功利性和实用性,呈现出闲适淡泊的生活情趣,如其《游钟山四首》之一:“终日看山不厌山,买山终得老山间。山花落尽山长在,山水空流山自闲。”再如《两山间》:“山花如水净,山鸟与云闲。我欲抛山去,山仍劝我还。”在诗人的笔下,山、水、云、鸟等意象,无不渗透着活泼灵动的禅意禅趣。黄庭坚评曰:“荆公暮年作小诗,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觉沆瀣生牙颊间。”[3](P234)这确乎也是诗人修禅的妙处。
三、禅宗思维与诗人的创作思维
禅宗新异的理论背后是其新异的思维,其思维方式即“顿悟”。顿悟自性,反照自心,即明心见性。而要明心见性,就要打破常规思维模式,运用非理性的思维。关于此,《五灯会元》记有很多公案。
卷第八《福清行钦禅师》记曰:问:“如何是然灯前?”师曰:“然灯后。”曰:“如何是然灯后?”师曰:“然灯前。”[1](P506)卷第九《芭蕉慧清禅师》记曰:上堂,拈拄杖示众曰:“你有拄杖子,我与你拄杖子;你无拄杖子,我夺却你拄杖子。”靠拄杖下座。僧问:“如何是芭蕉水?”师曰:“冬温夏凉。”问:“如何是吹毛剑?”师曰:“进前三步。”曰:“用者如何?”师曰:“退后三步。”问:“如何是和尚为人一句?”师曰:“只恐闍黎不问。”上堂:“会么?相悉者少。珍重!”问:“不语有问时如何?”师曰:“未出三门千里程。”问:“如何是自己?”师曰:“望南看北斗。”[1](P550-551)在这里,前即是后,后即是前,前后无分别,有就是无,无就是有,有无无二致,不出门而能行千里,南望却能看见北斗,这种离奇而怪诞的思维,带来的是一种对世界的全新认识,看到的是完全异于常规的情景,使人心惊肉跳、倏然觉悟。这种感觉让人会想到李贺的诗所带来的奇诡兀立的境像:“海沙变成石,鱼沫吹秦桥。空光远流浪,铜柱从年消”(《古悠悠行》);“茂陵刘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迹。画栏桂树悬秋香,三十六宫土花碧。魏官牵牛指千里,东关酸风射眸子。空将汉月出宫门,忆君清泪如铅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携盘独出月荒凉,渭城已远波声小”(《金铜仙人辞汉歌》)。
其实禅宗推崇的只是这样一种思维,用以打破常规的知见,而决非这种“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境界,因此还有夺人夺境的讨论。
卷第十一《涿州纸衣和尚》记曰:初问临济:“如何是夺人不夺境?”济曰:“煦日发生铺地锦,婴儿垂发白如丝。”师曰:“如何是夺境不夺人?”济曰:“王令已行天下遍,将军塞外绝烟尘。”师曰:“如何是人境俱夺?”济曰:“并汾绝信,独处一方。”师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夺?”济曰:“王登宝殿,野老讴歇。”[1](P656)卷第十二《金山昙颖禅师》记曰:问:“如何是夺人不夺境?师曰:“家里已无回日信,路边空有望乡牌。”曰:“如何是夺境不夺人?”师曰:“沧海尽教枯到底,青山直得碾为尘。”曰:“如何是人境两俱夺?”师曰:“天地尚空秦日月,山河不见汉君臣。”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夺?”师曰:“黄啭千林花满地,客游三月草侵天。”[1](P720)这里“夺”是除去的意思,修行的境界达到人境俱夺才是彻底破,彻底空,但还有更高的境界,那就是“人境俱不夺”,类似于青原惟信禅师所说的“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的第三种境界。这表现在诗歌创作上,就是追求自然、简淡的境界。
试以此分析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可谓人境俱夺,一片虚空;“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则是闲适自然,人境俱不夺了。再看一下杨万里《桑茶坑道中》其七,其诗曰:“晴明风日雨干时,草满花堤水满溪。童子柳荫眠正着,一牛吃过柳荫西。”也是物我双泯,人境俱不夺,禅意盎然而了无痕迹,活泼泼,一片生机意趣。足见,禅宗的“悟”与诗歌创作思维有很多相似相通之处。
四、禅宗语言观与诗人的语言观
禅宗主张不立文字,“诸佛妙理,非关文字”,“若取文字,非佛意”(惠能语),提倡见性成佛;然而佛性又不可言说,“说似一物即不中”(南岳怀让),一旦说出,就成为相对的,“出口便错”。但具体的传法过程中,为了指点后学,传授心得,又不能离开语言。于是,禅师们只好“绕路说禅”,选择俭省、多义而非逻辑的语言,来打破语言常规,以启发对方不要“死于句下”,因此反而要讲究语言技巧,否定比喻和象征,又运用比喻象征的方式阐明教义。《景德传灯录》卷第六《越州大珠慧海禅师》有云:曰:“不见性人亦得如此否?”师曰:“自不见性,不是无性。……马鸣祖师云:所言法者,谓众生心。若心生,故一切法生;若心无生,法无从生,亦无名字。迷人不知法身无象,应物现形,遂唤青青翠竹,总是法身;郁郁黄华,无非般若。黄华若是般若,般若即同无情。翠竹若是法身,法身即同草木;如人吃笋,应总吃法身也。如此之言,宁堪齿录?对面迷佛,长劫希求,全体法中,迷而外觅。是以解道者,行住坐卧无非是道;悟法者,纵横自在,无非是法。”[4](P144)此处用“如人吃笋,应总吃法身”来批驳“青青翠竹,总是法身;郁郁黄华,无非般若”的看法,提出“法身无象(相)”的观点,可谓自然、生动、明晰。
禅师说法还经常用诗意浓郁的偈语来传达。
《五灯会元》卷第五《夹山善会禅师》:“问:‘如何是夹山境?’师曰:‘猿抱子归青峰里,鸟衔花落碧岩前。’”[1](P295)《祖堂集》卷一七所记长沙景岑的示法偈:“百尺竿头不动人,虽然得入未为真。百尺竿头须进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即使现在看来,这些师徒问答和示道偈语也都形象生动,甚至诗意盎然,有着隽永的意味。
禅宗对语言的态度和反思也吸引了诗人。禅与诗在唐以后过从甚密,互相影响,互为补充。因为两者都注重内心感悟,都注重启示和象喻,追求言外之意味、幽远之境界。宋代以来,文字禅和禅悦之风盛行,诗人们更善于融禅理、禅趣入诗,出现了很多别有意味的诗作,如:王安石《即事三首》之一:“云从钟山起,却入钟山去。借问山中人,云今在何处?云从无心来,还向无心去。无心无处觅,莫觅无心处。”这里,“钟山之云”无心而来,无心而去,适意自然、任运随缘,是渺渺杳杳的诗境,也是渺渺杳杳的心境,有限的个体自觉地融入到无限的自然中去。再如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诗曰:“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在这里当时还年轻的诗人用飞鸿雪泥来化用“空中鸟迹”的佛教典故,将人生的无常、无我和无住表现得生动形象又有含蕴不尽的意味。
其实,僧人也有不少习诗、擅诗者,与诗僧交游唱和,也是吸引诗人向佛修禅的一个方面。禅宗演变为五宗七派后,开始竞相以诗偈来阐发禅理。“为爱寻光纸上钻,不能透处几多难。忽然撞着来时路,始觉平生被眼瞒。”(《林间录》卷下)这是杨岐派禅师白云守端对于悟道过程的描写,佛理不在佛经,不能“寻光纸上”,而需要顿悟“本心”。这些诗偈似诗似偈,锻炼了作诗能力,提高了写作技巧,诗僧渐渐多起来。宋代既通禅理又具文采的禅僧就有很多,如明教契嵩、佛印了元、金山昙颖、圆通居讷、觉范慧洪等,其中慧洪才气横溢,《僧宝正续传》卷二说他“落笔万言,了无停思。其造端用意,大抵规模东坡,而借润山谷”,由此也可以看出苏黄等诗人对他的影响,诗对禅的渗透。这些能文善诗的僧人对诗人也是一种吸引,他们乐于与之诗文唱和,“路逢剑客须呈剑,不是诗人不献诗”(临济义玄),建立了融洽的僧俗关系,促进了禅味诗的流行和文字禅的展开。
总之,唐宋时期,诗禅相融现象发生的动因是多维多向的。上述四方面主要通过分析诗人的心理诉求、生活观念、思维方式、语言观与佛禅本体论、方法论、思维方式、语言观的契合点、近似点或者可通约性,来揭示诗禅相融现象发生的主要内因。除此之外,诗禅相融现象的发生还有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诸多外部原因,篇幅所限,此不赘述。
参考文献:
[1][宋]普济.五灯会元[M].苏渊雷,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
[2]葛兆光.禅宗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3][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宋]道元.景德传灯录[M].朱俊红,点校.海口:海南出版社,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