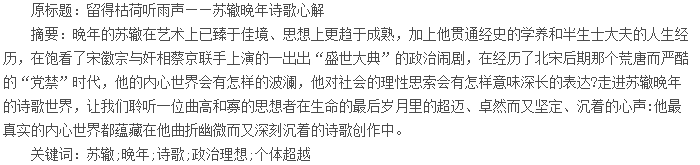
苏辙,字子由,一字同叔,自号颍滨遗老,北宋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与父苏洵、兄苏轼并称“三苏”,“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苏辙一生著作颇丰,“所著《诗传》、《春秋传》、《古史》、《老子解》、《栾城文集》并行于世。”(《宋史·苏辙传》)在文学史上,苏辙最为人所称道的是其散文创作,其诗歌作品似乎很少受人关注。宋人胡仔的《沼溪渔隐丛话》收录了包括苏轼、黄庭坚、秦观、张耒在内的诸多北宋名家的诗歌,唯独没有苏辙的作品入选。后来的诗评家、各类诗歌选本也很少选录苏辙的诗歌。
原因何在?是苏辙的诗歌创作不丰,抑或其作品不足为道?其实在当时苏辙就有一位知音———陆游,他对苏辙的诗情有独钟,宋人周必大《跋苏子由和刘贡父省上示座客诗》云:“吾友陆务观,当今诗人之冠冕,数劝予哦苏黄门诗。”既然是“数劝”,可见在陆游眼中,苏辙的诗是大有深意的。本文拟追寻陆放翁之意,对苏辙晚年诗歌作品中的深广忧思进行一番解读。
苏辙晚年的诗歌作品大多收集在他亲自编定的《后集》和《三集》中,写作时间从元符三年(1100)遇赦北归到政和二年(1112)去世,作品数量约三百余首,其中田园题材的作品近半。这一方面与苏辙的晚年隐居退耕生活有关,同时也反映了苏辙的诗歌创作活动受到宋诗内容的日常生活化倾向的影响,只不过苏辙晚年的诗歌题材将这一创作倾向发展到令人深思的境地———幽微曲折而有所指。宋人孙如听在《苏颖滨年表》中记录:“辙居颖昌十三年。颖昌当往来之冲,辙杜门深居,著书以为乐,谢绝宾客,绝口不谈时事,意有所感,一寓于诗,人莫能窥其际。”由此可见,著书成为晚年苏辙的主要生活内容,苏辙就生活在“夜雨独伤神”的晚年笔耕的世界之中。表面上看,晚年的苏辙终日默坐,著书写诗,不与外人相见,而其内心却沟壑万千:他最真实的晚年内心世界其实就蕴藏在他曲折幽微而又深刻沉着的诗歌创作中。走进苏辙晚年的诗歌世界,让我们聆听一位曲高和寡的思想者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所发出的坚定沉着而又超迈卓然的心声。
苏辙的晚年光景可谓孤独凄凉,身边的至亲好友都先他而去:他一生挚爱追随的兄长苏轼卒于北归的第二年,即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好友兼师生的秦观卒于元符三年(1100年);未曾谋面已成挚交的黄庭坚卒于崇宁四年(1105年),正如其侄苏过在《叔父生日》一诗中所云:“造物真有意,俾公以后凋”,此时的苏辙虽说多少有些曲高和寡,但却是当时北宋文坛上屈指可数的大家:艺术上已臻于佳境,思想上渐趋成熟,加上他贯通经史的学养和半生士大夫的政治经历,在饱看了宋徽宗与奸相蔡京联手上演的一出出政治闹剧,在经历了那个荒唐而严酷的“党禁”时代,作为被严酷迫害的元祐党人的他,内心世界会有怎样的波澜,他对社会的理性思索会有怎样意味深长的表达?对于这一切,苏辙在他的晚年诗歌世界里作了幽微深刻而又卓尔不凡的理性表达。
一、理趣、事趣
苏辙兄弟俩一生中常有“归耕”之念,然而在晚年光景中真正将之付诸实践的是苏辙。隐居颖昌的约十年间里,苏辙似乎真正做起了农民,“阴晴卒岁关忧喜,丰约终身看逸勤。家世本来耕且养,诸孙不用耻锄耘”。在他的影响下,据说他的三个儿子也都“善治田”。晚年的苏辙有关农事、田园主题的诗歌创作一下子多了起来,有关注气候节气的,如《春无雷》、《仲夏始雷》、《久雨》、《喜雨》、《小雪》、《十一月十三日雪》、《冬至雪》、《甲子日雨》、《苦雨》等;有议论农事的,如《杀麦》、《藏菜》、《秋稼》、《蚕麦》、《收蜜蜂》等;有记录田家生活的,如《索居三首》、《初得南园》、《泉城田舍》等,苏子由沉静好思、理智深刻,加之一生历经仕宦,他的农事、田园题材的诗歌作品比之前人创作,有着宋型文化特有的士大夫情怀,这使得他的此类作品突破了以往田园、农事题材的创作范畴,将农家叹的内容和对此所进行的政治剖析和理性思考写进自己的诗中,将田园诗、农事诗的创作提升到治国平天下的高度,并以其鲜明的理性特征直接影响了南宋范成大的田园诗创作。
十一月十三日雪
南方霜露多,虽寒雪不作。北归亦何喜,三年雪三落。
我田在城西,禾麦敢嫌薄。今年陈宋灾,水旱更为虐。
闭籴斯不仁,逐熟自难却。饥寒虽吾患,尚可省盐酪。
飞蝗昨过野,遗种遍陂泺。春阳百日至,闹若蚕生箔。
得雪流土中,及泉尽鱼跃。美哉丰年祥,不待炎火灼。
呼儿具樽酒,对妇同一酌。误认屋瓦鸣,更愿闻雪脚。
清人史震林《华阳散稿·序》云:“诗文之道有四:理、事、情、景而已。理有理趣,事有事趣,情有情趣,景有景趣。趣着,生气与灵机也。”作为文学家兼思想家的苏辙的诗歌作品,就是在理趣与事趣中追求自己的艺术风格,具有典型的宋型文化的特征,这实际上是宋代士人的政治诉求在文学观念上的体现。这首诗作于崇宁元年,这一年正是徽宗朝新旧两党相持的格局被打破,新党重新战胜旧党之时:徽宗起用蔡京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接着焚毁元祐法,恢复新法,确定“邵述路线”,开始了无休止的党派纷争。也就在这一年,全国多地发生蝗灾、旱灾,据《宋诗·徽宗纪》载:“是岁京畿、京东、河北、淮南蝗,江、浙、熙、河、漳、泉、潭、衡、郴州、兴化军旱。”苏辙的这首诗真实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实情。此时的朝廷正忙于党派路线之争,对旧党人物及其新党中的异己实现大规模整肃,立“元祐党碑”,毁禁三苏及其弟子的文集,甚至牵连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无休止的党派纷争,使得士人间正常平和的人际关系骤然紧张,破坏了以往派系间的大致平衡;而这种制衡关系,本是赵宋的祖宗之法所着意维持的”,因此朝廷根本无暇顾及各地的灾情,对于民间的请愿基本不予理睬。苏辙为人谨慎持重,政治见解周到而不乏主见,他清醒地认识到时局的严酷和朝廷的不仁,“闭籴斯不仁,逐熟自难却”,“闭籴”,指将辖区内的多余粮食统一收购起来,以防邻近灾区的难民来“逐熟”,必要时还可以囤积居奇,高价卖出以增加收入。诗中苏辙以一个士大夫政治家的眼光,一针见血地揭示出朝廷的腐败与不仁。
对于这样不作为的朝廷,他已不抱任何希望,只能寄希望于老天的慈悲:“得雪流土中,及泉尽鱼跃”,竟然老天开眼,降下瑞雪,将蝗虫遗卵打入土中,并随着雪水融化流入河中果腹鱼肚。“美哉丰年祥,不待炎火灼”,苏辙此时的“兴高采烈”,无疑是对徽宗朝无比失望下的谴责与讽刺,同时也是对黎民百姓的命运发自内心的同情与担忧,由于诗人士大夫的身份,使得诗歌的内容向义理的纵深处开展。看似琐屑的题材却表现以深刻的见解和艺术的形式,苏辙的作品正是在叙事和说理中达到一个兼具艺术特色的理性高度。
据史料记载,苏辙绍圣初年因上书谏事被贬,“筑室于许(今河南许昌),号‘遗老斋’,自作传万余言,不复与人相见。终日默坐,如是者几十年”(《宋史·苏辙传》),直至故去。苏辙此举看似弃绝外界,实则是为自己开启了一个新的生命空间:默坐不是封闭,而是澄明淡远的无限精神世界的敞开。终日静默的苏辙并非不问政事,他的内心一刻也不曾远离政治,“‘以天下为己任’可以视为宋代‘士’的一种集体意识,并不是极少数理想特别高远的士大夫所独有;他也表现在不同层次与方式上。”
正如他自己所言:“闲中未断生灵念”(《小雪》)。安贫乐道的苏辙在他的诗歌世界,以自己的方式来体认他的生命价值。刘攽《中山诗话》云:“诗以意为主,文词次之,或意深义高,虽文词平易,自是奇作。”苏辙诗歌创作历来风格清淡、格律工细,看似平易,实则蕴藏深“意”,对日常生活的细致描述其实正是其成熟诗风的表现。退隐后的苏辙在他的诗歌作品中依然表现出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蕴涵着对当时社会政治透辟的见解和深度的理性思考,超越了传统农事诗题材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这正是苏辙此类农事诗的意义所在。
与白居易的新乐府相比,在抨击政治的尖锐性上,白居易并不逊色,但从诗歌内容上来说,苏辙此类的诗歌是他晚年实际生活的真实体验,字里行间蕴含着诗人对田园、对农民十分真淳的感情,“旱久魃不死,连阴未成雪。微阳九地来,颠风三日发。父老窃相语,号令风为节”(《冬至雪》);“忽作连日雨,坐使秋田荒。出门陷涂潦,入室崩垣墙。覆压先老稚,漂沦及牛羊。余粮讵能久,岁晚忧糟糠。天灾非妄行,人事密有偿。嗟哉竟未悟,自谓予不戕。造祸未有害,无辜辄先伤。箪瓢吾何忧,作诗热中肠”(《苦雨》);或同情、或忧愤、或担心、或沉痛、或无奈、或心酸、或讽戒,因此其作品更具艺术感染力。
正如范仲淹在《岳阳楼记》所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晚年的苏辙仍在以自己的诗歌创作践行着他的政治气节和“与君同治”的政治理想。
二、个体生命的内在超越
然而苏辙晚年诗歌创作的意义远不仅如此。苏辙一生学术著作颇丰,有《春秋集解》、《诗集传》、《古史》、《老子解》、《孟子解》等著作传世,这些作品也大多完成于晚年闲居之时。正如作者自己所谓,这些著作颇能“得圣贤处身临事之微意”。事实上,苏辙不论是学术著作还是文学作品,皆以“求道”为最高境界。正如上述所引《十一月十三日雪》一样,苏辙晚年诗歌作品还有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地方,那就是常常在题目中标注年月日以及各种节气,如《冬至雪》、《立秋偶作六月二十三日》、《仲夏始雷》、《春尽三月二十三日立夏》、《立冬闻雷九月二十九日》、《还颍川甲申正月五日》等等,这样的标注在他的诗集中比比兼是,显然这是作者有意而为之。苏辙曾著《春秋集解》十二卷,这时的诗歌创作似乎也是在模仿《春秋》以年月日系事的体例,将自己晚年的每一次重要经历以及思想变化的重要阶段,均以史的形式呈现于世人面前,“就是诗的世界的展开过程与生命延续过程的高度一致性。”
不论是对风、雷、雨、雪、霜、星、月等自然现象的静观默察或春秋笔法,还是有关居室、庭院、松、柏、竹、兰等平居生活的写照或内心世界的隐喻,苏辙将自己晚年的日常生活和真实的内心世界在诗歌里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立体化呈现,以此来营造他的诗世界,体现了所属时代的文化精英勇于担当的社会良知与宠辱不惊的精神风范。
对政治气节的崇尚和对理想人格的塑造,仍然是晚年苏辙的人生追求,但除此之外,苏辙还在思考着比政治更具终极意义的人生价值。
遗老斋
老人身世两相遗,绿竹青松自蔽亏。
已喜形骸今我有,枉将名字与人知。
往还但许邻家父,问讯才通说法师。
燕坐萧然便终日,客来不识我为谁。
待月轩
轩前无物但长空,孤月忽来东海东。
圆满定从何处得,清明许与众人同。
怜渠生死未能免,顾我盈亏略己通。
夜久客寒要一饮,油然细酌意无穷。
藏书室
读书旧破十年功,老病茫然万卷空。
插架都将付诸子,闭关犹得养衰翁。
案头萤火从乾死,窗里飞蝇久未通。
自见老卢真面目,平生事业有无中。
《遗老斋》作于大观元年(1107)遗老斋初成之时,另苏辙还有《遗老斋记》,以叙其志。苏辙为官时,刚直耿介,与世俗多有违背,也不合自己的人生适意的原则,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退居遗老斋可以算作得其所哉。但‘遗老’二字,凝聚着苏辙的一生苦涩,可以作两面观:一是被遗忘的老人,二是以遗忘表示出的心如止水的绝望。”
苏辙晚年苦心经营他的“遗老斋”、“待月轩”、“藏书室”,就是要为自己的心灵找一个安顿的地方,“老人身世两相遗,绿竹青松自蔽亏”,用苏辙自己的话说,就是“行止未尝少不如意,则予平生之乐,未有善于今日者也”(苏辙《遗老斋记》),此时的苏辙就是要以恬然自适的虚静心境,观世间百态,品人生意味,传名士风流。
“已喜形骸今我有,枉将名字与人知”,悲观、酸楚的情绪却出之以平和、淡然的口气,“往还但许邻家父,问讯才通说法师。燕坐萧然便终日,客来不识我为谁”,没有倾诉、没有怨尤,平实淳朴、情理交融,感慨凄然中透露出的是苏辙内心的沉着与深厚,实乃“悱恻而不乱”的典范。
“待月轩”、“藏书室”也是其晚年修养之地,身处其间的作者正是在静观默察中展开对人生的感慨与思考。“轩前无物但长空,孤月忽来东海东”,诗境简洁明快却又丰盈秀澈,“圆满定从何处得,清明许与众人同。怜渠生死未能免,顾我盈亏略己通”,结合苏辙的《待月轩记》,可知整首诗表现出了苏辙这位文学家、政治家在历经人生坎坷后对儒家经典命题“性命”之说的探索与思考。苏辙认为“性”是不变的,发生变化的是“性”所寄托的“身体”,这就如同日与月的关系,人应该如月亮一样,虽有阴晴圆缺,但也要尽人事而顺天命。《藏书室》则是苏辙以谦虚的态度来委婉地总结自己一生坚持读书之道,“插架都将付诸子,闭关犹得养衰翁”,且将客观清寂的治学家风传于后辈;“自见老卢真面目,平生事业有无中”,问心无愧、淡泊超然,了无半点功利之心,自是令人倾服。
退隐之后的苏辙并不想做超然出世的达者,对于他所处的时代,始终不能漠然忘怀。“一时用舍非吾事,举世炎凉奈尔何”(《感秋扇》);“阴阳往复知有数,已病还瘳非即死”(《林笋复生》),“晏家不愿诸侯赐,颜氏终成陋巷风”(《初得南园》),这里苏辙表明的是:用舍穷达与人生价值的实现无关,“‘内圣’不是‘外王’的准备阶段,而是其本身就是人生终极价值的实现。学而优并不为仕,为的是个体生命的内在超越。”
苏辙的思想体系是以儒家为主,同时又会通三教。“就儒家学术的内在逻辑来说,如果‘外王’之路不通,人们自然要在‘内圣’之途寻找出路了。”
晚年的苏辙始终随缘自适、旷达乐观,立功不成,则努力立德、立言,在困境中仍孜孜不倦地思考着历史、感悟着人生、经历着王朝的盛衰、寻找着生命的价值,展现着个体生命的内在超越:用舍穷达无关乎人生价值的实现,“进亦忧,退亦忧”,“虽南面之王不能加之”(苏辙《东轩记》)。“北宋士大夫心态从‘先忧后乐’到‘箪食瓢饮’的内在转向,在苏辙的身上表现得极为典型”。
“对于伟大的文学家,如果我们放弃其思想学术而不顾,甚至抛弃其学术著作而不理,那简直就等于是舍其黄钟大吕而沉溺于里曲小调了。小调虽美,却非大雅正音,更非天地正气。以为这样能真正把握作家的艺术造诣和思想内涵,无异于舍本逐末、缘木求鱼矣。”
对于苏辙这样的学术著作颇丰的文学家,对他的文学作品进行鉴赏时,必须要“文”“理”结合,否则就是如入宝山而空手归了。
苏轼在《答张文潜书》中曾这样评价苏辙:“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子瞻实为子由知音也。苏辙晚年诗歌作品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其缜密超迈的理性精神以及独有的哲学思辨色彩,赋予他的创作以高明深邃的思想和坚定沉着的主体精神;而其义理兼融、法度雍容、雅健秀澈的文风更足以垂范后世。
唐朝诗人李商隐诗云:“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这诗句似乎很合晚年苏辙的处境和心境,只是这箪瓢自乐的“枯荷”所发出的坚定、执着的心声,给后世树立了为人、为文的不朽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