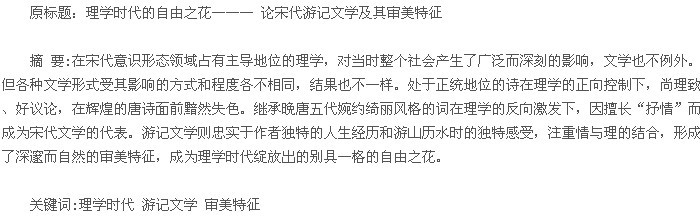
社会性和审美性都是文学的本质属性。社会性重理,讲规范,求统一;审美性主情,讲自由,求多样。
文学的理想状态是社会性与审美性、理性与感性的结合,历代文人也都在追求这种融合,但结合的程度却往往因时代、作家、体裁的不同而有别。在宋代,意识形态领域中占主导地位的理学使各种文学样式无一不受其规范、着其色彩,游记文学当然也不例外。但由于作者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游记文体因游而记的特点,使它没有成为理学的传声筒,反而在情理相融方面了达到较高程度,成为理学时代绽放出的自由之花。
游记文体:理学时代融合情理的独特形式宋代理学的形成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赵宋王朝鉴于秦后历代王朝无不毁于战乱的惨痛教训,确立了“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这一国策的推行,不仅大大激发了文人士大夫强烈的经世意识,同时也为宋儒们积极建构“以儒学为主体,吸收、改造释、道哲学”,“涵泳三教思想精粹”的新儒学体系提供了宽松的社会环境。新儒学继承孔孟思想,以“天理”为核心,力求贯通宇宙自然和人生命运,以使国家长治久安,“理学”之名由此而来。
关于理的内涵,宋代理学家们普遍认为,它是万事万物的本原,在宇宙表现为自然规律,在人类表现为社会伦理,在个人身上表现为人性,因而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不可或缺。但理并不是一个可见的东西,它藏于万物、隐而不显,人们要想依理而行首先需要求取,然后还要能守得住。无论求还是守,方法得当十分重要,否则便求不得,也守不住。对求理、守理的方法,宋代理学家也作了深入的探索,他们把“格物致知、反躬自省”奉为求理之法,把“存天理,灭人欲”视为守理之法。宋代理学家之所以要把“存天理,灭人欲”作为守理之法,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天理”与“人欲”水火不容、不可调和,不灭人欲无以守天理。宋代理学的这种主张表现在诗歌创作中,就是推崇“理致”、喜好“议论”,排斥属于人欲的情感。这种违背诗歌本质的做法,使诗失却了鲜活的生命力,变得黯然无色。
情感是人的心理动力,它总会寻找各种机会,通过各种方式表现出来。以宋代文学而言,当诗受到“理”的抑制而失去光彩时,“情”开始借助词的形式来表达,主情的词经过文人的精心创作,一跃成为和唐诗相媲美的文学典范。或许这样的文学格局并不理想,但却给宋代文人提供了更为灵活的创作空间:
当他们需要表达经世志向、才学胆识时,就选择诗与之相伴;当他们需要表现情感世界、心灵衷肠时,就选择词与其相依。“独步天下”的苏轼用诗“怨刺”、“讥诮”朝政,其词则“纯以情胜”;旷世才女李清照用词表达多愁善感、缠绵凄婉的愁情,其诗则显苍劲古朴之风,透露出“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豪气。
在肯定宋代文人的创作智慧和宋词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时,我们必须认识到,理与情分别由诗和词来表现,与文学以情为核心的情理相融之本质并不相符。在这种情况下,宋代游记文学所走的情理相融之路及其所取得的文学成就,就显得格外令人注目。
细细想来,宋代游记文学走上情理相融之路,与理学的反向促动有关。在宋代,理学激发了文人士大夫的经世意识,但朝廷却没有为他们的积极经世提供制度保障,遭遇贬谪之事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被赶出庙堂而又不愿于朝廷为敌的文人,就自觉地选择了走向山林的道路。当他们带着政治上的失意和心理上的郁闷走向山水时,情感找到了寄托,心灵得到了慰藉,束缚得以解脱,胸襟得以开启,于是,一篇篇融情于山、寓理于水的山水游记随之产生。
不仅如此,游记独特的文体形式也为情理相融提供了有利条件。游记是一种以纪游为主要内容的文体,任何一篇游记都是因“游”而生、为“游”而记的,“游”的状态决定着“记”的特点。关于“游”的状态,我们可以从自身的游览经历和“游”的词义角度去把握。《说文解字》把“游”解释为“旌旗之流”,意思是旌旗所垂之旒随风飘荡、自由自在的样子。从这一解释中可以看出,自由自在是“游”的本义。这与我们在游览经历中的感受是一致的,游者在“游”的过程中往往能充分感受物我相融的身心愉悦。梅新林先生认为,“游”具有形而上与形而下两种意蕴,形下之游是一种实践活动,形上之游是一种精神境界:“是主客关系中心物契合、活泼流动的心理状态和主体所达到的或获得的化同大道、游于无穷的超越性精神境界”。但两者之间又有着内在的联系:形上之游离不开形下之游,但又不止于形下之游,是形下之“游”的升华。有了这种升华,“游”才成为心物契合、化同大道的活动,并为“记”的情理相融奠定现实基础。可以说,人们只要清醒地忠实于“游”中的所见、所感、所思,其“记”自然会达到情与理的融合。
从上述简要分析中可以看出,游记文体是宋代文人的自觉选择,是时代特点、个人经历与表达形式相结合的产物,也是融合情理的最佳形式之一。随着诸多着名文人加入创作行列,宋代游记文学的影响日益扩大,成为当时文坛上一道别具一格、意蕴深厚的文学景观,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游记作品:理学时代凸显自由的文学景观中国文化中有一种把山林与仕途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其形成与社会现实有关。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现实造就了长沮、桀溺、荷蓧丈人、楚狂接舆等隐士;战乱不止、等级森严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栖竹林的七贤、居园田的陶潜、游山水的谢灵运等。古代高士走向山水是一种与强暴政治分庭、与社会庸俗扬镳的行为,表现着淡泊名利、刚正不阿的高贵品质,后人因此而景仰他们、效仿他们的行为,一旦看破现世“红尘”,就走向江湖之滨、深山大泽,或凿穴而居、结草为庐,或着袈裟衣、披鹤氅裘。这样一来,山水不仅标志着与仕途的对立,也标志着与整个世俗红尘的对立。走向山水成了人们寻求自由、标榜独立、寄托情志的最佳途径。宋代文人之游也如此,尽管他们走向山水的原因各有不同,但在山水中获得身心自由和精神愉悦是相同的。
一是奉命而游的洒脱。奉命而游带有明显的约束性。但是,当游者身处山水时,愉悦之情油然升腾,约束之感悄然远逝。谢绛在《游嵩山寄梅殿丞书》中一开头就写京城来的使臣“付仆诏书并御祝、封香,遣告嵩岳”。在履行庄严的圣命时,他们面带肃容,循规蹈矩,不敢多说一句话,不再多走一步路。
但是,当他们进入山水之中的时候,心境与先前大不相同:他们“升高蹑险,气豪心果”,“遇盘石、过大树,必休其上下,酌酒饮茗”,甚至“相与岸帻褫带”,“环坐满引,赋诗谈道,间以谑剧”,以至于“不知形骸之累,利欲之萌为何物”。山水之游中的自由与快乐,使他们体验到了完全异于官场和世俗的生活。
南宋赵汝驭在《罗浮山行记》中写自己“将天子命”而“有事于朱明洞天”。事毕,他攀高岩、观云气,登绝顶看日出,突然生出“若与抱朴子、桃椎子相期于缥缈”中的联想,获得了超越现实的自由感。
二是遭贬而游的超越。宋代文人中因遭贬而游山水的相当多,其中,最典型的恐怕要算苏轼。他多次遭贬,所处环境一次比一次恶劣,甚至经历生死考验,但山水之游却坚定了他随遇而安、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过白水、历沙湖、上庐山、游赤壁,苏轼留下了一篇篇脍炙人口的游记佳作。和奉命而游相比,遭贬而游者由于经历了人生的重大变故而对所观之景别有一种寄托,加之他们多从社会上层进入山水,故借景而抒发的情感更显苍凉与深邃。从流传下来的被贬文人所写的游记作品看,许多被贬文人都把仕途的失意、生活的艰辛、精神的磨难溶化在山水审美中,从而使他们的游记作品具备了旷达与高昂的基调。范仲淹面对洞庭的阴风浊浪和碧波浮光,联想到人生的进退荣辱和古代仁人的忧民忧君之心,抒发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怀抱。王禹偁连续四年展转流徙,带着疲惫的身心到黄州后,自建一座小竹楼,每当“公退之暇”就登上小竹楼,“披鹤氅衣,戴华阳巾,手执《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虑”,观赏“风帆沙鸟,烟云竹树”,“送夕阳,迎素月”,在游目骋怀中超然物外而忘世忧。事实表明,凭借山水实现精神超越是遭贬而游者的共同特点。
三是慕名而游的自得。慕名而游常因他人介绍或山景名世而产生。宋代“古文运动”的先驱柳开,居河南汤阴时因他人介绍而游天平山,果然得“山色回合,林木苍翠”,“泉声夹道,怪石奇花”之胜景,以至于“留观五日”而“不欲去”。刘弇听说白狼五山的景致“秀绝可喜”,便前往游览,当他力跻绝顶时,适逢“朝日初上”,所见之景使他心有“恍然忽从樊笼中出”之感。郑志道据古老传说而游刘阮洞,与同行者“幅巾杖藜,徜徉行歌”,如同仙游一般。南宋时期慕名而游者更多,刘泾探石门洞、叶梦得游茅山、孙觌历鄱阳、王十朋望九华、周必大观天平、吕祖谦察兰亭,等等,均属慕名而游。和遭贬而游相比,慕名而游基础上产生的游记,更充分地表现了游者自由自在的心境和悦目悦意的感受,基调多为轻松愉悦。
从上述分析看,尽管宋代文人游山水的原因不一,但置身山水的状态与感受几无差别。山水似有特殊魔力,让各种各样的人在她的怀抱中摆脱束缚、御下重负、忘情山水,让人显现本真、感受自由、体验愉悦。由此而产生的游记,也就比其它文学样式更能充分地表达身心的自由和精神的愉悦。
深邃自然:理学时代游记文学的审美特征对理学给宋代文学带来的影响,李泽厚先生作过这样的分析:宋明理学一方面把不怕艰苦而充满生意的“孔颜乐处”看作人生的最高境界,另一方面又通过禅悦之风把人引向了某种超伦理的审美契合,从而构成了“属伦理又超伦理,准审美而又超审美的目的论的精神境界”,给人带来“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审美快乐”。宋代游记文学正是如此,是当时审美与伦理、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典范,具有鲜明的“深邃而自然”的审美特征。这一审美特征具体表现在审美价值的经世致用、审美境界的深邃旷远和审美风格的平淡自然等三个方面。
1. 经世致用的审美价值
经世致用是儒家着力倡导的审美价值观,宋代游记文学主要通过情的抒写和理的阐述来表现。
宋代游记所阐述的理十分丰富。柳开的《游天平山记》,先写自己对天平山有胜景表示怀疑,“留观五日”后深为天平山的胜景所吸引而“不欲去”。从怀疑到确信再到留恋,关键是亲历、亲见,在这里,柳开所揭示的是认识之理。欧阳修在《丰乐亭记》中,纵论历史兴亡之因,并从丰乐亭所在地由乱到治的变化中,揭示了利民政策与百姓安乐、天下太平之间的辩证关系,在这里,作者阐述的是社会治乱之理。
王安石在《游褒禅山记》中以自己游览褒禅山的经历和从中体会到的“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来说明做学问必须好学深思才能有所收获,这是学问之理。苏轼游赤壁而思人生:宇宙无穷、人生有限、时事艰险,人该如何生存? 苏轼以主客问答的方式,表达了超越现实、顺从自然的人生态度,这是人生之理。曾巩的《趵突泉记》,考察了济南趵突泉的源与流的关系,具有名胜成因的考证性质,体现着科学之理。
抒发怀抱是宋代游记文学的主流。欧阳修在《醉翁亭记》中以摇曳多姿之笔,描写了山水之美、游人之乐、太守之喜,蕴含着“与民同乐”的政治情怀。文天祥浑身充满凛然之气,在《文山观大水记》中以“君子无入而不自得”之句,表达出要在任何环境中都须坚守节操的意志。谢翱曾和文天祥一起抗敌,文天祥殉国后,他多次登上富春江的严子陵钓台,用竹如意敲着石头、唱着招魂曲,哭祭文天祥,抒发胸中蓄积的亡国之痛(见《登西台恸哭记》)。这些游记中所抒写的情怀,对正直的人起着极大的激励作用。
宋代抒发情怀的游记中有不少是表现出世思想的作品。王禹偁在《黄州新建小竹楼记》中,以出世的怡然自得反衬入世的艰难困苦。苏舜钦的《苏州洞庭山水月禅院记》,通过水月寺的兴废、僧人的恬静生活以及对“民俗真朴”、“浮屠远俗”的描述,表现了对桃花源般生活的羡慕。从表面上看,这类游记似与经世致用的审美价值观相悖,其实不然。宋代游记中的出世思想,是作者们积极入世遭到无情打击之后的表现,是政治昏暗、仕途险恶的现实迫使他们把远离现实的自由、纯朴、洁身自好作为自己的向往和追求。可见,宋代游记中的出世思想是经世致用审美观的反向形态。
综上所述,经世致用的审美价值观在宋代游记文学中有着多种表现方式:或阐述哲理,或抒发情怀,或记写民情,或考证名胜成因,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强烈的现实性和丰富的知识性,并能把人带到“此在”作人生的思考、理性的探索和精神的超越。
2. 深邃旷远的审美境界
山水自然作为与世俗社会并峙的时空形态,具有空灵淡远、曲折幽静、灵动多变、悠久深广的特点。
要创造与此特点相吻合的深邃旷远的审美境界,需要处理好时间、空间与景致之间的关系。
在时间上,宋代文人善于从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变化中,表现历史变迁和人生感受。邵博游泰山观日出,从“星斗渐稀”、“天际已明”,到“大暗中日轮涌出,正红色,腾起数十丈”,再到“日渐高渐变色”,过程并不长,但情境变化却很大。作者仔细观察、具体记述这一变化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人生体验。王质游东林山水,日见荷花“红披绿偃,摇荡葳蕤”,人在荷中“歌豪笑剧,响震溪谷”;入夜则是另一番情景:“山益高且近,森森欲下搏人”,“回曲宛转,嘹亮激越”的歌声在夜间风露中“凄然使人感而悲也。”随着时间由日入夜,情境由闹入静,人的情感也由喜入悲。不同的时间造就了不同的景致,给人带来了不同的情感体验。
时间不仅能表现情境的生动,还能表现情境的深邃。对人来说,时间就是生命。在无限绵延的时间之流里,生命有限的个体该如何生存? 当人的这种意识伴随山水之景进入游记创作时,审美境界便向纵深推进。苏轼在《忆王子立》中,写自己任徐州知州时,曾与王子立共饮杏花下,可两年之后,苏辙被贬黄州,只有“对月独饮”,而王子立则由当年的少年变为“古人”,这岂不是人生的无常与悲哀吗? 在前后“赤壁赋”中,苏轼对变与不变、短暂与永恒等涉及人生出路的问题作了更深的思索,给人带来哲理的深邃感。时间不仅是人生的神秘伴侣,也是构成历史的基本元素。当名山大川有了文人的诗文墨宝、皇帝的祭坛御碑、僧人的庙宇禅房等人文景观后,历史也就在这里凸显了出来。邵博游长安,面对当年富丽豪华、而今沦为废墟的阿房宫、未央宫、大明宫遗迹大发感慨,认为秦、汉、唐不懂“仁义之尊,道德之贵”,只靠“阻固雄豪”来统治,结果这些“阻固雄豪”反倒成了可羞之物。这样的游记就给人带来了历史的深邃感。另一类表现方外之人清闲恬淡、不问世俗状态的游记,如苏舜钦的《苏州洞庭山水月禅院记》、晁补之的《新城游山记》等,以及把山水美景与神话传说串联起来表现羡仙的游记,如郑志道的《刘阮洞记》、曾原一的《游金精山记》等,从思想文化史看,它们所体现的是人类意识的深邃感。深邃感是人们深刻反思、精神震颤的结果,能让人悦神悦志。通过空间的拓展来营造审美境界,也为宋代游记所注重。事实上,人们游览山水时首先获得的是空间方面的美感,因为山川溪壑、林野烟霞、禅院道观、楼阁亭台、石刻碑文等,都以物化形态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占据一定空间。空间美既可表现为幽深,也可表现为旷远;既能显出优美,也能表现壮美。宋代游记虽以表现优美为主,但也不乏壮美。周密笔下的浙江之潮,“玉城雪岭际天而来,大声如雷霆,震撼激射,吞天沃日,势极雄豪”。孙觌游鄱阳龙停溪,山是“环拥林立。层峦叠嶂、烟云相连”;水则“旁有涌泉,坌溢四出。高有悬溜,潨泻而下。奔云溅雪,雷辊雹散,跳波急洑,千态万状”。这样的景就是一种壮美,当它在柔美的基调中奏响时,人们往往陶醉其中。
如果说游名山是空间的纵向跃升,那么观风俗就是空间的横向拓展。宋代游记中一些着重表现不同地方风俗民情的作品,虽然数量不多,但在游记文学史上却是一个突破。在《各地岁时习俗》中,庄绰就为读者描绘了一幅幅生趣盎然的民俗画,这里有宁州腊月八日的“竞作白粥”之风,澧州除夕夜通宵达旦燃放爆竹的习俗,湖北五月十五日“大端午”的泛舟竞渡;也有襄阳正月二十一日的“穿天节”求子的风俗:“妇女于滩中求小白石有孔可穿者,以色丝贯悬插于首,以为得子之祥”;还有成都从元宵节到四月十八日之间士民们竞相游览赏玩活动等等。在这些游记中,人们看到了中华大地丰富多彩、悠久深远的民族风情。
从上述分析中可知,宋代游记对深邃旷远之境的创造,主要是从时间和空间及其景致变化的角度进行的。登高而能搏见,长游而见地广,考古迹而思年久,这都显示了旷远的特征;无论是从天地之大中张扬主体精神的伟大,还是从朝代变迁中探求精神的永恒,都指向人的内心,从中显现出思想的深邃。
3. 平淡自然的审美风格
和谢灵运的山水诗所呈现的华丽的自然、李白所追求的清新的自然不同,宋人所追求的是平淡的自然。平淡自然的审美风格,其内核是“真”、“顺”。“真”指情真,唯有情真才能感人;也指理真,只有理真才能服人。“顺”既指语句,顺从流畅,不浮华夸饰,不辞涩言苦;也指结构,条达疏畅,自然浑成。在这方面,游记确有独特优势。远离尘世的山水为游者坦露心曲、表达真情创造了条件,而步移景换、时过境迁、情因景变而异、理随景变而发等的表达方式,则奠定了结构顺达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宋代文人钟情于“水”与“夜”的描写,对游记平淡自然风格的表现起着重要作用。
水的意象在宋代游记作品中十分普遍而突出,作者写得也很生动:泉水,“水声潺潺”、“泻出于两峰之间”(欧阳修《醉翁亭记》);潭水,“淫霖瀑注而不盈,大旱焦山而不涸”(郑志道《刘阮洞记》);瀑流,“初若大练,触岸石,喷薄如急雪飞下”(程端明《游金华三洞记》)。其它像湖水、江水、洪水、潮水等,在宋代游记中都无不尽显其姿。宋代游记借助水的描写创造了一个与世俗红尘相对的宁静、自由的生活世界。无论是“泻于两峰之间”的“酿泉”(欧阳修《醉翁亭记》)、“激泉成沸”的“松下石泓”(蔡襄《记径山之游》),抑或是“自高淙下”的山中小涧(朱熹《百丈山记》),其品质之清纯、形态之灵动,简直是自由之神的再现。还有被称为“天籁”的“溅溅”、“潺潺”,“铿然而鸣”、“锵鸣如琴筑”的流水声,使山林之境显得格外空灵幽静。在这样的境界中,自我融入山林,万物被我摄入,水声引发了心声,人的生命默默地吐露光辉,并孕育了平淡自然的审美风格。
宋代文人夜游山水的不少,具体情形可分两种:一是夜以继日式。这与游程长、游兴浓相关。欧阳修游龙门、晁补之历北山、王质步林东,吴龙翰登黄山等等,均属此类。二是入夜始游式,秦观的《龙井题名记》、叶梦得的《夜游西湖纪事》就属此类。在宋代文人中,苏轼的夜游最多,《承天寺夜游》、《石钟山记》、《儋耳夜书》、《记游松江》、《记过合浦》,以及名垂千古的前后“赤壁赋”等,所记的均为夜游。夜游为人感悟人生创造了条件。身披如银的月光,仰观灿烂的星空,由宇宙的广邈想到个人的渺小和人生的如梦,并在淡月疏星中,抒发深怀幽怨,使自己在与天地相融中超越现实的纷扰,让精神与山水共存。
夜游中能诱发游者反观自身,具有更深的审美意义。
从写自然之景到抒真挚之情,从状景物之态到刻情感之微,从营宁静之境到传心灵之神,从描山水之变到探人生之理,柔美的质材、深幽的情怀、淡泊的心境、反观的沉郁,无不表现出平淡自然的审美风格。平淡自然是宋代游记最具时代特色的审美风格。
宋代游记创作致力于时代精神与“游”的精神的结合,在实现情理相融的过程中,形成了深邃自然的审美特征,成为宋代文学领域内独具魅力的文学奇葩。如果我们把宋代游记放在历史的框架中作一比较,又可发现它的历史性突破。
从作品内容看,宋代游记文学更注重哲理的深化和精神的升华。“游”是文人的一种生存方式和生命活动的组成部分。无论是北宋文人的遭贬而游,南宋文人的慕名而游,其记都集中而深刻地表现了他们的人生经历与感悟。从表现方式看,宋代游记文学的叙述形态已臻完善。这主要表现在宋代文人对行踪转移、景物变换、情感抒发、哲理阐述等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了高妙的艺术处理,从而大大丰富了作品的审美意蕴。从体式看,游记文学发展到宋代,各种样式的游记纷呈叠出,已趋完备。其中,日记式游记如陆游的《入蜀记》、范成大的《吴船录》等,首次出现在宋代文坛上;小品型游记也于宋代趋向成熟。这样,宋代游记文学就组成了小品与长卷同存,题记、日记与笔记共处,书信型、杂感型、文赋型与记游型游记会集的大家族。总之,宋代游记文学标志着我国游记创作已经走向成熟,是我国游记文学史上的一座高峰。
参考文献:
[1]冯天瑜等. 中华文化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2]陈廷焯. 白雨斋词话[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3]梅新林、崔小敬. 由“游”而“记”的审美熔铸 ——— 中国游记文学发生论[J]. 学术月刊,2006(10) .
[4]李泽厚.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