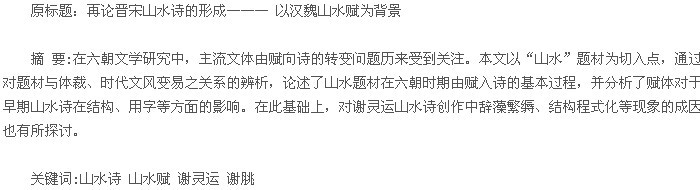
历来讨论山水诗的形成,必然会提及此前的山水赋①,譬如王国璎教授在《中国山水诗研究》中指出:“由于汉赋中表现的作者对自然界山水景物的体认,与后世山水诗人登临山水以求心神自由和美感经验的情绪遥想呼应,他们对山水景物的刻意描写,为后世山水诗人模山范水的艺术技巧奠定了基础,因此汉赋虽然不是纯粹的诗,却是探索山水诗的渊源时必须涉及的重要领域”,不少学者也从山水诗的玄言背景、特殊的审美观照等方面充分说明了山水诗不同于山水赋的独特魅力,对此,笔者不拟赘述。本文试图展开的,是从五言诗与赋这两种不同的文体出发,通过比较两种文体不同的结构、修辞、节奏特点,讨论晋宋之际澄明观照的山水审美方式如何借助五言诗这一体裁进行创作,此前已经存在的山水赋何以不能满足玄学家和名士们的创作需求? 在山水诗发展的过程中,原有的山水赋是否对其产生影响,而山水诗又如何建立起自己的文体特点,从而确立起其山水题材大宗的地位?
一
在展开关于诗赋文体特点的辨析之前,我想首先应该辨清:山水诗的产生会否只是五言诗内部的一次题材扩展? 也就是说,究竟是否存在本文试图讨论的关于山水的描写从赋体转向诗体这一过程? 这是本文论题得以成立的基础。
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讨论这个问题。第一,在山水诗产生的年代,五言诗是否已经具有了文坛主流的地位? 也就是说,如果在晋宋之际,五言诗已经超越赋体成为一种最普遍的文体,那么作为新出现的题材,当然倾向于选择这种主流文体进行创作,而本文试图论证的诗赋文体转换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我们不妨选择两晋的一些作家,比较他们的诗赋存目:潘岳存赋 19 篇,诗 15 首;陆机存赋 30 篇,诗 48 首;郭璞存赋 10 篇,诗 7 首;王羲之无赋,诗 2 首;孙绰赋 3 篇,诗 5 首;何承天赋 1 篇,无诗;傅亮赋 6 篇,诗4 首。这是《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在谢灵运之前的一些作家的诗赋作品资料,可以说,除了陶渊明,晋宋之际士人的创作往往是诗赋兼重,尚未出现南朝以后士人诗作数量往往远胜赋作的现象。
第二,在山水诗正式形成之前,是否存在一个山水赋的线索? 如果此前并无这条线索,那么关于山水题材由赋体转向诗体的假设同样不具备成立的基础。我们仍然借助《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的存目来看,王粲有《游海赋》、《浮淮赋》、《初征赋》、刘桢有《黎阳山赋》、潘岳有《沧海赋》、《登虎牢山赋》、成公绥有《大河赋》、张载有《蒙汜池赋》、郭璞有《江赋》、《巫咸山赋》、《登百尺楼赋》、《盐池赋》,孙绰有《天台山赋》、《望海赋》等等。显然,在山水诗尚未形成之前,有大量的士人利用赋体记述山川之美,这条山水赋的线索,应该是比较明朗的了。
第三,在晋宋之际,是否存在着山水赋向山水诗的转换? 也就是说,会否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山水赋继续在赋这一体裁内发展,而山水诗另辟蹊径,独立地发展起来? 这是本文论点能否成立的核心要素。
我想可以用这样一种方法来进行确认:山水题材作品的创作背景大抵有两种,一是行旅,二是游览。我们不妨就以这两者为线索,比较山水诗产生前后,士人在游览或者行旅之后,主要利用哪种体裁进行创作。我们重点关注的是,在山水诗产生之前,赋体是否在游览、行旅题材中占据主体,而在山水诗产生之后,诗体是否取而代之。翻阅《百三名家集》,我们会发现这一对比颇为明显。汉末魏晋以来,纪行成为赋体中的一个重要题材,曹植、王粲、阮瑀、潘岳、陆机、郭璞等都有大量的纪行赋记述他们游览、行旅之事,而除了陆机,其他人的诗歌中却很少描写行旅,对于魏晋的诗人而言,他们的绝大部分五言诗是用来赠别酬唱的。但自陶渊明、谢灵运而下,这种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陶谢、鲍照、谢希逸、谢脁、沈约、何逊等都是大量用诗歌记述自己的游览和行旅,而谢灵运尚有四首纪行赋描写山水,灵运以下诸家山水赋作就至多只在一两篇了。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论证,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认识:汉魏以来,山水题材在文学作品中逐渐成长起来,并逐渐具有独立的文学价值。这一价值早期主要在赋作中体现出来,但是随着其文学意义的不断深化,艺术水准的不断提高,山水诗逐渐超越山水赋,获得了士人更多的关注,成为山水题材的大宗。
那么,这一过程是如何实现的呢?
二
我们首先看汉魏山水赋的发展情况。
山水作为文学题材,早在先秦就见于诗赋之中,但学者已经指出,早期诗赋中的山水只是作为一种文学意象出现,尚未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而且,早期的文学作品中也极少对于山水的正面、细致描写。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较早集中对于山水进行正面描绘的,是枚乘的《七发》中自“恍兮忽兮,聊兮栗兮”而下对于八月水景的那段长篇描写,细读其文,我们可以总结出《七发》描写水景的几种主要艺术手法:
其一,是大量运用双声叠韵词。《诗经》和楚辞中已经大量运用双声叠韵词,因为诗骚可用于歌、诵,而双声叠韵词的语音美正可以通过歌、诵充分体现出来。汉大赋同样可用以诵读,且其形成与楚辞渊源有自,也就很自然地继承了这一艺术手法。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艺术手法在描写水景,尤其是江海水景时取得了特别的艺术效果。因为《七发》写水本就是为了突出其浩瀚雄壮之美,意在以创造一种宏阔广大的效果而震醒太子,而大量开口呼的双声叠韵词,正是造成了一种听觉上的冲击感。因此诸如“颙颙卬卬,椐椐强强,莘莘将将”这样的词句,虽然很难获得知觉上的具体感受,却具有听觉上直接的冲击力。这种手法遂成为赋体描写山水的一种经典手法在以后的山水赋创作中长期沿用。
其二,是运用大量的比喻。以描写海水涨潮的部分为例,从“其始起也”,以白鹭喻之;到“其少进也”,以素车白马喻之;既而“波涌而云乱”,以三军奔腾喻之,其“旁作而奔起”,以轻车勒兵喻之,接着,勇壮之卒、雷行、奔马、雷鼓,种种喻象,层出不穷,整个一段文字,便是以排比式的比喻和穿插的双声叠韵词支撑起来的。其三,便是描写上的全方位性。从海水的声响、广域、方位、涨落、力量,乃至人的听觉、视觉、联想,凡是作者可以想及的,都不遗余力地铺陈开来。《七发》本不是专门写山川的赋,却用了相当长的篇幅来展开描写,足见其方位、角度之全。
《七发》之所以具有这些艺术特色,当然与其选材、题旨有密切联系,但是,这些手法之所以能够在文中起到良好的艺术效果,也与它们契合了大赋这一文体本身的艺术功能有关:汉大赋是文士向君主展现才华的一种主要文体,因此它必然立足于宫廷文学的审美取向,追求字句的修饰美、取境的崇高美和结构的宏大富丽之美,可以说,这些艺术追求对于赋体尚“丽”特点的产生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当赋作为一种文体确立、固化之后,即使时代变异,人们的审美追求发生了变化,文体的功能、接受对象也发生了变化,但是这种文体所特有的艺术手法仍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留下来,成为这一文体的基本特征。一种文体艺术手法的演变往往要远远滞后于其美学追求的演变,这不仅在赋,而且在其后齐梁诗向盛唐诗、南唐后蜀词向北宋文人词的转变中都有所体现。因此不难理解,随着《七发》作为汉赋的经典体式获得认可,《七发》的这种山水描写手法也就与山水息息相连,成为赋体写山水的一种基本样式了。即便到谢灵运的《山居赋》,其创作旨趣、艺术追求、审美情趣已经与汉人大相径庭,但是他的基本手法,仍不外乎上述三种。
当然,基本手法的确立,并不意味着艺术探索到此为止。到了西汉中后期,辨丽可喜的小赋开始受到文人士大夫的喜爱,而行旅之余创作纪行文字,记录沿途山川美景,同时抒发心志郁结,则成为东汉一种重要的私人创作行为。由于公共层面与私人层面的赋作在不少方面都表现出差异,因此为了全面了解东汉山水赋,我们分别选择一篇宫廷赋作和私人纪行赋进行分析。
第一篇是班固的《终南山赋》。此赋留存不全,只有一段对于终南山的正面描写见于《初学记》:伊彼终南,岿嶻嶙囷。概青宫,触紫辰。嶔崟郁律,萃于霞氛,暧日对晻蔼,若鬼若神。傍吐飞濑,上挺修林,玄泉落落,密荫沉沉。荣期绮季,此焉恬心。三春之季,孟夏之初,天气肃清,周览八隅。皇鸾鸑鷟,警乃前駈。尔其珍怪,碧玉挺其阿,密房溜其巅。翔凤哀鸣集其上,清水泌流注其前。彭祖宅以蝉蜕,安期飨以延年。唯至德之为美,我皇应福以来臻。埽神坛以告诚,荐珍馨以祈仙。嗟兹介福,永钟亿年。
从“我皇应福以来臻”、“埽神坛以告诫”这些文字来看,这是一篇为祭祀终南山而作的赋。与《七发》相比,此段仍主要使用双声叠韵词、比喻以及全方位描写等手法,但又有新意。首先是描写性文字中四言体成为基本句式。联系东汉的其他一些纪行赋中的写景文字,我们发现这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可以说,随着整个东汉文风的骈偶化,四言和六言已逐渐成为赋体写景的基本句式,这与《七发》中的那种奇偶搭配的形式已经相当不同了。就四言来看,我们通过这段文字发现它大抵有三种基本结构:第一种是并列结构。也就是两个或四个并列的形容词,比如“嵚崟郁律”、“暧日对晻蔼”,这些形容词词义相近,往往还有相同的义符,显然是力图通过反复达成对于山川风景之或峻险、或宏阔、或幽涩、或明朗的特点的强化;另一方面,这些形容词又多用难字,彼此之间的意义区分,若非专门的文字学家,很难说清,若将其与《七发》中那些同样语义难解的双声叠韵词相比,后者似乎更强调语音美,而东汉赋中的文字则更看重形象美,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字的字形本身就显示出作者意图描绘的山水之美,比如“嶔崟郁律”四字,读者见之便觉高山峻阸之气。虽然它们往往还是双声叠韵词,但是从西汉的听觉美到东汉视觉美的转变,成为赋作写景笔法的一个重要革新,并延续到两晋。后来木华、郭璞的《海赋》、《江赋》,虽同是写水,但是他们的用字却更近似班固而非枚乘。
四言赋体的第二种结构是主谓结构,主语部分的第一个字和谓语一般都是由形容词来充当。比如“玄泉落落,密荫沉沉”。这种结构在写景文字中使用的频率极高,与上面的第一种句式相比,因为它有名词作为中心语,可以说是言之有物,因此又常常充当主题句,领起类似上述第一种全为形容词的句式,可以说,这是四言写景句式中的一种基本句型。
第三种结构,就是如“傍吐飞濑,上挺修竹”的述宾结构。其述语部分一般是方位词配上一个动词,而宾语则是一个形容词作定语、名词作中心语的小偏正短语。这种结构在交待山川方位的时候经常使用。
四言体除了本段出现的这三种结构,还有一种结构在赋体写景文字中经常出现,就是如“茂竹修林”者,由两个形容词配名词的偏正结构组成的并列短语。不过,总体而言,这些句式具有两个相同的特点,第一,他们从音节上说都是二二结构,与四言的语气节奏相吻合,因此不会造成语意停顿和节奏停顿的错位,应该说是一种比较成熟、稳定的句式。第二,在所有这些句式中,形容词具有一种特殊的重要地位。它们或许并不能准确、细腻地刻画山水的特征与变化,但是他们直接、反复、排比的表达方式,却正适应汉赋的文体要求,也满足了汉人尚丽、尚宏大的审美需要。
第二篇是蔡邕的《述行赋》。此赋乃是蔡邕因病归乡途中所作,篇中有一段写山景:登长阪以凌高兮,陟葱山之嶤崤。建抚体而立洪高兮,经万世而不倾。回峭峻以降阻兮,小阜寥其异形。冈岑纡以连属兮,溪壑琼其杳冥。迫嵯峨以乖邪兮,廓岩壑以崝嵘。攒棫朴而杂榛楛兮,被浣濯而罗布。亹菼奥与台莔兮,缘增崖而结茎。行游目以南望兮,览太室之威灵。
顾大河于北垠兮,瞰洛汭之始并。
与上段不同,这一段是骚体赋,因此句式结构自然不同,但是,除此之外,两者还是具有很多共同点。奇字、难字比《终南山赋》有过之而无不及,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不必通过对于文字的细细品味来获得对于山景的感悟,其崎岖险峻触目可及、一览便知。这种粗犷、宏观、直观的鉴赏方式,正是汉人特色。
可以说,从《七发》到《述行赋》,两汉赋作中的山水风物描写与汉人的审美情趣是完全契合的,他们喜欢宏大崇高之物,因此他们看到的是洪波浩渺、高山万仞;他们触物生情,自然兴会,因此山的峻峭也就给他们人生实难、道路不平之感,而山的物产丰富、树木荫翠则让他们欣欣于帝国强盛、天下康安。这种从大处着眼、从整体着眼的审美情趣与赋体重篇章、重句式排比的体式正相匹配,而他们直观明了的审美方式与赋体好用奇字的习惯也恰相吻合。汉人不但充分地运用赋体来模山范水,而且,他们的心情、理想、感叹、思索,也都通过这些赋作充分地表现出来,赋成为汉人描摹山水、抒写情志的主要题材。
随着汉末儒家思想在士大夫群体中出现的松动,思想界开始出现各种其它的思想潮流,而随着汉人古典式审美情趣的式微,魏晋以来的士人在选择以赋体描摹山水的时候,在艺术手法上不免发生新变。
玄学名士孙绰的《游天台山赋》可以作为我们分析的材料。且看《游天台山赋》中的一段:赤城霞起而建标,瀑布飞流以界道。睹灵验而遂徂,忽乎吾之将行。仍羽人于丹丘,寻不死之福庭。苟台岭之可攀,亦何羡于层城。释域中之常恋,畅超然之高情。被毛褐之森森,振金策之铃铃。披荒榛之蒙茏,陟峭崿之峥嵘。济楢溪而直进,落五界而迅征。跨穹隆之悬磴,临万丈之绝冥。践莓苔之滑石,抟壁立之翠屏。揽樛木之长萝,援葛藟之飞茎。虽一冒于垂堂,乃永存乎长生。必契诚于幽昧,履重险而逾平。既克隮于九折,路威夷而修通。恣心目之寥朗,任缓步之从容。藉萋萋之纤草,荫落落之长松。觌翔鸾之裔裔,听鸣凤之嗈嗈。过灵溪而一濯,疏烦想于心胸。
这段赋节奏整齐,对仗精准,是比较典型的魏晋赋作,其写天台山而及于游仙论玄,也是东晋诗赋的主流题材。从这篇赋来看,我们发现其中真正描写山景的文字非常少,大量穿插着游仙的叙述和玄理的阐发,只有一些零星的句子正面写山景。我们再将这些零星的句子抽出来,比如“赤城霞起而建标,瀑布飞流以界道”、“披荒榛之蒙茏,陟峭崿之峥嵘”、“践莓苔之滑石,抟壁立之翠屏。揽樛木之长罗,援葛藟之飞茎”、“藉萋萋之纤草,荫落落之长松。觌翔鸾之裔裔,听鸣凤之嗈嗈”,会发现他们在艺术手法上与汉赋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双声叠韵的形容词仍然是造成这些诗句修辞效果的主要手段,奇字难字确实是少了很多,但是代之的并不是能够准确描摹山水特色的文学字词,而是一些流易平常之字。读起来虽是便利了不少,修辞效果却也丢失了大半。简单地说,六朝赋固然在句式、音节、思想等方面与汉赋相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就其描写手法这一点而言,却没有能够实现新的突破———汉赋既定的文体特征限制了魏晋士人的艺术创作,他们的情感并没有能够通过艺术描写有效地传达出来,只能够转而借助议论或者叙述的方式来直接交待玄理———在山水文字中,我们看不到玄学家新的审美观照。其实我们知道,孙绰的《兰亭诗》和《秋日》两首诗歌已经颇具山水诗的风味,比如其中“疏林积凉风,虚岫结凝宵。湛露洒庭林,密叶辞荣条”这两句,置于齐梁人诗集中也几可乱真。为什么同样是孙绰,在诗中就可以写出如此清新澄澈的佳句,而到了赋里却只能写出那些带着汉人气息的陈词滥调呢? 这是特别需要解释的一个问题。
笔者以为,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进行解释。首先,我们细读孙绰这四句诗,会发现他们与赋句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的主干结构。上文已述,汉赋的经典句式是四言或者六言,四言的几种句式上文已经列举,而六言与四言相比其实句式更为单一,因为六言为了达到节奏的协调,往往第四个字为虚字,可以说,正是这个虚字限制了六言的灵活性,因为它既然必须处在第四个字的位置上,那么整个句子的节奏就只能是“× / × × /○/ × × ”或者“× × / × /○/ × × ”两种。第一种句式往往首字是动词,后面两个双音节奏则分别用名词或形容词,或者首字用名词,后面用两个形容词。第二种句式往往开头双音节是名词,第三个字和最后的双音节是动词或形容词。然而无论是哪种句式都有一个问题:每个单句一般只能有一个主题名词,这就造成了每个单句只能描写一个景致,而需要通过上下两句的搭配才能完成景物高下、明暗、深浅、大小等等不同特点的对比,孙绰的这篇赋也正是这么写的。但是因为分为上下两句,虽然可以造成对比,却也同时使两个事物之间的关系淡化了,“藉萋萋之纤草,荫落落之长松”比起“纤草荫长松”来,味道不免差了一些,因为对比的意味被拉长的句式冲淡了。而偏偏魏晋士人最喜在这种远近、高下、明暗、疏密的对比中描摹风景特征与细微变化,这样一来,赋体就在新的审美需求面前显得无能为力了。
其次,我们再看孙绰这两句诗,“疏林”、“凉风”,“虚岫”、“凝宵”这四个意象并不存在严格的方位关系,完全是诗人兴之所至,触目而及,特别是“虚岫结凝宵”这一句,用一个“结”字,将两种相近相融却又着实不同的景致粘合起来,达到一种虚实有致的艺术效果。但是在赋中,这种艺术效果便很难达到。
因为赋是一种十分强调上下文之间逻辑关联的文体,如果是写山水,大多是移步换景,一句一景,每个景是独立的,同时又处于上下句的方位限定之中,我们看前面所引的《述行赋》就可以得到验证。因此,赋家既不能在上下句之间随意拉扯意象,更不可能将两种不同的意象粘合起来。对汉人而言,他们的景物描写往往是罗列式、排比式的,因此不存在意象的安排问题,但是到了魏晋,随着山水独立审美意识的形成,人们对于山水之美的认识也开始细化,好像山水画中要讲究布局一样,人们赏鉴山水,也开始讲究布局选择,而不是仅仅按照自然界的原始方位。这一审美需求,赋似乎也很难满足。
复次,前文所说,汉赋好写宏阔富丽的景物,因此作者好用奇字,因为奇字可以直观地造成险峻、浩渺、巍峨、壮阔的艺术效果。但是魏晋士人受玄学思潮影响,他们的审美情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南渡之后,他们的审美情趣更倾向于细丽清远,沈约、谢朓等诗人都明确追求“清丽”的诗风,奇字与僻典越来越受到文人的冷落。由于汉赋大量运用排比的修辞手法,往往一种句式一连十数句,当句中有不少奇难字的时候,读者受到奇难字的阻碍,可以延长这些句子的阅读时间,对不少词句可以有比较深刻、特别的体味,产生看山起伏之感。但到了魏晋赋中,由于不用奇字,句式又单调连续,极容易使赋作失于流易平乏,影响审美体验。
总结上面这些分析,我们就可以对于晋宋之际、随着玄学改变了士人的审美方式和审美情趣之后,以赋体写山水所面临的困厄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赋本是一种崇尚铺陈的文体,可以说,赋体艺术效果的达成,并不依赖于个别字句的精巧,而是依赖于篇章结构的完整协调、段落上下文的连贯顺畅、句子上下以及内部的对称粘合。此外,赋又是一种尚“丽”的文体,这种“丽”表现在语音、文字和语意等各个方面,就是双声叠韵词、奇字和形容词的大量使用。但是,这三个方面在充分发掘了语言“美”的一方面的同时,却难以同时完成语言的另一个要求:“表意性”,而这正是南朝士人所不能接受的。汉人追求崇高美,因此他们可以忽略局部细处,站在高山之巅,观大川之浩渺,而南朝士人的胸襟自无汉人般博大,目力所及,也就自然没有那么辽远开阔,他们更属意于那些具有画面感、可以细细体味的风物,尤其对于季候、雨水、光照等因素带来的山水景物的细微变化充满兴趣,他们在细细的赏鉴中品味到了山水的灵秀、敏感、脆弱、柔情,而这些正是他们自身人格性情的投射。在这种审美需求下,赋体的艺术手法对于南朝士人来说自然是难以满足了———他们希望即兴式的、点化式的、疏密有致的、私人化、微观化的文学样式,需要清晰而具有情致的、能够细腻地表现山水风景之光、色变化的文学语言,在这种种需求不断涌现的时候,也就是山水从赋走向诗歌的时候了。
三
东晋中后期,已经出现了一些山水诗歌作家,其杰出代表则是庾阐和湛方生。然而阅读他们的作品,会发现他们诗风清雅洒落,重情思、写意而不重藻饰、炼字,很明显地带有汉魏“古诗”的特点,与后来蔚为大观的南朝山水诗表现出较远的距离。因此,笔者认为,庾阐、湛方生虽然开山水诗之先声,却并不对南朝以后的山水诗创作产生实际的影响,也就是说,庾阐和湛方生虽然独立地描写山水,但是山水题材在他们的笔下却是从属于玄言诗的,在他们的笔下,山水诗并没有因为其题材的不同而显示出创作意图、诗歌结构、修辞艺术等方面的新变。因此,它们很难被置入系统的山水诗歌史中去考察,只能说是山水诗的灵光初现。有意思的是,由于山水诗是经历了大谢体的繁缛再往小谢体的清新回归,是经历了一个过度修辞的弧圈才螺旋式地登上了新的诗歌艺术层次,而庾阐、湛方生却是直接在汉魏古诗的基础上来作山水诗,因此,从抒情方式、思想寄托等很多方面来看,他们的作品甚至比大谢的山水诗更接近南朝后期的典型山水诗,山水诗在庾阐、湛方生的笔下似乎早熟了,然而如果关注诗歌的结构、炼字的用心,就会发现他们的山水诗仍然属于古诗的时代,与刘宋以来整个文坛的新变无涉。
而无论如何,谢灵运作为最早大量写作山水诗的诗人,他何以能够首创新变,另辟蹊径呢? 山水题材由来以久,但谢灵运之前毕竟没有人如此大量写作山水诗,除了才力大小之外,恐怕还有一些具体的因素,使得谢氏能够比较迅速地掌握五言诗体写山水的方法,并创作出一批优秀的作品来。这里我们就来探讨其中的原因。
笔者以为,谢灵运之所以能够完成从山水赋到山水诗的转变,关键的一个原因,是他的审美情趣与东晋以来的多数士人并完全不一样,他性格当中倔强、自傲的一面使得他对于山水特好奇险。而这种爱好恰与汉人具有某种相似,正是这种相似使得他能够比较顺畅地完成从山水赋到山水诗的转化。
东晋以来的士人受玄风影响,赏鉴山水,好其清远,这一点从孙绰的《天台山赋》便可以感知,而谢灵运则不同,他于山水好其险峻,有《山居赋》为证:爰初经略,杖策孤征。入涧水涉,登岭山行。陵顶不息,穷泉不停。栉风沐雨,犯露乘星。
研其浅思,罄其短规。非龟非筮,择良选奇。剪榛开径,寻石觅崖。四山周回,双流逶迤。面南岭,建经台;倚北阜,筑讲堂。傍危峰,立禅室;临浚流,列僧房。对百年之高木,纳万代之芬芳。
抱终古之泉源,美膏液之清长。谢丽塔于郊郭,殊世间于城傍。欣见素以抱朴,果甘露于道场。
谢灵运穷山涉水,就是为了找到一处奇险的道场,其好险好奇的个性可见一斑。因为他好奇险,因此他的赋作中就大量出现对于山势之峻险的描写,而这些描写与整个作品的情绪也是一致的,比如上文所举的《山居赋》。在这一点上,谢灵运似乎非常适合以赋作来写山水,这可能也是他的山水赋在整个东晋南朝数量最多的原因之一。但是,谢灵运毕竟已是魏晋之人,虽然他也好奇险,但是他的心境与汉人却不同。汉人以一种乐观的、开阔的心境来看待那些峻峭的山峰,在汉人的审美世界里,那代表着旺盛的生命力,即使是东汉晚期蔡邕的《述行赋》,也彰显着作者坚韧的气质与卓拔的生命力。然而谢灵运之好奇险,却是贯注了很多生命的执拗,因此一个极关键的区别就是,汉人的奇险只是奇险,而谢灵运却在奇险之外增加了强烈的孤独感。在汉赋中,那奇绝的山峰是一个充满生命力量的活的世界,而在谢灵运的作品中,那些险峭的山谷只是他孤独自守的道场,这是魏晋人特有的时代气质。因此,谢灵运虽然在好奇这一点与汉人相似,但终究不可能与汉赋尚丽的底色相适应,他在《山居赋》的小序中明确地说:扬子云云:“诗人之赋丽以则”,文体宜兼,以成其美。今所赋既非京都宫观游猎声色之盛,而叙山野草木水石谷稼之事,才乏昔人,心放俗外,咏于文则可勉而就之,求丽,邈以远矣。
览者废张、左之艳辞,寻台、皓之深意,去饰取素,傥值其心耳。
可见,谢灵运已经自觉地意识到其辞赋创作与赋这一文体的自身艺术传统之间的矛盾,而从东汉末以来,五言诗已经得到充分的发展,士人赠答言志,往往选择五言诗。谢灵运变山水赋而为山水诗,或许开始只是出于偶然,但确实也是顺应了文学发展的潮流。魏晋人对于山水的赏鉴在山水赋中既已进退失据,一旦转而用五言诗来写,对于当时人来讲,当有豁然开朗之感。
由赋入诗,固然是另创新路,但是对于初创者而言,筚路蓝缕,自也有许多艰辛。首先,诗与赋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体,在结构、句式、语言风格、接受方式等方面都有很多差异。而且每一种专门题材的诗歌又有其专门的特点,比如咏史诗、赠答诗、言志诗,就各有其体制。如何开头,如何收尾,如何结构句子,都是谢灵运面临的问题,既然此前没有别的山水诗可以借鉴,而山水诗又是由山水赋而来,谢灵运似乎也只有先借鉴山水赋来结构山水诗这一条途径了。我们如果把谢灵运的山水诗拿来与那些赋作中的山水描写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两者之间存在大量的共同点。而有意思的是,其实我们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些共同点,只是在没有理清山水诗与山水赋之间的承接关系时,常常将其视作谢灵运诗歌的缺陷,现在,我们把握山水诗与山水赋之间的关系,再来重新审视这些“缺陷”,就会对它们产生的原因有更深刻的了解。
我们一般将谢灵运诗歌的缺陷归结为以下四点:第一,结构程式化。第二,用字奇难,辞藻堆砌。第三,情景分裂。第四,有句无篇。以下逐一辨析:。。
首先,前文已言,汉赋是一种非常注重篇章结构的文体,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开头叙述事由,中间大段具体描绘,末尾小段从思想上进行总结升华,所谓“劝百而讽一”。作为一种具有强烈官方色彩的文体,这种结构可以把颂赞和讽谏、文采和议政有效结合起来,自有其合理性。可以说,随着司马相如、扬雄对这种结构的充分开拓,到了“作赋拟相如”的年代,无论是大赋还是小赋,篇幅固然有不同,结构却是基本不变的,孙绰的《游天台山赋》、《望海赋》以及谢灵运的那些赋作都遵循这一结构。而前文已经说过,晋宋之际山水题材由赋入诗,并不是因为赋在整体结构上存在缺陷,主要的问题是在具体的句式上,因此在山水诗的创作初期,谢灵运自然也就不会着力于其结构的重建,而是自然地延续山水赋的传统结构,将注意力放在诗歌句式的革新上。故此,结构程式化正可谓山水诗脱胎于山水赋的胎记,而有句无篇也恰是谢灵运新用诗体的成功和局限———他试用诗体来写山水,本就是看重诗歌更能够细致、动态地描写景色,不像赋一样每句话都淹没于大段铺陈的语流之中,因此,他写山水诗最为看重的,自然是那些妙句、妙字的锻炼,至于篇章结构,还要等后来的山水诗人来进一步发掘。
其次,关于用字奇难和辞藻堆砌,如前文所言,赋体于用字特为讲究,好用奇难字。而谢灵运本好奇险,其山水诗又从山水赋而来,在谢灵运的“词库”里,关于山水奇险的描写尽是汉赋中那些字形繁复的奇难字,如此,虽是写诗,仍常常不免要依赖汉赋以奇难字堆砌写景的方法。从谢灵运的整体诗歌看来,运用奇难字及单纯堆砌辞藻的那些句子虽然大多难称佳句,但它们的存在,正透露出大谢山水诗与山水赋的亲缘关系。
第三,关于情景分裂。这本是山水从赋转入诗歌的关键原因。汉赋的山水摹写方式本是适应汉人的审美方式而产生的,但当人们的审美方式发生变化之后,赋作为一种文体却已经成熟起来,有了自己比较稳定的文体要求。用奇字、重结构、重排比、全方位等等特点已经和赋这个文体紧密联为一体,抛开了这些特点,赋就不成其为赋。魏晋士人试图在赋体内部进行改造,使之适应新的山水审美形态的实验在孙绰的赋中已经被证明是非常困难的,孙绰固然可以在赋中穿插那些玄言道理,但到了描写山水的部分,则又不得不退回汉人的老调上去,这便是所谓的“情景割裂”。谢灵运以诗体写山水,固然是体式新变,而且他的诗歌中已经出现了很多情景相合的句子,比如“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与谢灵运孤傲的个性都非常契合,但是新变之初,主要还是以因袭为主,而且关键是诗歌结构没有变,景物描写和叙事、言志还是如《天台山赋》般割为两部分,以赋为诗,自然处处显得不能圆融。
换言之,其实谢灵运的这些问题,并不自其山水诗始,它们在孙绰以及谢灵运自己的山水赋中已经体现出来了,只不过山水赋于赋体已是强弩之末,而山水诗蔚然大家,人们关注山水诗新体超过山水赋的末流,这样也就造成了对谢灵运山水诗的批评。其实大谢为山水描写另辟蹊径,其开辟之功,自当充分肯定;而对其首创之艰,我们亦当同情会心。
谢灵运最为后世所称道的,是他的那些具有高超描摹刻画技巧的佳句,而这正是谢灵运以诗代赋所获得的巨大成功。我们细读这些名句,会发现他们大多充分发挥了五言诗的句式特点,第三个字、第五个字往往安排一些匠心独运的动词或者动词化的形容词,这些动词上下句相对,有时还与句中的修饰词相对,从而将山水风物的明暗、疏密、高下、大小、远近对比展现得错落有致,比如“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变”字启动全句,平中见奇。“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抱”与“媚”,一浑融而一明丽,“抱”又与“幽”相配,“媚”则与“清”相属,炼字之功可见其深。“近涧涓密石,远山映疏木”,远近相间,疏密相对,“涓”形容词而用为动词,借助语法上的距离感平衡语意上的密集紧凑,这种写法在后来的南朝山水诗中极为发达。
在一句之内,谢灵运锻炼修饰词和动词,在上下句之间,则构造其光线、方位、季候、时间上的对比,这些都是适应了魏晋士人不同于汉代的审美方式、情趣,因此迅速被同时代的士人所接受,并确立起山水诗的经典地位。
诗歌以名句而传播,结构的缺陷在当时而言问题并不突出,人们传诵谢灵运的这些佳句,对于以五言诗写山水也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于是,在谢灵运之后,山水诗歌便迅速地发展起来。
通过上面的梳理,我们对于山水题材如何一步步从赋体转入诗体的过程有了一定了解。其实这一转变,到了谢灵运这里并没有彻底完成,前文已言,谢灵运除了在炼字、句式上发挥了五言诗体的特点之外,在结构、用字等很多方面还都残留着赋体的方式,他也因此受到后人的诟病。从体裁转换的角度而言,真正确立山水诗独立地位,完成山水诗在结构、用字、句式等方面独立体式的确定的,是被称为“小谢”的谢脁。首先他抛弃了赋的结构模式,确立了山水诗真正的“诗”的结构。情绪表达与景物描写有机地结合起来,开篇的方式也不再局限于叙述事由一种。其次,他充分发挥五言诗的体裁优势,注重炼字,使得景物描绘愈加显得清新到位,不再像汉赋般宏阔模糊。再有,他的诗歌用字简易,与当时的时代风气相契合,更与五言诗的体裁传统相契合。谢灵运虽然在整个南朝卓然名家,但是山水诗最终却是沿着小谢体的方向发展,可以说,小谢山水诗与五言诗体裁要求之间的契合当是“小谢体”后来超越“大谢体”的一个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王国璎. 中国山水诗研究[M]. 北京:中华书局,2007.
[2]袁行霈. 中国诗歌艺术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3]费振刚、胡双宝、宗明华. 全汉赋[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4]徐坚. 初学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5]张溥. 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第三册[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