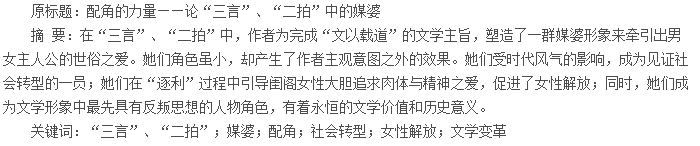
文学不仅是一种艺术现象,同时还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现象。它的出现是作家根据自身独特的世界观对社会现实的艺术创造,它不仅是自身艺术审美和感悟的结晶,还记载了孕育它的民族、时代和社会的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有着珍贵的审美价值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因此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和阐释就是对历史背景的重现和“获得生命的存在”。
“三言”、“二拍”作为明代社会的一面镜子,具有“史”的价值。明代中后期社会处于变革时期,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它的出现是对中国封建统治基础的小农经济的冲击,同时也是对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封建统治思想的严峻挑战。随着市民阶层的扩大,“存天理,灭人欲”的陈腐观念开始被人质疑,涌现了王阳明、李贽等要求解放人性的的启蒙家。而冯梦龙和凌濛初是他们思想的追随者,在为正统文学不耻的“妾小说”中大量描写了市民阶层的日常生活和男欢女爱的情感生活,这是对正统文学的一种挑战,熔铸了时代下的新风气。而在“三言”、“二拍”中媒婆作为复杂世相的一个被批判的组成部分,却起到了“小角色,大作用”的效果,给人印象深刻。在作者笔下,她们是家庭收入的创造者,也是闺阁女性连接墙院之外的桥梁,她们巧言善辩、唯利是图,却也是时代桎梏的一丝曙光,成为文学变革的先行者。
一、社会转型的见证者
韦勒克与沃伦曾说:“文学作品最直接的背景就是它语言上和文学上的传统。而这个传统又要受到总的文化‘环境’的影响。一般说来,文学与具体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状况之间的联系是远为间接的。”在“三言”、“二拍”中两位作者都在试图建构这种“背景”,反映那个时代下的经济、政治变化和个体精神的形成。而媒婆走街串巷的步伐不仅踏出了历史的轨迹,同时其匆忙有力的步伐声也影响着社会的现在和未来。
中国有着悠久的媒妁文化,尤其在中国封建宗法制度的背景下,她们成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制度下左右婚姻的重要力量。在封建男权制度中,女性没有经济地位,被束缚于闺阁之中,而媒人的产生就是为了更好地维护男权对女性的掌控,它是父权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她们被统治者赋予正当的、合乎伦理道德的社会身份,受到统治者的保护。“处女无媒,老且不嫁”,媒妁成为缔结婚姻的重要基石。在“妇无外行”的社会传统中,她们是最先被社会认可的可以“足履阈外”的女性。
但在每个时代媒妁也有着各自不同社会的文化内涵。明中后期,政治腐败,社会风气腐朽不堪;经济上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在金钱的诱惑下,市民队伍逐渐扩大;而思想界在“情、理、欲”的矛盾中更为直接地对传统思想进行了批判和要求对封建秩序进行整建,而这些都充分有力的反映在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三言”、“二拍”之中,尤其是历来不被文学创作者重视的媒婆这一文学配角,在“三言”、“二拍”得到大量涉及,成为这一时期新的社会形态出现的见证者。这些社会变化使得女性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复苏,在经济潮流中,市人“逐利”的风气也吹进了更多的家庭,在有限的女性职业中,更多的女性开始摆脱男权的藩篱,走出家门,加入到媒妁行业。庞大的队伍和对金钱的渴望使她们逐渐摆脱了官媒的控制,成为社会上十分活跃的社会职业——私媒。她们不再仅仅依附于男性,而成为家庭收入的重要劳动力。经济地位决定政治地位,她们虽然困囿于男权思想中,但却在“男尊女卑”的社会中有了一定的话语权。这也促使她们“东家走,西家走,两脚奔波气常吼”,有了很强的职业意识和职业愿望,成为新的社会形态下的转变者之一。如《醒世恒言》卷七高赞欲替女儿择风流佳婿的消息一传出,众多媒人出于对高额媒妁礼的渴望而趋之若鹜,各显神通与同行竞争。也只有生活在这个社会生活日益商业化的时代下,才可能出现如此场面。但是在“上梁不正,下梁歪”社会不正风气下,在金钱的诱惑中,“诚、信、仁、义”的商业道德崩塌,媒人也沾染了堕落的商业文化气息。《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姚滴珠避羞惹羞郑月娥将错就错》中说:“看来世间听不得的最是媒人的口,他要说了穷,石崇也无立锥之地;他要说了富,范丹也有万顷之财。正是富贵随口定,美丑趁心生。再无一句实话的。”
她们由于自身的知识水平限制和时代腐朽风气影响,做着唯利是图的勾当。但是在新思潮的吹袭中,封建思想对她们的束缚较之以往要松弛很多,使她们有了更大的空间活跃在男权社会中。因此,虽然她们在现实与艺术中一直属于配角地位,却是包涵着丰厚历史内容的文学典型,成为读者通过文学认识特定时代生活的方式之一。
二、女性解放的牵引者
中国古代,女性长期束缚在封建礼教道德规范下,“丧失了自我,丧失了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文化和思想品格”。但在明代中后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新思潮的涌现,一股新的价值追求和审美观念,开始向传统伦理文化发出挑战。而被“三从四德”束缚在庭院中的女性也在这个特殊的文化背景下开始疏离传统道德规约,而这其中起到很大作用的就是媒妁群体。她们终日游走于大街小巷、出入庭院闺阁之中,有着相当丰富的见识和风趣幽默的市井之语,这些都是让闺阁之女感到新奇和渴求的外界信息。正如普列汉诺夫说:“任何文学作品都是它的时代的表现。它的内容和它的形式是由这个时代的趣味、习惯、憧憬决定的”。
在“三言”、“二拍”中融入了时代风气,新的资本主义观念促使人们萌生出追求人生价值、婚姻自由的想法。因此,在这两部小说集中,大量描写了女性对爱情的憧憬和情与欲的纠葛。而这其中,媒婆起到了很大的诱导作用,她们将外界的信息传输进了闺阁内,促使闺阁之女第一次直接地去面对内心最真实的渴望。如在《喻世明言》卷一《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三巧儿被“俐齿伶牙,能言快语”的薛婆诱哄的“一日不见他来,便觉寂寞”,最后“这婆子或时装醉作风起来,到说起自家少年时偷汉的许多情事”,勾起了三巧儿的春心,促成了一段精神与肉体共同出轨的恋爱。在《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姚滴珠避羞惹羞郑月娥将错就错》中姚滴珠离家出走被拐,在王奶奶别有用心地大骂姚滴珠公婆虐待儿媳的挑破中,引起姚滴珠辛酸不已,并循序善诱的为她另寻“良人”:“他把你象珍宝一般看待,十分爱惜。吃自在食,着自在衣,纤手不动呼奴使婢,也不枉了这一个花枝模样。强如守空房、做粗作、淘闲气万万倍了。”
这促使姚滴珠“听了这一片活,心里动了”。虽然两位媒人的行为都是不被社会认可的,但在封建礼教观念中,两位少妇在媒人的牵引下,勇于承认自身的情欲,打破了封建礼法的束缚。她们不再对“父权、夫权”唯唯诺诺、逆来顺受,而是大胆与情人私会、另寻“良人”,走出了自身解放的第一步。同时,她们不再严守“男女大防”,在性的问题上,“凭他轻薄”,“分明久旱受甘雨,胜似他乡遇故知”,这是对封建贞洁观念的极大挑战。媒人的行为间接唤醒了女性的性意识,让女性顺应本真的人性,去享受自己生命的快乐,而且这也改变了传统观念中女性必须为丈夫守身如玉的不对等的性爱关系。
虽然媒人“逐利”过程中不顾商业道德为人诟病,但是站在时代变革的高度看,她们直接导致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她们为已婚妇女的拉媒行为,间接地促使女性开始反对不公允的社会制度,争取与男性平等的社会地位,并且对父母、公婆言听计从的愚孝提出了质疑,要求摆脱卑微顺从的处境,具有强烈的反传统精神。这些女性没有受到完整的理论体系的指导,但在媒人有限的知识下,遵从自身原始的欲望,开始走上懵懂的女性解放之路。虽然道路艰辛,但她们的行为却给阴霾下麻木到绝望的女性带来了一丝希望的曙光。
三、文学变革先行者
明代中后期,思想文化统治并不严厉,给予了针对封建正统思想弊端而产生的新思想一席生存空间。新旧思想激烈碰撞,涌现了令人瞩目的价值理念。而“三言”、“二拍”的两位作者都是新思想的拥护者,在他们的作品中积极发扬了“文以载道”的文学传统。他们通过世俗小说的创作将新思潮的价值观念宣扬出去,以情感来传达自己的社会理想。冯梦龙和凌濛初从广泛、复杂的社会生活中择取题材,试图以市民文学解构封建,努力促使世人觉醒。马克思说:“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的衡量。”
在“三言”、“二拍”中,女性成为与男性平等甚至高于男性地位的作品主角,这在以往的作品中几乎是不存在的,有着划时代的文学意义。而女性配角——媒婆,在作者笔下虽然没有姓名,被冠以“薛婆”、“张婆”、“李婆”、“张六嫂”、“王奶奶”等只有姓氏的称谓,呈现出符号化的特征,但是她们在文学和历史的意义是不可忽略的。
她们在作品中很少有正面形象,多是被塑造成伶牙俐齿,不顾伦理道德、贪图金钱的卑劣形象。
作者延续并强化了这一创作传统,让她们继续成为主角顺利出场和完成作者主旨的牵引者,成为没有结局的存在。但是在作者主观意图外,却产生了超出作者意图的意料之外的效果。她们多次在作品中出现,极大地丰富了古代小说对配角的艺术处理,为中国古代小说创作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并使得读者在文学作品的阅读中,对作品出现的媒婆这一审美对象产生了兴趣。她们不再是默默无闻,成为可以“调唆织女害相思,引得嫦娥离月殿”的能言善辩的固定形象,并对小说情节发展和小说市井风气的渲染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因此成为读者对作品更深认知的一种不可忽略的文学形象类型。
同时,作者在作品中试图通过男女之情来传播情本论时,将重点放在男女主人公身上,来揭示社会变革的趋势,但是媒婆这一形象的塑造却是在作者不经意间成为了最先实践文学变革的先行者。这在作者的创作意图中,却没有这种认识。在“三言”、“二拍”中,作者对她们是持讥讽、否定的态度,但是跳出时代的局限,我们却可以从这一人物类型中发现她们身上值得肯定的反封建礼教的解放精神。她们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制度的守护者,同时又是这一制度的破坏者。她们率先打破这种不合理的婚姻桎梏,开始征询婚姻男女双方的意见。她们在女主人公还未萌发反叛思想前,就已自撬墙角,成为拥护社会新思潮“主情”的先行者。在《通闺闼坚心灯火闹囹圄捷报旗铃》中媒人杨老妈在征询了婚姻当事者幼谦和惜惜的意见后才积极为二人牵线搭桥,摆脱了盲婚哑嫁的婚姻悲剧。 她们在“三言”、“二拍”中,成为了作者主观意旨的先行者,具有不可忽略的历史意义和文学意义。
总之,媒人是“三言”、“二拍”中的重要角色,她们身上散发着明代特有的新思潮的气息,闪耀着时代的光芒,揭示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她们在历史和文学中,占据了前沿地位,成为具有独特魅力的文学形象。她们突破了传统女性的保守、卑微和柔顺,走出家门去“谋利”,表现出与男子一样的胆识和机智,见证了时代商业氛围中的变革。她们通过对闺阁女性信息的传递,成为文学中“变革那可能变革世界的男人和女人们的内驱力”,促进女性意识的觉醒,争取女性的解放。同时,她们是作者主观意图的先行者,促使了作品的思想登上一个新平台。她们角色虽小,却拥有“永恒的价值”和“不朽的艺术魅力”。
参考文献:
[1]美,雷?韦勒克、奥?沃伦.文学理论[M].刘象愚.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106.
[2][7][8]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M].北京:中国盲文出版社,2000:17,20,20.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普列汉诺夫.论西欧文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121.
[5][6][9]冯梦龙.喻世明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17,18,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