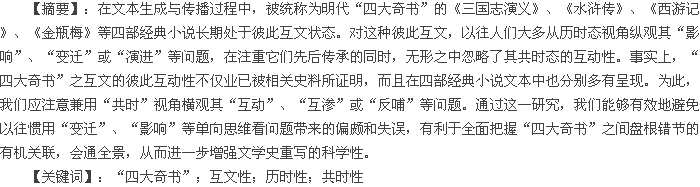
由于小说创作要大量借助引用、暗示、参考、仿作、戏拟、剽窃等叙事手段,因此文本之间的“互文性”现象随处可见。①在阅读和研究《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经典小说时,人们之所以会经常产生某种似曾相识感,原因即在于此。要中正公允地对“四大奇书”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关系进行研究,必须全方位、多视角地看问题。“历时态”纵观视角固然重要,“共时态”横观视角同样也不可忽视。②然而,以往人们多运用“历时态”视角,要么本着“影响”或“传承”思维探讨彼此之间的文本关联,强调后来者居上;要么本着“特色”或“个性”思维强调它们“各擅其奇”、“自成一家”,探讨其类性延伸和后起同类作品的效颦等问题。显然,这些研究只看到了“四大奇书”先后文本之“互文”,而没有或很少顾及非同类的四部小说彼此之间的相互吸取、相互作用,无形之中忽略了其共时“互文”问题。为此,我们有必献实证等方法,兼用历时态、共时态两种视角来重新审视“四大奇书”之间盘根错节的“互文”实景。
研究“四大奇书”关联应兼顾“共时”视角
虽然《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四部经典小说之渊源仿佛黄河之水天上来,令人难以确定一个诞生的具体年代,但它们各自以“最完整的形式流传于世”的时间段还是大致能够确定的,即集中于明代嘉靖至万历年间的百年。在此百年之前,四大小说确实还有一段相当长的共时并行传播岁月。在这相对漫长的岁月里,它们既经历了先后“历时态”的创作生成,又经历了近乎齐头并进的“共时态”传播完善。况且,更大程度上由于“共时态”传播完善的作用,四部小说之间不断聚合归并。大约于明末清初,人们把它们汇集到一起,并命名为“四大奇书”。换句话说,“四大奇书”之由来与命名并非仅仅基于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小说、世情小说四类专题小说之“奇峰并峙”,而更大程度上则是基于四部经典小说之“互融共通”。
对“四大奇书”之间的这种“互融共通”关系,以往文学史研究或文学文本研究基本上是在“历时态”视角下进行的。尤其是,上世纪20年代,受到“进化论”等学术思想的影响,鲁迅先生作《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难能可贵地“从倒行的杂乱的作品里寻出一条进行的线索来”。大略与此同时,胡适先生也给中国传统小说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即“历史演进法”。
他认为,对那些由历史逐渐演变出来的小说,“必须用历史演进法去搜集它们早期的各种版本,来找出它们如何由一些朴素的原始故事逐渐演变成为后来的文学名着”。在运用“历史演进法”研究中国古代小说过程中,胡适先生曾得出过这样的一些结论:《三国志演义》“不是一个人做的,乃是五百年的演义家的共同作品”;《西游记》“起源于民间的传说和神话”,也“有了五六百年演化的历史”。后来,在评论《三侠五义》时,他提出了一个“滚雪球”的理论:“我们看这一个故事在九百年中变迁沿革的历史,可以得一个很好的教训。
传说的生长,就同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初只有一个简单的故事作个中心的‘母题’(Motif),你添一枝,他添一叶,便像个样子了。后来经过众口的传说,经过平话家的敷演,经过戏曲家的剪裁结构,经过小说家的修饰,这个故事便一天一天的改变面目:内容更丰富了,情节更精细圆满了,曲折更多了,人物更有生气了。”胡适先生认为,很多章回小说都是经过或五六百年,或八九百年的“历史演进”而成的,其间不断地添枝加叶。这种研究强调了成书的累积性,但对于其间所添加的“枝叶”由来并没有追踪,忽略了这些小说之间共时相济以成“经典”问题的探讨。在鲁迅、胡适等着名文学史家们的影响下,人们针对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古代章回小说研究,“历时态”纵观视角受到追捧。这一视角固然曾经使得一系列学术问题迎刃而解,功不可没。然而,由于基本一味地依托“变迁”、“演进”等“历时态”观念,再加后来各种“文学史”或“小说史”撰写基本按历时态的时间先后顺序排列,因而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各章回小说之文本关联几乎被描绘成一条直线,颇具立体性的“共时态”修订以及渗透传播语境便被遮蔽起来。
众所周知,《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四大小说的源头活水是讲史、说经、小说话本。在较长的流程中,一方面是大量丰富而鲜活的民间性注入,另一方面是大量不断累积的文人性输入。其间,《大宋宣和遗事》、《三国志平话》、《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等“前期成果”固然可供相对应的小说去选择遣用,但这些“前期成果”的分量及其渗透力毕竟是有限的,对文本形成发挥主要作用的还是后天创造。如果还原到那段历史时空来看,在现存最早版本出现之前的几十年乃至数百年间,四部小说的身影已若隐若现。换句话说,在现存最早版本现身之前,它们之间早已有过一段互相影响的传播史。延及明末清初这段齐头并进的“共时”岁月,四部小说彼此之间更是拥有了互相渗透的现实语境。种种迹象表明,在“四大奇书”成书与增订、修订过程中,无论点铁成金也好,还是化腐朽为神奇也罢,浸润在小说发展与传播洪流中的小说作者及评改者们不可能对前人亦步亦趋,定然会凭着各自的博识和开放的胸襟来润饰他们的文本。明代中后期,书商们瞄上了这些不断加工的成品,几乎于同一时间段先后将多部小说一一推出。如此这般,经过民间广泛的甄别和遴选,再经李卓吾、金圣叹等精英们慧眼识拔,四部小说便逐渐脱颖而出。在金批《水浒传》的强力影响下,明末清初的才子们群起而评改之,于是便将《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四部小说推举到“奇书”高度。以往围绕“四大奇书”文本关系问题所进行的各种“对比研究”和“影响研究”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缺陷,若借用有人探讨“渊源批评”的说法,即一味地“强调对创作过程的‘前文本’给以历时动态结构的分析”,重视了彼此之间的传承关系,而忽略了“文本内部的共时静态形式的分析”。于是,四部小说就被整合排列到一条时间直线上,从而给人这样一种错觉:是《三国志演义》影响了《水浒传》,又是《水浒传》影响了《金瓶梅》,而这种影响是先后传承性的。而今,我们非常有必要再添加一种眼光,即运用结构主义的“偏重文本内部的共时静态形式的分析”的互文批评方式,打破以往研究的缺陷,对这四大小说之文本关系进行重新审视。
概言之,“四大奇书”并非一蹴而就之作,它们既经过了“历时态”的血脉传承,又经过了“共时态”的互动互渗,彼此之关联可谓“剪不断,理还乱”,错综复杂。因此,面对“四大奇书”文本之间所存在的错综复杂的“互文性”,我们既要秉持“历时态”视角勾勒出其“前后影响”、“一脉相承”的画卷,又应该兼而通过“共时态”视角绘制出其彼此“相互浸润”、“相互渗透”的图景。在具体研究中,就是既要靠文献说话,又要用文本比勘方法佐证。
“四大奇书”之双向“互文”合乎史实事理
众所周知,章回小说得以形成的历史时空苍茫而迷离,尤其是《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四部小说均非一时、一地、一人完成,不仅主撰者的身份复杂,而且参与评改者的人数也特别多。要系统地研究这些小说,非常关键的问题自然是理清彼此之间关系。在“四大奇书”错综复杂的文本关系中,“互文”关系位列其首。
法国批评家罗兰·巴特曾经指出:“任何文本都是一种互文。在一个文本中,不同程度地以各种多少能够辨认的形式存在着其他的文本,譬如,先前文化的文本和周围文化的文本。”由于“互文性”赖以形成的文化语境有“先前文化”和“周围文化”,因此所谓“互文”也就包括“历时互文”和“共时互文”两种方式,前者是先后传承性的,后者是周围互动性的。在经典小说创作与成书过程中,后起文本仿拟先期文本,乃天经地义;而在同一阶段性的传播时空中,小说文本之间出现仿拟、效法等“交叉感染”,也理在其中。为此,要全方位地看问题,我们就必须坚持“历时态”纵观与“共时态”横观两种视角并用,既“强调对创作过程的‘前文本’给以历时动态结构的分析”,又“偏重文本内部的共时静态形式的分析”。相关史料业已表明,“四大奇书”文本内部及其彼此之间的“互文”关联是客观存在的。以往人们多用“历时态”视角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从《三国志演义》到《水浒传》、从《水浒传》到《金瓶梅》等先后单向性的逻辑链条,在此我们兼用“共时态”视角,更多地从《金瓶梅》到《水浒传》、从《水浒传》到《三国志演义》等反向或逆向关联方面进行探讨,以证明这种“互文”的彼此双向互动性。
首先且看《三国志演义》与《水浒传》到底谁仿拟了谁,二者文本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这个貌似不成问题的问题其实不能作简单化回答。文献史料只是告诉我们,二者在传播过程中曾有一段彼此互相影响的历史,而并没有明确告诉我们谁是父谁是子、孰是兄孰是弟。前些年,人们更多地认定《水浒传》受到了《三国志演义》的影响。可是,明末清初人却多持《三国志演义》仿拟《水浒传》之见。根据那个时代的有关资料,可以发现,二者之间“历时”传承影响的影像和踪迹反倒不如“共时态”传播互动的影像和踪迹更为清晰。如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庄岳委谈下》有如下记载:“然元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世率以为凿空无据,要不尽尔也。……其门人罗本,亦效之为《三国志演义传》,绝浅鄙可嗤也。”这几句话特地指出,罗本是施某的门人,并说罗本效仿施某的《水浒传》而写了《三国志演义》,只不过这种效仿属于“东施效颦”而已。显然,这与后人所持较之《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系“出于蓝而胜于蓝”等论调南辕北辙。与胡应麟之论一脉相承,主要生活于清代乾嘉年间的章学诚所撰《丙辰札记》更是明确指出:“《三国志演义》固为小说,事实不免附会,然其取材则颇博赡。……且其书似出《水浒传》后,叙昭烈、关、张、诸葛,俱以《水浒传》中萑苻啸聚行径拟之。诸葛丞相生平以谨慎自命,欲因有祭风及制造木牛流马等事,遂撰出无数神奇诡怪,而于昭烈未即位前,君臣僚寀之间,直似《水浒传》中吴用军师,何其陋耶!张桓侯史称其爱君子,是非不知礼者,《演义》直以拟《水浒》之李逵,则侮慢极矣。”在这里,章氏通过文本人物之风貌的比照,指出诸葛丞相与吴用军师相似,而张飞则好比李逵,认为《三国志演义》“似出《水浒传》后”,并且指出《三国志演义》模拟《水浒传》是“邯郸学步”式的退化,持“扬《水浒传》而抑《三国志演义》”之见。姑且不论章氏关于二书高下之论是否得当,他们对“谁仿效谁”问题的明确回答也与今人之说大相径庭。当然,即如当今,也还是不断有人坚持诸如此类的观点:“根据今传明清两代文献的记述,倒可推定《三国志演义》的成书,至少在《水浒传》和《西游记》(或古本《西游记》)这两部长篇章回说部之后。”这种矫枉过正之论,源于四大小说的“共时”传播之实。
再说,明末清初人在提及此二部小说时,也大多先说《水浒传》而后说《三国志演义》的。如明崇祯间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说:“元施罗二公大畅斯道,《水浒》、《三国》奇奇正正,河汉无极。”④即便到了清康熙年间,将“四大奇书”这一专名的由来论述得最充分的刘廷玑在其《在园杂志》卷二中,也是先论《水浒传》,而后才说《三国志演义》的。
这种顺序应该也包含着时间先后性。虽然对“先《水浒》而后《三国》”这一结论目前学界未必能普遍接受,但至少在问题搞清楚之前,我们不应单向性地臆断《水浒传》仿拟了《三国志演义》,或印象性地认定《水浒传》后来者居上。关于《水浒传》一书,明代李开先《一笑散·时调》说:“崔后渠(铣)、熊南沙(过)、唐荆川(顺之)、王遵岩(慎中)、陈后冈(束)谓《水浒传》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史记》而下,便是此书。且古来更未有一事而二十册者。
倘以奸盗诈伪病之,不知序事之法,学史之妙者也。”在此,李开先所提到的崔铣等人都是嘉靖时期的名流,从他们如此这般热情赞扬《水浒传》来看,这部小说在当时已经成书是毫无疑问的;况且,现存《三国志演义》最早版本也出于嘉靖年间,与《西游记》、《金瓶梅》出现的年代相距不远。因此,二书问世的时间实在难分先后。此外,关于罗贯中《三国志演义》仿拟《水浒传》之实,我们还可运用向来被视为他创作的两部小说来佐证:二十回本《三遂平妖传》第八回所写“野林中张鸾救卜吉”故事摹拟了《水浒传》第八回野猪林谋害林教头未遂的故事,就连两个防送公人的名字也与押解林冲的两个解差名字相同,都叫“董超”、“薛霸”;《残唐五代史演义传》第一回所写“安景思牧羊打虎”故事与《水浒传》第二十三回“武松打虎”有大段雷同。长期以来,虽然关于《水浒传》、《三国志演义》二书的作者一直存有争议,但关于《三国志演义》作者系“罗贯中”说却最有市场,而人们又基本公认罗贯中是施耐庵弟子。如此这般,《三国志演义》仿拟《水浒传》即能自圆其说。
种种迹象表明,在《水浒传》与《三国志演义》之“互文”关系问题上,“历时”传承的成分少些,“共时”互动的因素多些。当然,如果两部小说共同出自施、罗二公之手笔这种说法能成立,那么,它们之间的“互文”问题就更理所当然了。既然两部小说之成书基于“共时态”的“互文”,那么以往似乎是不易之论的各种“传承”说法便是片面的、误解的。
据此生发出的一系列申论自然也就站不住脚了。
诸如“从《三国志演义》到《水浒传》”等命题,以及“《水浒传》描写的‘梁山聚义’无疑受到‘桃园结义’的思想影响,并进一步发展了‘义’的内涵”云云,均因讲得过于绝对而必须修正。
说到《水浒传》与《金瓶梅》谁仿效谁,看起来似乎更不成问题。然而,事实却照样并非那么简单。笼而统之地说,《金瓶梅》因袭了《水浒传》,并无大碍。且前人也曾言之凿凿。如,明代袁中道《游居杮录》曾经说过:“模写儿女情态具备,乃从《水浒传》潘金莲演出一支。”这是从题材生发的角度立论的。又如,清代张竹坡《金瓶梅寓意说》也曾指出:“《金瓶》一部有名人物,不下百数,为之寻端竟委,大半皆属寓言。庶因物有名,托名摭事,以成此一百回曲曲折折之书。如西门庆、潘金莲、王婆、武大、武二,《水浒传》中原有之人,《金瓶》因之者无论。”这是从人物由来之意义上说的。不过,由于在《水浒传》传播过程中,人们曾对其文本进行过多次增而删、删而增,其文本状况显得颇为复杂。对此,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指出:“余二十年前所见《水浒传》本,尚极足寻味。十数载来,为闽中坊贾刊落,止录事实,中间游词馀韵,神情寄寓处,一概删之,遂几不堪覆瓿。”可见,胡应麟在万历十七年(1589)的二十年前曾见过较完整的《水浒传》嘉靖本,后来因书商一味地追求商业利益,将其越删越简、越删越糟,殆至“几不堪覆瓿”。明末清初人周亮工《书影》曾据卷首诗词考证《水浒传》不同版本的演变,并指出:“故老传闻:罗氏为《水浒传》一百回,各以妖异语引其首;嘉靖时,郭武定重刻其书,削其致语,独存本传。金坛王氏《小品》中亦云此书每回前各有楔子,今俱不传。予见建阳书坊中所刻诸书,节缩纸板,求其易售,诸书多被刊落。此书亦建阳书坊翻刻时删落者。”由这些零散的记载看,现存《水浒传》各版本均经过书商们一删再删,当为不争的事实。再说,因经过不断删改,《水浒传》的质量大为下降,后来便有人进行“复原”、“充实”。在“复原”、“充实”过程中,时人除了像金圣叹一样依靠或搬弄所谓的“古本”,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顺手拈来“现行”而“现成”的《金瓶梅》等小说文本来添补修复。以往,论者单向地一概而论说《金瓶梅》沿袭了《水浒传》;殊不知,《水浒传》后期版本的续者或评改者也在跟踪出自“嘉靖大名士”手笔的《金瓶梅词话》,并不断与时俱进地从《金瓶梅词话》那里获取某些“看点”来“充实”《水浒传》。较早提出这一问题者是陆澹安先生。在《说部卮言》一书中,他敏锐地指出:“《水浒传》写王婆说风情一节,亦非常工致,似乎施耐庵也是社会小说能手,但是我把《金瓶梅》与《水浒传》对照,方知《水浒》这一节,乃是直抄《金瓶梅》,并非施耐庵自己手笔。”尽管目前对这里所谓的《水浒传》抄袭《金瓶梅》之论尚有争议,但如此敏锐地运用“侦探的眼光”提出的大胆而又合乎情理的观点,至少提醒后人应全方位地看待二者之双向性的“互文”关系。
通过文献资料,我们已经对《三国志演义》与《水浒传》、《水浒传》与《金瓶梅》之间的“互文”情景作了如上探讨。而关于《西游记》与《水浒传》之间的“互文”关系,以及《西游记》如何与《三国志演义》发生“互文”等问题,传统史料文献涉及较少,我们可以借助文本比勘来坐实。
“四大奇书”彼此双向“互文”之文本实景
“四大奇书”之“互文”关系的彼此互动性不仅符合史实事理,而且也存在许多有迹可循的文本依据。
从总体上看,“四大奇书”彼此之间所发生的“历时”、“共时”彼此双向“互文”并非是等量齐观的,相对于较为有限的“共时”渗透而言,“顺时”因袭的势头自然要突出一些,前人的相关研究也主要瞄准这方面。就拿《西游记》与《水浒传》而言,尽管它们彼此之间的“互文”关系相对较为隐蔽,但也曾被明眼人察觉到。如,美国汉学家浦安迪先生曾根据清代汪象旭《西游记证道书》等资料指出:“第18回孙悟空为了诱捕猪八戒在新房中假扮成新娘一节分明与《水浒传》第五回里鲁达的巧设骗局如出一辙。”“第39回里用的家喻户晓字句‘哭有几样,……’,与《水浒传》描绘潘金莲假哭用的完全是同样文字(见《水浒传》第25回)。同样的字句也搬用在《金瓶梅》里。”“第82回中那行‘若是……第二个酒色凡夫……’,我觉得活像《水浒传》第72回里不无反讽意味地用来描绘宋江的那一行文字。”在一定程度上讲,浦安迪所指出的以及尚未提到的大量一再“重复”出现的片段,表明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互文”关系。再说,《西游证道书》基本完成了《西游记》的文本演变,不但诸种清刊本大多以此为底本,而且直到现在,坊间最为通行的《西游记》版本也基本依此。况且,《西游记》在“反抗”、“招安”思想以及“人物个性”、“整体结构”等方面更是与《水浒传》颇为相像。这些“同样的字句”以及相似的叙事格调只能证明两部小说之间存在“互文”关系,而并不能单向性地认定就是《西游记》袭用或仿拟了《水浒传》,否定反向互动的可能性。沿着彼此双向“互文”这一思路,许许多多有意思的问题或推测就出来了。如,《水浒传》开篇所叙写的洪太尉误走妖魔故事,大意是,因洪太尉望文生义,自作主张,搬到镇妖石碣,黑洞中跑出一群魔王(或魔君),而这群魔王的真正身份乃是三十六员天罡星和七十二员地煞星,系因触犯天条而被长期镇压在龙虎山的。前者讲述的是致乱之由,后者讲述的是解放之道。
如此叙述是否模拟了《西游记》所叙述的孙悟空因大闹天宫而被如来佛镇压在五行山下,后来终得唐僧搭救这一故事呢?再如,《水浒传》第七十三回所叙述的“黑旋风乔捉鬼”故事与《西游记》所叙述的“悟空收八戒”故事,都是征服者凭着装扮来糊弄所谓的“鬼”、“怪”,其戏谑笔法和审美格调自然也不无相仿佛之处。至于前述《西游记》所叙述的孙悟空“大闹天宫”等故事,与《水浒传》所叙述的鲁智深等人的屡次“大闹”之类的故事,是否也存在一个互相启发的问题呢?一句话,《水浒传》与《西游记》之间的确存在难分难解的彼此双向“互文”关系。至于这种“互文”关系究竟是由此及彼还是由彼及此,需要进一步考察。在问题弄清之前,不能轻易得出后者系模仿前者的结论。
需要指出的是,对“四大奇书”之间呈现出来的彼此双向“互文”情景,以往人们也并非完全没有意识到。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由于《水浒传》与《金瓶梅》的关系较为密切而特殊,因此前辈学人曾经从不同版本着眼对二者的文本关系展开过多次、多向度的考察。上世纪80年代,黄霖先生曾对《忠义水浒传》与《金瓶梅词话》进行过认真比勘,一口气举出《忠义水浒传》在人物与情节上影响《金瓶梅词话》的十二处,如“第30回写张都监陷害武松的圈套与《金瓶梅》第26回中西门庆陷害来旺儿相似”、“《水浒传》第32回刘知寨老婆被劫往清风寨事,被移到了《金瓶梅》第84回吴月娘身上”等等,并得出结论说:“《水浒传》与《金瓶海》在故事流传阶段,可能是交叉发展、相互影响的,但在写定《金瓶梅词话》的时候,晚出的《金瓶梅》肯定是参考了基本定形的《水浒传》的。”“有的地方是直接抄写,也有的经过了改头换面,还有的进行了移花接木,但都不难看出,《金瓶梅》的这些描述与《水浒传》有着血缘关系。”黄先生在论述时间相对晚出的《金瓶梅》之“沿袭《水浒传》何种版本”这一问题时,指出两部小说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交叉发展、相互影响”的。可惜,《金瓶梅》是如何影响《水浒传》的这一问题,向来未能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1994年,徐朔方先生在其《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综合考察》一文中也曾谈到“小说名着在长期流传中彼此影响、互相渗透”问题,指出中国古代长篇小说“都曾经历或长或短以数百年计的竞相流传时期,它们难免彼此影响,互相渗透”。
他特别指出,这种“彼此影响,互相渗透”是“双向作用”的。为此,徐先生进而说,“古代早期各长篇小说名着在流传即形成过程中双向的蹈袭”不仅表现在赞诗或引首词的运用上,而且它们之间的彼此影响还出现在题材相近和题材迥异的作品之间,并指出《金瓶梅》第八十九回的引首诗被《水浒传》第三十八回引用,因不甚得当,故而给人以“生搬硬套”感。由徐先生提供的这些蛛丝马迹,我们可以断言,从《水浒传》脱胎而来的《金瓶梅》也曾一度影响过《水浒传》。遗憾的是,这种研究思路和理论方法照样没有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
大致说来,不同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性”所呈现出的形态非常复杂,至少有显性呈现与隐性呈现两种情况。由于产生年代漫长,版次较多,“四大奇书”之“互文”关系之错综复杂的程度就可想而知了。对其进行探究,难于一蹴而就。限于篇幅,以上仅仅涉及了《水浒传》与《西游记》、《水浒传》与《金瓶梅》等小说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
可以肯定地说,除此之外,“四大奇书”其他小说彼此之间也都或多或少、或显或隐地存在着一个彼此双向“互文”问题,期待我们施展“文本细读”的硬功夫去不断地探索与发现。我们相信,随着不断地借助文本比勘来逐一坐实,除了上述黄霖、徐朔方等先生的零散考信,“四大奇书”之彼此双向“互文”迹象会越来越清晰。
“四大奇书”彼此“互文”对重写文学史的启示
归根结蒂,文学研究中的“互文性”探讨,主要旨在解决一个“跨文本”关系问题,而这种“跨文本”关系问题的提出,又使得人们在理解各个不同文本时彼此镜照,相互阐发。因此,兼顾运用“历时态”、“共时态”双视角来重审“四大奇书”彼此之间的双向“互文性”,自有其不可小觑的学术意义和价值,尤其是对我们全方位审视文学生态史、写出更富科学性的文学史着,具有重要启示。
首先,“四大奇书”之彼此双向“互文性”研究为我们系统化阅读小说提供了一条颇具联想性的理路。彼此双向“互文”将“四大奇书”这一经典小说系列有机链接起来,形成强强链接的经典化风范。如果人们兼用“共时态”眼光阅读“四大奇书”,便可以通过各种阅读联想,去充分感受其中的“似曾相识”段落,并进一步加深对其“互文”衍生意义的理解。这样,既可从中获得艺术强化效果,又可从中享受到反讽美感。如,由《西游记》所叙猪八戒智激猴王故事,联想到《三国志演义》所叙诸葛亮智激周瑜、孙权故事;由《西游记》所叙之猪八戒贪食、好财的“快活”观,联想到《水浒传》所叙之梁山英雄的“吃喝”和“贪财”,抑或作一些相应的反向联想,等等。显然,这一增值性阅读方式打破了以往在解读这些作品时所惯用的“渊源”和“影响”等相对固定的思维模式。其次,“四大奇书”之彼此双向“互文性”研究让我们在文学史史着,尤其是小说史着撰写过程中更清醒、更严密。
凡是撰写《中国文学史》或《中国小说史》之类着作的学者,几乎总是会遇到这样的困惑:如何在描述文学或小说发展史时准确地引用“四大奇书”原文?早期版本时间上居前而文字却显得粗疏,各种修订本文字成就较高而又在时间上居后。这种困惑常常引发出一些“史着”撰写的失误。如,有的研究者一度甚至犯了诸如引用清代毛评本《三国志演义》讨论被放在“元朝文学”里的《三国志演义》如此低级的错误。再如,有的论者无视四部小说传播的“共时”性,试图通过文本比勘,来推断或解决《金瓶梅》的成书时间或作者问题,也会容易招致这样或那样的错讹,招致别人强有力的诘难。
“四大奇书”之彼此双向“互文性”现象提醒我们,在涉及“四大奇书”文本关系等问题时,引用小说原文来证明文学史问题应该注意版本的复杂性;在探讨作品的着作年代以及版本等问题时,不应一味地运用“演进”思维来看问题,而是要注意对一些相关悬而未解的问题进行全方位的纵横观察。
再次,通过“四大奇书”之彼此双向的“互文性”研究,我们可以在强化“共时态”史识的基础上,修正以往文学书之失误,为重写更为严密而科学的文学史提供理论指导。如上所述,前些年人们热衷于运用“历时态”眼光纵观“四大奇书”与先前文化以及四部小说彼此之间的嬗变,基本解决了四者之间的关联传承问题。然而,如果仅仅运用这种单一视角,一系列偏见性的结论亦容易随之而来。如,在对《三国志演义》与《水浒传》所作的各种对比中,许多人或本着从前者到后者的意识,得出一系列“后来者居上”的结论。又如,有的人说,从《三国志演义》到《水浒传》,人物描写实现了由“类型化”到“个性化”的演变,等等;也有的人不顾不同年代版本的错综,在引用小说原文时颠倒了前后不同文本,甚至无意中把毛评本《三国演义》的文字当成早于金评本《水浒传》的文字,等等。再如,有些论者只注重关涉小说本身素材的“累积”,而得出一些“四大奇书”乃“滚积而成”、“集撰”之类的结论。这就无意之中把“四大奇书”简单地视为由不同部件组合而成的,从而遮蔽了各部小说文本与文本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
事实上,除了“历时态”传承以及“纯属偶然”、“纯属巧合”等因素,“四大奇书”中的任何一部作品之生成与定型均有赖“共时态”时空中的彼此“互文”或“仿拟”。
概而言之,“四大奇书”彼此之间的“互文性”既是“历时态”单向传承式的,又是“共时态”互动渗透性的。这种彼此双向“互文性”曾经使四部小说文本彼此互惠互利,发挥过提升各自经典品牌的作用。而今,运用“共时态”眼光来重新审视“四大奇书”,不仅启示我们通过联想阅读来全方位地解读它们,而且还启示我们在中国文学史之类的史着撰写以及其他相关研究中,更加审慎地使用这些小说版本及其相应文本,更加有效地避免因单向思维导致的片面或错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