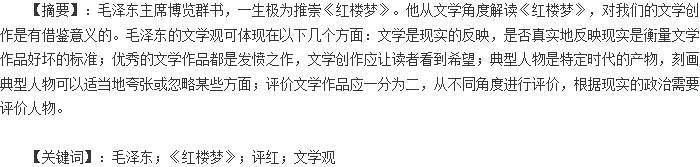
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主席博览群书,从青年时代就对《红楼梦》情有独钟,直到晚年还爱不释手。在戎马倥偬的岁月,他总把《红楼梦》带在身边。长征途中,许多书都丢了,却仍保留着一部《红楼梦》。他极为推崇《红楼梦》:“中国有三部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不看完这三部书,不算中国人。”毛泽东读《红楼梦》很注意文本的异同,常将十多种不同版本的《红楼梦》作对比阅读;除了读文本,他还读了许多红学研究着作。由此可知,他对《红楼梦》绝非泛泛阅读,已进入深入思考研究的层面。他从文学角度解读《红楼梦》,评论《红楼梦》的人物、主题、语言,从这些自成一家的解读、评论中,可看出他对《红楼梦》是多么热爱!毛泽东对传统文化,包括其中的文学理论都有很深的造诣。毛泽东的红学观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社会价值,而且对“红学”研究影响深远。
一、现实观--文学是现实的反映,是否真实地反映现实是衡量文学作品好坏的标准
随着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毛泽东的文学观侧重会有所变化,但“文学是现实的反映,是否真实地反映现实是衡量文学作品好坏的标准”这个核心文学观,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建国之后,都是他一直坚持的观点。这一观点是对唐代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文学观的进一步阐发,也是政治家,革命家的毛泽东评论文学作品时更为重视其社会功能的突出特色。
《红楼梦》作为他特别推崇的一部古典小说,经常成为他比附现实、开展教育的素材。“借小说喻政治,取其一点,不计其余,把艺术实例从它们所处的作品结构中剥离出来,从而更方便地以他特有的灵气、敏感和记忆,把小说读活、用活;读出新真理,用出新效果”。例如,年月日毛1938428泽东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中说:
鲁迅先生在《毁灭》的后记中说到,《毁灭》的作者法捷耶夫是身经游击战争的,他描写调马之术写得很内行。像上马鞍子这类细微的动作,《毁灭》的作者都注意到了,鲁迅先生也注意到了。这告诉我们,大作家不是坐在屋子里凭想象写作的,那样写出来的东西是不行的。《红楼梦》这部书,现在许多人鄙视它,不愿意提到它,其实《红楼梦》是一部很好的小说,特别是它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比如它描写柳湘莲痛打薛蟠以后便“牵马认镫去了”,没有实际经验是写不出“认镫”二字的。事非经过不知难,每每一件小事却有丰富的内容,要从实际生活经验中才会知道。……没有丰富的实际生活经验,无从产生内容充实的艺术作品。要创造伟大的作品,首先要从实际斗争中去丰富自己的经验。艺术家固然要有伟大的理想,但像上马鞍子一类的小事情也要实际地研究。过去一个研究《红楼梦》的人说,他曾切实地把大观园考察过一番。
现在你们的“大观园”是全中国,你们这些青年艺术工作者个个都是大观园中的贾宝玉或林黛玉,要切实地在这个大观园中生活一番,考察一番。你们的作品“大纲”是全中国,“小纲”是五台山。要把中国考察一番,单单采取新闻记者的方法是不行的,因为他们的工作带有“过路人”的特点。俗话说:“走马看花不如驻马看花,驻马看花不如下马看花。”我希望你们都要下马看花。在此,毛泽东由对《红楼梦》的评论谈到了艺术与社会的关系,他认为:“《红楼梦》是一部很好的小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进而他认为伟大的作品,都是从实际生活中产生的,“没有丰富的实际生活经验,无从产生内容充实的艺术作品。”为此,毛泽东要求鲁迅艺术学院的学员们,都要下马看花,真正地下苦功夫深入群众、深入社会实践中,做实际研究,从而创造出伟大的作品。这深刻说明了毛泽东的文学观是现实主义的文学观,所以他多次倡导文学是现实的反映,是否真实地反映现实是衡量文学作品好坏的标准。
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更是强调了其文学的现实观问题:“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毛泽东一再强调《红楼梦》不仅要当作小说看,而且要当作历史看,认为曹雪芹写的是很细致的、很精细的社会历史。早在井冈山时期,他与贺子珍谈论《红楼梦》时就说“《红楼梦》写了两派的斗争”。
可知那时毛泽东就对《红楼梦》形成了独到的见解,这种见解在随后的生活与工作中,一直表现在他对《红楼梦》有增无减的热爱与评论中。从以下的例子中,我们可以深刻地了解毛泽东的文学现实观,了解一个政治家独特的红学解读。延安时期,有一次毛泽东与身边的同志谈要读《红楼梦》时,很有感慨地说:“还是要看《红楼梦》啊!那里写贪官污吏,写了皇帝王爷,写了大小地主和平民奴隶。大地主是从小地主里冒出来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看了这本书就懂了什么是地主阶级,什么是封建社会,就会明白为什么要推翻它!”1945年在重庆与作家张恨水谈话时,张恨水说自己小说的脂粉气太浓了一些。毛泽东说道:“脂粉气也未必有什么不好,我看曹雪芹的脂粉气比先生要浓得多,但《红楼梦》不也一样令我们叹为观止嘛!我以为,文艺作品的好与坏,不能在题材上作统而言之,关键在于我们的作品,是否真实地反映了社会,刻画了社会的人和社会的事,反映出社会的矛盾和斗争。”上世纪60年代初期,毛泽东对大女婿孔令华说:“要你们看《红楼梦》不是让你们单纯看文学作品,是要你们通过看《红楼梦》了解历史和社会的复杂性,看了《红楼梦》才能知道什么是封建社会、封建大家族。”
1962年1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扩大会议上说:“十七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了十八世纪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1975年初夏,毛泽东对照顾自己起居生活的孟锦云说:“你看,那《红楼梦》里写的是几个家庭,主要是一个家庭。《红与黑》不过也是写了一个家庭,可都是有代表性的。通过家庭反映社会,家庭是社会的缩影。所以,我说过,不看《红楼梦》,就不了解中国的封建社会。书中的那些人,都代表了一定的阶级,得这样来看他们的矛盾冲突,矛盾纠葛,矛盾的产生和发展。”
综上所述,可知毛泽东在各个历史阶段,对《红楼梦》的评价、解说,鞭辟入里,新颖独到。一以贯之地说明了他的核心文学观--文学是现实的反映,是否真实地反映现实是衡量文学作品好坏的标准。正因为毛泽东认为文学是现实的反映,所以他能透过作品中的艺术形象,把握小说反映的社会实际,读出《红楼梦》里家长制度的分崩离析、封建社会的变迁兴亡。
二、创作观--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发愤之作,文学作品不能只揭露黑暗,应让读者看到希望,创作时最好开宗明义见主题,从小处着笔更有价值
文学作品是作家情感的流露,优秀的文学作品无不是作家的发愤之作。从孟子、庄子、屈原、司马迁、曹操、曹植,到阮籍、鲍照、左思、李白、杜甫、苏轼、李清照、辛弃疾、陆游,再到鲁迅、郭沫若,等等,他们那充满生命活力的作品,都是发愤之作。毛泽东之所以对此有深刻的理解,是因为毛泽东正是这样一位伟大的诗人。
1958年10月15日,毛泽东在天津视察的谈话中说:“司马迁的《史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都不是因为稿费、版税才写的,《红楼梦》《水浒传》也不是因为稿费才写的,这些人是因为有一肚子火才写的,还有《诗经》等。”的确如此,司马迁不遭受忧愤,怎会有对现实生活的深刻体验?怎会发愤创作出如此深邃伟大的《史记》!同样,“在饱经沧桑之后,曹雪芹郁结的情感需要得到宣泄,他的才华也需要得到一种实现,从而,他的生命才能从苦难中解脱而成为有意义的完成。……也许可以说,中国历史上除了司马迁作《史记》,再没有人像曹雪芹这样以全部的深情和心血投入于一部着作的写作。”若非如此,自然也没有满怀“一把辛酸泪”的《红楼梦》了。
毛泽东还认为优秀的文学作品不仅是发愤之作,还在于它们传达了积极光明的思想,让读者看到了希望。例如,1962年8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核心小组会上的谈话:“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等,是光写黑暗的,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不如《红楼梦》、《西游记》使人爱看。《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只写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红楼梦》就不同,写得有点希望么。”文学作品如果只揭露黑暗,让人看不到光明,找不到出路,精神上没有积极向上的力量,除了认识现实外,反而负面影响更多,又怎能引领一般读者产生积极的情绪?1938年4月28日,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中,毛泽东就说过:“一种艺术作品如果只是单纯地记述现状,而没有对将来的理想的追求,就不能鼓舞人们前进。在现状中看出缺点,同时看出将来的光明和希望,这才是革命的精神,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有这样的精神。”无论作者是否是马克思主义者,其文学作品必须写得有点希望,有一定的正能量,才能更广泛地传播开去。
在谈到文学创作的主题时,毛泽东认为最好在文章的开头就应提出主题。例如,1958年,毛泽东找田家英、吴冷西谈话,拿起当日发表的《再告台湾同胞书》谈了写文章的几点意见:“文章要有中心思想,最好是在文章的开头就提出来,也可以说是破题。……《红楼梦》中描写刘老老进大观园就是这样写的。”在文章的开头就提出主题,开宗明义先破题,这种写法,很符合毛泽东的思想性格。
而在谈文学的具体创作时,毛泽东却认为从小处着笔更有价值。例如,毛泽东在第六回《贾宝玉初试云雨情刘姥姥一进荣国府》回末写下批语:“第六回从‘千里之外,芥豆之微,小小一个人家’起,写得很好。其价值,非新旧红学考据家所能知,一边是宁荣府,一边是是小小之家。”可见毛泽东深谙文学创作之道,创作“从小处着笔更有价值”,正是以小见大,更可具体、真实、生动,再说,那“千里之外,芥豆之微,小小一个人家”,草蛇灰线,伏下了多少故事?
三、典型观--典型人物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刻画典型人物可以适当地夸张或忽略某些方面,把人物写“活”,这样才能塑造出性格各异、真实生动的个性与共性和谐统一的典型人物
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当时有人提道:一些干部群众盼“十大”,开过“十大”开“人大”,人大一开就要解决工资问题。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谈起了《红楼梦》中贾母死后众人“哭”的细节描写:各有各的心事。贾母一死,大家都哭,各有各的目的。如果一样就没有个性了。哭是一个共性,至于个人想的,伤心之处不同,那是个性。我劝人们去看柳嫂子同秦显家的争夺厨房那几回。毛泽东确实看得真切,评得深刻。众人哭贾母各怀心思:鸳鸯哭既是对贾母赤胆忠心,痛彻心肺,也是哭自己不能做主的命运,最终她以死为自己的命运作了一回主;湘云哭是既哭“贾母素日疼他”,也因为丈夫得了绝症而伤心;宝玉哭是由湘云、宝琴、宝钗穿孝念及黛玉,“但只这时候若有林妹妹也是这样打扮,又不知怎样的风韵了!”于是,宝玉心酸起来,放声大哭,他哭的主要是林妹妹。确实是大家哭的“各自有各自的心事。”如上文所谈,创作时若不“从小处着笔”,怎会写得如此生动、深刻?
《红楼梦》第六十二回中柳嫂子同秦显家的争夺厨房管理权的几段描写得又怎样?争夺的描写中,最精彩的是关于秦显家的忙着接收、清点货物,查柳嫂子的亏空,只见她又打点林之孝家的礼,账房的礼,又备菜蔬请几位跟前的人,忙得不亦乐乎。她正兴冲冲地忙乱着,忽有人来告诉她“看过这早饭就出去罢。柳嫂儿原无事,如今还交与他管了”。秦显家的听罢,“轰去魂魄,垂头丧气,登时偃旗息鼓,卷包而出。”这几段写得有声有色,如在眼前。两个仆妇争夺一个厨房管理权的日常小事的细节描写,也折射了那个特定的时代封建官场的争权夺势、尔虞我诈。
可见,文学创作“从小处着笔更有价值”!
“哭”贾母及争夺厨房管理权的细节描写,生动地写出了那个特定时代人物的个性与共性。只有对生活观察得细致入微,才能写出特定时代逼真而典型的细节,才能塑造出个性与共性和谐统一的典型人物。
但在个性与共性的和谐统一中,毛泽东更强调写出人物鲜明的个性来。
1975年,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与护士孟锦云谈《红楼梦》时这样评价林黛玉:
林黛玉有句话讲得好:“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她是个很有头脑的女孩子哩。
但是她的小性儿也够人受的。
孟锦云说:“我同情林黛玉,可不喜欢贾宝玉,他对那么多女孩子都好,这叫什么事啊,一点都不专一。”针对小孟的话题,毛泽东说:“贾宝玉,是个很有性格的男孩哩。他对女孩好,那是因他觉得女孩受压迫嘛。大观园里的女孩总比那些男人干净得多,你还不懂贾宝玉。”
在此,毛泽东突出评价了林黛玉、贾宝玉的鲜明个性。个性是一人物区别于其他人物的特点,人物鲜明的个性,是人物的生命活力之所在,林黛玉、贾宝玉的鲜明个性,都彰显了那个特定时代的而又超越时代的叛逆贵族子弟的特点。
对特定时代的典型人物的塑造,毛泽东认为可以适当地夸张或忽略某些方面。1953年10月,毛泽东说:人都是有缺点的,所以英雄人物当然也有缺点。但是,文艺作品中的英雄人物不一定都写他的缺点。像贾宝玉总是离不开女人,而鲁智深却从来没有考虑到女人。为了创造典型有意识地夸张或忽略某些方面是应该的。
这种“为了创造典型有意识地夸张或忽略某些方面”,正是为了强化人物鲜明的思想性格特点,使其更具个性魅力。文学创作源于生活,更高于生活,所以,这样塑造的典型人物反而更真实生动、栩栩如生。
当然,塑造这样的人物完全离不开作者出神入化的语言。语言是文学作品的载体,毛泽东向来重视语言的艺术魅力。他认为《红楼梦》“作者的语言写得很好,可以学习他的语言,这部小说中的语言是所有古典小说中最好的一部”这的确是实事,求是的评价。
毛泽东曾对王海容评说《红楼梦》:“《红楼梦》可以读……你看曹雪芹把那个凤姐写活了,凤姐这个人物写得好,要你就写不出来。”把人物写“活”,就得用生动活泼的日常生活语言,这才是有生命力的鲜活语言,不刻板,不陈腐,不故作高深,不矫揉造作。把“凤姐写活了”,也就是说用鲜活的语言写出了一个性格独特的凤姐。这样的人物是“为了创造典型有意识地夸张或忽略某些方面”的典型人物,是特定时代共性与个性和谐统一的人物,共性使其真实,个性使其生动。
四、评价观--评价文学作品应一分为二,从不同角度进行评价
根据现实的政治需要进行评价毛泽东说:“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他评价《红楼梦》坚持了这两个标准,从而形成其独特的评价观,既能一分为二,从不同角度进行评价,又常常能结合现实,根据现实的政治需要进行评价。
例如对王熙凤、贾宝玉、林黛玉的评价,时而对他们评价极高,时而又贬斥多多。其实细看这些评价,都确实很中肯。这是毛泽东站在不同的角度看问题,能一分为二从不同侧面评价人物,而且常常又是紧密结合现实政治的需要来评价人物,结论自然不同。也许有人会机械地认为这是毛泽东评论文学形象时矛盾思想的流露,而笔者认为站在不同角度,一分为二地从不同侧面评价人物,恰恰是符合现实的复杂性的,是辩证唯物主义文学观的体现,而辩证唯物主义文学观正是现实主义文学观的本质表现。
1951年秋天的一个夜晚,毛泽东接见周世钊等几位湖南教育界人士时说:
你们都是干教育工作的,应该把青少年的体育运动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必须记住:有志参加革命工作的人必须锻炼身体,使身体健强,精力充沛,才能担负起艰巨复杂的工作。大家不是读过《红楼梦》吗?《红楼梦》中两位主角:一位是贾宝玉,一位是林黛玉。依我看来,这两位都不太高明。贾宝玉不能料理自己的生活,连吃饭穿衣都要丫头服侍,这种全不肯劳动的公子哥儿,无论如何是不会革命的!林黛玉多愁善感,常好哭脸,她瘦弱多病,只好住在潇湘馆,吐血,闹肺病,又怎么能革命呢?我们不需要这样的青年!我们今天需要的青年是有活力,有热情,有干劲和坚强意志的革命青年!今天的青年学生应该既有文化,又会劳动;既用脑,又用手;既能文,又能武的全面发展的新人。男的绝不要学贾宝玉,女的绝不要学林黛玉。
评价两位主人公“都不太高明”,“无论如何是不会革命的!”“又怎么能革命呢?”毛泽东完全是从新时代青少年的“体育运动”,从培养“全面发展的新人”的政治角度出发的。这是极富个性的评价,体现出毛泽东与时代紧密联系中所包含着特定阶级观念、政治观念的审美观和文学观。
其实毛泽东对贾宝玉的评价是很高的,但也是有变化的。早在瑞金时他就同冯雪峰讲过“贾宝玉是我国文学中的一个革命家”。
张闻天的夫人刘英1935年遵义会议后,到中央队当秘书长。她回忆说:“(毛泽东)对中国历史、小说熟极了,闲扯起来滔滔不绝,津津有味。《红楼梦》尤其读得熟。有一回他问我:‘……《红楼梦》里你最喜欢哪一个?’我说:‘当然是林妹妹了。’他连连摇头,说:‘《红楼梦》里最招人喜欢的是贾宝玉。他鄙视仕途经济,反抗旧的一套,有叛逆精神,是革命家。’”
1936年,丁玲说:“毛泽东曾做了一篇关于《红楼梦》的文章,有好几万字长。毛泽东说贾宝玉是可以转变成为一个革命者的。”1937年5月,毛泽东在抗大讲演中有这样一段话:“《红楼梦》的贾宝玉,要是在今天,就不是去当和尚,而是参加革命了。”
这几段对贾宝玉极高的评语,是毛泽东看到了贾宝玉思想性格的另一侧面,也是毛泽东在战争年代,结合现实,根据现实的政治需要对贾宝玉做出的客观评价。可见,他评价《红楼梦》坚持了艺术标准和政治标准这两个标准,形成其独特的评价观。紧密结合现实政治的需要来评价人物,往往有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而失去客观性,但毛泽东的评价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他往往抓住了人物的某个侧面进行评价,反而让人感觉到是很有见地的一分为二的客观评价。
笔者透过毛泽东的这些自成一家的解读、评论,简要分析了他深深影响过中国现代人的文学观。这文学观在他的一段眉批中有很形象的说明。1954年9月毛泽东读《红楼梦》第十九回《情切切良宵花解语》在回末空白处批道:
此回是一篇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情切切之段,是将两种人生观相互冲突的爱情,用花一样的语言切切道出。宝玉与袭人的相爱,两方面都是诚恳的,但他们性格不同,思想有矛盾,无法统一。在袭人看宝玉,是“性格异常,放荡驰纵,任性恣情”。而宝玉对袭人,也只能以“坐八人大轿”慰之。
意绵绵段与前段相反,这里是同一人生观相互结合的爱情,像玉一样的光辉,香一样的气氛,绵绵地喷发出来。宝玉与黛玉相爱,不仅是真挚的,而且建筑在思想一致的基础上,是任何人不能相比的。故宝玉说:“见了别人,就怪腻的。”他把黛玉比作“真的香玉”。而黛玉向宝玉说:“真正你是我命中的天魔星。”从袭人口中听到切切的箴言,故待之以八人大轿。从黛玉的身上,闻到绵绵的幽香,故比之优美的童话。
毛泽东的这段批语,也用“花一样的语言”形象地表现了他的现实主义文学观:现实观-反映现实,反映了封建社会逐步走向没落、新的思想正在酝酿时那个特定时代不同人生的爱情冲突;创作观-文学创作从小处着笔更有价值,《红楼梦》从小处着笔写出了那个时代不同人物的人生观;典型观-典型人物是特定时代的产物,读者自然从这满含情感的批语中读到了三位红楼人物的共性与个性。“此回是一篇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也正是毛泽东以自己对《红楼梦》的高度评价鲜明地表现了他现实主义的文学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