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在对《搜神记》文本内容深入分析的前提下,在总结、借鉴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究了魏晋时期儒释道三教思想对《搜神记》的影响。虽然《搜神记》中记述了很多神仙鬼怪的故事,但是很多故事自始至终都贯穿着儒家的三纲五常等传统道德观念,干宝将儒家的伦理纲常与道教的神仙思想结合到了一起。道教的阴阳五行说、养生之道等神仙道教思想深刻地影响着干宝《搜神记》的创作,使得作品中充满着神仙道术和灵异鬼怪的故事。佛教的“死而复生”“因果报应”的基本教义也让干宝在作品中极力宣扬业报轮回的思想,劝诫人们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关键词:干宝 《搜神记》 儒释道 影响
Influence of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thought on Soushenji of KanBao
Abstract: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Soushenji text analysis, based on summing up, on theformer research results, explores the influence of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in Wei and JinDynasties Taoism thought on SouShenJi. Although Soushenji describes many fairy tales andghost stories, but the stories from first to last through all the three cardinal guides and othertraditional moral values, ethics and the Taoism thought the Confucian thought of celestial beingtogether. The Taoist Yin Yang and the five elements, such as a way of keeping good healthimmortal Taoism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thought Soushenji creation, so that works full ofTaoism and the ghost story. The Buddhist “revive” “karma” the basic doctrine also let KanBao inthe works to publicize the yebaolunhui ideology, advising people to be responsible for their ownbehavior, receive rewards for one's virtuous deeds Evil is.
Keywords: Kan Bao ;Soushenji ;Buddhism Taoism immortal ;effect
目 录
一、引言
二、儒家思想对《搜神记》的影响
(一)传统美德
(二)天人感应
三、道教思想对《搜神记》的影响
(一)阴阳五行
(二)养生之道
(三)道教神仙
(四)道教法术
四、佛教思想对《搜神记》的影响
(一)死而复生
(二)因果报应
五、志怪小说发展繁荣的社会原因
(一)道教的盛行
(二)佛教的盛行
(三)清谈、闲谈的盛行
(四)史传及文学创作的活跃与进步
六、结语
参考文献
一、引言
魏晋时期,佛道两教深受人们追捧,产生了许多神仙方术的故事,志怪小说也相应地发展起来。由于当时的思想束缚很松,所以儒释道三教齐鸣,很多文人或多或少都受到了这三教的影响。《搜神记》就是在此背景下写成的。干宝(?-336年),字令升,新蔡(今属河南)人。东晋时期的史学家,志怪小说的作家和创始人。干宝年少时即博览群书,尤其对阴阳术、占卜术等典籍感兴趣。后来因为才干出众,最后官至散骑常侍。
《搜神记》记录了许多奇闻异事,共有四百多篇。很多内容都与古代人民的思想情感有关,并开创了古代神话小说的先河。作者在《自序》中称,“及其着述,亦足以发明神道之不诬也。”。其目的就是想通过整理前人着述,说明鬼神的现实存在性。所以说,《搜神记》中的许多故事是来自于民间传说,还有一部分来自于神话传说。故事的主角也各不相同,有人、鬼、妖、神仙等等。文章构思巧妙,想象大胆,具有浪漫主义色彩。自古以来,我国就是比较信仰鬼神的,所以从夏商周至元明清,记载神鬼传说的典籍有很多,例如《楚辞》、《淮南子》,而《搜神记》可以说是鬼神传说故事的集大成者。
《搜神记》内容十分丰富。内容上,既有方士的神通,又有神仙的仙术;既有阴阳五行错乱所致的妖怪,又有符命讥纬所显示的天命;既有匪夷所思的灾异瑞应,又有自成系统的占梦解梦;既有德艺精诚的神奇境界,又有五气变化所致的反常人物;既有颇具灵性的奇物异产,又有闻所未闻的亦人亦怪;既有跨越生死、沟通人鬼的传闻,又有机智沉稳、降妖除怪的异事。
纵观《搜神记》全书,其中不仅有道教的思想,还有佛教、儒家的思想。本文就儒释道三教对《搜神记》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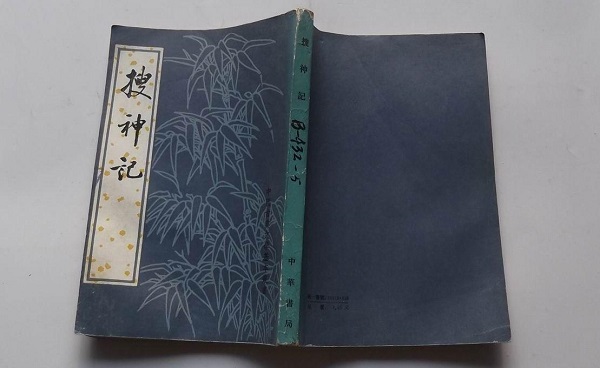
二、儒家思想对《搜神记》的影响
魏晋时期,战争频仍,君臣伦理纲常崩坏,文人、平民纷纷转向佛教、道教,希冀通过虚幻的精神来麻痹自己。为此,儒家思想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但是,儒家思想毕竟影响深远,经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就一直处于正统地位,人们思想中的仁义礼智信观念可谓是根深蒂固,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改变的。干宝出身官宦家庭,从小就受到了儒家文化的熏陶,虽然《搜神记》描绘了很多神仙鬼怪的故事,但是这些故事自始至终都贯穿着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等传统伦理观念。干宝在《搜神记》中将儒家的伦理纲常与道教的神仙思想联系到一起,在作品中可以找到很多具体的例子来证明这一点。
(一)传统美德
人之所以“最为天下贵”,就在于“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为人之根在于“孝”,而在人的最基本品质中,最为古人所称颂者,莫过于仁义礼智信了。干宝《搜神记》中第十一卷就集中讲述了关于儒家传统美德的故事。
首先是孝。孝顺自古以来就是人之根本,俗话说“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如果一个人有仁孝之心,那么天下所有不能做的事情,都是不忍心去做,所以孝顺是第一位的;一个人一旦有了邪念,那么一生中极不愿做的事情,都不是难做的。儒家的《孝经·开宗明义》指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本书中有许多表现孝顺的篇目。例如《曾子之孝》中,曾子跟随孔子在楚国游历,突然心中动了一下。回家后问母亲这个现状,母亲说:“我想念你了,所以咬了自己的手指。”孔子曰:“曾参之孝,精诚万里”。由此可见曾子孝心之精诚。和曾子相似的周畅,也是对母亲的思念有所感应的:
周畅每次出门,如果母亲需要周畅服侍,就咬自己的手指,周畅觉得自己手指很痛,就会回家了。又如《王祥孝母》中的王祥,生性非常孝顺。虽然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些事情可能有些匪夷所思了,但是这也正说明了当时人们对于孝心的看重。与王祥故事相似的还有很多,例如《王延叩凌求鱼》、《楚僚卧冰求鲤》,这三个故事都充分说明了孝心真的可以感天动地。在干宝的思想中,儒家的孝道始终是排第一位的,上面所列举的故事明显是干宝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结果。干宝试图告诉人们,只要能够至孝,就会感动上天,就会得到好报。
孝顺的故事还有很多,如《蛴螬炙》中的盛彦,《蚺蛇胆》中的颜含,《郭巨埋儿》中的郭巨,《刘殷居丧》中的刘殷,《王裒守墓》中的王裒,他们为后代的孝子贤孙树立了永久的典范。
如果说孝子贤孙的人物让人们敬佩,那么贤妇烈女带给我们更多的是感动。最着名的莫过于《东海孝妇》了,元代的散曲大家关汉卿的《窦娥冤》就是据此改编而成的。《东海孝妇》讲的是汉朝东海郡有一名叫周青的孝顺媳妇,对婆婆十分恭谨。婆婆自认为年岁已大,不想长久地拖累儿媳妇,遂上吊自杀。婆婆的女儿却认为是周青杀了自己的母亲,遂告官。官府抓住了周青,并严刑拷打逼供,孝妇周青忍受不住酷刑,于是屈打成招。孝妇死后,东海郡发生了大旱,三年都没有下雨。后任太守到职,有人说孝妇不应该死,是前任太守冤枉杀了她,大旱原因差不多在这。新任太守立刻亲自祭奠孝妇,天立刻下起雨来,这一年庄稼丰收。东海孝妇的故事真可谓是感天动地了。和《东海孝妇》相似的故事是《乐羊子妻》和《犍为孝女》。在儒家思想中,女子要遵从“三从四德”,“三从”是指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是指德、言、容、功。这些都是对女子的道德要求。从先秦开始,对女性的教育已经开始。及至汉代,儒家女性教育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尤其是以刘向的《列女传》和班昭的《女诫》为代表。在封建社会中,绝大多数的人都认为女性是男性的附属品,都应该严格遵守“三从四德”等伦理准则,干宝也不能免俗。上面所列举的贤妇烈女的故事,也是干宝受到儒家女子思想影响的具体体现,干宝借《搜神记》来宣扬这一伦理准则,希望人们都可以学习模仿,这样社会才能和谐。
其次,《搜神记》也有手足之情的描写。例如《艘衮侍兄》中廋衮的兄弟之情。《死友》中的笵巨卿朋友之情。虽然描写的场景不多,但却是精确地把握住了精髓——亲兄弟之间的友情,好朋友之间的信任。
(二)天人感应
天人感应思想源于《尚书·洪范》:“肃,时寒若····乂,时旸若”,认为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态度会影响到天气的变化。孔子作《春秋》言灾异述天道,到西汉时,董仲舒据《公羊体》集天道灾异说之大成。在董仲舒思想中,天人感应是其核心思想。天人感应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1、灾异遣告说,自然灾害和统治者施行的政策有关。如果统治者施行暴政,天就会出现各种灾难现象;如果统治者施行仁政,天下就会太平。2、“天人同类”说,认为“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而天之阴气亦宜应之而起。”干宝也受到了儒家天人感应的影响,他在《搜神记》中运用天人感应来解释很多福瑞灾异的现象。
《搜神记》中有一部分内容集中记录了一些与祸福灾难异有关的各类奇闻异事。就笔者所阅的《搜神记》中,有 4 卷内容是与天人感应有关的。《搜神记·卷六》,本卷记述了夏朝至三国期间各种妖孽怪异之事。干宝继承前人之说,引用《五行志》与京房的《易传》,以阴阳五行之消长来解释世间万物的变异,以及其中蕴含的祸福吉凶。如《论妖怪》中,“妖怪者,盖精气之依物者也。气乱于中,物变于外。形神气质,表里之用也。本于五行,通于五事,虽消息升降,化动万端,其于休咎之症,皆可得域而论矣。”他认为,各种灾异与妖怪是精气依附到物体上,充斥弥漫于物体内部,物体的外表就会发生变化。精气是源于金木水火土五行,即内因的消长;貌、言、视、听思五事即外因则是其外在表现。五行之道壅塞或者变异,就会有妖异兴起或出现。
魏晋时期,社会动乱、民不聊生,各种怪象层出不绝,干宝就是用这些怪异现象来影射社会。在《论山徙》中,山体移动,解释为:“山默然自移,天下兵乱,社稷亡也。”又如《龟毛兔角》、《马化狐》、《人化蜮》、《马生人》、《女子化为丈夫》、《五足牛》、《马生角》等等,这些怪异的、不正常的现象,都预示着灾难。由于当时的统治者大量地迫害文人名士,使得很多文人敢怒不敢言,只能投身到其他领域。干宝以一个史学家的身份来记录这这怪异现象,从侧面来反映的那个当时的社会现状。干宝借助儒家天人感应思想来解释这些怪异现象,这都体现了儒家的“仁政”思想,同时也体现了干宝的民本思想。
《搜神记·卷七》主要记述了与福瑞灾异有关的各类奇闻异事。如长者两只脚的老虎(《两足虎》)、死牛头会说话(《死牛头语》)、马匹生角(《辽东马》)、男女同体(《一身二体》)、女人逐渐变成男人(《安丰女子》)、狗会说人话(《狗作人言》)等等,所谓反常即妖,这些不正常现象都预示着自然灾异与社会动荡。作者记述这类故事时,通常先记述怪异的事情,然后再根据《五行志》和《易传》等典籍给出合理的解释,这样才能显示出这些故事的合理性。
《搜神记·卷八》主要记述与历代王朝兴替有关的符命谶纬之事。从上古时期,人们就把王朝兴替与天命联系起来,王朝的建立者也以奉天命而自居,也就是“君权神授”了。
《尚书·召诰》云:“有夏服天命。”《左转》僖公十六年,称“殷人尊神”。周人虽然重视民意,认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仍然要借天命来申诉民意。既然王朝的兴衰隆替皆由天命,因而藉天命所示现的各种迹象,即可预示王朝的更替。因此,与王朝更替相关的瑞应符命相继出现。例如《舜得玉历》中,虞舜在耕种时候得到了玉历,他认为这是上天的旨意将天下交给自己。又如《汤祷桑林》中,商汤剪掉自己的指甲、头发,把自己当作献祭的祭品,干旱七年的都城下起了大雨。更有神仙托梦、星化为人等方式,不管是什么方式,这些都论证了新王朝的建立者都是奉天命、替天行道,君权神授,具有合法性。干宝作为当时封建社会的官员,在他的思想中,儒家的三纲五常、君臣观念也是根深蒂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些鼓吹封建统治者合法地位的准则也深深地影响到他。
由于当时的社会动荡不堪,君不再是君,臣不再是臣,伦理纲常遭到严重破坏,这使得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极力宣扬这种思想,试图让人民相信君主的权威是不可挑战的,要做好君主的臣民,否则君臣失位、长幼失序、伦理失常,那么这个社会也就不再和谐,人民也不再会有好的生活。
《搜神记·卷九》也是记述了与瑞应灾异相关的故事。比如前面的《应妪见神光》中,汝南应妪白天见到神光后,子孙兴旺显赫。《张颢得金印》中,梁州牧守张颢得到金印后官至太守。《张氏传钩》中长安张氏得到金钩后而富贵,《何比干得符策》中何比干得到符策而子孙致宦。至于后面的一些故事,像狗咬鹅、狗戴帽着衣上房、狗衔衣、炊饭变成虫子等等怪诞不经的事情出现时,意味着主人要遭受各种灾祸。以上的故事都表达了一种“富贵由天,生死由命”的观点。
以上所论述的内容,都是从儒家思想对干宝《搜神记》的影响这个角度来阐述的。儒家的三纲五常、天人感应等观念,都深刻地影响着干宝对《搜神记》的创作。虽然从表面上,大家看到的是一个充满着鬼神的奇异世界,但是如果再深入地探究的话,大家不难发现,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始终贯穿着全文,干宝在《搜神记》中将儒家的各种伦理道德观念与道教的神仙思想联系到一起,从而给大家展示出了这副奇异的画面。
三、道教思想对《搜神记》的影响
道教盛行于汉魏六朝时期,对于当时人们的影响很大。人们都希冀追求长生不死,能从宗教中寻找光明。
众所周知,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政治黑暗腐朽,统治者之间相互争权夺利,党同伐异,杀戮异己,大批的文人名士成为政治中的牺牲品。在这种高压统治下,文人们或佯狂任诞,或放浪不羁。如果文人们要为这种风流倜傥、自由放浪的生活寻找理论依据的话,道教是最符合他们意愿的。传统儒家思想强调的是修身治国平天下,要积极地入世;而佛教强调的是注重来世,用来世来偿还今世的债;只有道教,既能注重人生哲理,又能注重养生;既能凸显士大夫的宁静淡远,又能使其获得现实享受,更有一些奇闻异事,给平淡的生活带来一丝新奇。所以说,道教是当时最为人们所追捧的精神寄托。当一种宗教思想深入人心的时候,就会被文人们用文学作品表现出来。干宝就是深受道教思想影响的文人之一,他做此书的时候就是为了“及其着述,亦足以发明神道之不诬也。”可以说神仙道教的思想占据了此书的绝大多数内容,足以感受到道教对干宝的影响了。
(一)阴阳五行
《老子》第四十二章云:“道生一,一生二,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阴阳一般是阴阳两种气,二者相互交流、交合,然后化生万物,并引起万物的变化。
同时,阴阳也是既对立又统一的,是万物形成和发展变化的根源。古人认为宇宙万物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变化生成的。和气所成即为圣人,浊气所成即为怪物;元气的性质决定了事物的属性,元气的流动变化必然带来事物属性的改变。干宝也受到了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搜神记》中就有很多具体的故事。例如《搜神记·卷十二》中所记述的故事,都是因元气的变化感应而发生的种种奇异故事,其中既有各种精怪如愤羊、犀犬、庆忌,也有能夜间匪头的落头民、可化为虎的人类,专门抢美女的怪物,人鸟之间的变化的越祝之祖,还有能致人毙命的刀劳鬼、鬼弹及各种蛊毒。
“阴阳五行学无论是在先秦,还是在两汉,都是披着经学、道家或道教的外衣出现的。除了在邹衍时代它有过昙花一现的辉煌外,似乎从来没有真正独立过。因此人们常常忽略了它对艺术,特别是对文学的影响。一些讨论也多是通过形而上的方士进行,而较少从形而下的方面仔细考察。应当说,阴阳五行思想作为一种各家共用的方法论、表述体系,足以成为时代文化的内在结构和时代精神的集体意识。”通过这句话,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到阴阳五行说在当时的社会上的地位。从先秦开始,阴阳五行说就已经开始崭露头角,直至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过董仲舒的发展,阴阳五行说开始和儒家思想结合起来,使经学走上了神学的发展之路。从那以后,阴阳五行说成为了当时文人名士的共同信仰,干宝也不例外。在《晋书·干宝传》中是这样描述干宝的:“性好阴阳术数,留思京房、夏侯胜等传。”由此可见,干宝对于阴阳五行说确实是深信不疑的,再加上当时的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可以说是朝生暮死,人们对于生死也就越来越看重。明代胡应麟曾说过:“魏晋好长生,故多灵变之说。” 所以,当人们无法解释死亡的时候,就只能借助阴阳五行说来说明了。这样,干宝的《搜神记》中就会有大量这样的故事出现,这也是干宝潜意识中思想的表现。
(二)养生之道
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动荡,让敏感的文人们感叹人生短促,生命脆弱,生死主题自然而然成为当时的主流思想,在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中有已经出现了很多这类主题,如《薤露》、《蒿里》。魏晋之后,生死主题也越来越成为主流。例如“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短歌行》)。文人们对待人生的态度有四种:1、提高生命质量,即及时建立功勋,流芳百世;2、增加生命长度,即追求长生不老;3、增加生命密度,即今朝有酒今朝醉,醉生梦死;4、态度,即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态度,例如陶渊明那种“采菊东篱下,悠然现南山”的隐逸生活。
道教追求的是肉体的不死,为了能够确立神仙信仰,不仅要大量宣扬各种神仙,还要宣扬如何成为神仙,这就使得修仙不再是缥渺无踪的事情了,而是有了具体的途径,在道家看来,服食是最便捷的途径了。道教服食药物分为草木之药和金石之药。按照葛洪的看法,草木之药的功效在于“救亏缺”,亦即治病补病,而金石之药的功效在于不死成仙。
干宝《搜神记》中也有很多服食的故事。例如第一卷中的《赤将子举》“不食五谷,而啖百草华。”《偓佺采药》:“好食松实”;《彭祖仙室》:“常食桂枝。”也有一些服食金石之药的故事。这些故事都体现出了干宝对于道教的养生之道的看重,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的因素,朝生暮死的下场使得人们不得不去看重生命;另一方面也是干宝本人受到了道教神仙思想的影响,希冀通过服食仙丹百草,能够羽化升仙、长生不死,这也是每一个人追求的目标。
(三)道教神仙
嵇康在《养生论》中指出神仙的确实是存在于现实世界的:“夫神仙虽不见目,然记籍所载,前史所传,较而论之,其有必矣!”道教的核心思想就是承认神仙的现实性。
《搜神记》中关于道教神仙的描写也有许多。例如《搜神记·卷一》,所记述的都是晋代以前的神仙术士,从传说中的神农到三国时期吴国的吴猛,其中神农、赤松子、宁封子、彭祖、师门、葛由等相传是远古及夏商周三代时期得道的神仙,能够呼风唤雨、骑龙驾虎、长生不死。还有春秋战国时期的琴高、陶安公,汉代淮南王刘安。此后的刘根、王乔、蓟子训、汉阴生、左慈、于吉、介琰、徐光、葛云、吴猛等人则是修道求仙的术士,能够役使鬼神,羽化飞升,腾挪变换,不受形神之限。卷一所描述的神仙中,只有几个是上古传说人物,如《神农鞭百草》中的神农,《雨师赤松子》中的赤松子,“服冰玉散,以教神农。能入火不烧”,“随风雨上下”,《宁封子自焚》中的宁封子。他们这几个神仙皆是来自于远古神话传说。而后面大多数描写的都是一些得道成仙的凡人。例如《彭祖仙室》中的彭祖,“彭祖者,殷时大夫也。姓钱,名铿”“历夏至商末,号七百岁”。《葛由乘木羊》中的葛由,《王乔飞舄》中的王乔,《左慈显神通》中的左慈。还有于吉、介琰、徐光、葛云、吴猛等等,都是从凡间修道成仙的人。从上面可以看出,干宝所描写的仙人中,没有那种令人敬畏的绝对力量,神话故事中的神仙也不多,有的大多数是平易近人的神仙,他们大多数只是凡人得道成仙的。这样,就给人们一种无限美好的幻想,即有一天自己也可以得道成仙。在当时那么黑暗的社会中,这种幻想给了人们活下去的希望与勇气,如同给了迷失在黑暗中的人们一盏指路明灯,指引人们继续走下去。
《搜神记》中除了男神仙外,还有一些女神仙的描写。道教认为,“道”是万物的本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阴阳要和谐,既要有阳气,也要有阴气;社会中,既要有男人,也要有女人。老子也是一种主阴的思想,女性形象在老子的思想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干宝也多少受到了一些影响,虽然干宝提倡女子要遵从三从四德的道德伦理纲常,但是在他的潜意识当中,对于女性神仙的观念还是比较开放的。
所以《搜神记》中对于女神仙记载,一般都是女神仙与凡人的恋情故事。如《搜神记·卷一》中最后几则故事《园客养蚕》、《董永与织女》、《杜兰香与张传》、《弦超与神女》。
这几则故事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仙女奉命下凡,帮助凡人,但是在仙凡之间很少涉及感情问题。如《园客养蚕》中的男子,长相英俊,当地有很多人都想把女儿嫁给他,但园客始终没有娶妻。“尝种五色香草,积数十年,服食其实。”忽然有五色神蛾,飞到了香草上面。夜晚就有神女来帮园客养蚕,蚕丝缫完后,神女和园客一起升仙而去,没有人知道到哪里去了。又如《董永与织女》,织女仅仅因为董永至孝,天地就让她下凡嫁给董永并帮助他还债。还完债后,就“凌空而去,不知所在。”。
另一类女神仙则与第一类有很大不同。她们刚开始也是奉天帝命令下凡帮助凡人,但是最后却日久生情,与男主人公产生了真感情。如《弦超与神女》中,天帝因为弦超早年失去父母,同情他的孤苦伶仃,所以令神女成公知琼嫁给他。直到有一天,弦超泄露了神女的秘密,使得神女不得不离去,临走前,知琼对弦超说:“我,神人也。虽与君交,不愿认知。而君性疏漏,我今本末已露,不复与君通接。积年交结,恩义不轻,一分别,岂不抢恨。势不得不尔,各自努力”。从上述的描写中可看出他们之间是有真情的,虽然最终还是要离开,但是相较于第一类神女来说,已经不是那么不近人情了。《杜兰香与张传》中女仙杜兰香下凡嫁给张传,也是自称“阿母所生,遣授配君,可不敢从!”同时也吟诗警告张传“从我与福俱,嫌我与祸会。”可惜两人情缘未达,若兰香所言“本为君作妻,情无旷远。以年命未合,其小乘。”
《弦超与神女》和《杜兰香与张传》这两个故事有许多相似之处:首先,仙女都是奉天帝的命令下凡,杜兰香是“阿母所生,遣授配君,可不敢从”,知琼是因为天帝同情男主人公的孤苦伶仃,所以被命令嫁给男主人公。 但是和织女的下凡又有点不同,虽然同是奉天帝命令下凡,织女下凡是因为男主人公的至孝感动上天;而知琼与杜兰香的下凡只是单纯的嫁给男主人公,其中已经不包含什么道德伦理的因素了。其次,仙女的形象较以前的形象更加丰满,织女的形象是普通的家庭妇女,会家务、会女工。而知琼与兰香则是作为才女的形象出现的,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神仙的描述,也从侧面表达了干宝的社会理想。在当时的那个社会动荡的年代,普通百姓纷纷逃到深山等人迹罕至的地方,以此来躲避战乱。他们希望在这些地方会有神仙,要么会给自己带来无数金银珠宝;要么赐予自己仙丹,帮助自己得道成仙;要么就是有女神仙哀怜自己的孤苦,从而嫁给自己。人们最基本的需求就是穿衣吃饭,能有一个安定和谐、男耕女织的生活,因此,就产生了像织女这样的女性神仙。虽然只是几个简单的神女下凡的故事,但是却表现了当时人们对于理想生活和美好爱情的向往。
(四)道教法术
法术是道教立教的根基之一,一般都是神仙才会这些法术。《搜神记》中也有许多道教的幻化之术。例如《崔文子学仙》中的王子乔。“子乔化为白霓,而持药与文子。”王子乔化身为白霓,带着仙药送给崔文子。《淮南八老公》中的八个老人可以变化为小孩,以此来展示自己的仙术。《王乔飞舄》中王乔的鞋子幻化为飞鸟,《左慈显神通》中左慈“少有神通”,能用铜盘钓鱼,能用极短的时间到蜀去买姜,又能偷窃酒肉,被发现时又能遁地隐匿,篇末老子曰:“吾之所以为大患者,以吾有身也;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哉?”这体现出了道教幻化之术的奇妙。《于吉请雨》中的于吉被孙策杀后,鬼魂经常来找孙策,孙策每次单独坐在房间内,就感觉于吉就在他旁边。《介琰隐形》中介琰“能变化隐形”,后来孙权想学他的法术,但是介琰没有教他。孙权大怒,下令把介琰捆绑起来,让士兵拿弓箭射他。箭矢射出去后,绑的绳子还在,却不知介琰到哪里去了。从上面几个故事来看,道教的法术具有极其神秘的色彩。从道教立教以来,无数的人都想学习道教的法术,既能飞天遁地,又能潜行隐匿,还能变化身形,但最终都是铩羽而归。作为一个有神论者,干宝也对道教的法术非常感兴趣,但也只能从别人口中得知这些法术,并没有亲眼见过。干宝通过对这些道教法术的描写,从侧面表达了自己愿望——学习道教法术。在当时的那种社会情况下,如果能学会一项道教法术,就等于多了保命的技能,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人痴迷于道教法术的原因了。
预言吉凶也是道教的特征之一。《搜神记·卷三》集中记述了汉晋时期的易学、卜筮和一些能为人预知吉凶、消灾祛魅的方术之士。其中,段翳、许季山及其外孙董彦兴能够通过占卜术为人们预知吉凶,郭璞还可以撒豆成兵,投符除魅。其中,管辂对神明与妖异的论述比较值得关注,他指出精神纯正者不会受到妖怪的伤害,万物变化的规律不是道术所能阻止的。在《管辂助颜超增寿》中,颜超命中将要死掉,颜超的父亲连忙去求教管辂,管辂告诉了他方法:你明天到麦地南边的大桑树下面,那里会有两个人在树下下围棋,你可以一边斟酒,把肉脯放在前面,任由他们吃喝。如果他们要质问你,你只要拜倒,不要说话。颜超按照管辂的话去了那里,最后不仅幸免于命,而且还增长了寿命。《淳于智杀鼠》、《淳于智卜居宅》、《淳于智卜祸》、《淳于智筮病》这几篇都描写了淳于智高超的占卜之术。《童彦兴》桥玄家“东壁正白,如开门明”,童彦兴占卜后显示为飞黄腾达的征兆。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占卜算卦等巫术活动,而道教的预知吉凶、消灾祛魅也是从那里演变过来的。
预言术只是其中一小部分,道教最大的能力是消灾祛魅。由于当时的生产力低下,很多的疾病、灾难都得不到合理的解释,人们就把希望寄托在了道教的法术之上,希冀能通过道教的法术来避免灾难。
四、佛教思想对《搜神记》的影响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五篇指出:“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由此可见,佛教的传入与发展是志怪小说发展的主要动力。
在《搜神记》中,有两则故事与佛教有直接关系。一则是《搜神记·卷三》中的《天竺胡人法术》:“晋永嘉中,有天竺胡人来渡江南。其人有数术:能断舌复续、吐火。”由此可以推断,这个天竺胡人也应该是个佛教徒。另一则是《李通》:蒲城的李通死后,见到沙门的法祖正在给阎罗王讲解《首楞严经》,又看到了道士王符,正在向法祖忏悔,请求原谅,但是阎罗王没有同意。虽然只有这两则故事是与佛教有直接关系的,但是我们不能就此做出佛教思想对干宝《搜神记》影响很小的结论。通读全文,我们可以在很多地方找到佛教的影子,可以看出干宝确实受到了佛教思想的影响。佛教的死而复生、因果报应等观念深刻地影响到干宝《搜神记》的创作。
(一)死而复生
“佛教的基本教义是三世轮回、死而复生、因果报应、地狱之说。”认为人生包含前世、现在和未来三世,佛教用教义和轮回的法则来掩饰真实的矛盾。佛教认为人灵魂不灭,能死而复生。干宝的《搜神记》就是因为感念他父亲宠幸的婢女和他哥哥的死而复生而作。
《搜神记·卷十五》则集中记述了一些死而复生的奇闻异事。例如《王道平妻》中,王道平不仅深情唤出了“乖隔幽途”的父谕神灵,还因“精诚贯于天地”而使其得以再生;《河间女》的复活也与此想类似。自古有言“生死异路”,如何才能让死者复生?“精诚之至,感于天地”,人与人之间至诚的感情成为唤醒死者的有效方式。另外贾文和、李娥、贺瑀、柳荣等人的复活后对其死后经历的口述,以及史姁、戴洋复活后所具有的神通,则展示了人们对另一个世界的遐想。
《搜神记》中的死而复生故事,明显受到了佛教的影响,是佛教“因果报应”和“三世轮回”思想的产物。即使是在当代,死而复生也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了,更别提干宝的那个时代了。为什么干宝还要记述这些故事呢?笔者认为这是干宝表达自己理想的一个方式。在他的那个时代,人命如草芥,朝不保夕,干宝就是想通过佛教的三世轮回和死而复生来安慰人们,希望人们能够忍受现世的痛苦,不断地积累阴德,然后才能在未来的世界中得到好报。有一些故事也表达了干宝对于恋爱自由和美满婚姻的向往,如《河间女》。
兵役制、父母的包办婚姻,是造成这对恋人阴阳分隔的罪魁祸首,但是佛教的死而复生给了他希望,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获得了圆满的结局。后世作品中还有很多死而复生的故事,《聊斋志异》中就有很多死而复生的故事,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当属汤显祖《牡丹亭》中的杜丽娘还魂了。
(二)因果报应
俗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佛教的教义指出:“人生的命运、前途完全受因果律的支配和主宰,善因得善果,恶因得恶果。”干宝也深受因果报应说的影响,《搜神记·卷七》集中收录了一些因果报应的观点,主要是野兽报答人类恩情的故事。例如《苏易助虎产》讲的是一个叫苏易的夫人,帮助老虎接生,久了难产将死的母虎。后来,雌虎玩为了报恩,多次送野兽的肉到苏易家。《玄鹤衔珠》中哙参救了一只被人射伤的玄鹤,后来玄鹤为了报答哙参,衔来明珠来报答他。《隋侯珠》中的隋侯救了一条受伤的大蛇,过了一年,蛇衔着一颗明珠来报答隋侯。除了龙虎蛇犬这一类自古以来就具有灵性的动物之外,像蚂蚁、蝼蛄这类小动物,也是能救人于危难。当然了,“恶有恶报”。《于吉》中的孙策杀掉了于吉,患上了心魔,最终“疮皆崩裂,须臾而死。”又如虐杀猿猴致使母猿肝肠寸断的人,全家遭遇瘟疫而死。
干宝借佛教的因果报应论,阐述了一种新型的人生哲学,即一种强调通过自己的行为来改变自我命运的新的理论。因果报应学说确立了世间一切事物的关系,每个人不同行为必将会给自己带来不同的结果,不仅会影响到现世的生活,还会影响到未来世界的生活,这就极大地约束了人们的不好的行为,使得人们能够积极向善。这就极大地突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生活的好坏,取决于自己的行为,不是命运的安排,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五、志怪小说发展繁荣的社会原因
(一)道教的盛行
道教是我国固有的传统宗教,产生于东汉中叶,盛行于魏晋时期。它描绘的公平、自由、繁荣的美好场景,提出的“乐善好施”的道教教义,强调的尊重天地和忠孝、仁慈的准则,受到了当时人们的追捧。道教是神仙思想和种种方术的混合物。他所鼓吹的长生不老、顿悟升仙的思想很是迎合当时腐化奢靡的统治阶级以及一部分陷入人生苦闷、希望得到解脱的士大夫的心里,更是成为了穷苦百姓的救命稻草。
这一时期,道教的神仙思想影响社会各阶层,不论是贵族帝王,还是普通百姓;不论是方士群体,还是文人名士,他们对于道教神仙思想的尊崇,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帝王贵族大多追求长生不死。例如曹操就希望延长寿命来建功立业,他写下了很多关于想长寿的诗,例如“思得神药,万岁为期”(《秋胡行》其二),“交赤松,及羡门,受要秘道爱精神。食芝英,饮醴泉,柱杖桂枝佩秋兰”(《陌上桑》)。又如三国孙权,他就比较喜欢神仙道术,史书载:“权与张昭论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语神仙,俗岂有仙人也!’权积怒非一,遂徙翻交州。”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方士人数众多,他们各怀绝技,占卦卜筮、变形隐遁、降妖除魔、治病祛灾,几乎无所不能,其事迹在社会上广泛流传,许多方士成为志怪小说的主角。较着名的有左慈、管辂、于吉、郭璞等人。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政治黑暗腐朽,统治者之间互相争权夺利,党同伐异,杀戮异己,大批的文人名士成为政治斗争中的牺牲品。《晋书·阮籍传》说:“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在这种高压统治下,文人名士或佯狂任诞,或醉心于玄学,企图通过种种看似怪异的方式苟全性命于乱世。“王瑶先生说:‘我们念魏晋人的诗,感到最普遍、最深刻、最能激动人心的,便是那在诗中充满了时光飘忽和人生短促的思想与情感。’”从汉代末年的《古诗十九首》开始,人们对死亡的感叹和忧伤就已经大量涌现,例如“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人生处一世,奄忽若飙尘;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以上的诗句,均表现出人生短暂、生活艰难、欢乐少有、忧愁长多的人生感叹。
干宝就是在此道教盛行的氛围下才写成了《搜神记》。虽然并没有史料记载干宝是一个道教徒,但是从他平时所接触的人物、生活氛围来看,干宝应该是一个具有道教信仰的文人。《晋书·干宝传》中就是这样描述干宝的:“性好阴阳术数,留思京房、夏侯胜等传。”
从这句话我们可见看出干宝的许多阴阳五行的思想应该源于京房和夏侯胜。干宝平时所交往的人也大多数是道教徒,例如葛洪和郭璞。干宝就是因为葛洪的道术道法成就很高,多次举荐他担任官职。干宝作此书的目的也是为了“发明神道之不巫”,他相信世界上是有鬼神存在的。
(二)佛教的盛行
“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国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这是佛教初次传入中国的标志。佛教的传入和佛经的大量翻译,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在社会各个阶层各个领域都受其影响。佛教得到历代统治者大力提倡,三国的孙权、孙皓、魏明帝、晋元帝、明帝、孝武帝及司马道子,宋文帝、萧子良,梁武帝、简文帝、元帝,陈武帝、后主,都崇拜佛法。其中梁武帝更是一名忠诚的佛教徒,曾经四次出家,讲经着说。
佛教对文学的影响,最大的反映是对文人的影响。正如上面所说,历代统治者对于佛教都是颇为尊崇,所以,上行下效,迎合时主,文人与佛教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尤其是佛理玄奥精微,很多适合知识分子的口味,正好被文人援入清谈。我们可以举出很多着名文人,如曹植、孙绰、许询、王羲之、谢灵运、颜延之、宗炳、王融、江淹、沈约、庾肩吾、徐陵、魏收、颜之推、薛道衡等等。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序》云:“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屣;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于是招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山之姿,竞模山中之影。”信佛风气之盛,可见一斑。
不仅是帝王贵族、文人名士对佛教尊崇,普通百姓对于佛教更是狂热崇拜。魏晋时期,战乱不断,民不聊生,老百姓是最大的受难者。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普通百姓更需要精神上的慰藉。而佛教所宣扬的“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的思想,迎合了当时的人们。
干宝虽说没有受到佛教思想很深的影响,但是在当时那种人人谈玄佛的时代,他也是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干宝《搜神记》中的佛教思想我们在上文已经讲过,就是“死而复生”和“因果报应”。对于干宝作《搜神记》的目的,也是众说纷纭,首推鲁迅的“发明神道之不巫”;第二个原因是干宝本人就喜欢阴阳五行之术;第三个原因当时志怪小说盛行,形成了志怪小说热;最后一个原因就是干宝因为感念其哥哥的死而复生和父亲宠爱的婢女复活而作,这里明显是受到了佛教的影响。
(三)清谈、闲谈的盛行
魏晋名士好清谈,这是名士风流的表现,清谈又称清言。大体有两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品评人物,这与“九品中正制”密切相关。例如《世说·品藻篇》载:“抚军问孙兴公:‘刘真长如何?’曰:‘清蔚简令”。’王仲祖如何?‘曰:’温润恬和‘。“另一个事谈论老庄哲学即所谓的玄理,东晋之后有掺杂佛理。谈论者相互辩论,清虚玄远,故此又称玄言。
当然了,清谈的主题除了玄佛等各种主流思想,为了增加清谈的乐趣,自然要掌握很多奇闻异事,这样才能有更多的谈资,以显示自己的博文洽见。例如《抱朴子·疾谬篇》云:”不才之子也,若问以《坟》、《索》之微言……曰:’杂碎故事, 盖是穷巷诸生章句之士,吟咏而向枯简,匍匐以守黄卷者所宜识,不足以问吾徒也‘。“ 大体的意思是说,大多数有才华的士大夫喜欢掌握一些奇闻异事来显示自己的博闻强识。在这种影响之下,很多关于鬼神的故事便在士大夫当中流传,从而谈论神怪成为风尚。
干宝就是因为博闻强识而显名于后世,他掌握了大量的奇闻异事,这也是当时风流名士的共同特征。因此,在当时那种清谈氛围浓重的时代,干宝很受王导器重,曾好几次出任着作郎,这也为他创作《搜神记》奠定了基础。
(四)史传及文学创作的活跃与进步
魏晋南北朝的历史着述和文学创作非常兴旺。曹丕《典论·论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促使文章事业的繁荣。学者、诗人、批评家层出不穷,诗赋、史传、碑铭、杂文等各类作品更是不盛枚数。萧统在《文选·序》中云:”词人才子,则名溢于缥囊;飞文染翰,则卷盈乎缃帙。“其中,史传和文学创作对小说的影响颇大。
魏晋以来,各朝颇为看重史事,纷纷设置着作郎、修史学士、秘书郎等史官,良史辈出。《史通》卷一《史官建置》云:”若中朝之华峤、陈寿、陆机、束皙,江左之王隐、虞预、干宝、孙盛,宋之徐爱、苏宝生,梁之沈约、辈子野,斯并史官之尤美,着作之妙选也。“作为史体之一的传记,此时尤繁。志怪书历来被视为一种杂传,在竞相进行历史着述的热潮中,它的大量出现也是必然的。
在文学方面,魏晋南北朝时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的自觉与文学批评的兴盛是这个时期的标志。例如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萧统的《文选》等等。
经过南朝的”文笔之辩“,文学作品不仅仅从非文学性的题材范围中独立出来,而且也同应用性的文章即所谓的”笔“划出界限。之后,文人对文学的各种体裁进行了更精细的区分。自觉的对文体进行辨析的是曹丕的《典论·论文》:”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文赋》进一步讲文体进行分类,并详细地论述了每种文体的特点。
他将诗和赋分为两类,并指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特点。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对各种文体追本溯源,又进一步推动了文体的演变。
干宝作为当时着名的史学家,他在作品中也表达了他的史学思想。干宝是一个有神论者,他确信有神仙的存在。虽然他的作品中充满了大量的天人感应思想,但是在解释这些怪异现象的时候,干宝总是以一个史学家的眼光来看待这些事情。他同时深受《周易》的影响,在解释怪异事件的时候,也会用周易中的观点来表述。正如上文所举例子,在论《山徙》中,山体移动,干宝借用《易传》解释为:”山默然自移,天下兵乱,社稷亡也。“可以证明这个观点。
六、结语
《搜神记》中儒释道三教思想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在一些篇目中可以同时感受到三教的影响。对于一些怪异事情的发生,三教都是会给出合理的解释。比如阴阳失调的怪异现象,既有儒家的天人感应,又有道教的天人合一、阴阳五行说,又有佛教的神变换化的思想等等。可以说,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三教合一“的现象开始越来越多,作为初始阶段,三教还是彼此独立的,但是三者还是相互影响的,三教之所以相提并论,则是偏重于它们社会功能的互补。干宝《搜神记》则是很好地继承了儒释道三教思想。笔者在此只是对其中的一个方面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搜神记》不仅是我国魏晋志怪小说的代表,在我国小说发展史上,更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它留给我们的价值还需要我们继续不断探索。
参考文献
[1] 干宝:《搜神记》,中华书局,2012年版。
[2] 丁晏:《曹集荃评》,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7年版。
[3] 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
[4] 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
[5]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华书局,1981年版。
[6] 葛洪:《神仙传》,中华书局,2010年版。
[7] 萧统:《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版。
[8] 陈寿,裴松之:《三国志》,中华书局,1982年版。
[9] 刘知几:《史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10] 林辰:《神怪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11] 葛晓音:《汉魏六朝文学与宗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12] 刘敏:《天道与人心--道教文化与中国小说传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年版。
[13] 程丽芳:《神仙思想与汉魏六朝志怪小说研究》,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4] 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天津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15]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
[16] 丁宏武:《葛洪的汉学倾向--兼论葛洪与魏晋玄学的关系》,《宗教学研究》,2008年 2 期。
[17] 刘敏:《汉魏神怪小说的宗教形态述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 3 期。
[18] 王瑶:《中古文学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9] 程丽芳:《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仙凡婚恋故事的类型及文化意蕴》,《学术交流》,2010 年11 期。
[20] 闫德亮:《试论<搜神记>中的佛教神话--兼论中国佛教神话的兴起与发展》,《中州学刊》,2010 年 6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