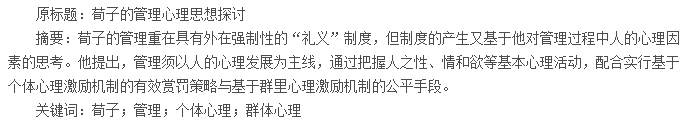
在荀子的管理思想中,他提出“隆礼重法”的外在管理策略,这一理论来源于他对人内在心理机制的分析,他说:“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故礼者养也”(荀子·礼论)。从欲——利——争——乱——礼义(养人之欲)的过程中,以人之欲为起点,以礼义法度的制定为终点,这是荀子所认识到的管理过程中的基本思路。制定礼义、法度等外在管理制度的原因是人“生而由欲”,其目的是“养人之欲”。
因此,在荀子的整个管理思想体系中,管理须以人的心理发展为主线,通过把握人之性、情和欲等基本心理活动,配合实行基于个体心理激励机制的有效赏罚策略与基于群里心理激励机制的公平手段,最终达到“群居合一,各得其宜”的管理目标。
一、人之心——行为产生的基础
人的欲望来自哪里呢荀子将其归为心。在他看来,“心”是一个特殊的生理器官,它本身具有认知功能,并无道德上的意义。心与耳、目、口等其他生理器官一样,具备一定的官能,即感知能力和欲望。如果说“耳好声”、“目好色”等是耳、目等的自然能力和欲望,那么“心”的欲望就是“好利”、“綦佚”等,他说:“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声,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荀子·王霸)。但“心”拥有不同于耳、目等的感觉或感知能力:“形体、色、理以目异,声音清浊、调竽奇声以耳异,……说、故、喜、怒、哀、乐、爱、恶、欲以心异”(荀子·正名)。心的感知能力最关键在于它能区别喜、怒、哀、乐等情绪。因此,心作为生理器官,它与耳目鼻口等存在差别,它把握的不是外在的感觉,而是蕴藏于人内在的情、欲等。并且,心能够居“中虚”以治五官,却不为五官所治:“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谓天官。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荀子·天论)。
除了支配人的五官,心还能支配人的整个身体和灵魂,如荀子说:“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故口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诎申,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则受,非之则辞”(荀子·解蔽)。“心”是发出命令的器官,而不是接受命令的器官。它能够自主地决定和支配自身功能的使用或停止,因此,口可以因为受到胁迫而沉默,形体可以因为受到胁迫而屈伸,但心却不能随便地改变自身的欲望。心的选择不受任何其他器官所限制,它只顺从自身的欲望自然而然的显现,它接纳的事物很繁杂,但如果精神专注就不会有所旁顾。除此之外,心还是一个连接知行关系的纽带,在学习的过程中,知识首先经过天官形成印象,再经过心的思辨、分析与记忆,形成支配人行为的意识,决定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荀子·劝学)。
虽然,荀子认为,“心”包含主导人之行为的自由意志,“心不可劫而使易意”(荀子·解蔽),但“心之所可中理”(荀子·正名),不能“离道而内自择”(荀子·正名),在荀子看来,人由于“欲”而产生行为的动机,但“心”能够根据“所可中理”而制止过份的欲望,“故欲过之而动不及,心止之也。
心之所可中理,则欲虽多,奚伤於治!……故治乱在於心之所可,亡於情之所欲”(荀子·正名)。因此,治乱的关键在于“心之所可”,它必须以“道”、“理”等为标准,这样才能不使“心”屈服于人之情、欲而产生恶,因而“心”成为社会治理的内在根据。
二、以心去“恶”之欲——管理的根本手段
荀子认为,欲扎根于人之情性之中,是人与之俱来的东西,正是它促使人们产生好利、争夺等行为,如他说:“今人之性,生而又好利焉”(荀子·性恶),又说:“故顺情性则不辞让矣,辞让则悖於情性矣”(荀子·性恶)。人之本性是“好利”,因而产生争夺等恶的行为,辞让等道德行为是违背人的自然情性的。那么,应该如何对待人之自然情性也就是,如何对待人性中这一“恶”的倾向荀子认为,“心”通过“知”成为制约由性、情、欲等主导的趋恶倾向:“见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不善在身,菑然必以自恶也”(荀子·修身)。
“心”通过自存、自省等对善与不善产生不同的情感,人见善,“心”自然生出“好”之情感,人见不善,“心”自然生出“恶”之情感,这些好恶情感促使人产生不同的行为。然而,荀子却并不由此而得出与孟子之善由“心之所生”相同的结论,因为“心”固然能够自动地辨别善恶,但又常常生出种种“蔽障”而使“心”处于危险境地,“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荀子·性恶)。人之“生而好利”的自然本性并无善恶之义,恶在于“顺是”所产生的结果,“争夺”、“淫乱”、“暴”等不良行为的产生都归因于“从人之性,顺人之情”,荀子举例说明这一问题:“假之人有弟兄资财而分者,且顺情性,好利而欲得,若是则兄弟相拂夺矣;且化礼义之文理,若是则让乎国人矣。故顺情性则弟兄争矣,化礼义则让乎国人矣”(荀子·性恶),“恶”出于人的顺“情性”之为。
梁启雄认为,荀子之“所谓‘性恶’,其实着重在指‘情恶’”,因“凡是‘情性’二字连用,便包含恶劣之意。”但“荀子此论,仍然不能圆通。”
这一观点一方面有意将荀子之“性恶”归为“情”,另一方面又找不到合理的依据。这一矛盾性的结论其关键在于没有发现“情性”二字之前的动词如顺、纵等。性、情、欲等的本义并无善恶之分,它们共同构成人之行为的动机,并通过“心”的选择、判断作用来完成人之知能的发挥:“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荀子·正名)。
儒家人性论“过于相信个人趋善的本性和可能性,必然导致对恶的监督和限制的缺失,人类本性中潜在的‘恶’无法回避,它是实现‘善’的不可或缺的条件。”
荀子则很好地规避了这一缺失,他认为,如果顺从性、情、欲等自然本性,那么人的行为动机就会朝着恶的方向发展,但如果发挥“心”的作用,将性、情、欲的作用联合起来促进人之“知”的发展,它们所发挥的便是积极作用,因为由心主导的“知”包含“心”的选择判断作用,“知”成为比性、情、欲等更为上一层的东西。“心之所可”可以为性、情、欲之行为动机选择“事物之理”。荀子因而提出“制天命”的思想,其本质在于利用人之自然本性来发展人之“知”能,而人所具备的知能是人把握外在世界的主导因素,顺从人的知能行为并遏制性、情、欲等干扰就会制约人的恶倾向,而不至于产生争乱,达到有效治理的良好状态。
三、有效的赏罚策略——管理的个体心理机制
荀子提出须用“心”控制人自身的欲望,但他又看到人之欲望在行为中的重要性。人之“好利”趋向一方面能够产生社会的争乱,另一方面,又能够激发人积极性,如柯雄文(A.S.Cua)分析:“这种自我追寻的‘好利’倾向标志着人的基本动机结构中的积极性。”
如果心要祛除“性情”等所产生的“欲”,就等于终止了人之行为的动机,而使得人之行为失去主动性和能动性。因此,心所要改变的是“欲”之方向。荀子将“礼义”设定为“欲”之终极方向,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既满足人之“欲”,又不使人为自身之“欲”所毁灭。
荀子看到有效地引导人之欲望、使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对于管理社会的重要性,他因而提出有效的个体激励策略,具体体现为赏罚制度,他说:“夫尚贤使能,赏有功,罚有罪,非独一人为之也,彼先王之道也,一人之本也,善善恶恶之应也,治必由之,古今一也”(荀子·强国)。利用赏罚来治理人民是自古以来就有的策略,人民常常因为竞赏而积极进取,也常常因为害怕被惩罚而积极进取。
无论如何,社会要得到有效的治理,必须采取合理的赏罚制度。并且,赏与罚作为激励策略的两个方面,必须同时进行,“赏不行,则贤者不可得而进也;罚不行,则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荀子·富国)。除此之外,赏罚还须分明,若不分明,就会“万物失宜,事变失应,上失天时,下失地利,中失人和,天下敖然,若烧若焦”(荀子·富国)。
荀子进而提出他的赏罚原则:首先,“无功不赏,无罪不罚”(荀子·王制)。赏罚必须与功劳和罪过等联系在一起,不无功受赏,无罪受罚,这是赏罚的基本原则。无功受赏,多功劳之人便不再尽心尽力,无罪受罚,老百姓就会怨声载道。其次,“赏不欲僭,刑不欲滥”(荀子·致士)。奖赏不能僭越法度,惩罚也不能滥用,因为“赏僣则利及小人,刑滥则害及君子。若不幸而过,宁僣勿滥;与其害善,不若利淫”(荀子·致士)。再次,“刑不过罪,爵不逾德”(荀子·君子)。刑罚不能超过其罪行,爵位不能超过其德行,罚与罪,爵位与德性之间必须想称。因为“刑当罪则威,不当罪则侮;爵当贤则贵,不当贤则贱”(荀子·君子)。刑罚与罪行相当就有威力,和罪行不相当就会受到轻忽;官爵和德才相当就会受人尊重,和德才不相当就会被人看不起。
除了物质、职位上的赏罚激励制度,荀子还重视精神层面的激励在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具体表现在:首先,领导者的表率作用。荀子说:“君者,仪也;民者,景也。仪正而景正”(荀子·君道)。
领导者首先要正己修身,在各个方面作出表率作用,成为人民的榜样、表率和典范等,这样才能使老百姓产生信赖感和敬重感,从而效仿领导者积极进取,辛勤工作,达到“上行下效”的管理效果。其次,任人唯贤的用人制度。在用人方面,荀子主张破除门第和资历的限制,使用统一的德才标准来选拔各类贤才,他说:“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於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於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荀子·王制)。这种大公无私、一视同仁的用人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激励人们争做贤士的积极性。再次,爱民、利民政策。荀子贯彻了先秦儒家的“仁政”方略,他认识到,良好的君民关系是社会治理的最有力法宝,他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君民关系如同水跟舟一样相辅相成,因此,通过爱民、利民政策获得人心,是激发人民积极性和进取心的长远途径。
四、公平理论——管理的群体心理机制
荀子的赏罚制度其主要实施对象是个体,其中包含了他对个体心理机制的理解,但荀子也看到了群体心理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荀子较早地认识到,群体是个体赖以生存的基础,如他说:“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君者,善群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荀子·王制)。
王天海注释“群”为“结成有组织的社会群体”,“善群”是“善于组织社会群体”。“群”是人之生存的本质,是人“胜物”的基本途径,但运用“礼义”等道德原则来实现的“群”所倡导的不仅要“胜物”,而且要使“万物皆得其宜”,这是使“群生皆得其命”的合理“群道”。“善群”和“群道”皆离不开管理者对群体心理机制的把握。
从辩证逻辑的思维出发,荀子认为要实现社会管理的总目标——“群”,就必须走向“群”之对立面——“分”,“人何以能群曰:分”(荀子·王制)。既然,人都有“好利”的趋向,但社会的物质财富并不因为人们欲望的增加而增多,势必在群体中产生分配多寡问题,如荀子说:“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离居不相待则穷,群而无分则争;穷者患也,争者祸也,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荀子·富国)。群体中如果没有“分”,人们就会随着“恶”的欲望而为所欲为,势必产生各种祸乱,最终导致内部争夺,彼此孤立,直至毁灭。这种结局,既不利于个体的发展,也不利于群体的发展。要消除内乱,并激发群体的积极性,其基本原则便是“明分”。
如何分呢荀子的“明分”首先用以解决财富的多寡问题,荀子看到“分均”的不可能,认为这既是自然之理,又是社会历史的必然:“分均则不偏,埶齐则不壹,众齐则不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荀子·王制)。“分”的实质在于承认财富的有限与等级的差别。
其次,“明分”用以解决社会分工问题,荀子提出社会分工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他说:“故百技所成,所以养一人也。而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荀子·富国)。社会的分工合作既体现社会发展的需要,也体现了人的社会本质:“然则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荀子·非相)。“辨”与“分”含义基本相同,即分别、分类的意思。有“分”或有“辨”是人的本质表现,也是社会存在的基本前提,“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荀子·富国)。当然,荀子的社会分工不能超出当时的时代局限,其在本质上是划分正确的社会等级。但这种社会等级的划分不是僵死不变的,个体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改变原来很低的社会等级地位,他说:“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於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荀子·王制)。
显然,“分”存在于两个领域:一个是物质领域,“分”使人有了贫富的差异;另一个是社会等级领域,“分”使人有了贵贱差异。荀子首先认为这种差异是“天数”,其原因在于“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又不能相使”,这是区分人等级差别的自然之理。在物质财富领域,“天数”是物质财富的有限性,不可能完全满足所有人的欲望,因此不“分”就会产生争乱。其次,荀子认为这种差异也在于“人事”,因为先王“恶其乱”,想要整个社会得到治理而变得和谐有序,因而制礼义以“分”之,这是“养天下人之欲”的根本。因此,按照“礼义”的标准区分出贵贱、贫富既体现了“天数”,也符合“人意”(先王之道),是一种社会治理的根本方法。
无论是财富,还是社会等级的划分问题,荀子提出依照“礼义”进行划分的原则,其本质是满足人们的群体归属和认同问题。但“礼义”等外在制度又如何作用于人的心理,使其在联结群体心理中发挥作用呢荀子的答案是“义”。他说:“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王制)。“群”与“分”最终要通过“义”来实现,“义以分则和”(荀子·王制)。
荀子之“义”的主要含义是外在的道德价值规范,“义”的主要功能就是与“礼”一起构成维护“群”之秩序的道德纲纪。如荀子说:“义,礼也,故行”(荀子·大略),荀子结合了“公”和“义”这两个观念组成“公义”概念,这使孔孟思想中特重内省意义的‘义’概念转化为具有外在规范意义的概念,并突破“个体”(我)的范畴而指涉“群体”(人)范畴。在此基础上,荀子主张“以义制利”,他说:“圣王在上,图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民载其事而各得其宜,不能以义制利,不能以伪饰性,则兼以为民”(荀子·正论)。荀子明确了义利之间的对立关系,又特别强调“‘义’不仅仅是一种客观、静态的观念而已,‘义’作为‘礼义师法之化’的一部分实具有相当的强制力,……它与荀子思想中的‘礼’一样,具有矫治人类自然本质的力量”。
但这不意味着荀子主张义与利之间的严格对立,相反,他反对那些打着“义”的幌子而欺世盗名的作法,他说:“夫富贵者则类傲之;夫贫贱者则求柔之,是非仁人之情也,是奸人将以盗名於晻世者也,险莫大焉。故曰:盗名不如盗货。田仲、史不如盗也”(荀子·不苟)。在这一基调下,荀子认为义和利是人之存在所不可或缺的两种价值,“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荀子·大略)。因而荀子并不一味地强调人的内在价值“义”,而是将外在价值“利”与内在价值“义”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
荀子之“义”具有强制性,但这种强制性应该不是外在的强制性,而需要转化为群体的价值认同才能真正地发挥功能,这是荀子对群体心理的最重要把握。在他看来,群体对“礼”、“义”等道德规范的认识和遵从恰恰在于它与群体自身的“利”存在紧密联系。“夫义者,所以限禁人之为恶与奸者也。……夫义者,内节於人而外节於万物者也,上安於主而下调於民者也。内外上下节者,义之情也”(荀子·强国)。“义”对人之“恶”、“奸”等的限禁其本质并不在于消极地扼杀,而是积极地肯定与调节人之“利”、“欲”。如韩德民所指出,“‘礼义’作为道德规范,其与主体间的肯定性联系,在于它体现了最大限度的群体的利益,包括其中每个个体的利益。正是由于起源上的这种特性,才使得它成为现实的群体制度之后,能够得到有效的维护。
群体中的个体,之所以其心知之‘辨’能够止于‘礼义’,认同‘礼义’之‘道’,依此逻辑,也是因为这是自己的根本利益所在。所以,说到底,‘礼义’之‘本’,仍然在自身。”
因而“义”在根本上是“利”之所在。
参考文献:
[1]梁启超.郭沫若,等.廖名春选编.荀子二十讲[M].华夏出版社,2009:159.
[2]张艳婉.儒家道德自觉的伦理设计[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3):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