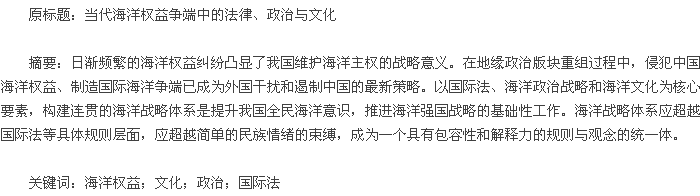
进入新世纪以来,海洋越来越成为主权国家角力的竞技场,其战略地位得到空前的重视。同时,在新的地缘政治格局重组的过程中,海洋安全的结构性意义也被重新定义和组织。海洋也成为区域政治利益博弈的重要突破口。围绕海洋权益的国际争端也日渐频繁和激烈,由此,人们把关于海洋权益争夺的跑马圈地称为“蓝色圈地运动”.分析当代中国所遇到的诸多海洋权益争执,我们会发现,以海洋权益争执形式表现出来的绝不仅仅是主权国家间仅仅基于经济资源而产生的利益分歧。很多时候,海洋争端的加剧反而是来自地缘政治版块的重组和某些大国干扰和遏制中国的一个具体策略。在这种实践背景下,我们关于海洋权益问题的研究大多是在因应实践斗争逻辑的背景下展开的,具有很强的具体指向性。但是也要看到,这种策略的局限在于,如果我们认可且唯一认可了这种“就事论事”般的斗争策略,将可能导致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形成应对规则之“昨是今非”的情形,甚至可能成为利益争夺相对方“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口实。
笔者认为,实践逻辑当然必要,它为激活我们的海洋意识提供了一个现实促动,对提升国家安全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也是极大的推动。但是,如果要更大限度地发挥海洋的上述功能,仅仅侧重海洋权益争端的斗争层面是不够的,过度放大或渲染海洋资源或海权的“权利意识”,也可能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消极结果,如它会强化国际争端的民族主义、甚至民粹主义情绪,人为地增加问题的复杂性等。因此,基于维护我国海洋权益的现实需要,基于培育和发展理性的海洋意识和海洋文化,构建综合性的海洋战略体系具有重要意义。这个综合性的海洋战略体系体现了微观规则与宏观文化的层级递进和彼此支撑,其核心要素体现为国际法、国际海洋政治战略和海洋文化三个方面的因素。从逻辑结构方面看,这三者反映了一种逐级递进的关系,比较而言,国际法则体现了微观的海洋权益纠纷处理策略,海洋政治战略则是一国政治战略在海洋问题领域的基本立场和战略定位,而海洋文化则是一个更为宏观,也是最具包容性的概念。建设海洋强国,从根本上要构建一种海洋文化和海洋意识,这对以陆地文化为传统的我国而言,是尤其需要强调的。而发达的海洋文化与理性的海洋意识需要明确的海洋战略来体现和表达,一国关于海洋问题的政治立场和战略,则表现为国际法等更为微观的规则和利益平衡策略的制定和运用。
一、海洋权益争端中的海洋法和国际法
在当代海洋权益纠纷解决过程中,最典型的机制就是诉诸由一系列海洋法所确定的国际法纠纷处理框架。1982年12月10日,经过九年漫长和反复的磋商与谈判,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在牙买加的蒙特哥湾落幕。这是迄今为止最为漫长的一项国际多边谈判。会议通过了由17个部分、320条款项以及9个附件组成的一个庞大的海洋法体系,形成了管理全球海洋资源、处理国际海洋纠纷的国际法框架,这就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称《海洋法公约》)。
《海洋法公约》确认了诸多形式的国家行为的正当性,如它允许各国在距海基线200海里以内的区域建立“专属经济区”.在专属经济区内,沿海国家有权勘探和利用海床以上、海床本身和海床以下的自然资源。从法理上看,对“专属经济区”这种新型海洋区域的确认,实际上是对传统国家权力结构的一场革命,它把传统的主权形态与海洋领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拆解,从而为当前争端国之间采取“共同开发”和“共享利益”提供了法律框架。在某种程度上,《海洋法公约》体现了相关国家基于分享海洋权益的目的而建立新型国际法和海洋秩序的要求,公约前所未有地提供了基于国际法准则处理海洋权益纠纷的制度性框架,在处理国际海洋权益争端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客观上有助于各国维护自身正当海洋权益,由此,《海洋法公约》获得了“世界海洋宪章”的赞誉(王铁崖,2002:337)。
但是,基于现实主义的考量①,我们还需要注意到,以《海洋法公约》为代表的国际法在处理主权国家间海洋权益纠纷方面还存在着不可回避的局限。
首先,《海洋法公约》以一部整全性规范,把全世界不同区域、不同地理环境和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的海洋利益以均质化、平面化的方式进行了一体性规定,这就回避了基于不同的历史和地理因素而导致的不同性质的海洋权益诉求;其次,基于国际法所具有的非强制性特征和基于缔约国可接受的需要,《海洋法公约》在实质内容上还是为缔约国进行“利益保留”提供了实施的可能,如公约对历史性水域的规定仅限于概念的使用而避免对内涵做具体而明确的界定,如在程序设计上诸如“用尽当地补救规则”的规定也为当事国选择性援用公约提供了便利;再次,美国等大国基于保护本国利益的考虑,拒绝签订公约,这使得公约本身的代表性大大减损。在第三次海洋法会议期间,作为主要的谈判国家,美国曾积极参与了公约的起草过程。海洋法会议结束前夕,美国政府一反常态,突然宣布对即将通过和签署的海洋法公约有重大的保留意见;最后,有关国家同样以国际法的方式来修改和排斥《海洋法公约》的内容。在美国的主导下,有关国家对公约中有关深海底采矿的条款举行了两轮15次非正式磋商。联合国大会于1994年7月以121票赞成、7票弃权、零票反对通过了“关于执行1982年12月10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的协定”.该项协定对海底管理局的决策,审查会议、技术转让、生产政策等一系列重大海底制度的规定都做出了修正。
本文并不主张“国际法xuwuzhuyi”思想,但值得思考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海洋法和国际法在解决海洋权益纠纷过程中的实质意义及其限度,如何看待《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规范对国际海洋政治和我国海洋事业整体发展的影响。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个是基于国际法规则上的规范实效,一个是基于国际法发展轨迹中的观念启示。
其次,关于国际法规则的规范意义。众所周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奠定了近代国际关系的基本体系,开创了政府间通过协商来解决国际争端的先例,由此确定了国际关系中应遵守的国家主权、国家领土与国家独立等原则,“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后,基于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国家安全战略开始变得越来越不适合时代”(唐世平,2003:145)。这对近代国际法的发展具有重要促进作用。但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并没有改变---基于国家实力消长基础上的国际权势格局的重组---这一国际关系的历史主线。
“即使在各国之间高度依赖、共同利益日渐凸显的当今世界,国际无政府状态仍是世界政治的一个根本结构特征,国家之间的争斗也仍是世界政治的基本方面”(何志鹏,2013:23)。二战之后建立起一些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但这不意味着国际关系进入一个国际法上的新时代。“不仅仅是因为人类似乎还远没有(也许永远也不可能)完全脱离野蛮时代,国家间的冲突仍旧频频发生,而在防止冲突和解决冲突的问题上,国际组织和机制仍然显得有些苍白无力”(唐世平,2003:145)。
需要看到,《海洋法公约》本身就是大国政治妥协和利益分割的产物,是以为发展中国家所不具备的科技和专业法律优势而确立的规则。由于确定大陆架外部界限等技术规则的高度复杂性,以及法律手段的专业性,主权国家间法律意义上的海洋边界的确立仍将会经历一个长期、反复的过程。这也意味着全球海洋秩序和海洋利益格局的最终确立也必将是一个复杂和艰难的过程。这个“最终确立”过程,在形式上虽然表现为统一的、全球性的海洋法和国际法框架的确立和普遍实施,但其实质过程则是大国政治和地缘利益格局的反复博弈和此消彼长。巴里·布赞(1981)关于20世纪中后期海底政治问题的细致分析典型地证明了如上的论断。确切地说,我们至今仍处于这个过程之中,格老秀斯意义的国际法并不是这种政治角力的开端,只是它的一个近代形态,而当代的海洋法和国际法则不是格老秀斯气质意义上的国际法(何志鹏,2013:282),相反,其更多地体现了霍布斯意义上“利维坦”气质(阿瑟·努斯鲍姆,2011:89),只不过这种强权和控制力乃是对外指向其他主权国家的。
就此而言,海洋法和国际法的限度并不仅仅在于宽泛的条款和执行的困难,还在于它并没有反映蛰伏在国际法规范背后的主权国家的政治立场和战略取向,而这种政治战略才是制约海洋权益争端的核心要素。所以,对于以海洋法和国际法表现出现来的“法律战”,并不能彻底涵盖我们关于海洋权益争端的本质性理解,由此,我们需要阐释关于海洋的政治取向问题,从而把海洋权益争端的实质从技术性转入本质性的层面。
二、海洋政策与海权战略的政治取向
从国内维度来说,海洋成为我国现代化发展战略格局中的组成部分经历了一个相对连续的历史过程,其大体上经历了---从把海洋视为现代政治国家之一般组成部分,到把海洋提升为经济发展之重要资源支撑,再到把海洋视为国家安全与强国建设的实践基点---这样一个过程。尽管后两者在时间和表现方式上有若干重合之处,但这种重合不能掩盖两者在对外关系方面的实质性不同:经济层面的海洋斗争策略可以或被迫实施“共同开发”,而政治和主权层面的争斗则不可能永远“搁置争议”,并且更为重要的问题是,不能通过无规划或无时间表的“共同开发”和“搁置争议”来反向“强化”争端相对国对“争议”确认,乃至对属于己方的确信。基于“现实主义”的考虑而采取的“搁置争议”和“共同开发”策略,它必须是建立在主权明确,立场鲜明基础上的权宜之计,但又绝不能让这种“权宜之计”侵蚀我们对海洋主权的一贯与明确的政治主张。这不仅关系到我们在“国际海洋政治”方面的基本立场与态度,更关系到国际政治战略的制定与实践。由此也凸显了超越国际法规则来构建应对方案的必要性,即把海洋权益争端纳入到政治战略中进行考量,建立连贯和有针对性的“海洋政治”战略。
从世界范围来看,海权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历史机遇在于中世纪晚期出现的地理大发现,对海洋的不同态度和不同处理,影响了不同的国家命运。但是,并不是海洋和海权意识决定和支配了世界历史格局的走向,相反,是基于资源需求或政治需要而推动了海洋开发。马汉的海权理论正是建立在强国战略基础之上,是基于国家战略而制定和实施海洋战略。在马汉看来,强大的国家、繁荣的商业贸易和稳定的政治格局与国家的制海权强弱休戚相关。一支强大的海军,以及由海上战略性岛屿组成的军事基地,并不仅仅在于保护美国的海外商业利益,同时也表明了一种政治性存在。这种海权战略的物化成果本身是服从和服务于整个美国的国家利益的。如果对海洋势力范围的维持构成了国家的负担,海洋将不会成为优先考虑的因素。这种结论也为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等传统老牌殖民强国的发展历史所验证(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2011:1-20)。海权意识的萌生和海上利益的争夺,乃是老牌殖民国家强国政治战略的组成部分。这同样说明了海洋政治(战略)对一国海洋事业的实质意义。
刘中民较鲜明地指出了“海洋政治”所指的对象:“海洋政治是指主权国家之间围绕海洋权力、海洋权利和海洋利益而发生的矛盾斗争与协调合作等所有政治活动的总和”.在他看来,“世界海洋秩序的演变历程体现的是从海洋霸权政治向海洋权利政治发展的历史趋势,这是从西方国家争夺和扩张海洋霸权,侵蚀殖民地、半殖民地以及发展中国家海洋权利,到发展中国家奋起抗争,重建国际海洋秩序的过程”(刘中民,2009:78-79)。海洋政治就是主权国家间基于海洋权益制定和实施的政治战略。
笔者认为,用“权利政治”取代“霸权政治”来概括海洋秩序的发展历程并不能揭示海洋权益纠纷的本质动因,相反还有可能过分高估了基于国际法框架解决海洋权益纠纷的可能性和有效性(当然这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国际法的实质功能)。本文认为,我们要突破传统的“海权”意义范畴,把“海权”从其一般意义(海上军事力量)层面解放出来,把“海权”构建成一个国家整体力量在海洋领域的战略体系范畴,而不仅仅是军事和政治力量。由此,“海洋权益”在国际法层面,也就不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法律正当性问题。比如以南海问题发生史为例,如贾宇教授所指出的,“南海问题的由来和发展是一个从无到有、从小问题发展为热点问题、从岛礁主权和海洋权益之争到海洋战略利益博弈的过程”(贾宇,2012:27)。而这个过程绝不是简单地基于经济资源而产生的物质利益纠纷,它是政治利益发酵和地缘政治格局变动的副产品。就此而言,我们在整理和重述南海、东海海洋利益纠纷的历史成因时,就不能再简单地把肇因仅仅归结为油气资源的再发现,否则就是用可计算的经济利益来替换或遮蔽无法进行物质利益计算的政治利益。换言之,岛屿纠纷、海洋权益纠纷等并不真正肇始于经济资源,只是经济因素在某一个具体时间点上扮演了先锋官的角色而已。而在近期的海洋争端中,经济因素已经不再显著,政治战略因素日益凸显,比如吉原恒淑和霍姆斯在其《红星照耀太平洋:中国崛起与美国海上战略》中对中国海权战略的发展走向做出了攻击性解读,认为中国海权的崛起将影响美国在亚洲的海洋战略①。
进而言之,晚近关于南海问题的论辩话语依旧集中于《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规范层面,这一方面显示了“法律战”和基于国际法的斗争策略的重要性,但“法律战”并不是真正的战场,我们应该看到的是,在南海争端的“法律战”这种表象形式之下的,是各利益相关国家对国际政治局势的实质性定位。同时,这也从根本上解释了国际法规则所具“局限”的主要缘由,国际法在规则的碎片化和内容上的歧义性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基于国际法解决纠纷的有效性,但这不是国际法规则本身的局限导致的,其根本上是由作为协议的国际法的多边协议主体的“利益保留”所导致的。国际法的“开放性”给国际习惯法发挥作用提供了可能和必要,比如对历史性权利的承认和确认就是一种具体表现,但是,这种虽然先于国际法,同时也为国际法所确认的历史性权利原则,却首先甚至主要是一种政治原则的表达。
在国际海洋权益纠纷日益增多,我国实施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背景下,提出“国际海洋政治”的概念具有战略意义,在实践层面有助于我们在国家整体发展的大格局下构建有针对性的国际海洋战略,从而有效地应对日显严峻的海洋权益纠纷。在理论知识体系方面也有助于我们改变基于学科分治而形成“剪刀手”般的“各取所需”式的策论视角。作为智库的一个基本主题,“国际海洋政治”是发展主题在海洋领域的集中表达,它需要融合基于当代国际关系状况而构建的支撑海洋强国所需要的,包括海洋文化观念、海洋发展方略和海事法律制度体系在内的一整套海洋理论和战略体系。首先,从国家利益原则这一角度去诠释新时期国家海洋关系,从而确立海洋利益是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国内发展维度,以及以和平崛起和民族复兴为主题的国际维度的结构性因素;其次,国家海洋政治战略要回答当代中国“海权”的基本意涵。当代国际海洋秩序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们需要超越传统海权观念,适时地反思传统的“有限的、防御型海权原则”,构建与当代中国整体发展相适应的海权新内容和新思维。再次,重视和有效利用国际法来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利益,准确地把握国际法在处理国际海洋关系时的有效性。
三、海洋文化与重构海权观念的实践内涵
在准确利用《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构建当代中国的海洋政治战略体系,还需要营造一种理性的海洋文化。海洋文化,是人们认识海洋的过程中形成的人类关于海洋的基本思想和观念意识,以及在利用海洋的实践活动过程中基于处理人与人或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构建的观念习俗和规则制度,它是观念和制度的统一。海洋文化为海洋法和海洋政治战略提供更为基础性价值观念系统。
构建适应当代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海洋文化,与强调海洋文化所“自身具有”的诸如“开放性、外向性、多远性、兼容性、冒险性、神秘性、开拓性、原创性和进取精神”等理由之间并没有必然和必要性的逻辑关联;也不必以“我国人民在长期的航海生活与商业贸易实践中创造了海洋文化”这种“追本溯源”的方式来以彰显我国海洋文化的“源远流长”.构建当代的海洋文化,就是基于当代中国发展的需要。在新的历史形势下,面对日益复杂的地缘政治格局,我国海洋文化的构建应该明确其核心要素,并在这一核心要素的辐射下来制定和实施我国海洋发展战略。在笔者看来,这一核心要素就是构建新型的“海权”观念。通过重新解释海权的当代实践意义,来支撑当代中国海洋文化的构建。
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这是“海洋强国”第一次上升为国家方略。在笔者看来,“海洋强国”战略的提出,一方面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和资源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越发激越的民族认同情绪对“海洋强国”意识萌生的推动作用。比如,近年来日益公开化的岛屿主权争端,海域划界纠纷等,适时刺激了国人关于捍卫海洋国土,彰显海权意识的神经。而马汉的海权理论和他对日益强大的中国的担忧,则更是一种有形的提示(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2011:153-175)。
从我国海权意识萌生的历史过程看,早期中国海洋文化观的一个核心特质在于对“海防意识”的强调(张作兴,2006:4-5)。在国人的观念中,海洋首先是一个海上军事防御问题,而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海洋文化观念的核心关注已逐渐扩展至包括军事与经济的海洋安全领域(倪乐雄,2010:130-132)。有论者指出,在当代中国语境中使用“海权”时,应该强调的是“一种隶属于中国主权的海洋权利而非海洋权力,更非海上霸权……中国海权的概念应该包括从中国国家主权引申出来的‘海洋权利’和‘海上力量’”,而就“海权权利”而言,包括诸如《海洋法公约》及其他国际海洋法认可的主权国家的各项海洋权利。后者则包括各种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张文木,2010:7)。
一个理性的海洋文化观念的核心要素在于对海权意识的科学理解和解释。一国的海洋力量包括硬实力与软实力两个方面的内容,它既包括海上军事力量的实质性存在,也包括主权国家对海洋事务和海洋利益的解释力和执行力。作为海洋文化观念的一个核心要素,海权既表达海洋领域中经济、政治和军事能力等硬实力,也表达一国关于国际法、国际海洋政治和海洋观念的软实力。“现代海权不是对传统海权的简单重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不同战略意识的国家演绎着的海权,有同,也有异,也就是说,海权的国家烙印十分鲜明”(张炜,2011:4)。我们需要把海权从海上军事力量的单一解释中开放出来,强大的海权和成熟的海权意识,以及理性的海洋文化,应该是包括了有效的制海权,繁荣的海上贸易、先进的海洋开发能力及完善的海洋管理制度等方面在内的综合体系(林国基,2012:5)。在海洋文明成为人类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之后,人们关于海洋的想象和开发改变了传统的制度和观念,甚至改变了人们对自身未来世界的预期和行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国法学家卡尔·施米特认为,海洋意识与属于海洋国家的普通法、代议制民主、自由贸易、市场资本主义一起,组成了宏大的制度组织及其社会观念系统(高全喜,2008:141)。由此,逐渐改变西方战略学者对中国海权定位的不准确理解。
四、结语
从海洋权益、海洋安全、资源安全到国家安全,这是一个逐级递进的利益格局系统。一个综合性的海洋战略体系的构建,既是以史为鉴的启示,也来自现实格局的需要。
以史为鉴,晚清国门洞开是从海防阙如,海权空白而由外侮任意欺凌开始的,如今,一个以和平和发展为立国方针的现代中国,必须把维护和平与促进发展的着力点放宽到海洋国土和海权政治方面。海洋不仅是我们强大国力的一个增长点,也是我们和平安定的大前线,海洋不仅有经济增长点的发展主义层面效应,同时它也具备政治和军事冲突的缓冲带效应。当然,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强国,其本身是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列强炮舰面前遭受的屈辱一直激励着我们要成为一个海上强国的决心。但是,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发展军力是为达成国家的战略目的,而不是为了满足海上强国梦”(唐世平,2003:203)。只有形成了系统的海洋文化观念系统和明确的海洋政治战略,积极关注以“国际法”等形式出现的规则和非规则机制,我们才能有效地保护本国的海洋权益和国家利益。
参考文献:
[1] [美]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2011)。大国海权。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 [美]阿瑟·努斯鲍姆(2011)。简明国际法史。北京:法律出版社。
[3] [加]巴里·布赞(1981)。海底政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4] 高全喜(2008)。格老秀斯与他的时代:自然法、海洋法权与国际法秩序。比较法研究,4.
[5] 何志鹏(2013)。国际法哲学导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6] 何志鹏(2013)。国际社会契约:法治理念的现实涵摄。政法论坛,3.
[7] [美]吉原恒淑、詹姆斯·霍姆斯(2014)。红星照耀太平洋:中国崛起与美国海上战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8] 贾宇(2012)。南海问题的国际法理。中国法学,6.
[9] 江河(2014)。国际法框架下的现代海权与中国的海洋维权。法学评论,1.
[10]林国基(2012)。海权、革命与现代的诞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1]刘中民(2009)。中国国际问题研究视域中的国际海洋政治研究述评。太平洋学报,6.
[12]倪乐雄(2010)。文明的转型与中国海权。北京:新华出版社。
[13]时殷弘、叶凤丽(1995)。现实主义·理性主义·革命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传统及其当代典型表现。欧洲,3.
[14]唐世平(2003)。国际政治理论的时代性。中国社会科学,3.
[15]唐世平(2003)。塑造中国理想的安全环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6]王铁崖(2002)。王铁崖文选。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7]张炜(2011)。大国之道:舰船与海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8]张文木(2010)。论中国海权。北京:海洋出版社。
[19]张作兴(2006)。船政文化研究: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福州: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