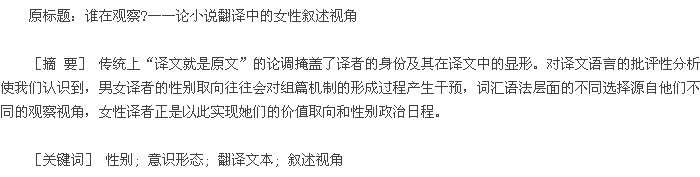
勒菲维尔( Adrew Lefevere)[1]12 -3在探讨中西方读者对待翻译的不同态度时,曾经指出西方读者在阅读翻译时,会越来越觉得原作伟大,而中国读者在阅读翻译时会觉得译作伟大,因为他们把译作当成了原作。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阅读取向显示了中西读者对待翻译的不同态度,西方读者在阅读译文时还记得其背后仍有原文,而中国读者则把译文当成了原文,这样所导致的结果就是读者往往青睐通顺的译文,如果译文不通顺,就会认为译者没译好。中国翻译史上的很多名家,如严复、林纾以及后来的傅雷,就是这样成名的———中国读者阅读《约翰克里斯多夫》就是认为自己在阅读“原版的”罗曼·罗兰。这个中的原因不管是因为译者努力声称自己是如何忠实于原作,还是中国读者对译者信任也好,都在说明一个问题,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以及其产品的背后是隐形的。肇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中,女性主义翻译日益受到重视。这促使人们开始审视女性译者的文本是否留下了“女性干预”的蛛丝马迹,或者展示不同于男性的女性对翻译的特殊体验。本文以选自女性叙述声音的经典之作———《简·爱》的语篇及三个译本为考察对象,旨在结合案例分析,在与男性译者文本进行对比的基础上,展示女性译者的翻译过程中在词汇语法层面所表现出来的性别倾向,并据此表明翻译过程中所呈现的不同视角和声音,因而不会涉及译者在前言、脚注和序言等副文本体现出的话语存在( discursive presence) 。
一、话语、性别意识形态和叙述声音
首先,有必要就有关“话语”( discourse) 和“性别意识形态”( ideology) 的概念给出具体的定义,以避免不必要的误解。这和以巴斯奈特( Susan Bassnet) 和勒菲维尔为代表的操纵学派有关政治意识形态的定义是不同的,而且操纵学派主要关注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操纵及对翻译的改写。而在批评语言学中,所有关于语言的使用都被认为反映了语言使用者的一套假设( assumptions) ,这种假设和使用者的态度、信仰和价值体系紧密相连。因而,上述两个概念的定义分别采用了辛普森( Simpson 1993) 和克拉斯( Kress 1985) 的观点,把意识形态定义为由社会群体所共享并默认的假设、信仰和价值体系[2]3; 话语则为说话或写作的体制化表达方式,这种体制化的表达能够给社会文化领域的特定活动提供具体的表达[3]7。性别化的意识形态通过话语层面发生运作,表现出男、女作者或译者在建构各自话语时所体现的差异,这些差异就是各自的角色、意义和价值取向。因此,不同性别的意识形态和话语都必然会影响文本的组篇机制,譬如主位结构、信息结构和衔接等。这些被编码进词汇、句法和语篇的性别意识形态向读者传达着某种社会意义和文化价值。因此,作为个体的译者必然首先被理解为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斡旋人; 对于这个斡旋人,其个人语言的语法、句法、发音和词汇在整个语言系统中都是一套特殊的意义潜势,表现为特定的观点和看法。这些特定的观点和看法在女性译者的文本中,可以让读者看到不同于原作中那套叙述模式的另外一种视角,即女性译者的叙述视角。真的存在这种差异化的声音和视角吗? 这恐怕还得从女性主义的文学研究说起。
多诺梵[4]348在《女性主义的文体批评》一文中,认为自从伍尔夫( Virginia Wolf) 提出“女性的句子”这一角度来衡量女性作家的作品以来,乔治·艾略特的作品实在“令人难以忍受”,同时她却极力称赞奥斯丁( Jane Austen) 和伍尔夫( Virginia Wolf) 等女性作家的作品对于表达女性心理的中肯。同样,在同一时期的男女作家之间,也会采用不同的话语策略来建构其叙事模式,这就是“话语中性别化的干预”。因此,在文学作品的“话语”层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声音”。文学批评中对叙事声音的讨论至少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中期,主要体现在对个体的文学作品叙事技巧的评论层面。
热奈特对小说叙事声音的探讨可以看作是结构主义叙事学对叙事声音研究的开端,之后“叙事声音”便演变成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关键术语[6]201。文学作品中叙事的“声音”包括各种类型的叙述者讲述故事的声音,那么翻译中的女性叙事声音往往隐藏在男性支配性的叙述声音之下,这种被压抑的“女性他者”( feminine oth-er) 只有通过细致耐心的分析才能被揭示出来。
在翻译中把对叙述声音的探讨和对“女性特质”在组篇机制中表现的分析结合起来,才能研究叙述声音在翻译中所具有的社会性质和意识形态内涵,并考察导致译者选择特定叙述声音的历史和社会原因。
然而,关于叙述声音的论述从没有在原作和翻译之间进行区分,那么原作中的叙事模式是不是也同样适用于被翻译的文本呢? 翻译文本和原文本是同一个叙述者在讲述故事吗? 在翻译书籍的封面上如果有女性译者的名字,那么在文本中能追溯到她在文本中所发出的声音吗? 从上面性别化意识形态的论述,我们也可以做出一种合理的推测。这种“性别化的干预”也同样存在于翻译文本当中。女性译者的任务就是要剖析、扭转甚至颠覆以符号系统的形式运作的父权制话语,彰显女性译者在其中的角色,在翻译的实践当中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哈蒂姆( Basil Hatim)[7]52曾经举过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 女性主义译者伽博睿( Linda Ga-boriau) 在翻译布罗萨德( Nicole Brossard) 剧本的时候,采用了激进的创造性翻译方法,女性主义译者的干预随处可见。仅举一例,原文西班牙语直译为英语: This evening I’m entering his-tory without pulling up my skirt( 今晚我将不撩起裙子而进入历史) ,而伽博睿的译文则为 Thisevening I’m entering history without opening mylegs( 今晚我将不张开双腿而进入历史) 。
这种近乎接近“语言暴力”的翻译显示了女性译者直接从传统的影子地位中走了出来,对翻译文本施加影响,当然读者尤其不懂源语或者没有看到源语的读者以为这就是原文,就是原叙述者的声音。这种强力的性别化干预被认为是女性译者对“语言阵地的重新占领以及由女性身体所体验的生命的意义”[7]54。这种从词汇语义层面对男女译者所做的分析显示了性别和意识形态干预在翻译实践中存在的事实。下面我们将结合实例,进一步探讨这种女性意识形态在翻译中的体现。
二、性别意识形态和翻译中的叙述视角
汤姆森( Geoff Thompson)[8]192曾经指出,词汇在语篇中所形成的衔接可以形成语篇中特定人物的视角。在下面我们把选自十九世纪英国女作家夏洛蒂 · 勃朗特的《简 · 爱》( JaneEyre) 的两个语篇和其各自的 3 个译文进行对比分析,以展示黄源深( 男) 、吴钧燮( 男) 和祝庆英( 女) 三位译者分别在翻译过程中对各个语言层次上所呈现的差异。为什么选用《简·爱》中的语篇进行分析呢? 就是因为它被认为是开创了“女性作家自传体小说传统的滥觞,被舒瓦特( Elaine Showalter) 认为是女性叙述声音的‘革命性的开端’”[9]122,展示了女性主人翁开始追求爱情和精神独立的叙事主体形象。那么女性的声音又是如何表达的呢? 在生活中,无论是我们看待事物,还是思考问题,如果观察的角度不一样,往往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得出不同的结论。这一点具体到文学理论中,声音和视角往往密不可分。叙述视角指叙述时观察故事的角度,角度不同往往也蕴含着不同的意义。
叙述视角是作者在叙事方面对读者阅读策略进行隐性控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当然也是最具有干预能力的一个方面。视角大致可以分为全知视角和受限视角两种,在受限视角中有一种叫“第一人称中的体验视角”[6]97。全知视角属于“外视角”,顾名思义,即观察者位于故事之外;受限视角及其中的“第一人称中的体验视角”
属于“内视角”,即观察者位于故事之内。这种第一人称的体验视角叙述几乎占据了《简·爱》书中大部分的篇幅,即叙述者经常放弃当下的体验,采用当初体验所发生事件时的眼光进行观察。因而会造成两种不同的视角。一个是叙述者的“我”当下追忆往事的视角,另一个就是被追忆的“我”过去正在体验事件的视角,这种两种视角的使用在小说中会导致过去和现在之间、“稚嫩”与“成熟”相互对照,以及懵懵懂懂和洞察一切的迥异。由于回顾性视角的运用,《简·爱》中存在明显的成人化叙述; 在叙述幼年简·爱的想法行为和宗教意识时,年幼的简·爱与成年简·爱的思想情感的差异得以融合,使得幼年叙述者的“我”成年化倾向极为明显。虽然成年的带有作者强烈个性色彩的简爱才是这种心理视角和意识形态观察的聚焦人物,但是小主人翁已经“是”接近定型的“叛逆者”了: 自尊、倔强,具有明显的反抗意识与坚强的意志力。自我和体验的描写与对照,以及体验事件者的观察,使得这位维多利亚时代的叛逆女性具有极大的艺术诱惑和伦理感染力。
如果说“是文本中的语言表达出来的价值或信仰体系”[6]97表达了叙述者的意识形态的话,男女译者的叙述视角与观察对象之间的关系也往往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关系,若聚焦者为男性,我们可以考察其视角如何掩盖了性别意识形态,如何将女性的情感等内容客体化或加以扭曲。若聚焦者为女性,我们则可以考察其观察过程如何张扬了女性经验以及重申女性的觉悟意识,或如何暴露和颠覆出父权体系的影响。下面来对比两个选自《简·爱》的语篇及其译文:
ST1: On that occasion I learned for thefirst time,from Miss Abbot ’s communica-tions to Bessie,that my father had been apoor clergyman; that my mother had marriedhim against the wishes of her friends,whoconsidered the match beneath her.( Chapter3)
TT1: 我母亲违背了朋友们的意愿嫁给了他,他们认为这桩婚事有失她的身份。[10]23
TT2: 我母亲不顾亲友们担心有失身份而纷纷反对,仍然嫁给了他。[11]2
1TT3: 我母亲不顾朋友们反对,和他结了婚,朋友们都认为她降低了身份。[12]19
原文中这句话是年幼的小简·爱讲述自己的母亲嫁给父亲的故事,采用的是第一人称的回顾性叙述视角,作为叙述者的“我”的视角似乎是中立的,没有表现自己明显的立场取向,这种“中立”在《简·爱》这部作品中有着特别的意义: 作者型叙述声音表达了对独立性的追求。
然而,三位译者对这原作者这一叙述的呈现却是有差异的。在原文中,marry him 是一个表现原文叙述者的一个中性词组,两位男性译者统统翻译成“嫁给了他”这种带着极强归属关系的词汇,聚焦者变成了男性,女人结婚就等于像卖商品一样被“给”了对方,反映了中国传统男权社会中,女性与男性婚后地位的不平等。这种叙述视角,把原文中的相对中立的女性叙述者变成了专制的男性声音,显示女性的被客体化。男性译者的这种强力干预在女性译者祝庆英那里,则变成了“和他结了婚”。“和某人结婚”这一行为的动作者可以是女人,也可以是男人,在措辞上显示不了性别取向; 因此女性译者祝庆英的翻译措辞平衡男女之间性别优劣取向,这种女性视角的介入使译文复原了原文的女性声音,避免了女性人物的客体化。
女性主义批评则往往聚焦于故事中男性和女性人物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女性人物如何成为周围男性的观察客体,如何成为男性的附庸和娱乐的对象。在此,译者的父权制心理和女性心理给叙述视角造成的影响会给翻译造成不小的麻烦:
ST2: I was honoured by a cordiality ofreception that made me feel I really possessedthe power to amuse him. ( Chapter15)
TT1: 很荣幸地受到了热情接待,因而觉得自己确实具有为他解闷的能力。[10]171
TT2: 我总是荣幸地受到热诚的接待,使我 觉 得 自 己 的 确 能 够 使 他 得 到 乐趣。[11]164
TT3: 我荣幸地受到热情接待,使我感到我真正有力量让他快活起来。[12]167
在阅读这个语篇时,我们感受到文字表达方式的平淡无奇和叙述中作者内心的欣喜之情之间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张力。原文中 I washonoured by a cordiality 好像人们在做演讲时开头所讲的一句套话,语气和用词都是司空见惯的,但就是这句司空见惯的一句话分别被两位男性译者加上“很”和“总是”予以修饰,以强调简·爱本人的心理感受,而这种心理感受恰巧就是传统上男性恩惠于女性的典型象征,而这一点和祝庆英未加任何修饰语的“荣幸地”构成了鲜明的对照。另外,三个译文在 amuse him两个短语的翻译上也表现出微妙的差异: 两位男性译者分别用“确实具有为他解闷的能力”和“使他得到乐趣”这种男性中心式的小句,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女性的存在以及与男性的交往都是为了供男性“解闷”,或者为了“能够使他得到乐趣”,女性的存在成了男性“解闷”的工具,翻译中这种文体层面的字词选择,再加上扭曲的男性译者主观性的第一人称叙述,表达了男性译者的男权中心主义的性别意识形态干预。与此视角形成对照的是,祝庆英则是用的和原文较为一致的女性叙述视角,“我”所感到“荣幸地”就是我受到了热情的接待,“让他快活起来”就是“我”作为女性所具有的“力量”,这种视角明显地表达了在前两个译文中女性所没有的积极性和能动性。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男性译者与女性译者通过语词表达分别在译文中构建了他们各自的性别身份,这种性别身份又反过来影响译者的观察视角和人物形象的塑造。译正面男性和女性人物时,女性译者往往积极地去认同、支持和褒扬; 译反面人物时,无论是男女,女性译者往往比男性译者更容易释放自己的谴责和鞭挞。这种女性意识形态的展露也暗示了女性译者能深入作品中的女性人物的心理,帮助建构和展示不同于男性译者的叙述视角。不管译者在文体层面上的选择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都能展示其性别意识形态对叙述视角的干预,以及对译文语篇的组篇机制不可避免的影响。这种女性主义叙事学关注的叙述视角以及所体现的性别政治,在翻译研究中成为一种不可忽略的重要维度,同时为研究翻译组篇机制中其他层次的问题提供了互为加强或互为对照的关系。
三、重建翻译中女性叙述的诗学
面对《简·爱》这样一部聚焦于女性意识的作品,小说的隐含读者( 也可以称为理想读者) 显然和我们引用的汉语翻译中的两位男性译者有很大的距离,因为按照女性主义的阅读理论,叙事文本是男权社会的文化产物。必须按照凯特尔( Evelyne Keitel) 所提倡的“女性阅读”( read like a woman) 的方式进行阅读,换句话说,理想读者应该有意识地拒绝叙事文本所引导的立场,采取“抵抗式”阅读策略,以反抗过去的那种叙事成规对性别视角或者女性形象的陈规思维[13]372。
从以上各节的讨论来看,小说叙述者“我”事实上也是小说的聚焦人物,叙述者的观察是颠覆男权话语,并试图建立女性权威的一种手段,也对叙事进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翻译中如何再现这种视角,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上面的讨论展示了女性译者祝庆英与另外两位男性译者在语篇中对词汇、句法,以及叙述声音的操纵上的差异。通过这些差异,男性译者与女性译者分别在各自的译文中构建了自己的性别身份,而这种性别认同又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小说中人物形象和性别意识的再现。
女性译者以自己情感的细腻能够深入到故事中人物的内心,深入挖掘并有意颠覆文本中以父权制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尽管如此,也许我们不能确定这是译者的有意行为,然而正是译者这种无意识的行为却更能说明性别身份对译文不可避免的影响。因为女性往往是男性“他者”的化身,不仅仅有别于男性,而且在地位上也低于男性并受到排斥。翻译研究的女性主义视角为女性人物在文本中的崛起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角斗场”,作家背景、译者因素、语篇类型、社会历史以及文化政治信息都可以纳入这个角斗场中,从词汇、语篇标志词、语义句法、语篇、语用和语法等不同的层面来展示女性主义对翻译的操纵和改造,从而能在更深层面上来标示意识形态、性别差异和翻译行为之间的关系。
由于父权制语言和其衍生的各种机构统治着传统语言的各个方面,不管是英语还是汉语,或者其他语言。上述我们对三位译者译文的讨论就可以清楚地说明语言是有性别倾向的,通过对英汉语篇中的意识形态、性别及其背后的动机进行对照和描述性分析,探讨它们在语篇和语用层面上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意义。在这方面,乐娜娣( Leonardi) 曾经得出过非常有趣的结论:
当男性译者翻译女性作家的时候,通常倾向于和语境保持中立和不偏不倚的立场,和女性译者比起来,语气更委婉; 而女性译者翻译男性作家的时候,她们要么完全忠实于原文,要么篡改原文以彰显自己在文本中的存在。[14]302显然,乐娜娣的这种结论是值得商榷的,男性也是属于这个社会上对立于女性性别的群体,他们的话语也必然带着他们自己群体的痕迹,也就是有着自己的话语和意识形态系统,在文本生产的过程中也必然会通过操纵词汇句法和语篇的生产以达到控制意义和价值的目的。
根据本雅明的说法,原文可以由翻译得到补充。那么这一点完全可以应用到女性主义的翻译当中,鉴于父权制语言对文本中女性意义的压制,以及女性译者对其本身作为斡旋者的政治角色的觉醒,完全可以促进女性意义在文本中的解放。这就可以解释本雅明所说的“增补”( supplement) ,即把前述哈蒂姆提到的“I'mentering history without pulling up my skirt”翻译成“我将不张开双腿而进入历史”的例子中所表现的“过度翻译”( over - translation) 策略所出现的成因,它补偿了语言之间的差异。女性译者对翻译过程的干预,也充分展现了女性译者:
通过复制文本的暴力行为使她自己那种逃离男性住宅和男性文本的疯狂欲念得以实现,与此同时也正是通过这个复制文本的暴力行为,这位焦虑的作者才能爆发出那种郁积在心中的不可扼制的怒火,为自己表达出用昂贵的代价换来的毁灭性的怒火[15]85。
上述引文中对这种女性表达的欲望虽然不无夸张之处,却也说出了被长期压抑在父权制文本之下的女性表达欲望。正是通过这种极具破坏和颠覆性的翻译,女性译者在文本中张扬了自己的存在,揭露了一直被隐藏的关于女性的种种“真相”,以体现反抗父权制压迫的“女性主义的怒火”,这也是以自己的“痛楚的生命经验来表达对男权秩序的质疑和抗议”[16]2。除了在词汇和句法上对文本进行操作和处理之外,女性主义译者还可能会在“译者序言”和脚注中表达她们的干预,以体现她们在文本中的积极存在。传统上谦恭隐形的译者所产出的通顺流利的译文已经成为女性主义译者不屑和攻击的对象,他们通过使用斜体、脚注和译者前言等策略来彰显她们在文本中的存在,积极参与对意义的再创造[17]50,从而成就了小说翻译中女性叙述的诗学。
四、结 语
由于小说中的观察往往是叙述者和小说人物的身体器官所发出的行为,特定的视角往往能构筑特定的意识形态并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到特定的人物身上,最终影响到男性还是女性成为被观察的客体。女性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指出文学语篇中被扭曲的“女性气质”,而这些“女性气质”可以表现在语篇的各个层面。本文就是从语篇的词汇和句法出发,探讨翻译中被扭曲的女性叙述视角。因为性别化的意识形态通过在翻译的话语层面发生运作,表现出男女作者或译者在建构各自话语时所体现的差异,这些差异就是各自的角色、意义和价值取向。不同性别的意识形态和话语系统都必然会反映在其各自文本的组篇机制之中,并且以语用符号学效果发生运作。通过对比分析男女译者在翻译中的移位,揭示性别意识形态在翻译作为决策的过程中,宏观和微观层面因素所发挥的作用。重视翻译行为发生的文化语境,把宏观的社会文化语境和微观的语篇各因素结合起来。通过对比,我们仍然看到在翻译中叙事传统的男性视角仍然支配性地控制着小说叙事,压抑着独立的女性“他者”。那么如果能为这种女性的被扭曲的视角进行复原,重新展示特殊的女性体验,也应该成为文学翻译批评的一个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1]Lefevere,Andrew. Chinese and Western Thinking ontranslation,in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in literarytranslation[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
[2]Simpson,Paul. Language,Ideology and point of view[M]. London: Routledge. 1993.
[3]Kress,G. Linguistic process in Sociocultural practice[M]. Melbourne: Deakin University Press,1985.
[4]Donovan,Josephine. Feminist Style Criticism[C]∥inSusan Koppelman Cornillon ( ed) . Images of Women inFiction. Ohio: Bowling Green State U. P. ,1981: 348 -352.
[5]Warhol,Robin R. Genered interventions: Narrative dis-course in the Victorian Novel[M]. New Brunswick. Rut-gers U. P. ,1989.
[6]申丹. 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