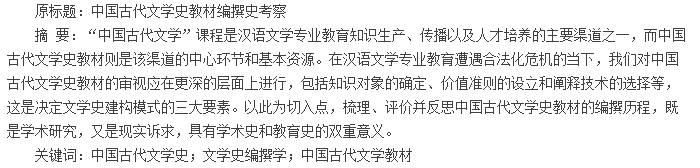
文学学科知识是现代民族国家文化形象和文化传承的重要内涵,而文学教育则为民族文化的塑型和延续提供了首要的方式和途径。前学科时代,由于古典人文教育知识学的整一性,作为古典学的文学教育在教育体制中占据着核心地位。
20 世纪初,随着现代性工程在中国的展开,中国高等教育步入了分科立学的轨道。汉语文学教育虽然凭借自身功能的特殊性在现代性高等教育体制中获取了合法化地位,但已然下降为一种专门教育,即主要生存于中文系或文学院的以汉语文学(用汉语作表意代码的文学)为主要教育内容的专业教育。新世纪以来,由于文化研究的兴盛和影响,汉语文学专业教育在知识边界、阐释技术等方面日趋模糊,同时学生就业市场亦渐趋缩小,汉语文学专业教育遭遇了合法化危机,学界开始从课程设置、教学方式、教材编撰等各个层面检视、反思之。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是汉语文学专业教育知识生产、传播以及人才培养的极为重要的渠道,而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则是这个渠道的中心环节和基本资源。“在中国,‘中国文学史’的出现,从一开始就与近代学制有着密切的关联,现知出版最早的,如林传甲、黄人的两种《中国文学史》,就是分别配合着京师大学堂和东吴大学的有关课程编写的”。
自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面世以来,迄今已出版 1600 多种文学史著作,其中,很多都是出于教学的需要而撰写。目前,学界对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编撰情况检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对具体作家、作品、思潮的重新评价上,比如某些作家地位有待调整、某一作品的评价有待更正等等。然而,正如怀特所说:“大凡历史著述必定包涵若干史料,以及诠释该史料之理论性观念,而借叙事性文体统筹二者,以期得以将公认确实存于既往诸事件之形貌重现于世”。
也就是说,我们对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的审视还应在更深的层面上进行,比如,知识对象(文学历史包涵的若干史料)的确定、价值准则(诠释文学史料的理论性观念)的设立和阐释技术(诠释文学史料的方法)的选择等,这是决定文学史建构模式的三大要素。以此为切入点,梳理、评价并反思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的编撰历程,既是学术研究,又是现实诉求,具有学术史和教育史的双重意义。
一、草创期(1904 年至“五四”前):新知与旧学间的游弋
20 世纪初,在中国,西式分科教育形态因为西学的纳入,逐渐成为学堂授习知识的主要方式,汉语文学教育已然“下降”为诸多普通系科之一种,走向了学科化、专门化道路。随着西式分科教育的施行,其背后所代表的西方知识分类系统,也因此而透过制度化的形式开始影响中国传统的知识结构。汉语文学专业教育出现了文学史、世界史、外国语文等新型知识内容。但是,西方新知识的介入并不意味着中国旧学术的退场,泛文学或杂文学的观念仍主宰着“五四”以前学术性知识的生产实践。比如,1904 年《奏定大学堂章程》的“中国文学门”课程体系中,有“西国文学史”,但未设“中国文学史”而命之为 “历代文章流别”, 将“文学”视为文章之学,固守了“文学”概念在中国传统学术中的初始而宽泛的意义。颇有趣味的是,林传甲等人在编写教材时,却借用了“文学史”这个转道东瀛的舶来品,以“中国文学史”名之,以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简称为林本)、黄人的《中国文学史》(简称为黄本)和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简称为谢本)为代表。
林本为作者光绪三十年(1904)于京师大学堂优级师范馆讲授 “历代文章流别”课程时所写授课报告书,据陈玉堂《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著录,有讲义本于 1904 年、1906 年两度印行。
1910 年,武林谋新室予以正式出版发行,共十六篇,11 万字,236 页。黄本由国学扶轮社 1905年出版,时为东吴大学堂教材。谢本是中国第一部由上古至清代的系统文学史专著,共 10 卷,中华书局 1918 年版。
首先,就知识对象而言,林本作为“历代文章流别”这一课程的教材,汇聚了小学、经史子集、文章技法等庞杂的内容,涵盖了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修辞学、中国史、诸子学等各类知识,与“皆录诗人名作”的他国文学史差异甚大,成了一本“内容不知道是些什么东西”的“国人第一部自撰文学史”。
显而易见,林传甲所理解的“文学”具有极为宽泛的意义,或者说,更接近中国古代的“文学”概念,“指一种博学的素质,远未具有现代意义上的专业化知识生产的涵义”,且一如既往地将“体格卑下”的小说、戏曲、词排斥在“文学”大门之外。因此,称之为“中国文章史”更为恰当。与此同时,“文学”的语词含义也出现了与西方狭义“文学”意义的部分吻合,这就是黄本引论部分介绍的当时西方学术界极为流行、中国读者感到十分新颖的文学观念“:美构成文学的最要素”“,而美则属于感情,故文学之实体,可谓感情云”。同时,黄人也强调了“真”、“善”两个要素的重要性:“远乎真者,其文学必颇”“,反乎善者,其文学亦亵”(《总论·文学之目的》),所以,文学之美也是应与“真”、“善”相统一的。自广义而言,文学实为“文明之要具,达审美之目的,而并以达求诚明善之目的。”(《中国文学史·总论·文学之目的》)无疑,在黄人的表述中,文学独有的审美特质得到了特别的关注,就文学性的纯度以及对这一意义表达的理论价值而言,黄人的认识堪称一次质的飞跃。但是,黄本并非就是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纯文学史,所收范围亦颇为广泛,制、诏、策、谕、诗词赋曲,以及小说、传奇和骈散、制艺,乃至金石碑帖,音韵文字,无所不包。或许,我们可以理解为,黄人在非现代意义的“文学”现象中找到了美,那么他所谓的“文学”,依旧属于泛文学的范畴。
而谢本则被后世学者誉为我国“率先出现的一部体制庞大、内容广博的文学史”,包括有纯文学、学术及与文学相关的文章,仍是在广义的层面上观照文学、圈定文学史的知识对象。
其次,在价值准则方面,林传甲、黄人在编撰文学史的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遵守了《奏定高等学堂章程》、《京师大学堂章程》等相关规定,“京师大学堂之设,所以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道德为人所需,经济亦为人所需,技艺为人所需”。
林传甲以开启民智、普及知识为指导思想,以完善封建士人内在人格修养、政治信念为核心宗旨,来甄选和阐释作品。
因此,伦理道德是林本依从的核心价值准则。黄人撰写文学史,虽有两个显在的价值准则,一是以“美”即“感情”为文学第一要素,二是“文学为语言思想自由之代表”,(黄人《中国文学史·总论·文学史之效用》)但其根本的价值准则乃是“文学为载道垂训之具”,“求诚明善”为文学之最大目的。谢本绪论部分开宗明义,重点论述了作者与时势的关系、从精神上观察文学趋势的方法,以及中国文学的特质在于形式美等问题,其目的在于昭示:治文学史不能仅从纯文学出发,必须联系当时的学术文化。但是,谢本各章节“先陈述前人的评论,再列举作品”的资料汇编式结构却淹没了属于作者自己的声音,从而也遮蔽或掩盖了作者关乎文学评论的价值准则。
最后,就阐释技术而论,上述三种中国文学史教材都采用了两种方法:一是引录法,“转引”前人的观点与“抄录”作品;二是点评式的阅读经验描述法,这是中国古人研读文章的重要方法之一,其特点是发表意见自由灵活,但也存在着繁琐为法、缺乏系统性等弊端。林本从治理小学和作文技法入手,于目录学、艺文志、文苑传、诗文评中获取资料来历史地串联经史子集“,目次凡十六篇”,“每篇三千余言,甄择往训,附以鄙意”,(林传甲《中国文学史·自序》)撮历代名家论文要言,间或夹杂自己的零星阅读感受。黄本对作品的阐释由三部分构成:按语、点评、注释,惜之泼墨太少,在字数上占绝对优势的仍是作品抄录部分。谢本每节叙述亦极为简略,一般是先罗列前人的评论,再列举作品,自己鲜有论述。
总的来说,草创期的中国文学史教材具有知识对象泛化、价值准则不确定、阐释技术非科学化等三个特征。“文学史”名称是西方的,装进去的却是传统的中国“文学”知识体系,是为“错体”的“文学史”,是“既要照顾被模仿被吸取的西方学理,又要迁就传统的中国学术思维的定势”的结果,是汉语文学专业教育学科化之初的必然产物。正是徘徊在新知与旧学之间,中国文学史的编撰者完成了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性建构。
二、发展期(“五四”到 1970 年代):在历史理性的规训之下
“五四”后,中国的高等教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随着英美大学体制影响的深入,汉语文学专业教育的现代性工程得以逐步展开。现代性的三大方案之一就是建立客观化、实证化的知识。在文学研究领域,规避传统评点式的主观性、以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文学的历史成为当时学界的主要学术目标,学者们通过寻找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改变了中国文学历史的书写策略。1950 年代初到 1970 年代末,文学得到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文学教育被视为“意识形态规训的主要方式”,合乎政党意识形态要求的阶级斗争等政治内容被塞进了中国文学史中。以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文学史简编》(1932 年 10 月大江书铺出版,本教材原是作者先后任教中法大学、中国公学、安徽大学、北京大学时的讲义,简称为“陆本”)、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本书是刘大杰 1940年代的旧作,1949 年初版。作为高校教材使用,主要是 1957 年、1962 年、1970 年代的修订版,简称为刘本)以及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五位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共四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 1963—1964 年初版,目前仍为某些高校所使用,姑且简称为游本)为代表。
综观三部教材,其中有如下值得注意的一些内容:
第一,知识对象相对集中。相较于刘本、游本的鸿篇巨制,“陆本”稍显简单。但是,比及林本、黄本,“陆本”的内容却有了根本性的变化,知识对象主要有诗歌、散文、戏剧、小说四种,小学、训诂学已被排除在“文学”之外。这一文学观念的变化源于“五四”时期以王国维、蔡元培等为代表的学者,他们提出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用审美代替宗教,文学的外延被缩小,逐渐朝着纯化的方向发展。刘本、游本,尤其是后者,采用按时代的断代面编排作家作品的框架,对上古至清代中叶有代表性的诗歌、散文、戏剧、小说、文学批评等作品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描述。
但是,当我们在游本中遨游一番后,就不难发现其间仍残留着历史等其他学科的东西,比如,《左传》、《战国策》、《史记》,是史书,但也被当作文学作品对待,且地位相当高;再如,《史记》与宫廷俳优故事,可能后者更具文学性,然而远逊于前者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的地位。
第二,以唯物主义的历史观、阶级论为价值准则。这种文学史观把文学史视为人民和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史,强调作品思想的人民性。凡是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家作品都会得到高度评价“,凡是为人民的作家、革命的作家就给予主要的地位和篇幅, 凡是反人民的作家就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以作家为中心,依其政治身份和态度来站队划线,严格区分敌我,用政治定性代替文学评判”。
仅以刘本为例。受当时社会政治的影响,刘本 1957 年修订版强化了社会政治、阶级斗争对文学发展的决定作用,运用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学观分析作家的阶级性、衡量作品的进步性,例如对嵇康的叙述:“……在他的悲剧中,充分说明了封建统治者的恶毒残暴和嵇康的高贵品质。嵇康的散文,有很强的思想性,斗争性。如《与山巨源绝交书》,对于黑暗的政治作了无情的讽刺, 表现出强烈的反抗精神。前人都妄讥阮、嵇乱俗露才,这是非常不正确的。”刘本1962 年版基本贯彻了建国后的文艺思想, 如文学反映论, 文学的人民性、阶级性、政治性, 文学内容决定文学形式等观念, 在对唯物史观的把握上较 1957 年版更专注、突出,在此基础上构建的知识体系, 其严密性和系统性也超过了 1957 年版, 直到 1983 年教育部还把 1962 年修订版列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文革时期的刘本(1970 年代版)将阶级论文学史观推向了极致:“阶级斗争不但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也是促进文学发展的动力。要评价诗人的成就,首先是看他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和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
阶级论文学史观滥觞于 1942 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要求把文学事业看成“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 认为文艺从属于政治, 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1950年 8 月, 教育部颁布《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其中规定: 文学史要“运用新观点,新方法, 讲述自五四时代到现在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史, 着重在各阶段的文艺思想斗争和其发展状况”。
所谓“新方法”,实际上就是阶级分析的方法。这个规定成了 50、60 年代文学史编写的指针,使文学研究者无形中确立了阶级论文学史观。正如章培恒、骆玉明在《关于中国文学史的思考》一文写到:“在五十年代,强调文学的政治标准第一, 强调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是一种强制的理论”。
我们认为,文学就是文学,“判断文学价值的一切外部(包括社会时尚、市场包装、政治压迫和宗教法典等)因素都不会长久有效”,但是,对于唯物主义的历史观、阶级论,我们需要小心翼翼地进行学术清理和价值辨析,不能不假思索地予以全盘否认。
第三,形成了以社会评价法为主的阐释技术。
所谓社会评价法,是把文学当作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强调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刘大杰在初版《中国文学发展史·自序》中这样写道:“可知文学便是人类的灵魂,文学的发展史便是人类情感与思想发展的历史”,“卜辞时代的艺术,正是用作迷信魔术的工具”(刘本 1957 年版),“唐诗兴盛的原因, 是比较复杂的: 人民生活、历史条件以及文学传统的推陈出新等等, 形成相依附的关系。但人民生活是其中的主要原因。毛主席指出,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源泉。”(刘本 1970年代版)。正是因为强调文学是生活的机械再现,是社会的简单反映,把社会的政治背景政治状况直接当作文学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所以,刘本在介绍某某时代的文学之前,总是千篇一律地概述当时的社会状况尤其是政治状况,然后把文学当作这种状况的反映,着重从阶级分析和思想分析的角度指出其内容的丰富或贫乏,即使谈及文学作品的形式与风格,也只是流于印象式、感受式的把握,缺少对于语言结构的细致分析。从而导致忽视了文学作品在技巧形式上的革新意义,呈现出一种机械唯物论和庸俗社会学的倾向,而“对形式的忽视必然伴随对于文学作品艺术特征与审美特性的忽视”。
游本使用最为广泛,但也是目前受到最严厉批判的一部教材。多数学者认为, 该书过于强调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执著于分析造成文学繁荣的政治、经济、思想等显性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聚焦于作家、作品的“反抗性” 和“人民性”,重视对文学背后的社会伦理与思想内涵进行挖掘,把文学作品看成是解释某种文化、思想、哲学、历史的资料,文学史变成了文化史、思想史、哲学史、社会史。它试图揭示文学,其代价却是遮蔽了现象的其他方面,比如,文学作品本身的体式构成与审美特征,常常被留在阴影之中,从而走向了淡化甚至消解文学性的危险境地。
文学的意义是自律的,话语形式是产生文学意义的根源,与社会生活关系密切,但绝不就是社会生活的简单反映。因此,社会评价法并不能揭示文学的所有属性,只应是阐释文学众多方法中的一种。
三、成熟期(1978 年—):审美解放的幻象
1978 年始,中国社会以“改革开放”为名展开了轰轰烈烈的解总体化运动。曾经一度因为与政治权力关系密切而显赫一时的汉语文学专业教育褪去耀眼的光环再次沦为普通的系科。学界主要是引进西方现代文艺理论,特别是美学,对汉语文学专业教育的学科知识自主性进行证明。
“‘文革’后的中国,出于对‘文革’的痛恨与恐惧,人们要‘美’与‘和谐’,不要‘斗争’。要美学,不要斗争哲学。在这种情况下,美学被当成是一种隐喻,它吸纳着一切为僵硬的政治意识自然会产生的离心力所抛出去的社会和思想力量。当时的美学,就与这种政治隐喻混杂在一起。
这一隐喻事实上形成了整个社会对美学的重视。”许多文艺理论家意识到文艺自身本属于“情感的领域”、“美的领域”,自觉地把审美当作把握文学自身性质和价值的基本范畴,把美学的方法当作文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强调“人对世界的艺术掌握,只就其精神掌握方式而言,是能动地反映世界的审美掌握”。
美学已然成为解读文学现象的重要理论尺度,“人类学本体论美学”、“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审美体验论”等与审美相关的文学理论层出不穷。到了 1990 年代,汉语文学专业教育以审美文化重新确认了学科身份。
审美文化在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中的贯彻大约是在 1990 年代后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前期,大多数高校仍然沿用的是游本。自1996 年始,随着章培恒、骆玉明编撰的《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一版,简称为章本)和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年第一版,简称为袁本)的先后出版,尤其是后者,作为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 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成果,逐渐取代了游本,成为延续至今的通用教材,并体现出鲜明的审美文化特色。
在知识对象的选择上,章本、袁本与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大体一致。所不同的是袁本将古代文论从古代文学家族中驱赶而出,因为古代文论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课程或学科。虽然章本、袁本与游本在知识对象的取舍层面达成了基本共识,但在价值准则的厘定以及阐释技术的使用上却有明显区别。
价值准则方面,章本从人性发展的角度编纂文学史,将文学史写成“心理文学史”或“人性文学史”,体现了一种深厚的人文精神。但对于纷繁复杂的文学史来说,仅仅从人性的角度来描述是远远不够的。袁本强调文学史的书写应立足于文学本位,遵从审美的价值准则,“重视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并具有艺术感染力的特点及其审美价值”。
当然,文学的内涵并不仅止于审美,以美学为知识学依据、把审美视作文学的全部内涵是 20 世纪 80 年代美学热的产物。说到底,审美也只是我们认识文学的一个维度。
在阐释技术的取用上,成熟期的中国文学史教材走向了多样化。叙事学、心理分析学、考古学等等,不同的知识介入中国文学史,形成新的阐释技术,铸就了多元阐释局面。比如,袁本编者在总绪论中就明确指出:“这是一部以文化学视角为编纂观念的文学史教材”,“借助哲学、考古学、社会学、宗教学、艺术学、心理学等邻近学科的成果,参考它们的方法,会给文学史研究带来新的面貌,在学科的交叉点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这种以文化作为切入点的文学研究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国际性乃至全球性的普遍趋势,这种文化角度的研究也还是可以继续充当对于文学的开拓视野的认识。”多种阐释技术交织,其正面价值在于开阔学生的视野,而不能形成文学研究的独立方法也是它显而易见的弊端。那么,究竟如何阐释文学?这种方法论追问的背后,实际上蕴含着“什么是文学”这一问题。
至今,学界关于文学的定义性表述并未达成共识。
但并不意味着文学阐释方法的无解。当问题的争执无法和解时,回到公认的原点进行反思或许会有意外的收获。毋庸置疑,文学是本体性语言,是语言能力的自由实现,话语形式是文学意义产生的根源,当话语指向审美语言活动时,便形成了文学。因此,文学研究的独特对象是语言,对文学作品的阐释应从话语分析着手,通过对语言结构的分析,发现语言症候和意义,形成话语分析技术,这是创新生产文学意义的基本机制。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在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的演变历程中,知识对象逐步得到了明确,但关乎文学文本评价的价值准则仍处于选择状态,学科化的分析方法仍不固定。根本原因在于文学是一个综合性、功能性概念(而非本体性概念),它的意义不是静态的,而是变动不居、不断生成的。这也就意味着,古代文学史教材的编撰永远是指向未来的,是一项具有未完成性的工程,它的面貌“总是取决于产生它的那个时代的审美需要和文学观念,取决于研究主体所授用的方法和价值标准”。
同时,我们也应该清楚,文学史既是对文学的历史性建构,又是对历史的文学性书写,这种学科间性决定了文学史的阐释学应该是跨学科的。我们不能无视历史学的文献考据法而一味追求文学中的审美意义,亦不能用社会学知识排斥审美,或是把审美内涵简化为社会学知识。未来的中国文学史编撰者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如何建构跨学科的文学史阐释学?当下,以批评和介入社会、跨学科研究见长的文化研究势头日益强劲,它或许能带来有效的启迪。
参考文献:
[1]戴燕. 文科教学与“中国文学史”[J] . 文学遗产,2000(2).
[2]韩春萌. 直面 1600 部中国文学史[J]. 中国图书评论,2005:68.
[3]海登. 怀特. 史元——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意象[M]. 刘世安译. 台北:麦田出版社,199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