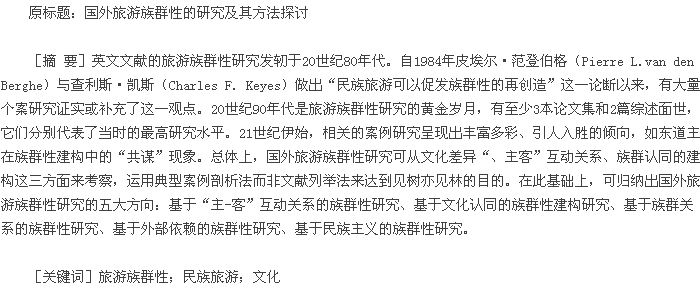
“ethnicity”(族群性)这个词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是民族-国家视域下族群关系日益复杂化的产物。正缘于此,ethnicity 指涉的内涵就相当丰富。理查德·詹金斯(Richard Jenkins)归纳道:(1)族群性与文化差异相关;(2)族群性根植于社会互动,且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互动的产物;(3)族群性与其构成要素——文化一样是不稳定的、可变的;(4)族群性既是集体又是个体的一种社会认同,在社会互动中具体化,在个人的自我意识中内在化[1]。因此,ethnicity曾有“民族性”“民族关系”“民族意识”“族群本质”“族群属性”等多种译法,但多数学者偏向“族群性”之译,笔者亦追随主流而选用“族群性”的译法。族群性既是文化人类学的学科术语,也是其传统研究对象,但自20世纪60—70年代民族旅游兴起以来,族群性成了旅游影响效应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层面,罗伯特·伍德(Robert E. Wood)把这类与旅游有牵涉的族群性表现称作“旅游族群性”(touristic ethnicity)[2]。这一研究旨趣直接促成一门新兴学科——旅游人类学的兴起。时至今日,旅游族群性研究仍是勾勒旅游人类学学科边界的重要颜料。鉴于上述,文章拟在纵览国外旅游族群性研究历程的基础上审视相关研究成果,从中探寻旅游族群性的研究方法,为国内相关研究抛砖引玉。
1 国外旅游族群性的研究历程
就目前搜集的资料来看,纳尔逊·格雷本(Nelson H. H. Graburn)在1977年编着的《少数民族旅游艺术品:来自第四世界的文化表述》(Ethnicand Tourist Arts: Cultural Expressions from theFourth World)①属于最早期的旅游族群性研究。该书收录的文章几乎都涉及弱势族群在旅游艺术品上所表现出的族群性,因此,纳尔逊在序言中写道:
艺术品在世界各国的价值体系里占有特殊的一席之地;国家或族群在谋求一种成功的形象时,艺术品是主要工具,它既表明新的认同又重申旧的认同,既美化了过去也保障了未来。他还总结了第四世界人群运用旅游艺术品表达族群身份的3种方式:(1)内部认同;(2)外部认同;(3)外借认同[3]。同年,瓦伦·史密斯(Valene Smith)主编的《东道主与游客 :旅 游 人 类 学 》(Hosts and Guests: TheAnthropology of Tourism)一书出版,该书在兼顾复杂社会的旅游业时,尤其注意到少数民族与旅游之间的密切关系。这些研究虽未直接针对旅游族群性,但至少表明研究者已注意到旅游对“第四世界”文化所施加的深层影响。因此,20世纪70年代可视为旅游族群性研究的萌芽时期,研究虽未被命名,但旅游族群性现象已初现端倪。
1980 年是个转折点,这一年人类学家皮埃尔·范登伯格(Pierre L.van den Berghe)发表《作为族群关系的旅游:秘鲁库斯科的个案研究》(Tourism asethnic relations: A case study of Cuzco, Peru)一文。
范登伯格指出,旅游中(尤其民族旅游)的“主客”关系与人类学家眼里的族际关系至少共享3项基本特征:(1)互动的肤浅、零碎、工具性、理性或丑陋面;(2)大量陈规陋习的形成和这些“掐头去尾”的互动关系有关;(3)接触中信任的相对缺乏与欺骗、操控的盛行。据此,范登伯格发表如下创见:(1)民族旅游是一种土着自身是主要的、至少是有意义的吸引物的旅游模式;(2)变成旅游凝视对象的当地人(土着或原住民)是一种新型人群—touree(译为“被旅游者”“吸引物”“旅游民族”等);(3)在一切旅游类型里,惟民族旅游显示了最有意思、最复杂的族群关系[4]。1981年,美国“族群意识与民族主义比较研究中心”在华盛顿大学举办民族旅游研讨会,范登伯格携“作为族群关系的旅游”一文参会,但据说此次会议是该中心的“绝唱”,不久就因资金短缺而宣告解散。1984年,《旅游研究纪事》(Annals ofTourism Research)第 11 卷第 3 期组织以“旅游与族群性”为主题的特刊,刊发了1篇序言和7篇论文。
序言由范登伯格与查利斯·凯斯(Charles F. Keyes)合撰,但它几乎是范登伯格“作为族群关系的旅游”一文的强化版;7篇论文全部来自1981年华盛顿大学的民族研讨会,此后这些论文成为旅游族群性研究的先锋之作。范登伯格与凯斯的序言亦声名大噪,二人关于“民族旅游可以促发族群性的再创造”[5]的论断振聋发聩,启迪了无数后来研究者。此后陆续有个案研究问世,但数量并不可观。必须提及的是1997年,这一年3本编着轮番问世。
其一,《亚洲与大洋洲的旅游与文化发展》(Tourism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Asia and Oceania)收录10 篇论文,研究范围涵盖加勒比海岸、泰国、印尼(苏拉威西的托六甲)、马来西亚(沙劳越)、中国(韶山)、日本、韩国以及东亚其他国家与地区。该书主要针对现代化、全球化背景下的新型“主-客”关系,揭示旅游文化影响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旅游者、旅游目的地文化背景与状况,旅游目的地的族群性表征亦因人群、地域不同而外显出不同形态。
其二,《旅游、族群意识与亚太国家》(Tourism,Ethnicity and the State in Asian and PacificSocieties),选编论文 7 篇,均针对旅游、族群性与当地政府的关系,研究范围包括中国、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与太平洋地区。主编米歇尔·皮卡德(Michel Picard)与罗伯特·伍德(Robert E. Wood)认为“地区旅游的日益发展与新政治情境下的族群建构进程之间的相互作用”是该书研究的焦点。查利斯·凯斯评论道,该书对旅游族群性研究有两大贡献:(1)研究者不再众口一词说旅游族群性是虚假意识,民族旅游亦不再单纯地被视为欧美文化精英、中产阶级旅游者发明的“组合文化”(packagedculture)或西方殖民冲动的产物,而是亚太地区少数民族与现代性创造性对话的结果;(2)当地政府在旅游与族群性之关系上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得到全面体认[6]。其三,《旅游者与旅游——人群与地方的认同》(Tourists and Tourism: Identifying with Peopleand Places)遴选论文11篇,其中,多数论文最初出现在1994年英国社会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举办的“旅游:认同的建构与再建构”研讨会上。全书表现出对“人们如何认同自我、如何与世界发生联系,旅游又是如何为人们提供反思平台”之类问题的兴趣,正如编者所言,该论文集通过关注两方面内容来阐述旅游人群与旅游民族的关系:(1)文化事项、族群或国族认同;(2)旅游者、旅游民族的想法与期待。由于缺乏对早期研究的梳理,例如纳尔逊·格雷本、范登伯格、玛丽-弗朗科西斯·兰芬特(Marie-Francoise Lanfant)、爱德华·布鲁纳(Edward Bruner)等人的研究,使得该书缺乏理论的成熟性。凯瑟琳·亚当斯(Kathleen Adams)则认为就案例研究而言,此书适于在校大学生阅读,对专业读者就显得过于简单[7]。总之,这3本编着代表了旅游族群性研究的高峰时期,所选编的论文几乎覆盖了全球的“第四世界”人群,民族旅游中的族群性样态以个案研究的形式被呈现出来,反映了旅游吸引力与族群性之间的复杂关系。20 世纪 90 年代末有 2 篇综述性论文,从不同角度总结了旅游族群性的表现形式及其研究视角。
其一,罗伯特·伍德的“旅游族群性:概述”(Touristicethnicity: A brief itinerary),文章从 3 个方面来观察旅游族群性:(1)国内、国际旅游是怎样成为重建族群关系的一股重要力量的;(2)在许多地区,旅游不再外在于族群文化,反而成为族群性表述和建构过程中的内在组成部分;(3)旅游与其他社会、文化活动之间的界限逐渐消弭,在后现代的迫力下,旅游活动的特殊性在衰减,导致族群性变成旅游趣味性的标识;反之,非旅游的族群商品和体验也在模仿旅游业的做法,例如主题化、舞台真实、再创造等。伍德还指出,旅游情境下的族群性自觉建构现象对诠解种族与族群关系研究领域中的两个重要论题大有裨益:一是“原生论”与“工具论”在族群认同、族群动员上的长期对立,前者认为族群性是一股牢牢根植于过去的强大力量,这股力量对于现在是难以言喻且不可抗拒,后者则强调族群性的情境性及其在稀缺资源竞争中的资本功能。二是真实性问题,焦点集中在“舞台真实”的逻辑是否阻碍了旅游者看到“真正的”文化并最终导致族群文化本身的衰落或毁灭,伍德认为类似“舞台真实”这样的旅游文化可能成为族群文化的一部分,甚至变成族群认同的凭据,因此,研究者的任务不是去揭露文化的非真实部分,而应该去解读文化获得真实性的过程[2]。
其二,密切尔·希区柯克(Michael Hitchcock)的“旅游与族群性:情境论视角”(Tourism and ethnicity:Situational perspectives)。希区柯克通过对族称、族群-民族主义、旅游者刻板印象的阐述,揭示“第四世界”人群对旅游的情境性(工具性)适应策略,从而总揽族群边界创造、维持与变化的复杂过程[8]。这两篇综述性论文共同反映了一个现象,即族群性浸润在旅游的许多层面。但无论是伍德所偏重的族群性、旅游与其他社会活动的关系研究,还是希区柯克曝露的族群对旅游资本效应的追逐,本质上都是范登伯格“民族旅游可以促发族群性的再创造”之论断的印证、演绎和延伸。
综观旅游族群性的研究历程,其轨迹是与世界旅游发展状况(尤其民族、遗产旅游)相呼应的,研究偏好是个案研究,研究对象涉及全球多种文化人群。20世纪80年代是旅游族群性研究的发轫期,90年代是积累期,族群理论是研究的重要依据,因此,研究者多具有文化人类学、人文地理学或社会学背景。但不能判定在这一领域是否已形成一个学术共同体,因为对于一些研究者来说,旅游族群性只是他们的偶然涉入。由于所搜集的文献截止于2003 年,在此之后的论文只涉及 2~3 篇,因此我们所勾勒的旅游族群性研究历程不代表2003年至今的研究概况。但就2010年纳尔逊在日本金泽组织的“ 东 亚 旅 游 中 的 族 群 性 与 国 家 主 题 研 讨 会 ”(Exploring Ethnicity and the State through Tourismin East Asia)所征集的论文来看,范登伯格关于旅游族群性的原创观点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具有强大的解释力。
2 国外旅游族群性的研究概述
吴其付曾经从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地方族群的文化认同、地方族群的文化变迁、民族艺术品的转化与复兴4个方面总结了英语文献中的旅游文化认同研究[9],文章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发,但认同只是族群性的一个层面,不足以代表整体的旅游族群性研究。因此,参考理查德·詹金斯(RichardJenkins)对族群性的理解,扩大英文文献的考察面,从文化差异、“主-客”互动关系、族群认同的建构3个方面来把握相关研究成果。出于方法总结的考虑,对于英文文献中的旅游族群性研究,没有采用一一罗列的方式,而是以解剖典型案例和凸显代表性观点为主,以便从中抽象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2.1 文化差异
根据文化人类学原生论、文化论、工具论或边界论的共识,族群得以区别于他群的一个重要标识是文化差异。在民族/遗产旅游中,文化差异是旅游吸引力的重要内容之一,所以乌尔夫·汉纳茨(UlfHannerz)说:民族旅游是将文化多样性视觉化、结构化的主要模式,同时它亦生产出多样性[10]。但文化差异的旅游化激起对文化商品化与文化真实性问题的长期探讨,原因在于文化商品化导致地方、族群文化的加速变迁,新质文化与原生文化严重脱节而引发真实性争辩,而真实性问题可能导致游客与族群成员的文化认同危机。
开拓这一研究领域的是历史学家布尔斯廷(Boorstin)和 社 会 学 家 迪 安·麦 坎 内 尔(DeanMacCannell),但最早把商品化和真实性放到一起来谈 的 是 人 类 学 家 戴 维·格 林 伍 德(DavyddGreenwood)①。1977年,格林伍德探讨了文化商品化造成的文化真实性丧失问题,也顺便揭示了西班牙巴斯克人对“阿拉德”仪式的认同弱化甚至丧失现象[11]。斯蒂法妮·扬(Stephanie Young)发现,曾令格林伍德痛心疾首的“阿拉德”仪式在20世纪80年代末依然生机勃勃,由于政府的干预,仪式内涵有所变化,男人们不再游行庆祝西班牙打败法国的战役,而是竭力彰显其巴斯克性(Basqueness)[2]。格林伍德亦于1982年承认是愤怒情绪阻碍了他对“阿拉德”仪式的理性判断,因为但凡有活力的文化,无不一直处在“自我调适”(making themselves up)的过程之中[12]。如今,“阿拉德”仪式的研究意义已超越案例本身,它隐喻一段对文化商品化和真实性变迁的判断历程。1988年,文化商品化与真实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埃里克·科恩(Erik Cohen)那里得到升华,科恩提出“渐变真实性”的概念,认为文化商品化是文化变迁的必然过程,曾经失真的事物可能会逐渐被认可为真实[13]。这一观点后来得到许多案例研究的印证。
在族群文化差异的研究历程上,有一些经典案例值得一提。一是马乔里·埃斯曼(Majorie R.Esman)对迪安·麦坎内尔“舞台真实”理论的逆运用①。埃斯曼调查的凯金人是18世纪末从今天的加拿大新斯科舍(Nova Scotia)流亡到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法国人后裔。自20世纪50年代始,凯金文化经历了飞速的涵化历程,埃斯曼指出凯金人的文化涵化先于旅游,但标志凯金文化差异的音乐形式、节日、娱乐精神、语言等却在旅游“舞台”上得以复苏并强化,这导致凯金人变成自己文化的“内部旅游者”(internal tourism),他们和那些外来旅游者一道探索凯金文化的神秘性。埃斯曼认为,东道主通常会提供一个“前台”给旅游者以保护“后台”生活世界的真实性,但凯金人的“前台”却保护了其原生的传统文化,从而掩盖了“后台”上演的标准的美国中产阶级生活图景[14]。二是范登伯格自20世纪70年代就一直关注的南美洲土着的文化变迁。1995年范登伯格发表“出售玛雅人:墨西哥的民族旅游促销”(Marketing Mayas: Ethnic tourism promotionin Mexico)一文,他发现,墨西哥恰帕斯高地的现代印第安人被定义成玛雅文明的后裔,印第安人的工艺品、编织、陶器、弓箭等文化物件被政府、精英阶层(墨西哥的混血原住民)用作促销工具,这样曾经被主流群体视为发展障碍的印第安“他性”变成引人遐想的旅游商品[15]。三是人文地理学家奥克斯·蒂莫西(Oakes Timothy)于20世纪90年代初对中国贵州的民族旅游调查②。蒂莫西发现民族村落能否吸引国际游客是其真实性的最佳标识,政府颁布的“文明保护村寨”称号是真实性的另一标识,一个村寨越有游客或政府所首肯的“真实性”,就越有“他性 ”,这 导 致“ 真 实 性 的 商 业 化 ”(commerce ofauthenticity)和村民对真实性的困惑[16],但两种导向的“真实性”都被村民不同程度地认同,民族旅游已悄然成为当地文化变迁的内在机制。四是格伦瓦尔德(Rodrigo de Azeredo Grünewald)关于文化复兴的非典型案例:由于历史原因,巴西塞古鲁港(PortoSeguro)的原住民聚居在一个无人问津的村落里,20世纪60年代末被外界发现时是一个操葡萄牙语、缺乏“族群特色”、极度贫困的人群,人们为其取名为帕塔科印第安人(Pataxó)。为了成为合情合理合法的印第安人并维系生计,帕塔科人在民族旅游这个竞技场上实施了“文化动员策略”。其主要复兴的3项文化元素为手工艺品、土着姓名(而非“教名”)和语言,后两项在向游客推销手工艺品时有强化族群身份的辅助功能,至于歌舞,则是从其他多种文化里移植而来。显然,帕塔科印第安人复兴并彰显了“我群”的文化差异,获得了旅游者主观体验的真实性,从而达到强化族群边界且提升旅游吸引力的目的。
虽然无法穷尽所有案例,但研究者对于旅游中文化商品化与真实性现象已形成一些基本共识:
(1)文化差异是被选择性地商品化,整个过程存在篡改、夸大、剪裁、创造等行为;(2)文化的商品化趋向于标准化、模式化,例如文化的麦当劳迪斯尼化、主题化、舞台化、博物馆化、克里奥尔化(混合化)、崇古主义、创造化、美国化等,有“多样性的一致化”(unity in diversity)[2]倾向;(3)麦坎内尔的六类型旅游“舞台”[17]在民族旅游中都存在对应物,族群文化与“舞台文化”之间的界限趋于模糊;(4)真实性的主位观点(emic)被凸显,它是评判族群成员和旅游者的认同感的重要依据。
2.2 “主-客”互动关系
范登伯格认为早期的民族旅游是一种特殊的族群关系类型:(1)旅游者是过客,“主-客”之间可能公然是欺骗、利用和怀疑关系,因为双方都能轻易从敌对、欺诈的负效应中脱身。(2)旅游者的身份自相矛盾,一方面,他通常来自一个富足社会或贫穷社会的富足阶层,其财富、闲情逸致与物质装备(相机、摄像机、汽车、露营设备等)都足以被当地人艳羡;另一方面,他对当地状况相对无知,就经常显得无能、可笑、轻信,极易被牵着鼻子走。(3)主-客的互动在本质上是不对等的,不仅由于财富(偏重旅游者)和信息(偏重东道主)的悬殊,也缘自游客是观赏者而东道主是表演者的角色分立[4]。迪安·麦坎内尔的看法①与范登伯格类似,他认为族群关系有两个维度:结构上的高等与低等;表述上的亲近与对立。两个维度排列组合后构成4个基本类型:
(1)低等族群试图攀附高等族群;(2)低等族群视自己为高等族群的对立面;(3)高等族群试图亲近低等族群,并以之为模仿对象;(4)高等族群视自己为低等族群的对立面。麦坎内尔指出,在一些地区例如巴黎新城,旅游者被当地人看成乡巴佬;在另一些地区,旅游者因其富有或俗气而被当地人嫉妒或憎恶。他认为任何短暂的、肤浅的、不平等的社会关系都是滋生欺骗、剥削、怀疑、狡诈与刻板模式的温床,因此无论哪一种情形,“主-客”双方的关系都短暂且失衡[18]。丹尼森·纳什(Dennison Nash)甚至偏激地将旅游视为一种帝国主义形式,他认为旅游活动是“主-客”(或更多关系群体)之间的交易,但交易表现为一种力量的悬殊,旅游目的地的命运可能会和越来越无法控制的外部力量联系在一起。
各介入主体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各方如何理解该怎样相互对待之基础上,而在政府激励型旅游中,东道主(或其他介入者)通常愿意承担与游客相处的额外责任,例如文化的调适、迎合、学习、改造等;而将他人视为客体的旅游者就不太可能受相关干预机制的约束,更易从自我利益出发[19]。
上述三人的观点在纳尔逊·格雷本与埃里克·科恩的研究中得到极端的印证。纳尔逊在一篇关于色情旅游的文章中指出,殖民宗主国对前殖民地的旅游,例如日本人到中国大陆、中国台湾、韩国、印尼、菲律宾等地旅游,欧洲人到泰国旅游等,是前者在失去其殖民帝国的殊荣后仍试图通过其他渠道(譬如旅游)来彰显其作为强国的雄性气概[20]。这种旅游关系充分利用了前殖民地的贫困窘境,使历史记忆、旅游、色情之间产生微妙的联系,从而更加剧“主-客”之间的不对等关系。科恩分别调查了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青年以及泰国女孩与欧美旅游者的关系:前者作为阿拉伯人却生活在犹太国家,游离于官方就业市场之外,族群身份与宗教信仰又使其陷入尴尬的文化处境,职业和文化的双重困境导致阿拉伯青年怀有“游客姑娘之梦”,他们与欧洲年轻女游客建立亲密关系并期待通过婚姻而移民,仿佛她们是解决其复杂困境的最好途径,尽管欧洲姑娘对这种关系漫不经心且鲜有修成正果者,但来自体系之外的女游客仍浑然不觉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体系内“潜在的功能失调”[21]。后者是从泰国东北贫困地区到曼谷“淘生活”的年轻女孩(包括已为人母的弃妇),她们通过吧台小姐、咖啡招待的角色之便与欧美男游客(farang)建立模糊的“性-情感”关系。科恩将这种关系分为4种类型:唯利是图型;舞台型;混合型;情感型②。他认为舞台型与混合型最为常见,体现了经济交换与社会交换的杂合[22]。
社会科学家对族群研究有个共识,即族群并不是单独存在的,它存在于与其他族群的互动关系中;没有“异族意识”就没有“本族意识”。在“主-客”互动中,东道主与游客相互强化了对方的“自识”与“他识”,研究者发现最多的现象是双方刻板印象的形成与影响效应。首先是旅游者对东道主的刻板印象。英国人类学者密切尔·希区柯克就此做过探讨。例如尼泊尔的“夏尔巴人”最初是指在喜马拉雅山给旅游者做向导的先锋族群,但在游客眼里他们是职业的挑山夫,如今夏尔巴人成了尼泊尔挑山夫的泛称,以至于附近其他族群的挑山夫也攀附性自称“夏尔巴人”;东印度尼西亚松巴哇岛上的马来人在文化特征上与当地最大族群——比马人并无太大区别,但游客只认马来人为典型的“山胞”,这导致当地马来人与比马人在族称与文化身份上的再次分离[8]。这个领域的典型之作是诺埃尔·萨拉查(Noel B. Salazar)的“印象化还是想象化?——文化表述与族群、地方的‘旅游化’”(Imaged or imagined-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the‘tourismification’of peoples and places)一文。
萨拉查认为,早期民族志所记载的马塞人的游牧生活与战士形象契合了西方人对高贵野蛮人的浪漫想象,于是马塞人成为狂野非洲的象征。在一些欧美大片里,马塞人则充当了非洲的男性化“他者”角色:赶牛群,住泥屋,与全球化绝缘。近几十年来,马塞人逐渐成为各种文化表述(如图像与文本记录、电影、艺术与博物馆展览、动画、照片与卡片、游记、博客等形式)的重要客体,他们被“曝光”的程度胜过非洲其他任何族群。马塞人与欧美游客的互动是典型的“中心-边缘”式关系,后者先入为主地对前者产生了刻板印象,这种想象式印象的力量是如此巨大,不仅被付诸于旅游场景,也建构了族群、地方以及相关的文化事件[24]。
其次是东道主对旅游者的刻板印象。当地人也会对旅游者形成刻板印象,并以揶揄、幽默的口吻“反唇相讥”。希区柯克总结到,在塞舌尔群岛的方言里,旅游者是“非常富有”的代名词,隐含“主-客”间悬殊的经济实力;东印尼的比马人概念里的旅游者也指富有、聪明的人;在印尼的约尔卡塔,当地人凭体貌特征识别旅游者,并一律用turis一词向白人模样的旅游者打招呼。西班牙马略卡岛上的人被分为3类:本地人、非本地西班牙人和陌生人(包括外国人、异族人或旅游者);因纽特人称旅游者为kablunarks,这是他们对非我族类的异族群和外人的统称;坦桑尼亚语中的mzunggu既指白人,也指旅游者,其原意接近“陌生的”“非同寻常的”意思。针对难以互动的旅游者,当地人尤其是导游自有泄愤的方式:在马耳他,“傲慢的日耳曼人”“挑三拣四的荷兰人”“吝啬的瑞典人”的故事到处流传;英国西部乡村用grockle(观光客)专指大都市旅游者,略含温和的奚落意味;巴黎人就乐得叫英国游客“烤牛排”,私底下还戏谑其低俗和粗野[8]。当然,旅游刻板印象的经典之作应属美国民俗学者迪尔德丽·埃文斯-普里查德(Deirdre Evans-Pritchard)的“‘他们’怎样看待‘我们’:美国土着的旅游者印象”(How“they”see“us”: Native American image oftourists),作者生动刻画了“土着”眼中的白人旅游者形象,以此反观白人对印第安人的刻板印象。普里查德以新墨西哥州的圣菲为田野点,搜集到大量旅游互动中白人的言行表现和印第安人的应对表现。印第安人心目中的白人旅游者一方面是消费奴隶,譬如苏人(Sioux)甚至觉得白人不是人类,而是像鹅一样的痴肥者(fat-takers),为消费而生;另一方面则是人类学家式的文化差异收藏者,对“他者”有狂热嗜好,但又极其无知、轻信、不合时宜甚至愚蠢。在旅游互动中,印第安人的心境相当复杂:面对被旅游者对象化的境遇,印第安人既不想成为社会问题,也不想做浪漫的“他者”,他们以戏谑、模仿、讽刺、沉默等方式对抗[25]。换言之,美国西南的“印第安人-旅游者”互动关系具有信息不对称的特征,印第安人既刻板化旅游者,又了解旅游者对自身的刻板印象,而旅游者对这一点知之甚少,因此,印第安人能够对“主-客”互动关系质量加以控制,这使他们既得以卖掉产品,又保住些许尊严。
但对于当今世界的旅游业而言,所谓“主-客”关系是抽象的理想型,“客”主要是指旅游者无疑,“主”却指涉多元旅游介入主体,包括原住居民、政府、旅游从业人员、旅游机构、旅游企业等。因此,“主-客”互动将会产生出更多复杂的关系类型,甚至旅游介入主体之间也会结成不同关系。例如在多族群的社会环境下,如果任一族群都未能占据旅游的垄断位置,旅游影响就可能形成裂变效应。根据巴斯“族群边界”理论,当合作能使利益最大化时,各族群会寻找抹平族群裂缝的空间,他们彼此依赖,甚至要看旅游“薄面”而克服族群差异和冲突,以维持互利的族群协作关系[26]。但当族群A、族群B在共同面对族群C的威胁之时,A和B会“捐弃前嫌”抹平族群差异而一致针对C。因此,只要旅游能提供一类在文化、语言与权力上都与当地人极为不同的外来者(包括旅游者),后者就有可能使原来的族群边界趋于消融。可见,旅游包含了大量的群体互动,它们导致了丰富的族群关系类型,具有深入观察和研究的价值。
2.3 族群认同的建构
正因为族群性是不稳定的、可变的,族群认同就有被建构的可能性。在旅游业中,族群认同的建构现象普遍地存在于“主-客”互动、文化商品化、旅游文化化、文化自觉等过程中,或者说,族群认同与旅游形成了互为建构的关系。凡关注民族旅游、遗产旅游的学者都或多或少会涉及族群认同的建构,因此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比较多,但略显杂乱,笔者尝试做出如下分类,并借用典型案例加以解释。
其一,利用文化差异来重建族群认同,文化差异可以是原生的,或再创造的。马乔里·埃斯曼的凯金人案例值得再次提起。凯金人的族群意识源于与区域外法裔人群的文化接触,这些“局外人”以旅游为媒介叩醒了凯金人的族群意识,激起他们对族群身份和族群文化的自豪感,并且变成自身文化的旅游者。于是,凯金人借用其早已衰微的渔猎生计模式、独特的音乐形式以及逍遥自在的族群精神成功重建了其作为法裔人群的族群性,许多凯金人视旅游版本的凯金文化为其真实的传统,尽管日常生活里他们并不践行这些传统。但埃斯曼的分析还未结束,他洞察到与其说是那些复兴的族群文化在维系凯金族群边界,毋宁说是凯金人对文化自豪感热情洋溢的表达勾勒了其边界[14]。凯金人对这种“舞台”式原生文化的笃信与追捧亦激起了外部旅游者的深层兴趣,族群的文化情感悄然取代了文化差异而变成一种吸引力。格伦瓦尔德(Rodrigo deAzeredo Grünewald)则提供了一个典型的创造文化差异的案例,即上文提到的帕塔科印第安人。帕塔科人竭力扮演其“被发现的印第安人”形象,尽管他们所呈现的文化材料是如此单薄以至一眼看穿,但这不妨碍他们利用这些材料来修砌族群界限。事实上,帕塔科人是用创造的传统维系了族群边界,但显然他们更愿意称此为文化保护或复兴而非传统的发明。格伦瓦尔德指出,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原生的帕塔科文化,旅游艺术一被生产出来就成了族群艺术,直接用来建构族群性,旅游场域中的“舞台真实”展演几乎是帕塔科人自我表述的唯一渠道[27]。
其二,利用遗产来建构族群认同。密切尔·普雷特斯(Michael Pretes)考察了美国南达科州的3处现代遗产:拉什莫尔国家公墓(Rushmore NationalMemorial,亦 称 总 统 山),沃 尔 药 店(Wall DrugStore)与拉皮德城恐龙公园(Rapid City DinosaurPark)。拉什莫尔国家公墓是政治性遗产,核心吸引物是美国历史上4位最杰出总统(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亚伯拉罕·林肯、西奥多·罗斯福)的面部雕像,他们分别代表这个国家成立、扞卫、地理与殖民扩张的历史,象征独立、自由、正义、公理等美国主流价值观。沃尔药店是经济型遗产,自1931年创立以来,它已从单纯的药店业务扩张到饭店、冷饮柜、西方艺术画廊、服饰店、书吧等领域。沃尔药店代表一种经济版本的美国传统,是私营企业、小城镇、西部开拓者、大萧条的奇迹、新教工作伦理等的文化杂合体,所以它不仅仅是商业实体,更是南达科州最重要的旅游吸引物之一。拉皮德城恐龙公园是科学与自然类遗产,恐龙在美国文化中占据特殊位置,它赋予美国西部广袤的土地以历史重要性和壮观感,这正是美国这个现代国家所需要的远古的过去,巨型恐龙唤起人类对自然的恐惧,但新大陆的开拓者们征服了这块恐龙曾经咆哮的土地,因此,恐龙一开始就被编织进国家认同之中。
据此普雷斯特认为,旅游景观与安德森·本尼迪克特(Anderson Benedict)的人口、地图、图书馆一样,隐含着一种民族主义的话语,是美国这个多元文化国 家 创 造 超 原 生 纽 带 认 同(supra- primordialidentity)的工具。由于缺乏“美国”(而非美洲)的考古遗址,像南达科州这样的遗产景观就被创造出来以象征一段深邃的历史或悠久的“人-地”关系,当它们被输入国家价值观念时,这些现代的旅游吸引物在形塑全民共享的辉煌历史上,就可能具有与埃及金字塔、希腊帕特农神庙、印尼婆罗浮屠相同的符号功能[28]。
相反,对于威尔士而言,文化最具魅力的时刻是与民族屈辱史相提并论,这正好与民族主义视角不谋而合。威尔士的文化复兴运动肇始于英格兰与威尔士历史上漫长的征服、反抗与再征服过程及其所导致的威尔士文化的断裂。这种文化抗拒从浪漫主义时期延续至今,虽然形式不同,但正如威尔士大学一名政治学者所言:威尔士的民族主义在政治上不成功,但在制度上却无处不在。苏珊·皮奇福德(Susan Pitchford)指出,通过矿场旅游、古堡旅游与博物馆旅游,威尔士与英格兰的关系史以及威尔士的文化独特性得到向外界表述的机会:历史的旅游吸引物创造了高贵不屈的威尔士人形象,而威尔士的边缘地位则是拜几个世纪前英格兰的无耻侵略所赐;文化的吸引物强化了威尔士远逝的传统,例如诗歌大会(eisteddfod)培养了威尔士对其吟游诗人的记忆,并成为威尔士的一种民族文化制度。对许多旅游规划与开发者而言,旅游不仅是帮助威尔士从依附型经济中恢复过来的方式,亦有益于威尔士界定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并播布于外界,使威尔士人保持鲜明的文化边界。威尔士民族党则很关心旅游者对威尔士的描述,这亦是其看重旅游形象的意义所在。因此皮奇福德指出,通过威尔士的民族旅游可窥见边缘化族群针对“内部殖民”史的双重诉求:对历史不公的矫正与对族群文化的重估[29]。
其三,利用旅游想象来建构族群认同。典型案例是诺埃尔·萨拉查的马塞人,据萨拉查观察,遭遇旅游者这一社会事实使许多马塞人有了很强的自我客体化(self-objectification)与自我商品化(self-commoditization)意识,他们知道自身形象对于国外旅游凝视的美学吸引力,于是竭力扮演欧美游客对非洲“他者”的想象(Western fantasy)。和其他旅游地的土着没什么两样,马塞人也学会了出售自己的边缘性(marginality)。最后,萨拉查指出,国际旅游互动中可能存在对马塞族群形象的浪漫化、扭曲化和异域风情化,但这并非理解旅游想象的关键,关键在于全球性的旅游想象是怎样被地方扮演出来以迎合旅游者、进而建构并固化这种族群形象的[24]。
但亦有反向利用旅游想象的“土着”,例如特罗布里恩德岛因马凌诺夫斯基(Malinowski)而蜚声人类学界,如今它在旅游业中变得有名。岛民深谙旅游想象与需求,他们为旅游者表演新创造的舞蹈、音乐,甚至编撰歌词来嘲笑这些闯入者,因而觉得在与观光客的关系中占了上风。调查者岗特·森福特(Gunter Senft)认为这是岛民在抒发对本土文化的骄傲和自信之情,他们用这种“阳奉阴违”的方式固守了文化认同与族群身份[30]。
其四,族群及其成员的身份重建。在政治、文化、经济上占优势地位的国际或都市游客对族群文化的青睐将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族群在民族-国家的结构地位或话语权。例如新西兰的毛利人,毛利艺术是新西兰的两个标志性旅游资源之一(另一个是其奇特的地貌),但毛利人在变成基督教徒后,毛利文化逐渐被同化,多数毛利人不再会说毛利语,因此有人说,当代毛利文化一半是白人的创造发明,另一半才是真实的毛利文化。为复兴文化,毛利人重修了他们的“marae”(神圣集会地),邀请城里的年轻毛利人来学习毛利语,同时也邀请新西兰人或白人来瞻仰其各种传统文化。毛利头人向政府施压要求更多的文化自主权,但效果不佳。20世纪80年代末,毛利人通过“国际艺术展”将其文化遗产推向海外市场,并在北美巡展,毛利文化在海外的声名鹊起增加了其向政府施压的砝码。旅游不仅提升了毛利人的国内地位,并使其成了自为的旅游民族,虽然毛利文化仍是新西兰一流的旅游资源,但毛利人已意识到无论是为旅游者还是为他们自身,都应看护好毛利人的文化形象[31]。
范登伯格与秘鲁本土学者奥乔亚(Jorge FloresOchoa)关注秘鲁库斯科的民族旅游与本土意识之关系。库斯科被视为具有历史、文化与地理重要性的非凡之地,它既是通往马丘比丘(Machu Picchu)和乌鲁班巴(Urubamba)①的必经之路,其本身亦是西半球最大帝国—塔万廷苏尤(Tawantinsuyu)即所谓“印加帝国”的首都;即使在西班牙殖民初期,它也曾充任秘鲁的首都。因此,库斯科原住民变成“印加文明”当仁不让的后裔。复杂的殖民史与贫穷落后的现状导致一种库斯科本土意识——印加主义(incanismo)的产生,其核心表征是说盖亚丘族语(Quechua),其次是彩虹旗、纪念碑、博物馆与Inti Raymi 节。尽管众多旅游产品事实上是印加文化与殖民文化的杂合,但库斯科精英阶层(包括导游)贬殖民文化而扬印加文化的做法与旅游者对印加神秘性的极度推崇,使旅游创造物都被加冕了“印加”真实性。范登伯格二人指出,印加主义所导致的地方自豪感和文化亲亲性将库斯科土着、城市混血儿整合成单一的安第斯文明,而旅游者的在场则将印加主义框限在商业网络里,强化且合理化了印加意识本身,于是当地人和旅游者一道共享一种肤浅的印加主义。范登伯格二人强调民族旅游与印加主义的彼此兼容与强化,但亦尖锐指出库斯科的民族旅游并非“社区主导型旅游”。无论印加主义还是民族旅游都是精英文化现象,旅游只使城市中产阶级受益,作为印加文化主体的原住民被悬置在这种现象之上[32]。该研究完成于2000年,至今库斯科仍是一个沦陷在经济停滞、政治危机、战乱频起的偏远孤立落后之城,旅游与印加主义是唯一可慰藉这困境的两种现象。一方面,旅游将库斯科的历史、文化与地理重要性兑换成现实,国外旅游者的关注痴迷使库斯科从贫穷之城转化为旅游胜地,旅游光环遮蔽了城市的其他缺陷;另一方面,印加主义者视自己为印加人的后裔,而城市阶层则视自己为印加贵族后裔,印加主义为这些族群精英提供了逃避、怀旧与复兴意识,凭借印加帝国的回光返照,他们可暂时忘却落后、失业、污染、恐怖主义、不公正、失地、腐败等残酷现实,获得身份的象征性提升。
20 世纪 60 年代,挪威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Fredrik Barth)提出族群边界理论(简称“边界论”),“边界论”的逻辑在于:族群认同是族群存在的基础,认同产生于“我群”与“他群”的互动;互动以族群边界为凭借或区隔,边界通常以客观文化差异为标识;但在族群互动中,每个族群都会创造新的文化差异或标志物以维系族群边界[33]。约翰·厄特尔(John Ertl)指出,巴斯运用“边界”的隐喻,使族群研究从此摆脱对语言、文化和生物性(它们是界定族群的关键要素)的纠结,转而去看这些“材料”(指语言、文化、生物性)是怎样被用于区隔不同族群及其成员的[34]。因此,巴斯(Barth)的“边界论”亦隐含“情境论”的观点,即族属辨识和维持族界的需要可以使许多文化差异被生产出来或相反的情况,标志边界的文化符号是可变的、可商榷的、分场合的,亦即情境性的。据此,假设旅游者是具有模糊边界的“超族类”(super-ethny)[35],他们与东道主形成一种理想型的“主-客”二元互动关系,在此过程中,东道主的族群边界被刻意维系并创造。这一方面是出于吸引旅游者赚取经济收益的工具性需要,另一方面是出于树立族群信心的情感性需要,如麦坎内尔所说,旅游关注是一种无形的奉承和恭维[18],它强化了族群在维系文化与身份认同方面的自觉意识。
通常认为,民族旅游有建构或解构族群认同之基础的两种可能性,亦即它有强化或削减族群认同的正负功能。关于其负功能,多见于早期研究之中,主要观点有二:其一,强调旅游者作为异文化人群的在场性,通过当地人的“内化”“社会化”过程而引发示范效应,挫伤当地人的我群意识,弱化其族群认同;其二,真实性与文化变迁问题,文化真实性的弱化或丧失会割裂文化主体与文化之间的亲亲性,引发认同危机。但该视野忽视了一个问题,即旅游只是影响族群认同的外部力量之一,现代性、民族-国家的干预力量先于旅游。世界各国的“第四世界人群”多在旅游之前就进入文化变迁的历程,因此,并无多少案例支撑民族旅游对认同的解构性这一说法。相反,上述案例研究大都表明,无论东道主借用文化差异、遗产、旅游想象还是别的什么来建构族群认同,本质上是在扮演旅游者眼中的“他者”形象,从而在族群身份和文化归属层面上形成不可复制的旅游吸引力,与此同时,东道主的族群认同与族群身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重新建构。
综上,旅游族群性研究是旅游影响研究的一个分支,它被国外人类学者高度关注是缘于民族旅游或遗产旅游的盛行。自范登伯格将“主-客”关系视为一种族群关系类型以来,旅游族群性研究断续至今,但多为案例研究,即便成书出版,亦是论文结集,少综合性论着或文章。综观旅游族群性研究30余年的历程,就覆盖范围来看,虽然研究者更偏爱第三世界国家的第四世界人群,但对象亦涉及全球几乎所有大洲的族群:从被旅游影响甚深的巴厘人、毛利人、夏尔巴人、因纽特人,到遍及美洲的印第安人、泰国原住民、日本阿伊努人、中国少数民族,以及欧洲国家的边缘人群等;就研究内容而言,囊括文化复兴与再创造、文化商品化与真实性、旅游中间人与族群分层、族际关系、民族-国家下第四世界人群的身份、文化与地方意识、旅游中国族或民族主义的抒发等主题,较《旅游研究纪事》1984年特刊所涵盖的内容要丰富许多;就研究成果而言,范登伯格关于“民族旅游可以激发出族群性的再创造”的论点被众多案例所证实,而1984年特刊的另7篇文章至今被频繁借鉴而非驳斥,这暗示族群理论解读民族旅游的有效性,1984年特刊意味着较高的研究起点,它导致后续研究难以超越之。
3 旅游族群性研究的方法探讨
族群性是一个敏感的论题,它在旅游(尤其民族旅游)中表现出复杂的面象,引发不同学科的极大兴趣,但如何研究这些族群现象却是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在借鉴国外旅游族群性研究历程和成果的基础上,拟从研究的切入点、方向和理论三方面来探讨旅游族群性的研究方法。
其一,旅游族群性研究可以从族群文化的变迁入手,重点考察音乐、舞蹈、服饰、建筑、岁时节庆、宗教仪式等表达性文化(expressive cultures)的旅游化过程。对东道主来说,表达性文化的参与性强,且易于“舞台化”;对旅游者来说,他们较为喜闻乐见听觉、视觉刺激感强的文化元素,表达性文化更符合其对观赏性的要求。但对于旅游业渗透强深的民族地区而言,表达性文化的变迁只是个开始,伴随旅游中文化传播与创新机制的确立,变迁会波及其他文化类型,例如语言、生计模式、生态观、亲属关系、家庭结构、社会组织、价值观等。通常,文化的商品化与真实性既是旅游业中的一对悖论,亦是考量文化变迁的重要标尺。族群性与文化差异相关,因此,文化差异的变迁是观察旅游族群性的一个切入点和重要视角。但文化变迁并非唯一的切入点,例如国内学者孙九霞等就专门研究了不以族群文化为主要旅游吸引物的民族社区,发现参与旅游商品销售、旅游运输业、旅游餐饮业等相关行业使当地居民的族群认同发生了一定变化,主要体现在宗教意识得以强化、传统习俗发生改变、旅游与传统产业的职业认同有所分化等3个方面[36]。
其二,族群文化变迁只是接近族群性的一个窗口,并非最终的研究目的,因此,必须根据文化变迁的内容与性质来把握研究的大致方向。在英文文献研究(包括一部分中文文献)的基础上,归纳出旅游族群性研究的几个方向:
(1)基于“主-客”互动关系的族群性研究。族群性根植于社会互动,互动将激发、强化或改变族群的“自识”与“识他”,“主-客”双方刻板印象的形成即是这一类研究;互动的强弱程度亦会影响族群认同,例如孙九霞对云南迪庆雨崩村、西双版纳傣族园和各类民俗村的比较研究,她发现旅游接触的强度、深浅与族群认同的保持、强化、分化有密切关联[37]。
(2)基于文化认同的族群性建构研究。文化是建构族群边界的重要材料,文化变迁将导致不同的身份建构与认同倾向,因此,这一方向的研究囊括最多,也最为复杂。例如杨福泉的东巴文化研究,作者全面回溯了纳西东巴文化在宗教、民俗与旅游圈内的变迁历程,并将现代东巴文化认同归纳为4个层次:表层认同、审美认同、实践认同与信仰认同[38]。
(3)基于族群关系的族群性研究。分为族内关系与族际关系研究两部分。前者针对族群因旅游利益而分化或弥合的现象,约瑟夫·甘培(JosefGamper)的“奥地利的旅游——旅游影响族群关系的案例研究”大概是最早关于旅游族群关系的研究[39];后者针对族群之间的旅游竞争与合作现象,戴维·贾米森(David Jamison)对肯尼亚马林迪小镇的研究是典型案例,无论旅游被视为机会还是威胁,它都使东非旅游胜地——肯尼亚的多元族群成了“一条绳上的蚂蚱”[40]。旅游既带来竞争、威胁与其他负面效应,亦带来机遇、利益与发展,案例中无一族群能强大到足以主宰地方局势,他们彼此依赖,甚至要看旅游“薄面”而克服族群差异和冲突,以维持互利的族群协作关系。
(4)基于外部依赖的族群性研究。这一论题有3 个层面可供分析:一是族群对旅游的主动共谋现象,例如马塞人为迎合旅游想象而主动扮演“他者”的案例[24]。二是政府主导的民族或遗产旅游,政府及文化精英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族群认同的依据之一——文化真实性的裁决权,这一方面激起文化主体的文化自觉意识,另一方面则导致其丧失文化自决权。三是族群对旅游者力量的过度依赖,琳达·里克特(Linda Richter)认为巴基斯坦旅游即是如此,旅游人次的减少可能会动摇其族群甚至国族自信,在这样的国家里旅游者的兴趣承担着确证其国家独特性与卓越性的功能[2]。
(5)基于民族主义的族群性研究。这种民族主义体现为利用旅游来抒发族群情感、表达族群话语、提升族群地位、激发族群认同、施展族群抱负等形式,以达到改变族群命运的目的。
其三,族群性研究是文化人类学的传统论题,这方面有许多可参照的理论和可借鉴的观点,譬如族群观、族群认同理论等。最好能在掌握文化人类学者关于族群概念的辨析以及完成对原生纽带论、文化论、边界论、工具论(情境论)的具体解读之后,再着手从事旅游族群性的研究。在边界论与工具论者看来,文化差异只是修筑族群边界的原材料,文化的真实性并不重要,但在东道主眼光与旅游眼光的对峙张力下,真实性变成旅游吸引力的潜在标尺,并反作用于族群认同。因此,真实性理论尤其麦坎内尔的“舞台真实”是旅游族群性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工具。对于该理论,有必要赘述几句。
麦坎内尔“舞台真实”理论源头是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印象管理”理论。戈夫曼“印象管理”理论的核心在于:当个体面对他人注目时会有意无意地使用各种标记来强化行为,行为的戏剧化有助于实现其理想化的期待,在观者心目中塑造出其想留下的影响与观念。在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周围环境之间的互动中充斥着表演、场景、舞台与观众的隐喻,因此戈夫曼将社会结构分为“前台”和“后台”,个体的社会行为是“前台”,其真实流露则是“后台”[41]。麦坎内尔的“舞台真实”理论正是对“印象管理”理论的巧妙还原与延伸,他将戈夫曼对“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的解读又还原到戏剧舞台上,但此舞台已非戈夫曼意义上的舞台,而是旅游时空下历史、传统、文化展演的抽象或具体的“舞台”[42]。虽然麦坎内尔之后的真实性研究早就突破“舞台真实”理论的桎梏,但“舞台真实”似乎却超越了令人反感的策略性展演印象,反而作为文化呈现的重要方式在民族旅游、遗产旅游、古镇旅游等文化旅游模式中约定俗成。作为旅游互动的一种结果,“舞台真实”对族群性的影响效应激起国外人类学者的兴趣,对此有两种主流观点:其一是“舞台真实”与族群文化的真实性存在差距,它歪曲、弱化、消解了族群性,从而弱化了族群认同;其二是“舞台真实”复苏、复兴、再创造了族群文化,它重新激起成员对我群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从而强化了族群认同。但有学者将“舞台真实”作为旅游文化的一种形式,认为“舞台真实”起到了保护活着的原生文化的作用,它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旅游者有可能伤害原生文化的旅游行为。
4 结束语
自范登伯格将“主-客”关系视为一种族群关系类型以来,旅游族群性研究断续至今,但多为案例研究,即便成书出版,亦是论文结集,鲜有专着或论述性文章。这暴露出旅游族群性缺乏相对系统的研究。皮卡德、伍德二人则指出早期的旅游族群认同研究忽视了族群认同的政治源泉,特别是国家政策和国家资源的使用权,因为在第三、第四世界社会里,这些东西尤为重要。一方面,国家致力于培养新的国族认同,缓解多元族群与现代国家之间的矛盾张力;另一方面,当地人发现其必须在国家控制下的竞技场上就族群认同进行商榷,因此民族旅游、民族博物馆、主题公园的增生以及族群器物的商品化等使族群认同与国族认同的并存情形更趋复杂。虽然民族主义、政治利益与地方旅游促销之间关系密切,但国家精英主要是被旅游的经济效益所吸引。然而,民族旅游对族群多样性的促销把一些复杂问题摆在国家面前:(1)旅游促销中被挑选出来象征族群界限的族群标志是怎样与国族整合、国家认同相协调的;(2)民族旅游是将族群更紧地与国家政治经济体系绑在一起,还是强化了族群的分裂感且潜在地为之提供了抵制整合的资源;(3)地方、地区与国家层面的族际关系会受到怎样的影响[43]。此类问题应成为研究者针对现代民族-国家予以关注的方向。
至于旅游族群性的走势,如伍德所言,首先是族群认同日益“去分化”(dedifferentiated),族群认同将与其他生活场域交织在一起,在和其他群体或机构的互动、反应过程中被普遍性建构;其次是旅游与其他社会文化活动的边界的消解,即社会生活领域的旅游化与旅游领域的社会化[2]。在这样的旅游话语与体验模式下的族群性将会如何演变?目前可见的是,旅游不再外在于族群文化,在族群性呈现与建构过程中,旅游文化将内化为族群文化。伍德于1998年的预言正变成现实,这是旅游世界与生活世界边界交融、互疏互通的结果,也是研究者所面临的旅游族群性现状。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Li Xiangfu. Some concepts about the racial group research andbasic theory [J]. Journal of Guangxi University forNationalities, 2000, (5): 17-20. [李祥福. 族群性研究的相关概念与基本理论[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2000, (5): 17-20.]
[2] Wood R. Touristic ethnicity: A brief itinerary [J]. Ethnic andRacial Studies, 1998, 21(2): 218-241.
[3] Graburn N. Introduction[A]. //: Graburn N. Ethnic and TouristArts: Cultural Expressions from the Fourth World[C].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23-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