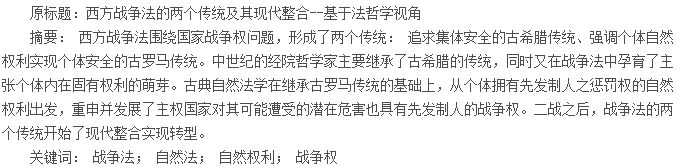
围绕国家战争权问题,西方战争法形成了两个传统:发源于古希腊文化追求城邦集体安全的战争法传统、发源于古罗马文化强调个体自然权利实现个体安全的战争法传统。在中世纪神学时代,经院哲学家出于对基督徒和异教徒之间关系的思考,更多继承了古希腊的传统,用自然法思想对正义战争的标准重新进行阐释。从16世纪开始,随着欧洲国家陆上冲突和海权争夺的日益加剧,以及肇端于18世纪后半期的工业革命的影响,崇尚个人主义,从个体自然权利出发、主张先发制人之国家战争权的战争法理论逐渐丰富成熟。但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祸,使得自20世纪开始,在对既有战争法则反思的基础上,战争法的两个传统逐渐汇合,并开始现代转型。
一、追求城邦集体安全的战争法传统
追求城邦集体安全的战争法传统,认为对于公民参与的军事行动应保持警惕,否定以战争作为实现个体安全的手段;反对立法家们以战争和克敌制胜作为整个政治体系的目的,强调不能将关于和平的立法变成战争的工具,相反,关于战争的法律则一定是实现和平的工具。
(一)古希腊的战争法传统
追求城邦集体安全的战争法传统,起源于古希腊文化,它有三个鲜明的特点:
1.否定以战争作为实现个体安全的手段
柏拉图在《法律篇》中,以雅典陌生人对克里尼亚斯的评说,反对一个后来在西方法哲学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观点,即"人类处在每个人对每个人的公共战争状态".他认为"正义是强者的权利"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最大的善既不是对外战争也不是内战,而是人们之间的和平与善意。[1]
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因为各个私人和公众社会的善德是相同的,城邦向外扩张的政策孕育着对于内政而言的重大隐患,即任何公民如果受到以暴力欺凌它国的教导,则一旦有机会,公民同样也有可能用暴力来强取本邦的政权,由此,城邦就有可能陷入到专制的暴政之中。[2](P397)
2.实现和平的方式依靠理性和法治的结合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在讨论城邦的优良政体时,都主张城邦不应主要是为战争而设计。"立法家对于他们所订立的军事法制,务必以求取闲暇与和平为战争的终极目的。"[2](P398)和平与善意,依靠理性和法治的结合来实现。理性本质上是追求一种秩序化的世界,在古希腊哲学家看来,人类用理性控制激情和欲望,于是,社会所有成员能够就良好生活的本质和取得良好生活的方式达成共识,这也是法律得以形成和被遵守的原因。对于"国家和公民,一个最好的人,他与其在奥林匹克竞技会上或其他任何战争与和平的竞赛中获得胜利,倒不如以他对本国法律的尊重所取得的荣誉来击败每一个人。这种荣誉是因为他比其他任何人更出色地终身尊重法律而取得的。"[1](P138)3.关于战争合法性的两个主张。
亚里士多德说:"尚武教育的目的应该是这样:第一,保护自己,免得被人所奴役;第二,取得领导的地位,但这种领导绝对不企图树立普遍奴役的体系而只应以维持受领导者的利益为职志;第三,对于自然禀赋原来有奴性的人们,才可凭武力为之主宰。"[2](P398)在古希腊文化中,战争的合法性为:①从城邦的优良政体出发,为求自保的自卫战争是合法的。所谓自卫战争,是指当城邦遭受到实质性的攻击,就可以用一些适度和相称的形式进行报复。②与城邦秩序的建立相适应,从人类本性的政治性出发,为劣等人应受统治的原则而战在道德上是正当的,这是基于理性的善德(理性化的世界同样存在着等级),因此,构建伦理秩序是发动战争的主要理由。
(二)中世纪的自然法思想中的战争法传统
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对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法律思考,是从上帝永恒法和世俗法律(源于自然道理的人类法)出发,来讨论基督徒与异教徒的关系问题,而这一问题不但贯穿至亨廷顿所说现代社会"文明的冲突",更在法律上涉及基督徒与异教徒战争的合法性、以及由于这种战争带来对被征服的异教徒是否应该定位为自然奴隶,教皇的世界统治权、以及由于教皇的授权导致欧洲君主的统治权(包括海洋管辖权的发生)等问题。
经院哲学家认可基督徒为了其所在城市的利益而使用暴力,只要这种暴力与任何性质的私利无关,而是为了和平以及与人类社会的法律相一致的事物。为此,经院哲学家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及始于阿奎那的多明我会传统,都沿着古希腊的传统:①肯定对战争问题应该极为慎重,主张不能以宽泛的条件来随意为战争辩护;②罗马教皇没有理由声称对异教徒拥有特殊权力,不应该用暴力使不信仰者转变观念,征服美洲是不合法的;③重新解读(甚至质疑)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奴隶思想,认为在征服自然奴隶之前必须先符合正义战争的传统标准。[3]
在托马斯·阿奎那看来,人们自然倾向的事情,必须认为是善,并且必须视为是自然法的一部分。正义战争的传统标准源自于两个因素:一是人具有法律必须予以承认的、自我保护的自然本能;二是人希望过社会生活、具有避免伤害与之一起生活的人的自然倾向。"如果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由于不能赔偿所造成的损害或不能归还非法占有的东西而应当受到惩罚时,那些为某种损害复仇的战争一般叫做正义的战争。……如果战争不是为了贪婪或出于残暴,而是从抑恶助善的和平愿望出发而掀起的,那么对于上帝的真正的信徒来说,即使战争也是和平的。"[4](P135-136)因此,出于自卫而确保安全、不随意剥夺别人的财产、不伤害无辜、不违反其他对所有人都公正和便利的法律而发生的战争,被认为是正当的。
由上可知,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对古希腊的传统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因为在经院哲学家主张的"和平以及与人类社会的法律相一致的事物"之中,既有出于自然法倡导的追求集体安全、实现人类共同利益的考虑,又孕育了主张个体内在固有权利的萌芽,当然,在经院哲学家看来,个体内在固有权利是服从于人类共同体的整体安全和利益的,这是评价战争正义与否的标准所在。也正因为此,我们认为古希腊文化与经院哲学的战争法传统一脉相承。
但是,以城邦集体安全为出发点的战争法传统,在17世纪之后的战争法理论中是遭受冷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