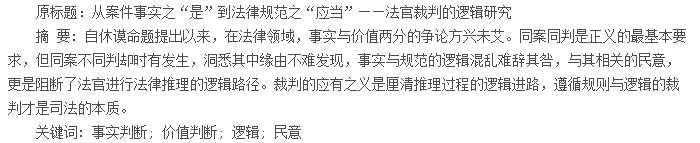
“大陆法系法律推理的基本模式,是以认定的案件事实和相关的法律规范为前提,根据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合乎逻辑地演绎出法律效果的演绎论证模式。”司法中法官进行法律推理,小前提是案件事实,大前提则是法律规范,进行法律解释和事实认定的过程中必须进行价值判断,究竟应该用价值裁剪事实以得出结论? 还是该综观事实后得出价值判断以解决个案纷争? 规范具体诉讼流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大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第六条,《民事诉讼法》第七条,《行政诉讼法》第四条)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法条要求,则明确表明了: 价值判断当在事实判断之后! 事实判断是一种描述性判断,事实判断之间的关系是科学逻辑的研究对象,只关乎真假,与此相应,价值判断是一种规范性判断,规范判断之间的关系则是规范逻辑(也可称为价值逻辑) 的研究对象,仅关涉是非。两者存在着泾渭分明的差别,令人遗憾的是,在真假和是非之间,我们并没有形成西方那种价值与事实两分思维方式,反倒大多数时候都是用简单的价值判断取代了事实判断,而这种思维方式偏离了司法裁判的应有逻辑,也是导致冤假错案的重要因素。
一、法官裁判的逻辑———科学与规范
自 18 世纪休谟命题提出以来,对于事实与价值、实然与应然关系的讨论一直方兴未艾。本世纪初,关于刑法中犯罪构成理论的争论,则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讨论推向了高潮,一些学者就指出传统的犯罪构成四要件说模糊了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而主张犯罪构成三阶层说。“主流的观点强调从事实判断不能推出价值判断”。[2]同样的,从价值判断也不能推出事实判断。
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区别,正因为其分属于科学逻辑与规范逻辑的范畴而得以体现。科学逻辑是关涉真假的逻辑命题,也是理性能够把握的逻辑方式,如我们为什么知道“铁是导电的呢?”,这是因为“金属都是导电的,而铁是金属”,所以任何人在面对这样的基本逻辑推理时,都会得出唯一且相同的结论。那我们该怎么解释,当法官面对同一个个案事实和同一个法律规范体系,不同的法官会得出迥然有别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呢? 这其中的缘由也是导致同案不同判的逻辑内因。这是因为以上的科学推理的大小前提都是事实判断,其中并无价值判断的适用余地,而事实判断的大小前提之间具有直接的同一性与递进性关系; 而法律推理的小前提是事实判断,而大前提则是价值判断,价值判断是情感在主导,价值判断之间不具有同一性更没有递进关系,价值判断是个因人而异的主观性裁量,在这种兼具事实与价值的推理中,不同的人很难得出同一性结论,这也就是同案不同判的最基本逻辑内因。
在法律推理过程中,要想判决结论得到最大程度的认同和接受,不仅法官做出的事实认定应该具有确定性与客观性,而且法官所援引的法律规范体系中的具体法条和进行法律解释背后的价值裁量也应该得到其他人的认同,至少不该让他人觉得是武断或恣意的,因此,法律推理的过程就显得复杂的多,它混合了事实判断和价值考量,就很难会像科学推理那样具有稳定的确定性与同一性。
法官裁判不是任意的,而应是按照一定的推理规则从相关前提中合乎逻辑地推导出来的,法官的目光需要在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之间往返流转,依照人的基本思维方式,对从所有能够合理解释事实的法律规范的事实构成要件中优先选择一个假设来进行推论证成,所有法律推理赖以存在的大前提(法律规范) 与小前提(案件事实) 都是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综合体,法官所认定的涵摄到法律规范事实构成要件的个案事实应该是相互符合的,而且涵摄到其下的规范条文的解释还要与法律规范所蕴含的整体法秩序价值相吻合,遵循这样的逻辑进路,法律推理的大、小前提之间就具有了同一性———以整体法秩序价值为归一。事实要件的相互符合和价值判断的相互统一,就在大、小前提之间建立了完整的、充分的传递关系,因此,就可以逻辑自洽地推导出法效果的判决结论。
在法官进行规范判断和事实认定过程中,事实判断的表述总是显明确定的,而法律规范的整体价值和法官个人对案件的价值判断却是无法直接看到的,总是潜在于文字表述的背后,有时甚至隐含不露。在当前法院判决书千篇一律且缺乏说理与逻辑论证过程的背景下,我们很难从直观上看出判决是从案件事实之“是”推导出当事人之“应当”,法官裁判的逻辑路径也隐而不彰,因此,如何判定蕴含于法律规范的价值判断和对案件事实所作出的个案价值判断是否具有同一性,就成为研究裁判逻辑的重要任务,法官在证成判决结论合法有效的时候,也必须遵循两条逻辑路径的同时满足。当法官面对具体个案时,怎样处理案件事实,在案件事实与规范构成要件之间如何勾连,这就需要法官的“前理解”(对整体法秩序的领悟) 了,也即所谓的“价值剪裁事实”,当然这种截取不是恣意的,它必须以整体法秩序为媒介,当法官面对个案事实,他需要考虑所认定的事实是否符合规范的事实构成要件,在相符合的情况下得出的法效果,是否和整体法秩序价值相符合,如果答案时肯定的,那么这个推理过程也便是合法有效的。法官的“前理解”是价值评价的基础,也是“由案件事实判断推出规范判断的逻辑桥梁,它从具体个案事实涵摄到法律规范具体法律条文之下以得出规范性判断(即判决结果) 的逻辑中介,也就完成了从个案事实之“是”到法律规范之“应当”的逻辑过渡。在这逻辑过渡中对于法律规范背后所蕴含的价值评价就是指导法官进行推理的那只“看不见的手”,法官对所认定的个案事实所作的价值评价不同,最后得出的判决结果也就是不同的。这也就是同案不同判的原因之所在,也是法律推理的内在逻辑机制。“这种推理机制对分析法律推理和辨证法律推理同样适用,只不过价值评价在分析法律推理中可以隐之于心,但在辨证法律推理中必须明确地表示出来。”[3]在法律推理过程中,假设没有法官的个案评价,其中的案件事实就无法转化为具有法律意义的具体条文构成要件中的法律事实,也就无法找到与之相对应的法律规范体系,就无法确定法律推理的大、小前提之间在事实构成和价值要素上是否具有同一性和可评价性,也无法对案件事实进行规范裁判,对个案的事实定性和裁量也无法进行。
因此,价值判断是勾连个案事实之“是”与当事人之“应当”的逻辑桥梁。在司法裁判中,科学逻辑的事实认定与规范逻辑的价值判断总是相伴而生,相随而形。
二、法官裁判的扭曲———民意躁动
近年来,民意审判日益盛行并得到了大众的好评,但是从法治的本意上看,民意审判对法治的破坏远远超过了它本有的益处,民意审判也是导致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纠缠不清的主要原因。中文“民意”一词可以用来表达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公众意见(public opinion) ”(民众意见或舆论) 和“人民意志(the will of people) ”。[4]支持民意审判的学者,大都认为法律代表人民的意志,所以审判考量体现人民意志的公意也无可厚非,用三段论表述就是: 大前提为“法律是民意的体现,审判适用法律。所以审判也应是民意的体现”,但是这里明显存在着中词不一的逻辑混论,代表人民意志的立法公意和审判的公意是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的,在三段论推理中,中词不一得出的结论就必然为假! 我们把法律是公意的体现称为“立法民意”,而审判中的公意称为“司法民意”,这里的“立法民意”和“司法民意”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它们的区别在于: 第一,主体范围不同。立法民意的主体是全体人民(应然意义上该如此) ; 司法民意的主体则可能仅仅是人民的一小部分,这部分的民意有时甚至是很小的一部分,构成这种民意的主体主要有关注争论个案的网民、相关媒体人员和不明真相的群众。这种司法民意无法完全体现全体人民的意志; 第二,内容不同。
立法民意往往是规范性内容的表达,即使不具有规范性,也是可以反复适用的,具有规范的抽象性特征,然而,司法民意却截然相反,当争论个案出现时,反应出来的司法民意往往是一种情绪性的表达,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且仅仅是适用于个案,缺乏规范性特征; 第三,表现形式不同。立法民意通常是通过法定的机关进行收集,具有法定的表现形式,且具有相对的确定性,而司法民意没有法定的表现形式,往往跟随争论个案而应时出现,具有恣意性; 第四,形成方式不同。立法中民意的形成一般都需要经过严格的程序控制,具有一定的程式,而司法民意则是在自发且无序中产生的,具有很强的暂时性与随意性。
司法民意是一种典型的群体意识,与立法中的人民意志明显不同,法国学者勒庞对民意进行了深入研究,他指出在群体中形成的大众心理具有很多缺陷,勒庞认为: “群体是冲动、多变与急躁的,群体易受暗示易轻信,群体的情绪夸张而单纯,群体偏执而保守,群体不可能是道德的。”[5]群体的这些特性决定了在群体中形成的民意特点,尽管群体意识中也有理性,但是庞大的群体很难进行逻辑推理,也就无法分辨真伪,群体中的个人很易受周围的人影响,往往每个人的判断是情绪化的,无法进行理性归纳,因此,这种大众民意具有固有的缺陷,它对司法的副作用远大于其正面影响。因此,民意的情感性与规范的法律性之间存在无法弥补的张力。
民众的意志已经通过定罪量刑所依据的实体和程序得到体现,如果再强调涉案民意,从逻辑上来说实际上就是通过民众的意见来否定民众的意志。[6]如果允许司法民意随意干涉审判,很可能导致通过立法民意制定的法律被司法民意所取代,这种情况是法治社会所不能容许的,那么我们该怎么对待司法民意呢? 或者司法民意的价值在哪里? 一般都认为,当法官面对个案时,在事实认定的过程中,民意的影响几乎不存在。只有在运用规范进行价值判断的时候,民意才会发挥其作用,因为当法官面对具体个案时,与共是认定事实之后就进行规范评价,毋宁是“目光之交互流转”于规范之构成要件及案件事实间。[7]因此,事实认定与规范评价总是包含着一定的价值因素。相较于刑法适用过程的较少民意参与,民事诉讼活动中民意则体现较多,民法基本原则诸如公序良俗、诚实信用等都内涵了较多的民意参与其中。民意参与诉讼并对司法过程与判决结果产生深刻影响的当属引起学界广泛讨论的 2001 年四川的泸州二奶继承案。在本案中,法官肆意动用民意,歪曲解释个案事实,当事法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条“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基本原则,否定了案件当事人的遗嘱效力,认为被继承人的遗嘱虽然系合法有效,且真实的意思表示,但却是一种严重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和法律基本原则的行为,因此遗嘱该属无效,判定了二奶败诉。在本案中,法官将民意纳入价值考量之中,这样的判决和民意的主要倾向基本是相同的,大众民意也基本是左右了法院的判决,在民事司法活动中,这种民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可接受性,但是在关涉人的生命及自由的刑事司法中,倘若躁动的民意左右了判决,那种结果是无法想象了,法治的基本程序将荡然无存,法院的判决也将沦为民意的狂欢,这对法治国家的建设无异于饮鸩止渴。
司法中所展现的民意具有固有的缺陷,它多元且混乱、易受操纵、易变动且无理性,这种非理性的民意背离了司法的应有之义———理性地追求公平正义。虽然有些民意在时下看似得到了公平正义,但是对于长远的法治建设却是透支的,它摧毁了司法的理性之基。有的学者认为民意审判具有息诉止争的效果,这是以后总短期的实用主义评判,从长远来看,民意审判于法治的建立无益,反而会破坏法治之基———规则之治,因为民意审判总会以牺牲一定的规则为代价。民意也造成了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的脱节,民意过多地参与了本只属于法官的价值判断,阻断了法官的专业化与职业化的思维方式,必定带来逻辑的混乱,结果是裁判的扭曲,导致更多的不公。
三、法官裁判的本质———规范逻辑
法律固有的滞后性众所周知,法律规范制定以后就必定会与社会需求形成张力,法律整体上是人的一种意思表达,法官在司法过程中,也总会遇到一些难以用现存的法条解决的疑难案件,这时候就需要法官的价值判断,实质上,自由裁量权就是法官进行价值判断的法定权力,但是,这种价值判断不能是恣意的更不能是专断的,它应该秉持一定的法律价值,正义最优,效率其次,秩序第三,当然在一定情况下,正义需要让位于秩序,因为秩序是人类的最基本需求,没有最基本的秩序,正义就是虚妄的。当法官面对法律漏洞或疑难案件时,法官裁判的两条逻辑进路中的其中一个已被阻断,法官该怎样处理呢?
我们认为尽管没有可资援引的法律规范,甚或案件事实不明难以查清,法官在进行法律推理时也要遵循最基本的司法程序,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结合整体法秩序价值并运用司法经验,创造性地寻找相似法律规范,最大可能地追求案件真相,真正无法做到查明案情的,按疑罪从无处理,从而得出理性的价值判断。
法律作为一种规范的存在,内在逻辑就是规范逻辑,它无关乎真假,只评价罪与非罪。司法作为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理应遵循其内在的程序规范和逻辑进路,法治的本质是规则之治,司法更应是理性中立地解决社会纠纷的最佳途径,躁动民意扭曲了司法固有的理性中立,法官裁判理应合乎逻辑理性地展开。法治的基本要求是权力的行使以法定为限,“法无规定不可为”,就审判权来说,它必须遵守法律,当以规则为裁判的基准。法官裁判只能“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模糊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逻辑,或者简单地用价值判断替代了个案事实,将会玷污司法的纯洁,在司法过程中,法律应是排他性的权威,逻辑是推理的基本工具,让法官的裁判在理性清晰地沿着逻辑进行,厘清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同时避免躁动的民意扭曲,也就是我们所追求的最优化司法———当以理性的规则化治理取代非理性的民意狂欢。
参考文献:
[1]麦考密克,魏因贝格尔. 制度法论[M]. 周叶谦,译.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53.
[2]刘笑敢.“反向格义”与中国哲学研究的困境———以老子之道的诠释为例[J]. 思想史研究,2006(2) .
[3]张继成. 从案件事实之“是”到当事人之“应当”———法律推理机制及其正当理由的逻辑研究[J]. 法学研究,2003(1) .
[4]周永坤. 民意审判与审判元规则[J]. 法学,2009(8) .
[5]古斯塔夫勒庞. 乌合之众[M]. 冯克利,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52.
[6]孙万怀. 论民意在刑事司法中的解构[J]. 中外法学,2011(1) .
[7]卡尔拉伦茨. 法学方法论[M]. 陈爱娥,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3: 7.





